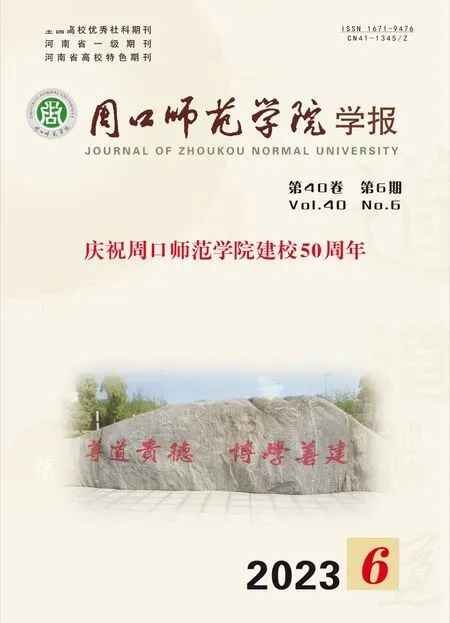宋代宴会词的演绎艺术与文化传播功能
纪昌兰
(信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宴会词以宴饮中用于娱宾遣兴的词为独特属性。宋代社会文化繁兴,赋诗填词作为一种常见的文艺活动日益盛行,众多创作场景中尤以宴饮聚会颇为典型。这一时期世人宴会中赋诗填词十分普遍,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之间更是蔚然成风。宴会所见词曲创作,由于场合的需求而被赋予了极具特色的艺术化属性,而词曲本身又深刻反映着士人的娱乐心态和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蕴含着独特的时代文化审美趣味。目前学界对于宴会词已有所关注,大多从宏观层面予以把握,而针对宴会词具体创作情境、独特演绎效果等艺术层面的关注略显不足。本文拟就宴饮这一特殊环境和需求对词曲创作及其演绎艺术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观察蕴于其中的时代文化审美艺术,展示宋人在樽俎流传之际如何将生活艺术化,探讨宴会词之传唱对于社会文化风尚所产生的影响。
一、宋代宴会词的创作与传唱
(一)宴会词的创作
赋诗填词是中国古代社会诗词兴盛以来宴饮中常见的活动内容,也是颇受欢迎的文艺娱乐形式,唐时人们便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唐人燕集“必赋诗,推一人擅场”[1]41。唐末军阀罗绍威“每宴会,与宾优赋诗”[2]725。五代时期著名文人王仁裕“暮春与门生五六人登繁台,饮酒题诗,抵夜方散”[3]6。宋人沿袭前代饮宴习俗,把酒言欢之余赋诗填词日渐成为一种风尚,文人士大夫之间更是蔚然成风。仁宗朝臣杨安国“每会集学官饮酒,必诵诗书首句以劝侑举杯”[4]878。北宋末年朝奉郎中丘舜诸女“皆能文词,每兄弟内集,必联咏为乐”[1]416,诸如此类现象不胜枚举。与之相应,这一时期宴席活动中通常伴有歌曲以佐酒。宋代的歌曲实际上就是词,也叫近体乐府或者长短句。这种体裁肇始于唐朝中期,到晚唐及五代时期逐渐流行,宋朝为鼎盛时期[5]50-55。所谓“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即是对此类现象的真实描述。
宴饮中伴随的乐舞之类娱乐活动为词的传播与歌唱提供了相当优越的环境。词,作为一种配乐而歌唱的抒情诗体,其兴起与音乐有着密切联系,产生可以追溯到隋唐的“新声”(燕乐)或更早的汉魏乐府[6]。序言早在唐代中后期,宴会词就已经开启了歌唱的传播模式。景龙四年(710)春,唐中宗宴于桃花园,学士李峤等各献桃花诗,宫女歌之“辞既清婉,歌復绝妙”[7]1329。中唐以后已然形成“《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8]85的繁盛景象。时代发展到宋朝,传唱的歌曲与前代相比词调上已经有很大不同[9]7-8。宋人胡仔曾经有云“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1]317,指出唐代曲调到宋朝逐渐被新曲所替代的事实。即使如此,宴饮中创作并歌唱词曲的做法却是一脉相承,诸如“一曲新词酒一杯”[10]2、“殷勤更唱新词”[10]16之类现象在宋朝已经相当普遍,所谓“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宴饮对于歌曲娱乐的需求催生了大量新作,日益成为宋人诗词创作与传播的一大潜在驱动力。宴饮中传唱的歌曲有清唱、和乐而唱两种基本类型。无音乐演奏的清唱一般会和以牙板之类便于把握节拍,如“花前月底,举杯清唱,合以紫箫,节以红牙,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信可乐也”[11]151,意在享受其声音之清丽可听。但所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12]253,完全的清唱仅仅适合三五宾朋之间聊作清欢,既无法调动宴席整体气氛,也失去了众人把酒言欢的宴乐欢闹情趣。因而宴会常见的歌曲一般会伴有音乐,甚至是佐以歌舞助兴。席间用以传唱的歌曲从创作形式上来看主要包括即席作曲和提前预备两种。
首先,即席作曲。宴饮中即席创作歌曲既是对创作者才思的一种考验,又是向众人展示才华的良好途径,因而为文人士大夫津津乐道且颇为自矜的一件雅玩趣事。宋代社会世人把酒言欢之际即席作曲相当普遍。东坡曾在上巳日饮宴中即席填写《满江红》词一阕,“妓歌之,坐席欢甚”[13]201。南渡初,会稽一带士子陆子逸饮宴即席作《瑞鹤仙》,有“脸霞红印枕”之句,“一时盛传,逮今为雅唱”[14]63。著名词人张孝祥任职京口期间,多景楼落成大宴合乐,酒酣之际“赋词,命妓合唱甚欢”[15]209。周密在《瑞鹤仙》自序中指出与友人饮宴“初筵,翁俾余赋词,主宾皆赏音。酒方行,寄闲出家姬侑尊,所歌则余所赋也”[16]2194,颇得娱宾遣兴之效果,终席众人为此尽醉而归。以上种种,皆是即席而作的真实写照。
其次,备歌而宴。宋代社会歌曲作为调节宴会气氛、引导宴会进程的重要活动内容,随着时代发展已经相当普遍。为使宴会顺利进行,宴饮中的歌曲传唱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预先准备者。如北宋真宗著名朝臣寇准早春宴客,便自撰乐府词“俾工歌之”[17]44。南宋词人仲并也曾在词序中坦言:“《好事近》宴客七首,时留平江,俾侍儿歌以侑觞。”[16]1822有七首预留曲目,都属于为宴会歌唱而提前准备的。宋末著名词人吴文英曾道:“次吴江小泊,夜饮僧窗惜别,邦人赵簿携小妓侑尊,连歌数阕,皆清真词。”[18]126-127此处的清真词即为周邦彦所作词集,词风清婉,适合樽俎流传之际伴乐传唱,是当时宴席间侑觞佐欢的常见预留曲目之一。关于宴会中用以传唱的歌曲,清人宋翔凤有过一段颇为精彩的评价,其中有言:“词实诗之余,遂名曰诗余。其分小令、中调、长调者,以当筵作伎,以字之多少,分调之长短,以应时刻之久暂。”在论及南宋著名词集《草堂诗余》时又进一步强调指出:
《草堂》一集,盖以徵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19]1483。
以上宋翔凤根据《草堂诗余》所收录词曲的大致特点,推测该作品属于“徵歌而设”,分题分场景以“随时即景,歌以娱客”,其中所见词语“间与集本不同”,总体上以便于歌唱为突出特色,因此“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具有类似于歌谱的传唱和参考功能,是备歌而宴的典型。提前预备者大多是当时社会席间颇为流行的曲子,一般情况下客至信手拈来伴乐歌唱,以达到娱宾遣兴之良好饮宴效果,蕴含浓郁的娱乐功能。
(二)宴会词的传唱
唐宋词有两个组成部分,词(歌词)、乐(乐调)[20]378,词除去本身所赋予的文学化特征外,最具特色之处在于樽俎交错之际,丝竹管弦相伴之下的吟哦传唱,在宴会中扮演着歌词的角色。关于词曲一类用于传唱者,宋人陈应行就曾指出:“自古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入韵之首。”[2]161明确了诸如诗颂之类作品在宴会上佐以乐器、歌讴欢唱的娱宾遣兴之功能,同时强调了宴乐与情境适宜的协调之美。因此有学者就认为,词的产生乃至盛行与妓乐唇齿相依,自唐代温庭筠以来,填词的主要动机是为歌妓歌唱以侑觞、佐欢。词之应歌是词坛的主旋律[21]206。
值得注意的是,词之所以具有歌曲的传唱效果和功能,对韵律及歌咏内容甚至演绎艺术都有一定的严格要求。对此,宋人有着不同见解。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指出:“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22]3著名词人张炎同样认为词“当以可歌者为工,虽有小疵,亦庶几耳”[23]256。二者都注重强调词的歌唱旋律,演绎效果之外对于词作本身的质量要求却降到了其次。
歌唱谱曲要求作者对歌词韵律和吟唱内容有十分准确的掌控,词曲写作必须符合歌曲伴唱要求才能广泛流传。晏几道的《小山词》就是宴乐成功的典型。词集自序中有言:“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蘋、云,工以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8]38坦言该词集完全是清讴娱客之作。因而后人评价其词“字字娉娉袅袅,如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蘋、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24]122,对于晏几道词曲的演绎效果有着相当高的赞誉。宋代诸如晏几道之类善于作词谱曲的词人还有很多。柳永就以善为歌辞而著称于世,当时“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以至于形成“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25]49之歌吹盛况。柳永之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字少游)亦以擅长作乐府歌词而闻名,其词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25]50。范仲淹之侄孙范周“少负不羁之才,工于诗词”,颇受士林推崇。元宵节期间作《宝鼎现》一词,大受欢迎,“播于天下,每遇灯夕,诸郡皆歌之”[26]110,足以说明其传播之广。仁宗朝苏州人吴感以文才知名,曾作《折红梅》词,“传播人口,春日郡宴,必使倡人歌之”[26]14,诸多词句令人称赏不绝于口。合乎韵律要求的词曲佳作辅以丝竹管弦,备受欢迎,历久不衰。南宋文人张世南指出刘过《贺新郎》词“至今天下与禁中皆歌之”[27]5。词人吴用章去世后其“词盛行于时,不惟伶工歌妓以为首唱,士大夫风流文雅者酒酣兴发辄歌之”,甚至到了南宋末咸淳年间“永嘉戏曲出,泼少年作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然州里遗老犹歌用章词不置也”[28]185-186,足见其受欢迎程度之深,流传之广。关于歌曲传播及当时著名词人的词曲创作,李清照给予了细致评价,认为“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针对宋代则指出: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1]254。
在李清照看来,能够称为绝妙好歌词者不仅要求歌词五音、五声、六律的协调,词曲的清浊轻重也要严格把握。在音律上属于押仄声韵者“押上声则协”,而“押入声则不可歌矣”。对宋初柳永到中期的秦观再到晏几道等著名歌词作家一一拣择,直言不讳各家词作之弊端,以其观之则无一堪称完美。对于这种略带挑剔的严苛评价,宋人胡仔直言不讳地指出,“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1]255,给予了相当猛烈的回击,认为李清照评判诸人揭其短处实属自不量力之举,言语间暗含对于北宋诸位词曲作家所取得成就的一种肯定。对于李清照以上之言论,现代著名文史学家缪钺先生在《论李易安词》中评品道“此非好为大言,以自矜重”,“盖易安孤秀奇芬,卓有见地,故掎摭利病,不稍假借,虽生诸人之后,不肯模拟任何一家”[29]57,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回护。事实上,李清照本人所作词曲在传唱过程中也时有争议。宋理宗时,太子设宴赏芙蓉、木犀,宴席上“韶部头陈盼儿捧牙板歌‘寻寻觅’一句”,理宗听后,大为不悦,当即表示“愁闷之词,非所宜听”[30]4。从理宗对易安歌词传唱的效果反映来看,在以上宴饮欢快场合歌讴“寻寻觅觅”之类风格韵律伤怀歌曲,确实显得“非宜所听”。因此,不同心境和氛围对于词曲的要求和传唱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歌词的长短也会影响其传播状况。北宋词人晁元礼《绿头鸭》一词“殊清婉”,但樽俎间歌喉“以其篇长惮唱,故湮没无闻焉”[1]321。词曲虽好,因篇章过长受到严重影响,最终被淘汰。
在宋代,东坡属于名副其实的文化名人,而东坡词的传唱功能和效果在当时乃至后世都颇具争议。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饮酒、唱曲也”。《苕溪渔隐丛话》转引《遯斋闲览》云:“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1]284,认为东坡词多不入腔,总体上不太适合进行歌唱。陆游则对“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之说充满了些许质疑,认为东坡“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31]66,虽稍有袒护之言辞,但言外之意亦是东坡词过于豪放旷达而稍显不宜,事实却不尽相同。东坡守定州期间,宴饮中即席作《戚氏词》,“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而“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问它词,亦不容别进一语”[32]500。在徐州时,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追问逻卒始末,其人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33]21,都是东坡词可歌可唱的实例。另外,宋人胡仔甚至指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东坡所作词曲可谓大受欢迎。直到南宋绍兴中,曾宏父守黄州,有双鬟小颦,颇慧黠,宏父令诵东坡《赤壁》前后二赋,“客至代讴,人多称之”[34]216。以上种种,从实践来看东坡词并非如世人所传不适合歌唱,而是与陆游所说“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有密切关系。东坡本人也曾就自己的词与柳永词进行对比,并询问他人两者之区别。其人回答:“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7]1363以此观之,或许更容易理解东坡词曲风格上的独特性。有学者根据宋词的总体发展特征将其分为三个段落,即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各个时段词都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东坡时代,词的特征凸显出来,内容复杂,词人个性也日益彰显。一改前期“歌者的词”之平民的文学特色,词曲不再寄希望于歌姬弹唱,而是用一种新的诗体来作“新体诗”,大开风气。而东坡对于词的改革是多方面的,包括提高词品,扩大词境,变更词调等,风格趋于豪放[35]462-465,[36],所谓“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31]66。或许正与这种时代特色相符合,词曲并非一味迎合乐工歌姬的声口,具有全新的境界。
二、宋代宴会词演绎的艺术要求
宋代的歌曲,就其艺术形式而言包括叫声、嘌唱、小唱、唱赚、鼓子词五种[37]302-310。如嘌唱,为“上鼓面唱令曲小词”,此种歌唱“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宅院往往有之”[38]7。南宋时期杭州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更有小唱、唱叫、执板、慢曲、曲破,“大率轻起重杀,正谓之‘浅斟低唱’”[39]192。基于宴会场合的特殊性,对于词曲演绎效果的艺术化要求相较而言更显严苛。一般而言,宴会中歌唱的词曲具有娱宾遣兴、佐欢侑觞、调动宴会气氛等独特的演绎功能和场景需求,是当时宴会中一种必要的娱乐方式,有时甚至具有调节宴会进程的重要作用。宋人对宴会歌曲的演绎有着相当独特的艺术要求:
第一,歌者婉媚。宴会中歌吹唱作除了对词曲本身有所要求之外,对于歌唱者同样颇为挑剔,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40]2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早在唐代,李白曾于《听歌鹧鸪辞》序中回忆陕州夜宴之场景,特意提到席间有妓人歌鹧鸪词,“词调清怨,往往在耳”,盛赞其“响转碧霄云驻影,曲终清漏月沈晖”[41]2755。在另外一首诗中同样对“笛声喧沔鄂,歌曲上云霄”[41]821的饮宴歌吹场景感叹不已,颇有意犹未绝之意。五代时期韩熙载“后房蓄声妓,皆天下妙绝,弹丝吹竹、清歌艳舞之观,所以娱侑宾客者,皆曲臻其极”[42]244,就已经十分注重饮宴席畔歌者演绎的娱宾效果了。相比之下,宋代社会饮宴中人们对于歌者的要求有过之而无不及。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8]27,并且“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突出“朱唇皓齿”即佳人进行歌唱演绎才能充分彰显词曲的“要妙之声”。若非如此,便不能达到“妙词佳曲,啭出新声音能断续”[43]439的良好歌唱效果和艺术特色。如唱令曲小词要求歌者声音软美,与叫果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也”[39]192。这种欣赏品味的变化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即是对于歌者本身的独特要求。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时至宋代,世人的审美意趣却有着相当迥异的标准和倾向,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做歌词,亦尚婉媚”[8]27,总体上要求歌唱者声音柔美婉媚,审美喜好和欣赏品味可见一斑,表现在实际演绎中即对“女音”情有独钟。政和年间,文人李方叔听闻一老翁善歌唱,戏作《品令》一阕,有言:“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对擅长歌唱的老翁未闻其声却有“怎如念奴”的偏见,流露出对于男声的些许挑剔,此处提及的“念奴”则代表为大众所推崇的女音风尚。念奴原为唐代著名歌女,元稹在《连昌宫词》中注曰:“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念奴歌唱声韵优美动听,具有令“万籁俱寂”的超凡艺术效果,因此元稹不吝言辞以“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盛赞其歌唱之绝妙无比。后人尚有“念奴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的誉美之辞[8]112。上述李方叔直言不讳老翁之声不如念奴歌唱之妙,实际上是强调男声终究难敌女音之柔美圆润,而这种看法在宋时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意义。南宋人谢希孟就认为“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44]205,直言不讳对于女音的特别偏好。欧阳修《减字木兰花》词曰:
歌檀敛袂,缭绕雕梁尘暗起。柔润清圆,百琲明珠一线穿。樱唇玉齿,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云。满坐迷魂酒半醺[45]123。
词中极尽笔墨描绘宴席上所听女声歌唱之美妙绝伦,甚至达到“满坐迷魂酒半醺”的完美境界,夸张中充满了无限叹美之情。类似感官体验在宋人诗词中极为常见,如“唱得主人英妙句,气压三江七泽”[16]2024、“美容歌皓齿,齿皓歌容美”[16]527,给予女声柔婉绵长以十分的肯定,女性歌者以“声出莺吭燕舌间”而善于演绎词曲中的无限意韵,所谓“簸弄风月,陶写性情”[23]61正是如此。
当然,宋时也有少数因擅长歌唱而闻名的男性歌者。王明清舅氏曾宏父“生长绮纨,而风流醖藉,闻于荐绅”,其人“长于歌诗,脍炙人口”[34]216。宋代男性歌者以声音擅长而闻名于世者属于少数,尤其是与唐朝不断涌现的大批男性“歌星”相比更是相形见绌。唐朝以歌唱闻名于世的男性歌者莫过于李八郎和李龟年。唐玄宗朝李八郎“能歌,擅天下”,新科进士曲江宴上酒行乐作,其人“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1]254。同一时期的李龟年更因擅长歌唱而名留史册。相传其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杜甫“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46]27便是对其深受当时名流欢迎的真实写照。宋朝时期名动一时的男性歌者如李龟年、李八郎者寥寥,与不同历史时期世人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的差异不无关联。有学者就指出,宋代的宴饮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宴饮和歌女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种尊前月下、偎红依翠的情调和文人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微妙心理[47]。从所见饮宴词曲相关的演绎效果来看,确实如此,当时社会盛行“男不唱艳词,女不唱雄曲”[48]301之说法,以女性之柔美为衬托,所谓“歌翻檀口朱樱小,拍弄红牙玉筍纤”,浅唱低吟中尽享欢宴之意趣,为这一时期以饮宴为典型的社会生活渲染了一层闲逸底色。
另外,宴席上所唱歌曲对于歌者的演绎艺术和技巧也有着极高要求。关于歌唱技艺与效果,《新唐书·礼乐志》载,燕乐“从浊至清,叠更其声,下则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节,急者流荡”[49]473,要求韵律跌宕起伏,和谐中富于变化。因而歌唱技巧对于歌曲演绎效果无疑影响深刻。对此,沈括有着颇为独特的见解: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50]38-39。
沈括认为,歌唱对于歌者从喉、唇、齿、舌的音效到整体感知音律的抑扬顿挫之技巧都有着极高要求,不能把握其中奥妙便难以成为优秀歌者,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歌唱技艺具有“吹毛求瑕”的高规格要求。诸如“响亮歌喉,遏住行云翠不收。妙词佳曲,啭出新声音能断续”[43]439,“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51]81等赞美之辞,无一不是注重声调抑扬顿挫而富于变化,佐以丝竹管弦,由此产生扣人心弦的歌唱演绎效果,带给与宴宾客以意犹未尽的极佳感观体验。
第二,宜景怡情。宴饮中觥筹交错,宾主把酒言欢,曲尽其妙乃得欢宴之极致。一般宴席上的歌曲既要达到娱宾遣兴的良好效果,又要适合调节饮宴气氛与进程,所谓“词调不下数百,有豪放,有婉约。相题选调,贵得其宜。调合,则词之声情始合”[19]1851。对于词调拿捏恰到好处之外,对场景的营造更是不能懈怠,总体上以宜景怡情为佳。
宋代宴会中歌曲唱作所选曲目本无定法,只需根据饮宴情形灵活变通即可,通常情况下需要择取与饮宴气氛相协调的曲调。演绎与宴者本人所作歌曲往往事半功倍,也是这一时期宴会中常见的娱宾遣兴方式。北宋中期,秦观(字少游)被贬南迁途经长沙,受到一歌妓宴饮招待,“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阕以侑之”,宾主“卒饮甚欢,比夜乃罢”[52]1559-1560,饮宴气氛相当融洽。欧阳修(字永叔)使北还,北都居守贾氏开燕,歌妓奉觞尽歌永叔词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53]27,可谓是尽兴而归。辛弃疾“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54]34,表现出了相当的满足与自信。反之,如果所选词曲适度把握不够,不仅难得预期饮宴效果,甚者会破坏席间气氛影响宴会进展。邵博秋天里于咸阳宝钗楼上设宴饯客,席间有歌唱李白伤今怀古之作《忆秦娥·箫声咽》词者,以至于“一坐凄然而罢”[55]151,此情此景,无论如何也难得尽兴而归了。东坡曾畅游寒溪,与众人置酒欢乐。其间有郭生善作挽歌,改白居易《寒食诗》歌之,曲风凄清哀婉,听罢“坐为凄然”,甚至“坐客有泣者”[1]140,难免有大煞风景之嫌。
歌曲唱作过程中宾朋尤其是主宾的情绪心境也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晏殊罢相后出镇近畿名藩,自南都移陈留之际,离席上官奴歌“千里伤行客”词。晏殊听后大怒曰:“予生平守官,未尝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伤行客也!”[32]475唱出了客人相当忌讳的内容,场面一时相当尴尬。杨万里为监司巡历至一郡,郡守开宴款待。席上官妓歌《贺新郎》词助兴,有“万里云帆何时到”之句。杨氏遽曰:“万里昨日到”,如此情境之下“守大惭,监系此妓”[56]870,同样是选曲未能思虑周全,引来不快。
三、宋代宴会词的文化传播功能
宴饮作为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既是饮食活动,又难以摆脱浓郁的休闲色彩,用于娱宾遣兴的宴会词更是如此。综观宋人所作的宴会词,可谓最为典型和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的享乐生活和享乐心理[57]220。但不容忽视的是,宴会词不仅仅局限于佐酒侑觞的消遣功能,更以歌吹弹唱的演绎方式日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喜闻乐见的文艺娱乐活动和文化消费内容,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促进宋代社会文化繁荣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歌姬为例,作为宴会中词曲唱作的主要演绎者,对于其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之提升就有着相当直观的体现。南宋时期“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58]5,佐酒助宴的歌姬才华灼灼者比比皆是。江浙间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且属于“京都遗风”[59]277。当然,此种现象之普遍出现与宋代女子所受教育也有一定关联。宋代女子教育勃兴,众多女子多才多艺,或精通经史学问,或善于诗词文章,或成为绘画、音乐高手。位于社会下层的女艺人、伎乐等,也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尤多精妙的诗词之作。歌妓是个庞大的创作群体,在《全宋词》中的女性词人约占四分之一的比重,女子文化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60]。针对女子教育,司马光就曾明确指出,“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61]107,认为女子也应该接受基本教育。诸如此类教育规范及倡导对于宋代社会包括歌姬在内的女性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能言善作的才女亦是不足为奇的现象。
为了适应宴饮场合的特殊化需要,催生出了大量词曲作品。仅就《花间集》、南唐二主、冯延巳词、《全宋词》等作品进行统计,共收入词22000余首,其中题序直接标明在朋僚聚会时用以佐欢寄情、唱和者有2966首,包括席间记趣者416首,筵间赠妓者325首,筵席饯送者376首,聚会唱和1849首[62]206-207。统计结果充分说明宴饮活动中赋诗填词之类文艺创作及歌曲演绎活动的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宴会词曲娱乐化和艺术化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兴起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至少在文化传播层面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另外,以宴会词曲创作和传播为媒介的文娱生活时尚,对于宋朝社会文化时代发展特色影响巨大。唐人相关诗词中有很多关于宴饮场景之描述,如“金衔嘶五马,钿带舞双姝。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歈”“锦帐郎官醉,罗衣舞女娇。笛声喧沔鄂,歌曲上云霄”[41]821等皆是宴席上以歌舞曲乐助兴者,其歌舞之喧嚣沸腾、曲乐之热烈狂放不言而喻。宋人作品中也不乏类似宴饮场景,“当筵秋水慢,玉柱斜飞雁”[63]147,“昵昵琵琶恩怨语,春笋轻笼翠袖”[64]99,皆属浅唱低酌之轻慢风尚,曲乐清丽,与唐人的雄浑气象相比又别具一番精致细腻之品位特色。宋代社会世人这种独特的审美风格与文化意趣,既影响宴会词曲的创作,又深受以宴会词曲为媒介的社会娱乐风尚之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65]271-274展现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结语
宋代社会市民阶层崛起,宴会词曲以通俗的演绎方式为广大市民所接受和传唱,对于城市娱乐大众化和文艺通俗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当时社会“《麟角》、《兰畹》、《尊前》、《花间》等集,传播里巷,子妇母女,交口教授”[66]626,所列诸多词集中很多就是饮宴聚会中专门用于传唱的宴会词。南宋人严有翼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人多称之”,“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1]321,强调了柳永的词作通俗易懂、便于传诵的突出特点。宴会词在勾栏瓦舍、酒楼店肆、高墙宅院甚至是深宫内廷都有其形,广泛传播之下改变了传统娱乐方式的严格阶层界限区分,雅俗共赏,成为各个阶层颇为喜闻乐见的文化消遣内容,对于宋代社会文化的繁盛与普及贡献巨大,在文化传播中所具有的意义和潜在影响力广泛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