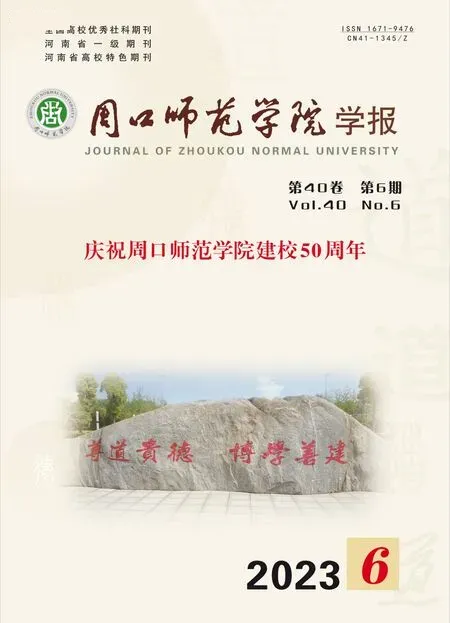可能性的对话:中国古典园林的时间观探赜
李 稳
(宿州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一、西方“时间”概念的探索
世界万物变化和四季更迭对于常人来说是最普遍的自然现象,这种气候冷暖与植被变动可以推衍出时间意识。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约前8世纪末—前7世纪初)的《神谱》是西方最早涉猎时间观的著作,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公元前610—约公元前545年)的残篇著论中“时间”的概念则已经出现。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44—前483年)的万物生灭循环论将“时间”列为一种反复,即构造宇宙物质的各种成分按照一定的规律在时间中运行。
在西方哲学史上,最先系统思索“时间”问题的当属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他开创了希腊哲学史上的第一个思考“时间”的传统,即“时间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派生物”[1]700。这种传统“时间”的定义把世界划分为“理念世界”和“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理念世界”更恒久稳固。柏拉图的“时间”理论不是依靠观察物体的运动,而是被当作永恒理念行为的折射,而且“时间”是按照数的固定法则进行运转。柏拉图在其专著《蒂迈欧篇》中给“时间”下了明确定义:“永恒之运动的形象”。他的理想是将“时间”嵌入“太一”之中铸造无限永恒的形象——时间。当然,我们理解的这个“时间”只是永恒的摹相与仿效,是永恒运动罢了。
与老师柏拉图观点迥异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第一次对“时间”问题做了系统而全面的注解。他在著作《物理学》第四卷中提出了“时间是运动先后的数目”[2]的论断。他认为,物体运动有快慢,时间应是均一的,运动与时间是相互谐和的,时间虽不能运动,但它是标度运动的计量,是运动的映射与表达,天体的运动自然就有了时间的测量尺度,同时把“现在”作为边界的尺度,形成“时间”前后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基础的时间观,较为圆满地呈现出“时间”的均质性、不可逆性、可分割性、不停歇性等特征,具有计数活动视野的“时间”拥有了科学成分和理论界定,即科学的物理学时间(时钟时间)概念的形成,这一学说奠定了西方传统时间哲学的主体。此外,亚里士多德还首次确立了西方哲学将时间与人的心灵或灵魂相关联的传统[1]704。他认为,时间与人的心灵主观性相连是感知外部世界运动的整体印象,只有灵魂才能计算运动的变化,这种心灵关联性学说一直推展到当代,具有独创性意义。
在哲学上,对“时间”进行神秘思考且具有典范意义的当属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年)。他是首个把“时间”归结为人的精神活动之人。他在《忏悔录》中说,对于“时间”这个问题,“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无解了”[3]。奥古斯丁又说,过去形成了记忆或回忆,未来往往在我们的预言或期望之中。因此,过去与未来并不存在,以往的过去、现在、将来应描述为: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奥古斯丁这种“时间”的延展是在心灵的度量中实现的,但他依然还坚信“时间”是伴随上帝的创世而出现的另外一种时间观。
虽然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念在中世纪影响深远,但他的学生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年)才是奠定中世纪“时间”哲学总基调之人。托马斯的“时间”问题是从神学观念切入,他的实在论时间观承认,“时间”是连续与不连续的归纳,既存在于灵魂之中,又部分存在于事物内部。
英国的牛顿(Newton,1643—1727年)传承老师拜娄的几何学演讲稿中的部分内容,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著作中,明确提出了“时间”是内在的绝对性,独身于运动与静止,依附于上帝,无所不在,具备了绝对真实、数学测算的属性及无限、永恒、永在的上帝特性。
康德(Kant,1724—1804年)在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并立相持的思想背景下,提出了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的“时间”观念,他认为“时间”是我们自身及内在状态的形式,首次将“时间”问题看作认识论的最高范畴之一[4]。他强调“时间”不可定义,是一个唯名论的范畴,这种把时间认定为客观性和普遍性相对窄化的理论,其实并非康德时间观的全部。他在“先验逻辑”与“图式论”的范围内,将时间划分为“直观形式”与“形式直观”,形成了我们先天具有的形式逻辑,空间与时间被一起讨论并赋予先验形式,同时也被表象为直观本身。这种内化与科学化的直观性,形成内感时间(算数)与外感空间(几何学)相统一理念。康德的时间理论,对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缘始时间”的讨论有所抉发。
海德格尔在著作《时间概念》的演讲稿中,全面展开了对传统线性时间的批判。他直截了当地说:“与时间的始源交道的方式不是测量”[5]。他强调的时间是非均匀、非线性、非测量的思想,与传统哲人的时间观唱起了反调。他颠覆了基督教末世论,以及基督的降世为历史终点和目的的学说,将存在的意义得以自由开合,首次将“时间”问题与存在问题进行关联,这样的时间理论,才能把传统哲学遮蔽人的生命真实解蔽完整。
传统线性时间观从亚里士多德流俗时间的始源表述、康德的本源时间性的认知基础及黑格尔(Hegel,1770—1831年)的“现在—点”的“现在序列”性的线性表象(具备了某种圆圈式的结构)[6],对流俗时间进行了最极端的领悟形式理论(时间是纯粹抽象、观念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时间观没有思考“时间”的真正意义,直接把时间看成一种现实存在物、计数活动或纯抽象的理论,也就是把“现在”变成了一种当前化的活动,却忽视了过去与将来的联系,割裂三者的依存关系,是非本真的时间。他认为,三者的关系是浑然一体的关联结构,“现在的我”即是“原来的我”更运化着“未来的我”,时间是“此在”的时间,它的存在是以过去、现在、将来三个维度为根基,形成“此在的本质是时间”的伟大论断,将“此在”的意义,解释为“时间”替换了“逻各斯”是存在意义的问题。
海德格尔时间观的形成,似乎与尼采(Nietzsche,1844——1900年)的“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学说有着紧密联系,打开了一种以“瞬间—时机”为主旨的“圆性时间”的剖析[7]。虽然他的“时间”学说受到基督教时间观的影响,但他舍弃了基督教神学以基督为历史的轴心思想,推演出没有轴心使存在意义自由绽开的视角。而“相同者”(Dasgleiche)我们按照孙周兴理解尼采的观点,即“同”并非一样、一致的词汇,而是一个变动不居、有差异化的“同”。海德格尔的“时间自身是一个圆圈”,这种轮回思想的开拓,并非宗教的来生意义,本身触及了每个瞬间都有新的创造,克服所有以往无意义的重复和空虚,是一种新的复归循环,这样形成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线性时间观相反的基调[7]。这种理论的形成就是用“过去”与“将来”的相遇——“瞬间”来阐释时间,表达一种圆性的时空一体观,这种时间观既不是特指我们的物理时间(可测量计算)与钟表时刻,又不是大家惯常思维中牛顿的绝对时间概念,而是个体差异产生的新的创造活动。
与尼采“瞬间”的圆性时间不同,海德格尔首次提出了以“将来”为核心的时间循环结构。海德格尔追问,什么是时间?时间是通过对“将来/未来”的“定向”和对“将来”不断地“先行”而发动起来的三位结构,也就是我所论述的“圆性空间”。
总之,尼采以“瞬间—时机”为核心创造的“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循环时间观与海德格尔以“此在”为中枢的“时空一体”的“将来”时空构架为我们提供了无法规避的“时间”问题。这种“圆性时间”的架设旨在推翻传统哲学均一的、不可逆的线性时间理论,打造出一种时刻都有创造性生成、以时间—空间为一体化的生命经验以及时间感觉、直觉、文化生活为真正本质的新颖视角,对我们思考当前技术化的生活世界意义重大。
二、“天时”何以可能?中国古典园林的时间营造理论
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往往交合于日常语言与平居生活之中。古代先民在农业生产、日常生活、军事行为中都有着原始的“时间”态度。这种执着的时间观是由中国文化恒常稳定的结构决定的。一方面,这种素朴的“时间”意识主要体现在对具体事件秩序一致性上;另一方面,是双重“时间”意识之流的混同。这种既有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念,又有线性时间观的理论都没有像西方那样一分为二的极端呈现,往往成为合二为一的生命时间观。这个整体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时间含嵌其中,与万物生长、孕育、繁茂、息灭,具有循环不止、绵延不绝、节奏无常的特性,这种反思的生命体验反而更接近时间的本质。
中国的象形文字“时”:左面的“日”对应的是太阳,与植物、动物、人类生长息息相关,寓意孕育生命之源;右面的“寸”与《淮南子》著作中名句“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金句不谋而合。中国的时间概念往往与中国的节气、时令、时代、纪年等词汇有关。节气的更迭往往以四季的变化为表征,天气的阴晴雨雪与温度的冷暖感知都关涉到人类的活动,它包孕着植物的生长、动物的“换装”以及人的耕作制度与生活方式。“时令”往往特指“各月的政令”[8],代表着中国的皇帝、大臣、布衣须严格尊崇每个月的政策布令,在着衣色泽、食材物料、交通工具、耕作出访等方式上伴随节气而变。这些“天命”法令的实施也具有了人体养生的丰富内涵,并与我们的五脏六腑协调一致,这就是节气、时令的运行时常与道家的“阴阳理论”唇齿相依的重要原因。其理论的精髓与植物的生长、人类的健康之间始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联关系,中医的理论来源也体现于此。这里面未有任何的计数关系,始终是对天地苍穹的敬畏之感,同时也与天宫的群星及其位置进行了内心的勾连。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综合建筑艺术,特别注重园林建筑与自然花木同构共生,以“天人合一”的哲学之维观照山川,以山为骨、以水为血共同支撑和营卫,常以“一池三岛”为蓝本,携造园家修习“胸有丘壑”为前提,讲究建筑、山水、花木各要素的衔接,通过适恰的经营位置,达到摆脱尘垢物累、超越自我的至高境界。在中国建筑史上有着四维空间(长、宽、高、时间)的共识,时间的介入增加了园林景观的空间体认,成为我们探索园林深层要义的阅读方式。中国古典园林多为文人兴建,有着浓烈的文人气息。物质的优渥与时间的闲暇造就了这些有闲阶层,进则护卫国家,退则置办园林,交流雅集。他们园林时间观念的营造方式通常由物态化与心理化交织而成。首先表现在园林空间路线的设计上,中国古典园林在初创之时就将路线定格为曲折无定式,这种布局创造既扩展了空间,又绵延了时间,无论大园还是小园都有着共同的感知。按照古建筑园林大师陈从周的大园“动观”理论,要求步移景迁,谋求多变无法,防止一览无余、平淡无奇,找寻时间的绵延;小园“静观”要求精思妙识,方寸多变,排当有方略,追求时间的延宕。两者无论在园奢或园素、园巨或园狭上都有着“时间”的共同性。其次,园林物质材料遗留的时间化痕迹。我们游赏古典园林,在日光、竹影、漏窗、门洞、隔扇中感受到空间的延长,在假山、立柱、碑刻、道路、朽木、残瓦中阅览时间留下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种折返历史萧瑟衰飒的图像重影,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兼集,丰富拓远了诗境。
中国古典园林乃人工模拟自然的作品,无人工斧痕,植物、动物、山水、建筑都是表征“时间”的载体,在营造理论上有着特殊的表达。如植物以视觉演替为表征“时间”,如春花、夏叶、秋黄、冬谢展现时令。动物以听觉的“声音”为生活习性表现“时间”,如春鸟、夏蝉、秋虫、冬雪为悦耳。山水以色彩的变化为考量“时间”:春水蓝染,山色显青;夏水无波,山流瀑布;秋水如天色,山势如沙汀;冬水浅而平,山形瑟而萧。建筑以光影的微妙变化投射出时间的变幻,伴随着一天日照弱—强—弱的改变,强化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应。中国私家园林在营造设计上,就提供了表现“时间”的造景载体,让我们在相同的空间中可以观览到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异样风景,进而在园林的实体之外感悟到时间流逝的迷人之境,这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魔力所在。
总之,中国古典园林的时间与空间双向融通,让我们在饱游山水、观览花木之时,这种物化的时间表现出处处生情、面面藏诗,雅趣无尽,培育出“自然”生长的土壤。广博的“大宇宙”,无影无形,这种图像的博局常常映射在人们对阴阳、天文、日历的时间理论之中。以园林为“小宇宙”的图像,涵括了历史、记忆、人生、未来、生活、装饰等意识,这些可以表现出整体合一的宇宙观,是古人、今人在“时空一体”的意识上形成的价值判断,而非图像本身,是图像背后我们理应寻找真正的“通名”。
三、可能性的组入:中国古典园林时间观念的中西推展
时间是无言的存在,当属文化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具有自身的流逝轨迹、模式结构。中西方在地理、历史、经济、宗教、生活中对待“时间”问题往往有不同的支配规则和理解取向,儒家理论的溯源之本《易经》,在六经之中名列榜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纲领,孕育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强调人与世界整体和谐,是历史思维与逻辑思维、时间与非时间动态的有机结合,本质上也是一种时间文化,体现出总体的循环与周期,具有随机应变、涨落不一,承载着关联与系统的时间概念。文本中关于时间的词汇,如演进、改变、持久、循环、创造、不息等,这种阴阳卦理、五行干支的内涵不是静态非时间的逻辑,也非诉诸测绘与丈量架构,而是具有超越、开放、敞开、创造的思维模式。与传统西方将“时间”数学化、空间化相比,无论从巴门尼德的“时间”低层次、柏拉图“时间”是永恒的拙劣模仿、笛卡尔“无时间”的逻辑存在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消除历史、消除时间,都将“时间”变成了“非时间观”对“时间观”的绝对统治。康德从认识论视角,将先天感性形式与范畴衔接主客体,提出了“时间”与人无关的立论。虽然爱因斯坦通过相对论,提出物质运动与时间有着内在的互联,从根本上放弃了牛顿的时间与物质运动无关的“时间筐”体系[9],但是“时间”依然外向化、形态化、对象化、线性化。海德格尔提出了人与世界相互关联的“时间”理论,将笛卡尔的时间逻辑、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导向此在的“圆性时间”。这种圆性的时间观与中国将宇宙意义对应的时间、空间,阐述国人居于天地间“求天、开物、成务、崇德、广业”,建立浑然一体的圆融哲学,既足以接洽人生宇宙[10],又与昭示道德仁义的文化深层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西“时间”文化的重要之别表现在:其一,共时与历时的时间哲学。共时强调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心理学大师古斯塔夫·荣格在阅览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后提出了共时性与中国不可明辨的“道”之间的对应关系,对“天人合一”理念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提出“共时性原则”[11]。国人常常强调天、地、神、人的整体内在系统,注重自然的“道”,他们承载着人类的情感、精神、生活及回忆,通过给予性、具身性、介入性、期待性,成为天人关系精心编织的强大网络,从而引发生命与天地的精神关联,时间观念灌输于四季变换和农业风俗之中,成为人类洞察世界和阐扬世界的尺度,有强烈的农业文化遗留的痕迹。西方往往是线性思维的单向度,强调逻辑分析,重科学实证,求因果,表现为主客二分,呈现出单一孤立、封闭片面,具有典型的历时性的时间逻辑。其二,时空范围不同。西方从古希腊到当代的“时间”问题是从工具理性主义不断批判累积成的强大“时间”架构体系。而中国往往从无穷的宇宙观、星体运转思维,返照万物、返照自我、返照自身的“宇宙”。中文中,“宇”是房屋,代表上下四方,是空间,“宙”是古今往来,代表时间,宇宙变成了一切时间和空间的统称。
从以上分析看,中西时间观在文化的内容上并立两极,在千年的传统中有着自己的亲缘根基,区别之大是不争的事实。探明两者的差别或许能解开隔膜,有“闲坐”对话的可能。1930年,海德格尔在家中举办的讲座中,将德文的《庄子》秋水篇“庄子与惠施濠上观鱼”的故事分享给学者表达出自己的真理本性;1934年,海德格尔以“逻辑”为主题的讲座打开了西方时间理论与东方学说对话的可能性;1938、1946、1966年,他多次在公共场合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吸收,尤其以老庄为核心的道家学说。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西方传统线性“时间”理论能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脱胎换骨的重要原因,这种“圆性时间”观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突破口和合理路径,那种“诗意的栖居”充满着诗歌、音乐、舞蹈的历史时空与对未来技术时代的深刻领悟。
圆性时间与中国“天人合一”的时空一体观不谋而合,是一种无目的、非物质、涤除杂念的原发性时间观,与人生、历史打通的管道,具有了立体多维、无法超越的终极智慧。海德格尔后期用“缘构”思想来阐释中国“道”的理论,是因为他始终认为“道”的思想是精深而有诗性的,或由语言本身而出的,将“道”扩展了包括语言在内的含义。
中国古典园林深受道家浸染,老子的“时间”哲学从“天下有始”宇宙论出发,以“古始”为中坚理论,具有伦理与历史的本体论意义[12]。“始与母”是时间形式、“无与有”是存在形态,两者奠定了老子的“相对时间观”理论。本体论要求以自然之心,守虚静之体,极而复反;“相对时间观”则是祈求摆脱纷扰,以荏弱心志,顺古今之变[13]。海德格尔在人与自然的基础上,反思西方国家与自然为敌的种种弊端,他在庄周“鱼之乐”中体悟到人与自然本性的问题,从而反对科技支配自然带来的可怕现实[14]。今天,我们反思半个世纪前海德格尔的未来技术预言,地球变暖、土地荒漠、物种灭绝、垃圾成灾、全球疫情等生态危机已经刻不容缓,这些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当我们陶醉于高科技带来的成果和便捷时,却发现我们完全成为高科技的控制者,自然也以自己的方式对我们进行惩罚,其结果是深刻的。所以,回头检索道家、儒家思想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时间”的理论,对我们全面理解古代文明与当代文明大有裨益。
从文人园到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古典园林的内涵和外延在逐渐深阔。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样板,是文人士大夫追逐仕途、文学、生命、审美的精神理想之所,也是不断创新、锐意进取、流动超越的时间精神!我们以哲学之思探讨中国古典园林的“时间”问题,向内连接中华文明“天人一体”的东方审美思维,向外接纳西方时间之维的国际化视野,意在建构跨越时空的具有时代精神、贯穿中西审美意象的时间语言体系。这种思考是基于当前技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压迫与无所依从,表明了技术文明并不能确证人的生存意义。我们从中国古代时间观和西方时间观的对比、融合来看,其目的是追逐真正属于人类的“时间”本质,即更高的、理想的、超验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也是审美的世界,充满着柔情蜜意,以“我”为精神核心,把有限之物,时间中的“物”统一组入无限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