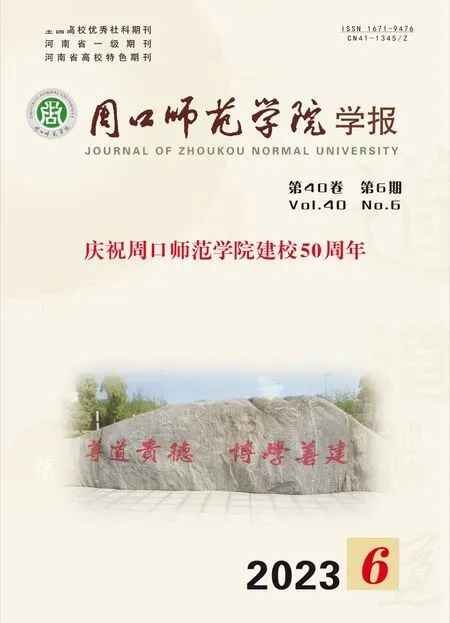伊恩·麦克尤恩小说中的伍尔夫元素——以《赎罪》为例
朱子琪,辛雅敏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谈到《赎罪》主人公兼自己的文学代言人布里奥妮时坦言:“她有些伊丽莎白·鲍温(Elizabeth Bowen)《正午的炎热》的意思,又带点罗莎蒙德·雷曼(Rosamund Lehman)《含混的回答》的味道,在她最早的文学尝试中还闪烁着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火花。”[1]正如布莱恩·芬尼(Brian Fanny)所言,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这本小说的影响是复杂的。在外部技巧层面,麦克尤恩在《赎罪》中借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之口所提及的故事骨架方面,试图进入和现代主义及其摒弃的职责的对话。在呈现受伍尔夫影响的内在线索时,麦克尤恩采取了一种反讽的态度。他安排年轻的布里奥妮用类似的叙事风格,描述自己在护士轮班间歇阅读《海浪》时的场景。布里奥妮受到伍尔夫现代主义风格的蛊惑,认定“人物这个概念”只不过是属于“十九世纪的古雅有趣的手法”,而书中的情节“只是锈迹斑斑的机器,其轮子已不会再转动”。通过西里尔·康诺利对布里奥妮第一部小说的点评,麦克尤恩表示《喷泉旁的两个人物》即折射出这样的现代主义偏见:把自己的意识深埋在自己的意识流中。布里奥妮对自己早期文稿曾这样批评道:“难道她真以为能够假借现代的写作观念,把自己的负罪感淹没在一股——不,三股!——意识流里吗?”[2]322麦克尤恩的这些字句,无不体现着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遮蔽当代文学创作的再更新的。在批判性阅读与继承伍尔夫的同时,麦克尤恩着力为英国当代文学的焕然一新寻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一、伍尔夫式的叙事技巧
伍尔夫式的现代主义技巧与风格对《赎罪》的影响是突出的。《喷泉旁的两个人物》修订版作为《赎罪》的中心场景,让许多读者捕捉到了伍尔夫的影子。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观察到,麦克尤恩小说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式的微光覆盖了澳大利亚式的情节”,《纽约时报》评论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评论了第一部的“朗伯·伍尔夫式散文”。有学者将《赎罪》与《幕间》进行比较,两部小说都写到了“一群出身优越的人聚集一堂参加家庭盛会,而背景则是即将爆发的战争”[3]。也有学者指出,《赎罪》第一部中那场“闷热烦躁的客人不得不享用灾难性的烤肉大餐”的情节,是对伍尔夫《到灯塔去》中用餐场景的模仿[4]。
尽管《赎罪》在整体结构上与《到灯塔去》更为相似,但《海浪》对布里奥妮护士期间所写的中篇小说影响最大。她对它的“设计”和“纯粹的几何形状”以及现代的“决定性的不确定性”[2]282感到兴奋,并出色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就像《海浪》一样,《赎罪》的第一部分虽然要粗略得多,但它在一天内跟随太阳描绘时空。塞西莉娅发现,“落地窗的东南面使得平行四边形的晨曦穿过粉蓝色的地毯”[2]16。这种光线前进和后退的想法,太阳在室内勾勒出几何形状的设计无不体现着《海浪》的特点。例如,在《海浪》中,傍晚的太阳“使椅子和桌子变得更柔和,并用棕色和黄色的菱形镶嵌它们”[5]159。同时,和伍尔夫一样,布里奥妮也拒绝情节和人物的“生锈的机器”,支持“思想、感知、感觉”,试图描写“有意识的头脑向前滚动,就像一条穿越时间的河流”[2]282。正如编辑西里尔·康诺利在回信中所言,布里奥妮“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洋洋洒洒地描绘光影和散乱的观感”[2]315,“一味地大写特写他们每个人的感受感知”[2]316,并指出“老成练达的读者可能对柏格森有关意识的最新理论有所耳闻,可是我确信他们还像孩子一样想听故事,想处于悬念之中,然后获悉故事的前因后果”[2]317。事实上,布里奥妮显然未能渲染河流般的柏格森式“滚动”时间。虽然《赎罪》在人物视角之间不断穿梭,但它并没有试图将一个多重的、共同的意识聚集在一起。而《海浪》则避免了这种停滞,在没有传统情节和角色帮助的情况下,将读者从童年带到“死亡”的开始。
康诺利以初版小说过于“伍尔夫式”(Woolf-ish)而拒绝刊发。经过多次修订,布里奥妮在最后一版小说中确实清除了早期明显的实验痕迹,但是她和麦克尤恩都无法完全抛弃伍尔夫式的技巧与风格。从第一部中关于几何形状与时空的描写,到各式人物针对同一事件呈现的复杂的视角变换来看,不得不说《赎罪》仍处于对《海浪》等作品的绵绵回声之中。除前文分析的片段外,第一部模仿的伍尔夫风格与伍尔夫自己还有着对话般的张力。例如,塞西莉娅对马歇尔房间内部的看法是:“空气中弥漫着蜡的香味,在蜂蜜般的光线下,家具闪闪发光的表面似乎在波动和呼吸。当她走近时,视角发生了变化,一个古老的嫁妆箱盖上的狂欢者扭成了舞步。”[2]41《海浪》中也有此种联觉效果(“平滑的空气”),光将固体物质液化成无定形的物质(“波纹”家具),以及将对客观世界的描写自然地带入痛苦的生活。关于对物质不变性的怀疑,伍尔夫如此写道:“这里摆着刀、叉和酒杯,但它们的样子仿佛被拉长了、胀大了,显得十分怪异。镶在一圈金框里的镜子将景物静止不动地映照出来,好像它所映照的事物将会永恒地存在下去。”[5]159第四章中塞西莉娅的午后顿悟,正可以看作对《海浪》的某种回应:眼前的这一切好像是固定不动的,她又一次觉察到了,这一切在很久以前也曾发生过,所有的结果,在一切程度上——从最渺小到最庞大——都已各就各位。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无论表面上多么的怪异或惊心动魄,都会有一种毫不惊奇、非常熟悉的品性[2]52。这些外部层面的呼应体现了麦克尤恩与现代主义和英国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对话的尝试。
二、小说理念的交互
尽管有这些伍尔夫式的片段的存在,读者对《赎罪》的主要印象仍是《海浪》的文本性被省略多于保留,即使在第一部分也是如此。布里奥妮在设想小说时的野心是“再现夏日早晨的清光,孩子站在窗前的感觉,燕子在水池上飞行的曲线和俯冲”[2]282。虽然布里奥妮在窗边的感受被捕捉到了,但重要的不是其感官即时性,而是其在总体叙事中的功能。在《赎罪》中,只有两段文字专门用于描述燕子在池上掠水翻飞[2]21,282。燕子作为《海浪》中反复出现的鸟类之一,在文本中如此罕见而引人注目。虽然《赎罪》的整体结构具备伍尔夫式的标志性,但它的描述性段落被作者刻意修改和限制,只呈现给读者纯粹的场景。在此,伍尔夫的影响显然逐渐超出了诗性描述的闪光和柔和,她的小说理念对布里奥妮的成长和麦克尤恩的创作更起着重要作用。
在《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一文中,伍尔夫强调小说的中心是人物,而人物的核心是她/他的“人性”[6]297。她所指的“人性”即是人物的“生命”,人物“赖以生存的灵魂”,它“就是生活本身”。这与布里奥妮的早期写作理念相契合,也与创作《赎罪》的麦克尤恩有所呼应。虽然麦克尤恩提倡一种理性、科学的生活与写作方式(如《星期六》),但在关切人物的“生命”和“人性”时不得不求助于人物内在的“真实”的力量。他的小说展示了“心理学的黑暗之地”[6]10是如何从物质的视角来呈现的,这种视角不仅凸显了现代主义的特性,而且指引了一种现代小说的可能向度。例如第一部中对布里奥妮、塞西莉娅、罗比等人内心独白的描写,尤其是第六章对艾米莉·塔利斯意识流动的铺陈,都表现着在传统世界中的现代西方人的内心变动。纵观全书,支撑《赎罪》的核心要素一直是人性。是布里奥妮丰富的想象力遮蔽了她的理性行动,从而导致悲剧;也是布里奥妮在外部行动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体验,从而开始赎罪。《赎罪》的主要情节发展,几乎完全建立在主人公布里奥妮的“人性”上,随着她人性的变动而更新。在劳拉·马库斯(Laura Marcus)看来,在小说中表现人物的消解与再造正是麦克尤恩转向伍尔夫的明证。
这种对人性变动的把握引向一种时代变迁感的产生。“大约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左右,人性改变了。”[6]299伍尔夫特别指出现代人所面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代代沟(generation gap),而是与先辈割断联系的一种隔绝感,因此她才会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生活如此像万丈深渊之上的一条小径?”[6]352一战之后,人性复杂化了,自我也就更加模糊不定。1914年后的艺术家们居住的不再是稳固的象牙之塔,而是“倾斜的塔”。这不得不引人思考: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原封不动地使用传统的艺术形式是否恰当。伍尔夫认为,过去的艺术形式显然无法涵盖当前的现实,“要是时代的印记还有任何价值的话,人们正在感觉到作出新的发展的必要性”[6]337。故而,在讨论真实的问题时,伍尔夫强调人物内在的心理真实,对现实的观感(vision)要比现实更重要。在此,可以观察到布里奥妮对现代主义叙事的思考,但也看到布里奥妮误读这种美学原则的方式。就她对伍尔夫的理解而言,布里奥妮对“性格”的拒绝消除了伍尔夫认为叙事必须传达的人性元素,她误以为仅靠技巧就足以传达“现代”体验。尽管现代主义美学对探索“感知”和“感觉”的“有意识的头脑”感兴趣,但对伍尔夫来说,这些概念必须建立在一个可识别的人物故事的基础上。由于没有确切的情节可循,也没有完全发展的人物可以识别,布里奥妮的读者便无法追究她的行为责任。康诺利指出了这种逃避,他说:“如果这个女孩对眼前发生的奇怪的小场景完全误解或困惑,这会对两个成年人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她会以某种灾难性的方式夹在他们之间吗?”[2]315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指明了布里奥妮叙述的模糊,她企图用这些现代主义技巧将自己的罪行隐藏在文本中。事实上,布里奥妮后来承认:“关于光、石头和水的无休止的书页,叙述分作三个视角来回变换,处处萦绕着似乎万古不变的凝重——但这一切都不能掩藏她的懦弱。难道她真以为能够假借现代的写作观念,把自己的负罪感淹没在一股——不,三股!——意识流里吗?”[2]322在麦克尤恩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由于布里奥妮为了遮盖自身的道德责任而误读了伍尔夫,还由于现代主义本身就已在麦克尤恩那里预示着一种现代文学的新向度。
三、一种现代文学的新向度
在《文学、科学与人性》一文中,麦克尤恩引用伍尔夫的名言:“1910年左右,人性发生了改变。”接着,他肯定了人性中不易变化的品质——我们的超越历史的情感,我们的家庭和最终的物种纽带:“如果有超越文化的人类共性,那么它们就不会改变,或者说它们不会轻易改变。如果我们在历史上确实发生了变化,那么根据定义,改变的不是人性,而是某个特定时期和环境特有的某种特征。”[7]对麦克尤恩来说,我们最终保持了自己的本性,这确实是在“情感和表现力”之内。同时,麦克尤恩也对时代变迁给英国文学带来的变化感兴趣。与伍尔夫大力开掘“精神主义者”的写作不同,麦克尤恩并未“把似乎是外来的偶然因素统统扬弃”[6]8,他坦言自己总会被一种强烈的理性传统所制约,关注“物质主义者”[6]4的书写模式。《赎罪》中的塔利斯庄园与19世纪小说的氛围相处融洽,在描写塞西莉娅与罗比发生关键交集的泉畔场景时,麦克尤恩几乎要和威尔斯、贝内特、高尔斯华绥一样耽于树林、喷泉、房屋的修辞了。小说的卷首致辞借简·奥斯丁的《诺桑觉寺》,点明麦克尤恩对想象与真实之间关系的探讨意图。他所追寻的人物概念属于19世纪,而不完全是伍尔夫所倡导的那种人物理念。麦克尤恩明确表示,自己更倾向于把人物塑造、对他人内心世界的描画以及邀请读者踏入这些内心世界的体系,归于简·奥斯丁、巴尔扎克、福楼拜和狄更斯所建构的文学体系,尝试在当下描述一种看似真实的小说世界[8]。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指出,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这种效果依赖于后辈作家的阅读和阐释活动,这些活动又与新的创作相一致[9]7。事实上,现代主义在当代英国文学中的大量批判性反思可以说是具有革新意义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当代文学的方式,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很少有研究能将这部小说置于完整的现代语境中(布莱恩·芬尼和理查德·罗宾森的文章例外),但评论家们仍然注意到,作者正在回归既往文学中感知的传统,并反思其在发展历程中引起的误读,以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主义与当代文学向度。在小说中,麦克尤恩既没有对伍尔夫的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也没有不加批判地致敬,而是巧妙地更新了伍尔夫的小说理念以设想现代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在一篇未署名的1919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文章中,伍尔夫阐述了现代小说与现代时期更传统的小说之间的区别。伍尔夫将贝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等作家的“物质性”作品与詹姆斯·乔伊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的“精神性”作品区分开来,认为真正的现代小说避免了对外部描述的“琐碎和短暂”渲染,而倾向于对意识思维的“真实和持久”再现[6]4。为了“传达这种变化的、未知的、未循环的精神,无论它可能表现出什么样的偏差或复杂性,尽可能少地混合外来和外来的东西”。因此,现代小说家通过时间因果关系的不断重组,将叙事结构从严格规划的“对称排列的一系列演出灯”重新定位为相对无情节的顿悟(“发光光环”),强调事件在角色意识与时刻中的表现。伍尔夫以乔伊斯为例,认为现代作家必须“揭示通过大脑传递信息的内心火焰的闪烁”,而忽略任何“几代人以来一直用来支持读者想象他既摸不到也看不见的东西的路标”[6]8。
有鉴于此,麦克尤恩特别探讨了伍尔夫现代小说中那些被高度认知的“存在时刻”(moment of being)所特有的间隙。伍尔夫的叙事实践隐含地将“现代”小说等同于对“存在时刻”的几乎排他性的描绘,即代表极端意识的短暂的强烈意识时刻。然而,麦克尤恩将非存在的时刻视为以心理为中心的“现代小说”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麦克尤恩拒绝将一种意识凌驾于另一种意识之上,他为主人公描绘了一幅心理画像。这种由非存在的某种外部时刻构成的心理画像,使麦克尤恩及时地转移了叙事的方向,能够成功地重新评价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对医学的蔑视,去关注那些即使没有得到充分展示,也能够传达意识信息的物质性疾病。《赎罪》和《星期六》都“揭示了最深处的火焰的闪烁,它通过大脑传递信息”,这些复杂的叙事实践努力看到生活并观照它的整体,人物以一种“向前运动的感觉”的方式去解决当代的忧虑[10]。同时,这也表明,外部行为可以表现出一种更为真实的思维和存在方式。如果在伍尔夫的时代,最需要叙事声音的视角是一个长期不在文学对话中的女性,那么麦克尤恩则暗示,现在最需要的视角是科学家,能够为被遗弃的现代主义和当代文学带来急需的物质基础[11-14]。
尽管麦克尤恩在写作实践中重新想象并逐步抛弃了其“疯狂”角色的内心生活,但它仍然为其黑暗的替身提供了伍尔夫丰富的故事中所没有的东西——一个超越结局的机会。《赎罪》以叙事比例的重新确立而告终,这为接下来的小说提供了一种逻辑上的连接。只有当布里奥妮承认,对可以通过经验验证的东西的认同,比沉溺于创造性自我的艺术想象更重要时,她才能完成自己的故事[15-16]。她公开了自己的诊断结果(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会破坏她的记忆),这只会为她最后的写作行为增加即时性。麦克尤恩的小说并没有排斥布里奥妮,甚至没有排斥被布里奥妮迷惑的读者,但它确实证明,布里奥妮从一个完全内化的意识到一个对时间和地点都敏感的基于经验的叙述者的转变是正确的。麦克尤恩含蓄地承认,伍尔夫“通过一种不再屈从于宗教或政治教条的新艺术,直面和描绘人类灵魂的痛苦,并试图为人类心理的各个领域发声”[6]324-335,这使他自己的小说成为可能。他重新应用了她的“现代小说”理论,使她的仍然具有相关性的文学经验更适合当下。
四、结语
对现代主义实践或信仰的反思与批判并不是完全拒绝现代主义,相反,它是现代主义主题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变体。通过展示当伍尔夫式的现代主义原则以突出观感而不是形式主义[6]291的方式“重新应用”时可以做些什么,《赎罪》尝试推动当下文学中智识与感性的发展。作为麦克尤恩文学代言人的布里奥妮,其写叙事技巧和小说理念的变动体现着作者创作的历程。从对心理领域的关注和多视角变换的尝试,到自我反思寻找心理写作与现实交互的另一处幽暗之地,布里奥妮完成了自己文本意义上的“赎罪”。麦克尤恩有意借此表达对现代主义突出观感与想象的特质的批判,他巧妙地指出了该特质的道德遮蔽性,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更新与转向。
麦克尤恩继承了伍尔夫的心理写作的部分理念,重申对人类共性的认识,并尝试在19世纪的文学传统中寻找一种真实的人物塑造方式。在此过程中,他以自己的方式尖锐地追随了伍尔夫的经典化时刻,反思了现代主义实践与信仰的元素,提出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理性传统的力量应用于现代主义写作的可能,肯定了关于非存在的外部时刻的描写在叙事层面的重要性。他大胆地提出一种现代主义发展的可能向度,即将物质基础作为文学实践的条件之一。麦克尤恩广泛汲取与批判伍尔夫的文学经验,以便为当代重新定位现代主义,促进当代文学的更新与繁荣。如果读者注意到这些巧妙的重塑与转向,就能意识到许多著名的当代英国小说作品确实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让现代主义和当代文学再次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