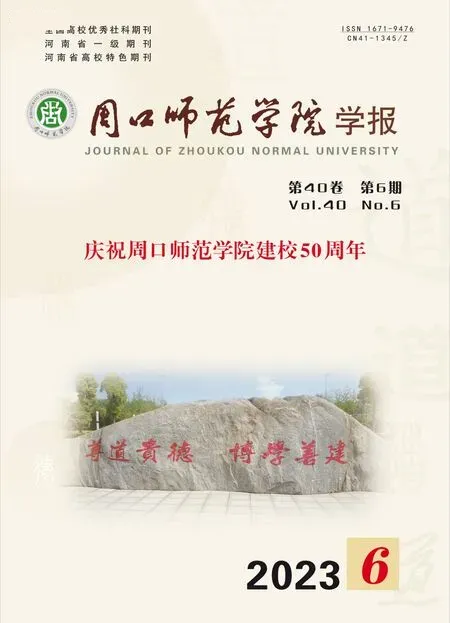怀旧意识与刘庆邦柔美小说的文体生成
刘成勇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刘庆邦是个怀旧感很强的作家,从几件小事可窥一斑。有一次,电视正播豫剧电影《穆桂英挂帅》,看的时候,刘庆邦“就感动得不行,心里一鼓一鼓的,喉头发哽,眼睛发热,鼻子发酸”[1]。画面和声音唤起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引发出许多复杂的、一言难尽的感情。作家尉然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刘庆邦特别“恋旧”:在刘庆邦的老家,保留的还是一些落伍的陈设,旧式的大床、没上漆的躺柜、蝴蝶牌的收音机、屏幕只有手绢大的电视机、扶手亮晃晃的几把椅子。保留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出于他本人节俭的习性,更主要的是他想挽留住一段岁月和记忆”[2]。刘庆邦每次回老家,都会让大姐蒸上一锅馒头带到北京,放在冰箱里慢慢品味。尉然对刘庆邦这一做法的理解是,他品味的不是馒头,而是在品味家乡。
对于家乡,刘庆邦的记忆尤为深刻、牢固:“家乡的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树皮、野菜和杂草养我到19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野、秋天飘飞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流一样,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只要感到血液的搏动,就记起了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3]当提笔创作,作为生命底色的“家乡”经过“回忆”的曝光后成为“理想的美化后的乡村”,在勾起作者对农耕文明深情回望的同时,也寄托了他的思乡和怀旧之情[4]293。
“写作是一种回忆的状态。”[5]一旦笔涉乡土(煤矿也是乡土的一部分),“怀旧”成为刘庆邦小说中浓郁的情绪主题,在个体存在对生存环境越来越感到惶恐不安的现代性语境中,散发出直抵灵魂深处的神性光芒和诗性魅力。在农耕文明成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环境中,乡土是怀旧最主要的审美对象和价值载体。当刘庆邦隔着一定的时空距离回望乡土时,他“用审美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观照,使其上升到一种美学的层面”[1],文本整体也因此有了一种“怀旧”色调。
刘庆邦在多篇文章中谈到文体的重要性,并且对文体有着明确的追求和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不论写到什么时候,都要认真,诚实,别想着玩技巧。还要在构思上多下功夫,莫要轻易动笔。行文简洁,少说废话。短篇创作是需要有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覆盖面,但最重要的还是质量。……写得要自然,但不能自流[1]。在怀旧意识的支配下,刘庆邦选择了最适合表达记忆、心理和情感的文体样式,成为当代文坛一个独具特色而又不可或缺的文体家。一般对于刘庆邦柔美小说的主题价值、情感审美、文本结构、语言特色的研究文章多不胜数,但对其文体生成的心理动因进行专门性探讨的却不太多见。从“怀旧意识”入手,探究刘庆邦主体心理与其柔美小说文体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其文体构成的独特之处。
一、短篇体制与散文化结构
尽管刘庆邦不愿意戴上“短篇王”的帽子,但提到刘庆邦,必然想到他的短篇小说,而提到当代文坛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必然要以刘庆邦为代表。刘庆邦与短篇小说之间的关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双向选择的结果:“首先是我选择了它,我很尽心地伺候它,把它伺候得不错,然后它就选择了我,这么长时间的磨合,我跟短篇小说好像达成默契一致,形成一种亲密关系。”[3]
短篇体制与主体生命遇合的媒介是怀旧。刘庆邦说过:“短篇小说是一种比较接近诗性和纯粹文学的文体”,“短篇小说之所以那么美,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类对美的向往和理想,是一种精神重构”[6]。短篇小说最适合表达怀旧,不仅仅因为怀旧是对美好岁月的回忆,而且因为怀旧的过程是一种精神重构的过程。怀旧不是对过往岁月回忆的全部呈现,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标准对回忆的净化与遴选。如果说回忆可能按照过去的原样再现历史,怀旧则是对历史断片的审美观照。“怀旧的‘看’不是无目的的,其‘看到的过去’也并非完整,甚至未必真实,怀旧必定是一种有选择的、意向性很强的、构造性的回忆。”[7]39由此可见,怀旧是对过去的删节和缩写,同时也造成日常生活逻辑的空缺和断裂。体现在文本中就是“因果”关系的隐匿。失去了因果,小说在表现故事情节方面就显得零散,跳跃性比较大——当年有人就是以此指出《呼兰河传》不是小说:“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8]与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较少受到因果关系的限制,在表现主体偶然生发的思想情绪方面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当然,短篇小说并非是一点逻辑性没有,只不过所遵循的是情感逻辑而非事实逻辑。就此意义而言,刘庆邦选择了短篇小说是因为它更适合怀旧的选择性心理机制。
英国社会学家基斯·特斯特认为:“怀旧/恋乡感可能并非一种非历史性的常项,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感。相反,只有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刻,才有可能产生怀旧/恋乡感。”[9]怀旧需要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生,而特定情境又非具备本质性,也不是怀旧主体的故意创设,具有刹那闪回、转瞬即逝的特点。怀旧的这种“突然袭来”的偶发性特点及其刹那间的感受也只有短篇小说能迅速反映出来。就像刘庆邦所说:“短篇小说的力量,还在于它的快捷……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相比,写一篇短篇小说所需的时间毕竟少一些,出手毕竟快一些。”[10]
不能说怀旧的文学表达就一定得选择短篇的形式——《呼兰河传》《长恨歌》等经典的怀旧之作都是长篇。但从文学史来看,怀旧作品却大多集中于短篇领域,比如鲁迅、沈从文、汪曾祺、林斤澜等的小说。对于刘庆邦而言,怀旧情结尤其浓郁,记忆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童年和乡土的因子,与故乡的大平原“有着割舍不开的情愫”[11]。建基于个人记忆之上的怀旧使刘庆邦在短小的篇幅中找到了抒情达意的最佳方式。尽管他写出过《红煤》《平原上的歌谣》《遍地月光》等长篇小说,但真正体现出刘庆邦文学价值并被读者所认可的还是他的短篇小说。
汪曾祺说过:“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份,把散文、诗融入小说。”[12]77刘庆邦的小说和他所师承的汪曾祺以至于沈从文的作品一样,呈现出明显的散文化结构。换句话说,刘庆邦的小说是散文化了的小说。《鞋》《梅妞放羊》《种在坟上的倭瓜》《红围巾》《燕子》《黄花绣》等小说情节淡化,结构散漫,但在近乎无事的叙述中却散发出绵绵不绝的情绪和韵味。
对散文化文体的选择与作者怀旧情绪表达相关。“散文化小说文体的表现性特征与创作主体自我内在关怀的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作家写作和坚守散文化小说的内在动力机制。”[13]在文学体裁中,散文和怀旧有着本能般的亲和关系。散文是怀旧的产物。散文的长处不在于叙事,而在于情绪的抒发,是对逝去美好岁月的回望和挽留。怀旧也是对遗留在时间长河中价值片段的审美体验,是主体精神遭遇现实生活损伤之后转向过去打捞的情感补偿。就像沈从文所说:“若能温习过去,变硬了的心也会柔软的!到处地方都有个秋风吹上人心的时候,有个灯光不大亮的时候,有个想从‘过去’伸手,若有所攀援,希望因此得到一点助力,似乎方能够生活得下去时候。”[14]怀旧不可能回到过去,时间的不可逆性使怀旧主体只能站在此时此地对遥远的过去做想象性还原。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白日梦,怀旧同样是白日梦。如此看来,以怀旧为情感基调的创作主体采取散文化结构编织小说既是出于审美追求和自我表达的需要,也与怀旧的散文化内容相关。刘庆邦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写作的过程就是审美的过程,哪儿美,我们就得往哪儿写。”[15]“哪儿美就往哪儿写”也就是心绪流动的过程,行文散漫,却处处受着怀旧情绪的牵引。
怀旧情绪的散文化表达也与生活结构本身有关。汪曾祺认为,应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结构作品[16]。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日常化的。在日常生活惯性中,能够引起人生发生重大变故的矛盾和冲突仅是例外。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活本身就呈现出散文化结构。当以散文化方式表现生活,推动情节发展的矛盾张力就会淡化。尖锐失却了锋芒,冲突抽空了紧张。即如汪曾祺所言:“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12]79怀旧也是对生活硬度的软化处理,在一种流动的情绪反应中重构真善美和谐一致的理想化情境,一个心灵乌托邦的再现。因此,怀旧在美学风格上偏向于柔美。出于怀旧美学表达的目的,刘庆邦对小说进行了散文化处理。就像他说的那样:“小说所传达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关注的是人类心灵的历史,它是一个再造的慰藉人们心灵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小说创作从来都不是人类坚强的表现,而是脆弱的表现。”[17]
对古典文学“审美趣味”的迷恋和追寻同样影响到刘庆邦小说的散文化建构。从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发生的文学机制来看,小说散文化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杂糅性、诗词的抒情性相关,“较为自觉地承传了中国传统美学之精华,如意境的感受、营造和情绪的抒写、表现等”[13]。这种中国传统美学的“精华”在刘庆邦那里就是一种“审美趣味”:“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我们应从中继承一些什么。我们不可能全盘继承,只能有选择地继承。……我们继承的不是实的东西,而是虚的东西。这个虚的东西就是审美趣味。”[18]刘庆邦对古典文学的接受有些被动性:他是在祖父的怀抱中“不知不觉间、潜移默化中”无意识接受了古典文学的熏陶。无论是童年时期的无意识熏陶,还是长大后的有意识阅读,古典文学中的“人物、情节和细节,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信仰、世界观、价值观等”[18],构成了刘庆邦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他的文化性格。古典文学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潜隐表明对传统的依恋也是怀旧文学的情绪主题之一。刘庆邦在以文学表达怀旧情绪时,自然会以古典文学的“审美趣味”作为美学原型。
二、反速度叙述与意义呈现
刘庆邦的小说不以讲故事为主,读他的小说可以读得很快,经过几番跳跃和省略就可以明白小说要表达的大致意思。这不是阅读刘庆邦小说的方法,过程简化的结果就是文字和意义的双重失落。刘庆邦以缓慢的甚至是凝滞的叙述抵抗着阅读的速度,这样的小说需要用心去品读,让心灵而不是眼睛去直面氤氲在字里行间的情感和韵味。
刘庆邦减缓小说叙述速度的文体策略是闲笔和细节的大量使用。所谓“闲笔”就是与故事情节发展关联不是很紧密的句子和段落。在小说整体氛围中,闲笔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刘庆邦将“闲笔”称作“综合形象”,“综合形象是短篇小说中的主要形象背景,是对主要形象的铺垫或烘托”。“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增加短篇小说的立体感、纵深感和厚重感。”[19]闲笔可以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如《红蓼》《燕子》由写雨开始,《黄花绣》由雪写起,《梅豆花开一串白》的开始写到院子里的梅豆、菊花、鸡冠花、柿子树、鸽子、鹅等。大多数闲笔则是在行文过程中,笔触犹如平地流水,遇到某物某景便止步不前,以三五句话对其描神绘状。
细节的大量使用更是减缓小说叙述速度的主要方式。细节的出现意味着故事时间的中止。不断涌现的细节片段淡化了情节,破坏了速度的连续性,从而最大化地传达了文本的诗意内涵。刘庆邦对细节非常重视,赋予细节以本体性意义:“世界是以细节的形式存在的,我们看世界,主要是看细节。我们捕捉到了细节,就看到了细节。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细节,等于什么都没看到。如果抹去了细节,世界就是一个空壳。”在刘庆邦看来,细节同时也具有主体性特征,细节描写的不同构成了作家文体风格的区别:“细节是一篇小说的真正胎记,小说与小说之间的差别也体现在细节上。”[20]他所师从的汪曾祺也有类似的说法:“细节,或者也可叫作闲文。然而传神阿堵,正在这些闲中着色之处。善写闲文,斯为作手。”[21]刘庆邦小说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比如获奖小说《鞋》,守明对“那个人”名字的呵护、看彩礼包的反应、做鞋时的想象、针脚花型的选择……细节的铺排悬置、延宕了情节的进展。甚至如果不是小说结尾的“后记”,人们也许会忽略情节的存在。刘庆邦认为:“细节的好处在于它仍是形象化艺术化的东西,到头来还是很含蓄,很混沌,给人许多联想,使短篇小说纸短情长,开拓出辽阔的空间。”[22]刘庆邦的小说情节大多溶解在丰富的细节中。阅读小说也就是在内心抚摩、赏玩细节的过程,在细节涌入眼帘的同时,接受主体会调动起全部感知体味文本的诗性魅力。
刘庆邦小说中叙述的减速与他的怀旧意识有关。在怀旧的审美冲动中,刘庆邦试图存留住那些永恒的东西——人性与美——重建一座圆融和谐的精神家园,让疲惫的心灵驻足于此,在对永恒的体验中修复被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无穷的欲望撕裂的残缺自我。
与缓慢、静止的传统生活相比,“速度”代表了现代生活精神。从蒸汽机火车到磁悬浮列车,从电报到手机,现代生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速度的变化,而休闲时尚的兴起、欲望消费的盛行、快餐文化的流行也都是现代生活速度化的结果。麦克法兰曾经指出:“可以看到,时空结构已开始变化。由于通讯系统的改进,距离缩短了。由于城市生活的狂热节奏强加于社会的广阔领域,事件的发展更迅速了,整个生活的节奏也加快了。”[23]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速度的加速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与传统社会的断裂,而且使现实生活失去了整体性和连续性,社会呈现为脱序状态,心灵折射出的是生活的碎片。人们越来越难以把握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越来越趋向于对外部世界做即时性和当下性感受。现实在心灵上的留影如蜻蜓点水,真实感在心理节奏的快速变化中稍纵即逝,灵魂再难找到一个稳固的价值支点,人在奔波于速度带来的欲望追逐中陷入意义的真空。
现实生活速度化影响到文体的变迁,在小说中的表现就是越来越重视故事的讲述。故事越讲越精彩,越来越好看。事件的连续不断使故事高潮迭起、悬念不断;或是多个事件前拥后呼、挤挤挨挨,让人目不暇接。小说营造出新闻的在场感,而忽略了事件背后隐含意义的深度开掘。就像顾彬批评的那样:“中国当代小说集中在于故事,不在于人的心。”[24]
当代小说的叙述速度与现代生活速度表现出同构关系。在文体表现上就是生活的表象化和碎片化,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比如《秦腔》《兄弟》《尴尬风流》《万物花开》等小说中表现尤为明显。速度重塑了人们的感知经验,对时间和空间的敏感超越以往,“此时此地”成为确证自我存在的内容要素,但同时也成为自我分裂的起点。就像学者赵静蓉所说:“对速度利益的享用是以丧失对生命情绪的细腻感受为代价的,而缺乏后者,现代人就难以在瞬息即逝的生活表象背后寻找到意义、价值和信念的归宿,从而无法确切地把握生活把握自我。”在这种情况下,“怀旧作为一种‘反速度’的或‘倒速’的心理冲动才应运而生,它所体现的正是现代人在迅疾飞逝的岁月中想要记住什么、留住什么或拥有什么的心理”[7]331。
刘庆邦对小说叙述速度的减缓就是怀旧心理与现代速度对抗的结果。他认为:“小说所传达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关注的是人类心灵的历史,它是一个再造的慰藉人们心灵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17]因此他在作品中以大量的闲笔和细节致力于对人心、人性、爱情、死亡做静物素描式处理,它们所包含的诗性意蕴在怀旧空间中自由敞开。刘庆邦在怀旧中赋予永恒以时代价值,以此为锚,牵坠住飞逝的时间。来自“过去”的“神性和诗意”[17]为主体所召唤,纷至沓来,散发着来自源头的精神之光,缓解、抗拒着时间的不可逆性带来的生存焦虑和忧伤。反速度叙述在时间静止状态下使笔触延伸到生活的皱褶之处,揭示了被速度遮蔽下生活的应然状态,意义也因此而悄然呈现。
三、语言的乡土性与诗意传达
刘庆邦对语言非常重视,在多篇文章中谈到过语言与文学、语言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要判断一个作者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最直观的办法,就是先看他的文字是不是有个性,是不是打上了心灵的烙印。”[25]163“短篇小说的味道就在字里行间。”“作者以不同的心性和气质赋予语言文字,所产生的作品味道就不一样了。”[26]无论写景、写人还是写事,刘庆邦总是以一种平淡的语言娓娓叙来,不夸张,不矫饰,如乡间泥土般的质朴,与之相伴随的则是缕缕诗意:
棉花地里陡然飞起一只鸟,她打着眼罩子,目光不舍地把鸟追着,眼看着那鸟飞过河面河堤,落到那边的麦子地里去了。麦子已经泛黄,热熏熏的南风吹过,无边的麦浪连天波涌。守明漫无目的地望着,不知不觉眼里汪满了泪水。
——《鞋》
一群绒团团的小炕鸡跑过来,像是一致要求梅妞姐姐把它们也带上,它们也想到外面去玩耍。梅妞嫌它们还小,不会躲避饿老雕,扬着胳膊把它们撵回去了。小炕鸡们仰着小脑袋叫成一片,似乎对梅妞只跟水羊好不跟它们好的做法有意见。
——《梅妞放羊》
当他向高玉华接近时,高玉华又向前走去。他舍不得高玉华走,只得站下。只要他站下,高玉华就站下。他们在夜幕下走走停停,没有接触,也没有分开。在走动中周文兴嗅到了高玉华的体香。停下来时,周文兴听到高玉华有些急促的呼吸。高玉华还咳嗽了一下,她咳得轻轻的,像是用咳嗽告诉周文兴,她真的是高玉华。
——《夜色》
刘庆邦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平易自然。他认为:“强行给汉语穿上燕尾服,总是给人一种舞场上的表演感。”[1]因此,“对一些流行的时髦的语言,我们都应尽量不用”[17]。从以上几段文字可以看出,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过多的修辞,而是以极为简洁的词语直面对象本身,如简笔画般,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事物情貌;又如轻音乐,在轻盈明快的节奏中传达出温馨自然情调。这种语言效果就是刘庆邦追求的小说的通感:“从一定意义上说,小说也是视觉艺术,文字组合要美。小说也是听觉艺术,要有好的节奏感。”[1]
与汪曾祺一样,刘庆邦追求语言的口语化、日常化表达。但与汪曾祺不同的是,他的作品中少了一些奇崛的文字,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雅趣。他的语言文字更多来自民间、来自乡土,平淡而简洁。宋代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平淡不是平常,简洁亦非简单。平淡的后面是诗意,简洁带来的是韵味。同样的文字,即使是日常口语、俗语俚语,在不同作者那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照刘庆邦看来,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文字的使用是否有个心灵化的过程:“用心血把文字浇灌过,浸泡过,并打上我们心灵的烙印,那些文字才有可能属于我们。”[27]经过作者心灵打磨之后的文字因此就有了“灵性”:“我们锤炼文字,对文字久久凝视,目的是要启动我们的灵感,赋予文字以灵动之气。没有灵感参与的文字是僵死的,可憎的。注入灵动之气的文字才是亲切、自然和飞扬的。”[28]语言与主体相互指涉:“文字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在使用文字,而是在使用自己,使用自己的心。”[25]163这样从心灵里面孕育出来的文字才能够更有效地传达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情绪。
汪曾祺认为:“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的。”[29]刘庆邦小说的语言在审美体验、诗意传达、家园追寻等方面和怀旧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美学效果。
从审美体验的发生来看,语言和怀旧都是主体心灵化的产物。刘庆邦认为:“中国的汉字就那么几千个,祖祖辈辈流传下来,你用我用他也用,带有很大的公共性。有人跟汉字打了一辈子交道,说不定没有一个字是属于他的。而有的人或许只写过一封信,那封信里所使用的文字却是属于他的。”[27]其原因就在于语言是否经过心灵化处理。刘庆邦对语言文字的锤炼也就是对过往岁月中那些美好情愫的反思和怀想,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30]怀旧是一种诗意化的行为,是一种抚慰生命的精神活动。因此,怀旧思维也就是一种审美思维,对怀旧的把握和描述最终要外化为语言形式,而怀旧主体也须经语言之舟摆渡到过去。怀旧主体总是在静观默想中品味生命“诗意地栖居”的自在和自由,并由此获得一种久违了的“家园感”。在怀旧意识的濡染下,童年与故乡、自然与过去呈现出的是未经修饰的本色之美。表述这样宁静自足的审美心态和素淡静雅的情感特色,自然需要文字的质朴自然。文字流泻于笔端,思绪也就徜徉于往昔。经过心灵化处理之后,语言与怀旧共同散发着诗意灵光。
从小说语言的文本呈现来看,它和怀旧一样都注重诗意传达。刘庆邦的小说中有着大量的方言俗语,也许方言更能传达出怀旧的审美内核和诗性色彩。在海德格尔看来,方言是本真的源初语言,是语言之母。在聚焦意义上,是存在的本真之家。在方言中栖居着乡土乡情,栖居着家乡。也因此,方言天生就比普通话和打磨得光滑的交往语言更能诗性地言说[31]。刘庆邦对语言的选择几乎是一种本能性反应:“语言文字仿佛已溶入我的血液中,成为我血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贯通和活跃的部分。换句话说,我笔下的文字仿佛是我血液中的添加剂,有了添加剂,血脉就畅通,带劲。否则就血液粘滞,以至头脑昏昏,光想睡觉。”[32]当他表现那生活了19年的流淌在记忆的血管里的家乡时,方言便会不由自主地汇至笔端,乡风民俗迎面扑来。
从终极目的而言,主体在语言和怀旧中都可以追索到灵魂栖居的家园感。海德格尔给予语言以本体意义,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其实,怀旧也是一个寻找和重构精神家园的过程。一般而言,怀旧主体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适和焦虑,他转向过去,向故乡、童年、传统等寻求意义。当然,怀旧既不可能重返历史情境,也不可能做到对其现实化和实体化。只有借助想象,怀旧主体才能将逝去的岁月和美好的情感转化为心理现实。就像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作序时指出的那样:“要紧的不是生活在幻觉之中并且为这些幻觉而生活,而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寻找失去的乐园,那唯一真实的乐园。”[33]怀旧既然不可能回到过去,只有在语言的表述中怀旧主体才能寻找到一种家园感;那么,怀旧的文学表述就是为“精神家园”赋予形式意义。语言与怀旧在家园的意义上合而为一,为淹没在凡俗庸常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主体缓解和移除现实痛感提供着来自过去的精神安抚和美感体验。
四、内向化视角与氛围的忧郁
怀旧的产生是主体在现实生活中自我认同发生危机的结果。生活节奏的加速和欲望的倍增造成了个体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断裂,生存意义的匮乏会使主体本能地转向永恒存在的并且能为自我把握的过去,以此消除陌生的现实世界带给主体自我的惶恐不安和焦虑忧愁。因此,怀旧是主体自我认同的需要,是在对自身生命历史的回溯体验中重构自我发展的精神优势。由此可见,怀旧主要是一种心理审美体验,是对过去生活细节的想象性还原。那么,怀旧的文学表述势必会取一种内向化视角,在对主体心理的细致剖析中再现过往人生的感觉、经验和印象。
刘庆邦在叙述视角方面表现出了内向化倾向。刘庆邦写小说有一个宗旨,就是“贴着人物写”,“用心去贴作品中人物的心,只有做到了与人物贴心贴肺,才能把人物写出一二”[34]。刘庆邦的柔美小说大多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展现人物心理的隐秘与意识的潜在活动。“贴着人物写”是刘庆邦从沈从文、汪曾祺、林斤澜那里学得的写小说的“诀窍”。与他的老师们多采用侧面烘托表现人物不同,刘庆邦总是直面人物的心理活动,试图“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独立完整的心灵世界”。所谓的“心灵世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它来源于现实,却是反现实的,与现实并不对应。它是超越于现实的独立的心灵建筑。二、作者把从现实中得来的材料打碎、分拣、消化、处理、建设,整个过程都是作者的心灵在起作用。……三、现实是雷同的、千篇一律的,而每一个真正的‘心灵世界’因人而异,都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5]《鞋》《梅妞放羊》《种在坟上的倭瓜》《谁家的小姑娘》《女儿家》《怎么还是你》《走姥娘家》《户主》《拉网》《远方诗意》等小说,无论是第三人称叙述还是第一人称叙述,作者聚焦于人物心理活动,在心灵细节的丰富和情绪的颤动中传达出人性的幽微与神秘。
归根结底,文学作品是作家的心灵产物。采取内向化视角也是刘庆邦更好地表达自身情感的需求,是以文学的形式确证自我的一种方式。他曾经就文学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表露过:“通过写作抓住时间,通过抓住时间抓住生命,建立和世界的联系。”[3]“写小说的过程就是寻找自己的过程,寻找自己心灵的过程。”[35]自我的介入,使作者很难冷静地去对生活做客观描述,他笔下的人物、事物、景物皆携带上主体的情感因子。写小说也就是写自我。就像刘庆邦所说:“短篇怎么写,我有一个说法是‘在无文处作文’,在题材中找到自我,找到内在的情感动力,而不是只靠思想、逻辑去推动,这样才有可能写好。”[36]在内在情感的驱使下,刘庆邦将自我意识投射在作品人物身上,赋予他们以生命意识和美好情怀,作品人物也因此承载着创作主体自我救赎的意义。就好像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那样:“有时我莫名地伤感起来,脆弱得不能自已。这时我意识到,又该写一篇小说了。当我进入写作过程,心里果然好受些。这么说来,写作好像是自我救助的一种方式。”[32]
怀旧一般会被指责为保守衰朽或是颓废悲凉。其实,这种指责恰恰道出了怀旧的反思性特征及其文化意味。怀旧的价值固然在于重构过去的美好,但主要的还是为沉沦于世俗泥淖中的主体提供价值支撑,以从历史深处涌出的人文精神为支援批判现实。怀旧的诗意和美好来自于现实的非诗意和不美好,来自于主体心理、情感的伤害和失落。在对过去的诗意化抒情中,弥漫着的是主体挥之不去的沉重的忧郁情调和生命受挫的悲悯情怀。沈从文说过,“美丽总是使人忧愁”。也许,在现在和过去碰撞中生成的怀旧,其情感本就不是单质透明,除了美好诗意外,“其中也不乏噫嘘、惋惜、失落、忧郁、愁苦等消极的成分”[7]69。
刘庆邦认为自己的性格中有一种忧郁的东西存在:“性格深处有感伤的东西,忧郁的东西。”[3]忧郁既来自于残缺家庭带来的伤感,也有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坎坷经历的痛苦记忆,更多的则是对那些美好东西渐逝渐远的痛楚和现实生活越来越丑陋、平庸的惋惜:“由于大面积的挖地烧砖,几千年农耕文明时代留下的土地被开肠破肚,挖得千疮百孔……显得突兀而丑陋。更可怕的是,人们的思想受到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浸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变成了金钱关系或利益关系。张家帮李家干一点活儿,要事先讲价钱,干完活儿用现金结算。夜间如果一家遭到抢劫,不管遭劫的人家如何呼喊,别的人家听见了如没听见,都闭门不出。这些负面的东西让人痛心,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没办法。”[4]289
创作主体的忧郁影响到柔美小说的整体氛围,并且体现出某种刻骨铭心的人生悲剧意味。河生(《少男》)因为姐姐的定亲而“情绪低落,沉闷,还有一些伤感”,当他想到有一位女同学会因他做了条新裤子而多看他几眼时,“心里悄悄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有些柔软,有些滋润,还有些漫无边际的忧愁……”;守明(《鞋》)想到自己将来就要在河对岸庄子的地里干活,也要在那个不知多深多浅的庄子里住,“她就愁得不行,心里就软得不行”。平路(《小呀小姐姐》)是个小罗锅,虽然小,却已懂得死的含义。当母亲叹息着说“平路,你死了吧”时,“平路没有对母亲的话作出答复,眼里却涌满了泪水”。成长、爱情、生命在对主体构成诱惑的同时,又使他们生发出一丝莫名其妙的恐慌情绪。渴望中有拒绝,拒绝之后又是失落和惆怅。其实,这种拒绝又何尝不是创作主体抗衡未来的心态体现。
人性是美的,这种美的东西仅只是存留于过去的幻影。在对过去所做的无奈的挽留中,此时此地人生的悲剧意味渐渐凸显。陈思和先生曾经谈到过读《鞋》时的感受:“我记得一次参加评审鲁迅文学奖时读到了《鞋》,我起先一路读下去,恍惚是在读孙犁的小说。我不断在问自己:我们还需要重复孙犁写过的境界吗?但读到最后的补白,我才感到了一阵刺心的悲哀。那个补白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结尾,也不是为了真的说明这是一篇作者的情场忏悔。有了这个补白我们才意识到,小说作者以全力讴歌的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7]刘庆邦小说体现出一种日常悲剧。与西方悲剧或是中国传统悲剧比起来,没有呼天抢地的场面,没有人心撕碎的渲染。但因为日常生活的亘古和循环,悲剧性从而成为生命的胎记。悲剧的宿命意味难免使人陷入悲观绝望境地,被抛在此的孤独无援更增添了人生凄凉感,但人们也可以因此更好地珍惜生命的每时每刻,细细品味和享受苦短人生中的幸福与感动,体现出一种“向死而生”的积极意义。这也许是刘庆邦小说在哲学层面与存在主义的相通与契合之处。
总而言之,怀旧是刘庆邦回叙乡村、童年、过去的审美动力,也影响到了其柔美小说的文体生成和呈现。怀旧不仅确证了主体自我精神的优势,而且为文体的选取奠定了心理基础。在怀旧意识的烛照下,刘庆邦有了文体的自觉。这是刘庆邦小说风格稳定和成熟的标志,也使他在当代文坛独具一格,有着不可取替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