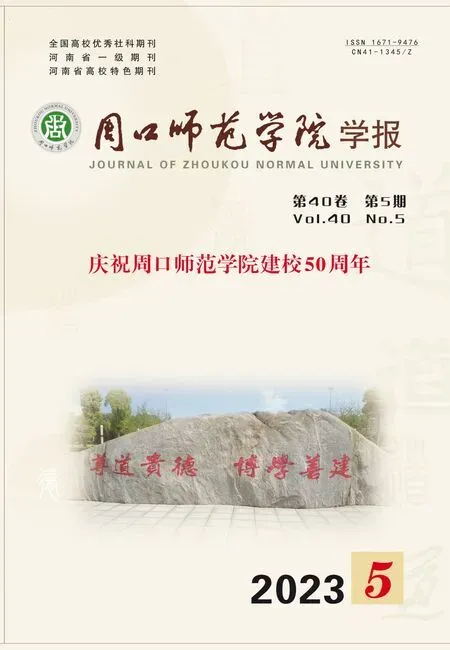广东徐闻藤牌功班舞彰显的中国精神阐释
——基于身体展演与话语叙事的分析视角
韩青松
(湛江科技学院 教育学院,广东 湛江 52409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域中多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这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精神标识、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的重要方式。徐闻藤牌功班舞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当代徐闻人民在共同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共识。其作为地域性身体文化符号,历经500多年的裂变、转型、融合与创新,已成为雷州半岛极具代表性的民俗体育事项,不仅在纵向历时性的话语叙事中获得发展支撑,而且在横向共时性身体展演的交流、共享与互鉴中获得发展活力。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制高点上,需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重新定位藤牌功班舞,从培育中国精神的独特视角重新认知藤牌功班舞,将其从一般民俗体育事项提升为突显中国精神的实践载体。
据笔者考察,藤牌功班舞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最南端徐闻县迈陈镇东莞村,其参与抗倭斗争及与宗族融合发展的“故事”被不同时期的群众讲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故事”实例,这些故事与宗族先祖、宗族繁衍等密切相关。其作为宗族文化的身体象征,通过身体展演和话语叙事表达对宗族先辈的尊崇,形塑族群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和新举措视野下的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在民族形式和思想内容上,都极大地拓展了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现有研究多以讲好中国故事作为研究起点,鲜有学者从身体展演与话语叙事的角度开展研究,缺乏体育故事的本体论研究。换言之,民俗体育研究所重视的话语叙事与现有文献积累形成极大反差,这一现象引起笔者深思。鉴于此,旨在讲好蕴含在藤牌功班舞中的故事叙事,通过身体展演和话语叙事双重逻辑阐释其蕴含的中国精神,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以期为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理论探索与赓续传承提供价值参考。
1 研究方法与史料梳理
为清晰化、脉络化呈现徐闻藤牌功班舞身体展演与话语叙事的理论逻辑,课题组成员采用“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法”“口述史”等多种形式,分别于2022年6月4-5日、2022年9月14-16日、2023年2月1-2日先后3次深入广东徐闻县迈陈镇东莞村,重点围绕社会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族规祖训等方面开展田野调查;主要选取徐闻县文化馆馆长,藤牌功班舞代表性传承人、总指挥、组织者、参与队员等作为无结构访谈和口述对象。在3次调查期间,课题组共拍摄照片近400张,视频近4小时,访谈录音5小时,并及时记录了大量的田野笔记,搜集了第一手素材和资料,以获取最自然状态的真实材料和数据。
2 徐闻藤牌功班舞彰显中国精神的理论逻辑
2.1 身体展演:徐闻藤牌功班舞形态演进脉络及演绎程式
藤牌功班舞由明代万历年间戚继光抗击倭寇藤牌阵法演变而来,是集军事训练、武术和古乐为一体的男子群舞,表现了沿海军民为捍卫海上丝绸之路而抗击倭寇的顽强斗争情景,讴歌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其形态演进脉络及演绎程式变化如下:其一,将逢双年演练改为每年必训练、展演。五百年来,东莞村俗传,藤牌功班舞娱神健体演练系逢双年活动(即三年两拜)。为适应新形势发展需求及防止时隔太久,日渐生疏,现改为每年春节、元宵节必聚众弟子训练、展演;其二,新老结合,以老带新,促进传承。原省级传承人郑庆荣师傅年迈体弱,重于言传,而套路、形意身教示范重任由钟茂松实施。尤其是对执掌难度最大,变幻莫测的三钗队并对四个钗队的攻防套路、舞(武)者形意的一一示范实施,两代传承人老幼结合悉心调教,收效显著;其三,对过分庞大的队伍进行精简,以利于舞台调度及身体展演。原主战场上四钗队,每队16人,合64人;母龙队长32米13节,舞者32人;子龙长22米11节,舞者28人,加上司鼓、掌钹、旗手、总指挥及后勤管理人员共134以上。精简后,战场四钗队,每队12人,合48人,比原64人减少了16人,双龙队精简4人,共减少了20人。
藤牌功班舞以村落为传承场域,以村落宗族男子群体为传承主体,以家族和师徒传承为主要传承方式,在节日庆典、宗族祭祀等场域展演。目前藤牌功班舞的演绎场域已推广到诸多领域,不仅在村落及社区传播,已在武官训练及中小学等教育场域广泛开展,逐渐成为日常化、常态化的身体展演形式。如第19代传承人郑妃雄和郑平奋到徐闻迈陈镇角尾乡和西连镇等地开馆授徒,到东莞小学和角尾乡放坡小学等学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2017年11月5日参加首届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开幕式展演。2018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参加珠海市斗门区第十四届民俗文化艺术节大巡游。2023年1月参加徐闻县“乡村振兴-工商联(总商会)杯”舞狮、武术比赛。不同实践场域的身体展演,旨在倡导多方位、多渠道推动文化的交流、共享与互鉴。作为一种“身体文化”的特殊载体,藤牌功班舞起源于抗倭斗争实践,根植于节日庆典,依附于宗族祭祀活动,以自在的形式将民族意识、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融入村落社会成员的生活血脉之中,自发地存在并发挥规范作用[2]。尤其在持续了三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藤牌功班舞的发展受到严峻考验,因此需借助以地缘为纽带、以血缘为根基的共享场域身体展演,使民众更易体悟其先辈所赋予的身份象征与精神力量。
2.2 话语叙事:徐闻藤牌功班舞的历史叙事
2.2.1 藤牌功班舞参与抗倭斗争的历史叙事
在藤牌功班舞参与抗倭战争实践所演绎的历史“故事”中,戚继光的鸳鸯阵常被作为“故事”叙事的主要部分。明天顺六年(1462年)由于西寇(安南和葡萄牙海盗)的骚扰作乱,作为抵御倭寇及海盗的侵凌骚扰的军事要塞,徐闻县土城被破,迁徙海安所城,至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才迁回故地,历时达39年之久。这段时期,东莞圩也深受其害,百姓惨遭荼毒。据藤牌功班舞传承人口述,面对强敌,东莞村民为保卫家园,维护圩集安宁,商贾出资,聚青壮年习武,成立堂口称功班。缘份所至,浙江一武林教头,云游四方,抵广西合浦,拟泛舟琼州,因海上潮流所追迫,靠东莞港。东莞圩繁荣兴旺,且同讲闽南语,引教头驻足。数日圩上习武热闹,吆喝之声震天动地,令其关注,移步武场,察看有日,悉习武缘由,自荐为师。他针对西寇敢于进犯,必有备而来,可东莞圩无城堑可据,须避短扬长,制定既要单兵作战,更要众人合力攻防之策,而力推戚家军抗倭藤牌阵。经东莞堂口有识之士认可,取名“功班藤牌阵”。此阵攻防兼备,刚柔相济,疏密相通,动静结合,用兵灵巧。攻,有32件长短兵器结合,远距攻上,有长矛、狼筅、钩镰枪。近战袭下,用短兵器。守,有32个藤牌配刀变化多端,时而长龙,时而结墩,时而相吞,时而圆山,布防险恶,稳藏杀机。功班练成藤牌阵,狠狠打击了敌寇嚣张气焰。虽然,目前并无确切资料证实戚继光的“鸳鸯阵”就是现在的藤牌功班舞,但据史料记载及其代表性传承人普遍认同藤牌功班舞以戚继光的军事布阵为历史缘起,将藤牌功班舞与戚继光抗倭战争历史事件关联起来,并通过“人为加工”逐渐演绎成为民间历史“故事”。
2.2.2 藤牌功班舞与村落宗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叙事
依据故事本体论,不难发现,藤牌功班舞的故事本体是基于宗族先祖而开展的,宗族成为话语叙事的逻辑起点[3]。在藤牌功班舞数百年的历史传承中,东莞村村民基于“英雄祖先崇拜”建构了与宗族祭祀互融发展的历史“故事”,“故事”在一代代人的叙述中,形塑了东莞村的宗族文化传统。据钟茂松、郑平奋等代表性传承人口述,东莞村居钟、郑、黄、招等姓,钟郑两姓的起水祖上都来自福建莆田,钟姓始祖钟宸湖,其后裔钟震国,是位武略骑尉(正六品),还有武举人钟铭泰、武秀才钟汝材、钟山楼、郑承贤。明代郑姓出了郑昊(黎源知县)、郑敬(乐安知县)、郑时宾(徽州通判)、郑时贤(隆安知县),他们祖籍均来自福建莆田。这些历史名人崇文尚武,“一文一武,一张一弛”,开馆授徒,形成堂口武功帮派。此外,东莞村俗敬奉西汉名将“飞将军”忠顺侯王李广、天妃圣娘、招宝夫人、青惠夫人、马大元帅、左顺风耳、右千里眼共7位神圣。经漫长历史进程,藤牌功班舞演化成为东莞村独特的人神同乐的传统习俗活动,并将其作为东莞村每年正月元宵节期间酬贶妈祖的开春巡游表演重要节目。在明弘治倭患时期,东莞村村民演绎了历史记忆中的“藤牌功班阵抗倭故事”,这种基于“英雄先祖崇拜”而衍生的“历史故事”不仅成为东莞村宗族文化象征,突显出艰苦奋斗、团结友爱的宗族尚武精神,同时也逐渐成为村落群体对自我认同、宗族血缘认同及中华民族身份认同[4]的理据。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场域的身体展演和话语叙事,无论是缘起于抗倭斗争所形塑的历史记忆,还是凝聚于仪式场域演绎所形成的身体记忆,从中孕育出的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等,为徐闻民众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形塑及其精神标识的挖掘与提炼提供学理支撑。
3 徐闻藤牌功班舞彰显出的中国精神内涵阐释
徐闻藤牌功班舞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对徐闻人民的生活、生产实践方式及情感样式有着深刻影响,使其在长期的赓续发展中孕育出独特的价值传统,这种独具特色的价值传统正是徐闻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核心。中国精神的挖掘与提炼离不开血缘、地缘根基,更离不开同源文化脉系,凝聚了本体文化的信仰、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与价值理念,是新时代徐闻藤牌功班舞最高层面的价值定位。因此,需以抗倭战争与宗族祭祀的叙事逻辑为现实依托和实践根基,立足身体展演和话语叙事关照藤牌功班舞蕴含的中国精神表达。
3.1 伟大创造精神:永葆生机的动力源泉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5]。善于探索,积极创新是中华民族永葆生机活力的不竭动力[6]。徐闻藤牌功班舞不仅创造性地指导徐闻人民将藤牌功班舞作用于战争实践,而且通过不同场域的身体展演指导其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蕴含的伟大创造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文化艺术创造。以徐闻藤牌功班舞为代表的民俗体育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尤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徐闻先民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抗倭战争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徐闻人民的强大创造力,发明创造了攻守兼备的近身格斗战斗队列—“藤牌功班阵”,不仅通过宏观叙事记录了他们大胆创造的事迹,帮助人民告别了战乱,并由此孕育了民族精神的创造性基因,而且是无数个普通参与个体的身体演绎和精神凝聚,蕴含着丰富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创造力,体现了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旨归。二是现代化传承与传播手段创新。现阶段,通过虚拟现实技术、5G技术及短视频技术等数字化传承方式,初步实现了对藤牌功班舞的唤醒、激活与复现。首先,在历时性方面,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将虚拟场景与现实场景进行融合,再现历史人物与事件,让当下的受众与历史人物对话,在互动中参与叙事,借助数字媒介,藤牌功班舞在参与式、沉浸式传播中,连接历史与现实时空,让接受者在虚拟在场的互动交流中进行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共享中华文化精髓。其次,在共时性方面,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的快速发展,让身处不同场景的人们与其进行共时交流,加速其在现代空间环境和社会场域中的仪式化呈现,凸显其对现代生活的新意义,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例如,2022新年期间,湛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举行“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非遗展演活动,为响应疫情防控号召,观众通过识别二维码线上观看直播,并将展演的形式与内容上传至抖音、快手、百度等短视频APP。以藤牌功班舞、人龙舞为代表的体育非遗文化在短视频中的“活化”现象的典型例子,是对“数字+文化”理念的全新阐释,通过数字媒介将藤牌功班舞创造性转化为社会共享的文化成果。
3.2 伟大奋斗精神: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支撑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5]伟大奋斗精神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支撑。徐闻藤牌功班舞彰显的伟大奋斗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锲而不舍的励志抗倭英雄效应。抗倭英雄所具备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心性,以及不畏强权、保卫家园的决心和斗志,将中华民族之尚武精神进行了演绎,藤牌功班舞也成为保卫战中的战斗“工具”,抗倭英雄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伟大的奋斗精神。二是战胜倭寇的伟大壮举。据藤牌功班舞传承人及习传者口述,他们的先辈皆参与到抗倭斗争中,与倭寇展开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同时还在记忆中存留了抗倭英雄的故事。这种抗倭斗争故事,在区域社会形成了广泛的精神宣传和凝聚效应,极大地鼓舞了民众保家卫国的思想斗志。此外,“抗倭战争”之所以在物质条件、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能取得胜利,与徐闻人民伟大的奋斗精神是分不开的,在抗击倭寇的关键时刻,以徐闻人民的聪明才智、辛勤汗水与巨大牺牲创造孕育出了优秀民俗体育事项藤牌功班舞,突显出了徐闻人民革故鼎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品格,藤牌功班舞表明了徐闻人民战胜敌军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与天斗、与地斗、与强敌斗的伟大奋斗精神。三是社会文化建设初见成效。藤牌文化的交流、共享与互鉴,不仅仅局限于身体运动的演绎层面,更重要的是经过历史故事的叙事和重演,将先辈们的历史遭遇在现代共享场域中场景再现,强化了村落民众的文化认知、血缘认知及身份认知等认同观,将中华民族尚武爱国的奋斗精神在这种场域中体现出来。此外,藤牌功班舞作为满足公众体育参与的健康因素和精神需求的社会文化因素,不仅使徐闻人民在努力拼搏与艰苦奋斗过程中始终坚持藤牌文化的守正创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价值诉求,同时能够通过身体展演获得健康需求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
3.3 伟大团结精神:维稳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石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5]伟大团结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在徐闻藤牌功班舞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伟大团结精神不仅体现在以攀登高峰、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为主题的藤牌功班舞缘起阶段,也体现在徐闻人民学习、参与和演绎藤牌功班舞过程中以团结协作、迎难而上、不怕挫折、健康快乐为主题的现代传承与发展阶段,更体现在以藤牌功班舞为代表的民俗体育事项作为独具特色的非正式制度参与村落社会治理所凸显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
藤牌功班舞起源与演变的过程,正是徐闻人民历经磨难、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的过程。拥有共同祖先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构成紧密团结、内聚力强、一致对外的精神命运共同体[7]。面对抗击倭寇的历史重任,徐闻人民正是凭借着勠力同心、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伟大团结精神,在较短时间内基本遏制住了敌军的强筋势头,初步稳定了局势、扭转了局面。徐闻人民讲述了令举世瞩目的“团结抗倭”故事,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充分彰显了伟大团结精神。藤牌功班舞蕴含的民族团结精神在新时代的彰显,得益于以下两个因素:其一,以徐闻藤牌功班舞的赓续传承与现代化发展是维持社会和谐与弘扬团结精神的文化基因。其二,徐闻藤牌功班舞作为独具特色的非正式制度在村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藤牌功班舞是徐闻人民抗击倭寇、抵御外敌,建立在人民群众祈求平安、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及村落宗族发展需要的基础上而衍生出的一种社会模式。其所蕴含的民间信仰、消灾祈福及神灵崇拜等民俗心理对乡村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规范和约束作用。简言之,藤牌功班舞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以通过非强制性手段规范村民的身体行为与社会行为,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和关系互依的开放性建构理念,突显其在村落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3.4 伟大梦想精神: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追求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5]。伟大梦想精神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创造和积淀出来的,也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8]。徐闻藤牌功班舞作为抗倭时期的经典文化遗产,需继续发扬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伟力,重塑人民群众刚健的民族性格、阳刚的民族精神的实践途径。徐闻藤牌功班舞彰显的伟大梦想精神,能够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价值观,助力体育强国梦。一方面,古代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自然条件与社会环境恶劣,可以说是偏隅南疆的荒蛮之地,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徐闻人民,“性悍喜斗、轻生敢斗”的野蛮性格,也导致了当地教育落后,人文凋蔽。藤牌功班舞涵养的伟大梦想精神,使其重视人的生命价值,更加关注健康、珍爱生命、热爱生活,改变其“轻生好斗”的陋习,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同时能够形成乐观开朗、积极进取、充满活力的人生态度,为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及农民健康文明生活提供实践指导。另一方面,藤牌功班舞源自藤牌武术,武术是培育人民群众“刚健自强”精神,凝聚中华民族“精气神”的实践途径[9],其最本源的价值是技击防卫[10],迎合了防御为主,攻击为辅的演绎阵法,攻防结合的十八式武术套路。徐闻藤牌功班舞中蕴含着藤牌武术的传统技击动作,凝聚着中国精神,汇聚着中国文化,承载着徐闻人的梦想,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其所蕴含的不仅是梦想,更是一种精神和品质,有助于唤醒与改善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理念。因此,需将藤牌功班舞放置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量,加强对其挖掘和阐发,不仅对体育强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其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徐闻藤牌功班舞作为雷州半岛最具代表性的民俗体育事项,历经数百年的岁月洗礼,在裂变、转型过程中与抗倭战争、宗族祭祀逐渐融合,通过仪式符号、族群认同及演绎场域形成多元化集体记忆。在身体展演和故事叙事场域化过程中凝聚了精神力量,彰显了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为内核的中国精神内涵,是徐闻人民抗击倭寇取得来之不易“决定性成果”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基于社会语境与传统话语所演绎的中国故事,是基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所形塑的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及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路径。因此,继续维稳徐闻藤牌功班舞身体展演和话语叙事的实践逻辑,迫切需要当代学者对其所蕴含的中国精神内涵进行挖掘、提炼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