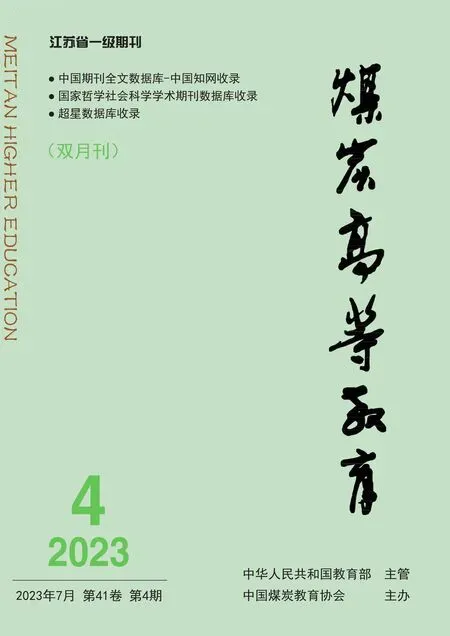论黑死病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
陈璇木子
14 世纪肆虐于欧洲大陆上的“黑死病”是整个中世纪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瘟疫之一。由于病患死亡后皮肤上存在黑色斑块故得名黑死病,现代人推测为腺鼠疫的暴发[1]1。该病最大的特点是传染性极强,并伴随着高死亡率和反复性。短短几年间,这种传染病横扫了中亚、北非和欧洲,其恶劣的影响被后人称为“大灾害、大死亡、大萧条”[2]24。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中所呈现的黑死病给佛罗伦萨带来的沉重打击也正是当时整个欧洲社会的缩影。受限于中世纪的科学水平和蒙昧认知,当时人们对黑死病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未见成效。但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的政治、宗教、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在“恶”历史的浇灌下,在阵痛中实现了跃升和交融,经历着转型与裂变[3]。黑死病虽然是一个偶然性的历史事件,但如马克思所言,“如果偶然性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么历史本身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4]。本文基于对部分史料的梳理,分析中世纪大学在黑死病面前的表现,把握黑死病与中世纪高等教育的关系,以期大致还原该时期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样貌。
一、黑死病对高等教育人口的影响
黑死病于1348 年在欧洲暴发,其后百年经历了多次反复。历史学家们认为1353—1500年间欧洲大约出现了18 次大规模的疫病反扑。“到1480 年前,西欧城市中平均每6~12 年就有一次疫情报告,也就是每代人碰到2 到4 次,此后则是15~20 年一次。”[1]11这导致学者们将黑死病的作用无意识地夸大,将其视为引发整个西欧经济社会巨变的直接原因。实际上,黑死病对整个欧洲大陆最直接深刻的影响是人口的大量死亡[5]。“1348 年黑死病前夕,英格兰、威尔士的总人口在四五百万之间,1377 年下降到250 万,1525 年时英格兰总人口仍然不足226 万。”[6]203由于当时编年史和其他材料付之阙如,学者在统计瘟疫致死人数时很难得到一个准确描述欧洲人口下降的具体数据。一般来说,基督教会的主教登记簿中的数字对于当时人口数据的描摹来说意义重大[2]105。目前普遍承认的是,黑死病造成了14 世纪欧洲1/3~1/2 的人口死亡。不过,比恩 (J.M.W.Bean)认为,研究者会假定疫情必然导致人口减少,从而将教堂的讣告名单作为黑死病对人口影响的直接佐证,但这种结论没有确定的根据,因为讣告的原始手稿中并未标明死者死亡的具体原因[7]。所以,很难说瘟疫是当时造成人口减少的唯一力量,北部寒冷潮湿的气候以及灾荒可能才是更加致命的[8]。无论是何种原因,当时人口大幅下降造成了欧洲秩序的混乱,反复发生的疫病使欧洲社会经济难以稳定,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也只能在动荡中低效运转。
中世纪大学的师生通常居住于本地城镇中,而城镇恰恰是黑死病的重灾区。在大瘟疫期间,师生人员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死亡威胁,或患病致死或逃离居所[9]120-121。例如,1349 年剑桥大学国王会堂有16 名学者死于黑死病,会堂的负责人托马斯·鲍伊(Thomas Powys)及其他8 名学者也于1361 年2 月相继殒命[10]117。安娜·坎贝尔(Anna Montgomery Campbell)认为大约1/3 的欧洲知识分子领袖在这场流行病中丧生[11]108。不过有学者认为,尽管坎贝尔所征引的数据来源于黑死病后十年间的中世纪大学,但一些证据不具有强指向性,且调查样本过于局限和缺乏说服力。他们认为,14 世纪欧洲大学人口比例的下降应当更多地归咎于战争、宗教、疫病等多方面综合因素[12]。其实,早在黑死病暴发前,欧洲人口数量就已经有开始下降的趋势[5]207。也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是由当时耕作条件不利、饥荒频发、多地战争的爆发、人口出生率下降等原因所致[13]。所以,黑死病对于大学人口的影响可能远不及坎贝尔等人认为的那么大。例如,考特尼(W J.Courtney)调查了67 名定居在牛津的神学家,发现其中的61 人在 1350 年后死亡,1 人在黑死病前死亡,只有5 人死于 1348—1349 年间[14]700。
为什么学者之间的研究结论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其原因大概如下:其一,学者们依靠部分中世纪大学的传记登记册(Biographical Register)管窥该校人数[15]。然而,由于中世纪大学管理的开放性,登记在册的人数并非是大学总人数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大学都有登记册名录。其二,中世纪的学者们并不会长期稳定地居住于某一固定的地理位置,即使有些师生会长期居住于大学里,他们也仍存在短期内迁移的可能。而在很多关于中世纪高等教育的研究中,迁移人口是没有被统计在内的。其三,中世纪大学是“精英机构”,其人口的类别、层次及其比例与整个社会相比具有独特性,所以根据社会总体人口的变化情况来推演大学人口的变化其逻辑是难以自洽的。其四,中世纪大学往往没有招生人数及资格上的限制,理论上所有有愿望、资源和教育准备的人都可以加入大学之中。由于中世纪大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弹性”地补充学生,所以单凭遗存的数据后来的学者们很难判断黑死病对大学人口数量的影响程度。其五,黑死病具有冬季弱、夏天强的流行特征,而在夏天大学会有一个长假期,一些人在疫病流行高峰时可能选择假期后不返校。其六,平均年龄在15~35 岁之间的大学生群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更强,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条件可能也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二、黑死病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
无论如何,黑死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或夺走部分学者的生命,或伤害部分大学的知识生活,或降低学生的就学质量,这是事实。在1348—1349 年间,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去世了。例如神学家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 牛津逻辑学学者霍尔科特(Robert Holcot), 英国自然哲学家、数学家布拉德华(Thomas Bradwardine), 神秘主义代表人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等等。学者的陨落令人扼腕,而这仅是黑死病给高等教育质量带来的冲击中即时可视的一部分。由于教育的发展具有滞后性,黑死病带给教育体系的衰减从底部向上移动,且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
一方面,黑死病影响了学生质量及大学的发展方向。与大学不同的是,中小学教育通常依赖于本地教师,本地教师的存在及其提供的培训决定了小镇上大多数男孩的教育未来[14]707。黑死病期间,部分懂拉丁语的教师死去了,而教会任命的大部分教师更像是“贪婪的文盲”,学生的拉丁语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障。黑死病之后,本就为数不多的拉丁语学者大多在大学任职,初等教育的拉丁语教学存在着巨大缺口。中世纪大学所追崇的哲学和神学科目本就是非常复杂的,不仅需要良好的拉丁语水平,还需要较好的逻辑学和数学基础。但是无论多么有天赋的大学生都无法修复羸弱的中小学教育给高等教育质量带来的损害。进一步说,缺失的优秀生源和日趋下降的初等教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方向。在1365 年之后,文学院的知识逻辑转向了更古早、更基本的逻辑,并且同一时期的神学从复杂的元语言学问题转向了实际的神学问题[2]14。大学的哲学和神学研究变得更容易掌握,学者们不再需要复杂的逻辑和数学方面的技术培训。然而,这种变化却是由于学生无法胜任以前的高深学习任务而被迫降低质量标准的无奈之举。另外,由于疫病频发,中世纪大学的学术生活经常被打乱。1448—1464 年间牛津大学全校教职员大会(congregation)出台了瘟疫期间的应对性动议(grace)和特许(dispensation),允许学生缺席瘟疫期间学位课程的学习,或到其他大学学习学位必修课程,并于1452 年允许以12 节普通讲座课程来抵消学期必修讲座课程的学习[10]118。传统大学里的拉丁语教学研究本应十分严格,但在瘟疫期间,由于学生得不到良好的拉丁语教育,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逐渐走向衰落,欧洲各国的官方语言普遍从拉丁语转向方言[16]154。在大学和教会中,拉丁语的地位虽短时间内难以被颠覆,但方言文学通过诗歌、瘟疫传单、祈祷文等得以广泛传播。
另一方面,在黑死病的冲击下,大学的神学教育理念发生动摇。中世纪时期的教育基本被教会垄断,大学是培养牧师的唯一场所,很多弥撒、宗教活动都是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牧师举办,主教们基本都有大学学习经历[17]。例如14 世纪赫里福德主教区中有六位主教拥有神学、法学或社会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刘易斯·查尔顿作为牛津的名誉校长和知名学者也是主教中的一位[18]。而教士们既要能够精通拉丁文的听说读写,又要了解圣礼的基本情况与步骤,以便能更好地服务和照管堂区居民[19]。在黑死病泛滥后的几年中,随着神职人员的大量死亡,教区和修道院迫切需要各级接受过教育的教士。对神职人员的大量需求导致在1349 年之后的十年里神学学生的数量增加了28%,并且在整个14 世纪下半叶间持续增长[14]709。学生们依靠所学习的神学专业知识来谋职就业,这一定程度上使教育变得更加世俗、更加功利。由于毕业生的数量远远无法填补黑死病造成的神职人员空缺,人们的精神信仰寄托于教会,教会的运行离不开教士,教会只得通过降低神职人员的质量来吸纳更多的教士。坎特伯雷大主教宣称,在瘟疫中幸存下来的牧师们开始“受到无餍足的贪婪的影响”,收取额外的费用而无视人们的灵魂[20]124。14 世纪中期前,教皇严格控制高声望的神学硕士学位的授予,神学教学只被限定在巴黎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与之同等层次水平的大学以及教廷学馆中进行,直到14 世纪60 年代后,这项政策被废止,神学教育被分散化处理[21]62-63。新的教士占比很大,但他们的能力一般达不到以往的水准,这不可避免地对中世纪大学的神学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大学一面接收初等教育送来的大量神职候选人,一面为教会输送大量质量普遍下降的毕业生。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创建人罗伯特·沃德拉克(Robert Wodelarke)反思说:“长远意义而非眼下功利倾向的教育理念是大学实际的存在价值。”[22]248从这个角度看,面对瘟疫,中世纪大学并没有能在崇高目标与经验主义的反差中坚守“过去的坚持”。
综上,从初等教育入学到高等教育毕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疫情对高等教育人才质量的反馈既难以即时显现又难以观察评测。某些时候、某一环节出现的教育偏差尚可以对二三十年后的成人、成才造成影响,遑论黑死病这类对整个社会都造成巨大震动的大灾难。“欧洲一下子失去了知识、技能、经验、关系和新鲜劳动力,许多东西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才能恢复。”[1]12事实证明,直到一两个世纪之后,大学才彻底驱散了黑死病带来的阴霾。
三、黑死病流行期间中世纪大学的应对
黑死病暴发前,中世纪大学作为学生和教师的共同体组织在社会中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地位。黑死病肆虐之时,大学虽难以独善其身,但教师与学生受疫情威胁的同时,并未怨天尤人、坐以待毙。学者的抗疫举措虽无实质性帮助,但也使大学在疫病期间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迷信与依赖。14 世纪中叶,欧洲地区的大学数量并不算多,但中世纪大学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已有体现。就黑死病期间中世纪大学的应对举措而言,大学及其中的教师、学者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尽到了自身的社会职责。同进,社会各界也为大学的运转贡献良多,甚至有很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1.黑死病与新大学
黑死病爆发前,中世纪大学已有150 多年的历史,大多分布于西欧和南欧。诸如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在中世纪享有良好声誉,并在与王权和教会的周旋中不断发展。至1345 年,共有20 余所大学维持正常教学活动[21]131。1348 年,位于黑死病暴发重灾区的佛罗伦萨决定创办一所新大学。新大学将拥有文、法、神、医四大学院,教师的薪资及大学所需的其他费用由城市的财政税收负担[9]125。市政府为佛罗伦萨大学拨款700 佛罗林用做启动资金,还成立了专门的八人委员会负责安排外地师生食宿、筹措大学资金、为大学选聘教师等事务[23]。大疫之年的佛罗伦萨兴建大学时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一,佛罗伦萨正处于长期战争中,资金应对战事已经吃紧;其二,疫病的肆虐带走了城市的大量人口。尽管如此,佛罗伦萨大学依然成功建立并顽强生存了下来,佛罗伦萨市政府兴办大学的决心可见一斑。大疫之年组建新大学,一来是为更多学子提供优良的高等教育,避免本地市民子弟远赴他乡求学之苦;二来是新大学的成立会吸引大量外地师生,以此增加城市人口。外来人口能够为佛罗伦萨带来大量财富,拉动消费的同时城市居民工作机会也将增加,城市经济也有望复苏回温。佛罗伦萨当局正是看中大学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这一点,在城市受疫病打击后,通过组建新大学来重振经济活力。
佛罗伦萨大学的组建并非个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在黑死病肆虐过程中愈加关心大学的发展,于1348 年创办了布拉格大学(Prague),并在接下来的5 年内给另外5 所大学——奥兰吉(Orange)、佩鲁贾(Perugia)、锡耶纳(Siena)、帕维亚(Pavia)、卢卡(Luka)——授予皇家认证[16]154。出于对学识传承的担忧,黑死病过后,欧洲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一方面疫情过后,存留下的民众获得大量遗产,市民在历经创伤后更慷慨解囊,为教会、大学资助善款,有些市民的遗嘱中也会提及筹建新大学与设立奖学金。另一方面疫情导致的大量教士、教师职位空缺使社会需求增加,也为受过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更多就职机会,民众更乐于送孩子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以便谋求更好的职位。这也给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第一,住宿制学院数量的攀升增扩了大学规模,人们不必再远赴他乡求学。剑桥在1348年后的5 年内相继成立了三一学院(1350 年)、圣体学院(1352 年)、克莱尔学院(1349 年);牛津大学的坎特伯里学院成立于1361—1362 年,新学院成立于1375—1379 年。第二,大学分布愈加广泛,14 世纪前中世纪大学的版图仅限于地中海沿岸和欧洲南部,14 世纪中后期逐渐向中欧和东欧延展扩张。1350 年,佩皮尼昂大学(Perpignan)创办于法国;1364 年,克拉科夫大学(Cracow)创办于波兰;1365 年,维也纳大学(Vienna)创办于奥地利;1376 年,佩奇大学(Pécs)创办于匈牙利;1386 年,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创办于德国,同年,德意志骑士团创办库尔姆大学(Culm);1395 年,布达大学(Buda)创办于匈牙利[24]。部分学校的章程中都着重提及疫病是它们组建的原因之一[11]149,152-154。总体上,新建的大学遍布欧洲,在1300 年有15~20 所大学,到1500 年时已有大约70 所大学[21]131。这些大学超过半数延续至今,如维也纳大学、布拉格大学等,少数大学的校史遗留在历史长河之中。值得注意的是,1378 年后新建的大学少有完全衰落的,这归功于很多大学在学生的人数和教学的影响方面所做出的努力[21]61。到后来这些大学都成为孕育新思潮、新知识的摇篮。众多大学共同书写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图景,为更多年轻、乐于求学的学子提供了更完备的就学条件。
随着识文断字的市民阶层人数增多,人们对于书籍与知识的需求愈加强烈。这种强烈需求促成了印刷技术的推广与更新,人们可以更高效、更便宜地印刷书籍[25]42。知识被少数阶层掌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文学盛行一时,人们对但丁产生浓厚的探究兴趣,薄伽丘的文字也有了大量的新读者。这一时期的大学在地域分布上急剧扩散,中世纪大学原有的“国际性”特征也逐渐为“地域性”所取代[26]66。各国在大学扩张过程中愈发结合本国人民的教育理念,逐步构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大学组织,现代大学的发展由此奠基。
2.黑死病与人文主义
在中世纪大学成立之初,自由性和独立性被强调用来使大学独立于王权和教会,但实质上“特许状”的获得与大学的延续发展都与教会、王权密不可分[27]。教会利用大学的神学学科培养神职人员,大学也在教会和王权的矛盾斗争中获得特权。因此,早期大学的思想在束缚的经院哲学统领下日趋保守,经院哲学是人文主义从外部逐渐渗透中世纪大学过程中的最大阻力。瘟疫流行时期大学内的神学家们坚信这是上帝对有罪者的惩罚;巴黎大学医学系的博士认为土星、木星和火星在宝瓶座宫40 度处相会是造成瘟疫流行的主要原因[28]。这类说法在黑死病流行时期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被浸润在宗教情感中的知识界和广大群众广泛认可和接受,而真正造成瘟疫的元凶——老鼠——隐匿在人们视若无睹中。经院哲学的腐朽性使大学的活力愈渐褪去,对新知识的排斥严重制约了大学的发展。
长久的宗教束缚麻痹了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当黑死病如魔咒一般席卷欧洲时,死亡是每个人面临的“平等”问题。在巨大的死亡威胁面前,宗教的桎梏让人们寄希望于教会,虔诚地祈祷并对神职人员抱有莫大期许。但教会在这一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更加暴露出其脆弱性。教会认为肆虐的黑死病是上帝施加给有罪之人的惩罚,一切的逃跑和治疗毫无意义,必须每日进行虔诚祈祷、忏悔和行善[29]。与此同时,教会在瘟疫中接受大量捐赠,大发瘟疫之财。巴黎圣日耳曼·奥赛尔修道院在9 个月内接受死者留下的49 起赠产,它此前8 年一共才收到了78 笔[20]128。而当大批神父、教士、虔诚的信徒染病身亡,“神谴论”这一基本信条被彻底动摇,教会的权威也在这场瘟疫中被削弱。黑死病给基督教教会带来了比以前更严峻的挑战,“教会在精神上和教育上的职能被检验是不合格的”[30]84。疫病无情地加速了人们对于死亡、神明、人性的思考,以其前所未有的冲击震撼人们的心灵,死亡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和艺术的主要题材。巨大的绝望背后是狂欢和享乐的甚嚣尘上——人们在黑死病的袭击下认识到生命的短暂与珍贵,不再寄希望于禁欲和来世,而是选择在有生之年纵欲狂欢。神学的光芒逐渐被遮蔽,人性的尊严日渐彰显。黑死病所带来的持续的高死亡率减少了学者、知识阶层的人数,削弱了欧洲文化的稳定性[31],但也为新思想的产生肃清了一些障碍。当人们的思想愈渐挣脱出基督教神学的枷锁,人文文化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纳,文艺复新开始孕育和萌芽。作为一种新思想,人文文化“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教育价值取向在当时初步具有了冲破神学荫蔽之势[32]。
教会的绝对权威在疫病的侵袭下变得摇摇欲坠,而人们平等自主的思想观念更是加速了教会的衰落。人文主义所宣扬的人的理性为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教育目的、内容等也受到人文文化的冲击,大学内部经院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裂缝。作为“教会的侍女和附庸”,中世纪大学在人文主义的冲击和洗礼下,宗教色彩逐渐淡化,世俗化气息渐渐渗透大学的高墙。中世纪大学的经院哲学渐逝往日荣光,法学、商学、医学等实用学科地位不断提升,大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加密切。早期神学独大的局面渐渐被一种各类知识平均化的趋向打破,实用课程在大学中愈发受到关注[26]70。例如,牛津大学关注到了那些希望接受快速填鸭式课程以便为商业生涯做准备的学生,设置了一些应用性课程教育,其课程内容包括文书的写作、法律公式汇编(legal formularty)、遗嘱和书信的起草、产权转让、记账、法庭实践和纹章术(heraldry)等[22]245-246。此外,大学的学科职业针对性逐渐增强,开始自主地参与部分社会事务,大学毕业生在政府中任职的比例明显增长。中世纪早期,社会提供给毕业生们的职位类别有限,学生大多选择进入教会任职或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5 世纪中后期,政府公职中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明显增长,博士和一些取得证书的毕业生往往可以在各地最高法院获得薪酬丰厚的职位,大学生也将进入政府公职视为社会地位的提升。部分大学教师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充当一些城市公社、大领主等的司法裁判和咨询者,开始将部分精力用于参与社会事务活动上[33]。
总之,黑死病在欧洲的蔓延给人们带来绝望恐慌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反思,人文主义以一种崭新、先进的姿态出现在经院哲学主导的大学校园里。然而,打破高等教育中陈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教会的文化精神禁锢,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事实上,直至中世纪末期,中世纪大学内被奉为圭臬的经院哲学才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文艺复兴高举的人文主义大旗才拉近了大学与世俗社会之间的距离。
3.黑死病与医学革命
文、法、神、医是中世纪大学的四大支柱学院。并非所有的中世纪大学都拥有这四所学院,但多数都设有医学院。14 世纪时欧洲六所名冠一时的医学院分别座落于萨莱诺、蒙彼利埃、帕多瓦、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30]106。当时的内科医师通常在医学院中接受盖伦和希波克拉底医学理论的浸染,将医学与占星或放血术结合。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医学生是医学界的精英,位于传统三等级制度医疗体系的顶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他们只从事理论研究,从不与病人打交道,而且极端排外[34]。外科医生处于三等级中的第二位,被视为地位低下的熟练技术工人。而位于三等级最下层的由理发师充当的外科医生大多是文盲,从未进入过大学接受教育[25]46。中世纪医学生的学习形式与现在并不相同,在传统思想和宗教信仰绑缚下,中世纪大学并不认可解剖学等外科实践类教学课程。黑死病暴发前唯一开展常规解剖的医学院是帕多瓦大学[35]。尽管1281 年博洛尼亚大学曾首次进行人体解剖,但直到瘟疫过后的1363 年,对医学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经典参考书籍《外科大典》才得以出版[1]37。当时医学生主要学习哲学、天文学等理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他们必读的经典。教学内容常常是诵读拉丁语的著作,教授逐条解释,学生逐条记录[36]。总之,中世纪医疗技术落后,受过大学教育的医学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医学水平,但是他们严格遵循古代医学权威,重哲学而轻实践,不愿意改变旧有的医疗模式。
黑死病出现后,中世纪大学医学院被社会寄予厚望。多所医学院的教师纷纷著述,分析疫情成因和对策。例如,莱里达医学院的教师达格拉蒙特(Jacme d’Agramont of Lérida)完成的《防疫之道》是第一份由大学教师所写的瘟疫预警;巴黎大学医学院应法国王室需要,在1348 年发布了《流行病概要》;佩鲁贾大学医学院的教师佛利尼奥的詹蒂莱发表了《抗疫忠告》[1]38-40。然而,当时的医疗水平仍囿于古希腊、古罗马医术,医师们通常将疫病归咎于腐败的空气或是行星运动,而就此提出的防疫举措,诸如不洗澡、多饮葡萄酒等更是对于抗病全无效用。尽管这些“良方”并未能提供真正有效的措施来减缓病害,但却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防疫意识及其对中世纪医学院和教师的依赖。在这一时期医学界许多“领先”的思想家、理论家死亡,如伯根第公爵的首席皇家内科医生、教皇克莱门特六世御用的5 名医生……1349年帕多瓦医学院医学和外科医师主席的职位也出现大量空缺[30]117。重大伤亡出现后,欧洲医学界迎来了改变。许多现代医学的新观念开始萌芽和传播,医学院的精英们逐渐抛弃种种占星说,转而将目光投向人类社会,由重视医学理论转向重视医学实践,医学职业化逐渐步入正轨。北欧的医学院对于外科医生敞开大门,解剖课程和外科医学课程成为重要部分;在巴黎大学,外科手术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到了1380 年,博洛尼亚医学院解剖学教程已经相当完备[30]118。黑死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实践性为主的外科医生与理论化为主的内科医生之间的不平等,外科医生的地位得以提升。
客观上,黑死病给社会各界造成的伤亡未能即刻扭转医学在大学内部的发展态势。从大学的应对来看,受限于落后的医学知识与医疗水平,中世纪大学没能即时提供科学有效的防疫方案。但结合当时的环境,大学人为抗疫采取了当时力所能及的行动。例如,大学及其教师发布了各类抗疫公告、指南。就长时段来说,经验科学的转向虽缓慢但坚定,大学师生开始反省典籍中的神学和医学知识,开始思考人的生命原理。理性和科学思想由此落地生根,最终在近两个世纪后科学革命之光得以耀眼夺目。
四、结束语
总之,黑死病的暴发是偶然的,但欧洲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逐渐从黑死病带来的伤痛中慢慢恢复生机。尽管黑死病对中世纪大学的教育人口影响未有定论,但其间知识分子的逝去、初等教育的颓势、拉丁语教育的缺失等,凡此种种都对中世纪大学的教育质量带来不可避免也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梳理大瘟疫进程中高等教育所受的影响及其应对方式,可以更好地还原瘟疫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助于了解高等教育在特殊时期所起的作用,这对现在及今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37]。“黑死病是欧洲历史的耻辱,因为它暴露了封建政府一切的涣散……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使人们认识到了自己居于危巢之中的本质。”[38]灾难终将过去,生活必会前行。黑死病只是短暂的寒冬,中世纪大学依然向着融化寒冰的春天稳步前进。根据可查找到的文献,没有一所大学由于黑死病的肆虐被迫关停。相反,大学的数量在中世纪末期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随着疫情渐去,人们的思想也像融化了的积雪,渐成河流,最终冲出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