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形象转变的合理性
陈珏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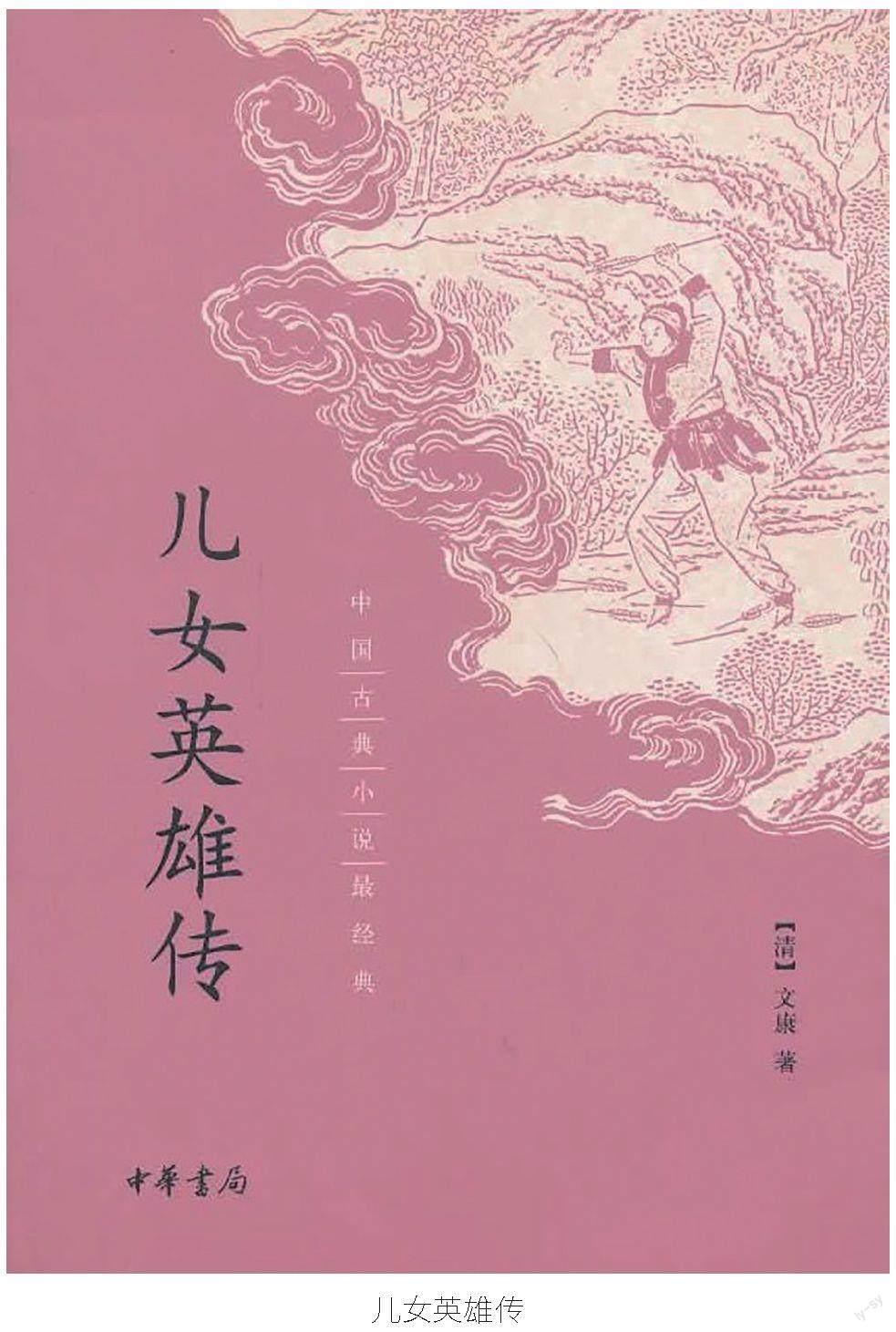


《儿女英雄传》原称《金玉缘》,经后世文人的补写而改名,是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在光绪年间刊行,叙述方式采用评书体。其作者文康,字铁仙,费莫氏,清代满洲镶红旗人,曾出仕,自称“雁北闲人”。马从善有序:“先生为文襄公大学时勒保次孙,以赀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洊濯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鲁迅也曾提到文康出生富贵人家,但后来因为“诸子不肖”而变得家境贫穷,到了晚年“块处一室”,只得以写书自遣,将自己经历的人生兴衰、世事变迁写进小说中。因此,《儿女英雄传》借叙述他人之事,表现作者文康的理想追求,这一点就不同于此前的大部分小说。文康的晚年过得艰苦潦倒不说,又恰逢政治、文化即将迎来巨变。道光、咸丰年间,古代白话小说进入终期,此时的小说在故事情节和人物上“多用传统的模式,缺乏作家自己的创作个性”。在此背景下,文康创作的《儿女英雄传》也被视为旧小说在新时代来临前的一次无力突围。
《儿女英雄传》诞生于旧时代尾声,被称为“清代小说的后劲”,自问世以来一直广受争议,称赞者如陈寅恪认为其“转胜于曹书”,贬斥者则认为其思想浅陋、内容不够丰富。
《儿女英雄传》的主角十三妹是古代小说中最后一位有影响力的侠女形象。她聪慧果敢,在能仁寺救下张金凤和安骥;仗义好强,在得知安公子为父奔走后被其孝心打动,毅然决定出手相助。十三妹兼具侠义与柔情,成为清代侠女形象的代表,得到肯定的同时,其身体建构的多重性、前后不统一的性格也引起了争议。
十三妹这一人物的身体是由旧小说各种人物模式重新组合叠加而来的,往前追溯,建构这位晚清侠女身体的材料在小说史上清晰可见,有唐宋剑侠小说中超越常人生理极限的神性身体,如胡适先生所说的聂隐娘、红线一流的剑侠“超人”,也有话本中绿林世界神勇的血肉之躯。治家贤惠的形象则是对明清世情小说人物的优化组合。这种身体的多重建构受到了晚清小说题材合流的影响。彼时,文康知道无人可以挽回即将解体的旧秩序,在他的想象中,只有十三妹这样“完美”的侠士才能挽救危局。尽管文康力求突破和创新,最后也难免落入俗套,没有跳脱出传统侠女的模式,而是对前代侠女形象进行择优重塑,希望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侠女。因此,十三妹这一形象并不是文康原创。这种身体建构的多重性也给十三妹的性格逻辑带来了混乱感。
历来学者主要的争议点是十三妹的性格前后是否具有统一性。以创作意图和创作目的为出发点,部分学者认为从十三妹到何玉凤的转变,不仅是人物从“英雄传奇”里的“江湖”走进了“世情小说”中的“家庭空间”,更是侠女形象被严重削弱、清高侠女形象被颠覆的过程。也有人认为十三妹的“性格失常”是文康庸俗世界观的具象和腐朽思想的体现。亦有学者分析,文康的创作意图是“圆梦补恨”,是为了与《红楼梦》进行“对垒”。与敢于直面自己家庭罪恶的曹雪芹不同,文康不但不愿意写自己家庭衰败的原因,反而渴望塑造一个理想的圆满家庭,颇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意。
十三妹是晚清最后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侠女形象。她身上既有侠士共有的武功盖世和雄心侠气等特点,也有大家闺秀的知书达理。不管是豪侠还是情侠,文康笔下的十三妹注定不同于前代任何侠女形象。这不仅是因为十三妹身体构造的复杂性,更是因为十三妹性格前后的不统一,但这种前后冲突又有其必然性。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十三妹原生家庭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
性格是人们对某事、某人所表现出的不同思想、情绪、行为、态度的总称。性格虽然一旦形成就会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具有可塑性。性格主要表现在“做什么”和“怎么做”两方面,“做什么”反映了个人对现实的态度,“怎么做”反映了个体的行为方式和特点。性格是包含在人格结构中的,体现了人的本质属性,并且最能表征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特征。影响性格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原生家庭、固有性格、外在环境和自身阅历等。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认为十三妹形象前后的不同是由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就以儿女与英雄一身兼备来说,也是理所当然地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两者哪一个是明显化,哪一个不是明显化,何玉凤前半部作为英雄形象出现,后半部是作为儿女情形象出现,这是由于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由此而堪称张冠李戴一样的不自然,那是不恰当的”。从十三妹到何玉凤,并不是侠女性格不真实。太田辰夫的这一观点被众多学者作为分析十三妹婚前婚后性格转变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但这只是简单地从外在环境进行分析,忽略了内在环境即十三妹家庭环境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
十三妹在第四回以一个神秘的形象登场:从路南那边,骑着一头黑驴,慢慢悠悠地走了过去。这种出场方式不同于以往的旧小说,更像是西方小说的手法,在描写中逐渐交代人物。在悦来客栈,十三妹抬起巨石第一次展示了自己的神通。随后在能仁寺,十三妹凭一己之力杀恶僧数十人,救了张、安两家,并周全地替他们考虑了后路。十三妹的性格特征在这些事件中逐渐显露。如安公子骗十三妹自己是保定人,但十三妹心思缜密,推测出安公子是京都人;在解救了张家和安公子之后,十三妹并未一走了之,而是仔细慎重地考虑了怎样善后以及两家四口人该如何上路的问题。她言语犀利、行事干净利落,已经展现出婚后“何玉凤”的雏形。特别是其中关于十三妹身世的情节,为十三妹从侠女形象到贤妇形象的合理转变埋下了伏笔。
文康在小说写道:“天下作女孩儿的,除了那班天日不懂、麻木不仁的姑娘,是个女儿,便有女儿情态,难道何玉凤天生便是那等专讲蹲纵拳脚、飞弹单刀、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的不成?何况如今事静心安,心怡气畅!再加上‘人逢喜事精神爽,怎叫她不露此女兒矫痴情态?”文康也在小说中简单解释了人物这种转变的社会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物心理变化与行为变化。他一方面歌颂十三妹的侠肝义胆,另一方面竭力追寻她由儿女变为英雄的社会动因以及与之相契合的心理动因。小说中人物心理动因的改变与社会动因的变化紧密相关,我们从小说中也能找到十三妹性格转变的基础—内在性格。
张、安两家询问十三妹的身世,她回答说自己也是好人家的女儿,父亲曾经做过朝廷二品大员。提到她超乎常人的武艺,“这也有个原故,我家原是历代书香,我自幼也曾读书识字。自从我祖父手里就有了武职,便讲究些兵法阵图,练习各般武备,因此我父亲得了家学真传。那时我在旁见了这些东西,便无般的不爱。我父亲膝下无儿,就把我当个男孩儿教养。见我性情合这事相近,闲来也指点我些刀法枪法,久之,就渐渐晓得了些道理”。十三妹幼年就开始学习各种武艺,十八般兵器她都熟悉,在拳脚、弹弓、枪法等方面更是得到了父亲的“口传心授”。“因此任我所为,就把个红粉的家风,作成个绿林的变相。这便是我的来历,我可不是上山学艺,跟着黎山老母学来的。”十三妹从小被当作男孩儿教养,便是性格也是如男子一般。女儿家该学的针线活儿她不会,也不能以此作为生财之道供她们母女俩生活,十九岁了还不清楚针线是横是竖,无奈只得靠着一把刀和一张弹弓行侠仗义、劫富济贫。
十三妹生在书香世家,幼时就读书识字,颇有才气,故可以在能仁寺墙上写下令安公子拜服的豪语。又因她祖父这一代开始得了武职,家中研究兵法、练习武艺。受家风影响,十三妹开始练习武艺,并被当作男子教养,有了男子的雄心侠气和慷慨大义,“路见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便肯沥胆订交。见个败类,纵然势焰熏天,他看着也同泥猪瓦狗;遇见正人,任是贫寒求乞,他爱的也同威凰祥麟”。行事作风也如男子一般豪爽仗义,这是她与生俱来的性格,做不来像一般女子那样含蓄扭捏。家庭环境让十三妹的性格成形:既有大家小姐的知礼节、懂才学,又有男子的豪爽不羁、直言不讳。婚后的何玉凤想要有所作为的志气,比起侠女十三妹在能仁寺拯救安公子等人的果敢并未改变,她的英雄气概不曾消退,不过是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
文中多次提到十三妹性格的“天生”:“原来这人天生的英雄气壮,儿女情深,是个脂粉堆里的豪杰,侠烈场中的领袖。……虽然是个女孩儿,激成了个抑强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杀人挥金的事业”“大约他自出娘胎,不曾屈过心,服过气,如今被这穿月白的女子这等辱骂,有个不翻脸的么?谁知儿女英雄作事毕竟不同。”张金凤等人被救下后感谢十三妹,十三妹只说:“你我今日这番相逢,并我今日这番相救,是我天生好事惯了,你们倒都不必在意。”这种“天生”其实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十三妹与生俱来的儿女情长让她对安公子千里救父的孝心感到动容,于是在能仁寺救下张、安两家,她自小接受的官家小姐教育也让她对如何侍奉公婆、持家理财颇有心得。不管是作为侠女还是作为人妇,十三妹身上兼具的英雄侠气与儿女情长并未减少,其形象并未发生变化,不过是婚前、婚后的侧重点略有不同。
“十三妹”无疑是一个合格的侠女形象:机智勇敢,胆大心细,独立反叛。她不受束缚,自有一套生活哲学。生存环境的恶劣并没有让她屈服,她依旧是那个桀骜不驯、无比洒脱的侠女。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她做到了,她以女性的柔弱躯体承担重任,这是很多男性角色都做不到的。因此,十三妹这一形象具有表现男女平等的意义。文康把她写得活灵活现、不让须眉,这不仅是展现文康对女性态度的典型,還是其肯定女性地位的表现。此外,何玉凤式侠女出现在晚清,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被平民意识改造的文学题材。文康尝试重新把侠女形象放到“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里,使其从神异化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尝试恢复女性的正常伦理诉求,将侠义精神和日常伦理、民间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近代平民意识。二是随着晚清小说创作中各类题材的合流趋势,出现了各种人物模式重合于一个人物的现象。何玉凤式侠女可以视为一个特殊阶段的文学现象,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