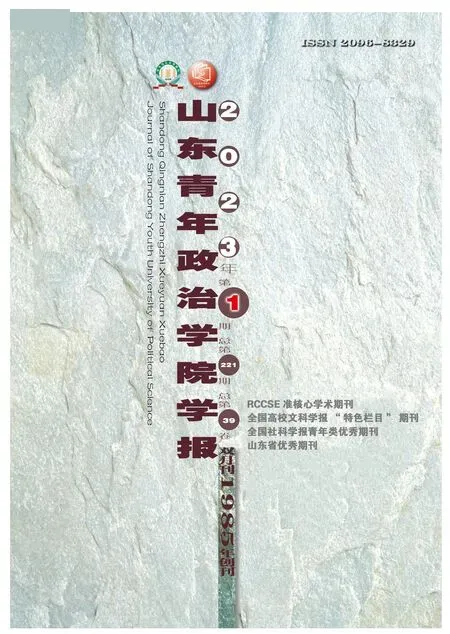宋元哲学研究的新成果
——评《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
孙自磊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自学科成立起,“中国哲学史”就在不断重写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哲学史”框架逐步完整、范围逐步确立,研究方法也成熟多样起来,既适应了不同时期变化的要求,也展现了不同作者独特的理解。新世纪以来,尽管以“思想史”或“儒学史”名义编撰了一些多卷本的中国学术史著作,但中国哲学史领域的新作则仍以适应教学需要的教科书为主。在以充分的篇幅总结中国哲学史研究新成果方面,本世纪的头二十年似乎不及上世纪后二十年那么热闹,这和国内西方哲学史方面的情况正好相反。最近由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以下简称《通史》)的出版,终于使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由田文军教授和文碧芳教授领衔撰写的“宋元卷”,就是这部哲学通史中的一个分册。该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主体自觉
如果说上世纪后二十年,老一辈学者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主要意图在尽量摆脱教条,相对坦诚真实地表达研究者自己的学术理解,今天的情况则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意识形态教条对学科的限制已经基本得到解放,另一方面,自本世纪初以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争论热度持续不退,对中国哲学史学科造成了一定冲击。今天重写中国哲学史,不可避免地要对此新局面予以回应。
“宋元卷”有着明确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论的自觉,这种自觉表现在多个方面。在论及“理学”和“道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问题时,作者说:“当我们以考察宋代哲学的形成及其发展为学术目标的时候,应当且只能将道学与‘理学’的概念纳入哲学这个特定的视域和范围来进行考察与解析。”[1]在讨论到学派划分问题时,作者说:“学派应当是在同一学科中,因为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我们考察宋元哲学,应当在哲学的范围内,以思想理论的差异来区分与判定其内部出现的不同的学术派别。”[2]在评论邓广铭先生提出的理学家这一学术流派直到南宋前期才形成的观点时,作者写道:“若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否定北宋道学中已经存在理学这一派别,论据并不充分。因为,当程颢、程颐的思想系统完成时,理学作为一个具体的学术派别,不论基本范畴还是理论架构实际上都已经建构起来了。”[3]可见,哲学立场的自觉渗透在本书的方方面面。正是这种自觉,使得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哲学史”。今天我们确实应该警惕一种倾向,以中国哲学特性的名义模糊哲学史与一般思想史的界限,这实际上是“中国无哲学论”的变种。
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在哲学史范围之内考察宋元道学,不能不对西方的哲学观念有所借鉴。但并不是因为借鉴西方的哲学观念,或说将‘欧洲哲学的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宋元道学才成为宋元时期的哲学。道学也不能‘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因为,道学本来即是一种历史的中国哲学理论形态。”[4]从长远影响来看,多年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的真正意义,正在于让更多学者在经过反思的更高基础上更加明确了中国哲学的哲学性和主体性的意识,而这种觉悟的意义实不限于宋元哲学研究的领域。
二、全面深入
在哲学史研究领域,通常把宋元明三朝哲学合称“宋明理学”,也有学者主张把“理学”研究延伸到清代,如侯外庐等先生的《宋明理学史》就用了颇多篇幅介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陈来先生也强调:“就理学史本身而言,尽管宋代和明代是最重要的,却不可抹杀元代、清代。如从相对全面、完整、科学的角度,应该叫‘宋元明清理学’,这是使用‘宋明理学’概念时尤为需要注意的。”[5]在学术史写作中以宋元为一期、明为一期,肇端于黄宗羲、全祖望等的两部学案,汤一介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也采用了这一做法。关于明学相对于宋学的特点,钱穆先生曾说:“我们若说宋学在人生问题上是探讨发明的阶段,则明儒是在享受和证实的阶段了。”[6]也有学者认为,宋代理学和明代理学的主流,可以从理性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角度大致区分。
无论如何,《通史》的分卷方式使本书得以用84万字的篇幅单独叙述宋元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让这一段哲学史得到全面、深入的阐释。不但两宋道学大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的思想都得到充分的论述,承先启后的程门弟子吕大临、谢良佐、杨时也都有专章讨论。其他如和“理学”有重大分歧但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司马光,湖湘学派、浙东事功学派诸重要学者,也得到了在哲学上应有的重视。本书也对元代理学的传承作了清晰的叙述。中国古代哲学和经学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但总体来说,过去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对于主要以经学名家的学者关注不足。如程门四先生之一的吕大临用力于《礼记》,其哲学思想一向暗而不彰。本书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吕大临的哲学,并且指出吕大临先后问学于张载和二程,兼传关洛之学,在宋明理学史上有着极为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又如胡安国和朱震,分别以治《春秋》和《易》名世,一般的哲学史对他们多略而不提,本书则以专章形式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介绍和分析。
三、新见迭出
本书作为“学术版”中国哲学史,当然不会仅止于按部就班地叙述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而是颇多新颖的论述。但作者决不是简单否定旧说而成立自己的新说,而是在旧说的基础上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这也正是我们对于一部哲学史所当有的期待。
仅举一例。胡瑗是宋初“三先生”之一,过去研究道学者无不注意到他的重要影响,本书特别关注到了胡瑗与程颐的关系。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是道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曾得到胡瑗的称赏。汤用彤先生曾说:“就中国思想之变迁前后比较言之,则宋学精神在认为圣人可至,而且可学;魏晋玄谈盖多谓圣人不可至不能学;隋唐颇流行圣人可至而不能学(顿悟乃成圣)之说。伊川作论适当宋学之初起,其时尚多言圣人可至而不能学。伊川立论反其所言,安定之惊或亦在此。”[7]这显然是强调了胡瑗对程颐此论的新异感。至于其和周敦颐思想的关联,更成为常识。本书作者则特别指出此文和胡瑗思想的关系:“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的这些观念,既精炼地论述了传统儒学的基本理趣,也体现了胡瑗在理学理论方面对程颐的影响。胡瑗读完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后,之所以‘大惊异之’,则是因为程颐对孔门弟子中‘独称颜子为好学’的回答和胡瑗对儒学主旨的理解高度一致。”[8]作者还指出:“从思想源头来说,程颐解《易》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深受胡瑗解《易》方法的影响。”[9]道学固然受到当时一般政治文化和学术风气的影响,但其建立终究要归功于若干大师的崛起。因此在追溯学术影响时,私人交往和具体的学说影响也是重要的一环。作者在胡瑗与程颐间建立了具体的思想联系,超越了传统的泛泛而谈,这就丰富了我们对胡瑗和程颐关系的理解,也加深了我们对胡瑗对道学影响的理解。
当然,任何一部哲学史都不会完美无缺,这也是哲学史需要不断重写的一个原因。宋元哲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而复杂,尽管本书篇幅已经较大,但仍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有限的篇幅里,自然只能突出核心和重点,将论述集中于哲学思想,而省去一些历史背景和文献学上的论述。这是无可避免也不能苛求的。本书是集体工作的成果,确如作者后记所言,“不求教科书式的章节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而是“展示不同作者对各派哲学独具会心的具体评断”。通观全书,作者们确能做到“毋私己意,毋主先入,虚心体察”。总之,《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实为宋元哲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一部新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