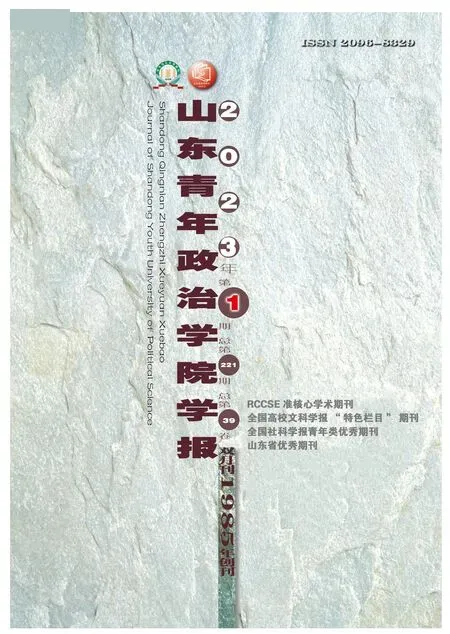《四库全书总目》词学思想探析
高明峰,魏蓝婷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大连 116081)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清代的官修目录学著作,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目录学、校勘学知识,而且也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从一方面看,也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1]《总目》“宏纲巨目,悉禀天裁”[2],“实是钦定之书”[3],也是四库馆臣集体智慧的结晶,其词曲类“提要”集中代表着清代中前期主流的词学思想和意识形态。
近年来,学界对《总目》词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解析“提要”来论述《总目》的词学思想,但《总目》词学思想的成因及影响尚有可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总目》作为清代集大成性质的官修目录学著作,代表了当时主流的文学观念,在清代词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值得深入考察。本文以《总目》词曲类“提要”为切入点,将其中蕴含的词学批评观点整体放入清代词学批评史中,以此透视《总目》的词学思想及其价值。
一、体格卑微的词体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总体上对词体是持贬斥态度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词体产生来看,《总目》认为词乃诗之闰余,是乐府的余音,在文坛处于“末技”的地位;另一方面《总目》认为词虽由诗演变而来,但其过程是“层累而降”的,因此诗尊词卑。
《总目》集部总序中写道:“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4]闰余,本义指农历一年和一回归年相比所多余的时日。这里《总目》言词曲乃集部之闰余,认为从整个集部的发展历史来看,词曲最晚出,在集部处于闰余的地位。在词曲类小序中写道:“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5]这一观念在具体的词集或词学论著“提要”中也得到了体现。如《填词名解》“提要”指出:“古乐府在声不在词。唐人不得其声,故所拟古乐府,且借题抒意,不能自制调也。所作新乐府,但为五七言古诗,亦不能自制调也。其时采诗入乐者,仅五七言绝句,或律诗割取其四句,倚声制词者,初体如竹枝、柳枝之类,犹为绝句。继而《望江南》《菩萨蛮》等曲作焉。解其声,故能制其调也。至宋而传其歌词之法,不传其歌诗之法,故《阳关曲》借《小秦王》之声歌之,《渔父词》借《鹧鸪天》之声歌之。”[6]其要义在于指出词与古乐府都具有音乐的属性,在声而不在词,唐人不能得其声,只能作拟古乐府,所作的新乐府,也只是五七言古诗,而不能自制调,自竹枝、柳枝之类才开始倚声制词,而后便出现了《望江南》《菩萨蛮》等依曲填词的作品。通过论述乐府和词都具有音乐的属性,指出词由乐府演变而来,进而说明词乃乐府之余音。
乐府本来是指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西汉时期设立乐府专门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之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后来人们将合乐吟唱的诗称为乐府歌辞。北宋人从“合乐歌唱”的共性出发,称唐、五代以来流行的曲子辞为“乐府”。王灼《碧鸡漫志》中认为:“古诗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7]北宋人将词体起源追溯至乐府,是从词和乐府都具有音乐属性的共同点来追溯词体的起源,而《总目》意在强调词从乐府发展而来,却只是乐府的余音,是贬低词体。
关于词乃诗之余的说法始于南宋。北宋灭亡后,民族危机唤醒了南宋文人的爱国意识,在词学领域则表现在词学家们力求改变原有的词学观念,推尊词体,方法之一便是将词的创作与“诗人之旨”建立联系。后来“诗余”逐渐演变为词的别称,反映了人们对于诗和词关系的认识。南宋人虽极力将词与“诗人之旨”建立联系,但终究没能让词处于和诗同等的地位,只是别称“诗余”。王灼《碧鸡漫志》指出苏轼“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8]。南宋词人将词体与“诗人之旨”建立联系,是为了提升词体地位,而《总目》意在阐明词乃“风人之末技”,虽承袭宋人的词体观念,肯定诗词同源,但强调词是诗的闰余,在文坛处于“末技”的地位,是贬低词体。
另一方面,《总目》将词体演变融入“格以代降”的文体理论以指明词体卑微,认为由古诗变而为词,其文体演变过程是逐渐退化的。《总目》词曲类提要写道:“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尚属附庸。”[9]明代胡应麟《诗薮》云:“《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矣。”[10]胡应麟在《诗薮》中论述了文体“格以代降”的主张,《总目》认为词由诗演变而来,其体格是经历了一个降级的过程的,因此词体卑于诗体。《总目》在别集类典籍的“提要”中也反复阐明了此观点,如《御定历代诗余》“提要”:“唐初作者云兴,诗道复振,故将变而不能变。迨其中叶,杂体日增,于是《竹枝》、《柳枝》之类,先变其声。《望江南》、《调笑令》、《宫中三台》之类,遂变其调。”[11]《碧鸡漫志》“提要”:“盖《三百篇》之余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12]《总目》诗尊词卑的体格论在《花间集》“提要”中论述得尤为剀切,其云:“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13]
《总目》“词体颇卑”之论,一方面承袭宋人观点,从词乃诗之闰余的角度加以阐述,另一方面将“格以代降”的文学理论和词体演变理论结合起来,既肯定诗词同源,又论述了“厥品颇卑”的词体观念。
《总目》作为乾隆年间的官修目录学著作,既受到明人文体“格代而降”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显然受康熙皇帝词学思想主张的影响。康熙皇帝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词学主张,但通过敕修《御选历代诗余》和《御定词谱》,明确表达出他的词学思想。《御选历代诗余》序中写道:“诗余之作,盖自昔乐府之遗音,而后人之审声选调所由以缘起也,而要皆昉于诗。”[14]康熙皇帝认为诗余乃乐府之余音,皆昉于诗,肯定诗词同源,将词归入诗体领域内加以论述,代表了清代前期官方的词体思想。《总目》继承了康熙皇帝的词学主张,并且将词体在文坛的地位作了详细的论述,认为词虽为文坛的附庸,亦是诗之流裔。二者皆是在儒家正统的诗教观念下论述词体。
《四库全书总目》词体“厥品颇卑”的观念与乾嘉时期盛行的诗教传统息息相关。清代自清初开始便极为尊崇《诗经》,乾嘉之际更是发扬诗教传统尤为突出的时代,如沈德潜、纪昀、翁方纲、章学诚、袁枚等皆主张诗教。他们把《诗经》当作最高的文学典范,并且以《诗经》为阐释对象,主张文学要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一切文学作品都要以《诗经》为标准。如沈德潜《说诗晬语》中写道: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16]沈德潜认为《诗》可以梳理性情,更好地改善人伦物理,感通鬼神,有利于设邦教国,因此应复归“诗教”传统,明显体现出以《诗》为尊的倾向。乾嘉时期尤重诗教,词作为诗的余续,“风人之末技”,其文体地位自然是“厥品颇卑”的。
二、合辙入律的词律思想
词律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词的音律,一是指词的格律。词的音律,乃是与词有关的乐律、宫调、曲调谱式、叶乐方式以至歌唱方法等音乐上的问题。词的格律,则是来自作词所遵从的各种词调的字数、句式平仄等体式上和做法上的问题。[17]《四库全书总目》合辙入律的词律思想主要表现在推尊浑然天成的合律的词和依照词律进行校勘两个方面。
《四库全书总目》在强调词由诗歌演变而来的同时,重视词的音律,反复论述词的音乐性。《碧鸡漫志》“提要”云:“盖《三百篇》之余音,至汉变而为乐府,至唐变而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其时士大夫多娴音律,往往自制新声,渐增旧谱。故一调或至数体,一体或有数名,其目几不可殚举,又非唐及五代之古法。”[18]提要强调至宋,词随着歌诗的消亡而达到繁荣的顶峰,表现为士大夫往往自制新声,词谱发展呈现繁荣局面。《宋名家词》“提要”:“词萌于唐,而盛于宋。当时伎乐,惟以是为歌曲。而士大夫亦多知音律,如今日之用南北曲也。金、元以后,院本杂剧盛,而歌词之法失传。然音节婉转,较诗易于言情,故好之者终不绝也。于是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词遂为文章之一种。其宗宋也,亦犹诗之宗唐。”[19]《总目》认为词体产生之初,就具有音乐的属性,宋代娴于音律的士大夫往往能够自制新声,因此旧谱渐增,一调甚至有数体,一体甚至有数名,词律的发展促进了词作的繁荣,词作繁荣也表现为词律的发展,意在强调对词的音乐性的重视。
《总目》极力褒扬合律的词,如《片玉词》“提要”称赞周邦彦:“又邦彦本通音律,下字用韵,皆有法度,故方千里和词,一一按谱填腔,不敢稍失分寸。”[20]又《和清真词》“提要”:“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调,不独因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21]《总目》认为周邦彦能“妙解声律”,称周邦彦为“词家之冠”,指出周邦彦既通音律又懂格律,赞美周邦彦制词不仅讲究平仄,同时注重上、去、入三声之别。《总目》尤其重视韵律流美、浑然天成的合律之词,《石屏词》“提要”云:“今观其词,亦音韵天成,不费斧凿。”[22]
《总目》词曲类“提要”还依据词律对词进行校勘,主要表现在依据《钦定词谱》对词调名称进行校正。如《书舟词》“提要”依据《钦定词谱》所载进行校勘:“集内《摊破江神子》(娟娟霜月又侵门)一阕,诸刻多作康与之《江城梅花引》,仅字句小有异同。此调相传前半用《江城子》,后半用《梅花引》,故合云《江城梅花引》。至过变以下,则两调俱不合。考《词谱》载《江城子》亦名《江神子》。应以名为《摊破江神子》为是。详其句格,亦属垓本色。其题为康作,当属传讹。”[23]
依照万树《词律》对词的分调进行校正,如《乐章集》“提要”云:“宋词之传于今者,惟此集最为残阙。晋此刻亦殊少勘正,讹不胜乙。其分调之显然舛误者,如《笛家》‘别久’二字,《小镇西》‘久离阙’三字,《小镇西犯》‘路辽绕’三字,《临江仙》‘萧条’二字,皆系后段换头。今乃截作前段结句。……万树作《词律》,尝驳正之,今并从其说。其必不可通者,则疑以传疑,姑仍其旧焉。”[24]依据万树《词律》对词调的划分,对词作的分调之误进行校勘。
根据词调校正词作文字或断句之误。如《东坡词》“提要”云:“至集中《念奴娇》一首,朱彝尊《词综》据《容离随笔》所载黄庭坚手书本,改‘浪淘尽’为‘浪声沉’,‘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多情应是我笑生华发’。因谓‘浪淘尽’三字于调不协。”[25]依词调对词作进行校勘,指出词作应该与词调的韵律相叶。
再如《孏窟词》“提要”云:“毛晋尝刻之《六十家词》中,校雠颇为疏漏,……他如《水调歌头》之‘欢倾拥旌旄’,‘倾’字不应作平。《青玉案》之‘咫尺清明三月暮’。‘暮’字与前阕韵复。又‘冉冉年元真暗度’句,‘元’字文义不可解,当是‘光’字。其‘遥天奉翠华引’一首,尤讹误几不可读。今无别本可校,其可改正者改正之,不可考者亦姑仍其旧云。”[26]依据词调词律或上下文义对词作进行了校勘。
此外,《总目》推崇“情韵兼胜”之词。《淮海词》“提要”中称赞秦观的词:“观诗格不及苏黄,而情韵兼胜。在苏黄之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27]韵即词的韵律,即要求词合乎韵律。《总目》崇尚情韵兼胜的词,不仅体现在秦观的词籍“提要”中,而且还将秦观推为情韵兼胜的典范。如《姑溪词》“提要”称赞李之仪词:“之仪尺牍擅名,其词亦工。……殆不减秦观。”[28]《东堂词》“提要”称赞毛滂词:“其词情韵兼胜。”[29]
《总目》推重韵律谐美的词,是词律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词律研究至清初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并且取得显著的成果。万树的《词律》纠正了不少旧词谱的错误,筛选唐宋以来词作为规范。康熙皇帝敕修《钦定词谱》则为填词合律提供了官方指南。《总目》的词律思想可谓集前人之大成,又添己之新意。《总目》受乾嘉考据学思潮的影响,依词律对词作进行校勘,对规范词体与词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的词学研究开辟了新境。
三、清雅婉转的审美思想
南宋初期,民族危机唤起了人们的爱国意识,渗透到词学创作领域则表现为词人们改变了原有的词体观念,词学评论家们将词学创作和“诗人之旨”联系起来,掀起了一场词学领域的尊体运动。方法之一便是推尊典雅的词作,认可意格雅正的词。如张炎说:“词欲雅而正之,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30]元明时期,词学观念远离诗学传统,以婉丽为正宗,王世贞曾表明自己的词学主张:“词须婉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31]明人认为词乃小道,不重作词。入清以来,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开始总结明词衰落成因,强调风骚之旨,追摹清丽词风。其后以朱彝尊、厉鄂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推尊“醇雅”词风。《四库全书总目》论词受清代前期词学思想的影响,崇尚清雅婉转的审美思想。
具言之,“清”指《总目》推崇的清丽俊朗词风,主要表现在语言上追求清丽婉转,在总体风格上肯定清冷俊朗。《梅西词》“提要”云:“清词丽句,在宋季颇属铮铮,亦未可以其人掩其文矣。”[32]《总目》赞美史达祖的词为清词丽句,在宋词中亦属佼佼者。《归愚词》“提要”批评葛立方词:“多平实铺叙,少清新婉转之思。”[33]由此可见,《总目》主张词作应由清词丽句写就,反对俗艳,亦喜俊朗之风。《总目》论词推尊周邦彦,并且肯定清冷俊朗的词作。如《和清真词》“提要”云:“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34]《芦川词》“提要”云:“多清丽婉转,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35]《西樵语业》“提要”称赞杨炎正词:“其纵横排奡之气,虽不足敌弃疾,而屏绝纤秾,自抒清俊,要非俗艳所可拟,一时投契,盖亦有由云。”[36]这方面受浙西词派代表人物厉鹗词学思想的影响。作为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厉鹗论词亦追求雅,其独特之处表现在:他论词崇尚“清”“冷”词境,其词作也有“清冷”的格调。如吴衡照认为“樊榭有幽人气,惟冷故峭,由生得新”[37],指出厉鹗词具有冷峭清幽的特点。同时厉鹗论词也推尊周邦彦,他在《吴尺凫<玲珑帘词>序》中写道:“两宋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38]这便与《总目》崇尚清丽俊朗的词风有异曲同工之妙。
“雅”表现为:一方面词作语言要典雅,另一方面词作立意要“雅正”。《总目》强调词作语言须典雅,拒绝纤巧。如《安陆集》“提要”批评张先的词“以纤巧为病”[39]。《坦庵词》“提要”肯定赵师使词“萧疏淡远,不肯为剪红刻翠之文,洵词中之高格。”《无住词》“提要”指出陈与义词“不作柳亸莺娇之态,亦无蔬笋之气。殆于首首可传,不能以篇帙之少而废之。”[40]蔬笋气本是品评画作的术语,用僧人素食蔬笋比喻清淡本色,后来多用于比喻寒酸气,《总目》主张诗歌语言要摒弃低俗的气味,追求萧疏淡远的高格。《总目》主张词作内容要言之有物,以“雅正”为旨归,并以姜夔为雅词的标准。《山中白云词》“提要”云:“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至其研究声律,尤得神解。以之接武姜夔,居然后劲。宋、元之间,亦可谓江东独秀矣。”[41]“雅”文学观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诗经》中的“雅”指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雅”便有了“正”的意味。孔子《论语·阳货》将“郑声”与“雅乐”并举:“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42]孔子评价《诗经》“思无邪”[43],即指雅正。从此“雅”便有了义理上的审美含义。此后,“雅正”逐渐成为文学领域的一种审美追求,主张语言典雅,立意醇正。清人蔡世运说:“名之曰雅正者,其辞雅,其理正也。”[44]《珂雪词》“提要”赞美曹贞吉词:“其词大抵风华掩映,寄托遥深,古调之中,寄托遥深,纬以新意。”[45]可见《总目》主张词作内容要有所寄托,立意应“雅正”。《总目》追求典雅醇正的词学审美思想,继承了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的词学审美思想。朱彝尊作为浙西词派的领袖,以“雅正”论词,认为词作立意应与风人之旨相合,并将姜夔作为雅词的典范,朱彝尊称赞姜夔“填词最雅,无过石帚(姜夔字石帚)”[46]。
乾嘉时期正是浙西词派主盟词坛蓬勃发展的时期,并且浙西词派后劲人物王昶、郭麐、吴锡麟等人都与四库馆臣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可以看到,《四库全书总目》崇尚清雅婉转的词学审美思想,与浙西词派词学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浙西词派推尊“雅正”,朱彝尊《群雅集序》道:“予名之曰《群雅集》,盖昔贤论词必出于雅正,是故曾慥录《雅词》,鮦阳居士辑《复雅》也。”[47]朱彝尊填词入律的创作思想在《群雅集序》中也有论述:“徽宗以大晟名乐时,则有若周邦彦、曹组、晁辞膺、万俟雅言。皆名于宫调,无相夺伦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词,虽道学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声中律吕,而姜夔审音尤精。”[48]另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词学思想不仅深受浙西词派主张的清雅醇正思想的影响,也与乾隆皇帝提倡的醇正典雅文风契合,符合乾嘉时期儒家政教传统。《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悉禀天裁”的官方目录学著作,自然与官方意志相统一。
总体观之,《四库全书总目》词体“厥品颇卑”、词作“合辙入律”、词格“清雅醇正”的词学思想,兼融了词之体格、创制与审美,三者有机联系,统一于儒家的诗教传统。清乾嘉时期,文坛推尊儒家的诗教传统,认为《诗》是文学的源头,主张文学创作要复归雅正,《总目》的词学思想表现出以“诗教”观为统摄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清代集大成性质的目录学著作,蕴含着丰富的词学思想,这既是清代中期词学批评的集中体现,对晚清以来的词体接受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兼论梅里词派及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