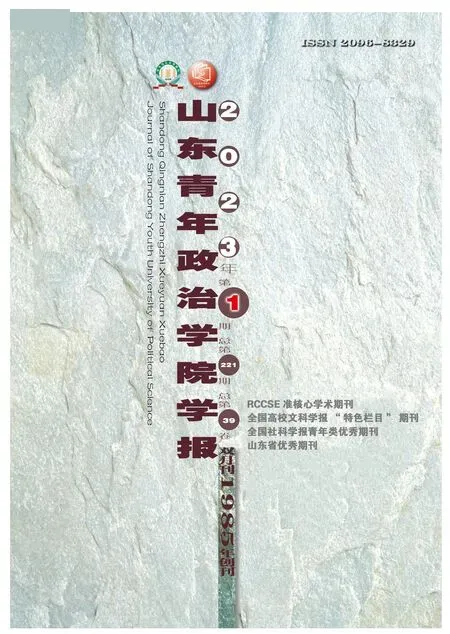透过注释的编纂史勘探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
——评谢慧聪著《<鲁迅全集>注释编纂史概论》
李宗刚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14)
谢慧聪博士的《<鲁迅全集>注释编纂史概论》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公开出版。作为参与和指导过她的论文写作的导师,想借此机会作些说明,既可以帮助读者对谢慧聪有更多的了解,又可以让读者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对这部学术著作有更好的把握。
一
谢慧聪于2014年秋季考取山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此期间,她除了较好地完成硕士学位的论文写作之外,还接受了较为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是文献资料整理方面的训练。缘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需要,我有一段时间沉潜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浩瀚海洋中,寻找有关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文献资料。正是在这一目标的驱动下,我关注到杨振声在大学管理、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典型性。但是,关于杨振声的已有文献资料和著作并不全面,这使我在研究杨振声的文学教育时颇费了一点精力,由此便产生了编选杨振声文献资料和研究资料合集的想法。
这一想法产生之后,我便考虑如何实施这一宏大的工程。如果单纯依靠我个人的力量,自然难以从学报编辑和论文写作中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这一工作,因此,我便考虑从自己所带的硕士研究生中选出一名可以潜心于资料汇编工作的助手。经过一番斟酌,我觉得谢慧聪具有这方面的潜质。她在考入研究生之前便有过基层工作的体验,深切地感受过现实生活的艰辛,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她没有多少功利心,能耐住寂寞,甘于坐冷板凳,富有韧性,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拼劲儿。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她时,果然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她愉快地答应了下来。于是,谢慧聪成为我在资料编选方s面的得力助手。
在编选杨振声文献资料和研究资料的过程中,谢慧聪沉潜于民国期刊数据库,搜索和整理杨振声文献资料和有关杨振声的研究资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宏大的工程。2016年7月,《杨振声文献资料汇编》(44万字)和《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49万字)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所辑校的杨振声的作品,不仅由新中国成立后业已出版的57篇增加到110篇,而且以原始版本为主,较好地还原了杨振声作品的历史原貌。正是在这一历练中,谢慧聪展现了她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非凡的毅力和聪慧,让我感到她是一个可塑之才。
2017年,谢慧聪又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由此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真正开始了独立飞翔的新历程。作为导师,我觉得在学生的培养上要注重因材施教,既要兼顾学生既有的学术素养,又要拓展其未来的学术发展空间。因此,在博士选题时,我觉得她可以对杨振声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也可以对鲁迅著作的注释进行系统研究。在杨振声研究方面,她已经完成了有关文献史料汇编和研究资料选编这类基础性工作,至于杨振声这一选题可否支撑起一部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大厦,则取决于她是否能够在未来的研究中拓展其深度和广度;在鲁迅著作的注释方面,她可以发挥既有的文献资料整理方面的特长。
鲁迅著作的注释这一课题,缘于我一段多年未了的学术情缘。30年前,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许多老师便开始从事鲁迅著作的注释编写工作,这使我较早看到了学科老师编纂的“红皮本”鲁迅著作。“红皮本”鲁迅著作的注释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作了很好的铺垫。然而,关于注释的演变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注释的历史演变所承载的时代变迁等文化信息,学术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由此切入研究对象,便可以打开一扇通向历史深处的大门。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我在10多年前曾经向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蒋心焕先生谈起过这一话题。蒋先生作为曾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学者,认为这个选题极有价值。为此,他还专门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鲁迅作品“红皮本”全部送给了我,希望我将来有机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然而,我的学术兴趣在后来逐渐地聚焦于五四文学发生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研究,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从事这一工作,而谢慧聪则是从事这一研究的最佳人选。2018年,当我向谢慧聪谈起鲁迅著作“红皮本”与《鲁迅全集》注释这一课题时,她表现出了足够的学术兴趣,并立志做好这一课题。于是,我便把蒋先生转赠给我的鲁迅著作“红皮本”悉数转赠给了谢慧聪,希冀学术研究在代际传承中发扬光大。
二
从事鲁迅著作“红皮本”与《鲁迅全集》注释这一课题,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需要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其一,《鲁迅全集》的注释经过诸多前辈学者的辛勤耕耘,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要想在此方面能够有所突破,其难度是较大的;其二,《鲁迅全集》注释具有“碎片化”的特征,要整合到一个学术体系中难度极大。然而,值得肯定的是,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谢慧聪较好地战胜了这两大困难,并顺利地把零散的注释整合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体系中。谢慧聪以鲁迅著作的 “红皮本”与 1981 年版《鲁迅全集》注释撰写为研究对象,集中梳理、发掘二者在注释方面的历史承继关系,又探讨了注释的选择和怎样撰写等问题,并由此上升到历史的维度加以阐释,使其研究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目标。2019年春节,谢慧聪在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中获得了答辩委员的认可,她的博士论文先后获得学校优秀博士论文和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谢慧聪的博士论文能够得到专家的认可,并获得优秀博士论文,我认为主要是源于以下三方面的学术创新:
其一,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几个历史节点的鲁迅作品注释的历史。谢慧聪的《<鲁迅全集>注释编纂史概论》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版《鲁迅全集》至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为时间节点,通过1958年版、“红皮本”、1981年版的编纂历程,串联起《鲁迅全集》注释的当代书写史,在纷繁芜杂的历史文献中打捞出注释撰写所勾连着的不为人所关注的、处于细枝末节中的“文学的力量”,进而完成了“红皮本”与两版《鲁迅全集》历史关系这一选题的研究。其整理完成的成果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是“红皮本”与两版《鲁迅全集》的历史关系,另一部分则是注释撰写与历史史实的关系解读。
其二,从整体上对鲁迅作品的注释进行了整合,把纷繁复杂的注释纳入一个相对合理的逻辑体系中加以学理性阐释。鲁迅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非常多,古今中外、林林总总,鲁迅作品的注释自然也就数不胜数。以历史化的视角和眼光阐述注释的变化原因,尤其是回到历史现场考察注释的撰写与变迁,并在此基础上对注释的产生、演变及影响进行学理性分析和研究便显得特别重要。事实上,鲁迅作品的注释,不仅可以使读者在解读鲁迅时抵达鲁迅所生活的时代,而且可以使读者切身体味到鲁迅作品注释生成的特定时代,并感悟到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潜在影响。实际上,鲁迅作品的注释作为出版社主导的工作,本身便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制导。由此一来,一条注释的撰写,不仅要查阅大量原始文献,对鲁迅作品中所涉人物、历史事件、方言俗语、历史典故、期刊社团、文学论争等了如指掌,而且要在既有注释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更要适合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接受习惯。因此,要从整体上对《鲁迅全集》的注释进行系统研究并非易事。值得肯定的是,谢慧聪通过她的博士论文对以上问题作了一次积极的回应。
其三,在对鲁迅作品注释的系统梳理和有机整合的基础上,注重发掘鲁迅作品的注释撰写变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注释的撰写也见证了建国以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实践了“小注释体现大历史”的观点。谢慧聪试图从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出发,以发掘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某种制导性规律,进而对学界关于“红皮本”的一些结论进行了重新反思和出新。对此,有学者认为,谢慧聪通过解读左翼人物、“现代评论派”“第三种人”、尼采等有争议的注释,阐述了其产生的理念与依据,是对当下“政治鲁迅”研究的良好呼应。一滴水可以折射出一个世界,一部《鲁迅全集》注释的编纂史便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
当然,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不断探索中绵延向前推进的,任何研究的结论都将是历史的“中间物”,谢慧聪的研究自然也不能例外。如果我们从更高的要求出发,还可以期待谢慧聪做得更好。对此,有答辩委员便期待她能够就“红皮本”对于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本的决定性影响作出更为精到的论述,更好地挖掘“红皮本”作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潜文本”的价值,还可以对从“文革鲁迅”到“新时期鲁迅”的鲁迅形象建构作出更深刻的历史考察,还可以就注释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在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作出更为精到的解读。答辩委员们的期待,意味着谢慧聪的学术研究之路还很漫长,还需要继续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
尽管谢慧聪还需要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跋涉,但就她在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而言,她已经初步窥见了学术真谛的光芒,并在沉潜于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体味到了从事学术研究给自己的人生带来的乐趣。她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始终没有忘记学术研究。2021年,正是在这一执着精神的驱动下,谢慧聪先后获得了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和教育部社科规划课题,她发表的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她关于鲁迅著作的注释研究初步获得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这无疑昭示着她已经迈入了学术研究的殿堂,期望她在学术研究上继续保持着这股矢志不渝、执着追求的精神,假以时日,相信定会再上新的台阶。
值得期待的是,当下学术界关于鲁迅作品的注释研究,已经开始呈现出蔚然成风的良好态势,尤其是有许多青年学者开始在这块园地里辛勤地耕耘,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值得赞许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无疑说明,谢慧聪正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个时代,学术研究开始注重回归于历史现场,注重在充分占有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富有新意的言说。我期待着,谢慧聪能够不负这个大好的时代,更好地潜心于学术,让人生在学术研究中焕发出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