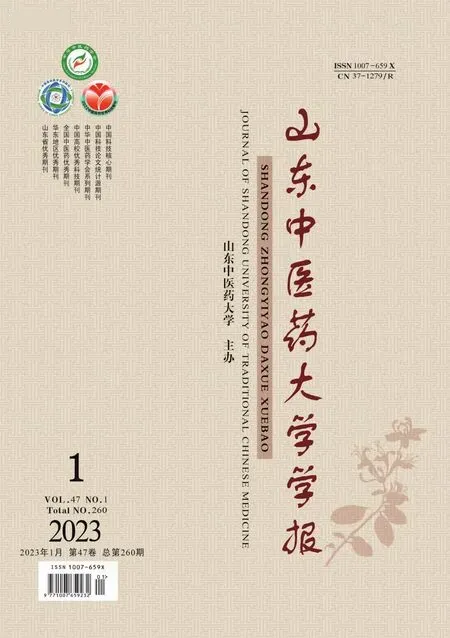《伤寒杂病论》癫狂病证治思路探析
彭爱能,赵永厚,赵玉萍,于 明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2.黑龙江神志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6)
癫狂病是中医神志病中最常见的疾病类型之一,根据患者证候属性之不同可分为“癫”和“狂”,二者虽有所区别,但在临床症状上不能截然分开,又能相互转化,故以癫狂病并称[1]。《黄帝内经》第一次提出癫狂的病名,并初步探讨相关病因及治法,如“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阳、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太阴、阳明”,形象地记录了癫狂病从抑郁转为躁狂的过程,提出相应的针灸治疗思路。及至汉代,张仲景行医时非常重视患者的精神状态,在《伤寒杂病论》中曾多次提及“其人如狂”“谵语”“躁烦”“如见鬼状”等,对癫狂病证治有较为具体的认识。笔者对《伤寒杂病论》中关于癫狂病的条文进行归纳分析,对张仲景治疗癫狂病的辨证论治思路进行探讨,以期为临床更好地运用经方治疗神志疾病提供借鉴。
1 病因病机
癫狂之病,病情复杂多端,其病因的追溯也较为复杂,在《伤寒杂病论》中,关于癫狂病的论述多见于六经变证,癫狂病多由于外感病邪之后,各种失治误治,或多种病邪交杂,或正虚邪实,病情恶化所致,普通的外感病邪一般不会直接导致其发生。
“谵语”“发狂”是张仲景记载较多的与癫狂病有关的症状。“谵语”即语声高亢有力,语言逻辑混乱,神识错乱[2];“发狂”不仅有语言的错乱,还有行为的异常,甚则“登高而歌,弃衣而走”[3]。“实则谵语,虚则郑声”,是张仲景对癫狂病虚实的重要论述。《黄帝内经》有云:“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强调辨“谵语”的病机多为“实邪内扰,上扰心神”,辨“郑声”的病机多为“气血亏虚,心无所养,神无所主”。《金匮要略》中云:“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阴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是张仲景对因虚所致癫狂的较为系统的论述,心阴衰而阳盛致癫,心阳弱则阴盛致狂,但对其治则治法未予深入探讨[4]。在《伤寒杂病论》中由实证引起癫狂病的条文居多,但在临床中也需重视各种虚证所致的癫狂病。现代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患病与遗传及幼时生长环境关系密切[5],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着先天肾气不足,或后天脾胃失养的情况。因此,补养脾肾也是癫狂病治疗的重要部分[6]。
1.1 太阳病篇
太阳病篇涉及“谵语”“发狂”的条文共15条,主要共同点在于癫狂发病均为外感邪气,经病程发展演变而来。所以在治疗过程中仍需注意其外邪是否已清,辨明病情所处阶段,在表者治表,在里者清里,半表半里之间者,表里俱除之。
《伤寒杂病论》中太阳病所致癫狂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一为太阳经病邪传入阳明,积于胃腑,郁而化热。如“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即是太阳病十三日不解,病邪已传至阳明,郁而化热,胃肠燥热,上熏于脑,致神昏而谵语;“伤寒八九日,下之……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伤寒八九日,邪气已成热,误下之后,邪热未去,里气亏虚,邪热客于胸中,胸满烦惊,邪热入胃出现谵语,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和解清热、镇静安神。二为太阳经病邪,随经入府,或妇人感邪,经水适来,热入血室,可致谵语,也可致惊狂。如“太阳病不解……下者愈”为太阳膀胱经病邪不解,随经入血府,热与血结,其人如狂,热迫血下,热随血下而愈;“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此为热入血室”是对于妇人热入血室所致癫狂状态的形象描述,妇人经期之时,血府空虚,此时感邪,外邪容易趁虚而入于血室,发为癫狂。三为太阳经证误用火劫发汗,热甚动血,或热甚亡阳,神明失守。太阳之病初起多有恶寒症状,经验匮乏者容易误认为其由寒邪所致,采用“寒者热之”的方法治疗,即误用火法。火法若用于太阳病已化热者,容易引起火热更甚,扰动心神,引发癫狂;若火劫发汗太过,津液大伤,气随津脱,阳气耗散,心神浮越,也可导致癫狂。四为太少两感,肝胆火热,上扰心神。对于出现“谵语”或“发狂”症状的患者,张仲景多次提到刺期门。期门者,肝经募穴也,刺期门可泄肝经之盛气。此类患者多存在少阳经病变,或为未感邪之前,本为肝阳亢盛之体,一旦感受太阳之邪,久而伤及脾胃,木行乘土,使脾胃更虚,肝经火热更甚,及至谵语发狂;或为太阳经与少阳经均受邪,两经之证同时或先后并现,太阳之脉,络头下项,少阳之脉,循胸络胁,均累及上中二焦,若不能及时清泻两经邪气,则邪气无出路,郁而化热,必发谵语。
1.2 阳明病篇
阳明病篇关于癫狂病的条文有14条,此为与急病、重病关系最为紧密的一部分。太阳病篇之癫狂病多初起于太阳经,病邪逐渐传变,及至癫狂之时,一般为多经受邪,非独太阳经。而对于阳明病,张仲景认为阳明居中,乃万物之所归,阳明感邪,无以复传,故阳明病所致癫狂多为本经之证。
阳明经为多气多血之经,朱丹溪曾说:“气有余便是火”。阳明经气血旺盛,容易滋生火热。足阳明之胃是受纳、转输、传送食物的器官,手阳明之大肠为传导之官,具有储存、变化和转运排泄的功能。胃有温热之气可助其接受、消化食物,大肠有温热之气可助其变化、传导糟粕[7]。胃与大肠的温热之气助其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但物极必反,若温热之气太过,则会引起阳明大热大渴之症。《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此总结了阳明病表现在外的最基本证候。柯琴言:“胃家实之外见者,其身则蒸蒸然……其汗则濈濈然……表寒已散,故不恶寒,里热闭结,故反恶热”[8]。阳明之热由于患者体质、诊治及时令节气等不同,其热势变化亦不同[9]。若胃肠津液亏虚,大肠糟粕未能及时排泄,热与糟粕相结,导致阳明腑实,可出现腹满谵语的症状;若阳明燥热与血相搏,热与血结,或燥热充斥,趁血室之虚而入,致热入血室,可表现为“下血谵语”;阳明病后期,燥热内结,伤津耗液,正气随之耗散,出现虚实夹杂的津伤便结证,病情较重亦可出现神志错乱与口干口渴并见;若阳明燥热太甚,大汗而亡津脱液,气随液脱,可出现亡阳之证,如“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介绍了亡阳谵语之脉与疾病转归的关系。汗出亡阳之后,若脉短,则是营卫不行,脏腑不通,为死脉;若脉自和,则说明虽津液亏虚,但不至于脱,胃气尚存,如抢救及时,性命可保。
阳明经所致癫狂虽多为本经之证,但亦有两条条文提到阳明兼证,一为三阳合病,一为太阳阳明并病。三阳合病,多条经脉感邪,燥热结于阳明病则腹满身重、谵语,热与湿郁于少阳则面垢,伤于太阳膀胱则遗尿,但以阳明证最重。太阳阳明并病,太阳证罢,因此无表证,热郁于阳明,发为潮热,令手足汗出漐漐,大便难而谵语。
阳明病所致癫狂病虽病情较单纯,但其发病多较为严重,进展迅速,预后较差,张仲景在阳明病篇多次提到癫狂后期的死证,如“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因此对于阳明实热证候应早期辨证,及时根据需要使用清法、下法等,以免病情恶化,以致诊治不及。
1.3 少阳病篇
少阳经之病邪多在半表半里之间,以口苦、咽干、目眩为主要症状。少阳之邪最先侵犯的部位为肝胆,胆为中精之府,主决断,咽为胆之使,胆火上扰,故口苦咽干;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故少阳病常累及目。“烦”是张仲景在少阳病篇最常提到的证候之一,“胸满而烦”,或“躁烦”,或“郁郁微烦”,诸烦躁之证均与少阳病枢机不利、肝气郁滞、胆火内扰有关,烦躁之证已有心神被扰之势,若诊治不力,亦可发为癫狂病。
1.4 三阴经篇
三阴经之病是疾病进展的中后期阶段,以虚证多见,癫狂之记载较少,但亦有虚实夹杂,或因虚致实,发为癫狂病者。如“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少阴病,本虚寒,且津液不足,若以火劫,强制发汗,伤及少阴之阴,则火邪内留,发为谵语。
2 辨证论治及常用方药
张仲景创立了六经辨证及脏腑辨证的思路,并形成一个体系,后世之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三焦辨证等,均是在其基础上的拓展和深入。张仲景非常重视辨证论治,对同样表现为“谵语”“发狂”症状的病证,详细追溯其发病缘由,观察发病时全身症状的细微差别,审证求因,并详细记载在册,为后世医家提供了辨病依据和许多流传百世的名方。
2.1 从热论治
癫狂病发病与热关系密切,在由热证所致癫狂病中诸承气汤的论述最多,由此可见通下之法是治疗癫狂病的重要方法之一。但通下之法最易伤及正气,因此张仲景在使用承气汤治疗诸疾时,重视患者本身的正气强弱,是否可耐受攻下之法,并多次强调中病即止,防止正气虚脱。针对不同程度的阳明腑实证治以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若能食,但硬耳”之痞满燥实俱全的阳明腑实重证,用大承气汤泻下荡涤胃肠实热;“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硬”之痞满实而燥热较轻的阳明腑实轻证,用小承气汤轻下热结;“胃气不和,谵语”之燥实而无痞满的胃肠燥热证,用调胃承气汤调和肠胃,祛除胃肠之热。此外,桃核承气汤是由调胃承气汤加桃仁、桂枝而来,对于蓄血如狂之热入血室证最为相宜,其不仅有大黄、芒硝的泻下作用,还有桃仁活血散瘀之效及桂枝通阳化气之功,使热气得散,瘀血得消,狂证乃解。除诸承气汤之外,张仲景还创立了其他治疗癫狂病的清热方。对于伤寒八九日,邪热传于少阳阳明之癫狂,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和解清热、重镇安神。承气汤以治疗阳明腑证为主,而对于阳明经证,张仲景用白虎汤,辛凉透表的同时养胃生津,最终大热去而神志清,病情好转。
2.2 从瘀论治
血瘀致狂起源于《黄帝内经》,有“血气未并……故为惊狂”之说。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创立了气血学说,并提到“癫狂一症……乃气血凝滞脑气”,认为癫狂是由气滞血凝、脑络闭塞所致,并创立了著名的癫狂梦醒汤,理气活血、化痰消瘀,对痰瘀互结型癫狂病效果明显。及至现代,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较正常值偏高,经活血化瘀疗法后其血液流变学指标均可下降甚至恢复正常[10]。《伤寒杂病论》中的抵当汤、桃核承气汤均有从瘀论治癫狂病之意。抵当汤与桃核承气汤虽同为治疗血证癫狂,但二者亦有区别。桃核承气汤主要功效在于泄热,其主治之证即为热入血室,然血室之证多兼有瘀,故以桃仁逐瘀;抵当汤攻逐之力最猛,其中虻虫、水蛭均为破血逐瘀之要药,再加上桃仁及大黄活血通经,整方的攻积破滞之力远甚于桃核承气汤[11]。就两方所治症状而言,抵当汤病情更重,张仲景对桃核承气汤的少腹症状描写为“少腹急结”,且有“血自下,下者愈”,可知此为热与血结尚浅;而抵当汤为“少腹硬满”,且“身黄,脉沉结”,可知此时瘀热已深结,唯有用攻坚迫瘀之猛剂方可使蓄血下、瘀热除。抵当汤药性峻烈,因此张仲景在抵当汤之后提到抵当丸,意在峻药轻投,在临床应用中对于瘀血重,但体质不耐攻伐者,可用抵当丸徐徐图之。
2.3 从虚论治
疾病初起常与外邪有关,表现为多种实证,但在病情发展阶段,人体正气奋起抗邪的过程中,常耗气伤血,伤津动液。若正邪交争过程中,正气较盛,驱邪外出,调养得当,则病情得以恢复;若正虚邪实,或治疗方法不当,更伤正气,则可导致心气大伤,或亡阴亡阳,以致心神无所依托,发为癫狂病。张仲景对于误用火法,致津液大出,阳气亡脱之惊狂,创制了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以桂枝、炙甘草辛甘化阳,复已伤之阳气;龙骨、牡蛎镇静安神兼收敛固涩;蜀漆辛以散残余之外邪,与龙骨、牡蛎升降相因;生姜、大枣甘缓和中,共助心阳恢复,心神回归。张仲景治疗癫狂病虽没有专门创制滋阴补液的方剂,但多次提及癫狂病患者津液受损的情况,如“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以强责少阴汗也”,误用火法或热邪壅滞,均可损伤津液,因此在癫狂病的治疗中,需要注意患者津液的丢失情况,适时加入滋阴补液的药物。
2.4 妇人癫狂治疗
有研究表明,精神疾病发病、治疗、转归过程中性别差异明显[12]。女性的精神状态容易受到经期、排卵、孕产等影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中医角度来说,女子以肝为先天,以血为用。女子在经、带、胎、产过程中,失血耗血,此时体质较往日虚弱,更易感邪,因此张仲景对于妇人癫狂病,非常重视结合其身体周期而辨证施治,多次在条文中提及“经水适来”,强调月经周期对妇人疾病的影响。女性疾病与肝关系密切,肝主疏泄、畅达情志。女性的情绪通常更加敏感细腻,易肝气郁结,且肝为藏血之脏,如肝气郁滞,会导致血行不畅,气滞血瘀易生癫狂之证,因此张仲景多次提到疏泄肝胆以治疗女性癫狂病。
对妇人杂病,张仲景认为“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当“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妇人杂病,虽变化多端,但究其缘由,不外乎虚、积冷、积气三个方面。妇人病之所以异于男子,以其有月经故也,若经不调,则百病皆生。崩漏之病,血耗过多,易生血虚;女子本为属阴之体,最易生虚寒,若寒与血结,积于胞门,则血凝气结而不行、经行不畅;妇人多思虑,思虑太过则气结,气结血亦结;故张仲景言“状如厥癫……非有鬼神”。张仲景把此类疾病所致的癫狂归为带下病。带下者,此处乃胞中冲任血病之总称。后世医家李彦师等基于张仲景的论述,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方剂,如妇人虚寒经闭用温经汤,经络凝结用大黄虫丸,呕吐涎唾用干姜半夏散,绕脐寒疝轻者用当归生姜羊肉汤,重者用大乌头煎[13]。
3 结语
西医一般认为癫狂病与精神分裂症类似,国内外对其病因病理的研究非常丰富,但仍以“多巴胺假说”“谷氨酸生化假说”等多种假说为主,尚存在许多未能认识全面的地方[14]。目前,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以各种抗精神疾病药物为主,但其对中枢神经、消化、血液等多系统存在不良反应[15],这也是近年来抗精神病药物种类不断更新的原因。研究表明,中医治疗能有效缓解抗精神疾病药物带来的腹胀、便秘、头晕、头痛、嗜睡、乏力等多种症状[16];其次,中医治疗疾病重视整体观念,癫狂病从整体而言,系由阴阳失衡、脏腑功能失调所致,《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不胜其阳者,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阴阳的任何一方偏胜或偏衰都可成为癫狂之因。中医审其阴阳、和于四时、调其脏腑,治疗癫狂病常有出其不意的效果,能弥补西医治疗之不足。研究中医对癫狂病的认识有助于临床更好地发挥其优势,对更准确的辨证求因和处方施药具有重要意义。
张仲景论治癫狂不拘泥于一证一病,其治法灵活,方药随证加减变化。临床中所见患者体质各异,治疗需要灵活变通,但万变不离其宗,从经典发散辨病思路,最终回归于经典,找到其原始依托,所谓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对于《伤寒杂病论》中治疗其他疾病的方药,若辨证得当,亦可用于癫狂病证治。如王松龄用三物白散加减,以吐法治疗痰涎阻于胸膈的癫狂病,显著效果[17];赵友良用附子汤治疗阴盛阳虚痴癫,用小柴胡汤治疗胆火内扰痴癫,用黄连阿胶汤治疗阴虚有热癫狂,用十枣汤治疗悬饮内停癫狂,均取得满意疗效[18]。癫狂病初起以实证为主,或为郁热,或为痰湿,或为血瘀,当泄其实,或下之,或清之,或散之;中期正气受损,虚实夹杂,症状常错综复杂,当准确辨其病位,攻邪不忘扶正;后期正气虚弱,甚则亡阴亡阳,当辨其虚损,以补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