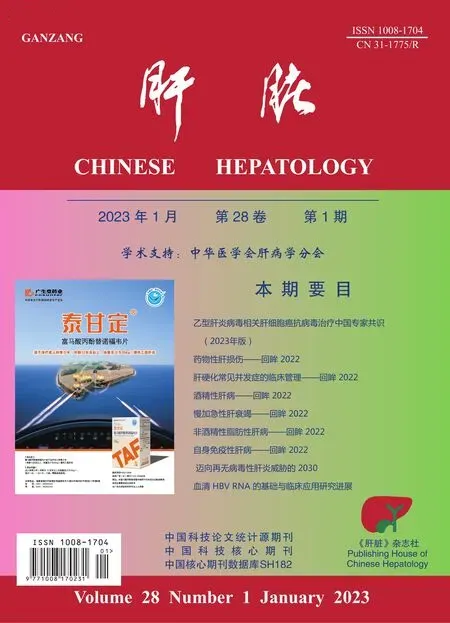酒精性肝病
高沿航
作者单位:130021 长春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
酒精性肝病(alcohol-associated liver disease, ALD)是全球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球酒精消耗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05年全球15岁及以上人群纯酒精消费量为5.5 L、2016年为6.4 L,预计到2030年将会增至7.6 L[1-2]。全球饮酒人数也高达24亿之多,过度饮酒者约2.8~3.7亿,酒精性肝硬化代偿期患者约2 360万,失代偿期患者约250万人,酒精相关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患者约30万人,ALD相关死亡患者占全球总死亡患病人数的1%[3]。在过去30年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酒精消耗的增加。从2005年至2016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人均纯酒精消耗量增长了76%,根据2022年WHO统计报告显示为6.0 L,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8 L[1,4],由此导致我国近年来ALD的发病及病死率情况也呈迅速增长趋势。
长期慢性饮酒所导致的严重肝脏疾病负担以及全身其他系统的多器官损害,尤其是恶性肿瘤发生引人注目。如何加强对过度饮酒人群及ALD人群的早期筛查,如何开展更为深入的机制探索为后续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理论支撑,一直以来都是热点难点领域。在辞旧迎新之际,现对既往一年间ALD领域较具代表性的成果从疾病负担、机制探索、诊断、治疗等四个方面进行回顾,温故知新,期待在新一年中有更多的进步。
一、 疾病负担
全球超过 50% 的肝脏疾病负担与过度饮酒有关,亚太地区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同时覆盖了全球 62.6%的肝病相关死亡病例,但亚洲地区 ALD的流行特征尚缺乏系统描述。
我国学者对近20年亚洲地区ALD的流行特征开展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5]。结果显示,ALD的总体患病率为4.81%(95%CI:3.67%、6.09%),男性[7.80%(95%CI:5.70%~10.19%)]高于女性[0.88%(95%CI: 0.35%~1.64%)];随着时间的推移从2000—2010年的3.82% (95%CI: 2.74%~5.07%)显著增加至2011—2020年的6.62%(95%CI: 4.97%~8.50%)。在469 640例肝硬化病例中,ALD占比为12.57%(95%CI10.20%, 15.16%)。在82 615例HCC病例中,ALD病因占比为 8.30%(95%CI: 6.10%,11.21%)。不同地域的肝硬化和HCC中酒精病因的占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肝硬化病例中酒精性病因占比最高的是印度[37.12%(95%CI:31.60%~42.82%)],其次为韩国 [23.15%(95%CI:12.91%~35.31%)]、日本[19.11%(95%CI:15.04%~23.97%)]。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以色列四国或地区肝硬化中ALD病因占比接近,约为9.48%(7.5%,11.92%)。亚洲地区肝硬化病例中酒精性病因占比最低的国家是伊朗和土耳其[2.48%( 95%CI:2.00%~3.00%)],这可能与这两个国家的人多信奉禁止饮酒的伊斯兰教有关。HCC病例中酒精性病因占比最高的也是印度[16.79%(95%CI:7.93%~28.06%)],其次为新加坡[12.58%(95%CI:11.44%~13.81%)],日本[8.79%(95%CI:5.66%, 13.67%)],中国等五国HCC病例中ALD因占比最低,约为[5.80%(95%CI:4.04%~8.26%)]。可能与HBV、HCV感染所致的HCC较多有关。随着我国HBV、HCV防治取得较好效果,ALD相关肝硬化和HCC占比可能会进一步升高。综上,亚洲人群 ALD 患病率、肝硬化和HCC中酒精相关病因占比低于西方国家人群。然而,在21世纪过去的22年间,ALD 患病率随时间推移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亚洲慢性肝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来自瑞士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全国性队列研究[6]显示,3 453例经肝活检证实的ALD患者在肝脏特异性病死率、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病死率以及恶性肿瘤病死率等方面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长期饮酒所导致的恶性肿瘤疾病负担引人注目,在3 410例包括各个疾病阶段的ALD患者中[7],HCC的10年累积发生率为3.7%,全身各系统癌症10年累积发生率为12.0%;进一步,在酒精性肝硬化的群体中,HCC 10年累积发生率增加至5.0%,全身各系统癌症10年累积发生率为12.8%。
ALD疾病负担日益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特殊患者群体对因治疗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目前,全球范围内降低酒精消耗的策略包括征税、减少供给及限制促销;同时,从社区卫生中心开始即早期筛查过度饮酒人群和ALD患病人群[3]。社会因素的变迁也会显著影响ALD的患病率和病死率。自2020年3月开始,随着COVID-19在欧美的大流行,居家、隔离、失业、医疗挤兑以及对疫情的恐惧等诸多因素导致因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失代偿以及酒精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住院患者显著增加[8-10]。经模型预测COVID-19大流行后的1、3、5年间,酒精消耗量、酒精相关病死以及失代偿期肝硬化发生率都呈现上升趋势[11]。
二、 发病机制
ALD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尚存诸多未知领域,炎症与免疫、肠道微生态及宿主遗传易感性等方面近年颇受关注。白细胞介素-11 (IL-11)是一种促纤维化、促炎症的细胞因子,对实质细胞和上皮细胞具有较高毒性。在一项包括50例酒精性肝炎(alcoholic hepatitis, AH)患者、110例肝硬化患者及19名健康志愿者的队列中测定IL-11血清浓度和组织表达水平,并在另外一个独立的患者队列中重复了前述结果(n=186);体外研究中,将原代人肝细胞暴露于酒精。对酒精喂养的野生型小鼠,用中和性小鼠IL-11受体抗体(抗IL-11RA)治疗,并监测反映ALD严重程度的标记物。结果显示,IL-11血清浓度及肝脏表达水平随肝病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升高,以AH患者多见。在多变量cox回归中,血清水平高于6.4 pg/mL是代偿性和失代偿性肝硬化患者无移植生存的终末期肝病独立危险因素。在小鼠中,酒精诱导的肝脏炎症的严重程度与肝脏IL-11和IL11RA表达的增强相关。在体内和体外实验中,抗IL11RA降低了致病信号通路(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c-Jun N端激酶,NADPH氧化酶4),并保护肝细胞和小鼠肝脏免受酒精诱导的炎症和损伤。肝细胞中致病性IL-11信号通路在ALD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可作为无移植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阻断IL-11信号可能是治疗人类ALD,特别是AH的一种治疗选择[12]。
近年,肠道微生态促进ALD发生、发展的影响是研究热点领域。长期饮酒破坏肠道的机械性、化学性、生物性等屏障,导致“肠漏”,进而促进内毒素血症、真菌毒素血症以及肠脑病等诸多并发症的发生。饮酒频率是影响微生物群变异的重要因素,使用同位素[1-13C]标记乙醇,宏基因组学和元转录组学在酒精喂养和灌胃小鼠模型中探索了酒精代谢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13]。通过元转录组学发现,肠道菌群对酒精喂养的反应是通过激活乙酸的异化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直接代谢乙醇。血液乙酸浓度在饮酒期间升高,通过补充三乙酸甘油增加系统乙酸水平,未发现对肝脏疾病有任何影响,但在小鼠模型中可诱导类似于慢性酒精喂养的肠道微生物群改变,与乙醇相关的肠道微生物群变化是乙酸水平升高的伴随效应。
宿主遗传易感性对于全面认知ALD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酒精性肝硬化患者HCC发生年风险高达2.5%,部分宿主遗传风险因素已被确定,鉴定酒精性肝硬化患者发生HCC新易感位点将在肿瘤的二级预防中发挥作用。来自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和英国招募酒精性肝硬化和HCC患者(n=1 214例)及非HCC对照组(n=1 866例),纳入一项采用病例对照设计的两阶段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另外设立一个包括1 520名过度饮酒但无肝病证据的验证队列,以控制酒精滥用产生的关联效应。PNPLA3中的rs738409变异和TM6SF2中的rs58542926变异之前与酒精性肝硬化患者HCC风险增加相关,在全基因组意义上得到证实。在联合荟萃分析中,TERT(端粒酶逆转录酶)中一个新的位点rs2242652(A)也与HCC风险降低相关,具有全基因组显著性(P=6.41×10-9,OR=0.61 (95%CI0.52~0.70)。在校正性别、年龄、体质指数和2型糖尿病后,这种保护性关联仍然显著(P=7.94×10-5,OR=0.63 (95%CI0.50 ~ 0.79)。TERT中rs2242652(A)的携带与白细胞端粒长度增加相关(P=2.12×10-44)。这项工作明确了TERT中的rs2242652作为酒精性肝硬化患者发生HCC的保护性因素[14]。
三、 诊断
不同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ALD一直缺乏较为完善的组织学分级和分期系统。SALVE组织病理学组(SHG)开发并验证了一种可用于ALD临床和全组织学谱系分析的分级和分期系统,并在445名跨国队列患者中评估了其预后效用[15]。在这一系统中,将脂肪变性、活动性(肝细胞损伤和小叶中性粒细胞浸润)以及胆汁淤积的半定量评分来描述SALVE分级。ALD引起的脂肪性肝炎的组织学诊断(histological ASH, hASH)是基于肝细胞气球样变和小叶中性粒细胞的存在。纤维化分期采用了临床研究网络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分期系统和Laennec分期系统,反映ALD纤维化的类型和程度。从无纤维化到严重肝硬化,有7个SALVE纤维化阶段(SFS)。在整个研究队列中,长期预后与活动级别、胆汁淤积以及肝硬化严重程度相关。在失代偿ALD中,短期不良预后与活动级别、hASH和胆汁淤积相关(P=0.038、0.012和0.001),而在代偿ALD中,hASH和严重纤维化/肝硬化与无失代偿生存相关(P=0.011和0.001)。在多变量分析中,严重肝硬化在整个队列中成为预测长期生存的独立组织学因子。严重肝硬化和hASH被认为是失代偿性ALD短期生存的独立预测因子,也是代偿性ALD无失代偿生存的独立预测因子。SALVE分级和分期系统是一种具有可重复性以及可预测预后的体系,可用于评估ALD疾病活动性和纤维化程度。
虽然上述分析能够有力推动ALD的系统性评估,但目前尚缺乏有关ALD从从未失代偿的ALD (ndALD)到危及生命的失代偿表型AH的多维度的差异性研究。通过建设国际性多中心观察性队列[ndALD患者的回顾性队列(n=110)和AH患者的前瞻性队列(n=225)],从临床、组织学和分子特征等几个方面揭示两种疾病表型背后的故事[16]。在平衡两组年龄和平均酒精摄入量等基线指标后,AH患者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比值高于ndALD患者,γ-谷氨酰转肽酶水平低于ndALD患者;AH患者表现出严重的肝衰竭和病死率增加,ndALD的1年病死率为10%,AH为50%。组织学上,两组患者脂肪变性程度、气球样变程度和细胞周围纤维化程度相似,而进展期纤维化、Mallory-Denk小体、胆汁淤积、严重中性粒细胞浸润和胆管反应在AH患者中更为常见。转录组分析显示,与ndALD组相比,两种表型均存在严重的基因失调,ndALD的特征是参与微粒体和免疫反应的基因表达失调,而AH的疾病发展导致参与肝细胞重编程和胆酸代谢的基因明显失调。综上,在酒精摄入量相当的情况下,AH患者与ndALD患者相比,肝功能水平不佳。胆汁淤积、严重纤维化和胆管反应是AH的显著特征,同时出现更为显著的基因表达失调。
多种组学检测技术的发展积极助力ALD机制及诊断研究。利用肝脏-血浆配对蛋白质组学方法来推断分子ALD病理生理学特征,探索血浆蛋白质组学在596名受试者(137名对照和459例ALD患者)中的诊断和预后能力,其中有360人进行了肝活检的组织学评估[17]。基于质谱(MS)的蛋白质组学工作流程,在较短的3周测量时间内分析了所有血浆样本和79份肝脏活检。在血浆和肝活检组织中,ALD组代谢功能下调、纤维化相关信号和免疫反应上调。机器学习模型识别出的蛋白质组学生物标志物面板比现有的临床检测更准确地检测出显著的纤维化(ROC-AUC:0.92,准确度:0.82)和轻度炎症(ROC-AUC:0.87,准确度:0.79)((DeLong’s test,P<0.05),在预测未来肝脏相关事件和全因死亡率方面具有良好的准确性,Harrell's c指数分别为0.90和0.79。基于该诊断模型在研究和炎症队列中所显示出的良好性能,为未来将MS作为肝病常规检测奠定了基础。
ALD作为代谢性肝病,代谢风险因素对疾病进展(尤指纤维化)的影响不容忽视。如在代谢风险因素基础上叠加遗传易感性,是否可进一步增加酒精性肝硬化的发生风险?目前,尚不能识别这类高风险人群,利用新近开发的遗传风险评分可尝试回答上述问题。该评分体系包括两个危险因素——糖尿病和高遗传风险评分,同时具备已知高遗传风险评分及糖尿病的过度饮酒者,酒精性肝硬化的发生风险增加超过10倍,使用这个评估系统可在高危患者中对酒精性肝硬化进行早期和个性化管理[18]。胰岛素抵抗是ALD患者肝纤维化阶段和肝脏炎症的最强预测因子,遗传易感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风险[19]。
四、 治疗
AH新药临床试验长期以来进展迟缓,白介素-22(IL-22)在治疗重症酒精性肝炎方面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令人兴奋。与此相关的进展中,口服聚乙二醇化Toll样受体7(TLR7)配体可通过诱导肠道IL-22,改善ALD[20]。TLR7是单链RNA的模式识别受体,其激活可防止肝纤维化。在AH小鼠模型中,小鼠慢性酒精摄入诱导肝脏脂肪变性、损伤和炎症,TLR7缺乏加重了这些影响,TLR7激动剂1Z1对AH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口服1Z1具有良好的耐受性,防止肠道屏障破坏和细菌易位,从而抑制乙醇诱导的肝损伤、脂肪变性和炎症。此外,1Z1处理上调了肠道上皮抗菌肽Reg3b和Reg3g的表达,通过分别减少和增加拟杆菌和乳酸菌的数量来调节微生物群。同时,1Z1可上调肠道白细胞介素(IL)-22的表达。IL-22缺失可消除1Z1对酒精诱导的肝脏和肠道损伤的保护作用,肠道IL-22是1Z1介导的保护作用的重要媒介。TLR7信号在AH小鼠模型中发挥保护作用,TLR7配体1Z1具有治疗AH的潜力。
与重症酒精性肝炎(SAH)疾病进展相比,等待新药成功上市的喜悦略显漫长。基于现有的药物治疗手段,面对大量SAH患者无法实现戒酒6个月即走向死亡的现实,早期肝移植进入了医生的视野。尽管已有前瞻队列证实,与戒酒满6个月的择期失代偿性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相比,早期肝移植的SAH患者并未增加复饮的几率、也未减低移植物存活的几率,争议一直此起彼伏。部分原因是SAH患者可以发生自发性恢复(SR)。通过回顾性研究对144例SAH患者(中位年龄45.5岁,68.1%为男性)进行分析[21]。其中,49例(34%)接受了肝移植,95例(66%)未接受肝移植,后者有34例(23.6%)经历了SR。发生SR的因素是年龄、国际标准化比值以及较低峰值MELD。只有7例(20.6%)患者达到了MELD <15、无腹水或HE的代偿状态。接受早期肝移植的患者与SR患者相比,生存期有所改善。与戒酒和接受肝移植的患者相比,复饮的SR患者生存期减少。在所有6个月的AH幸存者中,只有肝移植与死亡率风险降低相关。大多数SR患者继续经历终末期并发症,肝移植是降低死亡率的唯一因素。
除SR以外,早期肝移植另外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即为复饮。尽管有早期队列研究结论,仍然有工作小组进一步评估了SAH患者早期肝移植术后2年酒精复饮的风险。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19所医院开展了一项多中心、非随机、非劣效性对照研究。前瞻性招募了三组患者:全部患者为药物治疗无效的SAH患者,早期移植组符合早期肝移植的条件;标准移植组为戒酒至少6个月后列入肝移植的酒精性肝硬化患者;不适合早期肝移植组为治疗无效且根据选择评分不适合早期肝移植的SAH患者。主要终点为采用时间轴跟踪(TLFB)方法,考察早期移植组与标准移植组移植后2年酒精复发率的非劣效性;次要结局为复饮模式、早期移植组与标准移植组的移植后2年生存率、早期移植组与不符合早期移植组和历史对照组患者相比的2年总生存率。结果提示,早期移植组与标准移植组的非劣效性未能得到证实。早期移植组与标准移植组移植后2年生存率相似[HR:0.87 (95%CI0.33 -2.26)];早期移植组的2年总生存率高于不符合早期移植条件的组和历史对照组[HR:0.27 (95%CI0.16 - 0.47)和0.21(0.13 - 0.32)]。该研究未能就早期肝移植和标准肝移植在移植后酒精复发率方面得出非劣性结论,早期肝移植术后复饮者较多[22]。
这项前瞻性对照研究证实了SAH早期肝移植的重要生存获益,但早期移植后的复饮问题也面临挑战,因此,如何能减少移植后的复饮成为接受肝移植术后患者的重要慢病管理问题。随着对肝移植术后复饮的预测因素和供肝影响的认知不断提高,利用综合、多学科和多模态的方法来治疗肝硬化移植术后患者的过度饮酒可能改善患者的预后。充分考虑肾功能不全等共病因素后,对于肝硬化患者使用如阿坎酸、巴氯芬等药物控制复饮是可行的,该药与肝移植后常用的免疫抑制剂没有明显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将药物治疗与行为治疗及移植中心的医疗护理相结合,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预防复饮的潜力[23]。
五、结语
ALD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肝脏相关发病率、病死率和肝移植适应证的主要原因。虽然,ALD基础和临床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众多令人瞩目的进步,但尚存诸多未被解决的问题[24]: (1)利用大型管理数据库研究ALD的疾病负担;(2)开发AH非侵入性诊断的生物标志物及评估疾病预后标志物;(3)确定ALD和AH的治疗靶点;(4) 建立预测预后或移植后酒精复饮的准确模型,作为制定治疗方案及肝移植候选标准的统一方案的基础;(5)实施多学科综合管理模式,治疗肝病的同时管理过度饮酒等。未来,需要开展更多前瞻性、多中心的研究来解决诸多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采用医疗多学科合作联合护理管理模式积极改善ALD患者的长期预后。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