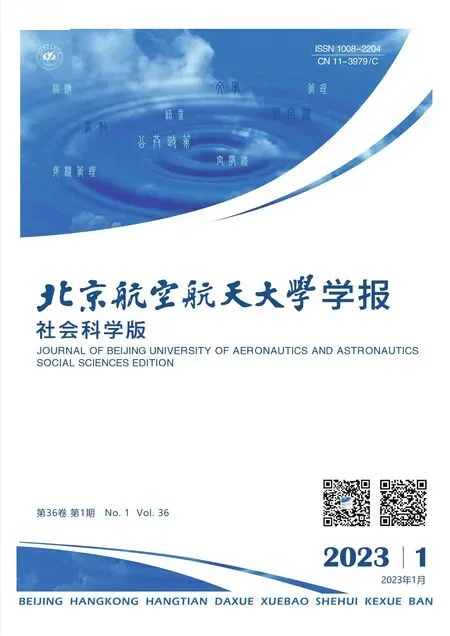信息网络犯罪证据问题的特殊性及其回应
冯俊伟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从证据法的发展趋势来看,证据法正在走向分化。威廉·特文宁也曾提出了一个证据法与一系列证据法的问题[1]。刑事证据法与民事证据法不同,进一步地,不同类型刑事案件所面临的证据问题也存在差异。相较于传统案件,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存在特殊性,这是有关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部门规章、法律文件的基本逻辑起点;其在证据问题上的特殊性也已被广泛关注,包括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办案更加依赖电子数据、电子数据可能在境外存储、电子数据取证难、电子数据保管要求高、电子数据检验技术性强等。在上述背景下,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下简称“两高一部”)颁发的《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等法律文件都在程序和证据方面对信息网络犯罪的特殊性作出了回应。为了进一步强化对信息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2022年9月,“两高一部”又颁发了《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22年《意见》”)。可见,关于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证据问题的法律规范正在不断增多。
在“两高一部”颁发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法律文件中,除了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外,还着重对信息网络犯罪的调查取证、证据可采性和案件事实认定等方面的内容作了特殊规定。从整体上来看,一方面,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信息网络犯罪的调查取证,丰富了中国信息网络犯罪的证据规则,降低了案件的证明难度,推进了信息网络犯罪刑事程序的体系化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关于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取证和证据运用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刑事诉讼法之外规定新的调查取证措施,其正当性需要反思,如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冻结电子数据、远程勘验等。从法律内涵上来看,这些调查取证措施的具体内涵如何界定,现场提取、在线提取与刑事技术、技术侦查措施如何区分,远程勘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上的勘验措施是什么关系[2-3],都有待进一步讨论。更为关键的是,在线提取、现场提取、远程勘验等措施的区分缺乏权利保障逻辑,在线和现场等的区分并不能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进行有效对接。从规范适用上来看,这些调查取证措施的适用程序包括哪些,又该如何保障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虽然相关部门规章、法律文件中作了部分规定,但这些规定不仅内容不一,还缺乏与法律保留、正当程序保障等的衔接。
第二,规定了调查取证的多元方式,缺乏对权利保障问题的有效回应。一是向网络服务者调取证据。2022年《意见》规定,公安机关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的,应当制作调取证据通知书,注明需要调取的电子数据的相关信息。二是抽样取证。一些司法解释、法律文件中规定,对于数量特别众多且具有同类性质、特征或者功能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办案机关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或者数量选取证据。三是跨区域取证。即中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办案部门之间的协助取证,包括协助远程取证(如远程讯问)和协助地办案机关代为取证等。四是跨境取证。主要是通过刑事司法协助、执法协助等途径,取得位于境外的各类刑事证据。这些取证方式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保障被追诉方的程序参与及如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相关法律文件还应当作出进一步规定[4]。
第三,更加关注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未形成关于电子证据可采性的规范体系。证据法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通过限制一些证据材料进入法庭使用,以实现对调查取证行为的有效规制。但在中国证据规则体系化不足的现实情形下,相关法律规定更加关注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证据法对调查取证行为的规制作用有限。“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7条规定了违反电子数据提取、收集程序的瑕疵证据补正规则;第28条则仅规定,电子数据无法保障真实性时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此外,现有法律文件中对《刑事诉讼法》第56条中“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是否包括非法取得的电子数据的问题未作回应,对于通过违反法定程序或损害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权利等方式获得的电子数据也未明确是否排除,实践中更多采取的是不排除的立场。
第四,规定了“综合认定”的事实认定方法,模糊了法定证明标准的要求。正如一些学者所关注到的,在涉及信息网络犯罪的部分司法解释、法律文件中出现了“综合认定”这一事实认定方法[5-6],这一方法明显区别于“通过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的证明”。例如,“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第4项规定:“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等原因,致拨打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的证据难以收集的,可以根据经查证属实的日拨打人次数、日发送信息条数,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时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等相关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中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可以有不同实现方式[7],但不应以“综合认定”等方式模糊法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笔者认为,中国相关立法在关注信息网络犯罪证据问题的特殊性并进行积极回应的同时,还应当回应证据法理、程序法理的基本要求,做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证据问题的解决应当尤其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电子数据取证方面,适应信息时代犯罪行为的特点,构建网络犯罪侦查措施体系,既对信息网络犯罪侦查进行明确授权,也对实践中存在的各种实质上的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重视取证措施的明确性、取证程序的规范性、取证过程的透明性和取证过程中的权利保障等。
第二,在电子数据可采性方面,要区分一般语境下的电子数据与法律语境下的电子数据,防止生活场景中的、非刑事程序中的电子数据毫无障碍地进入刑事诉讼中来作为证据使用。重视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完整性,建构以法律要求和技术标准为共同基础的电子数据可采性规则。
第三,在证据综合运用方面,对于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事实认定困难的难题,应当从提高办案人员网络犯罪侦查取证能力、强化数据平台履行合规义务、促进国际司法与国际执法合作等方面进行破解,不宜在相关法律文件中对证据要求、证据标准进行差异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