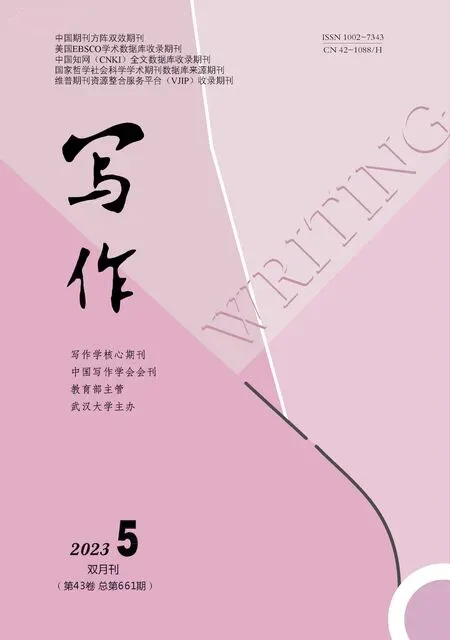“议题牵引”与“向内开掘”
——论《张医生与王医生》对于新世纪非虚构写作的意义
金 鑫 毛 敏
2021年11月,伊险峰、杨樱合著的《张医生与王医生》出版。这部囊括了沈阳地域史、家族变迁史、行业发展史,穿插引入大量社会学理论的非虚构作品,甫一面世就引起多方关注。《中国青年报》刊文,将这部书视为阶层跃升的样本;《文学报》节选这部书的片段,称它以两位医生的个体成长和人生境遇,描摹了一个兼具深度和广度的当代东北;《中华读书报》推荐这本书,认为它呈现了一部丰富的民间社会史。个人阶层跃升、工人家庭奋斗、70 后成长史、沈阳“去工业化”阵痛,这样的题材内容,决定了《张医生与王医生》的影响力。但在读者中间,除了对题材的关注,更多是关于这部非虚构作品可读性的争论,有读者喜欢,认为这部书信息量大,非常深刻;有读者不喜欢,认为这部书叙事不连贯,现场感不足。读者中产生的争议一定程度上与《张医生与王医生》“议题牵引”和“向内开掘”的写作特征有关。“议题牵引”打破了非虚构作品集中记录事件、片段式反映现实的框架模式,也弱化了文本的故事性;“向内开掘”将非虚构写作的内容拓展到难以实证的精神层面,但对文本的纪实色彩造成影响。站在21 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发展的角度看,“议题牵引”与“向内开掘”虽然引发争议,但也是在尝试解决当下非虚构写作遇到的某些根本性难题,进而拓展非虚构写作的表现空间。在一种写作类型影响不断扩大,读者接受习惯逐步形成的节点上,这种尝试称得上恰逢其时。
一、非虚构写作的现状:审视《张医生与王医生》的重要角度
21世纪文坛,非虚构写作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现象之一,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也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中国作家》的“纪实”、《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延安文学》的“零度写作”、《厦门文学》的“非虚构空间”……众多文学刊物为非虚构写作开辟了专属阵地,希望以非虚构的方式摆脱文学创作遭遇的困境,将社会变革引发的新现象、新生活以新的方式纳入文学书写的范围,拓展文学空间。诚如《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计划”开办宗旨所说:“以‘吾土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①《“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启事》,《人民文学》2010年第11期。
作为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人民文学》不仅推动了非虚构写作的发展,也影响了非虚构写作的审美旨趣。刊物发表的非虚构作品题材类型多样,以指向现实的作品数量最多,这无疑是对栏目“表现社会生活”宗旨的践行。从《梁庄》《梁庄在中国》到《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再到《女工记》《生死十日谈》,这些直指现实的非虚构作品无不显露出对真实性和现场感的强调,以真实经历呈现“不可辩驳”的现实,成了21 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最突出的特征。贴近现实生活的审美旨趣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也很自然地成为大众对非虚构写作的评价标准。每当有直指现实的作品问世,读者都会就其是否写出了中国的现实生活,是否能令自己产生共鸣发表见解。观察读者评论的兴趣所在可以发现,作品描绘的经验与读者个人见闻的重合度已逐渐成为非虚构阅读的焦点。
读者对非虚构作品“复制”现实程度的关切,与《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栏目对真实性、现场感的强调也完全吻合。事实上,在社会变革加剧的历史背景下,走进时代现场、捕捉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与精神裂变,抢占比虚构文学更丰富、更精彩的现实主义素材,也确实是非虚构写作的优势所在。梁鸿的“中国梁庄”(《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卧底传销组织的奇遇(《中国,少了一味药》),乔叶笔下的张庄人和事(《拆楼记》),郑小琼的女工群像(《女工记》)……这些作品截取当代底层群众的生活实况,将“底层”这一庞大复杂又与虚构文学长期“失联”的书写对象重新送回读者的阅读视野,揭示社会变革中隐而不见却又极其宽广的横截面,赢得了很多读者的青睐。这些作品都将视线聚焦于个体人物,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拥抱现实主义根基,深入事件,描绘波澜曲折的故事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满足了读者深度开掘社会问题的需求。这种以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的写法,与读者对非虚构作品真实性和震撼性的赞誉形成了良性互动,共同造就了非虚构写作贴近底层生活、以点带面叙事、情节曲折复杂等特征。
但应该看到,在“真实性”“现场感”上与读者达成一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虚构写作内在机制问题,对非虚构写作的质疑和批评也从未停止。
首先,非虚构写作较多地聚焦底层生活,作为作家、知识分子的写作者经常会与书写对象之间形成难以弥合的身份差异,能否平等地审视底层经验,是否以知识分子视角臆想底层生态等质疑始终存在。比如非虚构文学的代表作《拆楼记》,作者乔叶试图以“我”的视角介入张庄生活,揭露张庄人的拆迁真相,进而传递出一种被主流话语忽略的边缘经验。但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乡村叛逃者的身份,李敬泽在推介《拆楼记》时,建议与《月牙泉》对读,其中的暗示很明显,两部作品中姐妹之间的身份差异都是无法调和的。乔叶自己也承认“我有我的特定身份以及相随而来的局限和偏见”①李敬泽:《〈拆楼记〉:令人不适的写作》,《新京报》2012年7月21日C06版。。有读者就批评《拆楼记》中对乡农故里的体恤与关切,处处渗透着作者身为城市居民与成功人士的优越感,读起来觉得虚情假意。
其次,非虚构写作较多运用“以点带面”的写法,作者常常以个体经历为切口深入社会,描摹世间百态。这意味着“作家必须在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之间寻求稳妥的结合……寻求个体经验的公共性的书写”②林秀琴:《“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困窘》,《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但这种写法几乎只停留在理论上,因为个体差异永远存在,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之间必然存在无法弥合的裂隙。过分追求弥合这一裂隙很容易诱导作者预先介入事件发展,预设价值判断,造成对个体经验的扭曲。这样的作品看似能自圆其说,实则已陷入“先入为主”的价值圈套。刻板、表面化甚至是扭曲的真实,与非虚构写作的初衷是相悖的。
第三,非虚构写作往往想兼顾文学性和社会性,既要写出绘声绘色的故事,又要寻求故事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两种写作目标的杂糅,确实可以督促非虚构写作拓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边界,但也容易导致文本内部产生矛盾,造成叙事与说理相互纠缠,顾此失彼。一些非虚构写作者“借助于人类学、社会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力图通过‘客观叙述’,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呈现底层生活的真相”③张柠、许姗姗:《当代“非虚构”叙事作品的文学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从而在叙事中客观冷静地征用理论,揭示社会生活背后的真相。但这些作品常因呈现出的混杂的文本面貌遭到批评。比如《中国在梁庄》就被指文体模糊、不伦不类,《中国,少了一味药》因突兀插入的征引内容引起读者的不满。
第四,非虚构写作强调“复制现实”的创作方法,这很容易造成创作驱动力的衰竭。社会现实固然繁杂多变,但仅依靠捕捉现实素材无法保证非虚构作品能达到传统文学作品所达到的普适性和思想深度。有批评的声音就认为,非虚构写作如果继续沿着“复制”现实的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与文学渐行渐远……回避这个时代原本赋予它的反思与反省,以及任何一个时代文学都不应该放弃的理想和理性”④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
此外,非虚构写作对于主客观平衡的把握有着更高要求,作者稍有不慎,个人观念和情感就会越界,对作品的客观性形成压制,会被批评为矫情、滥情。
上述非虚构写作普遍遭遇的争议,同样出现在《张医生与王医生》身上。这是一部典型的以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的非虚构作品,张晓刚、王平作为出生在沈阳工人家庭的“奖学金男孩”,通过个人努力逐步走向专业精英层,实现了工人子弟的阶层跃升,两位医生的成长经历折射出在沈阳老工业基地半个世纪的时代浪潮中工人群体的命运起伏。“以点带面”的写作模式,势必遭遇主人公的阶层跃升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代表一种纪实性等非议。而叙事情节与历史记录、社会学理论缠绕在一起的写法,反映了作者对故事性与社会性统一的追求,却不免遭到叙事拖沓、故事性差的批评,被扣上以社会学理论粗暴验证复杂现实的帽子。争议和批评说明,《张医生与王医生》未能彻底摆脱21 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遇到的问题和局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者态度、能力问题,也有读者阅读习惯、批评者思维惯性等方面的影响。但这不能掩盖《张医生与王医生》一书针对非虚构写作困境所做出的探索,“议题牵引”的文本形式和“向内开掘”的内容指向,带有明显的突围、开拓的意味,这无疑是值得关注并加以讨论的。
二、“议题牵引”:非虚构写作的一次突围尝试
《张医生与王医生》的目录很整饬,每章内容似都可以独立成篇,这就是该书以议题牵引最直观的表现。作者伊险峰、杨樱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其实不觉得自己在写非虚构……相对精准的说法,就是它是一本以议题推动的非虚构作品。”①青青子:《相比语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新京报》2021年11月23日C06版。
议题牵引使《张医生与王医生》产生了不同于其他非虚构作品的阅读效果。两位医生的命运,两个家庭的际遇,不再是读者关注的唯一焦点,书中诸如东北命运的时代密码、工人阶级的性格底色等议题,因为是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公共话题,能够在更深层牵动和引起读者的注意。穿插于人物命运和社会议题间的社会学理论同样是读者关注的对象,他们对理论运用是否恰当,理论引入能否将议题的讨论推向更深处都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有些读者对书中大篇幅征引社会学理论表示不满,认为理论的运用零散不成体系,缺乏深度,还干扰了叙事的连续性。也有读者认为理论的引入恰恰是《张医生与王医生》的独特气质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他非虚构作品不够理性、渊博、沉实的不足,在追求叙事的客观、冷静方面又进了一步。
对于理论运用效果的争论意味着《张医生与王医生》以议题牵引推动文本的尝试给作品带来了新的变化,也使读者获得了新的阅读体验。但这种新是相对的,它确实有探索非虚构作品普适性社会学价值的一面,但仍沿用了非虚构作品最常见的以点带面的写作方式。有评论就指出,《张医生与王医生》是一部“四不像”的非虚构作品②青青子:《相比语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新京报》2021年11月23日C06版。。“四不像”或许就是寻求非虚构写作突围的代价,但寻求突围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
《张医生与王医生》设置有“两显一隐”三条线索,两条明线,一条记录两位医生的成长经历,一条展现推动两位医生原生家庭变迁的动力。两条线索既承担了叙事功能,又将“工人阶级子弟的成长”“社会人”“知识,尊严和自我”等社会议题纳入对主人公经历和家庭史的书写。一条隐线是各章结尾处的番外,它虽没有出现在目录中,却是全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书共二十章,其中十二章附有“番外”,主要用来填补正文中缺失或展开不足的人物命运、历史背景和社会心理。“番外”是写作者观点的存放地,为议题的展开和辨析注入个人的理解和思考。比如“废墟与沈阳的去工业化”,是理解张、王两家在80年代经历的种种变故的关键所在,“沈阳的穷和沮丧”,是探讨男性气概如何消失的绕不开的背景。三条线索中,提出、展开、分析议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分量已可与叙事比肩。
由于议题的不断汇入,《张医生与王医生》叙事的连贯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情节”这一非虚构作品中的核心要素不得不让位给“议题”。在大致遵循时间顺序的前提下,写作者用不断涌现的议题牵引着全书向前发展,主人公的家庭生活、成长经历被打散重组,服务于议题的引出和佐证。因此,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中,“议题”超越了“叙事”成为文本核心。
“议题牵引”的写作方式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中搭建起一个庞大的“问题系”,提出命题、验证真伪、寻找理据、建构联系取代了线性叙事成为全书的主要推动力。从第一部分开始,沈阳去工业化的议题就被明确提出,东北地区的沉浮、发展成为议题的大背景,工人阶级、单位社会、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地域性格等小的议题彼此关联穿插在沈阳去工业化的大议题中。这些议题抽象为几个词语,汇集一处,彼此纠缠,都作为影响因素参与到张医生和王医生的成长经历中。时代、地域和观念如何影响个人的命运这一庞大议题随之浮出水面。作者伊险峰、杨樱以历史研究的态度查阅《沈阳日报》,平移戴伦·麦加维针对工人阶级/蓝领社会的理论研究,从中外艺术作品中采集蛛丝马迹,让诸多议题或偶然或必然地发生合理碰撞,进而搭建起致密的文本结构,最终使整部作品形成一个庞大的问题网络。这种依靠议题牵引的写法,丰富了非虚构写作的支点,情节突转不再是文本推进的唯一动力,叙事、理论、作者观点、地方史等诸多要素都得以在文本中实现兼容,在议题的牵引下展开对现实的呈现和解说。如果说在梁鸿和慕容雪村那里,将社会学理论纳入作品仍是个极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有“夹生”之嫌,那么在《张医生与王医生》这里,两个家族横跨两个世纪的奋斗史、沈阳去工业化所产生的历史性震动、工人阶级子弟对自我和尊严的思考、希波克拉底誓言以及陆学艺的社会阶层理论都恰如其分地找到了容身之所。议题牵引的写法极富弹性,情节和理论,主体观点与社会调查之间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和,理论不仅介入了叙事文本,还有了比较好的融合。在大多数非虚构写作仍将主要精力用于“情节”的开掘时,《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作者已意识到过度依赖情节对作品容量的限制,也感受到仅依赖情节在深度挖掘社会命题时的捉襟见肘,他们尝试用议题牵引的方式破局,这实为一次大胆且有意义的冒险。
“议题牵引”不仅扩大了非虚构作品的信息容量,推动了理论与情节的融合,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体经验上升为公共经验。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之前,很多非虚构作品都为打通个体经验与底层经验之间的壁垒做出了努力。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以知识分子视角统摄全书,试图以权威姿态统一文本的声音,谋求传达公共经验的合法性。但这种做法遭到很多质疑,有批评者直言作者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俯视乡村经验,最终得出的结论也仅是流于表面的“真相”,实际上并未触及真正的底层生活。郑小琼的《女工记》则将女工还原为一个个独立个体,最大限度地保持个体经验的完整性,以个体经验拼凑底层生活的整体面貌。但遗憾的是,她在传记式的写作中不自觉地把自己从打工阶层中分裂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观察者和批判者,再一次落入“知识分子能否真实有效地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①林秀琴:《“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困窘》,《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的陷阱。
事实上,一旦写作者将主人公的个体经验置于文本的核心位置,无论他以何种姿态出场,声音都会天然地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在以往的非虚构写作中,作者的观点、态度以及可证明其观点带有普适性的理论都是文本的次要部分,它们不仅不能得到与“故事”(即主人公个体经验)同等的重视,甚至会被视为动摇文本核心的多余成分。这可以说从根本上阻断了个体经验被验证为公共经验的道路。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中,议题代替了对个体经验的叙述占据了文本的核心位置,作者的观点与主人公的个体经验都退居议题背后,共同为议题的提出、分析、作结服务。这样,作者观点、相关社会学理论就取得了与主人公个体经验同样的地位。这使得传递个体经验以外的观点、理论在作品中成为可能,而理论和观念又可以起到弥合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间裂隙的作用。这不但为多角度阐释个体经验扩宽了空间,大大增加了非虚构写作的丰富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采访对象的经验“不够典型”而出现的过度虚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张医生与王医生》议题牵引的写法,在文学与“当下”脱节的历史时刻,完成了重新对接现实的文学使命。
在肯定议题牵引的作用和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情节弱化确实导致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可读性的下降。我们可以肯定它纠正了非虚构写作中存在的过度商业化导致的模式化问题,却也不得不面对传统读者流失的风险。议题牵引的方式虽然通过吸引社科读物的受众填补了一部分流失的文学读者,却又在理论运用的精深度、匹配度等问题上遭到新读者的质疑。可见,如何灵活驾驭庞大的“问题系”,让“议题”向更深处开掘的同时保持可读性,仍是《张医生与王医生》未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今后非虚构写作寻求突围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向内开掘”:非虚构写作的一次拓土实验
议题牵引和社会学理论的引入,有意无意间还触碰到非虚构写作的另一困境,即精神层面的言说,向内开掘。从这个层面上说,《张医生与王先生》算得上非虚构写作的一次拓土实验。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非虚构并非“反虚构”,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属性离不开适度的联想、合理的虚构和恰当的修辞。但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是,“非虚构叙事的首要原则永远是真实……必须做到‘真实’‘客观’‘公正’‘全面’”①李法宝:《试论虚构性叙事与非虚构性叙事的差异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这便为创作中的想象和修辞划定了边界。深入人物内心的心理描写作为虚构作品中上帝视角的产物,带有相当强的臆测成分,会对文本的真实性构成威胁,违背客观性原则。所以,基于对真实性的强调,非虚构写作通常会避免深度触及人物的精神世界,控制对人物思想观念和内心情感的呈现。但完全通过外部观察进行场景塑造,主要依靠受访者言说推动情节,很容易使作品平面化,成为冰冷的资料记录,失去文学应有的温度。而且放弃对个体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的开掘,也阻断了作品对社会心理的探究,特定心理因素、精神风貌对社会行为、个体命运的影响也难以得到展现。这样塑造的所谓“真相”无疑是不全面的,甚至流于浅薄。就非虚构文学的读者而言,如果只能从作品中获得环境、人物的介绍,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和影响,无法获得对心理的感知和精神的理解,那么文学阅读就会沦为信息获取,难以实现共情,引发内心的震撼。可见,无论是非虚构写作还是阅读,向内开掘心理和精神因素都是必要的。
回看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非虚构写作,似乎始终未能为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开掘找到合适的书写方式。多数作者剖析人物情感和心理状态的方式,都是通过采访直接获得受访者对特定问题、特定事件的反馈,随后便请出叙述者,捕捉隐藏在当事人反馈中的情绪波动,解读情绪背后的心理机制。但外来的叙述者的声音在非虚构作品中的地位始终是“可疑”的,它的直接介入,经常是以牺牲作品的真实感和代入感为代价的。这样的精神、心理开掘对于非虚构写作而言总是有种无可奈何的尴尬意味。也有写作者尝试利用批判性眼光和社会学理论在故事之外另辟探讨心理、精神层面问题的空间。但这种写法对于靠情节推动,以叙事为核心的非虚构作品而言,不仅有些生硬,还容易破坏作品的整体性。还有一些写作者,将向内开掘的任务直接交给情节去完成,希望通过叙事层面的努力赋予情节一种“不言自明”的力量,使读者在对故事的理解中自动走向人物的精神和心理。但这种向内开掘的实现对作者的叙事、读者的阅读都要求很高,而且对题材的典型性、普遍性也有诸多的要求和限制。整体来看,在不破坏真实性的前提下将笔触自然延伸至精神、心理层面,是21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一直未能彻底解决的难题。
站在向内开掘的角度审视《张医生与王医生》,我们发现,议题牵引式的结构为写心理、写精神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一些蕴含在情节之内或悬浮在故事之上的抽象内容,通过议题设置,很自然地融入文本,获得了主体地位。
《张医生与王医生》中,“男性气概和它的消逝”一章是向内开掘的一个显例。作者从极具地方色彩的口头禅“你瞅啥”切入,呈现男性气概对沈阳青年理想人格、心理特征的塑造,再由此生发开去,剖析弥漫在工人阶级中的犬儒主义解构话语和波西米亚浪漫气质,最后将锋芒指向20 世纪90年代以来沈阳的经济萎靡和精神麻木。精神议题贯穿始终,成为行文支柱,占据了不可撼动的主体地位。像张医生和王医生的童年经历、“大东冰果厂受骗记”、沈阳街景以及完全游离在主线之外的黄棉袄大哥的故事,都可视为平行的例证,接受社会心理相关概念的检视。还有霹雳舞和牛仔裤,阐释了茨冈人的波西米亚风如何在中国东北演变成一种无法无天的浪漫;珲春路“金家大冷面”,折射出沈阳人对硬汉气质的推崇以及背后隐藏的源自80年代的工人阶级的集体优越感;90年代的社会失范和价值观崩塌则在频发的罪案和“东北文艺复兴”中得到印证。
由于作品采用了议题牵引的结构,像“波西米亚”“男性气概”“娘娘腔”“社会性沮丧”等明显触及社会心理、精神气质的小议题不仅很好地融入了文本,而且在局部还起到了整合个人经历、主导行文方向的作用。若将这些抽象的议题删去,一些情节就会减少推力,文献资料也会缺少组织,文本很多局部都会变得松散。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些对个体精神和社会心理进行探索的小议题为庞杂内容的徐徐展开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仅有小的精神性议题穿插,《张医生与王医生》整体上也是以精神议题为框架的。全书记录了张医生和王医生数十年的人生经历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背后其实是他们自我建构与调整自我认知的过程。正如作者伊险峰所说:“如果我们把张医生和王医生的成长过程分解一下,最开始的议题其实是他们的知识、尊严和自我是怎样形成的。”①青青子:《相比语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新京报》2021年11月23日C06版。作者的说法在全书最后一部分得到了明确印证。可见两位医生内在的心理、精神建构从头到尾都占据了文本的中心位置,是整部书的重要线索。也基于此,一些关乎主人公心理、思想状态但与阶级跃升、社会变迁等现实事件无关的只言片语,诸如二位医生关于过去老师、同学的闲聊,对医院同事的品头论足等,才能很自然地被纳入文本。这些只言片语服务于文本的精神议题,较为直接地传递出主人公对“社会”的态度,以及他们骨子里对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
书中很多关乎两位医生人生转折点的重要章节,作者的处理方式也体现出对精神、心理层面的探索,往往不是直陈其事,而是详述二位医生对事件的看法,分析事件对他们心理的影响,有时还会将事件作为主人公性格的佐证,比如对王平医生保送失败后心理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大书特书,比如详细记述张晓刚医生对成功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对他个人事业、爱情、生活的影响。记述这些人生转折点所用的材料常常溢出事件本身,最终落脚于心理和性格。人生节点处的精神、心理状态被部分地展现出来,无疑为我们深入了解两位医生,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打开了通道。
议题牵引的结构方式使精神、心理议题得以汇入《张医生与王医生》文本的核心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非虚构写作中精神议题无处安放或只能与叙事各行其是的问题,两位医生的经历、不同阶段的精神状态、心理机制,乃至作者对人物、事件的思考、态度得以较为完整地展现出来,三者彼此关联,赋予读者完整且深入的阅读体验。
作者的主体性是否影响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我们看到的问题和答案是否经过作者的主观预设和有意引导?这样的质疑始终困扰着非虚构写作,因为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几乎必然会包裹在文字描述中呈现出来②田香凝、刘沫潇:《新媒体时代非虚构写作的现状、问题与未来》,《编辑之友》2019年第8期。。对此类质疑的忌惮,使得21 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在揣摩精神世界时往往自设禁区,为非虚构划定了一条无形的边界。从这个角度说,《张医生与王医生》通过议题设置和牵引介入社会心理、精神状态,实际是在触碰非虚构写作的边界。这种探索为非虚构写作审视精神苦难、展现心灵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并有可能将非虚构写作的社会意义从“展示现实”拓展至“透视现实”甚至“击穿现实”。沿着这条道路,未来的非虚构写作将有机会展示更全面、深刻的真相,有机会由贴近现实的写作走向贴近心灵的写作,有机会不止于捕捉瞬息万变的社会变迁,更能剖析社会心理、描绘曲折的精神世界。
当然上述的这些效果还只是可能,毕竟《张医生与王医生》的尝试也并不完美,无法避免自问自答再自我验证的质疑。因为面对张医生、王医生以及他们背后原生家庭的命运时,我们还是会对阶级跃升与社会环境、阶级出身、心理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甚至影响作用产生质疑:具备两位医生的那些条件就能实现阶级跃升吗?还是说两位医生只是一个被精心选取、有意验证的偶然?质疑意味着《张医生与王医生》只是开始,非虚构写作还需要继续探索更为严谨、更具穿透力的书写模式,来发展自身同时消除读者、批评者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