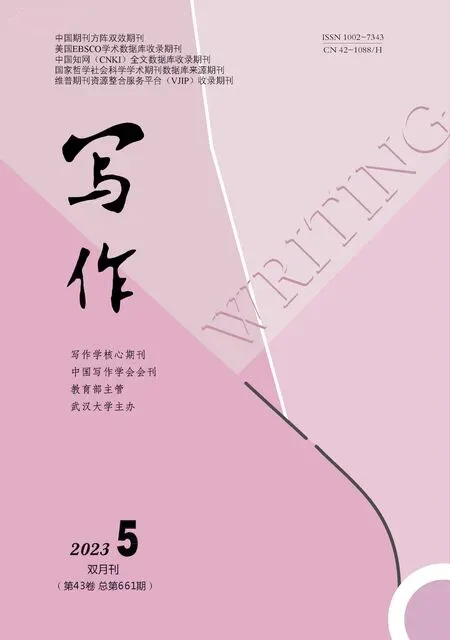特工题材的写作图式:茅盾《腐蚀》与陈铨《野玫瑰》比较研究
李金凤①
茅盾的小说《腐蚀》写于1941年孟夏,1941年5月起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香港出版)连续发表。陈铨的剧本《野玫瑰》写于1941 年5、6 月间,1941 年6 月起连载于重庆《文史杂志》。两部作品写作时间相近,连载时间也较一致,主人公都是女特务,属于特工题材。两位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一致,同属于抗日救亡战争背景,两部作品发生的背景与写作的内容皆与此有关。总之,《腐蚀》和《野玫瑰》在写作时间、历史背景、题材和人物方面皆有高度相似之处,但两部作品的主题意蕴、情节模式、叙事策略和人物形象却迥然有别,形成写作图式的巨大反差。如何看待这种反差并进一步思考反差的缘由,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不同作家关于特工的认知图式及其对抗战力量的认识。
一、迥异的主题意蕴与叙事策略
《腐蚀》和《野玫瑰》都是抗战时期的作品。《腐蚀》所描绘的1940—1941 年的重庆,属于国统区大后方;《野玫瑰》的故事发生背景敌伪统治区北平,属于沦陷区。两部作品在抗战叙事、情节布局、描画重点等关涉主题意蕴的叙述却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腐蚀》采用长篇日记体的形式,以1940年9月到1941年2月的重庆为背景,描写了女特务赵惠明的一段经历和故事。《腐蚀》的主题是内斗。主人公赵惠明是在国统区领薪工作的女特务,整部小说与抗战关联甚少,它的叙述重心在特务系统内外部的斗争,同室操戈、勾心斗角,出卖与利用,冷箭与围剿是叙述者经常提到的,如此就暴露了国统区特务系统的腐朽与人格的腐蚀。《腐蚀》的日记体写作方式擅长表现人物心理和情绪表征,茅盾正是通过女主人赵惠明自言自语、自我辩解、自我安慰乃至自我鼓励的日记体叙述策略,表现其矛盾、犹疑、摇摆的心路历程和心理活动,从而暴露了特务系统的黑暗,揭示了自新之路的可能,形成了左翼叙事特有的主题意蕴,塑造了符合茅盾政治诉求的人物形象。
《野玫瑰》的主题是锄奸。夏艳华是国民党的高级特务,为了完成政府交代的任务,她断然抛下恋人,不惜以身事伪,忍辱负重,长期潜伏,刺探敌情,组织暗杀。整部剧的主旨是抗日锄奸,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野玫瑰》主要通过对话来反映人物的思想和情感,并侧重于外部事件的叙述和人物行动的展开,通过紧张曲折、扣人心弦的谍战情节来呈现主题意蕴。至于夏艳华的心理活动、情感体验则处于叙述的边缘地带。剧本由此形成了抗战主题的宏大叙事,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一部正剧,符合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宣传诉求。
(一)主题的流变与人性的纠葛
《腐蚀》以女主人公自述的视角勾勒了赵惠明的特工生活。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茅盾本人对此部小说的主题有过多次变更。
《腐蚀》小说开头有“引言”,作者指出这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反映了青年们的“生活压迫”“知识饥荒”“精神痛苦”等。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腐蚀》时,茅盾“后记”指出该小说具有两个主旨:一是抨击特务组织,“通过赵惠明这个人物暴露了一九四一年顷国民党特务之残酷、卑劣与无耻,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只是日本特务组织的‘蒋记派出所’……”①《茅盾全集》第5卷·小说5集,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40、345页。;二是分化、瓦解特工,挽救受骗、被迫、无以自拔的青年,给予曾是胁从者的青年分子以自新之路。茅盾在应苏联杂志《涅瓦》之约时,写了一份俄文译本的说明,指出“《腐蚀》所反映的只是一九四○——四一年时期美、蒋特务的血腥罪行以及中国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在迫害之下英勇反抗、坚贞不屈的一个片段”②《茅盾全集》第5卷·小说5集,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40、345页。。由于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深处历史旋涡的茅盾无法不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他致苏联读者的信带有阶级斗争的鲜明烙印,但大体的意思是明确的,即这是一部暴露国民党特务机构及其特工生活的小说。
除开国际争端、政治形势和历史语境,整部小说的叙述重点在内斗,小说中的赵惠明始终处在“斗争”和“做戏”的状态中,欲罢不能、难以解脱。内斗的范围很广,隐含着三个层面:特务系统的内斗,外部社会的内斗,政治的内斗,等等,都在小说中有或轻或重的反映。
其一是特务内斗。贪财好色、笑里藏刀、看风使舵、落井下石成为这里的人际常态,赵惠明的处境相当艰难。由于赵惠明与小蓉、G 不和,他们多次在上级领导面前无中生有乃至在工作中做手脚,让赵惠明处处不顺,使之卷入内斗之中,成为G 和陈秘书斗争的牺牲品。赵惠明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为解救旧恋人小昭而左右周旋、四处求人,在她给小昭做思想工作时,小蓉故意瓦解小昭对她的信任和情感,部分导致惠明的间谍工作失败。无论赵惠明做什么,譬如解救恋人、帮助朋友,都不顺利,她深处特务系统的内斗之中,做着毫无意义、低效无聊的事情,这些无聊、内耗的工作慢慢使她陷入危险又难以摆脱。赵惠明在特务系统的工作就像现代人可能遭遇的职场困境,与其说是特务系统的罪恶,不如说是职场内斗的常态,小说将现代人具有的普遍性的职场困境表达出来了,故能引发跨世纪的读者共鸣。
其二是朋友内斗。不仅特务系统存在内部斗争,特务系统外部也是一个人吃人、互相告发的黑暗社会,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难以避免要牺牲朋友的利益来保全自我。赵惠明为了挽救她在特务系统的“信用”,不得不告发了朋友K和老同学萍。由于惠明的告发,上级又将侦察K和萍的工作交给她,以“美人局”的方式和K谈恋爱,探取相关信息。赵惠明所做的一切都处于一张被设计的大网,她的亲朋好友一一被卷入,而她却毫无应付之策。由于赵惠明的身份和态度,身边人都提防她,不信任她,背后中伤、背叛乃至拉她下水,这不仅给她带来麻烦和危险,也将她的朋友卷入艰险的时局,可谓两败俱伤。
其三是政治内斗。赵惠明并不关心国共政治,但时局却让她卷入政治斗争。从F 和N 的信息中她得知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场“细密猜测”“疑神疑鬼”的内外清洗运动开始了,寻找叛徒和双重间谍。这样一场严重的国共冲突,导致特务系统的工作更加繁忙:上街抓人、取缔小团体、撕毁报纸以免事态扩大。当时报纸刊登的资讯、青年学生的思想都在日记中有具体的记录。特务F就注意到N 思想不纯正,“在同学中间发了不正确的言论,拉扯到团结问题,还有别的表现都不很好”①《茅盾全集》第5卷,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86-287页。。该小说从侧面记录了“皖南事变”发生之后的事情,还模糊、含蓄地涉及汪伪政权求和的历史事件,由于叙述视角的限制,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晰,但还是突显了政党之间的斗争。国共博弈、军事冲突,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治内斗了。
综上所述,《腐蚀》以日记体作为叙述方式,通过记录赵惠明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呈现了女主人公犹疑、矛盾、复杂、痛苦的情绪,反映了正常人性被腐蚀、被击碎的纠结心理和动态过程,抨击了国民党特务内部之间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的状态,揭露了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的罪恶,同时也侧面表现了“皖南事变”、汪伪政权求和等重大历史事件。茅盾采用内视角为主的叙述策略,使作品的心理剖析和社会环境描写达到了“精微真确”的程度。
(二)集中的主题与浓厚的民族意识
话剧《野玫瑰》的主题就简单、清晰、明了多了。《野玫瑰》是描写国民党女间谍反日锄奸的正剧。夏艳华牺牲儿女私情,毅然“抛弃”热恋中的情人刘云樵,受命嫁给北平伪政委会主席王立民,目的是刺杀“同日本军阀浪人勾结,在华北无恶不作”的大汉奸王立民。但因中日关系越发紧张,战事随时爆发,上级指示她暂时不杀王立民,而要“利用他来探听日本人各方面的消息”。于是她费尽心机、赢得丈夫欢心,不断获取重要的绝密情报,成为埋在华北日伪心脏上赫赫有名的女间谍。剧中夏艳华先施“美人计”让警察厅长送走刘云樵和曼丽,再施“反间计”借王立民之手毙杀警察厅长,最后在身心上重创汉奸王立民,王立民在精神遭到毁灭之际怪病发作、自吞毒药,夏艳华收拾残局,带领同胞从容撤走、成功脱身。
陈铨大体按照戏剧“三一律”的要求,除了时间有所不同,地点都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重点叙述女主人公夏艳华的人生选择与行动,突出民族国家意识,驳斥只求“个人权力”的极端个人主义。整部戏剧虽然穿插了刘云樵与夏艳华的情感纠葛,但在剧中属于插曲,只是起协调的作用,并非描述的重点。《野玫瑰》宣扬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爱国情感,并且在剧中传达了陈铨的思想理论——尼采的意志哲学。《野玫瑰》正是陈铨理念的文本延伸和形象诠释。
总之,该剧的主题相对集中和明确,陈铨按照戏剧结构的要求,设置环环相扣的四场戏,情节跌宕起伏、前后呼应,以外部事件和人物对话作为叙事策略,重点描摹夏艳华的超级事功和家国情怀。为了更好地呈现民族意识和团结精神,《野玫瑰》的特工品质过硬、能力突出,特工之间配合默契、团结互助,既不勾心斗角也不暗射冷箭,他们服从命令、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可见,同属于国民党系统,《野玫瑰》与《腐蚀》描述的特工完全不同。《腐蚀》是暴露讽刺特工,《野玫瑰》是歌颂赞扬特工,两者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二、女特务:迷误弱女子与超级女英雄
“不同的主题意蕴决定着不同的叙事逻辑和描画重点,也决定着两部作品人物塑造的不同方向。”①孔刘辉:《谍战题材的两种叙述方式——〈色戒〉与〈野玫瑰〉》,《抗战文化研究》2013年第5辑。《腐蚀》和《野玫瑰》的主角同为女性特务,同样美貌能干,但人物形象却大相径庭。赵惠明就像一个单枪匹马的迷误弱女子,才貌双全,但业绩失败,在旋涡边上奋力挣扎,生死扑朔迷离。夏艳华就像一位智勇双全的超级女英雄,她创造了一个个锄奸业绩,属于走上人生巅峰的王牌间谍。一个是左翼作家塑造的女特务,一个是偏“右翼”的作家塑造的女特务,两者形象如此悬殊,值得探索。
(一)赵惠明:单枪匹马的迷误弱女子
茅盾将俄文译本《腐蚀》设定为“一个迷误的女人的日记”,整部小说的确充分刻画了赵惠明矛盾又迷误的形象,她单枪匹马、不群不党,具有强烈的弱女子气质和个人主义倾向,游离在好人与坏人之间,不明大义、明哲保身又尚存良知。
第一,茅盾塑造了一个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特工形象。赵惠明是一个聪明漂亮能干的女特工,曾参加过战地服务工作,她希望自己像个男人和战士一样工作,但她面对上级和同事安排的任务常常难以应付、敷衍了事。整部小说看不见赵惠明做对抗战积极有利的事情,相反,她被自身所处的环境和人事束缚住手脚,以一人之力、筋疲力尽地抵抗来自特务系统内部的一个个“阴谋”和“攻势”,一不小心就作茧自缚、引火烧身。当赵惠明真心想救昔日恋人小昭时,哪怕她殚精竭虑、费尽心机仍旧不能成功。当她不忍心青年女学生N 重走她的老路,把处于危险境地的N 送出虎狼之地,小说结尾她仍处在担惊受怕的实施过程中。小说极力描述赵惠明存有善良和底线,她觉得自己拥有特工身份是可耻和罪恶的,不愿和特务群体沆瀣一气,利用身份和工作发国难财,她不愿沦为金钱和政治的奴隶,虽然也有虚荣心,但多次拒绝诱惑,不去上海沦陷区工作充当汉奸。她内心深处也不愿伤害朋友,时不时冒险提醒朋友注意安全。由于自身的性格气质,加上黑暗的社会,严酷的制度,她多数时候只能单打独斗,以个人利益为权衡点,工作起来常常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成为一个完不成任务、无能又窝囊的特务。茅盾描述的女特工,尚未失去良知,保有向上的力量,但终究是一个失败无能、矛盾复杂的人物。
第二,在本质上赵惠明是一个精神痛苦、备受折磨的弱女子。小说开头就塑造了一个痛苦迷茫、敏感细腻的弱女子形象。赵惠明缺乏特工刚硬果断的一面,回忆往事将她折磨得神经衰弱,似毒蛇吮吸她的血液。赵惠明心中有梦想和希望,但重重的魔障,使她难以自拔,只能痛苦地诅咒这些“恶毒而无耻的诡计”。她遭遇了恋爱失败加情人背叛,政工人员为了自身前程狠心抛下待产的她,在她快要生育时卷走她所有的钱财,这样一个“卑鄙无耻”“虚伪自私”的“恋人”,她一想起“全身的细胞里,就都充满了憎恨”。赵惠明内心深处保持对情感的认真与柔情,努力坚守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但她的特工身份和过往决定了她不能像正常女子那样恋爱和生活。她希望两情相悦地谈一场恋爱而不得,她想做母亲抚养孩子也不可能,身份和性别决定了她总是成为“美人计”的实施者——“我们女的,不是人,只是香饵”①《茅盾全集》第5卷,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98、41页。。她被上级指派和旧日恋人小昭假谈恋爱以说服小昭投降,和小昭的朋友K谈恋爱以探取情报,身体和情感总是被特工身份利用,她处于巨大的痛苦乃至精神崩溃中。赵惠明曾经还是教书育人的高小教师,在“疯狗”“色情狂”的威逼利诱之下,在乱世中求生存和自保,她逐渐堕落、腐蚀,精神遭受打击,心灵遭遇破碎——“我怕我快要疯了!”②《茅盾全集》第5卷,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98、41页。尚存良知和灵魂的赵惠明就这样被罡风吹进了大漩涡,虽不是束手待毙,但她用尽力量,还是被那回旋的黑水吞噬。
小说表现了一个普通女性的情感和诉求,也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弱点和缺陷。茅盾从人性的角度精细刻画了赵惠明腐蚀、堕落、自救的生存环境、心路历程和复杂情绪,剥离特工的身份,她更是一个偶然失足、精神痛苦、敏感细腻、备受折磨的弱女子,值得读者同情。
(二)夏艳华:智勇双全的女英雄
陈铨在戏剧中塑造了一个简单又有力量的女性形象,在戏剧化的冲突中刻画了坚韧决绝、智勇双全、深明大义的王牌女特工,极具浪漫主义的理想化色彩。
首先,陈铨塑造了一个屡建奇功的王牌间谍。与《腐蚀》相反,《野玫瑰》塑造了一个战功赫赫的超级女特工夏艳华,整部剧都在突出夏艳华如何运用聪明才智、个人魅力和过人胆识实现抗日锄奸的特工任务。夏艳华曾经是上海鼎鼎有名的交际花、红舞星,“成天成夜同各式各样的人鬼混”,但她有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判断力。见识过各式各样的人并有识人之明,处在尘世之网而不受红尘之累,这正是夏艳华的高明之处。她心中有国家有情怀,听从国民政府命令,果断放弃个人情感,积极参与抗日事业。在与丈夫王立民相处的两年中,她周旋于汉奸、日本军阀之间,“同一个仇人,朝夕相处”,竟然不留下任何破绽,还赢得了丈夫和警察厅长的信任欢心,不断获取核心绝密情报。对旧情人刘云樵,她既有调度和掌控的权力,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也有保护和拯救的能力,危险时能将他平安送走。夏艳华在得知刘云樵被敌人识破身份之后,几个小时之内迅速扭转不利局面,巧妙借力,戏弄利用、分化瓦解汉奸,指挥同党,齐心协力,成功拯救恋人,消灭敌人,从容撤退。一系列事功都突显了超级女特工的非凡才能,她能够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洞察人心,巧舌如簧,采用纵横捭阖、声东击西的手段化解危难,完成一项项高难度特工任务,成为一个无所不能、手腕高超的女英雄。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夏艳华不追悔任何选择,不顾惜任何牺牲,她在陈铨的叙述中成为武解六韬、智勇兼资、具备家国情怀的女侠。
其次,夏艳华也是一株寂寞、隐忍、坚强的“野玫瑰”。夏艳华美艳、冷峻,深得异性喜欢,但交际花和高级特工的双重身份导致夏艳华在面对个人情感问题时常常身不由己,难以按照本心对待她的情感和生活,做戏与表演的背后是深深的寂寞与孤独。她拎得清、看得透彻,时刻摆正自身的身份和位置,清楚自己在各阶层的人眼中的地位和作用。老头子对她表示好感,是想利用她“开开心”;中年人和她交往,是想利用她的名声,显示他们交际的本事;年轻人对她诉说爱情,就像胰子泡,轻轻一吹就破了。夏艳华就像一株野外生长的野玫瑰,“随风漂泊,坠溷沾泥”,不能像家养玫瑰那样得到关爱和呵护,永远需要自我扶持。职业和个性使然,夏艳华长成了一株强大的野玫瑰,摒弃了家玫瑰天真、软弱的一面,独立对抗社会的风风雨雨。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她毅然“抛弃”热恋中的情人刘云樵,忍受恋人的不解和愤怒,独饮痛苦、甘愿牺牲。她不仅牺牲儿女私情,更能忍辱负重、牺牲名誉嫁给汉奸王立民,同仇人朝夕相处、逢场作戏、花言巧语,博其欢心,赢得信任。野玫瑰在地狱生活中寂寞孤独又坚强——“它天生就寂寞的性情,它永远是寂寞的!”③陈铨:《野玫瑰》,重庆《文史杂志》1941年第1卷第7期。夏艳华也渴望一份真诚的热烈的爱恋:如果有年轻人“发狂地爱上了我,苦苦地要求我,诚恳地告诉我,我不嫁给他,他就立刻死在我的面前,我也许会抛弃一切,跟着他走的!”①陈铨:《野玫瑰》,重庆《文史杂志》1941年第1卷第6期。高级女特工也有女性基本的人性诉求,由于作者叙述重心的游离,夏艳华复杂的心理情绪并未被读者充分感知,个人情感的纠葛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够紧张起伏,但从多处对话和独白可以看出,其孤独、寂寞、隐忍、理性、坚强又淡然的女性特征。
三、悬殊的写作图式:作家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
同一时间段创作的两部作品,一个是左翼作家写作的日记体小说,一个是偏右翼作家创作的剧本,体裁的不同决定了写作图式的不同,但不会导致两者对特务题材的文学塑造如此霄壤有别。两部作品之间的差异和作家固有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密切相关。《腐蚀》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叙事方式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统治的罪恶,并上升到普适性的职场斗争;《野玫瑰》更具传奇、虚构和想象的浪漫主义色彩,它用夸张、理想化的方式塑造了为国献身、英勇抗战的女超人形象。前者是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后者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其背后是作家不同的创作理念与风格,预设了各自的认知结构。
众所周知,茅盾的创作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他擅长捕捉、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将现实中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创作题材。《蚀》是对大革命的历史记录和艺术概括;《子夜》直接反映了1930 年春夏间在大都市上海发生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农村三部曲”真实表现了20 世纪30 年代初中国农村“丰收成灾”的现实和农民的觉醒、反抗;《访苏实录》则描述了作者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一般认为,茅盾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思想史的文学记录者。《腐蚀》则将笔墨聚焦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借助一个小人物来抨击国民党特务统治的腐蚀与罪恶,侧面反映抗战时期青年学生的苦闷、彷徨与痛苦的时代特征。
茅盾在小说的“引言”“后记”以及俄文译本中反复说明《腐蚀》的主题,它成为我们认识其创作背景和目的的重要材料。1957年茅盾执笔俄文译本时说明:
《腐蚀》所反映的只是一九四○——四一年时期美、蒋特务的血腥罪行以及中国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在迫害之下英勇反抗、坚贞不屈的一个片段。当时蒋介石反动集团正戴着抵抗日本侵略的假面具,他们就用爱国的幌子、挂起“××训练班”(比方说,“民众抗日工作训练班”)等等假招牌,引诱没有经验的、天真的青年们投入他们的罗网,用极端强暴的方法强迫这些误入网罗的青年受特务训练,成为特务人员。也正因为这样,这些青年们的内心是很矛盾苦闷的。《腐蚀》的主人公虽然没有经过那样骗人的所谓“特训班”,但她的失足的经验和那些被骗的青年是有些相同之处的。在一九四一年的历史情况下,暴露美蒋特务的罪恶及其内部的矛盾,并针对那些被迫参加的小特务的矛盾、动摇、而又苦闷的心理状态,给他们一记“当头棒喝”,争取他们带罪立功,回到人民这边来:——对于当时的革命运动是有利的。我就是根据这样的认识和目的,写了这部小说。②《茅盾全集》第5卷,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45页。
《腐蚀》保持了茅盾一贯的创作方式和风格,根据主题的需要,根据中心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来安排各种人物事件,通过赵惠明之眼,在日记体叙述中构建繁复的人物网络,这种茅盾式的庞大的“网状结构”,构成了其特有的写作图式。与此同时,茅盾十分擅长心理描摹,他注重“社会心理因素”的探索,从赵惠明丰富复杂的心路历程和心理状态入手,反映年轻人苦闷、迷茫、傍徨、矛盾的心绪,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冲突的社会性、时代性。
作为一个重要的左翼作家,茅盾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态度、情感与陈铨全然不同。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受过国民党的“通缉”,为此不得不东渡日本。1930 年代他参加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展革命文艺,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广泛团结国统区的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茅盾积极参加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的运动,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和文化部第一任部长,负责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宣传组织工作。从其经历和身份可以得知,茅盾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文化、艺术等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他的政治认知和经历决定了在作品中抨击国民党的统治而不可能美化宣传国民政府,即便是在急需团结和凝聚的抗战建国时期,茅盾的笔锋依然指向批判、讽刺和暴露。《腐蚀》中茅盾借国民党特务F 和青年学生N 迥然不同的行动和态度来反映“皖南事变”的面貌,并在国民党无法严格控制和监督的香港公开发表,这显示了茅盾的态度和认知。在茅盾眼里,特工就是一种罪恶肮脏的存在。沦为特工的情况非常复杂,茅盾正是希望通过对青年人的失足、落水抱以“同情”“怜悯”的态度,并通过“女主人”纠结、矛盾、摇摆的心境达成改过自新的道德召唤。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念认知与创作指向,茅盾在《腐蚀》中着力“暴露国民党大后方酷烈的特务统治”,“抨击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推行内战,破坏抗日的丑恶行径,同时讴歌了小昭、K和萍以及《新华日报》为代表的进步正义力量”①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陈铨是“战国策派”中最具争议的核心成员,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曾留学美国、德国,历任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南京大学教授,是典型的学院派文人、学者型作家。陈铨是国内第一位较为全面系统阐释叔本华、尼采思想的学者,推崇意志哲学、狂飙运动等德国思想文化。《野玫瑰》对汉奸王立民的塑造就带有意志哲学的色彩。对于国共两党,陈铨本身并无自身的倾向,他是一个游离于政治和政党之外的文人,在德国求学深造的三年培育了他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家国情怀。由此,他带着个人化的认识和理解,怀着抗战时期普遍的民族意识写下了《野玫瑰》。
陈铨万万没想到,《野玫瑰》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野玫瑰》风波”。《野玫瑰》剧本在重庆《文史杂志》连载时并未引起读者的批评与不适,相反多数读者是欢迎的。1942 年3 月,《野玫瑰》被中央文化部部长张道藩看中,他组织人马公演,此话剧顿时名声大振;与此同时,《野玫瑰》剧本获得了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颁布的三等奖。然后,《野玫瑰》遭遇了左翼文化界的强烈批评与抵制,左翼文化界要求教育部撤销对《野玫瑰》的奖励。《新华日报》《新蜀报》《时事新报》《华西日报》《国民公报》等报纸都刊载了批判《野玫瑰》的文章。左翼文人认为,《野玫瑰》在曲解人生哲理,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不利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是有毒的“汉奸文学”。原本是宣传特工抗日、主导团结的正剧,却被左翼人士大面积批判,到底是什么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左翼核心作家茅盾的看法。抗战胜利后,茅盾在总结抗战以来的文艺工作时不点名地重点批评了陈铨的《野玫瑰》:
然而必须指出的,也还有一种表面上与抗战“有关”,而实际则是有害的作品;这就是夸张“特工”的作用而又穿插了桃色纠纷的东西。理论上,在沦陷区作“特工”——对敌的各种工作,组织地下活动,搜罗情报,破坏敌人机构等等——的人物及其活动,亦未始不可描写;但应当从有民众掩护,民众组织的背景上去写“特工”,也只有这样的“特工”才不是牛鬼蛇神的两面人,才有意义。可是我们所见的这一类作品却并不如此,它们把“特工”人员写成黄天霸、白玉堂一类,而又夸张其所谓“锄奸”的作用,对于沦陷区民众的抗敌活动却避而不谈,这就不但歪曲了现实,而且暗示给读者,抗战只要有“特工”就成了,不需要组织民众发动民众。这样的作品,尽管与抗战有关,然而是有害的,且正其表面上“有关”,故其为害不在色情作品之下。①茅盾:《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文联》1946年第1卷第1期。
茅盾认为,特工在抗战中的作用不能夸大,特工当然有组织地下活动、搜罗情报、破坏敌人机构的作用,但特工人员不是神,不是黄天霸、白玉堂一类的人物,而应该按照普通人的特点来描写,诚如他在《腐蚀》中塑造的复杂、迷误又失败的特工形象一样,这才是茅盾认为的特工面貌。特工应该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进行抗敌活动,否则就失真,歪曲了现实,这是茅盾对特工叙事的认知。由于茅盾固有的政治立场及其政党倾向,他不认同“歌颂国民党特务抗日”,他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广大人民群众抗争的结果。左翼文人坚持“唯物史观”,认为群众才能决定历史的演进;而陈铨恰好相反,他认为,意志是人类历史演进的中心,英雄的意志决定了历史的演进,“英雄就是群众的领袖,就是社会上的先知先觉,出类拔萃的天才”②陈铨:《再论英雄崇拜》,重庆《大公报·战国》1942年4月22日第21期。。陈铨推崇“英雄崇拜”,茅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两者持有不同的理论认知,如此,陈铨塑造的特工十分理想化,理想到走向虚幻,时人就曾指出“这样的一个女人似乎不是血做的、肉做的,也只有尼采式的超人才能做得到”③西滢:《书评·〈野玫瑰〉》,重庆《文史杂志》1942年第2卷第3期。;茅盾对特工形象的塑造又过于软弱无能,小说中的赵惠明对抗战几乎无任何贡献。由于两位作家对特工、群众的认知图式迥然不同,作品中塑造的特工形象也就大相径庭。
其次,我们来看陈铨的创作阐释。抛开政治立场,关于《野玫瑰》的写作,陈铨有合理的解释:
《野玫瑰》就是想把三种题材,联合表现出来。在战争方面,正的有艳华,王安,刘云樵。反的有王立民和警察厅长。在爱情方面,有艳华曼丽云樵的三角关系,然而艳华的爱情,虽然还不少留恋,早已为着国家民族而牺牲。在道德方面,王立民所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错误的思想。所以曼丽问得他山穷水尽,艳华再指出他的理想主义是建筑在动摇的基础上面。假如作者能够在这三种题材之上,表现出中国新时代的精神,不引起任何的误解与事实的歪曲,就心满意足了。④林少夫:《〈野玫瑰〉自辨》,重庆《新蜀报》1942年7月2日。
按照陈铨的写作理念和理论逻辑,《野玫瑰》并非在歌颂、美化汉奸,它不过是将战争、爱情与道德三种题材糅合,通过锄奸抗敌来批判个人主义错误,宣传民族意识。陈铨试图综合“永远能够引起人类兴趣”的“文学最合宜”的三种题材,将战争、爱情和道德融为一体,形成备受读者欢迎的谍战作品。
由于茅盾和陈铨对特工的认知、对英雄群众的看法不同,又由于政治立场、情感认知、思维模式差异,他们在潜意识中建构了特工题材的写作“知识结构块”,即写作图式。心理学家认为,图式是储存于人们记忆之中的由各种信息和经验组成的认知结构,换而言之,“图式”是一个人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的结构,是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技术和技巧。“写作图式”即作家在不断积累的知识、心理和经验方面形成写作结构与框架,在大脑中形成写作框图,它建立了写作的序列和模式,形成了深层次的模块组构。
由于两者悬殊的写作图式,左翼作家和“右翼”作家无法在特工叙事方面达成共识。左翼人士始终认为“剧本的思想我仍认为是错误的,不是什么香花”①张颖:《有关话剧〈野玫瑰〉——抗战中的一桩公案》,《百年潮》2002年第9期。,而陈铨则指出,“尽管他们如何批判,我始终不承认《野玫瑰》是汉奸文学”②陈雄岳:《与家兄陈铨相处的回忆》,1980 年代手稿。转引自孔刘辉:《陈铨戏剧活动考——从清华学校到西南联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3期。。理念和认知的巨大裂缝,导致两者之间无法沟通弥合。陈铨自以为左翼文化界在“吹毛求疵”,其实不然,我们对比两部作品就会发现其中有趣的差异,正是这不可跨越的差异和鸿沟导致两者形成全然不同的面貌。
结语
学界一般认为,陈铨及其剧作《野玫瑰》之所以遭到左翼文化界的批判,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生态的缘故。有学者通过对《野玫瑰》论争全过程的完整还原和分析,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国共两党之间复杂的政治斗争③李岚:《〈野玫瑰〉论争试探》,《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这背后自然有政治力量的博弈,“战国策派”不合时宜、偏激的思想理念也加速了这一论争和批判,但个中原因不限于此。“《野玫瑰》风波”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学界对其有各式各样的探究,我们还可以从图式理论及写作视野出发,从创作的角度分析特定文本的主题、叙述、人物等的不同,重新理解《野玫瑰》的特异性,以及它与《腐蚀》在创作上的反差。综上所述,创作理念、历史认知、政治立场以及思想情感都决定了两者的差异,《腐蚀》和《野玫瑰》提供了两个有意味的文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写作图式。
另外,国民党特工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物,如何在文学作品中演绎并呈现,这既涉及历史的认知,也涉及写作的考量。如何创作一部经典的特工题材作品,《腐蚀》和《野玫瑰》都提供了答案。两者各有优缺点。《腐蚀》采用日记体形式,情节复杂,情感细腻,但视角过于狭窄、叙述过于碎片化,缺乏紧张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野玫瑰》情节集中紧凑,叙述波澜起伏,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过于单一扁平,缺乏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心理刻画和社会剖析。如果作家能够融合两部作品的优点而剔除两部作品的缺陷,也许会出现一篇较为完美的特工题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