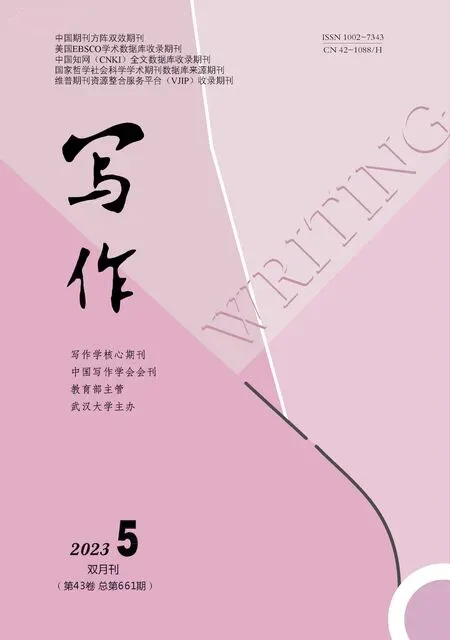“现代风景”的诞生:郁达夫小说风景书写与主体意识
丰 景
现代性是郁达夫风景书写的核心问题,也是探讨风景书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关键所在。以往运用风景学理论进行分析的论文,早已意识到风景问题并非简单的描写问题,而是代表着现代个体精神境遇的转变。例如,吴晓东《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①吴晓东:《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郁达夫与现代风景的发现问题》②吴晓东:《郁达夫与现代风景的发现问题——2016年12月13日在上海大学的演讲》,《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2期。《拟像的风景》③吴晓东:《拟像的风景》,《中华读书报》2010年7月21日第13版。三篇文章,将风景的发现与现代主体性的发现相联系,认为风景背后不仅是人性/审美主体,同时也是文化主体。郭晓平同样将风景与自我相联系,他将郁达夫的风景书写分为自然风景与现实社会两大空间,认为两者的错位与统一折射的是自我的矛盾、痛苦与欲望④郭晓平:《论郁达夫小说的风景书写》,《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3期。。
其实,早在风景学理论真正应用于郁达夫小说研究之前,大多数研究者便已发现“自然”在郁达夫笔下并非单纯的描写性存在,浅层景物描写之外隐藏着深层的寓意或指向:蔡震早在1980 年代便提出,郁达夫的自然观使其形成了在文学上追求“真”的创作观念⑤蔡震:《文学对自然的思考——郭沫若郁达夫比较研究札记》,《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黄川也曾将郁达夫的“返归自然”与人(个体)追求自由平等的诉求相联系⑥黄川:《“返归自然”在郁达夫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意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在比较文学方面,卢梭对郁达夫风景写作的影响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问题,唐小林曾指出,郁达夫眼里的自然就像在卢梭那里一样,是与传统社会文明对立的一个富有灵性的世界,但是郁达夫的回归自然尽管也有卢梭式的对当下社会及文明的疏远和叛逆,但更多地表现出传统士人将自我消融于自然的倾向①唐小林:《论卢梭对郁达夫人文精神的塑造》,《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由上可知,针对郁达夫与风景/自然的研究,已触及许多可供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风景作为主体的投射问题、风景在小说创作中的寓意问题、郁达夫的自然观与浪漫主义“回归自然”以及传统隐逸思想的相关性问题等。但问题在于,郁达夫风景书写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笔下出现了“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早”、最为成熟的现代风景②吴晓东:《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然而,早在《沉沦》诞生于1921年,五四白话文小说中即已经产生了不少风景描写,诸如郭沫若、冰心、叶圣陶、庐隐等人都是描写自然风光的好手。那么,与同样高扬现代主体、自我解放、社会问题的他们相比,郁达夫自身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如果从文本细读出发,则会发现几个高频词汇在郁达夫风景描写中常常出现,景观方面诸如碧落、日暮、江海等,观赏方面诸如闲游散步、眺望仰望等,这些词语组成了近似场景,使郁达夫的风景具有了某种极强的辨识力(例如主角总存在抬头看天、眺望江海、日暮散步等行为)。因此这些带有浓厚郁氏特征的观赏方式、描写方式都可以进行风景学理论的观照,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做新的解读。
一、“抬起头来看”:郁达夫的人与自然观
郁达夫的风景书写有着辨识度极高的郁氏特征。熟读郁达夫作品的读者应当都很熟悉这一场景:在情节描写后,主人公总会习惯性抬头看天,突然触景生情,生发出或是愁闷、或是释然、或是不能言表的诸多情绪。作为“抬起头来看”的对象,“天”成为郁达夫笔下极具标志性的景观。在所有表达“天”的词汇中,“碧落”这一非现代词汇值得注意。“碧落”原来是一个道教词汇,意指东北天界的烟霞和神祇,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后来被运用至唐诗中并逐步成为固定词汇,宗教含义逐渐弱化,世俗的、自然的天空含义逐步突出。到了五四仍有作家在采用这一说法,不过用法大多套用了《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典故。在郁达夫笔下,碧落”出现时并没有承担比这类同义词更为复杂的意义,只不过读者在阅读时,配合着他颇具蕴藉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更容易产生美的审美感受。
与“碧落”一样,长空/天际/天色/天空等词汇,同样是“抬起头来看”所注视的“天”之变形。归纳看来,郁达夫小说中涉及“天”的部分,可以根据风景带给主人公情绪上的变化而分为两类。在第一类书写中,主人公因仰起头来看见了这无穷的“碧落”而感到孤寂凄凉,从而陷入郁氏独具特色的自怜自艾的情绪之中。《秋柳》中的主人公从妓院中走出,一人在黑漆漆的街道走着,仰起头来看到阔大的“碧落”和明星,不禁在闹热的欢愉之后产生了一种“孤寂的悲感”③郁达夫:《秋柳》,《郁达夫全集》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在此类情景中,“天”像是自然的一个情绪触发点,能把主人公的视野拉远拉长,使主人公在天地悠悠的空间中,在苍茫无底的天地之间,抒发出现代人的孤寂情绪。其作用类似于催化剂,能在人与天/宇宙的比对、勾连过程中,加深现代人“个”的孤独。
而在另一类情绪中,主人公往往陷入某种和谐满足的状态,小说节奏也就此放缓,转入事件情节发展的缓冲地带,常见的描写逻辑便是抬头望见“碧落”,由此感物生情,产生平静、感谢、安逸的情感。例如《迷羊》中主人公在养病时总爱去郊外的小山中读书,有时仰卧在这大自然的清景中,看着这一片“碧落”,不觉便忘记了自身之存在,甚至于“把什么思想都忘记”①郁达夫:《迷羊》,《郁达夫全集》第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胃病》中的主人公因病发在房间中养病,清晨却被春日的阳光惹得开了窗,觉得外面的一片晴天,“看得人喜欢起来”②郁达夫:《胃病》,《郁达夫全集》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暂时性地忘却了久病的阴郁。在这些段落中,主人公似乎总处于某种病痛或阴郁心情的折磨中,而晴空所代表的自然风景,总能即时地给予主人公以安慰、净化和洗礼,从而使其陷入到或物我两忘、或感谢、或欢喜的情绪之中。与前文的伤感情绪不同,在这类情境中“天”成为引发大自然净化功能的契机,似乎“无穷的”“苍茫无际”的天空能开阔人的胸怀,产生遥远阔大的时空感,使主人公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从而陷入平静的、安宁的情绪之中。
以上两种情绪,大致可以代表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总体心境。不论情节如何改变,在与风景接触时,主人公的情绪大约总在两者之间摇摆。其中,“天”作为情绪的触发点,相比于其他景物,更为直接地沟通了风景与主体,可视为我们解决自然风景如何与主体建立起关系进而触发主体情绪的突破口。
在探讨天对人的情绪作用机制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郁达夫建立起“现代之天”影响主人公情感的方式,其实是现代天人关系转变的一个侧面。众所周知,“天”这一意象在传统文学和文化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位置,自然山水从来并非原始的、自然的纯粹物质体,而是承载了道、伦理等外在抽象观念。宋明理学虽说“人但物中之一物”,但却以理作为内在逻辑,为的是以物求理,达到天人合一的古代之“我”状态。道家虽推崇归隐自然,享受的却并非仅仅是自然之乐,还有最高原则的感性感悟。而在清末民初,作为承载了自然、伦理、神灵合体的“概念之天”,逐步经历了“风景的发现”,传统意义上“天”的神性地位被颠覆,自然性和人性精神得以展现,现代意义上的“自然”观念逐渐占据主流。人逐渐摆脱了终极意义的束缚,实现了与自然的沟通。
与此相对地,郁达夫在表述其人与自然观念时,似乎有意刨除了传统逻辑,采用的都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谈及天人合二为一,他引述的是上帝造人的起源,“人就是上帝所造的物事之一”③郁达夫:《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人与自然相融合而达到的和谐状态,乃至自然对文学产生的起源性影响,则被郁达夫解释为“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诗起源的另一个原因,喜欢调和的本能的发露”④郁达夫:《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至于自然净化人格、使人回归原始状态的作用,则更多地来自卢梭的思想,他认为社会虚伪堕落,自然能“给与本来是善良的人类以幸福”⑤郁达夫:《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页。。
事实上,天人关系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变曾作为研究现代文学转型的切入点,被一些研究者当作民初文学转型的样本来进行分析。耿传明曾以郭沫若(人凌驾于自然之上)、鲁迅(人与异己世界的对立)两位作家作为现代文学对待天/自然的代表人物,在分析文本的基础上展现了传统天人观念在现代文学书写中的两种形态⑥耿传明:《天人关系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变》,《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2期。。
与以上两位现代作家都不同,郁达夫并不着意于表现人与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他以现代之“天”作用于主体情感的方式,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壁垒,从而使两者达到某种和谐的平衡状态。在这样的逻辑下,郁达夫笔下的两种情感可作如下解释:孤寂的现代情感,是由于情感主人公在遥远的时空场景下找到了情感的抒发口,借用望天这一动作暂时性地逃离周遭现实(当目光抬高时,身边的景物、建筑、人事都得以远离)以专注内心世界。而“物我两忘”的情绪,则是因为“人就是上帝所造的物事之一,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当回复到原始状态,抛弃社会虚伪礼节,以求达到“蠛蠓蚁虱,不觉其微,五岳昆仑,也不见其大”①郁达夫:《住所的话》,《郁达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的“物我两忘”的状态。所谓“物我两忘”,正是强调了人向自然之天靠拢,摆脱被灌输的诸多观念,回归到原始性与自然性的本真之人。
可以说,郁达夫由观望“碧落”、与自然合二为一而产生的诸如感谢、喜欢的情感,主要源于人性与自然的交融,是在自然净化作用下产生的情绪快感。事实上,风景的净化作用是郁达夫风景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郁达夫不止一次地提及自然之于人的积极作用,主要功能便是使人性净化、人格发现。如许多研究者所言,这一思想主要受卢梭影响。卢梭的自然观是一个复杂的本体论概念,与社会、教育、宗教等概念互相缠绕,但基本不出个人/社会、原始文明/城市文明、野蛮人/现代人、自然/社会几组对立关系②唐小林:《论卢梭对郁达夫人文精神的塑造》,《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这种对立使个人与自然成为批判、纠缠现实社会以重建理想社会的重要资源与依据。换言之,重返自然,回归到超越了历史善恶的人类原始状态,并据此扬弃文明社会法律、道德、制度的不合理因素,成为消解现代人生存紧张的关键。卢梭的这一看法可以在郁达夫那里找到对应:正是因为“倾陷争夺,不害人不足以自安,不利己不足以自存,是近代社会的铁则”③郁达夫:《戏剧论》,《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他才会有“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④郁达夫:《忏余独白》,《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页。的论断。自然状态的人类比“现实的人”或政治人更幸福——这一来自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观点成为解释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为何总能在风景与自然中寻得平和、慰藉与净化的绝佳注脚。
然而,不能忽略的一个语境是,卢梭所处的时代是18至19世纪,彼时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暴露,现代都市文明也逐渐显示出压抑的一面,西方文明社会才受到沉迷于物质的批判。因此,卢梭才会从人类社会源头说起,得出“人类的束缚和不平等的起源,都因为社会的缘故”⑤郁达夫:《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页。的结论。和许多五四知识分子一样,身处现代化刚刚起步的中国,郁达夫对相对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所导致的人性腐败等问题,并未有卢梭一般的切肤之痛。因此,在论及现实生活所需要的自然观时,郁达夫对“人性发现”做了另一番中国化的解释。在他的笔下,“那些卑污贪暴的军阀委员要人们,大约总已经把人性灭尽了的缘故”,所以才会对这“自然的和平清景而不想赞美”⑥郁达夫:《感伤的行旅》,《郁达夫全集》第4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而“中国贪官污吏的辈出,以及一切政治设施都弄得不好的原因,一大半也许是在于为政者昧了良心,忽略了自然之所致”⑦郁达夫:《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231页。,至于那些因官场、名利而“利欲熏心的人”,郁达夫开出的良药便是“一服山水自然的清凉散”⑧郁达夫:《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231页。。如此看来,郁达夫所倡导的“人性”并非卢梭所谓返归自然的原始性,而是摆脱了卑劣国民性的人之天性。
在一篇《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的文章中,郁达夫指出种种国民性弊端,诸如利己、做官发财、利用机会的思想,其源头在于“三千年陈死人所遗下来的铁锁”⑨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其中又以其对青年人的毒害最为紧要。虽与卢梭一样探讨自然与社会之关系,郁达夫的“自然净化作用”更多地与当下中国国民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联系。在西方风景学语境里,“风景”与“国民”两个词语常常用“认同”来连接,探讨某一标志性景观的建立如何增强了国民的认同感。而在郁达夫这里,风景似乎成了改良国民性、使中国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良药”。在遭遇入侵危机的20世纪初,中国国民认同感的加强通常通过抵御外族强权的方式得以完成,相比之下,如何破除传统思想、惯例、规则养成的国民性成了郁达夫与众多五四知识分子选择的方向。与别人不同的是,郁达夫选择了一种颇具个人性并为西方浪漫主义所影响的方式。
二、如画(picturesque)风景意识
郁达夫小说中一个受到不少研究者探讨的特征,是他喜欢将西洋画、水墨画作为比拟的对象,犹如特意展示一般,将小说中的风景以画作的方式展现,以“如画一般”的间接形容代替了着重于实地体验的白描式书写。因此,郁达夫小说中的风景有时需要有相应知识背景的人才能“破译”。例如,郁达夫曾以密来(Millet)的田园清画/洋画上的瑞士四林湖为依托,来描绘日本从山顶看下去的稻谷平原和大观亭附近的山水。从“大观亭”“圣帝庙”的命名就能看出,这些地点都带有强烈东洋特点,郁达夫对此的处理则是从欧洲(法国、瑞士)中汲取养料,从而产生了景色与画作在比拟上的错位。
吴晓东在《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一文中,曾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拟像的风景”①吴晓东:《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郁达夫借前人之手写眼前之景并非局限于对西洋画的引用,还存在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挪用。这种描写更多地出现在中国本土化景观中,故乡尤甚。其意象大多采取了竹林、苍苔、船、草舍、大雪等中国古典诗文中的元素。例如,《逃走》中以传统景观面貌出现的圆通庵,周围装点的是些竹林花岩,竹林老树、岩石苍苔,这种点缀得凌乱却很美丽的景象,“像中国古画里的花青赭石”②郁达夫:《逃走》,《郁达夫全集》第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蜃楼》中的主人公早晨推开窗,便看到似乎被染成“墨色”的湖面,搭配着前后小山,仿佛成了一幅“中国水墨画景”③郁达夫:《蜃楼》,《郁达夫全集》第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240页。,高峰、湖面、湖船、船家、长堤、小山头、枯树林,这些近似于水墨画的景象,带来了“天地之间的那种沉默”,那种伟大而又神秘的沉默与传统美学的留白又存在着某种巧妙的共通性。与之类似,《出奔》中主人公快爬到山顶时,也望见了自然山水与打斜的太阳,活像是“水墨画成的中国画幅”④郁达夫:《出奔》,《郁达夫全集》第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而这水墨画幅,又是颇具中国意蕴的“江南的雪景”:半城烟户,参差屋瓦,远近诸山,水畔高塔、三面江水……让人颇有身入画中之感。此外,在一篇名为《小春天气》的散文中,郁达夫还将G君在陶然亭作画的过程、画作的内容事无巨细地写了下来,与其笔下的自然风景相互映衬。只是与郁达夫所观看的“迷人落日的远景”不同的是,G 君名为《小春》的“杰作”,却充满了“阴森的墓地”“冰冷的月光”“灰黑凋残的古木”等意象,从而使观赏画作的“我”起了“惊恐之心”⑤郁达夫:《小春天气》,《郁达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这种以画入文本的写作方式,使郁达夫的风景描写带上了某种“如画”的意味。除西洋画、明信片、照片等西方式风景外,郁达夫对传统水墨画的引述,表明其对于“像……画一般”的形容似乎有独特的热衷。这导致读者在阅读文本时,需要调动已有的审美背景,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到郁达夫所构建的如画图景,其阅读体验也从文本—风景转而成为文本—画作—风景互相补充的状态。
“如画”(picturesque)这一概念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彼时经验主义哲学追求观看的纯粹性,在视觉上更关注对象的表象和外观。因此,“如画”首先代表一种观察自然的新方法,即把自然看成一副图画,用主体自身的眼光来观看、创作。可以说,“如画”其实是一个涵盖绘画、文学、建筑等各领域的概念。如画风景的一个观察特征,是主体将风景视为一个展示物。W.J.T.米切尔曾如此解释这一特征:“视野中的如画结构,就是把自然再现的景色前景化,给它镶框或者将之置于某个台面上……有了这个框架就可以保证它就是一幅画,就是如画的。”①[美]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如同绘画写生时用手框出一个边框,选取景观以进行艺术创作一样,如画风景的观者也将风景进行了无意识的划分,框出了一个与自己头脑中想象中的画幅相契合的画面。“镶框”意识是风景成为如画风景的基础,它将读者的眼光聚焦在某一地方,把广阔的场景缩小为画幅能够表现的体量,也将观感具像化了。
这种将景物“标出”的展示意识,把一处景物框定了,仔细揣摩、细致欣赏的方式,通常是拥有广泛游历经历的人才会有的经验。而没有游历经验的人,往往无法对沿途的景观做这种展览式欣赏——对于他们来说,身边的景物过于熟悉从而丧失了“镶框”的价值。温迪·J.达比在《风景与认同》中就曾引用皮格特的话,强调了旅行之于如画风景的重要意义:“一种新文学——该文学与改善的公路和运输密切联系,概括起来讲,就是与旅行有关,旅行往往就是寻求如画风景。”②[英]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旅行经验让作家在相对陌生的环境中获得了“如画”的描写冲动,产生了将风景与画相联系的欣赏意识。这一经验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来说,则往往与留学密不可分。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学生时期即已具备了游历异国的经验,并且是在景观颇具观赏性的日本。闻一多虽并非留学缘故到日本,但对日本的“如画”性却也颇有感触:
就自然美丽论,日本的桐树真好极了。有这样一株树,随便凑上一点什么东西——人也可以,车子也可以,房子也可以——就是一幅幽绝的图画。日本真是一个picturesque的小国。虽然伊的规模很小——一切的东西都像小孩的玩具一般,——但正要这样,才更像一幅图画呢。③闻一多:《致吴景超、顾毓琇、翟毅夫、梁实秋(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闻一多书信集》,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页。
对于郁达夫来说,这一经验显然也是在留日时期获得的。日本以“一幅图画”般的东洋景观为图画式的联想奠定了基础;而郁达夫的远游经历以及“野游”趣味习惯——“我从前很喜欢旅行,并且特别喜欢向没有火车飞机轮船等近代交通便利的偏僻地方旅行”④郁达夫:《住所的话》,《郁达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都对其写作方式产生了影响。从中国到日本的一路风光,以及在日本生活期间的游历经验,使郁达夫将陌生的风景“镶框”成了一幅画,并由此获得了将风景与绘画相比拟的观察视角。
如同英国人在本土寻求意大利风景一样,郁达夫以西洋画对东方风景、以传统水墨画对现代景色的比拟也有些错位。这种错位源于两者均将自身的古典教育、绘画知识作为基础,使风景与绘画靠拢,满足了对理想之地的想象需求。可以说,郁达夫早在观看自然风景之前,就已在心里有了相应的风景视觉符号,小说中的风景书写,则是将这种先前积累的“感觉”投射在自然风景上。
有了“如画”的观赏意识,郁达夫才会把风景当作一幅图画来描写(从叙述方式上看,郁达夫的诸多描写都具有构图意识,甚至摄影意识),大大增加了小说的画面感。这一内在逻辑是在探讨西方印刷摄影技术、东西方权力之前,郁达夫书写“拟像的风景”所具有的前提性审美准备。
三、作为观看方式的“闲步”与远眺
跳脱出具体景观和描写方式,郁达夫小说中的风景书写还有一个典型的观看特征:主人公往往采取“闲步”/“散步”/“漫步”/“独步”的方式,自己一人在宽阔的原野,边走边看,以远眺的观赏方式将远近景色尽收眼底。《沉沦》中的主人公总爱随身携带一本华兹华斯的诗集,去原野“缓缓的独步”;《空虚》中的主人公,找到了一处“同修道院生活”的清净处,每到了无聊之时,总要拿了粗大的樱杖去山野乡道间“试他的闲步”①郁达夫:《空虚》,《郁达夫全集》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灯蛾埋葬之夜》的主人公养病期间,总爱去野外“行试一回漫步”②郁达夫:《灯蛾埋葬之夜》,《郁达夫全集》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看一看田埂土垄的田园景观,回来倒下便睡。
“闲步”的缘由,可以做诸多方面的解释。如前所述,日本人十分喜欢的野外郊游习惯(郁达夫说日本人称它为Hiking),带给郁达夫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也养成了无事散步的观赏习惯。此外,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每每涉及“闲步”的观赏时,郁达夫总将其与浪漫主义联系起来。“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暗示了主人公在稻田中间独步的审美基调,而“Idyllic Wanderings”(田园的漫步)的形容更是带上了浪漫主义的基因:Idyll本是希腊词,本意为微型的画卷,后来专指维吉尔等浪漫主义作家如画卷一般的田园诗。
在维吉尔、华兹华斯之后,浪漫主义作家们的确将“闲步”发展为了一种时代潮流,以至于到了19 世纪40 年代,对于西方身居城市的上流社会人士、人文学士来说,在乡间田园、山区荒野进行散步/徒步已经成了追赶潮流的平常之事。许多作家将“闲步”作为体验风景的一种方式,并将这种观赏方式融入了文学作品中,以一种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方式表露着对田园风光、荒野景观的热爱。
与当时许多华兹华斯迷一样,郁达夫在小说中对“闲步”的重复性再现,乃至于自身养成的散步习惯,都可看作对华兹华斯的某种模仿和崇拜。对外国文学极为熟悉的郁达夫显然也受到了浪漫主义风景写作的影响,在深入自然体验“闲步”的同时,郁达夫也给主人公设置了观赏风景的“幕布”,使其在漫步乡间田野的过程中,丰富了小说田园风光的描写,加深了浪漫主义基调。从“乡间的大道”“绿草丛生的矮小山岭”“黄苍未熟的稻田”“青枝落叶的野菜畦边”等乡间景观中,不难发现郁达夫对田园趣味的偏爱,以至于其小说中许多场景,都能归类到这类散步途中的乡间景色中来。
此外,“闲步”还是一种漫无目的的“云游”,这一特征让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常常在独步过程中边走边看,从而获得了思考和感受的空间。这种漫无目的的云游曾被安妮·华莱士称为“逍遥游”,“是一种陶冶心志的劳作,能够通过回顾和表达过去的价值,改造个体和他所在的社会”③转引自[英]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2-3页。。“回顺与表达”其实指向的是一个思考的空间,它存在于“云游”之中,以一种时空的暂时性延宕,留给思考者以梳理和表达的可能。
而当论及这种漫无目的的游走时,本雅明关于游荡者的论述则能为我们提供另一种思考角度。与浪漫主义作家对田园、荒野的观看不同,游荡者所张望的对象是现代化城市。此时,城市作为另一种“风景”,使游荡者在漫步过程中,找到了与机械化了的芸芸看客不同的特性——一种在现代社会中拥有闲暇的“回身的余地”④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8页。。而游荡者这种观看外界的意识,正是具备了强烈自我色彩的个人意识。他们在游荡、漫步过程中,对城市与他人进行思考,在沉思默想中表达自身。如张旭东所言:“文人的流浪为他(游荡者)提供了工作和休息,更重要的是,为他提供了自我意识,这成为他生命的最高意义。”⑤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8页。
与上述论证逻辑类似,对于郁达夫来说,“闲步”这一漫无目的走走停停的方式,使其主人公获得了“看”与“思”的空间。“闲步”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动作或习惯,而是成为思考自我、表达情绪的渠道。它触动主体,使主体迸发出在静止状态下不会产生的能量(如卢梭所言,“步行包含某种能够使我的头脑兴奋和活跃的东西”①[法]卢梭:《徒步旅行》,乐黛云主编:《远离喧嚣》,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从而建立起风景与主体间的关系,并给予了主体一个独自思考空间,使主体的自我意识得以突显,并进一步加深了主人公某种感物伤怀的情绪气质。
于是,在郁达夫的笔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作家或主人公在田间漫无目的地走着,“一个人背手走着,枯寂的脑里,有时却会汹涌起许多前后不接的断想来”②郁达夫:《灯蛾埋葬之夜》,《郁达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143页。,从而对过去和现状产生“回顾和表达”的欲望。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便往往会因一次野外、田园的闲步,产生类似于“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的感喟,或者由此回想起“使他脸红”的“两个女学生”的故事来。如此看来,“闲步”这一方式不仅是郁达夫受到华兹华斯的影响,在观赏自然、赞美自然、回归自然的同时对这一欣赏方式的模仿;同时,这种观赏方式也是小说叙事的一个线索和契机,使故事在景、事、情三者间得以自由穿梭。
在探讨柄谷行人“孤独的人才能发现风景”这一理论时,吴晓东挑出了国木田独步的小说《难忘的人们》的一段描写,借此说明柄谷如何对风景发现理论做出诠释。吴晓东认为,在这一段把内心叙事与风景描写相结合的文字中,“眺望”一词尤其值得注意,它是一个指向主体的词语,“这里的‘眺望’,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看’,‘眺望’正是使对象成为风景的方式”③吴晓东:《郁达夫与现代风景的发现问题——2016年12月13日在上海大学的演讲》,《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2期。。
观看方式的确是风景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突破点,尤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观看方式往往暗示了主体与风景间的关系,其最终指向往往还是作为观看者的主体。按照吴晓东的逻辑来思考,眺望之所谓能够使对象成为现代风景,乃是由于眺望由主体发出,如同焦点透视法一样,主体便是“焦点”所在,而眺望而来的风景,也必定是在主体观照下产生的现代风景。而在郁达夫小说中的风景书写中,眺望恰恰正是主人公观看风景最常见的方式:《出奔》中的钱时英搀扶着董婉珍,爬上高处往下“纵眺了一回”,各自感受到了“不同的喜悦”④郁达夫:《出奔》,《郁达夫全集》第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蜃楼》中的“我”同样是爬上了一个小山峰的茅亭,“放眼向山后北面的旷野了望了几分钟”⑤郁达夫:《蜃楼》,《郁达夫全集》第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向某地远远望去可谓郁达夫小说主人公观看风景的范式,而郁达夫似乎也有意在强调这一动作,使读者跟随主人公的视角,对周遭环境进行一览式的观望。
同时,身为作者的郁达夫也很偏爱眺望式的描写。郁达夫小说的风景书写,如若篇篇单独摘抄出罗列起来,不难发现每篇之间存在着不少的相似性。文中常常出现的景物是村落、树林、山、水、天等位于远处的景物,视线并非一处到另一处地从远拉近,而更像是平行地扫视:“净碧的长空,返映着远山的浓翠”⑥郁达夫:《微雪的早晨》,《郁达夫全集》第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一面宽广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⑦郁达夫:《银灰色的死》,《郁达夫全集》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远处的人家、树林、空地、铁道、村落都饱受了日光,含着了生气”⑧郁达夫:《南迁》,《郁达夫全集》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作者居于某个高地,以远眺的方式观看风景,并将其观看到的景象诉诸笔端。因此在郁达夫小说中,很少见到针对某个具体景观的描述,更多的是一扫而过的整体印象,景物密集型地层叠出现,一个接一个地一闪而过。
这一远眺习惯形成的原因,首先同郁达夫的生活经验相关。他在富阳看得到“一川如画”景致的书斋,正好位于房间的二层,开窗便是富春江江面,凭栏眺望,风雨晦明的景致一览无余。而到了岛国,各种坐船旅行、眺望海面的经验,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观赏体验。
此外,如吴晓东所言,眺望这一动作应当放在现代风景发现的语境中来讨论,这一点对郁达夫的风景书写同样适用。西方风景学中,“远眺风景”(prospect landscape)这一名词早在18 世纪初就由约瑟夫·艾迪生提出,他在《旁观者》(Spectator)一书中认为远眺是“各种想象的愉悦”①转引自[美]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1页。,在这种观看方式下,目光以某种开阔的、不受限制的方式在地平线上游骋,因此远眺可以看作自由之象征。其后,米切尔在《风景与权力》中又指出,远眺是一种最大限度打量无垠景色的方式,它能使主体观察到广阔而不确定的景观,并由此刺激想象力的产生:
这里的“自由”指的是观者的目光能“四处游骋”以掌握风景的全貌,并使之服从于人的幻想和想象。因此,观者对广阔自然的感受实际上是使这种广阔性服从于人的视觉控制。②转引自[美]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1页。
主体对风景的观看,以一种自由的的方式展开,主体成为视线的聚集点,风景则完全被覆盖在主体的目光下,服从于主体的控制。在此意义上看,郁达夫所偏爱的远眺正是现代人观看风景的一种方式,它不同于古人登高望远,有较为固定的场景(譬如秋天登高之习俗),或源远流长的传统(登高必赋的传统),或较为固定的情感表达(悲秋叹己、怀人怀古),现代性眺望得以展开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具备理性和想象力的个人,他能在广阔的地平线上驰骋目光,将风景与个体,以及个体的想象和情感相联结,表达出现代人的苦闷和感性自我。
郁达夫着意于这种观看方式,或许出于从小到大的居住和留学经验,或许出于某种表达的直觉,或是外国文学的阅读积累,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无意识,这一观看和描写方式都让其笔下的风景带上了更为突出的现代性。风景在人的观照下全貌尽显,而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也得以体现。相比于局部的景观描写,眺望的动作显然赋予了主人公更多的自由,思绪和情感随着主体视野的游骋飘荡,获得了表达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