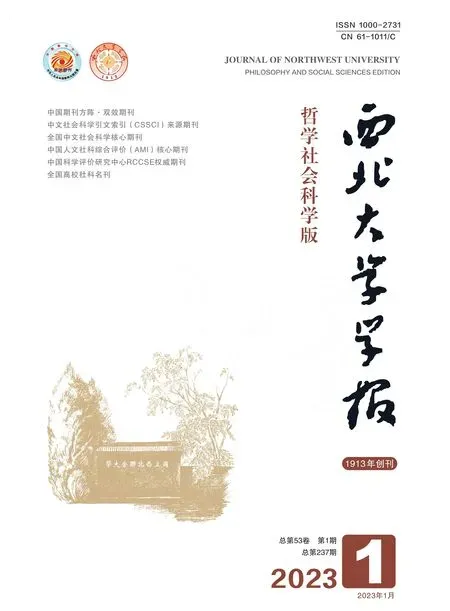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与文学概念的互动及其复杂性
王杰泓,武晓旭
(武汉大学 艺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回顾百年中国电影的演进历史,文学始终伴随左右。可以说,“一部中国电影史,也是一部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相互作用的关系史”[1]28。并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剧变之中,经济形势、社会形态以及政治局势瞬息万变,“过程远比结果复杂,其间的断裂更加值得注意”[2]82-91。在既有研究中,电影一度是“文学的附庸”,曾多年倚靠“‘戏剧’的拐杖”[3]3,未来或许会成为“文学的终结者”[4]74-80。类似情况,在早期“电影”概念初具雏形前,早以意义模糊、暧昧的“文学性”之名呈世。“文学性”(литератрность)一词最早由俄国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罗曼·雅各布森提出,指“使某一部书成为文学的那种东西”[5]23,简单说就是文学的本质或根性。电影学界借用此词来指称电影的本质或根性,即“电影的文学性”。因为电影是一门集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元素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具有典型的媒介间性,因此,与“戏剧性”“绘画性”“音乐性”一样,电影的“文学性”实质就是“电影性”的一种表达。中国社会在20世纪前半叶逐渐转型,“电影”概念也逐步确立。过去,电影与文学、文学性的关系史,常常被书写为线性时序下的事件史,学界更重视电影作为新兴艺术与古老的文学之间的身份差异,亦较为重视电影自身独立性的找寻,试图逐渐挣脱文学话语的束缚。但是,实际情况或较历史书写中的若干事件更为复杂。如果能多角度、分层次深入某一时期的历史裂隙,稠密观察电影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或许可以较大程度重返历史现场,管窥电影与文学的概念纠缠及其变迁,进而一探背后隐藏的复杂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状况。
德国概念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雷克设定了历史性基础概念的衡量标准: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时间化(Verzeitlichung)、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和政治化(Politisierung)[6]154。以这“四化”尺度衡量,1930年代中国“电影”概念已然确立其初步形态[2]。当时一部分人所讨论的“电影”概念,已经是作为“复合单数”[7]159的“电影”。影戏、影剧、电影、声片、movie、motion picture……无论大众用何种语词,他们对电影的思考都已抽象到一般的跨媒介层面。当时的“电影”,与此前所指的单个或单一类型影像已经有所区别,其内涵随影片形态发展而不断丰富,外延也随制作技术进步而不断拓宽。作为姊妹学科文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文学性”跨越学科边界,被中国电影界反复提及,并且在1980年代还引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论。作为文学与电影的跨媒介通路,“文学性”是否参与了“电影”概念的构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文学性”又是如何参与并帮助塑造出了当时的“电影”概念?“文学性”的介入,是否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一条可能的文学路径?
本文认为,在跨媒介视角下,借助概念史方法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有助于重新理解早期中国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化,进而反思中国“电影”概念的早期建构过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文学性”为化身,始终缠绕着“电影”概念,而“电影”的新旧语义也并未在这种纠缠中走向既往研究默认的线性交替,反而是以重叠的形式附着于概念之上,在复杂的“艺术”或“文艺”语义场中,体现出“不同时的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7]164。在此过程中,“电影”始终都在与其他概念的比较与区别中艰难寻找自身的独立性。本文期望在电影艺术本体论层面以及电影与文学的跨媒介比较视域中,为电影理论与历史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
一、被“文学”统摄的“电影”
“电影是否能在文学上占一个位置?”[8]9自1920年代起,文学与电影互动的语料便见诸报端。“影戏与小说”“电影与诗”“电影字幕”等一些“电影”语义场内部的零散议题,被整合、明确为“电影与文学”“影戏与文学”等抽象论题,以讨论电影是否有资格追求文学上的地位。而有趣的是,这些文章共同体现出一种以“文学”概念统摄“电影”的迫切心态,即“将它们运用到对象上面去,以及——若从对象的角度来看,将后者放到概念‘下面’去”[9]109。
在早期中国文人非体系化的散论中,“文学”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已高度成熟的抽象概念,而“电影”则被视为一种实体概念抑或纯粹的对象性概念,这阻碍了“电影”从作品式单数语词发展成为普遍性、多义性的“复合单数”概念。职业剧评家冯叔鸾较早地将电影视为一种文学体裁,继而在“文学”大概念之下探讨具体的“影片”,而非抽象、广义的“电影”。此举以具体对象替换抽象概念,在抽象意义上消解了尚未成形的“电影”。1924年,他曾以《影片在文学上之价值》为题在中华影戏学校开展讲演,直言“一部影片实无异于一部小说”[10]5-8,中外影片的差距主要在文学上,“影片以文学为其主要之成分”[10]。田汉明确将“电影”规定为“戏”的下位概念。在1926年晨光美术会发起的夏令文艺演讲会上,他发言称“影戏是戏之一种,戏是文学之一种”[11]23,用“文学的”电影与商业片对立,以赞扬艺术质量较高的影片。文学成为评判电影作品艺术价值的参照系,“用文学的方法或手腕”制作电影是“近来影戏的大进步”[11],在审美价值层面将文学凌驾于电影之上。侯曜也曾特地撰写《电影在文学上的位置》一文,认为电影具备文学的特质,所以“必能在文学上占一席(重)要的位置”,甚至感叹“电影是文学!电影是活的文学!”[12]20-21知性产生概念,概念统摄对象,大概念统摄小概念,侯曜的论断将“电影”拉至“文学”的语义场,意图使电影成为文学的新化身。
然而,侯曜的振臂高呼并没有引起电影界或文学界的重视,这使部分文人开始从文学的革命价值与社会意义层面寻找文学统摄电影的可能性,也推动了“电影”向“复合单数”式概念进一步发展。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竞争、论辩的时期,文学因而成为 “阶级的武器”[13]3-20。在许多人眼中,电影作为文学之一种,革命价值不言自明。潘垂统支持侯曜的观点,在《民新特刊》撰长文表达自己的疑虑和建议,“要使电影在社会上成为一种更有意义的东西,应使他在文学上占到一个地位”[8]9。在他看来,文学的社会意义远大于电影。他在文中倡议将电影提升到与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为其赋权,称电影不是“茶余酒后的消遣品”[8],并由此引出电影的社会使命,倡议影人“先重视文学方面的价值,也顾到营业方面的利益”[8]。可以看出,与田汉一样,潘垂统将优秀电影的艺术质量归功于其文学价值,将电影归入文学之一种,然后畅谈文学的“革命”与“彻底的觉悟”[8],暗示电影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必然具备某种革命潜力。作为鲁迅大力支持的青年文人,同时也是著名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潘垂统在文中暗含的左翼意识形态倾向可见一斑。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做法恰恰为“电影”发展为抽象的“复合单数”概念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当人们所定义的“电影”不仅仅是娱乐工具,还可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时,“电影”将有机会发挥塑造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14]223,而这正是成为“复合单数”概念的一段重要里程。
还有一些言论牵涉到更为复杂的“艺术本质”问题,体现出1920—1930年代暗流涌动的社会心理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人从发生学角度切入,或认为文学是一切艺术的基石,或将文学归于门类艺术中的一种,在此前提下才论及“电影”,仍尝试在文学学科内部讨论电影。“凡百艺术,莫不以文学为之基,有文学而艺术始立。”[15]31-32“艺者质也,敷之以文而彩色声音乃显,否则流于江湖,同于傩戏,大雅何取?”[15]就此,鸳鸯蝴蝶派文人陈小蝶指出了电影的改编问题。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为例,他认为,尽管电影向经典文学取材“志极可嘉”[15],但暂不具备改编条件,于是列举《茶花女》《复活》《红字》等由小说改编的西方电影以资借鉴。这一思路无疑在创作层面肯定了小说改编电影的做法,亦确证了国内古典名著改编电影的可能性。但在当时关于应当“全盘西化”还是“建设本位文化”的论争影响下,广泛的社会心理往往混杂着对国内电影创作技巧的极度不自信。作者认为,拍摄思维的落后,导致四大名著“一入银幕则迹象流漓”[15],才使得“盲本弹词,狐灯犬戏,悉上银幕”[15],此言直指当时热映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电影和“火烧”系列电影。陈小蝶的结论是,“大雅”已无处可寻。除了小说,还有人将电影与中国的古体诗作比较,先说“电影是文学的艺术,谁都承认的”[16]3,在此基础上,提出电影与中国古体诗的关系更为密切,认为电影导演也需要“略懂诗的意味”[16]。作者还以电影分镜形式分析唐诗内容,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融入电影这一“物质进步的产物”[16],此种观念正回应了193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17]4。在这些讨论中,电影与小说、诗歌平起平坐,“电影”便被纳入“文学”的语义场内,成为文学内部的一个新门类。
此外,报刊上仍有许多相似言论,均站在文学学科内部来探讨电影问题,甚至将电影论题看作是文学论题的延伸。“在从前,影片与文学是毫无关系的。在现今,影片与文学的关系很大而且将要更大”[18]41-44;“电影与文学,显然有密切之关系”[19]4;“电影是被称为第八艺术的,因此她与文学也就不能没有关系”[20]41;“其实电影与文学本有很深切的关系。……至于文学作品上了电影,这更是一件所谓珠联璧合的事”[21]2;1932年出版的《新兴文学概论》当中,除了文学内部诸问题、诗歌、戏剧、小说等十四个正式章节之外,作者特地在书中附录一篇名为《关于电影艺术》的论文[22]139-146;1935年出版的《文学百题》,也将洪深的文章《电影在现代艺术居怎样的地位?它和文学有怎样的关系?》[23]262-265作为论题之一列入正式目录中。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急切地将“电影”纳入“文学”的管辖范围。同一时期就有人认为很难在电影史上探讨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因为电影最初只是个“玩起来”“必定能够赚钱”的新事物[24]14。电影创作题材往往“在低级趣味的迎合”[24],是为了反映文学而存在[24]。尽管该文章意在号召文人脱离理论斗争、深入社会现实,仍体现出作者站在文学角度对电影的轻视。电影不过是高贵的、革命的文学表出的窗口,抑或是宣传工具,对二者关系的指认也只需停留在实际应用(技术)层面。不过在概念构建层面,该文作者介夫与前文提到的潘垂统观点表达的效果并不一致。潘垂统将电影划为文学之一种,而介夫则抓住了电影与文学的某种异质性,在强调“文学”革命价值的同时,扼杀了“电影”一词在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抽象化的可能性,以阻拦“电影”成为“复合单数”式概念。 有文人甚至对电影抱有敌意, 《影戏年鉴》曾刊登一则短讯: 《文学家咒诅电影》, 一英国文学家称“世界上没有比电影更下流的嗜好了。 我希望十年以后, 地球上不要再有电影的存在”[25]230。 此言或许过于极端, 但该文刊登在电影刊物上, 框定了“电影早已公认为最有意义之娱乐品”[25]的语境, 大方引用欧美文人针对电影的负面言论作为电影界的新资讯,反而说明至少在电影界内部, 有一些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已然不再寻求电影在文学上的地位。
从有关这一议题的诸多讨论中不难看出,“电影”概念的形塑,不断冲击着旧有的文学理论话语,引起了部分文人的强烈焦虑。当时公开发表的报刊言论里,与“电影”概念相互交织的复杂话语背后暗含着一项明确的先决条件:与电影相比,文学更古老,更成熟,更规范,更独立。在此前提下,“电影”被更高阶的“文学”纳入理论及批评话语乃至概念场域几乎成为一种必然。这种类比的范式还延展到电影与戏剧、电影与绘画的关系上,电影不仅一度险些成为文学的附庸,几乎同时还险些成为戏剧的附庸。1930年代,“电影”概念尚处于在多个混用概念中艰难寻求独立的阶段[2],而在混沌状态下,文学话语以强势的姿态,试图将电影挽留在自己的理论场域,并以更宽广的外延将“电影”概念圈禁其中。如今看来,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忽视背后的原因。早期中国电影艺术实践与理论的飞速发展给文学带来了极大压力,同时,文学理论话语面对新兴艺术实践的挑战,反反复复浮现出针对电影的“影响力焦虑”,在“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实践理性思想影响下,文人、影人面对民族国家危机顺势而为的功利性诉求,又被这种焦虑带来的问题所遮蔽。不过,这一尝试又是成功的,电影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并未因“电影”概念的初步形成而盖棺定论。站在跨媒介视角重新观照,“电影的文学性”似乎是同一时期文学擭住电影的另一条可能的路径。
二、“电影的文学性”作为“中介”
“电影的文学性”是什么?1986年版《电影艺术词典》将“文学性”定义为“电影艺术从艺术分类中的文学(即语言艺术或诗)中所吸收的因素”[26]162。看上去是定义“文学性”,实则是把文学特征嵌入“电影”概念之中。一直以来,许多学者试图直接通过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探讨来解答以上问题,而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同样的,试图对该说法进行一劳永逸的界定更是刻舟求剑。若回到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史现场,情况是否早已如此?文学是否天然地内嵌在电影之中?单纯就概念史而言,同一时期人们所谈论的“电影”、被拉入文学话语场域的“电影”、带有“文学性”的“电影”……是早期电影理论生发的多重语义在“电影”概念上的重叠,展现出某种“不同时的同时性” (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7]164。作为艺术领域的新概念,“电影”重叠的语义当中“聚合着不同时的经验和期待”[7]163-164,若能改换研究视角,观照不同“历史时间层”(Geschichtliche Zeitschichten)之间的差异,或许能突破已有研究的局限,超出特定行为者的心理[27]143,指向更为广泛的社会话语实践。早期中国尚未成形的“电影”概念在与“文学”的碰撞中,既融合了上千年的“文学”经验,又在当时“革命”“进步”的语境中对接、容受译介而来的海外电影理论,最终借助“电影的文学性”相关讨论表出,才使之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经典话题。
那么,当他们谈论“电影的文学性”时,他们在谈论什么?1930年代,有一条思路是将“电影的文学性”等同于单纯的电影创作要素——电影字幕、电影剧本、电影本事,有时也会涉及电影的叙事问题,如电影叙事结构、电影改编等。国内最早谈及“电影的文学性”的是一组译文。1934年12月10日到21日,《民报》连续刊载了以“电影的文学性”为题的系列文章,原作者若江俊三试图对“电影的文学性”作出界定,他认为“表现在电影作品上的文学形态,这就是成为在电影上没有肃清地照样留下来的文学的残滓(文学性)”[28]9。若江俊三引用巴拉兹·贝拉的著述,带出“电影的文学性”问题。从《可见的人类》到《电影精神》,有声电影的出现使得“视觉的人类”议题已愈显陈旧。他认为,若要讨论“视觉与听觉的人类”,问题症结在于“电影上的文学性”[29]4。具体到创作要素,首先,电影字幕被认为是电影中最明显的“文学性”所在。作家、翻译家汪绍箕称“影片中的字幕纯然是一种文学作品”[18]41-44,并将字幕与短篇小说进行类比,都有“经济,精悍,生动”[18]的特点。1932年,刘呐鸥在《影片艺术论》中专门开辟一节,谈“文学的要素和字幕问题”,认为电影的文学要素体现在电影字幕与影片叙事结构上。即便当时已经开始公映有声电影,但“因发生史上的关系,现代的电影可惜仍脱不了字幕这文学的要素的羁绊”[30]116。他用统计法诟病《啼笑因缘》的影片结构,字幕占据该片的40%,“说它是影戏,她却拿了许许多多的文字来给你读。说它是文学,它却用了好些动着嘴的半身像的画幕来打断了你的自由想象”[30]117-118。其次,“电影的文学性”还体现为电影的情节要素与叙事问题。殷作桢在《电影艺术》中称电影“有文学的要素(情节Plot)”[31]60,认为以人物性格塑造来推动情节发展,字幕或对白简单有力,就是文学技巧在电影上的优异表现[31]。第三,电影剧本及电影改编也是有关“文学性”的热点话题。若江俊三在研究“电影的文学性”时称,电影剧本是电影制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有内容的文学的阶段的表现”[32]9。藏田国正的译介文章《电影脚本的文学位置》提到“将摄影脚本,看作一独立的文艺作品”[33]15-16。还有英文报纸刊登快讯,某编剧将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出版为小说,记者便高呼“新形式的文学”(New Form of Literature)[34]14诞生了。关于电影改编问题,有人说改编是“文学电影化”[35]6,亦有人说是“电影文学化”[36]2。王平陵在其著作《电影文学论》中就谈到了“电影化”[37]10的电影剧本,以及“文艺作品电影化”[37]8-9的问题。时任《清华周刊》文艺栏主编的作家李长之,在以笔名朗琴[38]193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亦提到“文学作品电影化”[39]216-218的诸种困难。表面上,这些言论只是有关电影改编的不同表达,实质却折射出两种迥然相异的电影理论观念视角:一个是站在文学学科内部,将文学文本转译为电影文本的过程视为文学的“电影化”,即以电影特有的技术与艺术表现方式处理文学,电影是手段,文学是目的;另一个则是站在电影学科内部,在电影创作阶段打捞素材的多重路径中单独聚焦于文学,即电影是目的,文学降格为众多手段中的一种,为增强电影的艺术表现力而服务。
事实上,在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电影的文学性”更多化为对“电影的文学价值”的思考与讨论,早期的“电影”概念还衍生出了“电影文学”“文学电影”等一系列跨媒介交叉概念。相比之下,若江俊三等人直接论述“电影的文学性”,或讨论电影内部文学相关要素的文章只是部分案例。“文学性”议题在提法上的替换,下位概念的增殖,代表着“电影”概念建构在语用层面的策略转换,即试图争取与“文学”平等的话语权。1930年,作家李同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称,“电影艺术所包含的有文学光学美术三种,而以文学上的价值为最注重”[40]10。“左联”作家、翻译家韩侍桁则在《论文学电影》一文中称“所有的较好的电影片子,都一定地是含有文学的艺味”[41]11。人们在谈论电影时提到的“文学价值”“文学意味/艺味”往往带有“电影的”作为前置限制性定语,以期“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的文学价值”等一系列语汇能够将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性锁定在“电影”内部,在语用层面划分出明确的区别和领属关系。
此外,在广阔的文学语义场当中,考察“电影”“文学”“文学性”“电影的文学性”等语汇时还可以发现一种观点:“电影”与“文学”具有天然的亲缘性。背后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将“电影”概念提升至与“文学”平起平坐的地位。大卫·波德维尔认为,语义场结构分为丛聚、对组、比例系列和阶层四种类型,其中“丛聚”类语义场内部各条项的语义相互重叠,可能形成某种“家族相似”关系[42]141。如若在跨媒介的亲缘性前提下,将“电影的文学性”视为语言游戏,那么相较于代际特征,在某些语境中,文学与电影的关系更趋近于“家族相似”[43]38,“除了些形式上及技术上的差别之外,文学和影片在组织法上简直可称为兄弟”[30]117。“电影的文学性”提法,集中体现了早期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对电影在概念范畴划分上的某种妥协。既然将电影划为文学的附庸阻碍重重,就以另一种方式在“电影”概念话语场域内部取得专属文学的地位,目标是实现双重意义上的规训——表面上看,如果承认“电影”中存在“文学性”,那么将“文学”概念泛化的同时,也暗示电影是文学的某种衍生物;深层次看,先承认二者具备高度的亲缘性,并提出这种亲缘性集中表现为大家公认的、文学所独有的特征——“文学性”,实际上目的依旧是强调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代际差异。
“电影的文学性”作为电影与文学的跨媒介产物,抽象层面涉及“电影”与“文学”两个看似明确、实则模糊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可称得上是一个居间性概念[44]15-23,为“电影”和“文学”提供了概念角力的流动性场域。参考胡塞尔的思路,或许可以将穿梭于电影和文学之间的所谓“文学性”看作一种模糊的或图式性的本质,作为一种可感的文学作品和概念性文学本质的中介来思考和讨论。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观点更具说服力,借助他们对“圆形的”(Round)相关论述,“文学性”可以被视为“情状阈限”(非绘画的、非音乐的)和“过程-界限”(变得具有文学性)的某种存在,它贯穿着可感的文学作品和技术媒介(电影)。正如他们所说,文学性在此前提之下才能成为某种“中介”,这种中介是“自主的,首先将自身拓展于事物和思想之间,从而在思想和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联,一种模糊的同一性”[45]588-589。“电影的文学性”作为一种跨媒介的“中介”,首先将自身拓展于具备文学特征的电影作品与电影理论之间,在理论话语的碰撞中,使这一类电影作品及理论表露出某些专属于文学的痕迹,从而被批评家、理论家们识别、捕捉、研究,最终营造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话语空间。
不过,同样是在早期中国电影理论话语场域之中,在“文学”与“电影”的概念角力之中,在“电影的文学性”迷思中,一些人感知到必须寻找某些专属于电影的特质,并致力于找寻一条独立、直接、深刻的艺术本体论路径,希望将电影艺术的特殊性与文学带来的影响一起叠合在“电影”概念之上。这种尝试,使得“电影”在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46]269-280之间的张力中变为一个不断生成的概念。
三、“文学性”与“电影性”之辩
徘徊在历史的横截面上,当一些人讨论“文学”与“电影”,一些人讨论弥散于电影和文学之间的“文学性”时,或许透过“电影的文学性”,还有人得以窥见“文学性”与“电影性”的多次“紧急会面”。“电影”的多重语义交叠在一个、甚至多个语词之上,同一时期的不同语义都附着在“电影”语义场内部的语词上,被人们随意而广泛地运用。由于层出不穷的下位概念与一般语词尚未得到有序组织,人们的讨论总是在不断设定新的语境以规范用法。在1920—1930年代,“电影”概念的使用总体上是面向秩序的,但其目标似乎也在于废除秩序,即抛弃一切、反叛一切来寻找并建立“电影性”。
1930年代,部分文人、影人试图证明“电影是活的文学”(侯曜),讨论“电影的文学性”(若江俊三),亦有人认为电影与文学是“两种艺术”[47]792。换言之,这些人既不愿将电影作为文学体裁进行探讨,亦避免在电影内部讨论“文学性”或“文学价值”,他们站在电影艺术内部,表现出某种将“文学性”从“电影”概念中抹去的意图。例如,新月派诗人、后来的左翼翻译家邵洵美就认为,不该讨论文学改编电影的忠实性问题,还举例说文学的题材用于绘画时,“批评家是应当用看画的眼光来看了”,改编应当作的工作是“表现”,并表示痛恨批评家对各种艺术“自身价值”的忽略[47]。李长之也称“电影是独立的一种艺术”[39],即便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也“只能说是影片,而不是算是文学作品”[39]。王平陵则谨慎地探索语义扩充的可能性,将电影划分为一种艺术门类,提出“指示人生,渴求真理”的电影是“文学的电影”[37]8-9。此时,“文学的”作为“文学性”的另一重表达,既是文学某种模糊的标记物,又是独立于“电影”本身特质(电影性)之外的艺术价值判断标准。这一提法,在不同作者有关同一问题的论述,以及同一作者有关不同问题的论述中交叠,体现出“同时的不同时性”。科塞雷克为《历史基本概念》撰写的“历史”条目说,“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亦即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集于一个概念”[7]163,这也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现今,只是表面上如此,今天能够看到他们,但他们还没有同其他人一样生活。一个人的肉身,尤其是阶级属性在哪里,就有其自己的时代”[7]164。同一时期,一些报刊的作者在电影与文学的反复比较中,试图厘清专属于电影的艺术根性,关注的正是比较中发现的各种差异。李长之在论述电影改编时,就十分关注电影的与文学作为媒介的区别:“电影是直接由视觉召起意象,而文学作品却须先经过心的活动,由感觉通过了经验总和的心,然后才间接的形成意象”,是“表达媒介的功用不同”[39]。在对这些报刊的共时性消费前提下,针对同一概念(电影)的分析,不同阶级属性的读者、作者透过文字和观点的碰撞生成羁绊,是“同时的不同时性”。而无论是早期“电影”概念脱胎前后,还是到1980年代“电影的文学性”论争,甚至到今天,电影史研究几乎一以贯之地重视异质性,促使着“电影”概念不断更新内涵、拓展边界,这是“不同时的同时性”。
“电影性”的论述,初步展现了彻底将“文学性”从电影特质中剥离的意图。徐公美在1938年出版的《电影艺术论》第七章“电影艺术的特性”中,首次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电影性”。他提到当时人们已经非常普遍地运用“文学性”“戏剧性”“电影性”等语汇,甚至已有泛滥之势,如果不规定电影的特殊性、独立性,那人们就“不能明白什么叫做电影,又什么叫做‘电影性’或‘电影的’。”[48]53-55洪深在《论电影和文学》一文中也说,电影与文学的交流使得电影“失掉了它的特殊性”,“文学假使依着文学的表现而成为艺术,那么电影是必然依着电影的表现而成为艺术的”,“电影是集团的群众艺术”[23]262-265。
事实上,“电影性”对文学的排斥,源于晚清以降被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线性史观,亦浸染在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反叛”氛围中。自严复的《天演论》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演化”的基本心态是“求变”,“求变”是“追求进步”,于是“演化”在逻辑意义上成为了“进步”的同义词[49]621,那么“继着文学而产生的电影”[29],自然也在“演化”规律中,依着“进步”的要求走向反叛。而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环境又极度复杂,“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个自相矛盾”[50]72-73,应当“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50]73,以脱离在新旧之间的彷徨。这些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艺理论领域,将电影推向与成熟艺术决裂的境地。若要使电影成为一门独立艺术,除了需要从本体论维度定义其自律性,还需要从根本上否定、推翻文学、戏剧甚至绘画、音乐对电影的影响。徐公美在论述“电影性的发展”时,盛赞美国电影能“完全脱离了文学或戏剧艺术的影响,而以‘电影的特殊动性’为根据,开拓了‘电影性’的新的境地了”[48]57。理论家们“终能把陷在文学或戏剧的奴隶的处境中的电影,救出于正当的艺术的进步上了”[48]58。尽管“奴隶”一词略显激进,足见作者对电影艺术的怜爱。若江俊三也认同这一观点,他在《电影的文学性》系列文章末尾总结道:“伟大的作品是排除了文学气味的。……于是成为‘文艺电影’特殊的种类,便不得不被‘艺术电影’消灭了。”[28]他将“文艺电影”与“艺术电影”概念分离,事实上也是将“电影”概念进一步与“文学”“文学性”剥离,而他所说的“消灭”,则淋漓尽致体现了剥离行为之下潜藏的反叛性意图。这一意图在刘呐鸥的论述中占据突出位置,《影片艺术论》曾专门讨论电影中的文学要素,虽未提及“电影性”一词,却提出一种专属于电影的特性——“影戏的”(Cinegraphique):“这名辞之内是包含有反文学的、反演剧的、反绘画的意思的”[30]115,所谓的“反”,即通过电影与其他门类艺术的异质性来设置阈限,以达到框定“电影”概念外延的目的。他还将“照相的”(Photographique)视为“影戏的”前阶段,认为“不可一味把文学搬到银幕上来”[30]116-117,因为“文学要素的直接的搬运是‘杀影戏的’的”[30]116-117,这无疑是在反对纯粹的“文学性”以字幕形式进入影像之间。不过刘呐鸥并没有在“反叛”的论述中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不完全认同欧洲盛行的“纯电影”[30]115。在他看来,剧情才是电影的“生命素”[30]115。刘呐鸥从“电影”概念内部出发对文学要素的讨论,无意间发掘出“电影”概念的某种自反性,它并非文学本身,甚至拒绝纯然的“文学性”的干涉,却又紧抓着一些被指认为“文学”的要素,同其他门类艺术的要素一起,叠合成为“电影性”特征的一员。
在早期中国电影理论话语的场域内部,有人试图以“文学”统摄“电影”,有人试图以“电影性”反抗“文学性”,还有人译介海外电影理论,试图为电影发展成独立艺术门类而开辟一条道路。语用层面的努力无疑是珍贵的,概念的建构及其变迁所体现的立场、语境等操控意义生成的因素则更为关键。当“电影”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电影本身如果能突出自律性,发展成为一门全然独立的艺术,除却纯粹的艺术理论价值驱动,工具价值或许更加重要,背后亦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内驱力。
四、结 语
回到当下,早期中国电影理论中的关键概念研究,对中国电影史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在纷繁的门类艺术比较及“跨媒介”研究的热潮中,电影与文学百年纠缠的关系问题,是否能够以二者的概念交叠为切口,一窥其究竟?以往学界谈论媒介间的“跨越”时,无疑设定了一个先在条件,即首要关注媒介间的差异性而非共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差异性的关注和建构往往是话语的,而非事实的。这种观念指向的,正是复杂历史话语场域中涌动的社会与文化思潮。回溯“电影”概念的形成过程,并非要建立某种理性的连续的历史,而是希望“对聚合和完成的主题提出疑问”[51]9。对当时人们言论与观念的整理、分析,亦非要堆积出由陌生史料组成的思想史,“关键是把握概念网络中的大概念、下属概念、对立概念等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以揭示概念的内在语义结构”[7]139。“电影”与其他概念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史并非循着时间之河顺流而下的线性史,“已经”“尚未”“依然”意义上的时间[7]167或并列,或前后相连,或交替,或相互交错[51]9。因为“概念的历史不是一砖一石构造起来的建筑”[51]70,对该问题的反思,意味着当下的电影研究以及电影史书写应当“在断裂、偶然、异质、离散、停滞和失衡等电影状态中,寻求更加丰富有趣的过去并展现复杂影史的多样性”[52]3-11。
作为概念的“电影”,无疑是动态的、开放的,它在每一历史时期的形态都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信息。“电影”面向过去,面向当下,更面向未来,在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早期中国“电影”概念与其他门类艺术所产生的丰富而复杂的共时性互动,正是科塞雷克笔下“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跨越媒介疆界所散发的理论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