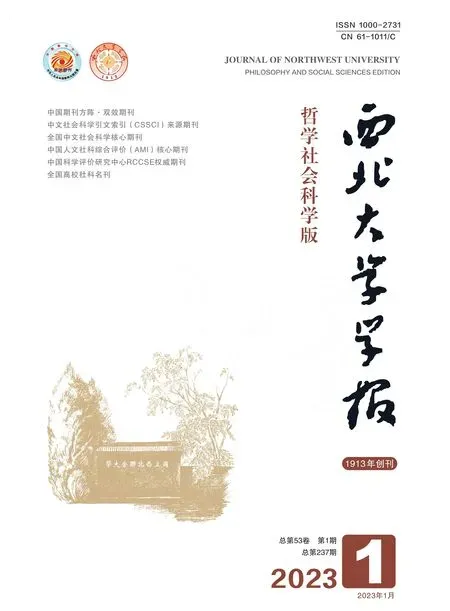家园、英雄与节日世界
程秋君,陆毅鸣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2.罗马第二大学 人文学院,意大利 罗马 00133)
家园、英雄与节日世界是深刻的关联在一起的主题。和平盛世,当人们安身家园,沉浸在节日庆典的气氛时,常常会吟诵为创建家园和守护家园的英雄而创作的史诗。然而,哲学家园学中,英雄是缺席的。专门探讨英雄本质的哲学,极少提及英雄诞生并成长于其中,因爱之故获得创造精神的家园。没有英雄建造和守护的家园的文明,是行之不远且缺乏安全感的文明。回避英雄与家园大地根脉相通的骨肉情结所思考的英雄的本质,经不起在历史与逻辑统一前提下的检验。家园中工作世界与节日世界的差异与互动下的平衡,为我们从英雄创造性的活动,英雄的业绩,英雄的形象溯源英雄的本质,开启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解释路径。
一、作为家园两重生活方式的节日世界和工作世界
家园是生活世界的中心。家园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与世界联系的方式,这两种方式总是同步发生,并在它们动态的相互作用中打开了真正的人类世界:一个是工作世界,一个是节日世界[1]88。博尔诺(Otto Friedrich Bollnow)曾写道:“人如果不想无助地被时间的洪流卷走,就需要一个牢固的居所。”[2]33这实际上隐含着人与世界两种联系方式本质的差异,以及人在家园大地上建立“牢固的居所”来平衡工作世界和节日世界的必然性。节日的世界肇始于人定居的时刻,发生在家园“牢固的居所”,这是生而为人就能亲身经验到的至为亲熟和先天信任的世界。居所抵御风险,是安全的、保护的领域。工作的世界在“牢固的居所”之外,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乃人为基本生存之故而不得不从事其职业的场所。在工作世界人身不由己,被计量的时间洪流裹挟前行。以居所为中心的节日强化了家园的友好气氛,克制住工作领域中对未知世界开拓性进攻性的生活节奏。对于投身家园建设,为家园献身的人而言,所谓完整的生活状态,就是在工作世界与节日世界之间巧妙地切换身份,并取得这两个领域最佳的动态平衡状态。
伽达默尔(Hans-Geora Gadamer)曾指出,节日庆典“首要的、活生生的本质是创造性,并使人提升到存在的不同境界”[3]548。这一关于节日本质的见解,为我们与之相对的本质迥异的工作世界,从时间、空间、人的内在品质的培养、共同交往方式的塑造,以及创造性活动的特性等方面提供了极具价值比较的视域。
重复性、循环可逆是节日时间的重要特征,而工作的时间则以据连续性的均匀的线性流逝特征计算。节日不只是日历上重复的日期。根据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考察,节日时间是对神圣创世时间定期的再现实化,其根源可追溯到神话的时间,亦即“元初的时间”[4]34。节日庆典或纪念活动可谓再创造的意义上对“元初的时间”的重复。中国传统视“过年”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无疑是对节日循环的和可逆性“重生”特性的精要诠释。这是以传统为基的革故鼎新的世界重塑过程。它承载着人作为完整生命的共同体验。节日庆祝把处于工作世界的人,从单调无聊的“时间的洪流”中拯救出来,共同参与到节日仪式当中,共享同一时刻,共享相同的习俗、饮食、服饰,加入到与过去创造性事件交汇的情境,人们聚集在自己建造的居所,置身传统,憧憬未来,讲述关联着“我们”起源的历史和命运的故事。在这与原始创生性事件交遇的时-空,以父母之爱为原型的生命孕育、出生、代际相续、与他者共生和永续发展,传递出令人敬畏的力量。再次,人因“重返起源“而如同“获得新生命”,“正像他出生的那一刻一样”[4]40。而当人走向工作的世界,就得遵循线性时间秩序下的工作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不能要求居家状态下享受的权利,人要持续地对抗身体中的惰性,还要谨慎地应对节日世界的亲密性向工作领域入侵。时钟指针的节奏指挥着身体的动作,人被迫按照既定的操作规程,完成一个接着一个的任务,克服不可预期的障碍,紧随着不可逆的时间之矢一往直前。生活世界如果被无休止的工作时日占据,就会失去节日世界中连接自身传统与未来的生命体验,时常面对作为族类整体的生命与工作之人之间的分裂而焦虑重重。
节日空间依托于家园中安身的居所,而工作的范围独立于节日世界,工作空间只是机械性的临时的容身的之所。节日发生在“有人的居住的完整的世界”最初始的建造,就是把一个混沌的地方,变成有秩序的宇宙,并以此为中心,构建一个无边无际的自然,让人开始有在家的感觉。居所作为家园本质的核心,“在其内部保持着节日世界和工作世界之间创造性的张力”[5]222。每当节日降临,日常繁忙的工作生活要为节日庆典腾出必要的位置,劳动者放下手头冷漠的物质要素回归居所,得到解放和休息,被日常工作磨损的身心、被消耗殆尽的能量在由爱支撑起的空间中得以修复。节日把人们团聚在共同的空间,人们庆祝节日,说着节日语言,停止抱怨命运的不公,停止工作场合各式各样的命令,在相互问候、感恩和祝福的语境,守护并培养互爱与团结的品质,享受安然无恙的时刻。而工作发生在居所之外。要进入这个世界,就得离开家人和朋友的圈子,用智慧的力量对付物质结构或要素没有灵魂的本性和人情的淡漠。工作所必需的先天分工把人拆分成独立的单元,分布在荒野,在天际,在办公机构、实验室、心理咨询室、公寓、体育馆、机器车间、公路、公众图书馆、学校、边境等等。在这些冰冷的物质空间,人的内心和身体不受保护,还要经受与自然或敌对力量进行斗争时的耗损。如若家园衰落,工作世界仅为制造产品而迷失方向,工作之人即使有工作场所的公共建筑护体,其精神也会因没有家园的吸引,没有来自家园的问候、感恩和欢迎而被抛荒野,漫无目的地流浪。
节日庆典仪式中,人的内在精神与创世的神话和人类自我创造的历史重复性的会聚,其内在品质也在参与节日仪式中自然养成,而工作的世界依赖理性筹划,不断练就精于计算的智力,轻慢后天的道德培养。节日世界以家园为中心,建立起人与天地,与原始创造者,与后世继承者生命整体性的关系。人在家园的土地上耕耘、播种、照料,使沉睡的自然苏醒,并以果实和美酒馈赠劳作的人们。家园是培育和保护的领域。家园的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使万物各安其所,免受伤害。而在工作领域,正如莫兰(Edgar Morin)精辟地指出“四个动力引擎”,即科学、技术、经济和营利,“每一个都带有自身根本性的伦理缺陷:科学排除了一切价值判断及科学工作者的主体良知,患有严重的盲症;技术是纯粹工具性的,傲慢地凌驾于精神和情感之上;经济用冰冷的计算将人类互助打入冷宫;营利则贻害所有领域,包括教育、政治、生物及基因研究领域”[6]15。“四个动力引擎”带动人全部的智力都服务于打开对象的本质,以便伺机为我所用。在这里,功利主义心态盛行,忽视道德培育,导致反噬理性和智力成就的后果,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没有持久的位置。如果不是以家园为根基,没有对家园的牵挂,人在工作领域的所有努力,所有创造都是空虚的、乏味的和无意义的。家园节日的圣辉,照亮爱与所爱的方向。自然的赠予与人类的感恩,加深了人“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亲密无间的家园意识。家园意识和节日的光晕下,劳动的双手诗化为抚爱的双手,摆脱了头脑精妙计算和一系列对物的操纵手段,人格力量受到广泛认可,并被真诚培养。如此一来,人以栖居者的存在方式实现人成为人的具体的、现实的本质。
“节日关注的不只是智力,而是整个人,牵连的是整个共同体。”[7]296节日的世界是培养共同体意识的场所。节日是对所有的人而言的,“假如有什么东西同所有的节日经验紧密相联的话,那就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节日就是共同性……”[8]63这里“共同性”不同于无差异的同一性,而是把所有的个体“聚拢”起来。节日的空间还敞开了代代人精神的传承与生命交替的场所,同时还开放了对自我与他人、凡人与诸神、人类与生物界、工作日与节日等差异性容受与接纳的场域。公共节日就是要把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使其具有“形同家人的气息”[8]296。“好客是节日王国的核心和灵魂。”[9]33热情好客是以欢迎、问候、祝福和感恩的姿态开始的。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性的时机,一个引发言谈的时机,以赞美、谈话、理解与相互认同的态度为起点,为建立精神联盟做好准备。在节日领域,人类创造物不再只作为世俗的“占用和使用”的冰冷物品,而是作为献祭的作品蒙上神圣光环。人与他者的契约,不再是工作世界那种服从效益的制度和规则,而是彼此之间以欢迎的、礼节性的肢体动作向对方显现自己,召示以团结为目的对话。工作世界则紧盯着生产效益,其重心在于物质制造,为了经济利益之故,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根据算法中的最优化数值被精致地安排,其结果是“拆散人们”[8]66。工作世界的交往,必须倚重于知性逻辑建立起来的刚性规则。这种交往秩序,存在先天的伦理缺陷。人创造的价值体现在用知识工具与自然力量展开斗争,强迫自然为人类的存在做出让步。在知识的视野下,所有的事物和所有的生命体都被降格为操纵物或操作工具。每个人都因明确的分工被安装上特定职能,人与人之间以职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工人、农民等身份交往。如果没有由家园奠基的爱、问候、友谊和信仰充实工作的意义,那些被工具化并以职业身份定性的人,就会被简化为社会机器上“零件”,蜕变为没有自主性灵魂的、身陷威权规则下的“工具”,没有任何安身立命的感觉。
节日世界引导诗艺创作,而工作的世界则是诗艺生活隐没的地带。节日总是围绕着庆典仪式进行。庆典仪式的内容,则围绕着人们思考神圣的本质、感恩自然慷慨所赐得到充实和丰富。它以宗教祭祀、诗歌、戏剧、艺术创作、舞蹈表演等具体形式,赞美天空与大地、神灵与祖先、英雄与凡人之圣德;它以公共的和私人场所的装饰、工作领域所获的财富,展示人不为专事劳作的日子束缚的自在状态。节日的气氛中,人们的身体动作收敛了工作状态下朝向确定目标的奋力与搏击、冷静与专注,而变得舒适自在、闲雅从容。而工作的世界,要求以逻辑前提清晰地表达科学揭示的自然规律,以算法为基础实施精确的技术性操作,以陈述句精准地表达理性的意图,以规范化的动作应和事态发展的内在逻辑,“所有的事物和生命都只是需要塑造的对象和需要使用的工具。做工的人意味着永远不能以自己的身份出现,永远不能有自己的声音、名字,甚至连自己的外表都没有”[9]224。凡此种种不无表明,诗艺生活必须隐藏在工作环节看不见的地带,悄然地维护着家园生活的意义。
众所周知,家园的建设、安全和富有是靠工作世界的劳作支撑起来的。不能没有工作的世界。没有工作的世界,以居所为核心的家园大地会至今沉睡在古老的荒野,居所就失去了赖以存在和繁荣兴盛的物质基础。正是人类工作创造的无数奇迹点亮了文明之火,让我们定居的地球化身为与我们血肉相连家园。工艺的奇迹、科学的奇迹、医学的奇迹、技术的奇迹、工程的奇迹……当这些奇迹服务于人类的福祉,使家宅与大地的连接不受岁月的侵蚀,使家抵挡危险的墙壁筑得坚不可摧,使人跨出家的门槛与友邻相望,聚拢在节日世界的人才会有深度的幸福感。尽管如此,必须慎记,工作世界的秩序不能构成理解世界的基础。现代社会有些文化实验,试图以娱乐和休闲排挤节日仪式,以消费的狂欢销蚀节日固有的神圣性,以短期的效益牺牲人类孜孜以求的善美。这种行为企图将人的一切潜能都锁定在工作世界之内。当人的身心被无休止的工作捆缚,无力面对养育、保护自己的居所和自己本应反哺的土地报以感恩和微笑的时候,就是节日的意义被遗忘的时候。人蜕变为“工作之兽”,丧失了筑建家园的使命感和定居大地的基本意义。
一个宜居的世界,一定是节日与工作齐头并重的双重世界。只有立足家园的工作之人,才有责任和能力把家门外的世界和远方世界与家庭成员的内部世界连在一起,才能够把本地人和异乡人、居住者和旅行者、人和神圣者邀请到一个共同的世界里,减弱歧见及隔阂,敞开彼此间的内在灵魂,抵达精神层面沟通。以家门为界的节日世界和工作世界的划分,强化了人生活在两个领域的差异性,以及两个世界相互依赖的必然性。节日世界对人是友好的,其“共在”的事实与“共享”的生活向工作世界溢出,使工作的生活之根深系家园。工作向域外世界开拓,创造出的科技的力量,向外而生提升了人的生活品质,向内而生训练了人反思自身命运的能力。
二、英雄与家园
无论出身于什么血统的人,都首先诞生在一个居所里。这个居所可理解为父母之怀,也可理解为带由屋顶和四壁围合起来的房子[10]1。父母的怀抱外或房屋的门前,必有通向他人、邻里、庄稼地以及由远方世界所规定的道路。人身处其中的居所,居所立身其中的家园大地,是人的生命诞生的地方,也是人的全部创造性得以开展的地方,“家园揭示了人类居住的终极基础”[11]4。正是这一点,家园成为神圣者、英雄和凡人聚集及奔走不同方向的出发之地,也正是这一点,英雄的肉身和精神世界与家园大地发生最深刻的连结,英雄奔赴工作世界的未知之地并最终返回家园的意义彰显。那些试图厘定英雄本质的人们,忽视了与英雄生命密不可分的家园,而声讨工作世界造就的现代科学技术伤害了家园原初本质的人们,因忘记了观照英雄存在,而宁愿把人类未来的命运交付给神秘的上帝,也不曾提起现代世界英雄救赎的价值。
探讨英雄的本质,经历了神话中英雄离家到哲学中英雄无家的理路。世界上伟大的神话,都记载有英雄响应家乡召唤,完成冒险之旅,返回安全的居住地,受到节日庆典般盛大的欢迎仪式场景。从中不难读出,英雄类神类人,植根家园。家是安全的庇护所,是英雄的出发地和归属地,而外部世界与人性所要渴望的满足感是相抵触的。但英雄担负着救赎的使命,必须有赴死的决心和不向艰难妥协的意志,到未知的领域探索和冒险。英雄有神的血统,也有人间之爱,渴望安宁,渴望享有幸福生活,对家园的眷恋深入脊髓。英雄旅途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凡人体验不到的悲剧情结。而生息于家园的众人,受到英雄的保护。当英雄带着胜利的喜悦,带着外部世界的礼物、异域见闻、丰富的知识返回家乡,定会享受到非凡的节日盛典般的礼遇。总之,古典英雄有凡人基因,血统高贵,禀赋超凡,不计生死荣辱,对族类命运有与生俱在的责任感,并经得起生死成败的考验。英雄创造性的价值只有到成年阶段,且在家乡之外的未知领域才可能实现。英雄的目标与人们对美好世界的期冀一致,其本质特征常被从现实生活领域抽离出来,被当作理想的范型。柏拉图《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与青年对话显示,为了向未来成长为城邦的护卫者的青年树立英雄典范,柏拉图保留了古典神话中英雄的勇敢、正义、忠诚、节制、有血性、不惧死、不享乐、不庸俗等优良的品性,而其作为凡人部分的七情六欲和与身俱存的家园感都被看做消极的因素删除。
无独有偶,蒙田(Montaigne,MD)也曾特别强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人在自己家里,还有在自己家乡做得成先知”[12]19。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在其论著《历史哲学》中表明,英雄乃是诞生于世界历史中的个体,“宇宙天才的实业家”。英雄本己的生活世界是无理性的、野蛮的,因而是混乱的。他们牺牲自己的幸福,不为追求名誉或名声,而使自己的本性、品格、欲望和激情,服务于实现世界历史的本质。“英雄是为世界存在的”“为了实在存在,为了真理存在”[13]120。尼采式的英雄,则是不依赖于任何神圣秩序的、个人主义的、 唯意志主义的超人。从半神半人的英雄离家成就不朽的事业,到英雄无家,超离现实的生活世界,其原因可追溯到自苏格拉底以降,西方哲学中的家,不是人诞生和成长于兹,由此地出发,并最终回归于此处的安身立命之家,而是有意屏蔽了人间烟火气息的“思想的世界”。
仅把思想作为人的永恒的“家”[14]78,导致思想本身游走于人世间的家园之外,也同时导致从哲学上究问英雄本质与家园主题的疏离。在深刻反思和批判现代科技造成人类家园感丧失的哲学文献中,现实生活世界英雄创造和救赎的历史价值及现实价值都令人遗憾地缺席。所谓“家园感”主要涉及四个层面,即:①自己的房子或类似家的环境;②自己的身体;③心理社会环境;④精神层面,特别是人类存在的起源。第一种解释是指一个人生死存亡的物质场所,第二种解释是指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第三种解释是指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第四种解释是诞生与死亡的过程。这四个层面贯穿人类“在家”、“思家”、“回家”辩证运动之中。家园感的内涵的四个层面,人与家园辩证法的动态逻辑,离不开英雄史诗最初的建构。但是无论是18世纪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极力推崇未经现代文明染指的原始的“自然状态”,还是20世纪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指出“接受天空,期待诸神,护送终有一死者——这四重保护乃是栖居的素朴本质”[15]71,其深刻哲思的宽度、广度和高度都未向我们透露有关英雄的哲思。从海德格尔着手时间、空间、建筑、语言、艺术探索存在之本真的努力,不难看出,他所要回归的家园,在被现代技术驱动下的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只存在于古典希腊的思想世界。另一位详尽讨论家园的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leel Levinas),在其代表作《总体与无限》中强调家的女性特征,强调家是受欢迎的地方,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地方,是一个流浪者找到可以避难的地方。就此“在家”是人类的基本状态,人活动的起点,以及人走向外部世界必要的条件[16]64。
尽管海德格尔的思想之家和列维纳斯的现实之家优先性地位没有为安置英雄留出位置,但他们都没有忘记,人类从来都不满足于家园的自足状态。居安思危是人生存的常态。安居在家时必然要迎候外部世界的他者,必然要思考如何应对无家可归状态下的生存考验。筑造起来的居所的物质架构,其墙壁、窗户、门扉,以及联通远方道路的门槛,既是家宅的阈限,也是沟通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标志;家宅中具有精神中心意义的炉灶和餐桌,连接着家园的土地和广袤的远方世界;家园的运动与静止的辩证法,对应着内部世界的和谐与安宁和外部世界的争执与冲突。家宅宁静的时刻,是在诞生与死亡、醒与睡、旅行与回家、劳作与休息、节日与工作的循环而叠加在生命的周期之上的。人穿梭在家宅内外,在家园大地上采集、驯化、养育、制作、筑造、教授,洞悉灵魂,培养友谊,礼物交换,发展对话,建构秩序,保护各种类型的人类合作事业,奠定文明基石;人或者沿着家宅门前的道路奔赴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领域,其行动包含着创造、征服、谋取、保卫,把熟知的秩序带向混沌之地,驯服荒野,以及谋求真理等动机和勇气。因此,家园的安宁与和平,是与外部工作世界的潜在危机和激烈斗争相对而言的。为躲避外部世界潜伏的危险,足不出户,精神生命就会萎缩。安全和危险同属人类的处境,人必须穿行两个世界,才能完成人作为一个完整生命的本质,才能作为创造者在家园大地上留下“诸多劳苦功绩”。海德格尔指出,“人的时代”为灵魂加载上“创造者”或“天才”外表,致使灵魂失去其本根,因为“一切‘创造者’必定在其产生的基础中有其家园。要不它何以能够生长而成其伟大。”[17]109一切伟大的创造者,一定出自以居所坚如磐石般地扎根于其中的家园。家园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中心与远方、运动与静止的辩证运动,激活了智力、道德、情感生活同源的创造力,共同铸就了以友善和团结为精神内核的节日世界。另一个是来自不满足居所短暂的安宁,在倾听和理解人类欲求的本质后,毅然去陌生领域冒险,涉身险地而被激发出非凡的创造意识的人。无论是在家乡世界还是工作在远方未知的世界,只要靠智慧和勇气,从事创造性的事业,征服死亡,终止杀戮,巩固天地间的睦邻之爱,使人完全按照人类的方式栖居天地之间,就不失为神圣的、勇敢的品质驻入血肉之躯的智者和勇者。无疑,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把现实的家园引入哲学,为重新发现英雄作为现实的人与家园整体的归属关系觅得一丝踪迹。
梁启超言,“英雄者,人间世之造物主也”[18]340。哪些人堪称“人间世的造物主”呢?在梁启超看来,被人类历史推出的“二三之英雄”,只不过立于表面,而未真正深入英雄之内在本质。真正“造英雄运动”的英雄,则是“隐于世界中之农夫、职工、役人、商贾、兵卒、小学教师、翁、寡妇、孤儿等,恒河沙数之无名英雄也”[18]363。无名英雄才真正是“国之生命也,世之光也,平和之泉也,世界之大恩人也”,因此是“真英雄”[18]364。正所谓“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19]。古往今来,天下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与家园的事业血肉筋骨相连,穿梭于节日的世界和工作的世界,创造着看似平凡,却虚化自我,造福人类,拯救世界,推进历史的伟业。而神话诗学和追求本质的哲学中,那些出走家园,远离人间烟火的“二三之英雄”,无非是有幸被“隐于世界中”的“真英雄”推动的时势造就出来的而已。无视或遗忘家园大地在节日的世界和工作的世界的隐形的英雄,只能无奈无助且悲哀地流连于家园挽歌,惧怕科学探索中的不确定性,惧怕人间世的技术革新,惧怕被工作世界带动的历史前进的步伐甩下不知所措的软弱灵魂,乞求彼岸神明救赎。
自古以来流传着一个俗常的生活道理:家有内鬼,外有强敌。尽管被描述为“庇护所”“避风港”,但不可否认,现实的家不失为脆弱的存在,而不是抗拒一切风险的堡垒,也不是盛产道德信条的圣地。不同世代对家风、家教、家德不遗余力的维护,还有从姓氏、姓名及一切能证明血统的文化符号竭力巩固家族的生命整体性,不就反向地证明了这一点吗?人们在乎家,因为从最直观的经验层面看,家是人出生的地方,也是人无论离家多远,都心中挂念并要返回之所在。以家为依托的家园的乌托邦,源自心灵苦痛时的期翼。人类定居是从驯服荒蛮,在混沌中建构秩序开始的。据考,“Kosmos”原意与主人“整理”家宅同源同义[20]。通过整理,驯服一块土地,使人定居;通过劳动,获享大地的赠礼,使人产生对一个地方的依恋;通过交往,区分并连接起本土人与异乡人,使人意识到真诚、正义和团结的可贵。为了使家真的变成“避风港”,为了能真正在家中无所忧虑地享受“白日梦”,大多数的人们必须暴露在家园之外,让自己的部分生命绑定在工作世界种种戒律的链条之上,承受工作的世界带来身心异化的之殇。在工作的世界,只有保留对经历艰苦才建设起的家的深沉眷恋,珍惜人际间的爱和友情,才会理性思考人的生命的本质和全部生活的意义,才不致沦为没有家园感的精神贫困的“工作之兽”。节日的欢庆或纪念活动强行克服连续的劳绩累累工作,其精髓应归于使人作为有思想的生命,从工作领域暂短撤退,切断工作领域短视计的算性造成人在时间、空间、共同交往、内在精神养成等方面的缺失状态,回归世界创生之源,直观命运整体,获致工作世界和节日世界有机的动态的平衡之道。
把英雄的纯粹本质或历史精神放在优先地位,就会脱离整全的家园虚构抽象的英雄主义。如果从家园中人与世界联系的两种生活方式和建设家园美好生活的角度界定英雄品质,那么英雄无处不在。英雄既在工作世界坚韧劳作,又在生活世界之源,享受节日庆祝和礼赞的有思想有行动的现实的劳作之人,而不是触摸历史本质无谓的牺牲自我幸福的个体,也不再是实现个人意志的“超人”。此岸世界的英雄,内含既为自己,也为他人未来的幸福和自由得到保障,而在顺应历史进程中进行富有成效的创造的品质。英雄出自家园,归属家园,作为生者而思考,为爱的生命和爱的土地宽厚而坚韧劳作,忠诚于让世界好好存在的事业。英雄们有信仰,不冲动,不颓废,不背信弃义,心中装着尚未到来也可能是遥遥无期的胜利的梦想。
三、从家园的两重生活方式追寻英雄的本质
人类思想在崇尚美好生活,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除了我们熟知的对俗常生活冷静审视和批判性反思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发展出的一种赞美的习惯。这种赞美的艺术在节日庆典中发扬光大。人们普遍赞赏“公认为光荣的事情”,赞颂“神和英雄、爱情和祖国、战争与和平、正义与智慧等等”[21]20。尽管致力于赞美的优良习惯流传已久,但不可否认,并不是所有的荣耀都能够汇入唱诵英雄的章句。正如在英雄史诗中看到的那样,英雄都是特定形式的主体,出身高贵,精神超凡脱俗,英雄的事业要在出离家园之外的荒野才可实现,如此一来,诸多家园内外现实生活中一般的创造群体成为与赞颂辞无关紧要的影子一样的存在,甚至大多数受权力支配的劳作被看作低贱的生活方式,根本登不上礼赞的大雅之堂。这种沉默不语,融汇于行动力量中的智慧、勇气和对家园生命整体忠诚的品质,长期以来被掩藏在历史的尘埃底下。
现实生活世界存在两种本质不同的财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这两种财富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的本质体现为“占有”“使用”和“分配”,这类财富是有限的,但人人对之有所需求,如果拿来共享和使用,那么占有者的财富数量就会减少。为了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就需要进行分配,“现代国家管理的本质就在于努力作出公平的分配”。而精神财富的本质在于它“不可能属于任何个人的”[21]39,也就是说,精神财富属于所有的人,其本质就是“共享”,并在“共享”的过程中会随着解释学意义的释放而无限增益。从根本上讲,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不可能为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独享。因为这两种财富的创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为了人能够更好地保护可定居的家园大地,过上美好生活,实现此岸世界的幸福。
选择一个地方定居,就同时启动了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种活动,这两种活动在工作世界和节日世界的对峙与同一中同步展开。驯化、整饬、修饰混沌之地,使其变成有秩序的、适合人类居住、保护人的内在性的家,既是物质时空秩序的重塑过程,同时也是精神秩序的建构过程,“房屋建造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一种创造世界和维持世界的活动”[2]137。在伊利亚德看来,这一物质性的创造活动,是人类对宇宙创始的神圣事件的模仿。把一个地方变成家,变成称之为“世界的中心”,其一是建立起以家为中心的文明秩序,“人类居住的地方提供了庇护所,可以躲避只有蛮力才能控制的自然世界”[22]。只有在“受保护”的中心,自然生命和人的生命才有“生生”之谓,人才能嵌入有信任的交往秩序之中,获得人之为人的自由。同时,“它开启了一个完全由自我约束和尊重邻居所引导的人类生活的前景。人类居住区将自我与他人分开,同时区分内部与外部、外部与内部。然而,它也创造了一种新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以主人和客人的形式出现。同时,它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来与去、旅行和回家的辩证法,将外部与内部、内在与外在结合起来”[22]。其二是家的发明和创建,为渴望迎接陌生世界挑战的离家之人有一个返回的据点。猎人、战士、科学家、工匠、冒险家或革命者,为了磨练他们的技能,训练他们的思维和体魄,战胜强敌以保卫家园,驯服蛮荒的自然界,使其交出蕴藏的宝藏,走出家园,走向荒野。他们的返乡之旅,就是把获得的物质财富和外乡的精神财富运送回家。特别是科学家带回一批经过数学处理的观测资料,这些资料后来成为技术和物质进步的宝贵资源。其三是家的发明和创建,为欢迎英雄返乡,为欢迎邻人到访,为节日的聚会和庆祝仪式准备好绝佳场所。在这里人们活在自己的传统中,创作赞颂神圣创始和人类创造的诗歌,撰写赞美各种人类荣耀之事的颂辞,把共同参与到节日庆典中的人们富有意义的谈话赋予语言。
现代世界的物质财富在工作世界产生。工作世界没有节日,远离家人和朋友的圈子,相当于史诗中英雄长成的未知领域,也是从理论上界定英雄和凡人分野的领域。由于自古以来,哲学家认定精神财富与高贵的、永恒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沉思的理论生活备受推崇。由此古典英雄的原型化身为思想和精神成果,赢得推动文明世界“第一动力”的美誉。与其相对的身体、家园以及与之相伴的物质财富的创造活动、物质享受被视为满足低层次生存的必然性,归属平庸世界而被遗落在获得至上性思维的最隐蔽角落。家园中节日世界与工作世界断裂的后果显而易见。发生在工作领域的现代科技革命催生出巨大的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爆炸式的增长,但物质的丰足非但没有印证“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预言,反而加剧了人与天地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掌握着资本和权力的少数人,汲汲于眼前利益,无节制地放大欲望,为争夺财富而不惜破坏人类同此寰宇、命运与共的事实。历经上万年才进化来的高级人类智慧,被用在工作领域升级武器装备,威胁人和谐定居的美好心愿。把物质关系和自然原理作为现代文明的基础,应用于工作场所,丰富了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增添了物质世界的复杂性,却使人深陷身心相离和精神失根的“无家可归”之境。马克思(Karl Heinnch Marx)对工业化时代工作场所极端异化情形的尖锐批判警示人们,当人被逐出家园,把全部生命简化为工作,就会毁灭性地瓦解人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工作对于工人是外在的,它不是工人本性的一部分;因此,工人在工作中没有实现自身,反而否定了自我,有一种痛苦而不是幸福的感觉,没有自由地发展他的精神和体力,而是身体疲惫,精神颓废。工人只有在闲暇时才会感到像在家一样,而在工作时感到无家可归。他的工作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的。它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是满足其他需要的一种手段。一旦没有物质或其他强迫,它就像瘟疫一样被避免,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异己性质。”[23]98-99当工作是异己性的,人与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物是“异在”的,人的情绪是消极的,甚至与自己生活的世界是对抗性的,人的劳动形式蜕变为“纯粹动物的原始本能”,身心不能够自由发展,思考能力被迫处于沉睡状态。人成为“放弃自我,放弃内在的上帝”的“跛脚的怪物”[23]99,其工作不再具有创造性,生产出来的人工物全部是待售的商品。正常的工作状态,是与“闲暇”时日动态平衡下具有可持续性的身心俱在的“在家”状态。“在家”状态下从事工作正常地表现自我生命,其生产的人工物乃融入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作品,乃“生命的自我创造行为”,人的“内在尺度”在创造物中的自我表达。无家可归的状态下,人的生命失去可以退守的保护之域,人生产的财富不为建设和壮大家园,人作为具有创造能力的生命都不能够自由表现自己,更遑论缔造英雄?等待英雄归家的节日领域,其家园和大地之基被资本和技术挤压,语言遭受异化,不再承载诗歌与思想,不再表达问候与感恩,不再产生团结邻居和异乡人的对话,不再孕育赞美英雄的章句,堕落为只发布一系列为利润出征的指令。思想、艺术道德、戏剧表演失去了英雄成长的土壤,关于神圣秩序的信仰在商业激流的冲击下松动,所有语言修辞向物质世界匍匐拜倒,摇身变为促销的辞令。这种不遵循人类在家状态下创造财富的文明是畸形的,追寻真正英雄本质的动机陷于迷惑,“英雄”的意义“被扭曲为商业社会丛林法则下的强者”或“机遇与陷阱并存的名利场中的赢家”[24]。
如何弥合工作世界与节日世界的裂隙,免除人在工作状态下精神的家园化为废墟?这既是谈论人之本质的关键,也是揭明英雄本质之根蒂。人“首先是居住之人,由于居住在地球上而成为人类的人”[25]175-190。马克思指出工作中异化造成身心分离是伴随着家园感的丧失而倒向人道灾难。从正相反的视角看,工作日的身体经验中家园失根之痛,无疑是对被物欲放大的工具力量主宰世界企图的有力抵抗。家作为整个生活世界的中心,在家作为人扎根大地的居住方式,其“所有的意义都根源其中”[26]7。在家中人能正固身心,敞显自我精神。尽管物质结构的家宅脆弱,但具有自主性的生命只要为了抵御暴烈的风雪,坚强家的精神中心,担起家园生命共同体的责任,走向工作世界,就在实现英雄的本质。这个过程包含着守护人在家状态下的生育、照料、培养、保护、好客、认同、赞美、感恩、坚守、敬重神明等日常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这些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以爱、友善,忠诚,对话和团结为内核的文明秩序。不同于批判与怀疑为先验前提的理性思维,以家为中心的节日世界,是由身体对扎根大地无条件地依赖和对家园先天地信任为前提的。这种信任远古而隐秘,其深层背景“是我们最平常的习惯、家乡、本国语言、孩提时代经验之魔力的基础”[21]39。在一个由爱、友善、团结对话充实的世界里,“‘天空’向‘大地’开放,‘这里’向‘那里’开放,‘自我’向‘他者’开放”[22]。世界真理的秘密就隐藏在“天空”与“大地”、“这里”与“那里”、“自我”与“他者”在彼此信任、真诚承诺下架设起来的“交往”的桥梁之间。信任与真诚是在以家为始点的、被经验证实了的人与世界、人与他者的原始话语。这种原始话语在为维系诸种脆弱的关系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基础,并延展到远方的异乡世界。英雄出征,与其说是征服和统治未知世界的壮举,不如说是自我通过展现在家园培养并增长起来的勇气和智慧的实力,进入自我与他者互认和彼此理解的过程。出征的最高目的,在于探索广阔世界的真理,身体力行地减弱自然的灾难或人为过失带来的苦难,而不是拆解关系,摧毁与他者共同居住的地球家园。当经由家园周而复始的节日庆典培育起来的真诚的爱、友善、对话和团结的精神,随着栖居之人进入工作领域,转化为更广泛的公共精神,化身为融合着家园亲密感、信任感的契约精神和商谈规则,人们搁置歧见,分享经验,创造工作世界的意义,在凝聚共识中消除他异性压迫导致的焦虑和恐惧,有效防止以工作领域为主的公共空间与人在家状态的分裂,防范内在自我绝对地原子化,塑造健康的社会交往。每一个具有丰富内在世界的个体,在经验他人的苦与乐,承担为他人而好好存在的使命的基础上从事创造性的事业,就冲破狭隘的唯我主义,分享着神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站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维度解读中国古人“满街都是圣人”,以及马克思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赞美理论。
“我们生活的宇宙中,混沌发挥着作用。”[27]34人类精神的伟大,就在于人类具有在混沌的宇宙中建构秩序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发生在人类维护定居的实践过程,在混沌中创造出属人的时空秩序。为护理这种原初秩序,使其不被异化,发挥自身的禀赋而在家园节日世界和工作世界耕作每一个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身融入与他者组成的命运共同体,担负起对天地人一体的责任。所谓“彼一片之石虽大,不足以筑高城,一个之人物虽伟,不足以为英雄,使高城如彼其高者,有无名之础石为之也”[18]363。英雄不是一味酝酿征服计划的精神个体,而是立根家园,在无言之言的行动中,为“天下”“国家”“社会”做了正义之事的人。当今之世为节日而备的诗歌和剧作,在本原的意义上,应是引导长驱工作的世界迷途忘返的英雄,踏上回家之路,回归人类生活世界稳固的原点,在家乡的欢迎、庆祝、祝福和感恩的盛典中,再度自由而严肃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