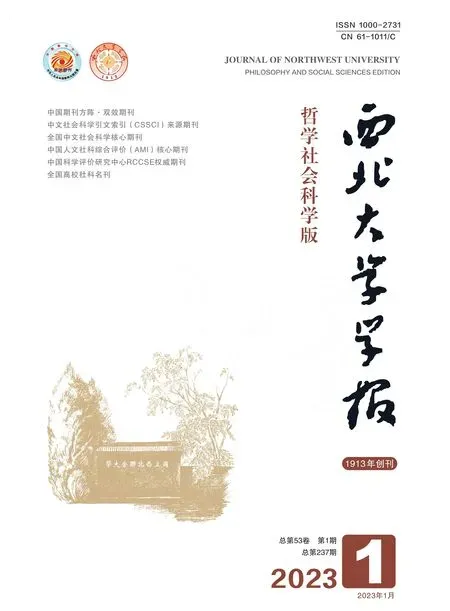新媒介技术时代文学经典的价值影响力考察
韩传喜,颜 逸
(东北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文学经典之价值不言而喻。一部好的经典作品不仅包含着独特的审美内涵和精神价值,而且还蕴藏着时代精神、民族文化乃至历史更迭的面影,对大众精神世界的浸润、社会文化生活的形塑、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化等均具有不可替代且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互联网、移动终端、智能媒体等主导的新媒介技术时代,文学经典的传播环境面临着颠覆与重构,多元文化的席卷、海量信息的促逼、生活方式的媒介化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学经典的价值影响力。
对于文学经典价值影响力的考察,应回归至经典作品的传播链条之中。M.H.艾布拉姆斯曾提出研究艺术作品的四要素框架,作品居于中间位置,与世界、艺术家、欣赏者相关联[1]5,国内学者在研究文学时,在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媒介”[2]57,强调媒介在文学传播、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影响力与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和媒介具有密切相关性。其中,作家和读者是实现其价值影响力的承载主体,作品是连接作家与读者的中介性因素,媒介是连接作品与作家、作品与读者、作家与读者的中介性因素,世界在艾布拉姆斯的理论中指向“自然”,可将之归于作品内容的行列,因此,媒介载体和作品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文学经典传播链条中的底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经典作品实现其价值影响力的过程中,媒介载体和作品本文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在新媒介技术时代,受媒介载体和作品本文转变的影响,文学经典价值影响力的承载主体、受众群体的接受行为等呈现出新的特征,经典作品价值影响的现实效力亦展现为不同的图景。
一、多元复合的承载主体
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认为,“精神只有通过在一个可感知的物质性(话语、文字、图像)中获得实体,通过沉淀于一个载体之上才能作用于另一个人。没有这种客观化或发表,任何思想都不能成为事件,也不能产生俘获力或抵消力的作用”[3]364-365。“可感知的物质性”强调了符号介质的重要作用,而“沉淀于一个载体之上”则突出了媒介载体的地位。由此来看,文学经典想要发挥其应有之作用必定要以一定的符号介质即文本形态沉淀于某种媒介载体之上,而媒介载体和文本之间具有相适应性,即不同的媒介所承载的文本形态之间存在差异。受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文学经典借以传播的媒介载体,从受时空限制的传统媒介转向了可随时随地传播的新型媒介,其文本形态亦由抽象的文字文本衍化为具象化、视觉化的数字文本。在媒介载体和作品本文的双重影响下,经典作品价值影响力承载主体的角色身份呈现为多元复合的发展样态。
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为研究传播媒介提供了重要参考,伊尼斯认为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时空偏向性,偏向时间的媒介适宜长久保存但不易于远距离传播,偏向空间的媒介适宜远距离传播但不易于长久保存。“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4]27纵观历史上文学经典的传播载体,早期具有时间偏向的媒介占据主导地位,最早未经加工的龟甲、兽骨以及后来出现的石鼓、青铜、简牍等作为媒介,均适合长久保存但不易于远距离传播,比如汉代名臣东方朔曾向皇帝上书三千简,由数人才能抬起。此类传播媒介因在空间上的局限性而极大限制了经典作品的传播范围,直至具有空间偏向性的纸质媒介的出现与普及,文学经典才实现了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的双向强化。而在纸质媒介等主导的传统媒体时代,经典作品的文本表征形式以文字符号为主,通过文字将作家的意旨投射其中传播给读者。在纸质媒介载体和文字符号表征的双重作用下,经典作品价值影响力的承载主体主要限制于作家和专业型读者之中。作家作为价值影响力的承载主体之一,一方面是受作家在文学场域中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读者群体对于作家之社会地位的认可和尊崇。皮埃尔·布迪厄曾将资本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资本的获取与争夺是个体在场域中占据不同位置的根本原因。作家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主要指的是作家既往的创作行为和作品所获取的社会名望与社会地位,著名作家的作品更有可能在读者的正向接受中成为经典作品。哈罗德·布鲁姆对西方历史中不同作家的经典作品进行了研究,比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狄更斯的《荒凉山庄》等等,他所强调的即是作家的中心地位,在布鲁姆看来,作家创作的原创性、陌生性、审美价值等对其作品是否成为经典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专业型读者指的是那些具备一定知识积累、社会名望与社会地位的群体,纸质媒介和文字文本的阅读为经典作品的接受设置了准入门槛,经典作品价值影响力的承载主体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于专业型读者之中。
与布鲁姆对作家的强调不同,接受美学家H.R.姚斯强调经典作品中读者的第一性,读者是作品达至完整性的必要环节,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便处于一种“未定性”之中。从接受美学视角来看,读者是文学经典历经时代洗礼不断生发新的时代精神与审美内涵的阐释者与传播者,经典作品在读者的参与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影响力。尽管接受美学存在其理论局限性,但是,在新媒介技术时代,接受美学对读者地位的重视恰恰应和了当前的时代背景和信息传播的现实。伴随时代的发展和媒介技术的迭代革新,信息传播与接受场域中的主导性媒介发生了转换,新媒介技术时代已然到来。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新媒介对纸张等传统媒介进行了“补救”,文学经典的传播在技术的加持下打破了时空界限,经典作品的数字化存在方式日益成为主流,以纸质载体形式存在的文学经典逐渐远离了受众阅读的主体地位。文学经典借以呈现的媒介载体趋向多元化,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喜马拉雅等听书平台、优酷等视频平台的叠加运用,使得音视频、图像、动漫、游戏等具象化、视听化的文本表征改变了经典作品单一的文字表征。而媒介载体的数字化和表征方式的具象化,极大降低了读者的接受门槛,读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数字化的传播渠道接受、共享经典作品,新媒介技术相对低廉的使用成本也促使文学经典无限扩大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经典作品的读者类型实现了多样化。尤为重要的是,受众的注意力或称之为流量,在信息传播场域中成为关注的重心,各类信息生产与传播行为主要致力于获取最广泛的受众关注。与之相应,在文学经典的传播链条中,读者或受众的重要性不断攀升,广大受众即大众型读者成为经典作品价值影响力的重要承载主体。以受众取代读者,是由于在新媒介技术时代,文学经典传播与再现的主要场域为互联网空间,再现的内容往往具有片段式、娱乐化等倾向,并且多以音视频、图片等具象化的表征方式加以呈现,传播时又常常夹杂于娱乐化的信息流之中,读者获取经典作品的媒介平台、信息类型以及接受方式等,与娱乐化信息相比并无二致,因此,经典作品的读者可称为受众。此外,作家、经典作品的二次创作者、专业型读者在经典作品价值影响力的实现中亦占据着重要位置。在新媒介技术时代,经典作品再现与传播的主体多元化,一方面指的是经典原著的创作者,其重要性体现在作家的社会名望和社会地位之中;另一方面指的是对经典作品进行再创作、再解读与再传播的阐释群体,此类群体兼具读者与二次创作者的双重身份,既有归属于大众型的兼具读者身份的二次创作者,又有专业型的兼顾读者身份的二次创作者,而后者以及专业型读者在经典作品实现其价值影响力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
二、文字失落:视听文本建构精神世界
新媒介技术时代,文学经典价值影响力的主要承载主体是广大受众群体即大众型读者,这不仅由于受众在技术赋权下享有信息生产与传播、共享与互动等权利,而且还由于受众在信息传播场域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如前文所述,获取受众注意力或流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当前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主要目的。而经典作品的文本表征与其价值影响力的实现之间具有直接相关性。文本表征是作家将其精神世界现实化的中介性因素,作品只有通过文本符号加以呈现才成其为作品;亦是读者与作品之间产生对话与共鸣的中介性因素,读者只有在接触文本符号并加以理解与阐释时才成为读者。在新媒介技术时代,经典作品的受众处于数字化、网络化的生存状态,从马歇尔·麦克卢汉将媒介视为人的延伸的视角来看,新媒介所延伸出的人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最主要、最发达的“人体器官”,甚至在一定情境中存在取代人脑也即人之理性认知能力的可能性,因此,新媒介平台中经典作品的文本表征,将对受众接受文学经典的倾向和效果产生直接影响,亦即作用于经典作品价值影响的现实效力。新媒介技术时代,经典作品的文本表征从线性的文字符号演变为具象化的视听文本类型,随着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经典作品的文字文本逐渐被置于边缘地位,文字文本的失落和视听文本的兴盛共同作用于经典作品价值影响力的实现。
一般而言,相较于具象化的视听文本,读者在接受线性的、具有逻辑性的文字文本时,需要想象力和理性思考能力的深度参与,在姚斯所言读者的“期待视野”即先在理解的加持下,在读者的头脑中构建精神和思想的感性世界,在此过程中,读者不仅会对经典作品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等产生切身的感悟,而且还会结合自身的实际境遇形成独有的深层认知。而具象化的视听文本属于非逻辑性的、直观的、诉诸感官刺激的叙事方式,从麦克卢汉有关冷、热媒介的观点来看,具象化的视听文本是具有明确信息指向性的热媒介类型,读者无需过多调动其想象、逻辑思考等能力,仅需视听感官等远感受器的参与,便可直接获知经典作品的内容和价值意蕴。此外,以影视剧作、短视频等视听文本再现的经典作品,属于二次创作,所传播的内容不仅包含原著的思想,而且还包含二次创作者的思想倾向,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具象化的视听文本表征因其较强的视觉冲击性,极易对读者形成先入之见,读者据此形成的对于经典作品的认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与原著相差甚远,而且还因媒介真实的作用而先入为主地对文学经典形成他者所设定的认知倾向,经典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进入“仿真化”的阶段。“仿真”的概念由让·鲍德里亚提出,强调的是电视等视觉化媒介所建构的媒介真实取代现实的“超真实”现象,在新媒介技术时代,媒介真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受众对现实世界认知的主要参照来源。经典作品的二次创作者通过新媒介载体和具象化的视听文本表征再现作品时,所建构的即是以媒介真实取代经典作品之本有价值的内容世界,而新媒介载体中视觉化的呈现通常又具有极强的逐利倾向,很大程度上是迎合受众品位、专注于受众注意力即获取流量的文本内容,而从本性上而言,受众更倾向于接受简单、易于理解的内容,因此,读者对经典作品的认知便容易局限于二次创作者的思想之中,经典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深刻意蕴和价值则往往被边缘化。“文学经典中关于人性的思考、时代变迁的记录、启迪智慧的真理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带有时代印记的浮于表面的浅层化解读、碎片化和拼贴式的非系统化认知、被娱乐化倾注的戏谑式狂欢。”[5]需要指出的是,读者对于以视觉化表征再现的经典作品所形成的先入之见,会随着阅读原著的不断深入而出现转变,最后将会形成契合原著本文内容且专属于读者自身的认知。但是,在新媒介技术时代,越来越多的读者趋向于在移动终端中接受经典作品,尤其是以具象化的视听文本再现的文学经典,在获取视觉化呈现的影视改编剧或短视频解说后往往便止步于此,与之相应,读者对于经典作品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亦止于他者解读之中。
以《城南旧事》为例可以窥斑见豹。经典作品的视觉化呈现是在原著基础上的再创作,导演、编剧等二次创作者的思想倾向,掺杂于影视剧的拍摄和制作之中,最直观的表现在于对原著内容的增设和删减,而经典原著的内容则在视觉化再现中以解码后的方式直接呈现给受众,比如对于原著中所描绘的老北京城风土人情的再现,无需受众想象力的参与,老北京城的样貌便直观地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对于人物细腻且丰富的内心活动以及在文字叙述中呈现的线性逻辑等,视觉化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较难与作品本文相契合。比如在原著中,英子在出院后去往新家的路上,看到“赶马车的人狠心地抽打他的马。皮鞭子下去,那马身上会起一条条的青色的伤痕吗?像我在西厢房里,撩起一个人的袖子,看见她胳膊上的那样的伤痕吗?早晨的太阳,照到西厢房里,照到她那不太干净的脸上,那又湿又长的睫毛一闪动,眼泪就流过泪坑淌到嘴边了!我不要看那赶车人的皮鞭子!我闭上眼,用手蒙住了脸,只听那得得的马蹄声。”[6]56如此细腻生动的描写,在电影中仅具象为英子拿手蒙住脸这样一个简单的画面,原著中人物的内心活动实则难以再现,受众亦无法更为深刻地体悟到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在经典原著或影视改编剧基础上再创作的短视频,不仅以他者解读取代了经典原著的内容,而且因其表征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消解了经典作品的价值影响力。以短视频再现经典作品的内容多为几分钟读名著或观影,主要对原著或电影中的内容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再加上创作者的部分认知与感悟,原著内容被压缩为由几个简单的故事情节所组成的短视频,经典作品的价值空间被压缩,更有甚者,在点击量或流量的促逼之下,以猎奇的标题、夸张的解说、低俗的封面图等对经典作品或影视改编剧进行再创作,造成经典作品内容和价值的变形、曲解甚至是颠覆。当然,以具象化的视听文本加以呈现的经典作品中亦不乏优质的剧作,老舍的话剧《茶馆》便是其一,该剧被成功改编为多种跨媒介的艺术形态,尤其是影视化呈现中所展现的时代的更迭、人物生命的流逝以及人物命运的多舛等,均产生了超越文字表征的情绪感染力,比如最后一幕中垂垂老矣的三位主角围在一起为自己撒纸钱的场面,影视化的呈现较之文字表征而言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经典作品的价值从而得以升华。
三、思想“阉割”下经典作品的接受
在新媒介技术时代,媒介载体的多元与便捷,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实现经典作品再现与传播的文本类型在数量上的增加,无论是短视频还是影视剧、游戏或漫画等,文本范围大多限制于耳熟能详的作品之中,比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骆驼祥子》《阿Q正传》《活着》《傲慢与偏见》《百年孤独》《悲惨世界》等等。而经典作品传播与再现的文本范围受限,意味着受众接受内容的有限性。新媒介技术时代,受众即大众型读者的关注、共享与传播等是经典作品发挥其价值影响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受众往往以看似主动实则被动的方式获取信息,在此所指的是受众在接受经典作品时,因新媒介赋权看似主动地选择了想要的信息,实则是在算法、大数据等技术的“劫持”下,以及二次创作者的引导下做出的选择。而经典作品文本范围的受限,将导致文学传播范围内的“信息茧房”,再加上个性化推荐技术的普及,极易在受众的作品接受中形成单一的文化氛围,在文学史中由经典作品所建构的深厚且多元的价值内涵被切割,经典作品亦难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影响力。而经典作品文本范围受限的主要原因,在于二次创作者的创作行为与受众信息接受偏向之间的相互作用。新媒介技术时代,经典作品的二次创作者既是读者又是作品的再创作者与传播者,对于受众即大众型读者而言,二次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接受经典作品的内容与数量。而经典作品的二次创作者尤其是大众型创作者在选择作品文本时,往往重视那些在受众群体中耳熟能详的作品,也即是与受众之间更具有亲密性、审美距离更短的作品,在契合受众阅读倾向与偏好的基础上通过视听文本直观再现,以获取更多的点击量和流量,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与接受。在此过程中,极易形成经典作品传播与接受的“怪圈”,即受众依靠创作者提供的内容接受经典作品,而创作者又依据读者既有的“期待视野”选择再创作的作品文本,二者互为参照、互相促进,最终导致所传播与接受的内容愈发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
经典作品二次创作者的创作偏向,源自消费主义的席卷及其对功利性目的之追寻。自古以来,文学经典的创作者通常限定于精英阶层之中,在“文以载道”的重任之下所创作出的经典作品,主要担任教育和精神传承的作用,力图以文学审美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因此,文学经典一直以来也因其崇高性和权威性而被置于高地。但是,在新媒介技术时代,文学经典以通俗化、具象化的表征实现了“再民间化”转向,消解了经典作品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与此同时,经典作品再现的创作者角色身份变得多重化,专业型、大众型的二次创作者成为再现与传播的主体,文学创作不再是传统的具有较高创作门槛的想象性文学生产活动,而是衍变成人人都可进行经典作品再创作与传播的文学再现行为。创作门槛的降低以及创作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经典作品再创作中的商业化、娱乐化乃至低俗化倾向。比如对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影视化改编,在当下出现了仅仅借用受众所熟知的角色之名而内容却与原著相差甚远的影视作品,甚至有些影视作品中加入了太上老君和铁扇公主感情线的剧情,不仅使文学秩序荡然无存,作品本身的文化意蕴也大打折扣。文学经典二次创作者的创作偏向反映了其创作行为的功利性,而此种功利性的源头可追溯至消费主义对于大众社会生活的全面接管,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文学作品、绘画、音乐等被归为想象性艺术范畴的感性存在,被资本纳入其生产剩余价值的范围之内。“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7]50由纸质媒介等统治的传统媒体时代,消费还仅限定于一定的范围之中,但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受众生活与消费方式的改变, 消费行为日常化、 日常生活消费化成为常态, 而消费主义常常与娱乐化相勾连, 文学经典在此环境中的再现、 传播与接受也逐渐呈现出娱乐化和消费化的倾向, 经典作品逐步沦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在“商品化”的文学经典作品中, 高雅的审美追求似乎已经成为明日黄花, 利益需求主导了文学经典的再现与传播; 而受众在接受经典作品时的消费性远远多于对经典作品的沉思与感悟, 交换价值主导了受众的接受行为。 二次创作者的创作偏向, 不仅导致经典作品再现内容质量的良莠不齐, 而且还可能造成经典价值体系的崩塌, 经典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流量、 点击量、 经济效益等的附庸。
在作品本文和创作内容的影响下,受众对于经典作品的接受与认知形成存在陷入思想“阉割”之困境的可能。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延伸人体同时也“截除”人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经典传播载体的便捷性、文本形态的通俗化与具象化,使经典作品更加易得、易懂,而受众在此过程中却可能会逐渐丧失其思考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文学经典本身承载着厚重的内容,不但结合了创作时期特有的时代背景,而且还融合了复杂的隐喻及内涵,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名小说《百年孤独》,如果对拉丁美洲的历史进程不甚了解,魔幻现实主义对大多数受众而言与科幻无异,他们更无法真正了解著作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受众在阅读经典时要亲近作品文本,通过直观的阅读体验,反复咀嚼思索才能真正获取独有的个人认知。而在新媒介技术时代,文学经典媒介载体和文本表征的变迁,带来了受众与作品之间距离的极大缩短,但是,文学经典的崇高性和严肃性却不断被消解,受众对经典作品的尊重感与崇拜感逐渐减弱,对经典作品的接受更是呈现出浅尝辄止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经典与受众之间的实际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被延长了。在此过程中,二次创作者对经典作品的简略解读在受众群体中广受欢迎,甚至成为很多受众接受文学经典的主要方式。毋庸讳言,他者解读后的经典作品更加直观、生动,通俗化的表达也更易于受众理解和接受,但是,他者解读不仅存在天然的缺陷,而且受众在接受此类信息的过程中可能会逐步让渡出独立思考的权利,成为思想被“阉割”的人。一方面,他者解读具有极强的个人主观偏向性,是他人依据其人生经历和个人认知而形成的,受众通过他者解读形成对文学经典的认知,看似了解其核心内容,而实则“得到的不过是因为不可遏止的异化而造成的‘形迹’(Trace)而已”[8]。从另一方面来看,阅读应由读者自身掌握阅读的节奏,在阅读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思考力,进而形成其独有的认知和理解,而他者解读后的文学经典更像是一种信息传播,受众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当受众习惯于接受他者解读的内容时,便不再追求阅读经典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亦是不再追求真正的文学,在此过程中,受众的深度思考能力不断被削弱,个体思维也被他者思想所禁锢,在他者解读以及通过新媒介平台所建构的媒介真实的影响下,文学经典对不同读者产生不同意义和价值的本质,也在经典作品文本的缺场和受众主动思考能力的弱化中逐步丧失。受众在经典作品的接受中不知不觉沉溺于此种不思而获的环境之中,成为柏拉图“洞穴隐喻”中的洞穴人,陷于已存在的“现实”,而几乎从未思考是否是真实的“现实”。
四、结 语
新媒介技术时代,在经典作品传播链条的各个环节的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借助于新媒介平台和视觉化的文本表征,文学经典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其价值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又因文字符号的失落、他者思想的侵入以及经典文本再创作的消费主义倾向等,导致经典作品价值影响力的削弱乃至消逝。事实上,由新媒介技术带来的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传播与接受方式,在当下已经成为大众的生活甚至是存在方式,因此,媒介载体比以往任何时代在经典作品价值影响力的发挥中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媒介载体的变迁给文学经典的生存境遇带来的挑战之一,便是网络文学的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主流关注的式微。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社会与时代中所创作的想象性文学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倾向,正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在新媒介技术时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进入新的场域,网络文学以及多种新的网络文艺均属于应时而生的时代产物,对这些新的网络文艺的格外关注既是时代的必然结果,亦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如此,文学经典亦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其价值影响力应被强调和强化而非遮蔽和弱化。随着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元宇宙”概念的提出,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应用与普及,都会关涉到文学经典的价值影响力。文学经典在未来应如何应对变动不居的传播环境,如何在智能化的媒介时代实现经典作品之价值影响力的持续发挥,进而实现经典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积淀,是亟待关注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