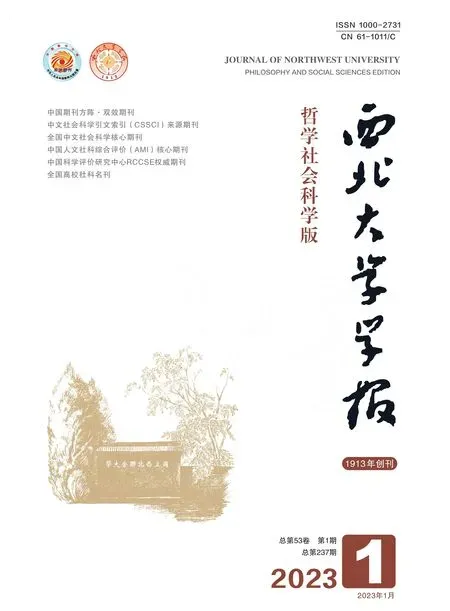历史的记忆化书写
——《刽子手之歌》创伤叙事研究
薛 婷
(1.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2.西安医学院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是一部记录美国犹他州普罗沃市凶杀犯加里·吉尔摩的非虚构小说。作品采用个人传记的文学形式,通过警方档案、新闻资讯、法律文件、书信和录音等历史纪实性材料,还原枪杀案件中的人物境遇和社会现状。本文不拟详细讨论非虚构小说的创作特征和表现形式,而是旨在分析作品中历史的记忆化书写,探讨创伤叙事的技巧和价值问题。虽然在叙事中,作者是以历史主义的笔触探寻时代精神与社会矛盾,然而创伤叙事才是小说艺术表达的主调,是作者藉以表现创作意图,探寻人类本性和生存意义的重要技法。
一、《刽子手之歌》的文学主题
小说《刽子手之歌》发表于1979年,梅勒以客观超然的笔触真实记录死刑犯加里·吉尔摩的人生历程和犯罪受审经过,此作品在美国文学界和新闻传媒界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并于1980年荣获普利策文学奖。《刽子手之歌》表面上是一部反映美国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非虚构人物传记,但作者在开头与结尾部分便引用《古老的囚歌》作为“呼唤与应答”,以言明创作意图,“在我深深的地牢里,我迎接你的来临。在我深深的地牢里,我羡慕你的恐惧。在我深深的地牢深处,我生活着。我不知道,我是否希望你平安”[1]1。由此可见,作者希冀以真实的社会纪实材料,扣寻记忆中的历史之门,探求迷茫与疯狂背后的创伤本原。
从文学题材来看,小说可视为一部运用大量纪实材料写就的非虚构个人传记,为读者在文学创作和叙事史观上开辟了新的视域。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语言学的转向使诗性思维在历史表现和历史写作中不可或缺。20世纪60年代非虚构小说兴起,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下,采用想象和虚构的技巧,运用文学的语言描写社会事件和历史人物,兼具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虚构性。一方面,创伤叙事诗意地消解了历史的理性表达,通过多重叙事维度补正、重构创伤个体的记忆框架。荷兰史学家富兰克林·鲁道夫·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曾指出,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具有“私人化”的特质,“‘记忆’代表着人类过去所有被抑制、被忽视和被压制的东西,从而依其性质从来没能进入被集体地认知与承认的公共领域——这一直都是传统意义上‘历史’的领地”[2]158-159。另一方面,德国学者蕾娜特·拉赫曼在研究文本与记忆的关系问题时提出,“叙述以双重方式具有记忆性能,即一方面叙述作为文本再生产和重复的过程,另一方面以特定的叙述模式使叙事具有记忆性能”。互文性被当作文本本身所具有的记忆,它是“一种有效的记忆方式,它可以改变角度来观察、平衡并修改大文化文本中的各种单个文本”[3]271。创伤叙事正是以历史的记忆化书写再现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社会事件和历史人物,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中生产、阐释记忆的意义和价值,由此更广泛、更深刻地还原社会和人物背景认知,折射民族、社会及个人创伤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动态演变。
小说《刽子手之歌》中创伤与历史互文书写的目的在于,通过抒写创伤超越历史存在的必然形式,通过书写历史的必然探寻创伤的可能本原。作者一方面用创伤叙事消解历史与现实的必然,另一方面又用历史纪实材料佐证囚禁与救赎的徒劳,同时还用幽灵与噩梦填充生死轮回说的空洞,从而使小说在主题上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前后呼应:小说上卷“西部的声音”是历史话语的诗性表达,描写加里·吉尔摩获保出狱后的生活经历和凶杀案件的整个过程,小说下卷“东部的声音”是纪实性的真实报道,还原死刑审判和枪决执行的一波三折,以及律师代表、社会团体与新闻媒体之间的角逐争斗,最后又以神秘的启示缓和人物内心的纠葛困扰。为了超越现实与记忆之间的裂隙,作者借用诗意的符码,来敉平历史叙事与创伤叙事之间的裂隙:出现在内华达洪堡盆地和冬夜停车场里的守护天使、水晶喷泉大街那座房子的灵异事件、时常萦绕的砍头噩梦和笃信的“人世轮回说”。正是由于小说中预言和启示的在场,作者才巧妙地将创伤主体的记忆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统一在创伤叙事之中。
《刽子手之歌》中主题的呼应性结构,不仅是非虚构小说创作技巧的标新立异之处,同时也是历史与创伤互文书写的本身困境使然。一方面,历史书写遵循由过去到现在的线性时间结构,通过记录和考察“历史事实”,实现人文价值和善恶观念的批判;另一方面,创伤记忆是个体的记忆,呈现碎片化、零散式的特征,需要身体的经历、体验和感受,而创伤叙事是一种语言再现,需要经过认识、理解和反思才能整合记忆、再现经历。正是由于两种表达的内在困境,作者才站在人类本性与生存意义的高度,选用“呼唤与应答”的结构,重新省思历史与创伤。小说借助创伤叙事完成历史书写向创伤书写的通达,经由创伤记忆实现创伤书写对历史的复原、理解和阐释。因而,作者悬置凶杀案件的善恶批判,抱守着挑战传统、宣扬自我的嬉皮精神,围绕加里·吉尔摩的生存境遇,书写社会与时代的精神困顿与迷茫,并试图在创伤的记忆框架中理解和阐释身份认同与历史建构。
二、《刽子手之歌》的创伤叙事技巧
在小说《刽子手之歌》中,作者表面上使用客观冷静的历史叙事叙述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实则透过历史场景、细节脉络和创伤记忆反观个体创伤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一般而言,历史叙事的目的在于阐明事物发展的因果规律,而创伤叙事的目的在于澄明人类个体或集体经验过的痛苦和伤害。前者关注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而后者则注重个体生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精神诉求和生存主张。
《刽子手之歌》中历史的记忆化书写首先表现在对自然与社会场景的白描式临摹。 荷兰学者杜威·德拉埃斯马在《记忆的隐喻:心灵的观念史》中提到古罗马人西摩尼德斯的记忆方法,即通过地点记忆与之对应的个体,再通过个体与地点的关联再现场景与故事。小说开篇便以地理空间为轴,展开故事的社会背景描写:“黎明那会儿,远山或者金黄或者绛紫,可现在到了上午,它们却呈现出土褐色,光秃秃的,显得十分高峻。山脊上淋过雨的积雪看上去灰蒙蒙的,这种凄凉的景色深深感染了他俩。从布伦达居住的厄伦姆北郊到普罗沃市中心弗恩的鞋铺仅仅六英里路,他们却花了好长时间。公路两侧购物中心、快餐店、旧汽车寄卖场、连锁服装店、加油站、工具店、交通标志牌和水果摊连绵数英里,还有银行、一家家房地产公司的平房小院和一排排复折式矮屋顶的公寓。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油漆得像托儿所似的:淡黄、淡橘红、淡褐色和淡蓝色。从厄伦姆到普罗沃的这公路两旁,褐色的两层木楼为数很少,看样子是三十年前建造的,它们又破又旧,简直像拓荒时代的酒吧间……头顶上是美国西部广阔的蓝天,只有它没有变。”[1]18-19这段话是加里获得保释出狱后,与布伦达一同前往普罗沃市的沿途景致描写,前半段是自然风光剪影,小说人物通过对时间的感知,察觉到远山色彩由绚烂的金黄、绛紫转变为凄凉的褐色,背景色彩的变换映射着斗转星移后的世事变迁和物是人非,人物记忆由过往转入当下,亢奋的情绪也在色泽浸染后归于平静。后半段是社会环境掠影,作者采用延长叙事时距的方式来调整叙事速度,叙事时间的停顿使记忆与想象冲破当下焦虑与不安的心绪,在未来时间里蔓延舒展;此外, 作者还以切换地理位置的方式构建了当下的叙事空间,借用视觉色彩捕捉特定时刻人物意识深处的心理活动。前半段自然景致中的色彩变幻与后半段社会生活里的环境更迭交叉铺展,揭示叙事中历史、当下与记忆的关系,记忆的意义来源是对历史的认知、对当下的关联以及对未来的想象。
普罗沃市是美国犹他州的一个主要城市,不仅是西部市场的理想集散地,而且是配套设施完备的工商业发展区。诺曼·梅勒采用白描式的语言,以加里·吉尔摩的视角概括性展现了这座城市的布局全貌,“普罗沃这座城市布局整齐划一,像个棋盘,宽敞的街道两旁又几栋四层楼房,室内一共有三家电影院,两家位于主要的商业街中心路上,还有一家在另一条商业街大学路上。普罗沃也有自己的时代广场,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这个广场的一角有座教堂,旁边是所公园,斜对面是座大药房”[1]23-24。小说中整齐划一的城市布局反映了普罗沃安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井然有序的生活环境,此处作者采用赋格叙事的技法,运用社会之境照映生活之境,视觉寡淡的城市格局折射着社会生活的人文风貌。历史中地点的记忆化书写以真实客观的描摹祭出宗教领域的信仰坚守、生存的原本状态和精神追求,普罗沃市的大部分居民信仰摩门教,摩门教推崇家庭价值与社区精神,遵守传统价值道德观和生活方式。小说中一隐一显的照映结构呈现出社会经济生活与精神信仰共建的平和状态,同时预示着枪杀案对犹他州法律制度、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
第二,对细节脉络和人物心理的复合式再现。作者对法院庭审、调查听证会及新闻采访等过程的一体式客观描写,阻断了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历史事实的浸入,使小说呈现出一种镜面的真实。普罗沃市枪杀案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律师、文学代理人、电影制片商就采访、电影制作和生平故事编写等事宜进行激烈角逐,采访专有权的纷争是助推加里成为时事焦点人物的关键,案件意义的大小不再受法律裁决与社会公正的影响,而由现实的金钱利益和人物内心的潜在欲望来决定。小说中,作者详尽描述了转折性事件的细节脉络,以期展现复杂矛盾的人物内心世界:自由撰稿人丹尼兹·博亚兹维护死刑判决,记者塔默拉·史密斯利用当事人搜集私人信件,狱友理查德·吉布斯背叛揭发加里,制片人拉里·希勒独揽采访专有权,作者一改历史主义小说聚焦时代背景和主要人物的笔法,对枪杀案件所涉及的多个人物进行家庭出身、生活经历及心理活动的细致描摹,展现人物心灵的本来样貌和自然状态。
从表面上看,小说情节的起承转合取决于法律裁决与庭审结果,然而其细节脉络却呈现出小说中各色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动目的。枪杀案的审判结果是多方代表求名夺利的必争之壤,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美国伦理学会、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美国行为精神病协会、美国犹太教士中央联合会或横加干涉,或暗中作梗。小说叙事中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精神诊断及书信录音资料,看似冷静客观地还原了凶杀案件的社会舆论倾向,实则突显了死刑犯诡秘莫辨、狂妄自私的人物形象。加里一方面获取亲友团和社会团体代表的同情关注;一方面把控辩护律师和新闻媒体记者的立场态度,并通过操纵利用社交媒体,多次干涉庭审审判结果,从一审死刑判决到暂缓行刑,再到推迟执行死刑,直到最终裁决执行死刑。身陷囹圄的一级谋杀犯三次更换辩护律师团队,两次谋划越狱行动,两次企图自杀……这种历史的记忆化书写,不是让读者站在温情的现实主义立场批判现实、反思历史,而是透过镜像反观自我,思考人性。在小说下卷中,作者节选加里的诗歌——《这里的房东》来印证其自我认知和自我反省,“……我感到自我只遇到自我, 一个红色的尖叫冲出来,但我把它揪回去检验了它的力量,它逐渐增强变成一个绝望的重量,在血液中然后倒下……”[1]771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真实刻画与细节呈现应被理解为创伤记忆的再现,作者的冷静书写是在警醒我们,每个个体的心灵深处都可能隐匿着凶恶与贪婪,血腥的屠戮和无厌的私欲会在同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造成创伤,而通过创伤叙事进行自我披露和自我疗愈是实现灵魂救赎和精神跃升的重要方式。
第三,对人物形象与创伤记忆的旁白式解读。在加里·吉尔摩短短三十五年的人生中,长达二十二年的监禁生活阻遏了其记忆与认知、个性与情感的妥洽整合与发展,使其在小说中展现出诡谲多变、疯狂残暴的人物个性。作者通过旁白式解读和多维度见证,围绕其创伤记忆、自我认同和身份构建来塑造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为读者原本自然地呈现真实人物,并为理解其本性和生存状态作出尝试。
获保出狱后的加里来到普罗沃市,遵纪守法、恪守教义的摩门教徒再次画地为牢,贪婪索讨薪资,肆意报复租客,醉酒滋事挑衅成为他完成身份认同社会建构的个性表征。虽然加里在审讯和采访中,未曾正面表达自己对摩门教的态度,亦未明确解释自己谋杀两位摩门教徒的动机,但其恣意妄为的种种行径与摩门教徒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父亲弗兰克去世后,母亲发现加里坐在自己的绿皮椅上乱翻桌子。他因出生证明中父子姓名不符,难遏郁愤质疑自己的真实身份,指责母亲隐瞒事情真相,并将昔日父亲对他的严苛归咎于自己不可告人的身世。几年后母亲才得知,加里在俄勒冈州教养院时便因自己与父亲的姓氏不同饱受凌辱与精神折磨。当时“他头疼得厉害,他们给他做了一次脑电图。他拒绝劳动、寻衅斗殴、结果多次受到书面警告。他对他的精神病医生说,他常做稀奇古怪的梦,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他总是疑心有人在背后讲他的坏话”[1]317。出生证明是加里佐证自我身份的凭据,身世之谜是困扰个体自我认同的根本。母亲贝西作为连接父子的唯一纽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她竭力通过回忆与倾诉,维系父子感情,修复父子关系。探视加里期间,她多次讲述父亲昔日的趣事,“酒醉翻筋斗”“羊的故事”和“蹩脚司机”等历历在目的往事将加里逗得捧腹大笑,但每次笑声过后,他都会陷入沉思。身份认同具有多重性,然而认同的核心是独一无二的“自我”或主体。自我认同感或自我同一性是“一种自然增长的信心,即相信自己保持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能力(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这种信心是与他对别人保持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相协调的”[4]797。法国学者马克·富马罗利认为,“同一性只有作为一种需要时才会在人类生活当中出现。它只在记忆中显现,只在依赖于记忆所观察到的相似性的意志中显现”[5]27。作为一种主观性的意识活动,记忆的态度、方式和内容与记忆主体的身份限定息息相关。因此,记忆主体增加、删改、扭曲、误解、改造记忆,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杂乱零散的记忆碎片中,加里凭借一张出生证吞噬无私的母爱,抹杀深沉的父爱,瓦解自我认同,阻扰个体、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自觉平衡与发展。由此,记忆的主观倾向性选择导致了身份的模糊和角色的混乱,加里的少年记忆也因此打上身份认同的创伤印记。
加里·吉尔摩的母亲贝西信奉摩门教,为了保住与丈夫弗兰克和孩子们共同生活的房子,她希望摩门教会帮助支付拖欠的税款,她将以房产抵押的形式分期偿还借款。然而摩门教一面借助市政当局的起诉施加压力,一面压价购进她的房产,以致晚年的贝西只能在破旧的活动房里栖身。“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在所有伤害我的人里面,只有摩门教徒能够伤害我。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在俄勒冈州监狱的探监室里当她告诉加里教会根本不愿意帮忙保住房子时,他脸上那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当时他的目光就好像是发现了一个值得与之拼命的敌人似的。”[1]518当记忆主体在特定空间范围内进行记忆活动时,记忆客体就会以此空间范围为限定被建构一个记忆的框架。记忆主体的主观倾向性及其情感指向的关联性决定了记忆客体的选择标准和选择内容。对于记忆个体母亲贝西而言,昔日的家庭生活与摩门教的冷漠逼迫占据着记忆框架的核心或中心位置,然而部分记忆客体——年久失修的房屋、杂草丛生的庭院及无力偿还的借款,在此被边缘化、模糊化。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记忆空间对身份建构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英国建筑学家罗伯特·贝文认为,“摧毁一个人身处的环境,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意味着从熟悉的环境所唤起的记忆中被流放并迷失方向。这是对人们丧失集体身份认同以及丧失它们身份认同稳定性连续性的威胁”[6]11。毋庸置疑,那幢摆满菲律宾红木家具的房子是贝西一家身份认同形成的记忆地理空间,一旦承载记忆的空间遭到毁坏,群体及其成员的个体记忆就变得零散而混乱。
对于一个深陷身份困境,缺失自我认同的创伤主体而言,死刑犯加里的形象塑造藉由身份认同的创伤性解读得以实现。从历时性的层面来看,加里自我认同的过程就是其个体历史建立的过程,个体记忆和与其相关联的感性感知空间是身份认同的核心。记忆不仅牵涉对个体过去生活的印证,同时关系到对当下境遇的引申及对未来前景的规划。身世疑团、童年噩梦、父子隔阂、常年监禁成为过往记忆客体的主要内容,囿于记忆框架的加里无法与真实的现实共处,更无力与陌生的未来应和。从共时性的层面来看,身份认同亦是一个个体社会性建构的过程。个性中一定包含了多重社会性,同时预设和形成了某种特定的社会性。人的归属需求与安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情感认知和社交能力的制约和影响,个体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才能成为自我,没有人能够与社会毫无关联地自足存在。加里的冲动与疯狂背后隐匿着迷茫与焦虑,二十二年的监禁生活不仅使他无法实现自我认同,还使他缺失了情感认知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与亲友反目成仇、与恋人爱怨交织、与雇主出尔反尔、与狱友大打出手皆可归因于个体情绪失控与自我意识膨胀的创伤来源,由此作者将人物形象赋予创伤和历史的分量,阐明创伤对个体记忆、身份认同乃至人物个性及精神状态的影响。
三、《刽子手之歌》的创伤叙事价值
《刽子手之歌》是一部长达千余页的社会纪实性小说,小说围绕死刑犯加里·吉尔摩的生活经历和枪杀案件,从“东部”和“西部”两个角度串拢情节。小说上卷“东部的声音”是美国东部犹他州社会现实的掠影,作者通过聚焦社会生活中的毒品、酗酒、纵欲与暴力事件,勾勒出底层市民颓废迷茫的精神状况;下卷“西部的声音”是美国西部文明势力争斗角逐的缩影,作者通过透视律师、记者、制片人和自由撰稿人的行为与心理活动,展现西部代表面对死刑判决的功利心态和无力举措。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认为,“一部小说的价值,则在于揭示某种存在直至那时始终被掩盖着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小说发现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着的东西”[7]277。本文也倾向于认为,作者在非虚构小说创作中,暂时搁置了对历史的理性因果分析,规避了对生命的价值意义思考,以社会历史事件的文学化记述,呈现生存的原本状态与创伤的未知面貌。但历史纪实材料与创伤叙事在小说中的互文共生,不仅为非虚构小说提供了一种突破性的文本阐释,并使诺曼·梅勒小说的主题得以深化,从历史与虚构、文学与政治的研究层面上升到人的生存意义和精神追寻的高度。
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指出:“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 这一传统观念表明, 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8]2在小说《刽子手之歌》中, 历史阐释与文学创作始终缠绕,难分彼此。 作者一方面通过创伤叙事消解历史的确定性, 一方面通过创伤叙事突显创伤的个体性, 坚持将创伤主体的记忆融入行为和心理之中, 摆脱历史主义叙事的窠臼, 通过历史的记忆化书写, 实现史料作为历史客体与人类作为历史主体的结合。 先说史料作为历史的客体。 首先作者在小说中客观选用纪实性报道和案件真实材料, 其中包括法院庭审笔录、 警方档案、 《盐湖论坛报》《洛杉矶时报》和《德赛瑞特消息报》等实时性新闻报道以及加里·吉尔摩的四十四封私人信件和采访录音资料。 此外, 作者以超然冷静的笔触描述凶杀案件和枪决过程。 在加油站工作的摩门教徒马克斯·詹森遭遇胁迫而被枪杀, 小说中的描写是“詹森的身体随着枪声颤动了两下”[1]221。汽车旅馆经营者本·布什内尔遇袭身亡, 作者的描述是“接着传来砰的一声, 像是气球爆炸了”[1]249。死刑犯加里·吉尔摩的枪决过程在小说中的叙述是“枪响时,加里的手指头都没动一动,甚至颤也没颤一下”[1]1039。小说中,人物生命走向死亡的呈现方式在于表明,人物命运并非受制于历史主义理性的必然链条,亦未被限定在先验的领域之中,人物的行动是其心理逻辑的自然延伸,而行动的不可预知性则源自于创伤主体内心深处的创伤。
再谈人类作为历史的主体。首先,就创伤个体而言,小说中的创伤叙事打破了由过去到现在的线性叙事结构,历史的记忆化书写借助想象在过去和现实之间不断往返,真实再现了创伤主体的生存困境。加里·吉尔摩的创伤借助亲历者与见证者的记忆,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环境,呈现出一种精神迷惘与亢奋的胶着状态。创伤叙事在特定的叙事维度和记忆空间中构建出创伤主体不为人知的秘密世界,借助失控的心理、情绪和意识,个体创伤表征为疯狂残忍的屠戮行为,并逐步演变为社会与时代的沉痛悲剧。其次,就创伤集体而言,多重视角的创伤叙事是一个创造能指和生成意义的过程,个体创伤只有经过集体反思和社会反思才能被深化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共同历史。小说中,加里的个体创伤记忆与父辈、祖辈的记忆以神秘怪诞的方式反复闪回,其视点交错密集,铺陈蕴藉美国西部的世事沧桑与时代精神。当创伤主体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与现实相遇时,作者运用历史题材去建构时代创伤的主题,通过创伤叙事呈现难以言明的羁绊挂碍,让个体和群体的创伤在历史的记忆化书写中真实再现。
在小说《刽子手之歌》中,诺曼·梅勒再次展现出记者的洞察力和独创性,以非虚构小说的文学形式弥合历史与虚构的边界。据劳伦斯·席勒统计,为全面了解死刑犯加里·吉尔摩的生平经历,作者收集整理吉尔摩的信件和诗歌,摘录《盐城湖论坛》《国家问询》《犹他新闻》等多家杂志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并撰写将近一万六千字的采访记录。然而作者并未沉溺于历史纪实素材的甄别与分析之中,亦未遵循个人传记的传统叙事模式,而是采用多个限知内视角观照人物的童年记忆、成长经历、犯罪过程和庭审判决,关注吉尔摩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聚焦其成长过程中的创伤经历,反观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物的精神困境。历史的记忆化书写在完整再现人物生活、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展现出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和创伤本原,并以别具一格的文学形式开创了非虚构小说艺术表达和文学阐释的新方式。在《小说的艺术》中,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的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9]54。小说《刽子手之歌》中的创伤叙事结合了历史的客体与主体,消解了历史的必然性和恒定性,并通过历史的记忆化书写还原了创伤的本原。作者正是运用历史题材在文学创作的世界中求索存在的可能性,揭示流淌在小说情节中的创伤本原,进而引导读者透视自我、整理记忆、反思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