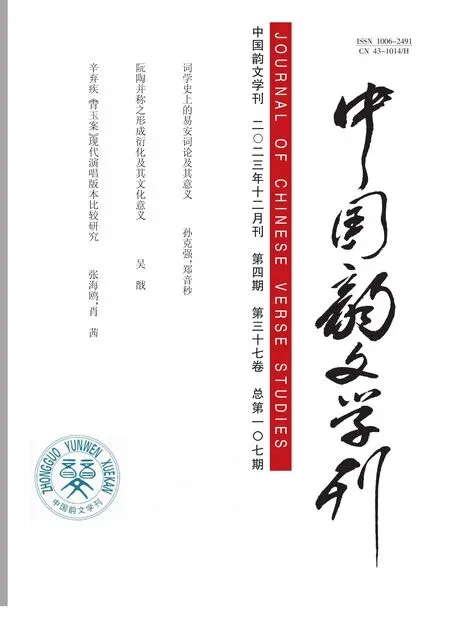论秦观的心说与词心说
关鹏飞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李廌说秦观作赋如作词,多是从技法角度而言,谭献则从词的创作境界指出秦观《望海潮》其三下阕对陈隋小赋的感物系统的继承[1](P10),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赋与词的贯通,背后透露出赋心与词心的贯通。所谓赋心,相传为司马相如所发[2](P93),后世受赋心理论之影响,提出秦观词心说。冯煦云:“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雋,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邪。”[3](P3586-3587)此论一出,得到陈廷焯、况周颐、邵祖平等人的赞同,成为重要的词学理论。而况周颐则从多方面试图破解“词心”奥秘,既从词境的角度来解释词心[4](P3),又从心本体的角度来论述词心[4](P7),还移词心以评词[4](P41),试图将词心说引入词学批评之中。目前学界也对词心说做了诸多探究,如邓乔彬、刘扬忠、彭玉平、杨柏岭、路成文、张静、汪泽、王伟、黄雅莉等皆有相关论述,从多角度对词心说作了阐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囿于词学范围和秦观身世,而对秦观心说涉及不深。实则冯煦、况周颐等人已略有提示,冯煦“得之于内”、况周颐“吾心为主”之说,皆与心学关系密切,而秦观之心学造诣尤深,无疑成为后人建构秦观“词心”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下面从秦观心说的心本体论、心伦理学、心说来源、创作中的词心四方面试作探究。
一 心本体论
真正能够代表秦观心说的,是其《心说》。秦观在《心说》中对“心”进行了深入阐释,将“心”作为与“道”并游于不穷、俱止于无所极的对象来加以把握,他说:“默而神之,与道全之;说而明之,与道散之。其全为体,即体而有用;其散为用,即用而有体。体用并游于不穷而俱止于无所极者,其唯心而已矣。”[5](P833)而“体用”之别也暗示了秦观心说的本体论及其现实伦理作用。秦观深受孟子心学的影响,但并非照搬,而是在魏景、佛僧、医学等学说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思考,以心为主,形成较为完整的心学系统。他先论述心之本体超越内外、主客、物我之别,甚至对这种超越本身也进行了超越,却又指出“心之真在”恰恰寄寓其间:“虽不在我,未始离我;虽不在物,未始离物;虽不在物我之间,而亦未始离乎物我之间者:此心之真在(1)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将“心之真在”误为“心之真”,此处据宋高邮军学本补“在”字,“心之真”与“心之真在”差别甚大。也。”[5](P833)秦观用“虚空”与心之本体进行类比,认为虚空是“即之不亲,远之不疏,万物方有则与之有,万物方无则与之无,俯仰消息,唯万物之与俱”[5](P833),指出虚空与心、心与万物之关系,这在其《醉蓬莱》词中体现最为明显,该词写琼花,即今之绣球花,秦观形容为:“九朵一苞,攒成环玉,心似珠玑缀。”[1](P161)绣球花是空心的,或者不如说是没有花心的,但是顾名思义,绣球花像球,这就使人会把四周“攒成环玉”一般的花朵的中间看作球心,实则球心是在花朵的映衬下产生的虚空,而一旦认可这个虚空就是花心,反过来看花朵,就像点缀在花心上的珠玑。“花心”之外,秦观另有“江心”之说,如《念奴娇·小孤山》云:“独见一峰青崒嵂,当住中流万折……应是天公,恐他澜倒,特向江心设。”[1](P169)小孤山因为是在江之“中流”,故而是屹立于“江心”,把心理解为中心之意,引申而为重要。这就说明,秦观所指之心,既指人心,亦有中心之意,而无论人心还是中心,在心之本体面前,皆如“一星之于天而一尘之于地”[5](P833),因心之本体即包含客观之万物却又远超客观之万物,要加上魏景“人心生万物”之论并推论到极致,才是心之本体,即心之本体既与万物俱,也与心所生之万物俱,犹如俄罗斯套娃,在物我、主客(2)此主客所取之意,不仅指主客对立,亦有主次补充之意,如《师友谈记》所记载秦观论赋中用字“主客分明”(《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1页),即六字句中“四字为客,两字为主”(《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2页)。、超越之中可以无穷无尽地循环往复,从而赋予不同层次的丰富意义。
秦观以心为主体,分别重新定义了性、情、意、志、思、虑、魂、魄、精、神等概念,他说:“即心无物谓之性,即心有物谓之情;心有所感谓之意,心有所之谓之志;意有所归谓之思,志有所致谓之虑;故合精以止谓之魄,配神以行谓之魂;与神为一谓之精,不离于精谓之神。此十者,入则一,出则不一,出入无常,要皆以心为主尔。”[5](P833-834)这十者,可以分为两层,第一层是由外向内,从客体世界进入主观世界,从而形成性情、意志和思虑;第二层以“故”为分界,进入纯粹的主观世界,从而形成魂魄、精神。只不过因为时代的局限,秦观在论述性情、意志和思虑时,都能通过经验把握而进行精细区分,像“即心”无物和有物是性和情,心有所感和所之是意和志,意有所归和志有所致是思和虑,不仅界限清晰,而且层层递进;可是在面对意识世界乃至潜意识世界时,秦观只能通过推论的方式进行模糊的描述(3)推论是秦观的思维特征之一,如其《十二经相合义说》:“阴阳之为道博而要,小而大。数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数之可千者,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也。然其要一也。”(《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43页)又苏轼《纪秦少游论诗文》云:“此未易以理推之也。”(《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6页)指出秦观认为杜甫善诗不善文、曾巩善文不善诗的观点不易以理推论,可见秦观之喜欢推论,已经引起苏轼的注意甚至批评。,像“不离于精”的是神,“与神为一”的是精,“合精以止”的是魄,“配神以行”的是魂,所省略的主语如果是“心”,则心与精、神实为异名而已,则“合精”“配神”又如何以经验把握呢?不仅陷入循环论证,而且使魂魄与性情、意志和思虑的关系被切断。虽然如此,秦观还是认为弄清这些就可以“动为一气,静为二仪,动静有万物,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阴可以开,阳可以阖,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5](P834),由此可见,秦观心说不仅涉及客观事物,也对广大的意识乃至潜意识世界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其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秦观的心之本体无法全部通过经验世界把握和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秦观之心学就是错误的,我们可存而不论,然而,他通过心之本体来重新阐释人之价值,则给我们理解其哲学观提供了一个方法。他说:“太上见心而无所取舍,其次无心,其次虚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众人之事也。虚心者遗实,贤人之事也。无心者忘有,圣人之事也。见心之真在而无所取舍者,死生不得与之变,神人之事也。呜呼,安得神人而与之说心哉?”[5](P834)可见秦观最终的目的不是成为圣人,而是成为“见心之真在而无所取舍者,死生不得与之变”的神人,他的最终价值取向既然是神人,那么只有读者成为神人,才能真正理解其学说,也就意味着其学说本身的门槛性和超验性。秦观又在《浩气传》中说:“圣人之心如众籁然,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其应物也如是而已,所谓无为而自正者也。彼众人则不然:有所距,有所受,有所将,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应之,弊弊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规,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吾见夫心劳于中、智尽于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谓有意而正之者也。”[5](P804)对众人“有意而正之”之心表示了批评,而对圣人“无为而自正”之心表示了赞许,但圣人之心虽然超越众人之心,却仍旧存有“正”与“不正”的痕迹,神人之心则“无所取舍”也就无所谓正与不正,从心之超越性而言,神人之心无疑在秦观心中是最高的;但从世俗社会而言,众人之心的“有意”是最能见效的;而在沟通世俗与超越的世界中,圣人之心的“无为”指向超越性,“自正”指向世俗性,此时圣人则具有了最显著的功能。秦观以心之本体为标准区分人之高下,只是出于超越性的考量,若以其他标准来衡量,会得出不同的优先级,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秦观对心本体作出详细论述的基础上的,由此亦可见秦观心说之价值。
二 心伦理学
具有超越性的神人、圣人如何与现实俗世接轨?秦观以有本、无本区分心、性,以重新定义的“德人”“道人”作为衡量标准来与天下之人建立联系,一方面使天下之人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也促使其心说落地,其《俞紫芝字序》云:“夫德人以有本为宗,道人以无本为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己也,不知有己所以失己也,而德人知之。于是内观无是,外观无彼。无是,故能以己为物;无彼,故能以物为己。己物不二,谓之真一,夫是谓以有本为宗。天下皆知有伪所以丧真也,不知有真所以丧真也,而道人知之。于是前际无舍,后际无取。无舍,故不断一切伪;无取,故不住一切真。真伪两忘,亦无真一,夫是之谓以无本为宗。”[5](P1251-1252)有本主张“己物不二,谓之真一”,然后达到“明心”的目的,知道这些的是“德人”;无本主张“真伪两忘,亦无真一”,然后达到“见性”的境界,知道这些的是“道人”。很显然,秦观通过有无之法来接通心性,并以心性来区分道人与德人,从而把空泛的学说作用到具体的人身上,而“人间所谓道德者,固不出乎此”更直白地体现出对人间道德的关注,使其心学带有积极的现实伦理作用。
把心说运用于现实社会、人生道德时,秦观认为无意比有心更为难得,认为谢安东山之志形于颜色,而王俭志在宰执见于所赋之诗,“无意之与有心相去远矣”[5](P745),王俭远比谢安逊色。《张安世论》中也认为张安世“有心”,而伊尹、周公则“实无心也”[5](P690),这些“心”都指私心。与之相对的则是“人心”,《韦玄成论》云:“礼非天降地出,出于人心而已。合于先王之迹而不合于人心,君子不以为礼也。”[5](P679)所谓“人心”即指公心。公私的转化关系,秦观认为是“能尽私恩,然后能尽公义”[5](P761-762),当二者矛盾时,秦观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以道权变:“然则公义私恩适不两全,则如之何?以道权之而已。义重而恩轻,则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赵宣子使人以其乘车干行,韩厥执而戮之是也。恩重而义轻,则不以公废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轮,去其镞,发乘矢而后反是也。”[5](P762-763)而一旦同心与天意相契,则无往不胜,他在《王朴论》中说:“其五策之意,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与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则无不成之功。”[5](P773)真正处理好公私者乃圣人,秦观《以德分人谓之圣论》云:“古之圣人,其道本于成己,而终于成物……圣人则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阳。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于物;出而不阳,故道济天下,而有以私于己。夫公于物,仁也;私于己,智也。公公私私,仁智两得,圣人之道尽矣。”[5](P795)可见秦观并不完全否定符合“道德之正”的“私”,指出“公公私私”能够仁智两得,而其词中大量的儿女私情之作无疑与此有关。
除公私之外,“心”还与“力”等构成内外之别,秦观《君子终日乾乾论》云:“日者,有为之时;夕者,无为之时也。于有为之时乾乾以致其力,于无为之时,则惕若以致其心……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内又有以尽其心。然则,德其有所不进,业其有所不修,而过其有所不补者乎?”[5](P793)秦观认为内求自然能达到内外兼顾的效果,他在《以德分人谓之圣论》中说:“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为人,己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绪余,足以治国家天下……彼圣人以德分人也,岂固有意于是哉?盖以为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与人者,亦理之适当然而已矣。”[5](P796)指出“与人,己愈有”的观点,又提出“理之适当然”的概念,把损己利人的公心从“有意于是”的嫌疑中解放出来,使公心的意义和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当然,秦观的心伦理学意义不仅在于直接从心出发作用于现实,表达道德看法,更在于通过澄清现实中的善恶观念来达到追本弃末的效果,其《芝室记》借僧人之口云:“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体,明白空洞,实无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觉真蔽于尘幻,由是清激而升者为想,浊污而堕者为情。夫情想之于心,犹珠鉴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沤,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无穷如虚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属,凡悦可于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变;而憎恶于吾耳目者,皆恶情之所生也。”[5](P1232-1233)此记作于元丰七年(1084),秦观自述此时自己“未尝读佛书”,但认为浮屠之论有可观之处。文中浮屠展现了三个观点:第一,天下万物都是心生,而心本体是明白空洞的。第二,当心被尘幻遮蔽时,其中清激而升的就是想,浊污而堕的就是情,因此想是善,情是恶,而灵芝显然是善想所生。第三,是浮屠和秦观都没有明说的观点,就是从“善恶毕寂,情想究空”的心之本体角度而言,灵芝也不过是幻觉,无所谓吉祥还是凶恶,但这样一来,就得罪张氏了,因此以“吾不能告子”结束来含蓄地展现。
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善恶都是情想,而情想不过是心本体之虚幻影像,那么,强调善恶是否还有意义呢?这就使现实中出于善恶对立而产生的撕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当然,作为现实中的人,秦观也难以完全不讲善恶,如秦观在《王俭论》中区分“终身之大节”和“一时之美”,认为王俭“该洽经史,明习故事,工词令,妙威仪,动为名流之所称,所谓一时之美、一日之长、夸污世而矫流俗者也”[5](P745),则秦观自身所重视者虽非此,但终归还是有价值判断的。换个角度来说,既然一切善恶都是虚幻,则纵情似也无妨,这一点对秦观的世界观可能影响更大。但从其对公心的推崇来看,秦观的心本体论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上,其建构心学体系的目的不在于去做空洞的理论推演,而是为现实道德提供理论依据。总之,秦观不是从现实中受到遮蔽的心的想、情出发来判断善恶,或反过来以现实中的所谓的善、恶来逆推其心,而是追本溯源,从心之本体与其伦理价值的角度,对现实社会做出新的评估和判断。其中公私、善恶等概念的重估,对秦观词体观念的解放有重要作用。
三 心说来源
李泽厚指出:“中国古代辩证法,更重视的是矛盾对立之间的渗透、互补(阴阳)和自行调节以保持整个机体、结构的动态的平衡稳定。”[6](P30-31)秦观的“心”概念似乎也是如此,已如上述。秦观心说受儒家心性之说尤其是孟子心学和苏辙的阐释的启发,吸收医学知识和佛道思想,形成自身颇具特色的心学体系。下面简要分类论述其心说来源。
儒家心性之说尤其是孟子心学对秦观有较大的启发。楚简《性自命出》有“凡人虽有性,心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与“凡心有志也”之论,二者看似矛盾,梁涛解释说:“上面第一段的‘心亡定志’,实际是说心自己不能确定意志的方向,不能直接表现为自主、自觉的道德行为,而必须或以外在之物,或以喜悦之事,或以后天积习为条件和依据;而第二段的‘凡心有志也’,则是针对心与外物交接中的自主、能动性而言,心的选择可以决定并支配性,它与‘心亡定志’不仅不矛盾,而且正好可以相互补充。”[7](P149)这类儒家心性之说虽出自楚简,也不能完全肯定秦观当时就无法阅读类似材料,因此也留作参考。
而《孟子》知言养气章对秦观的影响则较为明显。孟子在发现心之地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孟子把心与气联系起来论述。而秦观亦在《浩气传》中表达了自身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阐释。值得注意的是,秦观对孟子心性之学的接受,是在苏辙而非苏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辙是把欧阳修和苏轼的观点与心性之学融会贯通地加以推进了。苏辙明确认为“学圣人”不如“学道”,他说:“学者皆学圣人。学圣人者,不如学道。”[8](P953)这与苏轼“圣人之道,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9](P95)是有本质差别的。苏辙在《孟子解》中对性作了深入探讨,将之分为性与故(性之所有事),并认为孟子知性,只是因为主张性善论,犯了以故为性的毛病,苏辙对此作了澄清:“夫性之于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后形,应物而后动。方其无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则物之报也。惟其与物相遇,而物不能夺,则行其所安,而废其所不安,则谓之善。与物相遇,而物夺之,则置其所可而从其所不可,则谓之恶。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8](P954)在苏辙看来,性善性恶都不是性,而是故(性之所有事),但他也仍旧部分保留了苏轼的看法,知性而不言,这与苏轼圣人有所不知的观点仍旧有很大差别。
秦观看到了苏轼、苏辙之间的这个差别,他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今中书、补阙二公,则仆尝身事之矣。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补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书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5](P981-982)很显然,所谓“苏氏之道”包括了苏轼与苏辙的思想,这是正确的,如上所述,苏轼与苏辙皆已在欧阳修不言性的基础上作了发展,只不过苏轼是以“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的方式来知之(故把重心放在“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是以天下无不可学”上),而苏辙则知之而不言之(实际上是有言及的,只不过以行之为主),故苏轼之道能够像日月星辰那样运行而让天下之人都能看见他的高明,而苏辙之道则如混沦中的元气滋润万物而人们难以察觉,两相比较,秦观认为苏辙之道更为本质,秦观就是在苏辙的基础上对心性之学做了新的探索,故儒家心性之学对秦观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
秦观心说的另一个来源是医学。《黄帝内经》:“心藏神。”[10](P343)《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矣,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10](P128-129)赵献可认为心不是主,主是命门[11](P130)。先不去讨论人身之主究竟是什么,单从《黄帝内经素问》而言,显然心是主。宇治田对赵献可之说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反驳:“夫继天立极,临民出命,明明德于天下,是即君主所职,故曰神明出焉。天下非一人所治,诸官相与而能之,唯官有贵贱,君主为最贵,常位于上,得职要领,是以合而为十二官,曰故主明则下安,又曰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圣人之作经,一句一字不苟,此所谓‘故’字承上起下之辞也,若不承上而别有一主,岐伯何以有用此辞乎?此所谓主明与不明之‘明’,承上所谓神明之明也,的矣。”[12](P102)其实,赵献可出现误解的原因,在于对文法不熟,宇治田所云甚是,可从。秦观建构心学的思路显然用了《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的思维方法,以心为主来构建其他概念,但也有所不同,《灵兰秘典论》是合心为十二脏,而秦观则对心本身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与区分。
对秦观心说有所影响的还有佛道之说。先看道家。《列子·仲尼》云:“虽然,吾得之矣。夫乐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谓乐知也。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13](P116)注云:“都无所乐,都无所知,则能乐天下之乐,知天下之知,而我无心者也。”[13](P116)与秦观《心说》有较强的联系。秦观《俞紫芝字序》借童子之口发表对道家“有本然后明心,无本然后见性”[5](P1251-1252)的看法,又借魏景之口指出人心之神云:“甚矣人心之神也,虽造化亦无加焉。今夫天地之生物,煦之以阳,肃之以阴,然后乃成。人心则不然,一举而物已生矣。故天生万物,地生万物,人心生万物,是故人心之形象天地。”[5](P825)魏景融合释道之说,指出人心之神如造化,似天地,如此才能“盗天地阴阳之机”“识万物之理”[5](P825),虽然秦观认为魏景“虽不足以窥老庄之藩篱”[5](P826),因为据林纾所言,“真人盖知用心则背道,助天则伤生,故有所不为”[5](P831),秦观自己也说:“心本无说,说之非心也。”[5](P833)但是这种有为,比“道家之神仙”“佛氏之缘觉”已经远过之,因而被秦观“择其言之雅者,书而记之”[5](P826),可见秦观对所记魏景之论,基本上也是认可的。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秦观对佛教心学的认识上,他在《芝室记》中借浮屠之口说“心之本体,明白空洞,实无一毫可得而有”[5](P1232),尽管秦观对浮屠之论谦虚地说“余未尝读佛书,固不知所论中否”[5](P1233),但实际上秦观并非不懂,林纾评论说:“浮屠之言,盖谓心自心,物自物。所谓善想者,以芝生适在庐墓之时。芝本无情,而自庐墓之善想者触之,即据以为瑞:由己生耳。譬如为不善者,已蓄恶情,果有不祥之物适当其前,人即以为此恶情之感召也。所谓天下之物皆吾心者,盖谓祥与不祥,皆心造也。果善恶毕寂,情想究空,则芝瑞亦复何有?此即庄子‘彼是俱忘’之义也。少游湛深佛理,能叙僧言,安有不知?不过不欲将产芝之瑞应当面抹杀耳,自是行文应有之例。”[5](P1235)林纾所言甚是,但不论如何,僧道之论是秦观形成心说的资源之一,则是没有疑问的。秦观本身与佛学关系甚深,此不赘述。
四 创作中的词心
从心说来源可知,秦观的心学体系并非架空而来,而是综合诸家之说并结合时代思潮加以发展而成。这种方式本身,对秦观作词时博采众长加以推进自然有所影响。秦观既已知心如此,其作品,尤其是词,想要达到感动人心的效果,也就不能不从这个角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功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既最大限度地融心入词,也最为成功地以词见心。
先看融心入词。首先,将自己的心对象化入词,即把自己的心变为词中审美、思索之对象,如《望海潮》其三:“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1](P8)李攀龙《草堂诗余隽》评价说:“一寓目尽是旅客增怨,安得不归思如流耶?”[1](P10)只说对了一半,归心虽然如流,流水却直到天涯,如“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一般,流水却不以归家为念,因此归心并不能真归,也就是所思不可实现,只能成为一种写作审美对象,而无法在现实中返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秦观将文学创作等同于物,其《送钱秀才序》云:“其凡夫思虑可以求索、视听可以闻见、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娱,文字之乐,等物而已矣。顾何足以殊观哉?渔父有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浊因水而不在物,拘纵因时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复何苦窃窃焉随余而隘之哉?”[5](P1271)虽是在为别人质疑他“无特操”做辩护,但也代表了秦观自身对“歌酒之娱,文字之乐”的看法,这主要体现在其词的创作上。
其次,在词中为景物立心,将景物之心所生发出来的情思娓娓道来,直接的如《秋词》其二:“西风莫道无情思,未放芙蓉取次开。”[5](P1476)间接者更多,如“东风暗换年华……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1](P8)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为万物立心的同时,其实就是以不合现实情理的推测来暗示出人之心,如《水龙吟》“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1](P15),《野客丛书》记载程伊川认为此句亵渎上天,实则不懂词,《草堂诗余》云:“天也瘦起来,安得生致?少游自抉其心。”[1](P17)意谓这种推测如果成真,词意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天不知道,所以用“天瘦”的推测,才能表达出世人内心最深处的想法,这就是秦观“自抉其心”的内涵,“其”是指词中之人,而这不正是大多数人的脆弱所在吗?逃不过名缰利锁者读之,无不动心矣。此类甚多,如“无端天与娉婷”[1](P19)等。
最后,将对象化、审美化之心与立心后的景物意象结合起来,似有似无,难以捉摸,使读者之心与作者之心完美对接,如《沁园春》下阕:“风流寸心易感,但依依伫立,回尽柔肠……相忆事,纵蛮笺万叠,难写微茫。”[1](P12)才说寸心,又以伫立宕开,后写闺事,才入正题,又以“难写微茫”结束,正如《草堂诗余》所评:“委委佗佗,条条秩秩,未免有情难读,读难厌。”[1](P14)所评甚是。这在《风流子》中表现得更为全面,该词先从正面自抒“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1](P22),这是指出寸心北随、东逐之伤心,可是转眼又化为风景;下阕从“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1](P22)入手,以“谁念”使自我抒情间接化,故后面紧接着写此恨不绝之情,而以“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1](P22)作结,原来此恨不绝之情,终未亲口说出,只是“拟待”而已。诚如《草堂诗余》所云“东西南北,悉为愁场”[1](P23),但东北乱心是抒情主体先抒情再入景,西南肠断则是借“谁念”切入倾述对象后先写景再抒情,最终都归于“欲说还休”,既互补又完整。无论是先抒情再入景,还是先写景再抒情,这种抒情写景的方法,跟秦观对“心”的双重认定有关。秦观之“心”除了指人心之外,亦含有中心之意,故其创作,每有以写景叙事为周围,而中心自出之处,显得似有似无,蕴藉含蓄。
再看以词见心。这其实涉及一个根本问题:秦观的心说对其各类创作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为什么在词上最为成功呢?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秦观心说与词的文体属性最为适配。秦观在表达“心之真在”时,并没有给出一个概念化的僵硬定义,这与词体本身的开放性一拍即合,而不用像诗文那样一定要传达出某种情志、主题。如《捣练子》:“心耿耿,泪双双,皎月清风冷透窗。人去秋来宫漏永,夜深无语对银钅工。”[1](P151)《草堂诗余隽》卷二评价说:“泪随心生,凄其之景已见;至夜深无语,则幽思之情更切矣。”[1](P152)所云甚是,全词起首就写心事却不说是什么心事,后面依次引出泪、泪眼所观之景,由近及远,最后回到“夜深无语”的静态,似乎把心事越推越远,实则使“幽思之情更切”,这就是秦观词的艺术技巧与艺术效果。如果按照诗来写,“卒章显志”,如《满江红·姝丽》以“谩从今、一点在心头,空成忆”[1](P168)结尾,就被《草堂诗余续集》评为“太露,太急”[1](P169),而把顺序略作调换,如《忆秦娥》“空相忆,纱窗月淡,影双人只”[1](P176)就会显得“结语简隽”[1](P177)。当然,卒章显志也有成功的词作,如《画堂春》末尾的“无限思量”[1](P172),但该词主要出彩在写景状物上,尤其是“杏花零落燕泥香”之句,已为前人定评,而“无限思量”不过是起到自然引出而又没有像“空成忆”那样喧宾夺主的作用,诚如《类编草堂诗余》卷一所引《古今词话》之评:“至于‘香篆暗消鸾凤,画屏萦绕潇湘’(4)此二句引用略有出入,秦观原句作:“香篆烟消龙凤,画屏云锁潇湘。”(《淮海居士长短句》,第172页)比较而言,原句更入微。二句,便含蓄‘无限思量’意思。此其有感而作也。”[1](P173)所言甚是,其中“有感而作”更是指出该词与诗之同构思的原因所在,其实这是很危险的,稍一过头,就会刻露。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秦观词并非真没有情志主题,而是通过词心,将其揉进字句、景物、韵律之中,使词达到“心之真在”的境界,虽“不可以传”,却知词心已寄寓其间,这是以词见心的奥秘所在。因此,如果没有诗赋文的发展,没有秦观自身的诗赋文创作成就,秦观词也很难抵达词心境界。这里以秦观自身的诗词创作为例略加说明。秦观《调笑令》十首,都是先诗后曲词,其中诗主要叙述女子事迹,曲词则接着诗意展开。诗的叙事至末句达到高潮,曲词则直接由高潮而起,如第一首写王昭君,诗曰:“汉宫选女适单于,明妃敛袂登毡车。玉容寂寞花无主,顾影低徊泣路隅。行行渐入阴山路,目送征鸿入云去。独抱琵琶恨更深,汉宫不见空回顾。”[1](P111)从和亲写到王昭君出塞,路上所见,直到心底所思,可谓由外及内,渐中靶心。而曲词则相反,它是这样写的:“回顾,汉宫路,捍拨檀槽鸾对舞。玉容寂寞花无主,顾影偷弹玉箸。未央宫殿知何处?目送征鸿南去。”[1](P111)起首承接诗心,只不过并不是像诗歌那样层层递进,而是层层隐去,直到把靶心重新放回欲说还休的意象中。因此,如果说诗是由客体向主体进发,直达心曲,那么曲词就相反,是由主体向客体隐去,直到蕴藉其中。秦观此类创作还有《灞桥雪》《曲江花》《庾楼月》和《楚台风》等。总之,《调笑令》的诗词转换,使秦观更从容地体现词心,也暗示了中国文学后期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