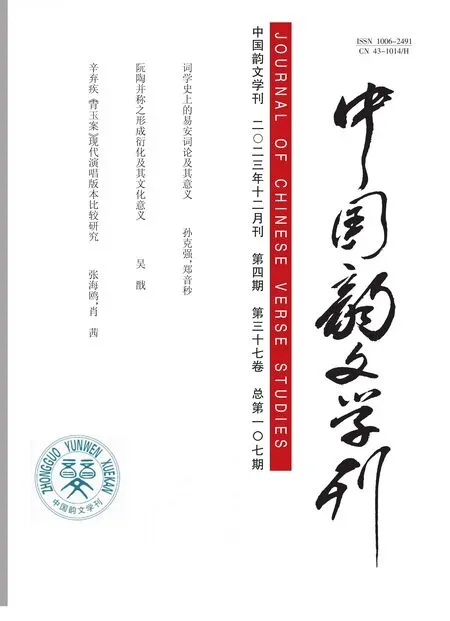从恐惧到依恋:唐宋诗人的湖湘印象变迁
谢安松,李 倩
(1.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2.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在人文地理学中,地方是被赋予意义的空间。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地方性,独特的自然山川、文化底蕴往往成为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关键因素。而地方与人之间往往有着特殊的情感关联。人们对于地方的情感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爱与怕。“爱”即地方依恋,“怕”即地方恐惧。(1)参宋秀葵《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73页。然而人们对于一个地方的印象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转移会逐渐发生变化。而“湖湘”(2)按,本文所探讨的“湖湘”范围为今之湖南地区。唐代主要包括江南西道的岳州、朗州、辰州、潭州、衡州、邵州、永州、郴州。宋代包括荆湖南路,加上荆湖北路的澧州、鼎州、岳州、辰州、沅州、靖州。作为一个特有的地方,唐宋时代集中了大量外来流寓诗人,其中唐代246人,北宋202人,南宋296人(3)参黄仁生、罗建伦校点《唐宋人寓湘诗文集》,岳麓书社2013年版。。他们或因仕宦,或因贬谪,或因避乱,构成了湖湘文学的创作主体。唐及北宋寓湘诗人以贬谪诗人最为著名,南宋则以迁居、仕宦诗人尤为突出。而在唐宋流寓诗人眼中,他们对于湖湘亦有着不同的地方印象。唐宋流寓诗人眼中的湖湘印象由地方恐惧逐渐转变为地方依恋,历经了六百余年。
历来的湖湘文学研究中,李德辉先生论及了唐代湖南的交通与文学(4)参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342页。,周建军先生探讨了唐代荆楚流寓诗歌的哀怨主题(5)参周建军《唐代荆楚本土诗歌与流寓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170页。。以上两先生均为研究湖湘地方情感提供了启发,然而均没有从人地关联的角度探讨唐宋湖湘流寓诗人眼中的湖湘印象。唐宋湖湘流寓诗人眼中湖湘地方印象的关联与变化,反映了人、地之间的密切关系。以下便从人地关系着眼分析唐宋流寓诗人的湖湘地方印象演变过程及其原因。
一 地方恐惧:唐代寓湘诗人的湖湘印象
唐代湖湘集中大批流寓诗人,他们或是贬谪之身,或入幕之人,或落第之人。其中贬谪诗人尤为著名,如褚遂良、张说、令狐楚、吕温、戎昱、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等皆贬谪于此。而大诗人孟浩然、杜甫、李白等皆曾流寓此地。人生的失意,加上环境的陌生,使得他们对于湖湘多有地方恐惧,贬谪诗人表现尤为突出。即便非贬谪诗人亦多表现出地方排斥。湖湘地方之远往往使得寓湘诗人产生怀乡念阙之悲。湖湘气候之卑湿、风物之陌生使得寓湘诗人颇为恐惧。而湖湘经济文化的落后亦使得寓湘诗人颇为不适。
首先,湖湘地理上与京城、故乡的遥远距离加重了地方排斥。姜斐德先生指出:“对于政治流放者而言,这一地区(潇湘)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是地理上和心理上与京城的遥远距离。”[1](P2)因为湖湘地方之僻远,故而诗人们时时怀乡念阙,透露出对于地方的排斥。这在贬谪诗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唐代湖湘地方偏远、经济落后,多着放臣。滕宗谅谓“李唐恢宇,享祚甚宏远,岳去长安尤僻在,当时名贤辈出,能至此者,率自迁谪而来”[2](P188)。唐代贬谪湖湘诗人常常苦于湖湘之远。吕温被贬衡州,作诗云“惟惊望乡处,犹自隔长沙”[3](P4174))。北望长安,尚有长沙阻隔,可见诗人怀乡而不得归的地方排斥。刘禹锡谪居朗州,称“郁郁何郁郁,长安远于日。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4](P408)。“长安远于日”极写长安之远,而其“终日念乡关”便是因为对于朗州的不适应。即便非贬谪诗人对于湖湘地方都有一种“天涯”之感。顾况客居湖南,作诗云“鸣雁嘹嘹北向频,渌波何处是通津。风尘海内怜双鬓,涕泪天涯惨一身”[5](P75)。顾况称湖南为“天涯”,而对于湖湘极为排斥,故而想着抛印绶而归隐家乡。
其次,“长沙卑湿”环境加重了地方恐惧。人的恐惧缘于环境的威胁性。段义孚先生认为:“心中的恐惧,除了病理情况下,其根源大都在外在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具有真正的威胁性。”[6](P4)所谓“地方恐惧”主要包含对自然的恐惧,包括自然灾害、恶劣的气候、洪水、干旱等;对人文环境的恐惧,包括战争、暴政、种族歧视等。[7](P70-73)唐代湖湘流寓诗人由于心理的排斥加上自然环境的陌生,使得他们对于湖南地理环境怀有恐惧。他们对于湖湘的印象多为瘴疠、卑湿之地,充满隐忧。
湖湘之地气候卑湿,来到此地的诗人对湖湘多充满了地方恐惧。唐代送人往长沙已体现出深深的地方恐惧。如薛能称“炎方好将息,卑湿旧堪忧”[3](P6470)。王建称“见说长沙去,无亲亦共愁。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8](P190)。不管是贬谪还是为官,唐人都对于长沙充满排斥。而这种地方恐惧尤其体现在湖湘贬谪诗人之中。永徽(650—655)中,褚遂良谪潭州,称“潭府下湿,不可多时。深益愦悴,况兼年暮。诸何足言,疾患有增,医疗无损”[9](P101)。褚遂良谪潭州因为年老不堪长沙之卑湿而患病,故而增加了对于长沙的地方恐惧。而开元(713—741)间张说谪岳州,称“长沙卑湿地,九月未成衣”[10](P398),意致哀恻。乾元(758—760)中贾至谪岳州送人往长沙,亦称“长沙旧卑湿,今古不应殊”[3](P2595)。元和(806—820)中刘禹锡谪居朗州,作诗云“邑邑何邑邑,长沙地卑湿”[4](P408)。妻子薛氏去世,更加深了他对湖湘地方的恐惧感。
而非贬谪的湖湘诗人,亦感叹湖湘之卑湿。孟浩然湘中寄友,称“长沙饶瘴疠,胡为久留滞”[11](P114)。大历中杜甫避乱湘中,称“春生南国瘴,气待北风苏……爽携卑湿地,声拔洞庭湖”[12](P1976)。杜甫称岳州“南国瘴”“卑湿地”,便见出不适之感。戴叔伦官湖南转运使,亦称“楚乡卑湿叹殊方,朋鸟赋人非宅已荒”[3](P3094)。即便是湖湘本土诗人,同样感叹长沙之卑湿。如邵阳人胡曾称“故乡犹自嫌卑湿,何况当时赋朋鸟人”[3](P7422)。
第三,人文环境陌生导致地方排斥。蒋寅先生指出:“人离开乡土流寓异地,难免会有不能融入当地生活的隔阂感。”[13](P20)湖湘经济文化的落后,使得唐代寓湘诗人难以产生地方认同。同时由于湖湘与寓湘诗人家乡、京城的差异,使得他们产生了地方排斥。
湖湘经济文化的落后使得唐代寓湘诗人倍感不适。张说贬岳州,苏颋以为“沦滞于遐方”。张说则称岳州为“水国”,如“水国何辽旷,风波遂极天”[10](P395),“水国生秋草,离居再及瓜”[10](P389),体现出一种文化排斥。刘禹锡谪朗州,作《采菱行》云“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4](P342)。语言的陌生、地方的偏远加重了诗人对于湖湘的地方排斥。而湖南之地,即便是潭州亦因落后而让人深感不适。戎昱送人知长沙而称“虽之桂岭北,终是洞庭南”[3](P3021),告诫友人“慎勿滞湘潭”。诗人以为长沙虽然在岭北,但是却在洞庭以南,从中透露出对于长沙落后的排斥。大历中韦迢称潭州“小郡海西偏”而“去留俱失意”[3](P2908),透露出潭州经济的落后。潭州尚且如此,南方诸州自不必说。
而湘中风物的陌生亦加强了寓湘诗人的地方恐惧。张说称岳州“物土南州异,关河北信赊。日昏闻鸺鸟,地热见修蛇”[10](P389),又称“湖阴窥魍魉,丘势辨巴蛇”[10](P414)。从张说的描述中可见出其对于岳州风物的恐惧心理。杜甫避乱湘中,称“潇湘水国傍鼋鼍”[12](P2039)。“鼋鼍”,汉族神话传说中是指巨鳖和猪婆龙。杜甫的异物描绘显示出与湖湘的疏离。而柳宗元谪永州,自云:“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14](P801)柳宗元对于“蝮虺大蜂”“射工沙虱”的描绘,可见对于永州的地方恐惧。
二 人地和谐:北宋寓湘诗人地方印象的变化
北宋湖湘之地集中大量外来流寓诗人,达到202人。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诗人基本为贬谪诗人。诸如刘挚、蒋之奇、沈辽、刘攽、张舜民、孔平仲、吕陶、范纯仁、刘奉世、范祖禹、秦观、邹浩等皆贬谪于此。赵抃、米芾、孔武仲等曾仕宦于此。北宋时期,湖湘流寓诗人对于湖湘的地方排斥部分承袭唐代寓湘诗人。然而相对于唐代,北宋湖湘流寓诗人的地方恐惧色彩渐趋减弱。仕宦诗人多以审美之眼欣赏潇湘山水,贬谪诗人则寄情潇湘山水以排解哀怨。
(一) “长沙卑湿”的惯性表达与地方恐惧的弱化
北宋诗人对于湖湘的印象仍然带有地方恐惧。嘉祐中梅尧臣送人知永州,作诗称“畏向潇湘行,不入洞庭去。鞍马踏关山,衣裘冒霜露。零陵三千里,楚俗未改故”[15](P1275)。“畏向潇湘行”便可见出梅尧臣对于潇湘的印象。而其原因则是“零陵三千里,楚俗未改故”,即零陵距离京城太远,同时此地经济文化落后,气候恶劣。治平中刘敞、刘攽兄弟送人知湘乡,对长沙亦充满了恐惧。刘敞云:“春风洞庭水,殊俗楚人家。回首伤卑湿,知君发易华。”[16](P582)刘攽亦云:“俗传鸮似朋鸟,仙化舄为凫。卑湿加餐饭,弦歌岂壮图。”[17](P114)然而梅尧臣、刘敞、刘攽的“长沙卑湿”表达实际上是一种惯性表达,并没有实际体验。
而在贬谪诗人眼中,对于湖湘的风土虽有排斥,但恐惧有所减弱。北宋贬谪诗人多客观表达湖湘气候暑热。元丰中,沈辽谪永州,称“夷天九月尾,秋气殊未肃”“瘴山旱无雨,憔悴兹不足”[18](P547)。元丰中,刘攽谪衡州,潇湘风土差异往往加重了诗人的地方排斥,如“渐南风土异,伤早岁时催”[17](P109),“南国秋常暑,凉风起自今”[17](P112)。政和中,唐庚贬惠州过武陵,作诗称“路入离骚国,江通欸乃村。垣墙知地湿,草木验冬温”[19](P144)。诗人只是客观描述长沙之卑湿,恐惧与伤感已减弱。然而即便是此种表达在北宋湖湘流寓诗人中也并不占据主流,多数湖湘贬谪诗人实现了与湖湘山水的和谐共处。
(二)寻求家乡相似点到人地和谐
地方排斥往往是因为流寓之地与家乡、京城的差异而产生的。京城的繁华、对家乡的熟悉使得诗人产生依恋。然而唐代流寓诗人对于湖南始终持有一种隔阂,很难产生认同。北宋寓湘诗人则积极寻找湖南与家乡的相同之处,从而逐渐产生地方认同。元丰中孔武仲自湘潭北归,其《自君山还岳阳》云:“云山深处望潇湘,岩石沉沉已夕阳。却整舟帆凌浩渺,回看城郭似家乡。”[20](P148)在孔武仲眼里潇湘为云山深处之所在,而其“城郭似家乡”。唐代寓湘诗人是断然不可能如此说的。元丰中张舜民谪郴州,作《温泉》诗回忆长安华清宫下的温泉水,“岧峣华清宫,下有温泉水。绣岭络千门,玉莲喷九蕊”,从而想到“忽惊郴岭下,和暖雅相似”[21](P9708)。诗人将长安之温泉与郴州之气候相联系,并称二者相似,可见诗人与郴州的和谐共处。虽然类似积极寻找湘中风物与家乡联系的并不多见,但已经与唐人截然不同。
(三)寄情潇湘山水到人地和谐
蒋寅先生指出:“即便处于失意状态中,只要心理能够调适,用超脱的态度应物,同样也能与地域相融。”[13](P21)相比于唐代,北宋湖湘流寓诗人积极调整心态,他们对于湖南地方恐惧渐渐减弱,即便是贬谪诗人亦是如此。他们多从审美角度欣赏湘中山水,实现了人地的和谐。
在仕宦诗人眼里,湖湘俨然是个美丽之所在。元丰中,孔武仲知湘潭县,其《代简答次中见留》称:“诗夸洞庭湖,盖举其粗尔。自此稍南行,更有潇湘水。潇湘如此流,浅深清见底。”[20](P77)孔武仲以居住经验告诉友人前人诗里描绘洞庭湖并不细致,而其南的潇湘风景更加迷人。而在贬谪诗人眼里,对于潇湘的地方恐惧亦渐趋淡化。他们转而欣赏潇湘山水以排解哀愁,实现了人地的和谐。熙宁中,刘挚贬衡州盐仓,却十分喜欢楚中的山水,故而频频游览,其自云“于此登临称谢公,湘南奇观欲吟穷”[22](P411)。刘挚在衡州多与同僚游楚中名胜,十分自得,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贬谪身份,称“心甘水石忘羁宦,耳冷弦歌叹土乡”[22](P403)。元丰中沈辽谪永州,后来忆及潇湘称“三年潇湘客,不厌潇湘游。二水相会处,下有白苹洲。洲上多美竹,出没清浅流”[20](P572)。沈辽将潇湘描绘为一个颇为美好的地方。绍圣(1094—1098)中,范祖禹谪永州,作诗云“京华驿候远,楚越山川分。心驰桂江水,梦绕苍梧云。夕与木石居,朝游麋鹿群”[23](P107),表现出对于潇湘山水的向往。崇宁(1102—1106)中,邹浩谪永州,潇湘道中作诗云“极目潇湘漾碧澜,万峰插水巧弯环。我来日日忘机坐,却爱真山似假山”[24](P245)。邹浩以贬谪之身过潇湘,却关注潇湘的风景。邹浩居永州乐于游山,如“潇湘之胜渺无穷,尽入西轩一览中”[24](P249),转而称赞潇湘之美景。北宋湖湘贬谪诗人通过关注潇湘风景从而淡化了迁谪之悲,转而实现人地和谐。而到南宋,由于诗人身份的变化与湖湘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湖湘的印象最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 地方依恋:南宋中期以来诗人湖湘印象的新变
北宋湖湘流寓诗人只有202人,南宋则增至296人。而仕宦、迁居、游历诗人为南宋湖湘流寓诗人的主体。诸如胡安国、胡寅、胡宏父子,张浚、张栻父子迁居于此。杨万里、张孝祥、项安世、陈傅良、赵蕃、萧德藻、李曾伯等仕宦于此,姜夔、戴复古、徐玑、徐照等游历于此。南宋中期开始,流寓诗人对于湖湘之地十分向往,主要便是对于湖湘自然风景与文化底蕴的归属感。他们对于湖湘的地方印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表现主要有二:文化印象上,从对“荆蛮”的排斥转变为对“潇湘为洙泗”的向往;地理印象上,从对湖湘地方恐惧转变到对潇湘山水依恋。
(一)文化向往:“长沙今洙泗”
地方依恋由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个维度构成,地方依赖是人与地方之间的一种功能性依恋,而地方认同是一种情感性依恋。[25](P70-77)地方依恋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对故乡和家的依恋;二是对宗教圣地的朝拜;三是对自然风景的痴迷;四是对文化底蕴的归属。[26](P103-104)南宋流寓诗人眼中湖湘印象的改变即体现为对于湖湘学术以及潇湘风景的向往。
文化印象上,唐及北宋湖湘贬谪诗人多视湖湘之地为“荆蛮”,极尽排斥。北宋诗人湖湘地方多以中原之眼光进行审视,故而往往斥之为“荆蛮”。元丰中刘攽谪衡州,称“无人同此酒,叹息滞蛮荆”[17](P91)。而沈辽流放永州,以“夷”“蛮”称永州,如《春日行》云“何况羁栖落荆蛮”[18](P524)。因为心境与文化的差异,沈辽对于永州有一种隔阂,如诗云“夷山邈无际”[18](P543),体现出诗人的地方排斥。南渡初期寓湘诗人仍然称湖湘之地为“夷”“蛮”。建炎间,陈与义避乱湘中,自云“居夷更觉中原好”[27](P308),“居夷惊有苗”[27](P347)。南宋中期以来,湘中印象则渐渐转变为对“潇湘为洙泗”的向往。湖湘仕宦诗人对于湖湘学术极为赞许。淳熙(1174—1189)间,赵蕃官湘中,其称:“去年五溪归,泊家长沙国。长沙今洙泗,不但谈贾屈。”[28](P69)诗人对于长沙印象转为“长沙今洙泗,不但谈贾屈”。所谓“洙泗”代称孔子及儒家。如今长沙学术颇盛,不再如唐代贬谪诗人回归屈贾。后来赵蕃忆及湖湘称“我爱长沙国,全如洛与伊”[28](P180),即表现出对于湖湘学术的许可。而过湘之人对于湖湘之学术亦十分向往。乾道间,范成大过衡州石鼓书院,称“俎豆弥文肃,衣冠盛事多。地灵钟杰俊,宁但拾儒科”[29](P168)。淳熙间,项安世过衡州,称“乐哉湘水是吾师”[21](P27372)。嘉定(1208—1224)中,刘克庄过衡州石鼓书院,称“石鼓名天下,州庠画不如……恨余非楚产,来借一房居”[30](P383)。从各位诗人的诗中便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湖湘学术的向往。
(二)山水依恋:“不到潇湘岂有诗”
南宋中期湖湘流寓诗人的湖湘地方印象转变还表现为对潇湘自然风景的痴迷。地理印象上,唐代寓湘诗人对于湖湘的卑湿有一种恐惧心理。北宋寓湘诗人对湖湘之暑热亦时有排斥。而到南宋中期则转变为对湖湘山水的依恋。乾道二年(1166),张孝祥自静江北归过湘江,作词云“吴山楚泽行遍,只欠到潇湘”[31](P1241),可见对于潇湘风物的向往。乾道三年(1167),张祁渡湘江,亦感叹“春过潇湘渡,真观八景图”[32](P1488)。张祁为张孝祥之父,乾道三年(1167)随张孝祥知潭州。张祁诗中潇湘已经转为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而“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则反映了长沙的繁华。而张栻有和诗云“斋舫凌烟浦,云屏入画图……湘中无限景,赋咏继三都”[33](P771),亦称赞湘中之美景。淳熙十五年(1188),赵师侠舟泛潇湘,称赞“溪山佳处是湘中,今古言同”[34](P2079)。其词中多以画称潇湘,如“八景潇湘真画”[34](P2093),“一片潇湘、真个画难成”[34](P2095)。潇湘已然成为人们向往之地。嘉泰四年(1204),陆游回忆旧游亦谓“挥毫留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35](P3474)。晚年陆游家居绍兴,时时以景物之美指称“潇湘”,甚至以之与故乡媲美,如“剡曲稽山是故乡,人言景物似潇湘”[35](P1758),“镜湖清绝似潇湘,晨起焚香坐草堂”[35](P3947)。可见在陆游心里,潇湘之地已经是一个美丽的存在。南宋后期,人们对潇湘之地的印象大为改观。嘉定末至端平间,戴复古两游湘中,作诗云:“荆楚一都会,潇湘八景图”[36](P34),“心怀屈贾千年上,身在潇湘八景间”[36](P173)。此二诗均表现了对于潇湘景物的喜爱。
四 唐宋湖湘流寓诗人地方印象变化原因
唐宋流寓诗人眼中的湖湘印象经由地方恐惧到地方依恋历经了六百余年。从流寓诗人湖湘印象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湖湘经济文化逐渐向好发展。而唐宋湖湘流寓诗人地方印象变化的原因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一)唐宋贬谪政治与湖湘贬谪文人心态
唐代湖湘流寓诗人的地方恐惧与唐代的贬谪制度密切相关。湖湘贬谪诗人因为对于贬谪的恐惧,故而往往加深了地方恐惧。唐代湖湘之地聚集大量流寓诗人,尤其以贬谪诗人最为集中。尚永亮先生认为:“至于唐、宋两代逐臣,亦多谪居荆湘之地。”[37](P28)而据周建军《唐代荆楚流寓诗人考》,唐代流寓湖湘30位诗人中有14人为贬官身份[38](P128-137),占比约47%。其中贬谪诗人多为著名诗人,诸如王昌龄、贾至、张说、柳宗元、刘禹锡等。而唐代贬谪制度的严酷则成为谪湘诗人情感悲凉之主要原因。唐代在政权更迭、党争酿祸与宦官专权过程中,统治者或专权者将政敌或杀或贬,故而湖湘贬谪诗歌情感悲凉。尚永亮先生指出:“处置严厉时,对重罪官员往往先行贬逐,既而赐死于途。或诛杀于贬所。”[39](P110-111)即便未被杀,亦有很多诗人卒于湘中贬所。诸如崔成甫、吕温等卒于湘中加深了寓湘诗人的地方恐惧。
北宋湖湘之地尚集中大量贬谪诗人,而到南宋湖湘已非贬谪重地。宋代贬谪惩罚程度较唐减弱。宋代“重文轻武”,诗人地位颇高,极少出现杀文人的情况。《宋史·曹勋传》载徽宗言于曹勋曰:“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40](P11700)即便被贬亦无性命之忧,故而宋代谪湘诗人内心的恐惧较之唐代要少很多。而贬谪往往是为了让诗人反省,并非为了排除异己而将其置于死地,且贬官之待遇相对于唐人要好很多。杨竹旺称:“唐朝对于被贬的官员,无论是政策制定、赴贬前与赴贬途中的执行、在贬所的待遇,乃至叙复规定,都极其严苛残酷。而两宋对被贬官员的权利有一定的保障,待遇同前代相比要更好。”[41](P66)这就是宋代贬谪诗人能对湖湘地方恐惧减弱,进而与湖湘山水和谐共处的根本原因。
(二)唐宋湖湘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
唐代,湖湘之地尚是蛮荒之地,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尚永亮先生称:“从地理的重要性看,自汉至唐,荆湘多数地域尚未开发,较之中原地区相对蛮荒、落后,故成为朝廷贬官时的首选之地。”[37](P28)其中湖湘经济文化尤为落后。李德辉先生指出:“唐代湖南被视为汉文化的南部边缘,真正夷夏分界线在五岭,湖南则是夷夏结合部,体现着中原文化与南蛮文化的混一状态,且蛮族文化占据主导地位。”[42](P318)
北宋湖湘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其人口持续增长。北宋后期惠洪《送廓然》即称:“长沙古都会,何以冠荆楚。但曰财富强,山水最佳处。那知号大藩,实以英俊聚。”[43](P1043)惠洪认为长沙“财富强”“山水佳”,显示出北宋时湖南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唐代天宝元年(742)湖南才95万余口。而到北宋崇宁(1102—1106)年间增长至260余万口。到南宋嘉定(1208—1224)间,湖南共有人口720多万。[44](P15-16)人口的增长反映了北宋以来湖南经济的发展。
建炎南渡后,湖湘经济文化迎来了大的发展。胡安国、胡宏、胡寅讲学衡山,张栻、朱熹讲学岳麓书院,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嘉定末真德秀即指出:“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此邦之士,登门墙、承謦欬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45](P617)透过真德秀的笔端可见出他对于湖湘学术、人才的赞许。宝庆、绍定间魏了翁对于湖湘的印象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姑考诸近世,倡明正学以绍孔、孟之传者前后迭出,率在湖湘间,至于登朝著、仕州县、奋科第者,又不可胜数,然后知柳、欧之言固不尽然,抑亦风气有时而变移邪!”[46](P234)魏了翁指出“抑亦风气有时而变移”恰好反映了湖湘文化从唐到南宋的发展。同时由于湖湘距离前线尚远,相对安定的环境促进了湖湘经济的发展。荆湖南路在南宋以来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至嘉定十六年(1223)人口达到125万户,仅次于两浙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淳熙末周必大判潭州,称潭州为“长沙巨镇”[47](P457),“大藩之名不一,南楚为雄”[47](P466)。可见淳熙、绍熙间潭州之地位颇高。张祁称“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戴复古称长沙“荆楚一都会”,便可见一斑。经济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宋诗人对于湖湘的印象。
(二)唐宋湖湘流寓诗人籍贯的差异
唐代寓湘诗人对于湖湘的地方恐惧缘于卑湿气候的影响。唐人张谓称长沙“郡临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衍时序”[48](P3809)。张谓称长沙“郡临江湖,大抵卑湿”“地边岭瘴,大抵炎热”颇为客观。而之所以唐代寓湘诗人排斥湖湘地理,与寓湘诗人,尤其是谪湘诗人中多北人有密切关系。据周建军《唐代荆楚流寓诗人考》,唐代共有96位著名诗人流寓荆楚(即今湖北、湖南),其中流寓湖湘30人。[38](P128-137)而流寓湖湘30位诗人中,籍贯为北方的共计21人,占比70%。来到湘中的北人或因流贬,或因避乱,或为入幕,或因落第漫游,多失意之人。加之对于南方气候的不适应,故而往往生发出卑湿之叹与地方恐惧。然而北宋寓湘诗人多为南方人,尤其是贬谪诗人中多以南人居多。据笔者统计北宋流寓湖湘诗人主要有180人。留下文集较为重要的有20人,而其中17人均为南方人,占比85%。诸如刘攽、孔平仲、孔武仲、沈辽、华镇、吕陶、范纯仁、刘奉世、范祖禹、秦观、邹浩、陈瓘、曾纡、范致明等贬谪诗人皆为南方人。这使得北宋流寓诗人对于湖湘的地理排斥大大减弱。而南宋由于政治的影响则全为南人,由于了解的加深转而欣赏湖湘风景。
总而言之,唐宋湖湘流寓诗人对于湖湘印象的变化与贬谪政治、湖湘经济文化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地方发展程度、诗人身份的变化引起地方与情感关联发生变化。唐代湖湘为贬谪重地,加上经济文化的落后,使得在湖湘之地的流寓诗人对于湖湘充满了地方恐惧与排斥。北宋湖湘仍然集中了大量贬谪诗人,贬谪诗人对于湖湘的地方排斥依然存在。然而北宋贬谪惩罚力度远不及唐代严酷,而谪湘诗人以南人居多,这使得他们对于湖湘的地方恐惧减弱。他们通过欣赏山水,进而逐渐实现人与地的和谐。到了南宋中期,湖湘之地非贬谪重地,湖湘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仕宦诗人眼中的湖湘印象转为山水、文化依恋之地。人与地之间的情感以诗为纽带,而情感变化的关键因素便是地方的发展与诗人身份变化。唐宋湖湘流寓诗人对湖湘的印象变化,反映了湖湘经济文化逐渐向好发展。透过诗人对地方印象的变化可以看到湖湘之地在宋代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