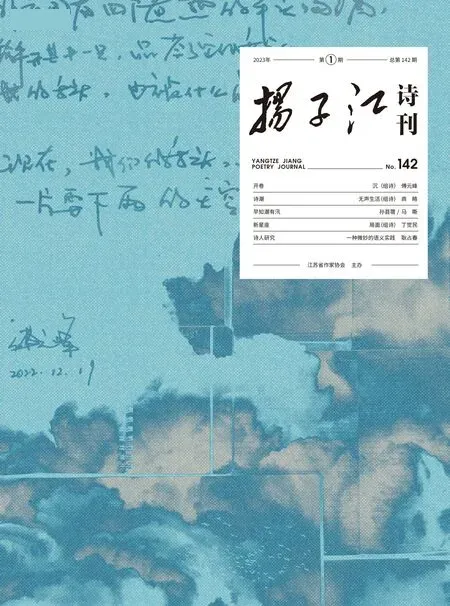自然伦理的诗性建构
——以十位诗人的自然写作为中心
马春光
新世纪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和西方生态理论的大量引介,中国的自然生态文学迎来了繁荣。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从不同的维度展开自然写作实践,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异常丰富且颇具深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少君、北乔主编的《群峰之上——自然写作十家诗选》(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年版)可以说是近年来自然生态诗歌写作实绩的一次集中展示,《诗选》收入沈苇、胡弦、李元胜、李少君、陈先发、阿信、剑男、林莉、北乔、冯娜等十位诗人的作品,这些诗歌共同诉诸对自然伦理的诗性表达,构成了自然书写的“诗歌盛宴”。十位诗人的诗歌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书写基点,集中传达了新的自然价值观念。基于新的自然伦理观念,诗人的写作面向和抒情姿态发生了转变,新的诗歌审美特质得以滋生。“诗性”地传达自然生态伦理,是十位诗人自然写作的共同审美标尺,也是其对当下及未来的自然生态诗歌的启迪。
一、地域书写与自然伦理的凸显
李元胜认为,相对于古代社会,现代社会面临着“自然的萎缩”,我们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也部分丧失了在自然中获取启发和想象力的能力。“自然的萎缩”是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总体性概括,当代诗歌的自然书写首先在具体的地域书写中感知自然的残缺与消逝,探寻自然伦理的诗学路径。
在《罗布泊》一诗中,沈苇痛惜于“罗布泊在死去”的现实,曾经的中国第二大咸水湖如今成为荒无人烟的大片盐壳。“游移的湖——/不再游移,不再起伏、荡漾/沙漠深处的走投无路/大荒中的绝域/留下一只沧桑、干涸的耳轮。”在现代人类活动的背景下,一些湖泊正难以逆转地走向消亡,对人类关闭了“凝视”与“倾听”的路径,这在李松涛《拒绝末日》、于坚《哀滇池》等1990年代的生态诗歌中得到了激烈愤慨的抒写。沈苇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弃绝了强烈情感的直接抒发,在貌似客观的形象抒写中洞见生命共同体的真谛,这“沧桑、干涸的耳轮”是“时光的一部分、我们的一部分”,人类和自然之间存在着隐秘而恒久的联系。沈苇敏锐的诗性直觉和灵动凄婉的语言,使其在传达自然伦理价值观念的同时,具有强烈的审美冲击力。美国自然文学的先驱大卫·梭罗曾深情地说,“湖泊是自然景色中最美也是最富表现力的一部分。它是地球的眼睛;凝视湖水,人能够衡量出自己本性的深度”。①[美]大卫·梭罗:《瓦尔登湖》,王家湘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沈苇的长诗《喀纳斯颂》在对新疆喀纳斯湖的深情凝视中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突然,人的史诗/在大自然面前变成了短章/阿尔泰史诗,是山的史诗/石头的史诗,树的史诗/也可能是鱼的史诗:/一条哲罗鲑和它后代们的史诗//风景无言。它的无言是无言的收藏/群山无言。它的无言是无言的雄辩。”诗人由对自然风景的深度凝视,体悟到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微弱,这虽是老生常谈,实则包蕴着自然伦理价值的转换。自然的“无言”源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诗性智慧,召唤着后工业时代的人类放弃对大自然颐指气使的态度。
沈苇对“罗布泊”和“喀纳斯”一正一反的书写,彰显了诗人基于独特地域景观的书写策略与价值路径。当诗人面对更细微和具体化的自然地域时,则会在更幽深的路径体悟更具启发性的生态伦理。诗人阿信长期生活在甘南草原,他在《河曲马场》中敏锐而感伤地喟叹,“马在这个时代是彻底没用了”,在漫长的历史中,成群奔跑的骏马、一望无尽的草地、蓝天白云构成了我们对草原的基本认识与想象图景,而在机械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中,“马”因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急剧减少,这无疑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其中隐含着现代机械对自然物种的戕害与挤压,彰显着“全球化”与“原生态”的剧烈冲突。阿信敏锐地意识到时代遽变对边地动物生命的剥夺,同时也深感这一转变对诗人心态和诗歌生态的深刻影响,他的《速度》一诗是对“加速度时代”中诗歌写作速度的关注与反思:“在天水,我遇到一群写作者——/‘写作就是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的速度。’/在北京,我遇见更多。//遥远的新疆,与众不同的一个:/‘我愿我缓慢、迟疑、笨拙,像一个真正的/生手……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里。’//而‘我’久居甘南,对写作怀着愈来愈深的恐惧——/‘我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它们就藏在每一个词的后面。’”
阿信以对诗歌的绝对虔诚抵达了对加速时代的反思,他思考的重心是加速时代中写作本身的异化,写作的神圣性被加速时代冲掉了,阿信的“恐惧”正来自于这种神圣性的丧失。诗歌作为一种“慢”的艺术,正面临着加速度的严重冲击,诗歌写作的快速化、浅俗化背后是诗人主体心态的浮躁。阿信以其敏锐、深刻、虔诚击中了“写作”当下的症结,启发我们重建写作的神圣性和缓慢性,只有这样,文学才不至于被加速度稀释,方能获得反思速度、抚慰心灵的精神力量。
充分发掘地域诗学的书写优势,为当下的自然生态诗歌提供了新的主题与审美可能。通读十位诗人的诗歌作品,我们会发现其中显豁的地域美学特征,如沈苇的新疆、阿信的甘南、李少君的南海、冯娜的云南等,为当下的自然生态诗歌提供了独特的地方性美学标识。在阿信的诗中,“马”这一动物不仅是写实,更构成一种象征和讽喻。在《草地酒店》一诗中,阿信将“游客”与“马”进行精神状态的对比,“只有檐下一众游客表情沮丧如泥。/只有院中几匹马神态安详,静静伫立”。这是对当下“旅游经济”的典型叙写,沮丧、惶迫的众生相背后是紊乱的精神生态,与草原的美丽景色所展示的自然生态极不协调。基于对这种图景的“诗的纠正”,阿信在最后两句中写道:“我也有天命之忧,浩茫心事,/但不影响隔着一帘银色珠玑,坐看青山如碧。”阿信的反讽和理想寄托都是以甘南草原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现状为基础的。出生于云南的白族诗人冯娜倾听云南大地上天人共奏的声响,“在云南 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一种在迷路时引出松林中的菌子/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 让它顺从于井水”,这种地方性语言奇迹般地联通着人与自然万物,谱写着生命体之间的内在和谐。在特定的地域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了天人和谐的自然生态图景,这恰是地方性特有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交融。
二、“自然复魅”与生态伦理重构
自然书写面向浩渺丰富、斑斓多彩的自然世界,优秀的自然诗歌旨在建构人类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相互融合的语言空间,它要求诗人在对自然的凝视与倾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学路径。著名生态美学家曾繁仁认为,生态文明时代自然伦理重建的要义在于“从工业文明时代‘完全’的自然祛魅到生态文明时代‘部分’的自然返魅”,“打破对于人的能力的过分迷信,打破人与自然的对立,部分恢复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与潜在的审美性”。①曾繁仁:《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应有的文化态度》,《生态美学——曾繁仁美学文选》,山东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诗人通过对“自然神性”的体悟与建构重铸自然伦理,“凝视”与“倾听”成为通向自然复魅的诗学路径。
十位诗人对自然保持着热爱的态度,长期浸润于自然之境中,他们得以深入自然的肌理,洞见自然的奥秘。阿信被小草的“生命的语言紧紧攫住”,“聆听其灼热的绝唱”;林莉认为“一株植物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她的《野地》抒写隐秘的自然体验,“雨后,每一根松针都悬垂晶莹的水珠/哦,神隐秘的指尖,湿润、微凉”。自然之物在诗人的笔下闪耀着神性的光辉,这“神性”包蕴着自然的神秘和生命的神圣。这种建立在生命意识基础上的对自然事物的重新认识,是对自然的重新赋魅。北乔在《莲花山,一座巨大的灯盏》一诗中写道,“大地最坚固的肉体/柔化众生的目光/莲花山,以静止/显示人类之外的另一种时间”。在“坚固”与“柔化”的悖论化书写中,莲花山获得了丰富的人性与神性内涵,成为引领人类众生的灯盏。在李少君广为流传的《神降临的小站》一诗中,诗人在空间的逐层推延中抵达“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在“小如蚂蚁的我”和逐层打开的神性自然之间获得了巨大的审美张力。
对于现代世界带来的“自然的祛魅”,沈苇怀着深深的遗憾与创痛,“曾经,我们把自己放得很低,将大自然与神灵同等对待,认为大自然中住满了各种神灵。山是神灵,水是神灵,一花一木都是神灵。大自然的远去意味着神灵的隐匿,神迹的消失带走了亲爱的大自然,也带走了我们对待大自然的谦卑与真诚,带走了人与自然的心心相印”。如果说沈苇是从时间维度谈论自然神性的消逝,那么阿信则从甘南高原的地域层面谈论自然神性的日常化存在,在高原上“遇到的一个人,一座寺庙,一朵花,一处海子,甚或一只无感无知的甲壳虫,都透着神秘或原初的味道。但我坚信,在平凡的人生与这种神性意味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古老而天然的精神通道,某种看不见的庄严秩序。也许,它藏在某种最平凡的日常生活状态之中,经由某种最不起眼的物质而弥散着”。阿信的观点与歌德关于自然神性的说法不谋而合,“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只有把自己提到最高理性的高度,才可以接触到一切物理的和伦理的本原现象所出自的神。神既藏在这种本原现象背后,又借这种本原现象而显现出来”①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83页。。这也启发我们,对“自然神性”的体悟与建构不是自然观的倒退,而是一种面向现代社会的精神与诗学建构。
《诗选》中的诗人善于从日常的“不可见之物”触摸自然的脉络与纹理。譬如,对于“风”,胡弦写道,“我知道风吹动时,比水、星辰,更为神秘”;陈先发写道,“风的浮力,正是它的思想”。陈先发通过对“风”的凝视、倾听与思考,获得了进入自然、与自然深度融合的隐秘路径:“我每个瞬间的形象/被晚风固定下来,并/永恒保存在某处/世上没有什么铁律或不能/废去的奥义/世上只有我们无法摆脱的/自然的伦理”。沈苇在《白杨》一诗中表达了与陈先发相似的伦理认同:“风的起义,使它揭竿而起/风与风、树与树之间/一种无名而沉雄的力/在寻找生与死的裂隙……//越过整齐划一的白杨林带/是风暴的耕地和旷野/呼啸或呜咽,都是/大自然出示的绝对权威。”对“风”的体悟与凝思,成为三位诗人自然写作的切入口,他们从“风”这一日常自然现象入手,在细微处体悟自然,从日常生活中重建自然的“伦理”与“权威”。这种自然伦理更广泛地表现为自然活力的激活、生态乌托邦的建构以及古典自然智慧的拓展。“‘风’的语义场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流动的、循环的、多层面的‘生态系统’,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生存大智慧的生态系统,一个展现了中华古代文明辉煌景观的生态系统。”②鲁枢元:《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第123页。沈苇、胡弦、陈先发等诗作对“风”的凝视与玄思,与中国古代的自然智慧遥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陈先发和沈苇诗句中不约而同的决绝口吻,对自然伦理进行认同的同时隐含着对绝对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质询。
诗选中的诗人通过各具特色的自然书写践行了自然伦理重铸的诗学使命。诗人们消解以往诗歌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秉持“生命共同体”的思维向度与伦理维度,诗歌中抒情主体的抒情姿态发生显著改变。李元胜在《透过云层的阳光》中深刻体认了“我”只是大自然“神秘的编织”中普通的一部分:“所有仍在呼吸的生命/都被纳入神秘的编织之中/我没有其他的线明亮/也并不比它们更重要。”这种体认消解了极端化的人文思想,在生态伦理的思想烛照下拓展了新的审美空间。沈苇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是一个充满悲悯情怀、在世界万物面前保持谦卑的形象,在《自白》一诗中,背离人群、返回旷野的抒情姿态已然清晰可见:“我看不见灰色天气中的人群/看不见汽车碾碎的玫瑰花的梦/我没有痛苦,没有抱怨/只感到星辰向我逼近/旷野的气息向我逼近/我正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然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一个移动的点”。返回旷野,是现代人内心深处异常坚定的一种声音。沈苇诗歌中透射出某种独特的领略自然的“神力”,这是一种难得的精神领悟。体悟到生命个体的卑微,融进浩瀚的星辰和无垠的旷野,正契合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沈苇以自己切身的生命体验汇入这一思想传统,在沉稳笃定的语气中彰显生存智慧。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本土化的思想与诗学资源已经在他们的诗歌中获得了某种创造性、个性化的运用,这对于建构本土化的自然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博物、凝视与生命诗学
诗人们的自然写作植根于长期而深入的自然观察,他们自觉融合博物学的相关知识与方法,形成了兼具自然基础与审美内涵的生命诗学。沈苇认为,“凝视产生‘物哀’和物心合一。当我们观察一种植物时,这种植物也在观看我们,这是主客交融、物我两忘的时刻。在某个忘乎所以的瞬间,通过显在的形态,经由隐喻和象征,我们是可以与植物隐在的神性和神秘性相通的”。陈先发则将凝视提升到诗歌写作本体的维度,“诗是从观看到达凝视”。胡弦强调自然需要被“深度注视,以便它来告诉你它一直忠实的另外的核心。那里,有另外的构造,藏着它情感的地理学”。胡弦的诗对日常事物有非常细腻的感受力,并且时常触及当下生存的某些根本性问题。《蚂蚁》一诗颇能凸显他的诗歌美学,蚂蚁是如此卑微、渺小之物,它并非典型的诗歌意象,胡弦对它的细腻叙述,既彰显了新世纪诗歌愈来愈精细的感受力,同时也体现了诗人洞见生活的反思能力:“一只落单的蚂蚁爬上我的餐桌,仿佛在急行中猛然/意识到了什么,停住,于是有了一瞬间的静止。/在那耐人寻味的时刻,世界上/最细小的光线从我们中间穿过:它把/圆鼓鼓的小肚子/柔软地,搁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上。”《蚂蚁》是典型的“咏物诗”,但如果放在整个中国诗歌的传统中,它则是“非典型”的。这是诗人的自我反思,细腻中浸透着卑微,卑微中又闪烁着光泽,它通向了对日常万物之存在状态的精神审视。《初春》一诗,非常短,可以作为洞察胡弦诗歌肌理的标本:“砖瓦厂里,老旧的拖拉机突然/发出轰鸣,喷吐浓烟,全身关节/喀吧作响,履带/扣紧尚未解冻的地面……/烟囱、枯草、坯房、树枝上的寒霜,都在震动中/猛然醒来。一辆/开始奋力前行的拖拉机,抖落积尘,着手解决/它和世界之间存在已久的问题。”这是一首即兴之诗,同时也是一首彰显雄心的诗。中国诗歌对于春的书写可谓卷帙浩繁,胡弦通过老旧的拖拉机来表现初春的万物复苏,别出心裁。拖拉机彰显的是人的意志,在深层次上是自然的伟大意志,“它和世界之间存在已久的问题”,充满了张力,它暗示了冬的漫长和人们对于春的期待,自然界内部的生命活力呼之欲出。
沈苇的自然书写在“博大”与“渺小”的交错中同时展开。“博大”指向新疆边地广阔浩渺的自然,这种“大”构成诗歌的视域与景深;“小”是指沈苇诗歌触角的精微,这是一种辩证关系。如他早期名作《开度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我俯下身,与蚂蚁交谈/并且倾听它对世界的看法/这是开都河畔我与蚂蚁共度的一个下午/太阳向每个生灵公正地分配阳光。”“交谈”“倾听”体现的态度是平等、尊重,最后一句升华到“生灵”,其实已经蕴涵了一种生态主义的自然观。在这些诗句中,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情感或意志的主宰,而是万物平等。沈苇选择了与自然万物交流的更主动的方式。与一只“蚂蚁”的交谈为我们提供了具象化的细微生命图景,同时也是“内宇宙”向自然敞开的某种象征。“交谈”“倾听”“共度”内蕴着平等化的生命视角,“诗人的情感赋予,敦促着文本对喜悦与艰辛的生命和命运形态的观照,在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局限的同时已有言外之旨,那分明是对普通生命的尊重和生命关怀”①罗振亚:《靠文本的“翅膀”飞翔:沈苇诗歌及其隐含的诗学问题》,《扬子江诗刊》2018年第2期。。这其中伴随着人类面对自然的姿态变化,自然世界由人类感情与意志的附着物转换为被人类欣赏的、平等化的生命个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由主客关系到主体间性的深层转变。“我俯下身,与蚂蚁交谈/并且倾听它对世界的看法”,作为一种自然态度与写作姿态的“倾听”所传达的是一种生态伦理价值观念的转变,自然世界不再仅仅是“我”情感抒发和意志表达的某种背景或依托,而是平等化的生命个体,我们持一种“倾听”与“受教”的姿态。如林莉《自然笔记》中“一次次,我们承接自然之道和恩典”,抑或阿信《对视》中“人类、自然、神灵平起平坐,促膝深谈”,都是一种“凝视”,洞见了自然生命的博大和深邃。
值得注意的是,对自然的凝视与倾听需要持之以恒地对某一地域或某一生态系统保持深度关注。如果没有对自然的“凝视”,那么自然写作的可信度和审美感觉可能会大打折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事情的关键恰恰在于,中国的生态书写由于缺乏有定力的对某一生态链条或生态圈持之以恒的观照,也就无法洞悉那一生态群落的奥妙所在”①马兵:《自然的返魅之后——论新世纪生态写作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李元胜和沈苇都有长期的对自然事物的田野考察,沈苇曾对新疆大地上的植物进行田野考察并出版散文集《植物传奇》,而李元胜则沉浸于对自然景物的摄影,并以“博物”而著称。李元胜的生态诗歌源于他对荒野自然长久而专注的观察,他善于通过对植物的细微观察,发掘其柔软形体背后的浩大生命,如《露珠》,“在这浑圆、渺小的液体中/有着想象不到的/巨大空间,很多层的透明雕刻/无穷多的窗户/舞蹈着,方格中间有一座/我们看不见的教堂”。这得益于李元胜长期以来的生态摄影,他对自然有一种微观的诗性观察。这也是博物诗学与生物科学研究的本质区别。博物诗学指向对自然万物的非象征化书写,恢复博物传统,裸露动植物、自然山水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诗人对微观世界的想象性敞开,获得对自然世界之神秘性和复魅性的体悟。诗人深深喟叹大自然如教堂般神秘的存在,同时也感受到自然万物中所凝聚的“大地的心跳”,如《桑树在北风中熟睡》,“桑树在北风中熟睡/如果紧握它的指节/我能感受到大地的心跳”。“熟睡”“指节”“心跳”既暗示了诗人自然体悟的触角之灵敏,同时指向人与自然声息相通的生命本质。李元胜“特别善于书写人和自然的对话和交流,大量的动植物喻体和本体的运用生动奇妙,而人的身体、心灵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的互为象征也开阔而有趣,最后再生发出由自然带来的对生命的更大的抒情和沉思空间”②曾子芙、夏玲:《论李元胜诗歌的生态美学意蕴》,《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这也是李元胜独有的生态感知视角。由日常经验出发,在体悟自然万物的绚烂生命的同时,其重要的落脚点是对人类的反观,这在《紫色喇叭花》一诗中有鲜明的体现:“晨光里,我想拍好/紫色的喇叭花,但相机力不从心/镜头没法解释如此美的紫色/始终犹豫着,在红和蓝之间/而我,只能看到酒杯般的花瓣/美得过分的紫色,斟得太慢/简直就要溢出,它经过漂亮的曲线/突然收窄,仿佛那里有/不想公开的楼梯/漆黑的地下室,凌乱的砖头/遮掩一条神秘的路/在路尽头,没有紫色,没有相机/世界尚未开启,我们尚未出生。”诗歌起于日常的拍摄经验,而止于对世界初始经验的感喟。实际上,在今天这样一个影像化时代,相机的拍摄无时无处不在,但诗人的独特之处在于,普通人对花花草草的拍摄是为了自我的愉悦,并不触及自然生命本身,而李元胜则将诗思的焦点投向“一条神秘的路”,这也正是生命诗学的重新建构,是在万物生命平等的基础上建构起的生命伦理,与沈苇、胡弦等与“蚂蚁”的平等对话异曲同工,消解了人类的历史主体性,充分肯定自然细微生命所蕴含的坚韧而宏阔的生命力量。
四、自然审美与现代性反思
自然写作的落脚点是“审美”,对其审美范式和艺术境界的建构与探寻是诗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问题上,十位诗人既有相通的审美追求,又筑造了具差异性的审美路径,呈现了以“天人交通”为基质的多元化自然审美景观。李少君对自然书写中“诗歌情境的现代方式”有精彩的论述,“诗呈现的不是客观的景或者说境,诗呈现的其实是已蕴含个人情感和认识的境,一个主观过滤刷新过的镜像,经过个人认识选择过的镜像”。李少君的论述是对古典意境理论的创新性继承,这在他的诗歌中有鲜明的体现。北乔“总希望运用或凝聚某种引物而生的意味”,李元胜格外重视“大自然偶然向我敞开的一切”,“十年的田野考察,之前以为只是给我提供题材,其实已经悄悄地改变着我的诗歌面貌和写作方式”。他们都遵循着“随物赋形”的自然诗学,探寻新的诗歌结构与语言形式。陈先发注重对“自然”与“词语”之间幽微关系的发掘,认为“出神,词语才能从既定轨道上溢出,实现一种神秘的开放性”。冯娜自称“我的劳作像一棵偏狭的桉树”,这自然让人想起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对于自然的长期且深入的观察为他们的自然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与审美经验。“只有当一个人作为栖居者站立在家园之中,打开与自然相接的所有通道,为物的本质存在留出自由空间,从自然内部经历自然生命的涌动,遭遇自然存在的本然显现,为自然的内在光辉所照亮,获得与生命存在本源的切近感,从而为一种惊奇、赞叹、快乐、震撼和感恩的情绪所充满,对自然的生态审美经验才会真正发生。”①赵奎英:《论自然生态审美的三大观念转变》,《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在对十位诗人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会时时停顿下来,陷入对自然的遐想和沉思,这正是“自然生态审美”的经验共鸣。
近年来的自然写作是在现代性的谱系中展开的,或者说它是对现代性的某种扬弃性的继承和反思。在这一点上,诗选中的几位诗人在不经意间达成了一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重构。李少君诗歌鲜明地体现为一种“生态启蒙”意义,是对“人的文学”的纠正与丰富,同时构成对中国古典诗歌“自然”传统的对接。正是基于这种诗歌观和自然观,李少君诗歌中的自然是神圣的,自然是人类灵魂最终的皈依之所。剑男认为,“如果我们撇开自然一味谈论和追求诗歌所谓的现代性是没有意义的。……我想每一位置身于他所处时代的诗歌写作者通过对自然书写激起的想象和情感回应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就是诗歌的现代性”。剑男的这段论述与李少君的诗歌《云之现代性》有着内在的精神契合,“云卷云舒,云开云合/云,始终保持着现代性,高居现代性的前列”,“云”作为亘古存在的自然物,它见证并参与着人类的历史。“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②[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页。李少君的《云之现代性》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洞视,这也恰恰说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构现代性成为当下自然写作的重要理论支点。沈苇强调大自然文学是“当代性之下的文学”,旨在强化自然写作的及物性和时代性,否则就容易陷入虚空化的写作误区。不管是“当代性”,还是“现代性”,诗人们都无意于进行理论的思辨,而是基于时代语境的诗学思考和理论建构,这折射出他们自然写作的出发点和基本面向,对于纠正当下生态诗歌的某些流行化弊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群峰之上——自然写作十家诗选》集束性地推出十位诗人的自然生态诗歌,既是一次丰硕的总结,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十位诗人的作品展示了近年来自然诗歌的创作实绩,用诗性的、审美的文学力量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地契合了新时代对文学的使命召唤和审美期待。而如何在未来的自然写作中不断突破,既关乎自然生态、精神生态与文化生态的深层融合与诗美锻造问题,同时涉及海洋、旷野、动物、植物等题材的进一步拓展与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