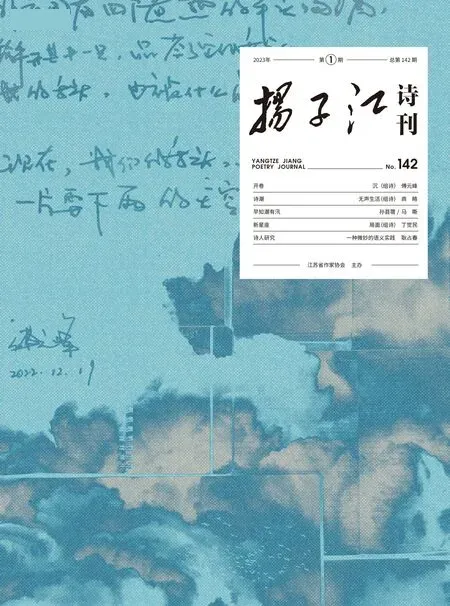秋天(组诗)
庞 培
夜风
我并没有其他的夜风
只有这一阵秋夜的风
头顶的灯
街道般摇晃
树叶变作窗户
蟋蟀揉了揉眼睛
在夜凉的草丛
这是风一阵阵大的声音
这是心情,不是天气
房屋的栋梁已被蛀断、凿空
人已身在废墟千年
在没有人的屋子里
风是一双望向窗外的眼睛
更多的树丛围拢过来
夜风,夜风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接下来的日子的秘密伙伴
愁苦的嘴唇在旷野的寄托
而树叶正变作窗户
往昔婆娑入梦
黎明
让两个房间都亮着灯
这里完全没有别的,只有
黎明
以及冰凉的天气,窗外冰凉的草丛
走廊尽头的光
还有夏天微微的暖热
冰凉的虫鸣声
比我裸露的上身更加年轻
吹来的风,几乎是童子身
似乎灯光能在夜晚
照亮一个人的孩提时代
四周被虫鸣声浸透
人在世上最初的苏醒
有时候被看见
有时候浑然不知
云灵山漂流
漂流结束后领队请大家吃饭
精美的包糍,纯白色,拌馅
一种不可思议的美味
另外盛放盘中,供大家
用手抓食
天黑后,我说:
云灵山和天成奇峡
两个兄弟
一个木讷、壮实、精怪
一个短发、炫耀,无法无天
山峰从云朵间穿行。峡谷俯身
载满百花的水流转动如高空璀璨的
摩天轮
大山千年的寂静被照亮
万物倒转,激流四泻短暂复原
橡皮筏是定制的,皮很厚
整个漂流过程中我一直在用手抚摸
摸着摸着,摸出了粗糙的树皮
摸到了湿漉漉的晨曦
摸出来一头丛林大象
人们傻愣愣地上岸
有人在吃烧烤
而使他着凉的,正是烧烤摊上的烟
因为水温过低,景区水域
傍晚四点,已全线关闭
海浪
大海上的浪涌过
我居住在县城的屋顶
我在这浪谷居住
转眼间被生活席卷
人世已分辨不出
我最初的模样
房间住了几十年
搬离只花费一瞬间
命运呵!你有一种
日日夜夜的迅捷
能够化高山为街衢
寂静的书房,变作村野耕地
我自己也不再回忆
我当年写出来的诗句
只记得世界浩瀚无际
如同水手沉落深深的海底
亨利·菲尔丁
亨利·菲尔丁
死在葡萄牙海
海浪严峻的下巴和乱蓬蓬的
胡须
临终一刻,他小说中酝酿多日的一个人物
差不多在呼吸了:
啊!“大部分哀凄动人的景色
都是含着泪写出的,写滑稽作品
也一样……”
海风下他的眼睛,他的目光逐渐黯淡
航行时他坐在甲板上
长时间欣赏落日余晖中
静寂的洋面
儿时的冬天
有时候轮船在江面上的时候
寒冷从围墙转角,从书架
背后渗出
寂静中似乎开始落雪
整个天空都是轮船声音
在迹近飓风的夜晚
难以想象船身周围的惊涛骇浪
即使用灯塔巨大的光源照耀
也看不见
风和浪沫会把光亮吞噬
那拉长的汽笛声
似乎逼迫县城的居民承认
他们每个人都曾做过它的船员
无论老幼
锚链厂。铁合金厂。冷冻厂……
这些厂名大抵能镇得住
整条北门街上的惊恐
老浮桥像水里一只晃动的铁桶
我试着读一本读不大懂的俄国小说
(那时不叫“俄国”,叫“苏联”)
一会儿,汽笛声音又响了
城区东南角
风吹进来时,一家四口
都盯着地上的风看……
诗篇
我读了两首诗——只有
树上的鸟知道
冬天。天气阴沉沉
仿佛被诗句惊呆了
窗外,鸟儿啼鸣的树枝
试图挽留,回味
那感觉融入小区空地
渐渐融入黑夜
读完诗后的休息和发呆
也和诗一样朦胧、神秘
充满停顿、渴望
书写过的美丽的星星
秋天
如果能做一阵风
在吉他上出现一会儿
我的脸庞一定会有光亮
一个寂静清晨
周围全是露水的歌唱
主人不在或已远离
那把吉他闲置在墙
仿佛室内阴暗的角落
一直在弹拨,在触琴、起调
一颗心来过,又走了
风也顺势吹来了秋天
一年里凉意特别重的日子
就这几天:润泽秋天
整个四季的低声部
春夏秋冬的和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