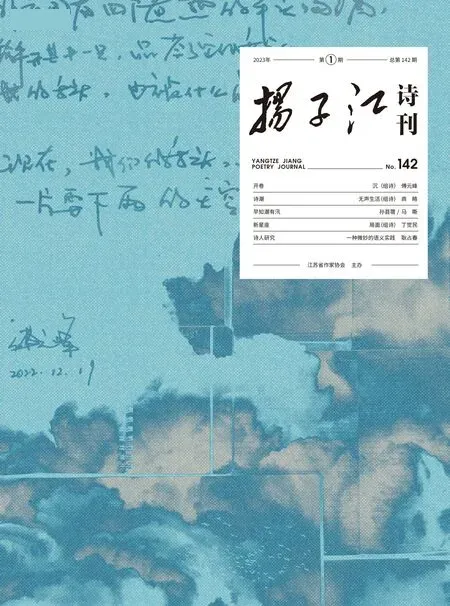杜甫形象:固化、位移与辨异
霍俊明
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诗诗人,在某些方面,他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好,起码他更自然和亲切。
——王红公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洪业
杜甫是中国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受后世评论最多的一位。
——戴维斯(A.R.Davis)
杜甫的诗歌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也同样属于我们的时代。
——冯至
杜甫是几千年来在中国文学中首屈一指的诗歌大师。
——柳无忌、罗郁正
我把这系列文章的总题目命名为“杜甫在我们中间”。这强调的不仅是杜甫诗歌的时代性,而且意在突出其超时代性和永恒性,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能够在“同时代人”的视野下在任何时代境遇和写作情势下与伟大的杜甫相遇,“杜甫的同时代人并不需要通过他的诗歌去了解他们时代的风俗和事件。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在诗人的诗歌声名上升到顶峰之后,在新的一代人开始好奇他们的祖父辈所处的那个令人震惊的时代之后,杜诗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一
显然,无论是在官史(比如《旧唐书·文苑传》与《新唐书·文艺传》)还是在野史及唐宋笔记小说、诗话(《云溪友议》《本事诗》《刘宾客嘉话录》《云仙杂记》《唐摭言》《开元天宝遗事》《唐语林》《唐国史补》《续世说》《避暑录话》《明皇杂录》《东坡志林》)和中国现当代小说(比如还珠楼主的绝笔之作《杜甫》)中,杜甫已经完全被经典化甚至成“圣”。他已然成为诗人的最高准则和时代良心,正如闻一多高度评价的,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杜甫》)。更为难得的是区别于不可复制的天才诗人李白,杜甫的诗与人都被认为是可以学习、追摹的,“那时,我十四岁。我先父教我怎样翻检诗韵,开始做五七言律诗。他拿给我一部石印的《杜诗镜铨》,告诉我说:‘不但杜甫如何做诗是可学的,而且杜甫如何做人也是可学的。’”(洪业《我怎样写杜甫》)但是作为一个丰富的生命、诗艺、思想的复合体,杜甫又总是如此亲近于每一个时代的诗人与读者。也就是说,作为集时代之大成的总体性诗人及精神共时体意义上的杜甫,他不只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不只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实则杜甫的人生、诗歌、情怀及世界观作为历史装置、伟大传统和精神共时体结构与每一时代的诗人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和贯通关系已经有目共睹。不同时代的诗人向杜甫致敬和学习已经成为常识,杜甫已然成为必备的诗人词典,是百科全书式的总体性诗人的典范。
越是在历史的转折点和时代的严峻时刻,诗歌阅读和接受就越会附加种种社会意义和伦理功能,读诗的人也总是希望从类似于杜甫的诗歌中读出更多的社会信息和时代意义,比如“诗史”“微言大义”“家国情怀”“社会正义”“时代良心”“现实主义”等。
要想全面、客观甚至富有创见地理解和重塑杜甫显然是一件非常艰难又非常冒险的事情,甚至杜甫的形象在不同时期的“千家注杜”的景观下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修正”,相应地杜甫研究也时时发生龃龉甚至悖反:“不过,反讽的是,英语学界对杜甫关注不够,在很大程度上正可以归咎于他的经典地位。很多学者和学生都有一种印象,就是杜甫‘已经研究透了’。此外,杜甫作为‘诗圣’‘诗史’的陈腐形象,也遮蔽了他的‘诗人’形象,甚至更糟的是,遮蔽了他的诗歌本身。”(田晓菲《九家读杜诗·导言》)
杜甫与李白、王昌龄、孟浩然、刘希夷、张若虚、常建、祖咏属于唐代诗人中怀才不遇的代表,“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明皇杂录》)“李杜”一直被后世并举,“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堂堂李杜铸瑰辞,正是群雄竞起时。一代异才曾并出,那能交臂失琼姿。”(何其芳《效杜甫戏为六绝句》)然而,杜甫在世时并没有像李白、王维那样受到追捧,反而是备受冷落。大唐历史近三百年,两千多位流传后世的诗人中杜甫的经典化程度越来越高,甚至超越了一直与之比肩的双子星之一的李白。
在大街上随机问一个人是否知道杜甫的诗,他(她)只要读过小学就应该能够说出杜甫耳熟能详的两首诗来,即:“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以上关于传统诗教中杜甫诗歌的约略印象,对于普通读者和大众而言已经足够了,但如果我们深究起来的话,杜甫实际上一直是被严重误读成刻板化、扁平化、类型化的诗人。
二
我曾读到过为数不少的风格迥异的当下中国诗人“致敬”杜甫的诗作,其中有一部分都是聚焦于杜甫当年以类似于“众筹”的形式建成的草堂——比如王十五司马、剑南兵马使徐知道、萧八明府、韦二明府、何十一少府、韦少府等出钱出物,而草堂也成为白居易、陆游等后世诗人追摹的“隐士”生活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初到成都时除了严武、高适之外,结识的基本都是基层的官员。在唐代的文官体系中,宰相、尚书、侍郎、中书舍人、盐铁转运使、刺史(使君)、大都督府长史等为高层文官,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遗、补阙、员外郎、郎中、县令、判官等为中层文官,校书郎、县尉、参军、判司、巡管、推官、掌书记等为基层文官。
乾元二年(759年)年底,杜甫由陇抵蜀,次年春末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又名濯锦江、百花潭)卜居建屋。我们再来看看杜甫所筑的草堂的位置和规模,“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堂成》)。由杜甫草堂最初的规制,我们可以进而发现唐代普通庶民或农家的房屋主要是以泥和茅茨(茅草)盖成三间四架的“草屋”,屋旁择地建有牛棚、猪圈、鸡窝(笼)、畜笼等。院墙一般以柴门和篱笆代替,“凡作篱,于地畔方整深耕三垄,中间相去各三尺,刺榆荚垄中种之。”(《四时纂要》)篱外为园、圃、场和花、树。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杜甫《客至》
关于这首诗的标题,杜甫自注“喜崔明府相过”。明府是唐代对县令的称谓(县尉称少府)。此诗作于上元二年(761年),杜甫交代了草堂的环境、偏远位置,以及屋舍的简陋,但是因为朋友(崔县令)的到来而颇为高兴。尽管菜肴单一,酒也是隔年的,但是兴之所至一起聚饮对于刚刚安顿下来的杜甫而言还是非常惬意的。尚能够与邻居老翁一起隔着篱笆对饮,则反映了杜甫为人处世的态度,亲近可人而倍显亲切。
杜甫的草堂成为颓败、高洁文士的精神象征,成为隔绝、孤独、清苦及一次次回忆往昔的中心,这使得我们想起加斯东·巴什拉提到的作为“修道院的原型”的“隐士的小木屋”;“面对一束远远消失在黑夜里的光线,谁不曾梦想过茅屋,谁不曾参与到传说中去,梦想隐士的小木屋?隐士的小木屋,这就是一幅版画原稿!真正的形象是版画,想象力把它们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们加深了所经历的回忆,把所经历的回忆变成想象力的回忆。隐士的小木屋是一个不需要变奏的主题。只要最简单的一次忆起,‘现象学的回响’就会抹去普通的回响。隐士的小木屋是一幅遭到过多风景侵袭的版画。它必须从自己的本质、从居住这个动词的本质中接受它真正的强度。并且,小木屋是集中的孤独感。在传说的领域里,没有相邻的小木屋。”(《空间的诗学》)
好友严武暴亡,杜甫不得不举家离蜀,草堂易主(曾经划归草堂寺)且很快崩毁、凋敝。杜甫去世五十七年之后,晚唐诗人雍陶于大和元年(827年)专门拜祭杜甫草堂:“浣花溪里花多处,为忆先生在蜀时。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山月不知人事变,夜来江上与谁期。”(《经杜甫旧宅》)时过境迁,物人皆非。韦庄于902年看到的则是:“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因命芟荑,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非敢广其基构耳。”(韦蔼《浣花集·序》)
到了宋代,随着杜甫成“圣”,修葺后的杜甫草堂,以及浣花溪交游、修禊和正月初七游览草堂,成为蜀地文人的习俗和交游的首选,正如陆游当时所记述的情形:“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老学庵笔记》)
现在我们看到的成都杜甫草堂则是后世不断重修和扩建之后的旅游景观了。此外,与杜甫有关的还有东柯杜甫草堂、成县草堂、三台草堂。元和十二年(817年),一向喜好山水之乐而成癖的白居易仿照杜甫,在庐山香炉峰下(今江西九江市南庐山西北部)修建了庐山草堂。我不由得想起撰有《杜甫年谱》的刘文典在1956年所作的诗《谒工部草堂》:“李杜文章百世师,今朝来拜少陵祠。松篁想象行吟处,云物依稀系梦思。濯锦江头春宛宛,浣花溪畔日迟迟。汉唐陵阙皆零落,惟有茅斋似昔时。”到了宋代,年近五十的大诗人陆游甚至专门在杜甫草堂附近的浣花溪畔过了一段致敬杜甫的耕读生活。在此,有诗为证:“莫笑躬耕老蜀山,也胜菜把仰园官。唤回痴梦尘机息,空尽闲愁酒地宽。无复短衣随李广,但思微雨过苏端。十年世事茫如海,输与闲人静处看。”(《躬耕》)
在宋代的伟大诗人当中有两个杜甫最大的拥趸,一个是黄庭坚,一个是陆游。正如黄庭坚所称道的“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
在成都杜甫草堂杜工部祠中,杜甫神龛的东西两侧陪祀的正是此二人。陆游曾看过一张杜甫的画像,还赋诗一首:“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枕,三百青铜市楼饮。杯残朒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题少陵画像》)陆游在杜甫草堂拜祭杜甫像时更是满怀的凄凉与落寞:“清江抱孤村,杜子昔所馆。虚堂尘不扫,小径门可款。公诗岂纸上,遗句处处满。人皆欲拾取,志大才苦短。计公客此时,一饱得亦罕。厄穷端有自,宁独坐房琯。至今壁间像,朱绶意萧散。长安貂蝉多,死去谁复算。”(《草堂拜少陵遗像》)陆游在夔州、成都任职期间最为追慕和凭吊的正是杜甫,在当年杜甫寓居的东屯高斋,抑郁不得志的陆游自是感慨万千:“比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俯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东屯高斋记》)
循着杜甫草堂,我们看到了很多当代诗人致敬的文本,比如梁晓明的《杜甫传第二十七页》:“杜甫从草堂里走出来 / 杜甫站在门口 / 看见我站在左面的一棵松树下 / 杜甫向我走来 / 他走到我旁边 / 把我的酒从手里拿过去 / 把我的肉从挎包里掏出来 / 然后他坐下 /两杯酒喝完 / 杜甫的脸红了 / 杜甫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 杜甫开始在草地上踱步 / 突然他向草堂跑去 / 拎起一支笔急速地写起来 // 杜甫走出草堂 / 他很快走到我面前 / 把那张纸递过来 / 一挥手赶跑了树上的两只麻雀 /然后他转过身一句一句地开始吟诵 / 杜甫的脸很红 / 嘴里的酒气一阵阵飘过来 / 黄昏的杜甫草堂 / 有蟋蟀的草地上 / 23岁的我脚边 / 杜甫传翻开到第二十七页”。
三
当代诗人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更为关注杜甫的“悲苦”形象。实际上,这只是杜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儒家诗人”“诗史”“诗圣”的一个主要的刻板形象而已,在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快乐的杜甫、少闲的杜甫、安逸的杜甫、饮酒的杜甫、交游的杜甫、偏执的杜甫及仕途上短暂闪光的杜甫,当然与此相伴的还有一个饥饿的杜甫、忧愤的杜甫、衰颓的杜甫、老病的杜甫、独孤的杜甫……
杜甫形象有的是其自身携带的真实性因素和客观存在,而有些形象甚至刻板印象则是后世的诗人、文士、普通读者为了一时的需要和想象及心理寄托而附着或假借在他身上的。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说法:“每一时代的诗人和读者为了从人类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价值观念,创造了各种英雄;而那些复杂而矛盾的凡人被迫成为英雄角色时,不可避免地在其最大的赞美者手中被曲解和简单化。”(《盛唐诗》)
在我看来,感受、理解、阐释、想象杜甫这样的诗人,“诗格”和“人格”是不可二分的。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就说道:“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也即是说,我们除了要对传主的诗歌创作的特质、风格有着极其深入且全面了解之外,还要对其生平、家世、品性、癖好、交游及政治经历、人生轨迹、动荡岁月等进行谱系学和年表意义上的搜集、考证、勘察和寻踪,甚至要重新发掘和进行考古学一般的工作。对于杜甫,我的出发点一直就是坚持立足于“诗”“人”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本相还原,立足于与杜甫有关的人、事、诗、史进行必要的佐证,在大场域与微观史的结合中还原出一个尽可能丰富、真实甚至驳杂的形象。显然,杜甫在任何时代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尤其在喧嚣、膨胀而又碎片化的时代,我们目睹的更多的是“写诗的人”而不是“诗人”。在我看来,“诗人”一定要是同时具备人格高度、精神深度和写作难度的综合体,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如此,杜甫才不再单单是一个被固化的“现实主义诗人”、失意困顿的小官员及衰病暮年的游荡者。由此,一个立体的、丰盈的、有机的杜甫形象才会重新来到我们中间:“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面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半个海豹。”(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
毫无疑问,杜甫是独一无二的诗人,可以被追摹,可以被崇拜,但是永远都不可能被替代和超越:“中国八世纪的诗人杜甫,作为中国的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华兹华斯、贝朗瑞、雨果、波德莱尔等,被介绍给西方。为何一位诗人会被比作如此众多、各不相似的诗人?质言之,杜甫不能被视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杜甫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成千上万的中国诗人当中,杜甫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一位随着时间流逝而声名与日俱增的诗人。”(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由杜甫独一无二甚至“千古一人”的形象,我们自然会想到很多年之后林语堂(1895—1976)笔下复杂多变的苏东坡(1037—1101)。苏东坡甚至被称为“五千年来活得最精彩的人”,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正如晚年的王安石所称道的“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杜甫与苏轼往往也是被对比谈论最多的诗人,苏轼受杜甫的影响很大:“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仕途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钱穆《国史大纲》)与此同时,杜甫与苏轼的创作量都是很大的,只是我们看到的杜甫的作品基本都是四十多岁之后的,而苏东坡则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及4800多篇文章。苏东坡的铁粉更是跨越各个行业和阶层而数不胜数。苏轼也是杜甫的超级粉丝,尽管他评价杜甫的角度有所差异:“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朱熹则把杜甫视为“五君子”之一,即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毫无疑问,杜甫在苏轼心目当中的至高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诗至杜子美,而天下之能事毕焉。”
苏东坡是官员、文人、诗人、词人、散文家、游记作家、书画家、思想家、美食家、造酒师、发明家、水利专家及佛教和道家的尊崇者:“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禀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师,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术,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是的,林语堂几乎道尽了苏东坡从人格、癖好、职业、阶层、艺术等方方面面的形象,但是他仍然觉得这可能并不是苏东坡形象的全貌。那么,从宋代杜甫被誉为“诗圣”“诗史”开始,我们是否已经穷尽了杜甫的形象呢?
四
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及读者对杜甫的形象充满了各种想象。
先来看看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对杜甫形象及诗歌成就的评价:“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以及虚幻想象的诗人。他比同时代任何诗人更自由地运用了口语和日常表达;他最大胆地试用了稠密修饰的诗歌语言;他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深奥的典故成语,并感受到语言的历史性。”(《诗的引诱》)
对任何诗人、作家的传播、接受都是综合因素合力参与的产物,甚至有时候会悖离诗人的本相而变得面目全非。不单是杜甫与苏轼,李白的传播史和接受史也是如此,总是掺杂了各种复杂多变的因素甚至主观化、主流化的因素,甚至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会被意识形态化。李白通过流传下来的大约一千一百首诗歌塑造了率真、狂放、怪诞、豪侠、放任不羁的性格——也被后世认为有机会主义者的成分,也由此成为游侠、求仙问道者、狂饮者、狎妓者、笑傲权贵者、“诗仙”以及“谪仙人”的天才诗人形象。然而,诗歌中的“李白”是修辞化的和想象性的,甚至带有虚构的成分,这显然与现实生活中的李白是有一定差异的,“包括杜甫在内的其他唐代诗人,没有人像李白这样竭尽全力地描绘和突出自己的个性,向读者展示自己在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两方面的独一无二。”(宇文所安《诗的引诱》)甚至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又增加了歧义和误解的成分。李白的诗歌从题材来看相当广泛、多样,比如寻仙问道、山川风物、诗酒狎妓、离愁别绪、边塞远征、民间疾苦、社会万象、怀古幽思等……显然,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道教诗人”或“隐逸诗人”的简单化标签所能涵括得了的。我们看到的杜甫与李白的形象恰恰是通过“诗歌”中的人物、意象、场景、情绪、背景空间等塑造而成的,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诗歌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及历史背景在唐诗传统中却往往缺乏必要的具体的交代,而往往是虚化的、模糊的、不连贯的碎片,但是杜甫却恰恰是一个例外。上至家国下至饮食等,事无巨细,它们都能被杜甫一视同仁地写入诗中。也就是说对于解读杜甫的人及其诗,“以诗证事”或“以诗证史”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的影响早已经超越了诗歌界,也不囿于文学界,甚至从唐代开始,历代的书法家、画家、戏剧家(比如他们创作关于杜甫的戏曲和现代舞台剧)都在向杜甫致敬。尤其北宋以来,杜诗成为历代书法家和画家所最为钟情的题材之一,甚至连元代的鎏金錾刻人物花卉纹狮扭盖银瓶、元代青釉印花瓷器及清代雍正时期的木纹釉地粉彩笔筒上均有骑驴出行的“隐士杜甫”形象。显然,杜甫的形象不断被扩大化、经典化至各个领域。
在抄录杜诗的历代书法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怀素、苏轼、黄庭坚(其江西诗派更是以杜甫为宗)、赵构、张即之、鲜于枢、赵孟頫、徐渭、董其昌、王铎、张瑞图、傅山、郑燮、朱耷、刘墉、何照基等,可见诗圣杜甫在文人心目当中是何等之重要。正如明代金冕所评价的苏轼抄杜诗:“昔先生尝赞美杜子美诗、颜鲁公书皆求之于声律点画之外,今观先生书杜诗,后千百年,宛然若昨日挥洒者,盖寓精神于翰墨而才品所自到尔。倘拘以宇宙之得而论之,是未可同赏妙也。”怀素、徐渭、祝枝山、赵孟頫、王铎、许光祚、张瑞图、陈淳、傅山等大书法家抄录最多的正是杜甫晚期风格的巅峰之作《秋兴八首》。
就杜甫的形象、画像、诗意图而言,自宋开始而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尽管今天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来认识有多少画作是受杜甫或者其他诗人诗句启发而成,但杜甫诗句比其他诗人诗句都更直接地影响到了各类‘诗意图’的创作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或许可以据此推论,这是杜甫在晚期帝制中国所达到的‘伟大诗人’这一地位的切实反映。”(艾朗诺《明清绘画中的杜甫诗句》)其中代表性的“杜甫诗意图”主要有宋代李伯时的《饮中八仙图》、赵葵的《杜甫诗意图》、佚名的《杜甫〈丽人行〉轴》,明代沈周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意画》、唐寅的《临李公麟〈饮中八仙图〉》、仇英的《〈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诗意图》、文徵明的《文待诏五月江深草阁寒图》、文伯仁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意图》、文嘉的《写杜诗山水轴》《柴门送客图》、周臣的《柴门送客图》、谢时臣的《杜陵诗意图册》、沈颢的《杜陵诗意山水图》、李士达的《饮中八仙图》、孙枝的《杜甫诗意图》、杜堇的《古贤诗意图》、谢缙的《潭北草堂图》、张复阳的《垂纶图》,清代恽寿平的《少陵诗意图》、王时敏的《杜甫诗意图册》、石涛的《杜甫诗意册》、傅山的《江山草阁图》、王原祁的《写杜甫诗意图》、王翚的《少陵诗意图》、王鉴的《仿范宽少陵诗意图》、丁观鹏的《杜甫诗意图全卷》、吴历的《少陵诗意图卷》、戴本孝的《杜甫诗意图册》、吕焕成的《杜甫诗意屏》、董邦达的《杜甫诗意高宗御题轴》、程梁的《饮中八仙图卷》,近代张大千的青绿山水《杜甫诗意图》,当代陆俨少的《杜甫诗意图册》,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陆俨少(1909—1993)。他于抗战时期流寓巴蜀,随身携带的正是杜甫的诗集:“入蜀前行李中只带一本《钱注杜诗》,闲时吟咏,眺望巴山蜀水,眼前景物,一经杜公点出,更觉亲切。城春国破,避地怀乡,剑外之好音不至,而东归无日,心抱烦忧,和当年杜公旅蜀情怀无二,因之对于杜诗,耽习尤至。入蜀以后,独吟无侣,每有所作,亦与杜诗为近。”(《陆俨少自叙》)
五
那么,杜甫的真实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历代文人关于杜甫的画像诗更是非常多见,比如欧阳修《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王安石《杜甫画像》、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陆游《题少陵画图像》、刘松《题杜草堂戴笠小像》、蒋灿《题杜少陵像二首》等。
我们先来看看欧阳修笔下的杜甫形象:“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言苟可垂后,士无羞贱贫。”至于王安石更是非常全面而深刻地概括了杜甫的形象:“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
正如画家蒋兆和(1904—1986)在1959年直接把自己的头像(自画像)套在杜甫身上一样,而早在1952年他就把自己岳父萧龙友的形象用在了李时珍身上,如法炮制还把竺可桢的原型用在了祖冲之身上。1981年5月,晚年的蒋兆和对杜甫的理解更为深切,于是创作了一幅《杜甫行吟图》,画面上背着手吟诗的消瘦杜甫身侧是一丛石竹。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形象往往是后世附会和想象的成分更多,所以蒋兆和会说出:“我与少陵情殊异,提笔如何画愁眉!”这就印证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确实,我们总是避免不了以当代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有一年的十月中旬,秋风渐起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站在温州的江心屿和楠溪江畔,望着眼前流淌不息的江水我竟然在一瞬间不知今夕何夕。千年万载不息的江水和崭新的拔地而起的高楼同时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我们不可能把这些时代之物从风景当中直接抹去或视而不见。这就是时代和生活的现场。在迅速转换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境遇中诗人应该时时提醒自己,如果你看不清自己所踩着的这片土地,你有什么值得信赖的理由去抒写历史,又何以感兴、游目骋怀、思接千载、发思古之幽情?
有意思的是在2021年4月,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与艺术家合作,利用AI技术重新整合了三个版本的杜甫像,即蒋兆和的杜甫画像、故宫南熏殿《唐名臣像册》中的杜甫像、吴为山所作的杜甫雕塑:“本次修复尝试了一个新的制作流程,运用AI风格迁移技术,让杜甫的相貌变得有血有肉,动了起来,仿佛杜甫穿越时空来到了现代了。甚至,AI人工智能还原之后的杜甫雕塑,还能吟诵自己的诗作《春夜喜雨》,令人十分惊喜。”(《中国青年报》)
大体言之,幽人、隐士、落魄的诗人形象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肯定不是油头粉面、肥头大耳、膀大腰圆的,而应该是瘦削的、憔悴的、多愁善感和病歪歪的那种,而这正是杜甫留给后世的形象。
说到杜甫形象,我们肯定是要将之放在整个唐代的文化和生活背景之下的,比如他的穿戴装束及所骑的一头瘦驴。由此,我们先来看看郑虔所作的一幅画。
郑虔(691—759)擅长书法、绘画和作诗,因此被唐玄宗誉为“郑虔三绝”,“工于草隶,善于丹青,明于阴阳,邃于算术,百家诸子,如指掌焉。家国以为一宝,朝野谓之三绝”。(《大唐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府君并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并序)》)郑虔曾任左监门录事参军、协律郎、广文博士、著作郎。“安史之乱”被平定后郑虔与王维一同被囚禁于宣阳里,后被贬台州司户参军。
郑虔与杜甫是莫逆之交,被贬台州时杜甫曾写道:“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乾元二年(759年)9月20日,郑虔卒于台州官舍,而此时的杜甫在两个月之前辞去华州司曹参军之职前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动荡不已和寄寓四海的颠沛生涯。郑虔去世,杜甫悲恸中赋诗感怀:“故旧谁怜我,平生郑与苏。存亡不重见,丧乱独前途。流恸嗟何及,衔冤有是夫。道消诗发兴,心息酒为徒。”(《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失真。”(《寄薛三郎中据》)正是因为郑虔与杜甫有着深入的交集,所以作为画家的郑虔,他笔下出现杜甫的形象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明代陆深在《玉堂漫笔》中记述了张说、张九龄、孟浩然、李白、王维、郑虔、李华在风雪中出蓝田关穿越松林游龙门寺的《七子度关图》(又名《七贤出关图》),“世传《七贤出关图》,或以为即《竹林七贤》。屡有人持其画来求题跋,漫无所据,观其画,衣冠骑从当是魏、晋间人物,意态若将避地者。或谓即《论语》像而为画尔。姜南(宾)举人云:‘是开元间冬雪后,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游龙门寺,郑虔图之。’虞伯生有题孟浩然像诗:‘风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又有槎溪张辂诗:‘二李轻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摩诘图中诗性长。’是必有所传云。”
然而,关于郑虔画中“七子”具体所指为谁,却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有的指认为“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有的则认为这七个人当有杜甫——“以其衣冠有类于唐而有乘驴者则以为李杜元岑之流,而引少陵诗所谓旅食京华与太白过华阴事”(明代金问《七子度关图·题跋》),还有的认为“此七人者乃宋之问、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崔日用、史白”(清代朗廷极《七子度关图·题跋》)。
我们来看看郑虔所作的《七子度关图》。今存为明代摹本,绢本设色,纵22.8cm、横164cm,藏于故宫博物院。另外,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传为宋人李唐(1066—1150)所画的《七子度关图》。画中七人或骑马或骑驴或骑牛,其间穿插了执缰绳或挑担的八个脚夫。骑行者七人中有六人“重戴”“皂纱遮面”,这可以看出是唐代士人非常流行的典型配置。从这些唐代特有的服饰我们也能更为直观地感受到杜甫的形象。
裹发的幞头巾子一般用黑色纱罗制成。在隋唐、五代、宋代不同时期,幞头(折上巾)的样式和系法(裹法)就有不少,比如软脚幞头、硬脚幞头、长脚罗幞头,再比如平头幞头、圆头幞头、前踣式幞头、翘脚幞头(朝天脚幞头)、直脚幞头(平脚幞头、展脚幞头)、交脚幞头、曲脚幞头、高脚幞头、宫花幞头、牛耳幞头、玉梅雪柳闹鹅幞头、银叶弓脚幞头、曲脚向后指天幞头等等。沈括《梦溪笔谈》:“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重戴”就是在幞头上加一顶帽子,帽子一般为紫色衬里,帽檐上悬垂方形的黑色罗帛,帽下有紫色丝编的系绦(缨带)用于打结固定帽子。《宋史·舆服志》:“重戴,唐士人多尚之,盖古大裁帽之遗制,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罗为之,方而垂檐,紫里,两紫丝组为缨,垂而结之颔下。所谓重戴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唐代薛调《无双传》:“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
到了宋代,御史台仍沿袭了唐代的重戴,其他官员则可戴可不戴。
马和驴的身价自是不同,二者也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对应标识物,“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徙”(《太平广记》)。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马因为战争的需要其价格要远远高于牛、驴、骡子等其他牲畜。驴子尤其是瘸腿驴(蹇驴)成为落魄文人、寒酸学士、穷途末路之上艰难苦恨的行吟诗人的标配,而一生不合时宜的杜甫自然与驴子就扯上了联系。确实,落寞、困顿的诗人于风雪中骑驴也成了千百年来诗人的典型形象。杜甫留给后世的正是于风雪中骑驴出行的潦倒、憔悴、多病、苦恨而多舛的形象,“骑驴三十载,旅居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六
由上可见,杜甫无论是在诗学还是社会学的层面都已经成为伟大的传统,成为一代代人追摹的“诗史”。从“诗史”“诗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等角度来看,杜甫无疑完全被经典化乃至圣化了,甚至成了诗人的教义。
为此,近年来我几乎通读了所有关于杜甫的诗文材料、研究著作及几百篇论文。在跨语际译介文化的传播背景下,我还阅读了包括著名的汉学家和海外诗人、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史研究专家埃兹拉·庞德、约瑟夫·布罗茨基、奥克塔维奥·帕斯、圣-琼·佩斯、维克多·谢阁兰、加里·斯奈德、詹姆斯·赖特、波顿·沃森、奥菲尔·戈蒂耶、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宇文所安、田晓菲、王德威、薛爱华、卢本德、罗吉伟、潘格瑞、艾朗诺、倪健、杜希德、高友工、梅祖麟、勒克莱齐奥、艾略特·温伯格、比尔·波特等人关于杜甫、唐诗、唐代史的专题研究材料。
与此同时,除了查找《礼记》《汉书》《后汉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唐六典》之外,我还通过《初学记》《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明皇杂录》《刘宾客嘉话录》《封氏闻见录》《北梦琐言》《朝野佥载》《唐诗归》《册府元龟》《云溪友议》《云仙杂记》《唐诗纪事》《唐摭言》《本事诗》《唐语林》《唐音癸签》《唐才子传》《太平广记》《世说新语》《酉阳杂俎》《云麓漫钞》《述异记》《集异记》《独异志》《夜航船》《诗品》《东坡志林》《沧浪诗话》《蠖斋诗话》《苕溪渔隐丛话》《石洲诗话》《唐人轶事汇编》《唐诗百话》《唐诗杂论》《唐代诗人丛考》《唐诗的读法》《唐代墓志汇编》《唐代财政》《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中国服饰史》《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隋唐佛教史稿》《隋唐五代史》《唐代舞蹈》《西南联大诗词课》等来了解唐代的年号、官职、政治、军事、经济、城市、宗教、艺术、生活、墓葬(壁画)及诗坛的掌故等。
当我们把杜甫还原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失意的老病的瘦削的诗人形象就显得更为真实、立体、可靠。也就是说除了关注杜甫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及不断建构的精神肖像之外,我们更应该把他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人。即我们既要关心杜甫作为一个诗人的精神境遇和时代背景,也要关注一个大时代之下具有“烟火气”和可感可触的微观生活。
也即是说,关于杜甫的形象我更感兴趣的是复现和还原杜甫,以及同时代的唐人是如何劳作、写作、科考、出行、贬谪、宴饮、交游的,探究他们的衣冠、服饰、妆容,以及起居环境和出行工具是什么样子的,还原出大唐的交通、财政、官场、风物、建筑、饮食、舞乐、绘画尤其是酒文化、佛道文化的面貌,考察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长安、洛阳、秦州、巴蜀、夔州等地的地方文化,包括市井状况、乡村生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