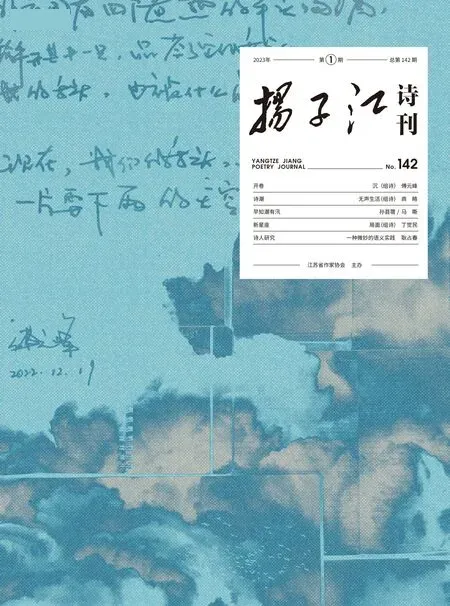[葡]努诺·朱迪斯诗选
姚 风 译
努诺·朱迪斯 (Nuno Júdice,1949— ),是 20 世纪70年代以来葡萄牙诗歌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作为一位学者型的高产诗人,他在葡萄牙诗坛从未沉寂过,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创作热情,甚至在某个阶段每年都有新诗集问世。他除了在大学教授文学课程并担任葡萄牙最著名的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之外,还涉足散文、小说、文学批评、戏剧、电影剧本等领域的创作,发表的作品数量惊人。作为翻译家,他翻译过莎士比亚、狄金森、吉狄马加等人的作品。他在葡萄牙获得过多项文学奖,在国际上也受到高度认可,曾荣获重要的巴勃罗·聂鲁达诗歌奖和伊比利亚——美洲索菲娅皇后诗歌奖等。
美的奥秘
绝对的呈现发生在一个水杯中,
此时太阳冲破云层,在这个
灰暗无比的早晨,以意外的光芒把水杯照亮。
有时,不可知论者认为,不真实的事物
纯粹来自逻辑上的自圆其说,
似乎偶然性并不存在。
不可知论者的做法是,当他发现
自己的脚踩在所知的事物
与无需探究的事物之间的界线时,
便把自己放在人为的立场上,
不接受美可以无中生有。因此,
当我端起水杯喝水,感觉
晨光溢满我的灵魂,仿佛
水不仅仅是无色无味的液体。
不过,当我放下空杯子,恍惚觉得
照进杯子里的晨光消失了,
这小小的美多么脆弱啊!
或许,我不该喝尽杯里的水,
我该继续渴着。
时间问题
在房子的一侧,孩子们在玩耍时间
而时间飞逝,让他们不再玩耍。
隔壁的房子里,一条狗看见时间流逝,
开始狂吠,吓得时间贼一般逃之夭夭。
在街上,乞丐哀求每个人施舍他一点时间,
但人人都说没有时间给他。在咖啡馆,
我要了一杯浓缩的时间,因为我没有时间睡觉,
在我身边,有人要了一杯满溢的时间,
因为他需要时间悠然地啜饮。
有人因为缺少时间而狂奔,而时间追赶他,
把他抓住。在地铁站,一个女孩子慢悠悠地
走过站台,比起那些斤斤计较而节省时间的人,
她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当有人问我是否有时间,
我会看看手表,似乎手表有用不完的时间,
然后我请求他们清空我的手表
拿走我所有的时间,不留一分一秒,
以便让我有时间看看究竟过去了多少时间。
黑岛访聂鲁达
我在聂鲁达一生采拾的贝壳中走过,
我知道每个贝壳里都有一个大海。
当贝壳掀起风暴,我听见聂鲁达所有的大海
在呼啸;我听见水手们紧紧抓住桅杆在呼喊,
船正在沉没。而我也在呼喊,
在黑岛,在聂鲁达的居所附近,我拾起
一个贝壳,这应该不算偷取
聂鲁达的贝壳。 我不知道如果我拿走,
他会说些什么;但我知道听完我的解释,
他会原谅我:“我想要的只是
一个贝壳,最小的一个,我偶然
在礁石间拾到的那一个。”而他会问:
“你为什么要它?” 我必须找一个
适当的理由来解释我的行为:“我需要它,
它可以让我听到我心爱的女人的声音。”
聂鲁达会对我说:“就为这个吗?那你
拿去吧。它是你的了。”就这样,当我想
听你说话的声音,就把贝壳放在耳边,
好似它不是我拾到的,而是聂鲁达送给我的,
我听见你自贝壳的最深处,对我诉说。
符号学
我说到了爱情。有的词语看起来很坚实,
与那些被你的手指拆解的词语截然相反。
比如:孤独,或者:恐惧。词语,任我们
选择,放在诗歌里,就像放进
一个盒子里。但不要这样隐藏它们。
让它们留在外面,不要看见,仿佛它们
不需要我们用声音说出。
现在,我说说词语的作用。它们在
我们头脑中旋转,通过动脉
抵达终点:心。人们会使用另一个词:
爱。但我不说它们是同义词;此外,
有些词语蕴含与字面相反的语义,
唯有深爱之人才深知此意,如果生活
还没有把他引入歧途。
我爱你。我本可以说:我用孤独爱你,
或者说,我用恐惧爱你。
从一个词语开始,一切都可能在白纸上发生,
一切尽在诗里。然而,是这些词语把我引向你,
也就是说,这些词语让你与它们心有灵犀。
正因为如此,爱情、孤独、恐惧,全都混为一体,
还有无法省略的生命这个词。
一首外用的情诗
我爱你,爱你如
冷漠的囚徒,情人中最
隐蔽的一个。我爱你那写着
苍白倦怠的脸庞,爱你
迟疑的双手,爱你
无意间送给我的词语。
我爱你记住我也忘记我,如同
我记住你也忘记你:在一个
黑白的背景中,你如清晨的白雪
脱尽夜色,赤身裸体,
冰冷、明亮,用玫瑰
迷离的声音低语。
基本概念手册
你要用一首诗在你的生命地图上
制定一个生存策略。 请使用
意象这个工具,你知道
它将为你提供快速抵达
灵魂的矿脉。 要避免深陷悲伤的泥沼,
打开灯,当你的时间枯竭,光芒将为你
带来明天的清晨。 如果你要寻找
生存之困的替代品,那么就在
身体的仪表板上重装欲望,
并用一个个新词打印你的感觉。
你无需掌握控制系统的所有规则:
你只要穿过记忆的屏幕,
就会有人助你走出困境。
选择一个光滑的平面:让你的目光滑过
诗节的河口,把激情的湍流
推向三角洲。 然后检查
所有的选项是否正确,并确认
梦想成真的日期,
好让诗歌与生命融为一体。
巴别塔
巴别塔之前,
所有的译者都是失业者。
巴别塔之前,
辞典出版社无法存活。
巴别塔之前,
没有塞万提斯和歌德,也没有法语联盟。
巴别塔之前,
同声传译只是鹦鹉间的学舌。
巴别塔之前,
没有人说:“我有语言天赋。”
巴别塔之前,
甚至蛇在夏娃说话时也吹起口哨。
巴别塔之后,
人们鸡同鸭讲。
巴别塔之后,
只有眼睛说一样的语言。
动物学:猪
猪像人一样,在柏拉图的
洞穴里存活:它的世界
是阴影的世界。
当它拱着地面,
便看到了天堂;当它抬头看天,
一把刀架便架在了脖子上。
不过,猪也有梦想
它梦见自己有天使的翅膀,
猪舍高在云端。
在猪的梦境里,上帝像它一样
嚎叫,天堂之树
结满了橡果。
因此,猪总是用鼻子拱嗅地面,
它要拱出一个通向天堂的
裂口。
在火车的座椅上
我坐火车去海边,她坐在对面的座位上,
用手紧抓住帽檐,目光穿过
风和随风飘来的火花,眺望着乡村景色,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正如她所愿:
让我不知道她不知道该想些什么,
风把她放下的帽子吹向后座,
我要去拾起它。此刻,
她用手捂住头发,我则让时间
在拾起帽子和归还帽子的间隙停顿,
这样她可以与风对抗,避免风吹乱头发。
当帽子又戴在她的头上,她看着我,
眼睛仿佛闪烁出从火车头飞来的火花,
燃亮我前往海边的这个早晨,
在这个木制座位的车厢里,她让我
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时至今日,
当一阵突如其来的风
吹进我对她的记忆,吹落她的那顶帽子,
她的头发迎风飘舞,却没有一只手伸出来
把头发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