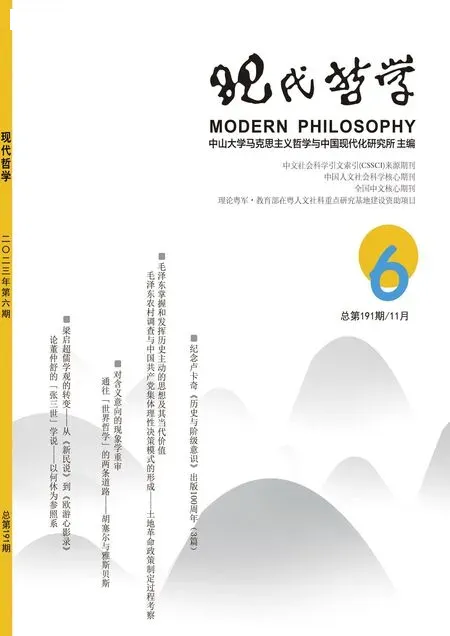临界的思想
——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三重构造及其思想方式
周展安
一、引 言
梁启超是一位始终紧贴着时代状况而铺展其理路的思想家。他关心时代乃至要介入并试图直接左右时代,于是有参与戊戌变法、成立政闻社、组建共和党、担任司法总长等一系列举动,使其在思想人物之外,更兼以政治人物闻名于世。1915年,梁启超自我总结道:“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1)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全集》第9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805页。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凡引梁启超文,均出自该版本,出版社和出版时间从略。这是梁启超属意政治的自白,也是其因袁世凯复辟而遭遇政治挫败的自我反省之言。但对政治生涯的反省并不意味着他从此消极避世,而只是调转其参与世事的方向,重思“吾今后所以报国”的新路。因为认识到一国之聪明才智之士辏集于政治而导致社会凋敝,于是从关心政治转向关心社会,以政治为社会之产物,以社会为政治之根基,认为“当知吾侪所栖托之社会,孕乎其间者,不知几许大事业,横乎其前者,不知几许大希望,及中国一息未亡之顷,其容我回旋之地,不知凡几”(2)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梁启超全集》第9卷,第2828页。。由关心时事而至于直接参与政治、由追随老师而独立组党、由“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而不惜加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与虎谋皮、由政治挫败而鼓吹夯实社会基础,梁启超紧贴时代、投身时代的执着与迫切于此可见。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梁启超抓住了当时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前沿性时代思潮与新颖政治方案的社会主义,并由置身于论争态势而来的紧张感和自觉性,发展出其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对于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述,学界已积累不少成果。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内在构造,主要基于三个层面的考量。其一,梁启超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关注,贯穿其思想生涯的始终。这提示我们社会主义问题在梁启超整体运思中的重要性,也提示我们需要在梁启超整体的运思过程中去把握其社会主义论的位置。学界既有的一些研究多侧重1906年前后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3)关于梁启超1906年之前接触社会主义之脉络的分析,参见[美]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82页;[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4-155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61-167页。诚然,1906年前后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和《民报》的胡汉民等人围绕社会革命、土地国有等问题所展开的论争,构成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重要内容,但并不能覆盖梁启超在此之外包含在今文经学、世界大势、经济竞争、欧战、先秦政治思想、中国阶级变动等课题中更为复杂的社会主义论。其二,对梁启超而言,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凝固的理念,而是在具体的历史中回应时代危局的诸多方式之一,其本身是处于状况中的,也是不断发展的,无法一言以蔽之。(4)勒文森认为“梁启超同共产主义者一致的地方”集中表现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参见[美]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0-295页。)研究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不是去测定梁启超距离某种规范定义的社会主义之远近,而是去考察梁启超经由社会主义如何理解和把握时代危局。在这种危局面前,“梁启超”和“社会主义”同时处于相互开放的、不断推进的状况之中。如果将这时的“社会主义”凝固化,或者立足历史后来的走势反观梁启超的论述,则可能只会赋予梁启超一个落伍的、有待超越和克服的位置。(5)参见蔡尚思:《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历史系中国近代史学批判小组:《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1期。比捏着一种标尺作价值评判更重要的,是如何跳脱目的论的视野,立足一种“同时代史意识”去激活似乎是落伍者的东西本身所可能包含的思想活力。其三,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展现了其运思的极限状态,这对于我们把握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位置有重要的启发。这里,我们需要首先辨析一个前提问题,即什么是思想,或者说,当我们说梁启超是思想家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般而言,我们称梁启超为思想家,或者我们去讨论梁启超的思想,是在讨论梁启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比如对政制国体的看法、对古今学术的看法,等等。但本文想进一步定义的,是所谓思想不是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而是如何把握问题的方式。而探讨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尤其能见出梁启超讨论问题的方式。这是因为和社会主义相关的世界局势、经济、阶级、民众的地位等问题,对梁启超既有的运思资源和框架来说,都是新的问题。或者说,学海堂出身的梁启超竟然可以把社会主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这本身就在呈现其思想的极限。
循着上述思路,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进行整体性的、历史性的考察。具体而言,本文将从世界大势与社会主义、中国现实与社会主义、中国思想与社会主义三个层面分别讨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世界大势、中国现实、中国思想,是梁启超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三条脉络,循各自脉络而来的社会主义论既有交汇,又充满张力。本文认为,通过对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探讨梁启超的思想方式,那是一种在极限状况中展开的“临界的思想”。所谓“临界”既指梁启超的思想不断向着新的现实问题趋近的态势,这些新的现实问题包括外资入侵的问题、贫富分化的问题、阶级对立问题等,三重构造的社会主义论即是这种态势展开的主要场合,同时也指在这种态势中,梁启超的运思方式本身不断遭遇极限的状况。换言之,在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上,梁启超既在思想内容上,又在思想方式上,使自己陷入不断突破而又不断遭遇新的界限的状况,即临界的状况。这种“临界的思想”展示了梁启超的运思特质,也提示了梁启超所代表的清末以至1920年代中国思想的走势及其突围的方向。
二、世界大势与社会主义
“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6)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的强烈冲击,迫使中国近代的思想者不能不越出固有的对中国本身的关心,而将眼光投射于以泰西诸国为主体内容的世界大势。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四书》中三次重复“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7)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22页。,显示出放眼世界大势、“天下大势”的迫切。从世界大势出发来运思,构成中国近代思想者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梁启超身上尤其突出。立足世界大势,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见解上,而且影响到其职业选择,从最初办《中外纪闻》开始,梁启超正是基于国人“全瞢于世界大势”(8)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启超全集》第8卷,第2508页。这一现实状况而展开其近乎终身的报业生涯。
追溯梁启超对世界大势关注的完整脉络,当从其初遇康有为接受“三世说”谈起,但就“世界大势”对梁启超的运思发挥支配性作用而言,则以1900年前后为顶峰。这是由1899年英俄两国就在华利益问题签订协约引起瓜分危机(9)1899年的《瓜分危言》和《亡羊录》即为此而作。、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及签订《辛丑条约》、1899年梁启超出游美国等事件与经历所促成的。经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梁启超对亡国灭种的危险有了更加切近的认识,使其确认“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天下万世之公理也”(10)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6页。。新的世界大势、新的时空观,都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而生成。正如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所咏叹的:“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鞈鞺。”(11)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梁启超全集》第18卷,第5427页。这种新的世界大势,即是民族竞争的大势;这种新的时空观,即是由“太平洋”和“世纪”为坐标轴的时空观。(12)关于“世纪”范畴的诞生如何重新界定晚清时期的中西古今关系,参见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94-106页。
从这时起,论及世界大势的文字就密集起来。1899年所发表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可推为第一篇纵论世界大势的文章。其中严格区分国民竞争与国家竞争,认为当今世界大势乃国民竞争,具体地说,这种竞争“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13)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310页。正是在这个“经济之事”上,“世界大势”与“社会主义”发生了关联。“世界大势”首先是国家间、政治上的竞争,这个竞争的完整链条,是从家族主义时代到酋长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再从民族主义时代到民族帝国时代,最后则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家族主义时代云云,属于过去,万国大同主义时代属于未来,而当前的大势即是从民族主义时代到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14)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458页。但是,在二十世纪的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竞争中,其核心“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界者则为强国,啬于平准界者则为弱国,绝于平准界者则为不国”,而在这种平准界也即经济领域的竞争中,则在国家间与国家内部同时产生“资本家与劳力者之间,画然分为两阶级。富者日以富,而贫者日以贫”(15)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898页。的现象,社会主义问题就从此发生。概括而言,即是世界大势进展至民族帝国主义阶段、民族帝国主义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由经济竞争而导致贫富的阶级对立、为了克服阶级对立而出现社会主义。用他给吴仲遥的《社会主义论》一书作序的话来说则是:“世界之问题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之内容亦多矣,而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是之故,而有所谓社会主义者兴。”(16)梁启超:《社会主义论序》,《梁启超全集》第6卷,第1701页。
梁启超还把这种和民族帝国主义相伴而生的社会主义归于一个更大的形势框架之中,这就是从“放任主义”到“干涉主义”的框架。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放任主义的时代,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干涉主义和放任主义竞争的时代,二十世纪则是干涉主义全盛的时代。梁启超认为,这种干涉主义全盛时代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他甚至断言:“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17)梁启超:《干涉与放任》,《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384页。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国家主义,即突出国家本身的调节力量,其背后的理论脉络即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将帝国主义/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并立,在一般看来是颇为突兀的,但在梁启超,这二者是相互配合的,这不仅因为它们都属于干涉主义,而且因为社会主义要处理的兼并问题、贫富问题正需要国家主义的介入。这一思路的归结就是梁启超对“托辣斯”的倡导。
梁启超把托辣斯组织的兴起和社会主义问题的发生叙述为一个共同的历史脉络:自由竞争导致弱肉强食,兼并盛行,生计界秩序破坏,劳动者不得已依附于大资本家,于是出现这样一种极端状况:“庸率任意克减,而劳力者病;物品复趋粗恶,而消费者病;原料任其独占,而生产者亦病。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梁启超认为,从学理上解决此极端状况的就是社会主义,从实际上解决此极端状况的就是托辣斯:“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托辣斯者,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18)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100页。托辣斯果然能解决上述问题吗?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梁启超极力为自己所认可的托辣斯进行辩护,他不是没有意识到托辣斯本身作为垄断组织也要参与竞争的一面,但他认为“托辣斯者,是使旧有之诸公司,悉逃其害,而共蒙其利也”,甚至认为托辣斯的宗旨与马克思的学理并不矛盾,这“有合于麦喀士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近阶梯”。(19)同上,第1101、1110页。在这一脉络中所勾勒的托辣斯,其精神就是梁启超后来反复论及的国家社会主义。
这种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国家主义的成立。随着欧战的爆发,梁启超预感到国家主义本身处在危机之中,所以原本在国家主义框架内存在且可以被国家主义化解的社会主义,隐然要取得一个更加独立的地位。在现实层面,则是社会主义理论意图回应的贫富差距问题将更加突出。在欧战刚刚爆发的1914年,梁启超就开始预测战争的走势。他坚信德国必将取胜,因为德国是当世国家建设的典范,也是符合国家主义标准的典范。德国若战败,则意味着作为政治原理的国家主义的失败,这是绝不能发生的,因为这根本违背他素来所信靠的进化论原则:“使德而败,则历史上进化原则,自今其可以摧弃矣。”(20)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梁启超全集》第9卷,第2719页。但是,战争实际的局势却不利于德国,巴黎的久攻不下,就已经使德国显出疲态。面对实际的战局,梁启超不得不对国家主义产生怀疑:“若问战后世界大势之变迁如何,则兹事体大,益非敢对。然吾犹有逆揣者二事焉: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也。”(21)同上,第2721页。如所周知,这一结果果然被其言中。1918年在欧洲游历了一圈之后,梁启超观察到欧洲思想乃处于一连串的矛盾之中:“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矛盾,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也矛盾,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矛盾。”(2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2975页。这一连串的矛盾使欧洲文明显出“世纪末”的颓势,而社会主义问题却愈形剧烈,使梁启超隐约感到“贫富两阶级战争,这句话说了已经几十年,今日却渐渐到了不能不实现的时代”(23)同上,第2971页。。面对这种局势,他观察到两种应对的方式,一是普通社会党所采取的承认现存政治组织而将生产机关国有化的方式,二是所谓俄国过激党的将现存政治组织打破的方式。梁启超通常被视为温和派,但面对世界局势的大变,他不能不将思路推进到这样的极限,即预测到“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世界上一切工业国家,那一国不是早经分为两国?那资本国和劳动国,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24)同上,第2972页。。
梁启超是立足世界大势而建立其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框架的,或者说,他是从世界大势的内在的、实然的、历史的角度来接受社会主义的,这一点区别于那种将社会主义作为应然之理念的思路。从以上分析可知,立足世界大势而把握社会主义,在梁启超那里还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即社会主义革命从在世界竞争大势内部可以被化解的状态,进至本身作为世界大势的状态。早期曾预测的“二十世纪民族竞争之惨剧,千枝万叶,千流万湍,而悉结集于此一点”(25)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899页。引文的“此一点”指社会主义革命。,对梁启超来说正是到了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真正化为现实。这种转变的过程,提示了梁启超思想中用通常的“改良主义”所无法涵盖的内容。
三、中国现实与社会主义
世界大势构成梁启超思想取径的判准,但这种判准却无法直接贯彻到中国现实这一层面。究其原因,乃在于世界大势本身所包含的等级性以及这种大势所依赖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对中国现实来说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斥意味。中国是世界之一分子,但似乎并不在作为原理和判准的“世界大势”内部,或者说,世界大势正以其对中国的排斥和淘汰而彰显自身。于是,在“大势”那边作为民族帝国主义在平准界竞争之结果的社会主义问题,对于梁启超来说,就无法立刻在中国现实内部找到恰当的对应物,也即循着世界大势所得的社会主义来观察其在中国现实中的适应性,首先所感受到的是时代的错位,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龃龉。
从这种错位的感受出发,是在立足世界大势以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相对中国现实而言过于超前的反复提醒。诚然“二十世纪之人类,苟不能为资本家,即不得不为劳力者,盖平准界之大势所必然也”(26)同上,第899页。,但这种在平准界的竞争之所以发生,是民族帝国主义膨胀的缘故,而民族帝国主义又是由民族主义的膨胀而来。反观中国,政治上尚处于不能自立的状态,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尚且不能谈,更何况社会主义。不仅如此,在国民竞争而非国家竞争的大势中,中国当时甚至还不止于政治的不能自立,而且处于国民对于国家没有爱国心、没有自觉意识的阶段,于是可能永远沉沦于被剥夺的位置而不自知。
这一认识在1906年前后与《民报》进行论争的过程中获得更加充分的说明。这场论争从1905年底开始,至1907年上半年结束,持续大概一年半有余。双方就政治革命是否应与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并行、是否应该实行土地国有、如何认识“下等社会”的国民程度、如何认识外资等问题展开了往复辩论。如伯纳尔的研究所指出的,论战的主题以及双方在论辩中的具体观点都有变化(27)[美]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118-119页。,但就社会主义的态度而言,梁启超可以说始终坚持将原理上即世界大势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施之于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加以严格区分的态度。他一方面宣告“社会主义为高尚纯洁之主义”,并且主张“开明专制中及政治革命后之立法事业,当参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以豫消将来社会革命之祸”;另一方面又历数土地国有之弊与国民程度之低,认为“社会主义之极端的土地国有主义,吾所不取。今日以社会革命提倡国民,吾认为不必要”,尤其是因为国民程度太低,所以“野心家欲以极端的社会主义与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同时并行,吾认其为煽动乞丐流氓之具”。(28)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梁启超全集》第6卷,第1626页。他将社会主义区分为“辨理的社会主义”和“感情的社会革命”两类,而“感情的社会革命”即是不顾中国之实际,拨动国民极端之感情,其结果只能是“为国中养成多数空论之辈”。(29)同上,第1626、1623页。
梁启超不厌其烦,不仅对《民报》的观点悉加驳论,而且从正面对中国现阶段之不能实行社会革命进行条分缕析的说明,其所论证有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三个方面。所谓不必行,是指中国因为没有贵族制度、财产继承上的平均相续法和极轻的赋税,使得社会上并无贫富悬隔的现象。所谓不可行,是指中国因为产业孱弱、生产落后,所以根本还谈不上分配问题,从而谈不上社会革命。所谓不能行,是指一场真正圆满的社会革命,必举一切生产机关而为国有,而此国家要能够担负全国人之各项需求之责任,然而中国今日绝无此等政府。所以《民报》所鼓吹的土地国有只能是鲁莽灭裂之举,“一若但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问题即全部解决者然,是由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30)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参见梁启超:《杂答某报》,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6、421、424页。
历数社会革命之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尤其是置身于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之中来阐发其观点,梁启超在论争中还悍然放言:“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厉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31)同上,第421页。“奖厉”原文如此。如此种种,容易予人一种梁启超站在所谓革命派的对立面、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印象。“革命与改良”这种素被广泛接受的认识框架,也因这种印象而更加得到强化。但是,革命与改良都不是单一层面的,而是有多样的层次;它们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有诸多的交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亦有不同内涵,在此一种政治、社会的力学关系中被把握为革命的内容,在彼一种力学关系中可能被把握为改良的内容,反之亦然。上文呈现了梁启超基于世界大势和中国现实而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评价和取舍,但这并不意味着立足中国现实就绝然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的反对。相反,正因为立足中国现实,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包含了更为复杂的面目,更展现了理念和现实之间的摩擦与纠缠。梁启超批评“感情的社会革命”,但高度肯定“辨理的社会主义”;他反对动员下等社会来参与政治运动,但认为“非必由人民暴动举行社会革命,乃可以达社会主义之目的,此吾所主张也”(32)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梁启超全集》第6卷,第1626页。。即便在论战的剑拔弩张之中,梁启超也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肯定。他之提倡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意义上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的肯定,而是激于一种强烈的外资亡国和国民竞争的意识。他所感觉恐怖的是外国资本将全体中国人置于被压迫阶级的境况。(33)参见梁启超:《杂答某报》,《〈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420页。这种恐怖直到其回国之后仍伴随着他,正所谓“若夫中国,则资本家多为外人非我国人,资本家日多则我国家即日即于亡,可不惧哉?”(34)梁启超:《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梁启超全集》第8卷,第2521页。这一担心并非无据,事实上,正是欧战的爆发给了中国民族工业以发展的时机,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也为随后政党政治的展开准备了一定的阶级基础。
不仅如此,即便是对于那种激进的社会主义倡导,比如资本国有之说,梁启超也并未回避,而是以之为现实选择的导引,时时悬在眼前。他预感到“‘国有’政策,自今以往,日益占势力矣”,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家言,且并倡资本归公(即资本国有)之说,此其义在今日中国,固万难实行,(即泰西各国亦未能实行。)然此实世界之公理,将来必至之符。今若为国家百年长计,则改革伊始,不可不为应此趋势之预备”。(35)梁启超:《外资输入问题》,《梁启超全集》第5卷,第1336页。他认为在产业萎靡的状况下,诚然没有发生严重的分配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问题就可以置之不问,因为“但使我国家既进步而得驰骋于世界竞争之林,则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一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所必至也,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抑章章”(36)梁启超:《社会主义论序》,《梁启超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8页。。这种将社会主义作为现实选择之导引的倾向,越到后来越明显,认为梁启超鼓吹社会革命之圆满只是一种“保守的拖延战术”(37)[美]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133页。可能并不公允。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作为“高尚纯洁之主义”的肯定绝非信口之谈,而近乎成为其思想的底色,这一点在欧战之后的思想言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1921年,在回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的信中,梁启超一开头就吐露其内心的苦闷:“所谓苦闷者,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面为本主义之敌,一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敌视耶?”(38)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329页。这里的“主义”即“社会主义”。这句话清楚地说明,此时的梁启超不仅对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而且对社会主义行之于中国是确信无疑的。这与他1906年前后虽原理性地肯定社会主义但仍将之置于未来的维度有显著不同,又呼应了上节所论社会主义从作为世界竞争大势的一个内部环节跃升为大势本身的脉动。在此语境中,可以说梁启超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运思的,他的苦闷源自如何更妥帖地立足现实来推行社会主义,更具体地说,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担纲者或者政治主体的思考。这也表现于其接下来一段时期对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1921)、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1925)、无业游民与有业平民(1926)等问题的反复讨论。梁启超此时诚然还强调应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不是对资本主义有何留恋,他明确说“磨牙吮血之资本主义”会导致“极可厌可憎之畸形的发展”;(39)同上,第3331页。他也不是尝试首先发展资本主义,待生产繁荣之后再考虑社会主义问题这种两步走的方法,而是意识到采取资本主义只是为了发展生产的不得已之举,采取资本主义的同时应采取社会主义的方式予以矫正,或者说,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如他所明白宣告的:“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骈进。”(40)同上,第3333页。由此,所谓苦闷,同时也是对于在中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而至少暂时不能不依靠此“磨牙吮血之资本主义”而来的苦闷。依靠资本主义不仅是生产所需,也是为了锻造劳动阶级,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41)同上,第3331页。。他由此而展望着“万不容缓”的“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今日可行否耶?吾以为吾辈既属望劳动阶级为将来改造社会之主体,则现在向此方而下功夫,实万不容缓,不能以其人数尚少而漠视之。”(42)同上,第3333页。在此,梁启超不惟是从中国现实内部去肯定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者,而且是一个几乎要踏入群众运动的、行动的社会主义者。
四、中国思想与社会主义
世界大势为梁启超认识和接受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框架,或者更直接地说,社会主义就是作为世界大势的一环而为梁启超所接受的。但梁启超之接受社会主义,并且推举它为“高尚纯洁之主义”,却不纯然是出于世界大势的威力,还由于他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内部看到其中可以与社会主义相接榫的内容,进一步说,社会主义就其作为一种思想而言被梁启超立足中国思想内在化了。前文曾提及在欧战之后,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中,社会主义甚至成为梁启超思想的底色,这一点正与梁启超对中国思想尤其是先秦思想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阐释同步。
将社会主义与中国思想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场合,是对自己老师康有为哲学思想的阐释。在1901年发表于《清议报》上的《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有这样的论述:“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43)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71页。诚然,这里所提及的社会主义还只是桑士蒙即圣西门一派的所谓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能将康有为的哲学断然定义为社会主义派哲学,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新颖的创造。读下文的长篇论述可知,这里说的康有为哲学就是《大同书》的内容概要,而这也是《大同书》第一次公布于世。将自己老师秘而不宣的著作直接称为社会主义派哲学,正说明社会主义在此时的梁启超思想中印记之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没有直接使用过“社会主义”的提法,但书中提及“傅氏之论生计”“工人联党”“人群之说”“均产之说”(44)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8-229页。“傅氏”即傅立叶。等说明他显然了解社会主义,(45)关于康有为接触社会主义的脉络,参见[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2-344页。实际上,“人群之说”即“社会主义”(46)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引述赫胥黎的话,以夹注说明“社会主义”即“人群主义”。这里的关节点是对social一词的译法。因此,可以说《大同书》是提到了“社会主义”的,这一点以前似没有研究者论及。(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026页。)。但是,梁启超此处所论,其语脉却不是在承接康有为的社会主义论而已,而是要将康有为从《礼运》以及佛学特别是华严宗那里得来的思想与作为一种外来新思想的社会主义进行对接,或者说,是要提出中国固有思想中的社会主义维度,从而为其接受作为世界大势之一环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他极力强调康有为“未读一西书”(47)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79页。,目的或许不仅在突出老师“冥心孤往”的独创性,更为了显示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中的源生性。
1904年,他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将麦喀士(即马克思)和拉士梭尔(即拉萨尔)论在一处,认为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虽“颇耸听闻”,但其实无甚稀奇,因为“吾中国固夙有之”,王莽的“分田劫假”和宋代苏洵所论井田制废除之后田主与耕者对立的状况,与麦喀士、拉士梭尔等人之论口吻逼肖,进而断言“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48)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392页。此处所论,显示三年前他对老师的表彰并非只是出于私意,而是立足更宽广的中国史与中国思想的平心之论。
致力于开掘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自身的社会主义维度,在欧战之后更加集中。这一点与梁启超逐渐淡出政治、转向讲学著述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研究有关,也与他从这时起对作为一种政治道路的社会主义有更内在的接受这一动向互为表里。如上文所述,欧战之后,梁启超不仅在世界大势的脉络上将社会主义作为大势本身来加以把握,而且更显示出将社会主义作为内在于中国现实的、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来理解的倾向。他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已经在中国发生的运动为前提,来思考如何扩大劳动阶级和转化游民阶级,从而锻造更广大的政治主体的。
对这一脉络的完整把握,或当从《欧游心影录》开始。《欧游心影录》已经提及其与欧洲“社会党名士”在谈话中说起“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讲到井田制度,又讲些墨子的‘兼爱’、‘寝兵’”等学说,从而引起对方的兴趣与赞叹。(49)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2986页。更重要的是,梁启超通过对战后西方的生计、财政、革命、科学、思想、文学等几乎全方位文明状况的检讨,而提出的新文明再造以及“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50)同上,第2985页。这一课题,相当于为其接下来系统整理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倾向确立了总前提。
这种整理可以分为两种脉络来加以解析。首先,是立足中国历史,对中国社会结构之阶级状况的梳理。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状况的论述散见于1920年代的多篇文字之中,最集中的当推1925年在清华大学所讲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题为“阶级”的上下两节。梁启超认识到阶级是人类社会所不能免的普遍现象。他历数从春秋时期以至清代阶级演变的脉络,并不否认比如六朝以至唐代的族望门第之别,也不否认在金元清时期以种族区别阶级的现象。在《阶级(下)》中,他对中国古代奴隶身份的源起和流衍也做了系统梳理,看到“最近至清中叶仍常发见有承认买卖人口为正当权利之法令”,而且“就事实上论,女婢至今依然为变相的存在”,但他的总判断是中国“自有成文史籍以来,严格的阶级分别,即已不甚可见”。(51)梁启超:《中国文化史》,《梁启超全集》第17卷,第5103、5089页。这个意思在1921年有更斩截的概括:“故就大体论之,自汉以来,国民之公私权乃至生计的机会,皆可谓一切绝对的平等。”(52)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345页。
对中国古代社会无明显阶级对立的现象,钱穆、梁漱溟等都有过肯定性的分析。梁启超的分析与钱、梁等有重叠之处,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梁启超的论述紧密承接对中国固有历史之平等精神和社会主义倾向的分析,是在经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之后,为了承当“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的脉络中引发的。其二,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并不否认以贫富对立为主要内容的阶级问题在现阶段和将来的存在,或者说,他并不否认现阶段和将来阶级斗争之可能,他所积极论述的是古代。他明确说:“现代新阶级发生,全以‘生计的’地位为分野,前此之血族的、宗教的阶级,已成陈迹。我国民虽未受旧阶级之毒,然今后新阶级之发生,终不能免,所谓‘绝对平等’者,权衡将破,不别谋所以顺应之,其敝或视他国更甚。”(53)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345页。这一认识也贯穿到后面,他对奴隶问题的预言是“奴之名义,固非现代所能复活,然而变相之奴且将应运生焉”(54)梁启超:《中国文化史》,《梁启超全集》第17卷,第5104页。。此“运”即生计分野之运,即现代新阶级分化之运。这也是梁启超在1920年代反复论及有业阶级、无业阶级、游民阶级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阶级状况的分析脉络之外,是更加密集的对中国古代思想之社会主义倾向的高扬。这当中尤其典型的是1922年先后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南京东南大学等地所讲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该书开宗明义,在“序论”中即指出:“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与现代欧美人所倡导者为同为异,孰优孰劣,此属别问题。要之此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5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12卷,第3604页。其“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梁启超从生计、阶级、法律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特别指出“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56)同上,第3605页。。这特别见于孟子的经济思想。附带着说,梁启超对先秦思想之积极面的发掘,特别注重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其表彰孟子“认经济问题为改良社会之根本,与后世之耻言生计而高谈道德者有异矣”(57)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324页。也是其夫子自道。这些分析的特点可以说都显示社会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总之,在梁启超看来,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不过百年,而“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5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12卷,第3605页。。
不仅春秋战国思想如此,在中国历史的源头处,在夏殷时期、在大禹那里就已经具备了此类思想:“其政治上之理想,则世界主义、统一主义、平等主义、博爱主义等,发达最早,此皆大禹人格之化成。”(59)梁启超:《纪夏殷王业》,《梁启超全集》第12卷,第3472页。为进一步阐明此义,梁启超详论三代时期的天教和祖教,认为“此等最闳远最普遍最高尚之世界主义博爱主义,三千年前西方各国各教所未见及者,我国盖视为布帛菽粟焉,此天教祖教之极效也”(60)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梁启超全集》第12卷,第3597页。。
更进一步,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固有思想中不仅富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从而可以接引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还有为后者所不及的、更加超越的维度。他认为儒家的絜矩之道和同类意识超过“国民意识”“阶级意识”,因为后者导向人之相离嫉,而前者导向人之相和合,导向一种“天下”政治。他认为《礼记》所载之“不必藏诸己”“不必为己”等“与今世社会主义家艳称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格言正相函,但其背影中别有一种极温柔敦厚之人生观在,有一种‘无所谓而为’的精神在”(6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12卷,第3640页。“无所谓而为”,原文如此,且多个版本如此,疑应为“无所为而为”。。他还批评“近代欧美学说——无论资本主义者流,社会主义者流,皆奖厉人心以专从物质界讨生活”,从而都是浅薄偏枯的,而儒家思想中别有一种可以导人精神生活向上、尽人之性的能量,可以建设一个“仁的社会”。(62)同上,第3694页。诚然,这些批评未必全部成立,在梁启超那里这些也并不是定论。他的儒家论持有一种始终开放的对话的态势,儒家自来就吸收过道家佛家的思想,现阶段也要吸收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甚至说:“凡欧洲新的政治学说,社会主义,皆与儒家以极大的影响。”(63)梁启超:《儒家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7卷,第4962页。当梁启超在去世前两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所想到的例证或许就是自己。
五、结 论
梁启超著述宏富,所涉论题极为庞杂。举凡古今中西的思想学术、政制国体、内务外交、财政货币、疆域民族、地理交通、天文历法、科学宗教、家族婚姻、国性民风、文学艺术,等等,无不论列。这当中,他所身历的戊戌变法、民国肇造、办报组党等事件,其以专书的规模加以探讨的新民说、新史学、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题,都是历来研究者所特别关注的。相比之下,其社会主义论述就数量来说在其全部论述中占比较小,又没有形成专书,不免显得浮泛。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社会主义问题在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绾合的作用,他对世界大势、中国现实、中国历史与思想的观念都汇集于其社会主义论这个点上,而且“社会主义”是作为这诸方面的观念之归宿而存在的。上文曾指出,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接受社会主义,而且近乎是一个行动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这一前景在其后期的思想世界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然,正如梁启超自己也意识到的,他从贫富对立、分配、有产无产等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未必符合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定义,然而这不足为病,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具体的时空条件能够完全复制那种规范的定义。进一步说,所谓规范定义只能是一种理论假说。历史总是在特定风土中展开的,在这特定的风土中,所有规范性的理论都可能而且必然是变形的。名与实的关系不是单向抑制或者相互束缚的关系,而是相互导引、相互激发的关系。在相互的导引和激发中,既有的名与实会同时蜕变,而将历史推向新的高度,这正是梁启超所努力的方向。
我们通过对梁启超在世界大势、中国现实、中国思想这三条线索的社会主义论述的分析,综合呈现了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来源、内容、特点、演变过程、现实效能以及这诸多方面所形成的张力结构,从而可以说勾勒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梁启超”的形象。但这并非是本文的终点,甚至并非本文的目的,因为这一形象本身仍然是开放的。这是一个通过自己的思想苦斗从内部凝结起来的形象,而不是随顺和屈服于时流的结果。本文想进一步提出的是梁启超在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将作为世界大势且是“高尚纯洁之主义”的社会主义运用于解释中国现实,并与中国固有的历史脉动和思想脉动相勾连的问题界面上,其所表现出来的欣喜、困顿、挣扎、激越等姿态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方式。相比于这一边界明晰的、作为结果的形象,更重要的毋宁说是这一形象所得以完成的那个绵延的、苦斗的思想过程。
然而如果不勾勒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就几乎不可能触及到严格意义上的梁启超的思想方式。正是由社会主义这个总问题才带出如下一系列问题:如何结合经济来运思或者说经济地思考,如何理解资本、暴力、精英群体、士人、群众运动、劳动阶级、游民,等等。在此,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作为答案的主义话语,而是作为新问题的一根引线而存在的。由此引线所牵出的这一系列新问题是他素所研习和写作的今文经学、清代思想学术、道佛学,以及他所表彰的大学问家如斯宾塞、赫胥黎、达尔文,大政治家如霍布斯、卢梭、伯伦知理,大哲学家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等所无法直接回答的,也就是能够暴露出其固有知识体系之限度的问题。而正是固有知识体系之限度的展露,或者说对这种限度的自觉,召唤着新的思想方式的诞生。
综合而言,经历了欧战、十月革命、“五四”等一系列新的历史事件,进入二十年代之后,新的社会现实逐步凸显,在这新的社会现实当中,最具新颖性也是最具冲击力的就是底层“民众”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的凸显。“民”、“民众”是在清末的历史变局中登场的,《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取名即来自那一变局。但在那时,“民”或者“民众”还主要停留在理念的状态中,民之名与民之实还没有真正对应。只有在经历了1920年前后内外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之后,“民众”才逐渐摆脱理念化的状态而现实化,作为理念的“民众”此时开始具备了自己的肉身。对于这种新的现实,思想界的回应方式可概括为三种。一种是绕开或者背向这一现实,仍然沿着清末以来的路径而拓展其思想和学问世界的,这一取向在进入二十年代以后逐渐被目为保守。一种是目击世变而迅速放弃旧学并抓住了新思想新学说而与新现实共同摆荡的,这一取向在当时被目为新派。第三种,则是没有放弃对新现实的把握,同时也不放弃自己的固有学问,于是呈现出一种竭力伸展自己固有学问之极致来触碰现实的运思轨迹。如果将1920年前后的现实问题比作是一面高墙,则第一种思想方式是貌似绕开高墙,而实质是驻足于高墙之内的方式,第二种方式是凭借新思想的云梯翻越高墙的方式,第三种方式则既不是驻足也不是轻松跨越,而是竭力伸展自己的思想指爪,试图推倒这堵墙而又不能不碰壁的方式。这第三种方式,就是梁启超的方式。从这里,也就能把握梁启超的思想位置。
梁启超的学问之密度与思想之深度,或有可商之处,但梁启超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始终努力自觉内在于自己的时代,始终努力保持把自己的同时代问题化并持续地加以追问。关心和思考现实是一句熟语,但要真正关心和思考现实又谈何容易。现实一方面是作为经验材料的杂乱无章,一方面又是作为瞬间的稍纵即逝。于是,我们习见的和现实的关系要么是被现实所压倒,要么是执守一套学说以试图压倒现实。执守无论旧或者新的某套学说以绕开或赶上现实,说到底都是将现实推开,让自己处于安全状态的外部性的方法。梁启超的选择则相反,他自然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所学所信,但他没有回避现实,他并且持续使自己保持对现实的敏感,持续地追问现实。现实横亘在他前面,他碰壁,但他没有停下,他持续使自己的运思趋向于去把握这种新的现实,从而使碰壁成为其运思的常态。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碰壁的过程之中,梁启超展现了其运思的极限状态。
这种极限状态的具体展开,即是既有的思想被撑到极致,不断向前、向着未知的状况伸展。及物、及于新的现实问题,但又不能完全地把握这些问题,更不能穿越这些问题,而只能竭力地去抓取,以至于在这些问题上留下斑斑指痕。这是一个思想与问题撕扯的界面。思想在这个界面上挣扎,乃至困顿、徘徊。它不是平滑流利的,而是带着迟疑的钝感。当梁启超属望劳动阶级成为将来改造改造社会之主体,而又认为“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有增加游民”(64)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334页。;当其意识到政治运动的意义,但是对“今日之中国,是否当以政治运动为主要的国民运动”,认为“吾亦不敢言”;(65)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338页。当其认识到“由少数而多数而大多数而最大多数而全体,便是政治的极轨,也是政治进化一定的程序”(66)梁启超:《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389页。,而同时困惑于中国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究竟如何划分;当其痛悔于“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67)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410页。,等等,即是展现了这种迟疑的钝感,展现了这种思想的极限。必须强调,这不是在检讨梁启超思想的“局限”,仿佛这是可以轻易跨过和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政治主体的锻造、政治运动的利弊、阶级的划分等,在此后历史上也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的,而且有的问题还不断反复。以为可以一次性就能解决问题,可能只是问题的空洞化和历史的反复。相反,正是在梁启超的迟疑的钝感之中,保留着对现实难题本身的忠诚,保留着其在极限中运思的艰苦,和由忠诚与艰苦而来的沉实之感。这也因此就是使思想不断地保持在由否定和自我否定所构成的不安定之中,使思想持续面对未知的次元,使思想裂变奔突而时时欲冲破其自身界限即处于临界的状态之中。这是一种临界中的思想,是思想的临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