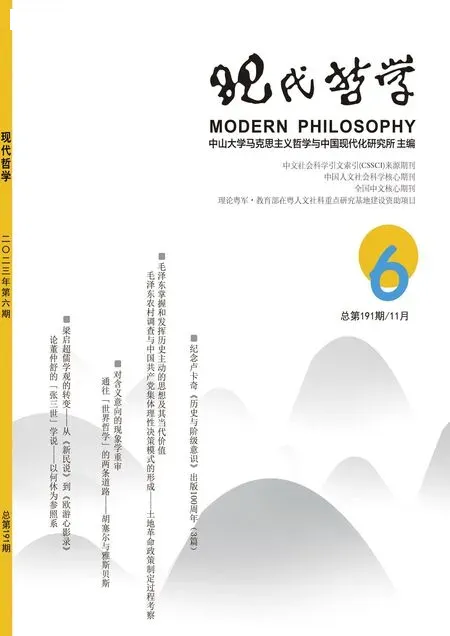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
——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干春松
一、“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
梁启超在投师康有为之后,在万木草堂与其他康门弟子一起研读《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因而成为晚清公羊学的追随者。不过,按梁启超的叙述,最令他激动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义”,曾决意要宣传而被康有为以时机不成熟而阻止。但是,康梁之间对儒家如何引领当时思想的路径分歧,在康有为集合学生撰作《新学伪经考》时期就已经有所表现:“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7页。的确,为了强调公羊学对于“改制”的意义,康有为多有引述纬书,将孔子视为“大地教主”的说法,而这些是梁启超所不能认同的。不过,梁启超的反抗也许并不十分激烈,1897年他去长沙时务学堂开讲,主要内容即是宣传康有为的思想,其中也包括陆九渊、王阳明的哲学和公羊家的思想。(2)苏舆所编的《翼教丛编》中收录有叶德辉批评梁启超《春秋界说》《孟子界说》的文字一篇,其中《春秋界说》主要阐发的还是托古改制等公羊学的思想。可见,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并没有真正放弃春秋学的观点,可能是不同意大地教主的思想。(参见叶吏部:《正界篇》,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89-94页。)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接触了日本思想界译介西方的许多言论。(3)郑匡民先生说,梁启超利用“和文汉读法”广泛阅读日本书以及日译西籍,涉及当时日本各流派的思想,也摄取了西方思想的许多方面,并经过他所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刊物向国内广泛传播。(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页。)他同样与革命派多有往来,在1903年春夏之交,甚至与部分康门弟子一样转而支持革命派的主张,引发了康梁之间的思想分歧。他这个时期开始写作影响巨大的《新民说》。就在写作期间即1903年前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在康有为的严厉斥责下,梁启超放弃了甚为激烈的革命主张,重新回到康有为的君主立宪立场,并写下《开明专制论》,主张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反对革命派的“共和制”理想。按张朋园等先生的说法,在1903年以后,梁启超改变了救国的方针,1903年以前的梁启超,“与其说他是维新派,不如说他是革命派,更为接近事实,更为合理”(4)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79页。。然而在考察了美国等地之后,梁启超发现民主制度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完美,他接受国家有机体的观念,强调群体自由高于个人自由,并认为一个国家的建立需要有强有力的权威。通过跟孙中山等人的接触,梁启超反而认为在缺乏政治基础的国家建立共和政治,可能的后果是诞生一个不负责任的专政,因此转而主张“开明专制”,认为这是在当时的中国最为合理的政治体制。特别是革命派所主张的民族革命的手段,让梁启超担心民族分离主义的滋长。在他看来,中国注定要建立成一个多民族国家,采用种族主义的革命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因此开始提倡大民族主义,并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
虽然在政治上与康有为再度合流,但梁启超在孔教问题上与康有为越走越远。康有为之所以强调孔教的重要性,是要为新的国家提供共同信仰以增强凝聚力;而梁启超则认为创立孔教与建立现代国家的目标并无直接关联,更与国家是否能强大无关。他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集,第279页。从这段梁启超的自述可以看到,对于康有为保教立国的设想,他不但不同意,还写专文批驳。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之后,深受日本进化主义思想的影响,将宗教视为迷信和缺乏人格独立的根源,因此反对将孔子视为教主,认为尊孔的本质是“依傍”,“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6)同上,第280-281页。。
由此,许多学者认为,康梁在孔教问题上的分途,表明梁启超的思想实质上已经离开了儒家。比如,列文森和张灏等认为,梁启超思想不再是儒家传统的现代发展。同样的观点以刘纪曜先生的表述最为系统,他认为“梁氏在形式上虽仍跟着传统,但是在实质上已离开传统……在理想上,梁氏肯定追求基本的道德社会,然而却已完全放弃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在手段上,他不再以圣人作为中心枢纽,而以国民全体作为手段的诉求对象;在论证上,他除了保留形式的道德本体之信念与修养工夫之论证外,其他传统儒家在‘心性’方面的论证,都已被抛弃”(7)刘纪曜:《梁启超与儒家传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85年。转引自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5-26页。,他的结论是梁启超与丁文江和胡适的思想立场更为接近。
将梁启超和胡适、丁文江这样的对儒家传统多持否定意见的人士进行比较可能并不匹配,即使在20世纪初,梁启超对孔教多有过激的言辞,但他并没有否定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人道德价值的基础。他在民国建立之后,也参与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活动。特别是作为巴黎和会代表游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之后,他对儒家的态度有很大的“反转”。据此,有许多学者认定梁启超没有脱离儒家立场。黄克武先生这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梁启超在1903年之后与儒家传统之间的连续性:首先,针对个人修养,梁启超依然持道德优先,这与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是一致的。其次,虽然梁启超重新定义了道德的范围,一度批评儒家缺乏公德只重私德。但1903年之后,他又强调公德的养成不能离开私德的基础,私德和公德之间是内在统一的,这与《大学》的修齐治平和《中庸》的成己成物的理想之间有连续性。再次,他对宋明理学中道德形而上学的部分虽然讨论不多,但是他思想中的良知本体论和其他修身工夫是紧密相连的。最后,梁启超继承了清中叶以来的经世传统,企图解决内在道德、知识追求和外在事功上的成就的统一,并一直尝试着会通中西,这样的观念被牟宗三和唐君毅等人所继承。(8)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李喜所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6-147页。这种强调梁启超与现代新儒家的连续性的说法,是将整个近代儒学视为一个整体发展的一种比较公允的看法。
梁启超与儒家关系的诸多分歧很大程度上源自其思想复杂多变,也是因为他思想上的新旧交战和性格上的矛盾纠结,正如他所说:“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集,第279页。将保守性和进取性的“交战”解释为生性上的弱点,多少是把近代士人的普遍性的困境个体化了。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在接触西方并试图学习西方,但包括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严复等西学先驱在内,他们身上总是能体现出由激进的反传统向温和的回归儒家传统的“回转”。梁启超因为经历复杂,所以在立场上的转变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多元。
梁启超转投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改宗公羊学,在湖南时务学堂时期主要是传播公羊学以及变法革新思想,由此引发了翼教派的攻击。梁启超虽然积极传播康有为的公羊学观念,但并不能看出他有坚定的经学立场。在戊戌前,梁启超就已经放弃了他的公羊学的立场。有趣的是,到了晚年转入学术事业之后,梁启超又开始借助一些公羊学的因素来阐发自己对儒家传统的理解。
在1920年所作的《孔子》中,他在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时候,就强调《春秋》是孔子政治观念的载体,并列专门的章节来说明“春秋的性质”。首先,《春秋》非史,如果春秋是记录史实的,那么孔子就不是好的史家,因为《春秋》含有大多的褒贬和“曲笔”,如果把《春秋》看成是历史的话,既把《春秋》毁了,也把史学毁了。其次,《春秋》是孔子改制明义之书。《春秋》是一部革命性的政治书,要借它来建设一个孔子的理想国,所以《春秋》说的是“天子之事”,为万世立法则。第三,治《春秋》当宗《公羊传》,辅之以《谷梁传》和《春秋繁露》。这一点继承了康有为将《左传》看成刘歆增裂改窜的说法,重视《春秋繁露》也是康有为的一贯理路。第四,《春秋》的微言大义,传在口说。第五,存在着未修《春秋》与既修《春秋》。最后两条都是在用公羊义理说明孔子的许多政治理想是要从《春秋》的字里行间仔细品读出来,而不能拘泥于字面。(10)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10集,第347-348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梁启超对谶纬之学做了有限度的批评,但基本立场是回归到乃师康有为的今文家的立场上。所以,梳理梁启超对儒学、儒教的认识,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梁启超政治哲学的演变。
二、《新民说》对传统儒家的反思
从效果而言,梁启超的言论以破坏为特色。不过,具体到儒家,他始终是褒贬并举。在影响巨大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在谈到儒学统一时代的到来所产生的影响时认为,儒学对于中国人的风俗、名节和民志的确立意义重大。他列举说:“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也”,儒家以名教行世,把名节看作是公私道德的根本,并转化为社会风俗,这样便抑制了人们求利的冲动;“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也”,儒家虽以大同为目标,但发展却不可躐等,小康是通向大同的必经之路,这样小康社会秩序也有其合理性。
而在不良后果方面,他也提出两条:“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则君民权限不分明是也……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规劝君主要行仁政和体恤民意,这固然是儒家所坚持的,若民无权制约,如或有君不行仁政,那些劝说就没有任何的效果。因为君有权而无义务,民有义务而无权利,这样中国几千年的政体是“儒其名而法其实也”(1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61-62页。。
还有一项不良的后果是“一尊定而进化沉滞也”。深受进化论影响的梁启超坚信只有竞争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政治上的权力独占谓之专制,而不容别的学说之发展的思想控制也是专制。儒家思想的一尊造成中国的思想专制,这虽非孔子之本意,“夫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1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63页。。应该说,这个评判还是比较公允的。
梁启超对儒家的思想进行更为仔细的剖析的是《新民说》,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至二十二号,五十三至五十八号)、《保教非所以尊孔》(二号)一样,《新民说》(第一至十四号),也是《新民丛报》时期的作品。梁启超《新民说》的写作,是在流亡日本时期大量接触当时在日本影响巨大的思想家福泽渝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的作品后所有感而发的。一直致力于制度变革却以失败告终的他深感国民的素质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期待塑造一代新的国民,就要从道德和价值观上入手。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要发展,要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关键在于国民的素质。他比较中西差异之后,指出西方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是有其国民素质和价值观念做支撑。他希望中国的国民也具备这样一些的“长处”,所以要“新民”。
由此可见,《新民说》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梁启超对中西不同道德和价值观念之间所进行的对比,并取长补短。所以在书的开头,梁启超就宣称:新民是要面对内政和外交这两个当时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新民”并非是完全移植外来的价值,而是面对内政疲弱和国际上的“民族帝国主义”,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国民”:“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3)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33页。他既反对墨守成规的保守,也反对“心醉西风者流”。但是从作品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倾向性,他更多是要用西方近代的观念来“革新”中国人的观念,而“淬厉”本有道德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展开。《新民说》中与儒家思想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是讨论天下国家观、公德私德之辨和自由民权意识的培育。
(一)对于天下国家
梁启超认为,欧洲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主要是基于“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
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而一用政策以指挥调护之是也。(14)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30-531页。
他举俄国和德国的扩张例子来佐证。这是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一种十分清晰的描述,并指出民族主义在对外关系上,往往会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对弱小的民族国家进行扩张和倾夺。中国近代的衰弱就是受到民族帝国主义的欺凌而中国自身则缺乏这种意识。
梁启超评论道:中国的儒者开口就是平天下治天下,将国家视为渺小的一物,这导致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将是否发展出“国家”的观念视为文明与野蛮之别。以前的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所以并没有发展出爱国的精神。在国际关系中,持有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立场,也会产生对国家在价值上的轻视。他说,世界主义固然是美好的理想,但在充满竞争的国际格局里,国家才应成为一切关怀的基点。他在《论国家思想》一节中,对“国民”概念做了解释。他说,人类早期并无国家思想,只有部落思想。“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15)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43页。有了世界,就有国家之观念,即你与别的国家一起构成“世界”:
宗教家之论,动言天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虽然,此等主义,其脱离理想界而入于现实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将安取之?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争竞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若曰并国界而破之,无论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况人之性非能终无竞争者也。然则大同以后,不转瞬而必复以他事起竞争于天国中,而彼时则已返为部民之竞争,而非复国民之竞争,是率天下人而复归于野蛮也。今世学者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为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由也。然则言博爱者,杀其一身之私以爱一家可也,杀其一家之私以爱一乡族可也,杀其一身、一家、一乡族之私以爱一国可也。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何也?其为部民而非国民,一也。(16)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44-545页。黄进兴说:“梁氏的《新民说》毋庸讳言,充溢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并且见证了中国从普遍王权(天下),至现代列国体系的转变;这个转变连带调整了固有的道德秩序。”(黄进兴:《追求伦理的现代性:梁启超的道德革命及其追随者》,黄进兴:《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18页。)
在这里,梁启超认为古代儒家的天下主义和其师康有为的大同主义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方案,如果方案过于理想而难以落实,则又为野蛮者也。
(二)对于公德和私德
公私问题为近代思想家所关注的大问题。梁启超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他对公私观念作了新的说明,并开始用新旧来描述中西的伦理观念上的差异:
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范围证明之。)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相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事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乎?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虽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全体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17)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39-540页。
梁启超以儒家五伦观念出发,认为儒家伦理中对于家族伦理有完整的系统,而对于社会国家的伦理则不完备。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但以往的道德教育只提倡私德而不注重公德,造成传统道德的偏向,也造成公德和私德之间的妨碍:“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18)同上,第540页。其实,就公私关系而言,近代的中国人并不提倡西方启蒙意义上的个体观念,而是比较重视“群”的意识。严复在翻译西方的自由概念的时候,就考虑到个人权利和群体责任之间的关系,所以强调“群己权界”。对此,梁启超批评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认为“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19)同上,第540页。。如果只享受权利,而不尽其义务,那么这个人不但无益于群体的利益,反而会称为群体之“蠹”,因此每一社会成员要善于“合群”。梁启超提倡的新道德就是以合群为目的的公德:“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画而不敢进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20)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42页。梁启超深受日本的进化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常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来评断传统儒家伦理,提出“道德革命论”。这固然是种族竞争的大势所趋,但对于道德系统的稳定性也造成一定的破坏。(21)郑匡民:《梁启超的政治哲学》,干春松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4页。
(三)自由和民权
梁启超的自由观深受中江兆民等人的影响,比较重视团体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他认为文明的发展就是不断由个人的自由向追求团体的自由方向发展,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对秩序和法律的服从。与此同时,梁启超的自由也指向对于思想的自由,因此要不成为心的“奴隶”,就要不做古人的奴隶、世俗的奴隶、境遇的奴隶和情欲的奴隶。
对于权利的思想,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他认为这会被人视为懦弱而变本加厉,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郑匡民先生认为,梁启超因为受加藤弘之和宇都宫五翻译的《为权利而斗争》一书的影响,认为人的权利来自于“强”,世界既然是一个竞争的场,所以无所谓道德和正义,只有生存竞争,而强者则是通过斗争才能获得,所以他甚至主张强权就是权利。(22)同上,第212页。他借用儒家的仁来说明中国人缺乏权利意识的根源:
大抵中国善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界,吾不敢言,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以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倚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乎?)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23)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59页。
儒家的政治哲学之基础在于仁,由不忍人之心而发展出仁政。但在梁启超看来,这样的政体因为抑制了人们的竞争求生存之心,导致人们缺乏权利意识,只是等待圣人来行仁政。所以,养成国民的权利意识是建构现代国家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他天真地认为个体权利之和就等于群体之权利,由此,他所谓的自由也不是个人基于权利基础上的自由,而是国家在竞争的世界中的平等权利。
从对于《新民说》的上述分析可知,梁启超虽然主张中西兼采,但总体的倾向是贬低儒学而褒扬西方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他的“新民”的基础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造中国人。
梁启超1903年有一次美国之行,在回国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私德》,当时就有人批评梁启超屡次自悔前论,适足淆乱人心。不过,因为过于从族群和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自由和权利,梁启超言论的自相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他辩解说:“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故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24)同上,第633页。梁启超说私德与公德之间不可区分。他自我批评道,以前认为建设新道德要尽弃旧道德有失偏颇,道德起源于人的良心,并无新旧之分,所以以别的社会的伦理原则来改造国民,就好像“吹沙求饭”,是不可能的。他还编写《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认为儒家的价值观,特别是阳明心学对于培育国民的私德十分重要。(25)郑匡民认为,梁启超由提倡公德向私德转变与访美体验和革命派的迅速发展有关,但其目的依然在于固群,所以不能将梁启超提倡私德和王学认为是政治上的后退。陈来认为,梁启超重视个人道德的重要性,表明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参见郑匡民:《梁启超的政治哲学》,干春松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3卷,第218页;陈来:《儒家美德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32页。)
三、《欧游心影录》对儒家文化的重拾
1919年梁启超在游历刚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的时候,发现欧洲人正在经历着一次价值观矛盾(26)20世纪20-30年代,欧洲流行一种有关没落和衰败的言论,其主要症侯是:反历史主义;体认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中所扮角色的重新重视;历史循环论的复活;体认欧洲并不居于世界的中心,且处于文化没落的痛苦之中。显然,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到梁启超晚年的文化主张,使他更接近于折衷主义。(参见耿云志:《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第240页。),社会思潮中互相对立的思想,如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都在发生尖锐的冲突。对于科学也是这样,在上帝已经被人杀死的时代,人们在质疑人生的意义能否由科学方法来赋予:“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要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象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27)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10集,第63页。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所以梁启超呼吁人们从“科学万能”中醒悟过来:“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28)同上,第64页。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呢?因为国家才容易把国家以内的一群人聚拢起来。然而我们却要去锻造一种新的文明,融合西方人的实验科学方法和中国人热爱和平的价值观:“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29)同上,第85页。第四步则是要把这个新文化系统向外扩充,使世界受益。
在这个时期,梁启超的想法更像是一个调和论者,即中国的道德原则和西方的科学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将西方的物质文明与东方的精神文明、西方的个性解放和中国的人格修养结合起来。他还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尽性主义”来概括这种结合了东西方优点的新文明形态:“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中庸》里头有句话说得最好:‘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我们就借来起一个名叫做‘尽性主义’。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就私人而论,必须如此,这才不至成为天地间一赘疣,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会国家而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30)同上,第73-74页。这种说法在《新民说》的“论私德”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里只是更为强调其与儒家思想的同调性。
梁启超一直将竞争视为进化的根据和文明创造的动力。在这个阶段,他了解了一些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他认为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助精神:“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出于克己精神和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也。”(31)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申报》1920年3月14日。(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页 ,标点有改动。)与《新民说》时期极力主张竞争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梁启超开始强调互助的重要性。
在政治制度上,梁启超一直主张国民的参与。这个时候,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有一种超脱政治的态度,所以像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政治并不符合中国人的政治习性:“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32)同上。梁启超在民国成立之后一直主张共和,并不惜与康有为决裂来坚持民主政治的理想。在经历许多政治波折之后,他改而认为民本主义和西方代议制的结合是最符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主张要把中国的国民性发扬光大。
四、总 结
以上分析揭示了《新民说》与《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在不同时期的儒学观的转变。《新民说》时期以贬低儒家为主,《欧游心影录》则强调儒家思想在现代世界中仍有价值。虽然梁启超的态度前后差异较大,但在目的上依然有着一致性,即培育国民道德以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正因如此,在批判儒学为主的《新民说》中,更为重视个体心性的阳明学还是受到了梁启超的青睐。而在深入了解西方文明危机之后,他又立足于文化层面找寻儒家的现代价值,以塑造新的国民性、建立一个会通中西的新国家。总的来说,梁启超的儒学观始终围绕着建设国家的主题而展开,并不断因时局改易。随着对世界局势认知更为清晰,梁启超对儒学也更加认同。这一现象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