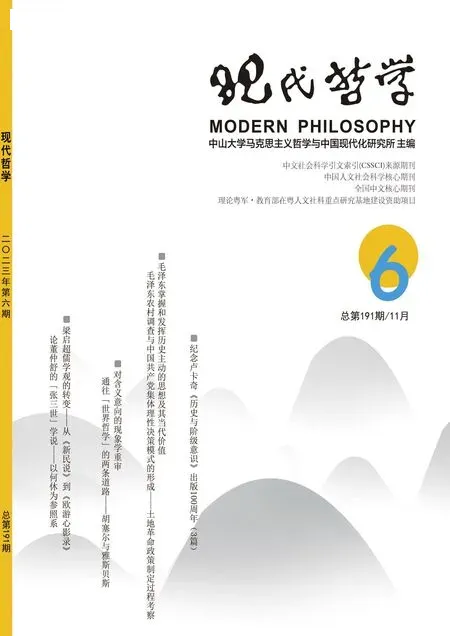破出存在:列维纳斯论身体
——物质性、感受性和超越性的三重交织
张荔君
西方哲学主流传统认为人由灵魂(精神/思想)和身体这两部分构成,这一传统强调精神、思想而贬抑身体,精神意味着人的崇高性和超越性,身体则标志着人的动物性和有限性,身体总是遭到贬抑和排斥。身体被当作精神的负担,精神的攀升最终通过摆脱身体的有限性来克服身体的障碍。身体问题在当代法国哲学的语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且与主体性问题密不可分,对身体的探讨构成了当代法国哲学探讨主体性的独特视角,身体的哲学地位经过当代法国哲学的重新诠释也得以愈加凸显。对身体的重视构成受胡塞尔、海德格尔影响下法国哲学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构成列维纳斯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列维纳斯看来,身体既是内在性或享受实现的场所,也是形而上学的超越运动(1)“形而上学的超越”表示主体“向绝对他者的超越”,超越并不是否定,而是与无限他者构成一种并不进行同一化的“关系”,既维持主体的内在性又维持他者的绝对差异性。因此就超越运动的方向而言,形而上学的超越是“向上的”,朝向绝对他者的;从超越关系的两端,即主体和他者而言,二者的地位是“不对称”的,他者高于主体,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对称”的,关系的不对称性保证了超越运动的单向性。(参见[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一部分第一章。)得以进行的基础。理查德·科亨(Richard Cohen)曾在《别于存在》(2)Le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La Haye :Martinus Nijhoff,1974. 本文将该书名译为《别于存在或超逾去在》(简称《别于存在》),伍晓明译为《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下文简称《另外于是》。的英译本导言中指出:列维纳斯的伦理回归到主体内在的感受性,回归到自我牺牲的、替代的主体,因此超越更深地根植于身体之中。(3)Cf. Richard Cohen,“Forword”,Lévinas,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trans. by Alphonso Lingis,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8,p. xii.本文拟通过物质性、感受性和超越性这三重特征对列维纳斯的身体观进行阐释,对这三重特征在身体问题上的交织进行说明,并以身体问题为示例来探讨列维纳斯“破出存在”(dés-inter-essement)的思想意图及可能的实现方案。
一、物质性与安置:身体的同一性与享受之延迟
身体与主体的主体性、主体的诞生相关联。主体的诞生通过安置(position)而发生,也就是通过身体的在此(ici)占据空间、通过身体以拥有位置(avoir lieu)而发生。身体安放于“此”,这个在此的“位置”(lieu)并不是一种客观空间或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作为开端的事件,身体的“此”就是安置这一行为实现的事件。安置(position)意味着存在者从有(il y a)的匿名性中自身凝聚,身体通过定位“在匿名存在中的爆发”(4)Levinas,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Paris:Vrin,2013,p. 105.并以自身为出发点。因此,身体首先并不是一个容器或者功能体,而是作为开端的行动和事件。列维纳斯指出,将身体当作事件,并不是将身体看作安置的工具或象征,而是将它看作安置本身,“通过身体完成了从事件向存在者的脱变(la mue)”(5)Ibid.,p. 105.。身体的安置作为开端的事件标志着一个存在者的诞生,即主体的诞生。可以看到,存在者的首要特点就在于通过身体而获取自身,列维纳斯称为“固守于(s’occuper)自身”(6)Levinas,Le temps et l’aut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3,p. 36.或“凝结于自身”(7)Levinas, 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p. 104.,这意味着存在者被束缚于其自身之同一性,这种固守于自身的方式即主体的“物质性”(la matérialité)(8)Levinas,Le temps et l’autre,p. 36.。鲁道夫·卡林(Rodolphe Calin)更进一步指出,身体能实现安置正是由于它的物质性,物质性使身体具有“重量”。(9)Cf. Rodolphe Calin,“Le corps de la responsabilité,sensibilité,corporéité et subjectivité chez Lévinas”,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2006(03),p. 300.
身体的“安置”使主体的诞生这一事件得以实现,然而作为开端事件的发生是瞬间性的,主体生存的维持无法得到充分地展示。因此,事件仅仅是生存论分析的第一步,还不足以说明主体的存在结构和存在方式。这就需要过渡到《总体与无限》(1961)阶段的相关分析中:“物质性”所表现的自身束缚和自身同一过渡为关于“内在性”(intériorité)的具体存在结构的分析,列维纳斯将这个结构的特点凝练为“享受”所具有的“感受性”(sensibilité)。“享受”意味着存在者诞生后的具体生存方式,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对他异性的吸收,意味着将其所享用的各种对象转化为同一。“享受”的运作是一种“需要-满足”的模式:需要源于缺乏,它寻求填补自身缺乏的对象,比如享用食物、睡眠、晒太阳等日常生活内容,它们都因缺乏而能够通过“享受”活动得以满足。(10)参见[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4页。“我能够‘享用’这些实在之物,很大程度上,还能够用它们来满足我自己,好像它们只是我的缺乏之物。因此,它们的他异性就被吸收在我的同一性之中。”感受性还意味着当下在此,进一步加强“固守于自身”的身体安置,“我是我自身,我在这里,我在家,我是居住,我是在世界中的内在”(11)同上,第119页。的这种自身同一,享受最终回返自身,即返回到主体内在性的生存,身体在享受的回返运动中不断自身凝结。
在“需要-满足”的模式中,需要具有某种两可性:一方面需要意味着依赖,对赖以为生的物质性或元素的依赖;另一方面需要的满足具有不确定性:满足需要之物(饥饿所需要的食物、口渴需要的水等)对于需要而言是外在的,属于与自身不同的相对他者。为了自身的满足能够维持,自我就必须在世界中通过一系列的家政活动(占有、劳动、居住等)延长满足,以克服满足需要的不确定性,需要因此同时包含着对不确定性的克服。“享受”活动通过身体进行,需要的两可性即身体的两可性:身体是对物质性或元素的依赖,同时是对不确定性的克服。身体一方面表现为对物质性的依赖,同一化运动进行的场所,同一化运动的中心;另一方面,为了克服需要之满足的不确定性,身体又是占有、劳动等一系列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通过承担一系列的家政活动,身体保证需要能够得到延迟的满足,并以此为基础克服存在者诞生于其中的有的匿名性,而将自身保持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个体,即保持为同一。然而,对需要及身体的这种两可性阐释为存在者存在的不稳定性留下了空间:由于维持存在者生存的物质性或元素来自于世界,它们相对于存在者而言是外在的,因此会产生这些元素的缺失或为了生存而争夺的情况,而克服这一问题的办法仅仅是通过一系列的家政活动。从时间性的角度而言,这种克服的方式是将需要延迟,以身体在世界之中不断地劳作和活动来抵御将来的不确定。这一解决办法实际上是不断地推迟不确定性,而并非真正地解决和面对不确定性。
可见,身体承担着两重功能:第一,身体通过安置,作为开端这一事件实现主体的诞生;第二,身体承担着主体生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身体承担着主体的同一化的具体活动,将主体维持为“持守于自身”的内在性;为了保存生存、延迟满足而建立起家,通过一系列家政活动实现对世界的占有。如果说通过身体的“安置”实现存在者的诞生这个事件是准备性的阶段,那么享受带来的占有将存在者安置于家中,这便是身体的同一化活动在世界之中的具体实现。(12)参见[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119页,第92页。换言之,列维纳斯通过对身体的安置和享受进行的分析表明了主体纯粹内在性的生存方式,身体在具体生存活动中承担着积极的作用,也是建立内在性的关节点。内在性的建立是为了给超越性提供基础,是通向他者的超越运动的准备阶段。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内在性的生存之中,身体似乎并没有为形而上学的超越留下空间,也无法解决将来之不确定性的问题。
身体仅仅为内在性的生存提供了解释,而并未为超越性留下空间,这种理解在列维纳斯更为早期的思想中已经可以窥见。早在1934年,列维纳斯在法国的《精神》杂志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反思》(13)Levinas,“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tlérisme”,Les imprévus de l’histoire,Paris:Fata Morgana,1994,pp. 23-33. 中译版参见[法]列维纳斯:《对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反思》,范民译,朱刚校,《西北人文科学评论》2010年第1期,第52-57页;[法]列维纳斯:《关于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几个反思》,邓刚译,《法兰西思想评论》2011年,第326-335页。本文引文参照范民译本。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列维纳斯指出由于西方哲学本身的缺陷,希特勒主义式的悲剧不可避免。在他看来,西方哲学的缺陷在于其主流思想将人与其肉身割裂开来,自苏格拉底开始就将身体看成是牢笼、枷锁,禁锢着人的灵魂:“身体像苏格拉底在雅典牢狱中戴着的锁链一样重压在哲学家的身上……身体是障碍。它阻碍着精神的自由冲动,它把精神又带回到尘世的条件中。但是作为障碍,它是要被克服的。”(14)[法]列维纳斯:《对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反思》,第54页。人系缚于身体,并且因为系缚于身体而没有逃避自己的权利,“身体不仅是把我们与不可改变的物质世界联系起来的快乐或痛苦的偶然物,它对自我的附着以其附着自身而宝贵。没人能够避免这种附着”(15)同上,第55页。,然而西方精神不愿意承认这种身体性的重要性。希特勒主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种族、血统等生物学观念混入其中,最终造成极端的种族主义屠杀。克里斯蒂安·西奥坎(Cristian Ciocan)指出,列维纳斯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关于身体的思想,他开始将人的身体看作是一种“依附/黏着”(attachement),“身体提供了一种体验,它使人依附在自己的位置上却又无法使其脱离”(16)Cristian Ciocan,“Le problème de la corporéité chez le jeune Levinas”,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2013(2),p. 204.,人之存在的根基就是以身体的方式黏着于这个世界,因此人的身体性阻止一切超越的运动。(17)Ibid.,p. 205.可见,在列维纳斯此时的理解中,人以身体的方式被固定于世界之中。身体使得人的存在有了支撑点,为人的具体生存活动的展开的提供了空间,因此为内在性的生存提供了积极的描述,同时内在性的建立构成超越的必要环节。但是,这种内在性的生存以自我保存为基础,它的运作方式即同一化,而同一化又意味着对超越的抵抗。更进一步,人被固定于身体产生了某种悖论式的影响:身体是内在性生存的基础,而内在性的生存一方面构成超越的前提,另一方面却由于其同一化运作的要求而抵抗着超越运动。这种理解延续到《总体与无限》之中,甚至到了《别于存在》中也依然能看到他对这种理解的坚持。
在写给戴维森教授的信(发表于1990年)中,列维纳斯坦言,在《对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反思》一文中,他确信西方“野蛮的根源在于根本的恶的本质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处于为了存在而操心的此在的本体论之中”(18)[法]列维纳斯:《对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反思》,第57页。,这预示着列维纳斯对存在论和西方传统理解的基调,也解释了为何他一直寻求超越,甚至寻求“别于存在”“破出存在”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身体真的无法为形而上学的超越提供某种说明吗?“破出存在”的可能性难道无法在其身体理论中找到突破口吗?
二、感受性的二重性与母性身体
1965年的《意向性与感觉》(19)Levinas,En découvrant l’existence avec Husserl et Heidegger,Paris:Vrin,2001,pp. 201-225.一文中,列维纳斯通过对胡塞尔的分析引出他自己关于身体的看法,他指出,身体既是表象的中心点和零点,它同时逾越出这个零点。换言之,身体既是进行构造的出发点和中心,同时已经内在于其所构造的世界,并由此能够“面对着”世界。这样的身体不仅“在世界之中”,“同时面对着世界并先于世界,并且抵抗着结构的同时性”(20)Ibid.,p. 222.。列维纳斯开始使用“历时性”(diachronie)概念,这一概念在其后期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列维纳斯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主体的终极秘密在于这种与结构的同时性不同的“历时性”,“历时性比结构的同时性更为强大”(21)Ibid.,p. 222.。“历时性”意味着非同时性、非同一化,不与自身等同,通过这个概念,列维纳斯将他异性的因素引入到身体的建构之中。尽管列维纳斯并未在这篇文章中进行详细阐释,但这个概念的引入表明了身体的建构中存在着裂隙,而这种裂隙为其后期思想的发展进行预演。然而,这种裂隙是如何可能的?它在身体问题中又是如何表现的?
阿尔特兹-阿尔贝拉(Altez-Albela)考察了身体在列维纳斯不同阶段思想中的功能,她指出,在《从实存到实存者》这个阶段,身体是“意识的降临”或主体的实体化的第一个场所(即“安置”这一事件),身体是关于“此处”的现象学经验。感受性被列维纳斯阐释为走出匿名性(即出离有)的因素,这与列维纳斯整个“超越性的计划”是相吻合的。她还强调,在列维纳斯的早期作品中,尽管身体承载着“作为超越的事件”的功能,但身体同时是固定住自身的基础。身体作为实体化的场所向自身回缩,受到存在和世界的限制,身体一方面是有限的,但同时承载着超越。(22)Cf. Fleurdeliz R. Altez-Albela,“The Body and Transcendence in Emmanuel Levinas’ Phenomenological Ethics”,Kritike,Vol. 5,2011(1),pp. 39-40.然而,在前述讨论中可以看到,身体尽管承担着主体诞生并维持主体生存的功能,但主体的整个生存结构是一种同一化的运作,这种运作之中缺乏进行超越的动力。那么,作为这种结构之基础的身体又如何能够承载“形而上学的超越”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要回到感受性这个关键性的概念。前文已表明,感受性是享受的特点,它的功能在于维持一个封闭内在的自我的生存。但是,感受性这个概念在列维纳斯思想后期具有新的含义。《别于存在》阶段,感受性从享受扩展为“易受伤害性”(vulnérabilité),扩展为“易受伤害性”的感受性在自我之中打开了一道缝隙,主体不再仅仅是自身同一的,其内部已经包含了差异。基于此,内在性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迎接他异性的可能性,而是在其内部已经产生裂隙并为他异性留出了空间。感受性新增了“易受伤害性”这一义,这一义主要体现为“母性”身体,“易受伤害性”和“母性”意味着主体内在的痛苦和创伤,易受伤害意义上的身体表明主体内在地受他异性侵扰,并在其同一性之先已经蕴含着向他者的敞开。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原本从外部而来的他人的诫命变成了“主体内在的沉默之声,它在同一的核心中震颤,并阻止同一安位于自身”(23)Francis Guibal,“Commandement,anarchie,ambiguïté:La pratique philosophique de l'excès chez E. Levinas”,Archives de Philosophie,2006(4),p. 557.。主体因此不再仅仅是封闭的内在性,而是由于其身体中的裂隙而蕴含了打破自身的倾向,因此也就具有了向他异性敞开的伦理倾向。如贝蒂娜·贝戈(Bettina Bergo)所言,列维纳斯“将感受性理解为向着他者的前自然的易受伤害性,以及被称为‘母性’的他者的内在控制……由于主体性是母性,分裂的主体性已经意味着伦理”。(24)Bettina Bergo,“What is Levinas Doing?Phenomen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an Ethical Un-Conscious”,Philosophy &Rhetoric,Vol. 38,No. 2,2005,p. 131.基于此,为了达到其思想的伦理诉求,列维纳斯将人的存在置于“享受的内在性以及伦理的超越性之间对立的紧张之中”(25)Ibid.,p. 136.,这种对立的紧张体现在感受性的享受和“易受伤害性”这二重性的对立紧张之中。
列维纳斯在其后期思想中指出“人的身体性作为感受痛苦的可能性,作为易受病痛的感受性,作为在毫无遮掩的自我暴露中、在自己的皮肤中的忍痛受苦的本己性,作为易受伤害的感受性”(26)Le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pp. 65-66;[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132页,译文对照法文原文有改动。。然而,感受性的痛苦这一义并不是在感受性扩展为易受伤害性的含义之后才存在的,在关于感受性之享受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窥见痛苦的端倪。列维纳斯在《别于存在》的注释中提示他早年曾对疲惫(fatigue)进行过分析。(27)Cf. Le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p. 69,note 39.在其早期的分析中,存在(existence)的基本结构分为两种:一是存在(être),另一是拥有(avoir)。这个结构被称为“存在之努力”(conatus essendi)。只有在存在之努力中才会有“疲惫”,疲惫本质上是疲于存在;努力意味着挣脱出疲惫,从存在的匿名性中挣脱,但这种努力却又随时可能重新落回疲惫。疲惫和努力形成了“存在之努力”结构中的张力:努力意味着承担存在,而承担存在就意味着行动,存在者的存在即行动。(28)Levinas,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pp. 37-46.然而,相对于存在的匿名性而言,努力构成的行动总是“滞后”的,这种滞后即疲惫感的来源。就时间性的角度而言,存在者的存在以时间性的“瞬间”之开端作为标志,瞬间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功能,是因为在瞬间中首先蕴含着“一个行动,通过这一行动,实存者获取自身”(29)Ibid.,p. 111.,每一瞬间都是一次行动的开始,即挣脱存在之匿名性的努力,瞬间的延续意味着作为开始的行动的不断重复。瞬间因此包含了一种悖论:瞬间是作为开端的存在者的一次性事件;但为了维持其存在,瞬间又必须不断地进行重复,不断地保持重新开始,否则就有重新落入匿名性的危险。这就表明存在者获得其存在的方式是一种延迟的方式,而为了维持其存在又必须克服这种自身延迟,克服匿名性的裹挟从而使得不断地开始成为可能。因此,在瞬间中实现的自身聚集总是滞后的,需要不断地重新开始才能维持自身之存在。(30)卡林认为,列维纳斯这里关于“疲惫”的分析指出了身体的两可性:身体既是定位,又具有重量(物质性)。身体的原初运动是一种“疲惫”的开始,它一开始的自身延迟恰恰使它能够成为开始,开始意味着在不离开任何地方的前提下进入自身,因此才能如列维纳斯所说“发生在瞬间或瞬间之前”。(Cf. Rodolphe Calin,“Le corps de la responsabilité,sensibilité,corporéité et subjectivité chez Lévinas”,pp. 300-301. )这种延迟表明存在者在诞生之初通过努力挣脱匿名性,却又随时可能陷于疲惫所具有的痛苦。不仅如此,在享受活动中,身体性的活动仍然是“存在之努力”带来的劳累,身体的延续是衰老的过程,(31)Cf. Lé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p. 71.劳累和衰老都是享受之痛苦的表现,是对自身存在的疲乏(lassitude)。可以看到,享受不仅仅意味着快乐,还无处不透露着身体的疲惫,享受的快乐中隐含着身体痛苦的延迟和逼近。
身体性的存在即便在享受的快乐中也已经处于忍耐和痛苦之中,感受性之痛苦因此才有可能打断享受,在痛苦中自我撕裂,将自己献出去“为了他者”。(32)Ibid.,pp. 70-72. 列维纳斯擅长这种两可性的表达。在《别于存在》中,他通过痛苦、焦虑等各种情感状态来表示自我的分裂状态:“这种两可性是不确定的,因为它的‘明见性’仅仅在于它是一种痛苦的感发性……并不能从任何时间或空间中发现它的来源。我们不能说痛苦有着某种内在的或外在的来源。”贝戈认为,列维纳斯这种描述或许为精神分析无法解决焦虑的起源这类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Cf. Bettina Bergo,“What is Levinas Doing?Phenomen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an Ethical Un-Conscious”,p. 130.)身体中享受与易受伤害性的两重张力通过给主体带来痛苦而使主体不安,阻挠着自我在享受的满足中获得的快乐。然而,享受之满足对于痛苦而言又是不可或缺的,倘若没有享受的满足,痛苦也会失去意义,列维纳斯始终坚持享受“乃是包含在感受性及其作为向着他人暴露的易受伤害性中的为了他者的条件”(33)Lé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p. 93.;[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182页,译文对照法文原文有改动。。感受性的痛苦使享受成为给予的条件,并且能以其全部的内在性暴露于他者的面前,直至于将享受的内在性作为礼物完全许献给他者。这样,享受之内在性才可能“食人以食,衣人以衣,居人以居”,倾其所有给予他人。(34)Lé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p. 97.礼物(don)和给予(donner)之间存在词源的联系,列维纳斯以此表明感受性“只有作为给予才有意义”,但给予却并不表明任何的主动性,给予是被动的。礼物并不是赠与,而是被感受性之痛苦所夺走的,夺走以直接的方式“破坏”了享受的内在性,因此礼物是我满嘴的面包、我的全部享受。给予是被动性,是从我这里“夺走”的意义,因此“只有作为从自身之享受中去夺走才具有意义”。(Lé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p. 93.)这样,享受的身体才能以其“血肉之躯”而为他者“出血”,而无论自己愿意与否都要“从那在完满的享受中品尝着面包的嘴里夺走满嘴的面包”(35)Lé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p. 93;[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182页。。
这一分析的关键在于通过感受性向主体“前起源”之处的回归,从而追溯到主体前起源地受到他者影响的状态,追溯到先于诞生(pré-naissance)或自然之前(pré-nature)的状态,列维纳斯以“母性”(maternité)作为示例来阐述这种状态。(36)列维纳斯曾指出,他将圣经中的Rakhamin一词翻译为“怜悯”,其中包含了Rekhem一词,即子宫。就像母性所具有的情感那样。 贝戈也曾指出,“母性”使人联想到rehem一词,在犹太传统中,rehem一词是仁慈(mercy)和子宫(uterus)的希伯来词源。(Cf. Levinas,Humanisme de l’autre homme,Paris:Fata Morgana,1972,p. 122,note 6;Bettina Bergo,“What is Levinas Doing?Phenomen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an Ethical Un-Conscious”,p. 141.)列维纳斯将母性表述为“同者中的他异性”(altérité-dans-le-même),“他者孕育于同一之中”(37)Lé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p.85,p.95.。主体因此被规定为“同中有异”者,被主体内在的痛苦所支配。母性这一概念的关键含义在于“孕育”(gestation),“孕育”表达出他者在主体之中并影响着主体的那种状态。母性身体的感受性是纯粹的忍痛受苦和受折磨,即“母腹之呻吟”(gémissement des entrailles)。这是一种彻底的被动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只有“对于诸他者的应承(responsabilité),一个直至于去替代他者的应承,一个既忍受折磨之结果,也忍受折磨本身的应承在进行表示”,“甚至怀有/支撑着(porter)对于折磨者之折磨的应承”(38)Ibid.,p. 95.“怀有”是“孕育”着他者之同一的另一种表达。。列维纳斯指出,母性的这种特征表达出“易受伤害性的最终意义”(39)Ibid.,p. 137.,即感受性的彻底被动性。列维纳斯以母性身体来表示主体的肉身化(incarnation),即忍痛受苦的感受性身体,“作为感受性的主体性,它的肉身化乃是有去无回的放弃,是母性,是那为了他者忍受痛苦的身体,是作为被动性并且否弃自身的身体,纯粹的忍受的身体”。(40)Ibid.,p. 100;[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194页,译文对照法文原文有改动。换言之,如果享受的内在性意味着身体构成了主体存在之“结”(nœud),那么对于母性身体的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主体的这个结“在被结到自己身上之前就被结到他人之上了”(41)Ibid.,p. 96;[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188页。。这与通过享受来阐释身体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列维纳斯从没有放弃过前一种解释方案。在他看来,自我的肉身化意味着我的身体中有着“某种不可克服的模棱两可”:作为纯粹享受性的身体,通过自我满足而自得其乐,并通过自身生存之努力(conatus)去维持享受,这是身体的积极方面。然而,列维纳斯认为这样的身体“将自身肯定为动物”,他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享受的身体“乃是一条狗,它认出了回来占据其财物的尤利西斯竟然是自己的主人”(42)Ibid.,p. 100;[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194页,译文对照法文原文有改动。,享受的身体最终是要被超越的。换言之,纯粹物质性和享受的身体是自我中心式的,尽管显示了存在者维持自身存在所进行的努力,但这种身体最终是要被否定的,它构成超越的阶梯。
如果说主体的建立是通过“安置”(position),即通过占据一个位置,通过居住占有而实现和维持,那么母性的身体则是通过“放倒/解除安置”(déposition)而朝向他人,以身体的安置和享受作为给予他人的礼物,主体才能以其“血肉之躯”为代价为他者“出血”。母性身体显示出主体在其内在的痛苦中孕育他人,以及奉献的无条件性和被动性。贝戈曾以拉康“莫比乌斯环”般的主体性来类比母性的特点:“当一个人沿着环状带前进时,里面的东西出人意料地成了外面的东西”,“身体在其内在的感受性中向外开放,同时也体验到他的内在”。(43)Bettina Bergo,“What is Levinas Doing?Phenomen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an Ethical Un-Conscious”,p. 137. 黑体字为引者所加。母性身体这种奇特的悖谬为列维纳斯式的形而上学超越提供出一种具体的可能方案。
三、破出存在:超越的方案与身体的内爆
列维纳斯哲学中,超越表示主体与绝对他者、他人的关系,超越是由“形而上学的欲望”引发的运动。“形而上学的欲望”不同于需要:“被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欲望的他者不是像我吃的面包、我居住的国家、我欣赏的风景这样的‘他者’……形而上学的欲望则趋向完全别样的事物,趋向绝对他者。”(44)[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4页。在列维纳斯看来,人们通常理解的欲望其实是需要,它本质上是渴望返回的“怀乡病”,而真正的欲望(形而上学的欲望)并不寻求也不可能寻求返回,形而上学的欲望不回头地走向绝对外在性。欲望的贫乏不能如需要那样被满足,在超越中,欲望者与所欲者之间的距离不但没有减少或取消,反而被不断地拉大。形而上学欲望的极致就是盲目地走向其所欲望者,即“为不可见者而死”(45)同上,第5页。。概言之,超越即朝向绝对他者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代价是对主体内在性的彻底放弃。
列维纳斯关于超越的方案主要有两种:一是超越由外在性激发,二是超越由内在性中的差异引发。前者主要见于《总体与无限》第三、四部分,主要通过他者的面容、爱欲关系、生育关系和子亲关系等进行讨论;后者比较复杂,在《别于存在》中主要通过感受性的拓展(“易受伤害性”“母性”),无限之荣耀与主体之见证等方式来讨论超越如何发生。就身体问题的视角而言,爱欲、生育关系中的被爱者(女性)或儿子,“面对面”关系中的面容都是外在的,它们外在于我的身体而独立,都属于主体与外在性关系的例示。与之不同,就第二种超越方案而言,母性身体并不是外在于我的身体的另一具身体,而就是我的享受的身体,就是同一化的身体,母性身体中孕育的他人意味着身体从内部对其自身的权能和同一性进行瓦解。
列维纳斯后期通过突出身体的“历时性”,转向了第二种阐释方案。阿尔特兹-阿尔贝拉指出身体是列维纳斯思想的一个重要隐喻,身体问题提供了谈论超越的方式,即“通过主体所具有的内在性来解释超越”的方式。(46)Cf. Fleurdeliz R. Altez-Albela,“The Body and Transcendence in Emmanuel Levinas’ Phenomenological Ethics”,pp. 44-45.在阿尔贝拉看来,《总体与无限》中关于身体的例子其实已经可以实现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向“为了他人”的伦理主体的过渡,体现在第一种阐释方案的例示中,它们被阐释为与他者的关系原型,以“面容”所具有绝对外在性为前提。因此,阿尔贝拉猜测:列维纳斯通过面容而彰显他者的话语,这或许是因为这种方式比“对主体的否定”的方式要更好。(47)Ibid.,p. 46.如果说第二种方案中“他者孕育在同一之中”的母性身体是阿尔贝拉所谓的“对主体的否定”的方式,那么这种“否定”实际上将主体从其内在性中“解放”出来,从主体内在的差异中找到了超越的动力。因此,这样一种“否定”方式在积极的意义上指明了超越运动如何在主体之内发生,为既封闭又向他人敞开的主体提供了一条从自身出发出离自身的通道。这也是《别于存在》阶段从第一种阐释方案过渡到第二种解释方案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种方案并不意味着对第一种方案的全然放弃,这一点体现在身体的两重性之中。卡林以身体同时具有“重量”又是对主体的“解放”来重述这种两重性 ,并进一步指出列维纳斯式超越的真正含义正是在于“解放”:如果感受性是“在他者的超越性中被抓住”(即“母性”),那么“超越与肉身化是同义的,因此身体性的主体才能从自身中解放出来,从其存在的重量中解放出来”。(48)Cf. Rodolphe Calin,“Le corps de la responsabilité,sensibilité,corporéité et subjectivité chez Lévinas”,p. 309.这意味着主体的肉身化过程已经蕴含着他者的参与,也意味着这一过程已然蕴含着超越,因此肉身化之身体才有可能构成超越的条件。换言之,身体作为“超越的器官”具体地提供了超越进行的方式。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说,身体的身体性“作为感受性本身”,“已经表示着存在之去在的一结(nœud)或一解(dénouement)”。(49)Lé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p. 97.nœud意味着“结”或“扣”,其动词意为打结;dénouement为“解开结扣”的名词含义,列维纳斯通过这两个词的词源联系来表明主体不仅是存在的一个“扣”“结”,还是对这一“扣”“结”之“解”,主体为解开自身之“结”而进行的超越即为其“解”。(参见[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第188页,第37页注释4。)这意味着身体既是主体存在之“结”,是其实现自身存在的方式,又是出离存在、实现超越的“解”。存在之“结”即主体之肉身化,这种肉身化在“被系缚至我的身体之前就已经被系缚于他人了”(50)Lé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p. 96.,也就是说,就肉身化的过程而言,身体性的实存方式已经处在对他异性的参照之中。身体的安置即存在之“结”,当它作为易受伤害的母性身体而将自身许献给他人时,通过身体的安置建立的整个生存结构就被“放倒”(déposition)。放倒意味着“解除-(身体占据的)位置”(dé-position),取消身体的安置,取消由于身体的安置所带来的世界中的一切所有物,乃至于这个身体本身,即取消整个内在性。主体通过放倒自身才能真正地实现肉身化,感受性的身体成为“纯粹的给予”,(51)佩雷(Félix Perez)指出感受性正是从享受转变为这种“纯粹的给予”,感受性作为享受的同时又因暴露于他者而被剥夺了其自身之享受,从而变成“纯粹的给予”。(Félix Perez,D'une sensibilité à l'autre dans la pensée d'Emmanuel Lévinas:ce n'est pas moi,c'est l'autre,Paris:L’Harmattan,2001,p. 144.)最终,身体以彻底破出自身的方式成为实现超越的“解”。
母性的身体成为第二种阐释方案的例示,身体的“放倒”已经蕴含在“孕育着他者”的母性身体中,这一分析带来的意义在于:作为绝对外在性的他人对于主体而言是超越的,而通过母性身体回溯到主体“前起源”的处境中,列维纳斯发现了“他者孕育于同者”之中这一结构,这意味着主体在前起源之处已经是某种“同中有异者”。换言之,外在性已经内嵌到主体的发生之中,甚至先于主体性的建立。这使得主体内部发生某种断裂,主体不再与自身重合,不再是自身同一,而是“已被毫无保留地献出”。他异性在主体的内部找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使得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能在主体之内得到说明,因此,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不再是“面对面”的处境,而是在主体前起源之处,他人原初的“萦怀”(obsession)(52)obsession一般译为“困扰”“纠缠”,本文按《另外于是》中的译法译为“萦怀”,详细理由将在别处给出。的处境。这就为主体对他者的“替代”,主体对他人负有无可逃避之责任提供了阐释空间,也为列维纳斯“破出存在”思想指向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实现路径。
四、结 语
在列维纳斯看来,西方哲学是“对内在性的认识”的传统,哲学成为这种“内在性本身”,哲学史便成了对“超越进行破坏的历史”。(53)[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01、95页。他的身体理论为主体如何实现超越,以及伦理关系如何通过超越性在主体内部具体地发生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身体展示出物质性、感受性与超越性的三重交织,感受性在享受的物质性与自身撕裂的超越性这两重特征之间来回摆动,这种摆动体现出列维纳斯式的身体性的辩证法,体现了列维纳斯从感受性主体的现象学走向伦理的超越性的挣扎。(54)Cf. Fleurdeliz R. Altez-Albela,“The Body and Transcendence in Emmanuel Levinas’ Phenomenological Ethics”,p. 47.如果说在身体实现的享受之满足状态中,享受之凝聚标志着主体最初的同一性,那么母性身体标志着身体内部的分裂就意味着最初的同一性中蕴含的分裂。这构成了身体的两重性,身体一方面是实现主体凝聚、主体同一化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是主体内部撕裂从而进行超越的场所。在列维纳斯看来,分裂中蕴含的超越性比主体最初的同一性更加原初,真正主体性不再意味着自身同一,主体的生存不再意味着同一化的活动,而是意味着自身分裂中向他者的敞开以及向他人的超越。这为内在性如何爆破,从而为如何走出存在论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