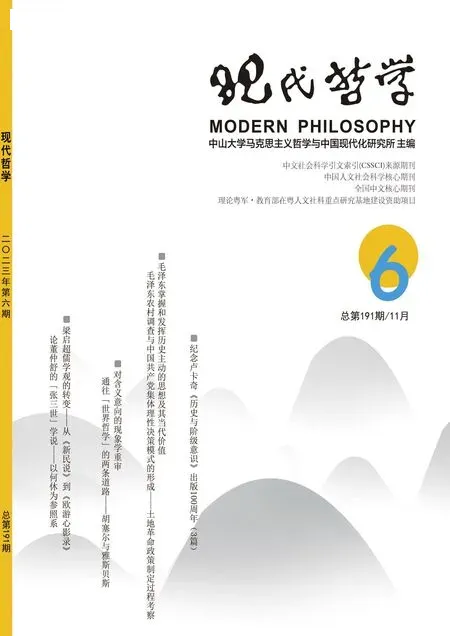卢卡奇与现代资本文明批判
——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趋势
鲁绍臣
一、物化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
就如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吕迪格·丹内曼(Rüdiger Dannemann)所认为的,“青年时代的卢卡奇是崇尚审美的,他的出身让他能够深入而真实地观察资本主义文化和生活世界的阴暗面。这造就了卢卡奇一生都一以贯之地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和蔑视的态度”(1)刘健:《卢卡奇思想遗产的批判性回顾与研究展望——访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吕迪格·丹内曼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4期。。换言之,自始至终,卢卡奇都与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对资本文明展开的科学与政治相结合的批判路径相去甚远。或者说,崇尚审美的卢卡奇自开始就拒斥了马克思哲学中的科学性。卢卡奇持续展开了“谁能把困于西方文明中的我们拯救出来呢”(2)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trans.by Anna Bostock,London:The Merlin Press,1971,p.11.,以及我们要如何摆脱“西方文明的奴役”的追问,这些追问基本停留在文化和意义的层面。在他看来,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是排斥英雄、缺乏根据、平庸乏味的“无意义”文明,他因此在《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等文本中用浪漫主义和个人好恶的笔调将西方现代资本文明描画为“被上帝所遗弃的世界”(3)Ibid.,p.88.,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序言中则借用费希特的话将其称为“绝对罪孽的时代”(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页。,人们不再能够体验为坚守最高的生命价值而不惜走向死亡的崇高的愉悦感,这种英雄主义情结的愉悦感来自对形而上学必然性的敬畏,对形而上学必然性的体验和理解所产生的“令人沉醉的愉悦”则是崇尚利己的现代资本文明所缺失的。(5)[匈]卢卡奇:《卢卡奇论戏剧》,陈奇佳主编,罗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承认自己受惠于德国浪漫派为自己提供的“理论起点”,试图通过“生命哲学”的“活的灵魂”的浪漫主义共同体思想,把人类从工业主义、世俗主义的现代“僵死的经济”中解放出来。(6)[英]G·H·R帕金森:《格奥尔格·卢卡奇》,翁绍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在早期卢卡奇的这些文字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种“禁欲主义和宗教救世主的弥赛亚乌托邦主义”情结,而这种禁欲主义批判路径的根本缺陷在于极强的主观性。这种反叛看似彻底,实则极度虚弱,经不起任何狂风暴雨或持久战的考验。这种虚弱甚至进而会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暴怒,并形成卢卡奇后来在《理性的毁灭》中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的动力源泉。
卢卡奇“能从早期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他的祖国匈牙利当时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7)刘健:《卢卡奇思想遗产的批判性回顾与研究展望——访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吕迪格·丹内曼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4期。,也与他对马克思思想的了解和接受,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关。后者使得卢卡奇看到新的希望,并被其形容为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口,也是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命运新曙光。在思想上,卢卡奇一方面开始清算新康德主义的主观方案,另一方面和第二国际无批判的“科学主义”保持距离:“《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3页。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文化批判的线索是卢卡奇的成就,他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道德问题》(1918 )、《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1919 )、《策略和伦理学》(1919 )、《道德在共产主义生产中的作用》(1919 )和《共产党的道德使命》(1920 )等文本中关于超越资本文明的思考,基本上都是道德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即使到了《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他也始终未能将无产阶级革命和物质利益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讨论。在加入共产党后,卢卡奇公开表示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仅仅是出于道德动机,他很渴望也很享受政党内部的“兄弟情谊”。但他没有考虑到共产党的特殊性恰恰首先在于其科学性,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取向进行彻底否定,这反过来是卢卡奇的失败之处。
卢卡奇借助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把现代资本文明理解为商品交换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从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和物化性质的批判。在这种总体批判中,卢卡奇思考的是商品形式绝对化的支配地位,以及由此造成的表现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的“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卢卡奇开始摆脱韦伯合理化意识的影响,进而追随马克思,主张商品形式的绝对化是现代资本文明的问题起点。现代资本文明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商品分析中得到解释的基本信念深深影响着卢卡奇,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商品形式的绝对地位所产生的物化逻辑使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管主观愿不愿意,在客观上都必须以效率为最高的目标,或者干脆完全成为生产的机器体系的一个环节,完全服从现成的、不依赖于劳动者而运行的规律与系统。在芬柏格(Andrew Feenberg)看来,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言的“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卢卡奇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也面临这一艰难的选择,即“要命令这个社会,就必须服从这个社会”(9)[加]安德鲁·芬伯格:《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当代社会运动》,孙海洋译,《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3期。,并且最终变成第二自然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直观态度。不过和后来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的绝对化描述不同,卢卡奇认为“工人以物化过程和变成为商品,虽然毁灭他,使他的‘灵魂’枯萎和畸变(只要他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反抗),然而恰恰又使他的人的灵魂的本质没有变为商品。因此他可以在内心里使自己完全客观地反对他的这种存在”(10)[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31页。。
也就是说,在卢卡奇看来,不管如何,无产阶级的生命仍然能感受到能动的主体与被动的主体性形式的错位与矛盾:“人同时是主体和客体,是主动的能动者和被动的受难者。”(11)Georg Lukács,Young Hegel: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trans. by Rodney Livingstone,London:Merlin Press,1976,p.194.作为无产者的工人在生产和劳动的过程中感到自身的被动性、无力、非人的生存的现实,甚至是毁灭。劳动者被撕裂为“物化的量”与“生命和灵魂的质”两极对立。不过,虽然“尚未枯萎的灵魂”仍然会起来反抗,但是相比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强大性,其是无比脆弱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屈服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绝对命令”。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物化的世界里,有机的共同体和完善的人格也就被破坏了,卢卡奇通过引用马克思的论述来阐明了这一境况:现代资本文明使得作为人与生命创造力的“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1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37页。
卢卡奇不仅看到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商品拜物教的意义上破坏了有机共同体,而且还在阶级统治和对抗的意义上撕裂着整个社会:它表现为资产阶级的量、知性的数理知识、流水线的管理和无产阶级肉体与生命的质的对抗。卢卡奇的洞见在于通过量与质的对立发现了西方现代文明类型的阶级性与统治性。卢卡奇指出:“剥削的数量上的差异对资本家来说,具有他从数量上规定他的计算对象的直接形式;对工人来说,则是他的全部肉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等等存在的决定性的质的范畴……量到质的骤变……是存在的真正对象形式的呈现,是那种混乱的反思规定的崩溃,这种反思规定在纯粹直接的、消极的、直观的态度阶段,歪曲了真正的对象性。”(13)同上,第225页。但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会使得自身在劳动的“数量化的外衣下”又一次认出“质的活的内核”,无论如何,无产阶级仍然是冲破物化命运的物质力量与肉身。
量与质的骤变使得黑格尔关于现代文明是一种以货币为中介的抽象统治、西美尔等人将资本主义视为死的事实、韦伯等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均质的合理化牢笼等说法变得可疑。卢卡奇指出,真正的辩证方法是洞察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错位,对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来说,“当然这一切都只是隐含在我们在劳动时间问题上所遇到的量和质的辩证对立之中”。(14)同上,第228页。在此,我们发现卢卡奇已经深刻洞察到在普遍商品交换形式中所隐藏着的阶级对立与不平等。卢卡奇也曾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自身能把社会认识为历史的总体,并且认识到不推翻这个由部分所构成的总体就不能获得解放。
在这种错位中,卢卡奇指认西方现代文明仍然是一种人类社会史前史的文明,在这种文明类型中,阶级与政治立场牢牢规定着其真理的内涵,其关于平等、自由和民主的理论与真正的社会实践是脱节的,或者说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幻象。在此,卢卡奇彻底摆脱了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个体批判的传统,对他来说,现代资本文明并不是由个体的自由意识所产生,恰恰相反,个体是这些已经存在,甚至表现为一成不变的社会条件的产物,因此个体决不能成为评判事物的尺度,最多只能作出承认或者拒绝的主观判断。与之不同,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宰制和反抗的过程中“才能和现实的总体发生关系并起到实际上的改造作用”(15)同上,第255页。。在这里,卢卡奇否定了晚年访谈中提出的个性与类的命令合一的思想,指出能承担起文明转型和共同体重建重任的是而且只能是阶级,这在今天可转换为民族,尤其是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被整体摆置于无产阶级地位的民族。对卢卡奇来说,阶级主体革命意识的“突出的实践的本质就表现为,相应的正确的意识就意味着它的对象的改变,而且首先是,它自身的改变”(1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62页。。革命与政治就顺其自然地变成立场与意识的转变,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 Jameson)以略带调侃的口吻评论道:“人们有一种感觉,卢卡奇思想的最纯正的后继者不是在诸多马克思主义者中,而是在某种女性主义者中,在那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独特概念运演已经被扩展到整个规划。”(17)F. Jameson,“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as an ‘Unfinished Project’”,Rethinking Marxism,Vol.1,No.1,1988,pp.49-72.
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强调,使得他忽视了利益、欲望和需要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即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生产的停滞与失业的增加的忽视。这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斗争原则——在发展生产力和财富增长的基础上减轻痛苦和缩短人类进步与解放的进程——相去甚远。作为一种伦理与价值主张,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对物质现实与生产力的关注,被卢卡奇批评为和西方资本文明分享了相同的真理。在卢卡奇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必然性和客观性是一种与自由和实践相对立的、完全异质的世界,并将自由明确定义为某种和必然性、客观规律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在此,我们也能感受到卢卡奇既完全不能理解马克思所阐发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也未能真正理解到马克思对资本文明面的称赞。
二、文化、伦理与类:卢卡奇的共同体思想
对卢卡奇来说,变革与实践的目标首先是作为总体的文化类型与生活范式:“文化:能够统一生活,一个强大到足以提高生活且丰富生活的统一力量……每一种文化都意味着对生活的征服。文化意味着对生活各方面的强大统一……一切表达最重要的东西是个人如何对生活作出反应,如何作为一个整体来回应和面对生活……在真正的文化中,所有的事物都具有象征意义。”(18)Georg Lukács,The Lukács Reader,ed. by Arpad Kadarkay,Cambridge:Blackwell,1995,pp.146-148.真正好的文化共同体的核心特征是人的全面发展:“一般来说,文化的发展如果只是涉及人的某一点,而不是使整个人格特征都得到全面发展,这往往会削弱人的个性。”(19)A. Arato,“Lukacs’ Path to Marxism (1910-1923)”,Telos,1971(7),pp.128-136.除了量质之间的骤变和不平等外,现代资本主义割裂了物质生产与文化生命意义的关联,新的共同体就是要重建这种关联性。在这种新的文化总体性中,“总体性只有在一切事物在未被形式所包含之前就已经具有同质性的情况下才有存在的可能;在那里,形式并不是一种约束,而只是一种逐渐形成的意识,一种对沉睡的一切事物的显露,一种在内心深处对必须被赋予形式的事物的模糊的渴望;在那里,知识即是美德,美德即是幸福;在那里,美即为显现世界的意义之地”(20)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p.34.。而资本主义的文化生活是碎片化、虚无主义和去神圣化的,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层次上,资产阶级的活动本质上是非生产性、随波逐流和盲目的,无法建构起稳定的、实质的、团结的关系。
在卢卡奇看来,虽然资本主义文明的范式危机重重,但文化和社会存在范式的变革并不会自动发生,而只能由政治实践加以介入。康斯坦丁诺斯·卡沃拉科斯(Konstantinos Kavoulako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危机与实践》一文中指出,对卢卡奇来说,危机被理解为社会生活更深层次的不和谐的表现,揭示了在“正常”社会条件下现代社会对人类施加的暴力。(21)See Konstantinos Kavoulakos,“Crisis and Praxis in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cience &Society,Vol. 87,No. 2,2023,pp.161-181.危机经验中的阶级差异可以导致新形式的社会意识,从而导致“革命性的实践”,但也可能会无限地通过生产与再生产的逻辑延续下去。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所代表的社会化形式仿佛有一种绝对的无限性,排除了经济自动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和变化的可能性。不过,虽然卢卡奇认为“无限广大”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远比古希腊封闭世界蕴藏着“更丰美之礼物及危险”,但他并不主张重回古代的地方性共同体。
按照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的分析,文化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旦参与政治,就反而成为纳粹的思想资源。在卢卡奇看来,德国贵族浪漫主义的根源“在于其近代资产阶级的缓慢发展”,但他们的兴盛“绝不意味着,德国可以免去一般的欧洲资本主义道路的普遍发展必然性,经历一个完全特殊的成为民族国家的过程”。(22)[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页。因此,德国非理性浪漫主义“最符合身处德国苦难之中的德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一方面符合他们那种没有根基的漂浮状态,另一方面也符合他们以客观上是错误的、社会上是危险的思想‘深邃’来克服德国苦难的企图”(23)范大灿编选:《卢卡契文学论文选(论德语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62-63页。,因此注定了是一场“民族的浪漫主义迷途”的悲剧。在和韦伯的谈话中,卢卡奇曾明确指出,贵族式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越好,就是越糟”。(24)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p.11.
在卢卡奇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与马克思类似,他有一个人类从地方共同体向民族-国家共同体、再向人类命运共同发展的历史逻辑线索:原始的人类小集体发展成为大集体,成为民族、国家这个必然的一体化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抽象和中立的,而是具有政治性或者阶级性的。卢卡奇据此指出,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史前史的阶段,只有阶级的立场,还未能真正上升到人类命运的立场,从而也没有真理的客观性。卢卡奇因此主张“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2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7页。。但改变现实的路径是自发主义还是实践与建构的路径呢?经历过工团主义斗争失败的卢卡奇深知,纯粹依赖阶级自发的意识是不稳定的,他因此批评自己的“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26)同上,第3页。。通过向列宁主义的靠近,卢卡奇为自己找到了新的理论突破口。在他看来,为了防止无产阶级个人被物的欲望所引诱,政党的高度集权、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就极为必要与合理:“在其他的领域中则有着稳定的假象(服务条例、养老金等等)和个人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抽象的可能性。这样‘地位意识’就被培养起来了,这种意识能有效地阻止阶级意识的产生。”(27)同上,第231页。很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原本在量与质的错位中能很好分析出来的自发主义逻辑,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民族-国家治理的复杂性(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和被压迫群众的复杂性,不得不转变成建构主义的列宁主义路径,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地位从而被抽象和虚幻化了。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假象无法完全避免,那么,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先锋队就“担当着崇高的角色: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28)同上,第86页。对承担教育和引导责任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共产党的纪律、每一个成员无条件地全身心地投入运动实践,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唯一可能途径……纪律问题一方面是党的基本实践问题,它真正发挥职能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它绝不仅仅是技术和实践问题:它是革命发展中最崇高和最重要的精神问题之一”(29)同上,第369页。。卢卡奇成功借用列宁的先锋队思想,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最觉悟部分即先锋队所构成的,其既以无产阶级为思想前提,又对整体性和纪律性的联系有本质的理解,其和资产阶级政党最不相同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以权利与义务关系为特征的政党类型。在卢卡奇看来,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就是通过政党组织形成的无产阶级的伦理学,通过将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从经济领域辩证地转变为自由领域的政治行动,才能完成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为了更高的伦理秩序,卢卡奇完全不顾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国家的统一性与个体特殊性的统一,在马克思那里是共同体与全面发展的个体的辩证统一,是人的需要、欲望与审美的辩证统一、人的本质的积极实现与人的积极存在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通过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卢卡奇给出了批评卢森堡的理由:岂不说无产阶级尚且会受到资本主义的物质诱惑,如果其他阶层,比如小资产阶级、农民、被压迫民族等“也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他们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推进它。但是他们也很容易使它偏向反革命的方向”(30)[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53页。,因而批评卢森堡的阶级理论是一种对理想型式(ideal-type)的分析。而彼得·胡迪斯(P. Hudis)反过来批评卢卡奇:“卢卡奇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辩护表明,他原来的哲学范畴无法解释无产阶级的自我活动,所以他最终神化了‘党’。”(31)P. Hudis,“The Dialectic and the Party”,News and Letters,Vol.46,No.5,2001,p.5.贾菲(Aaron Jaffe)据此认为:“卢卡奇对康德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他自己的评价:由于不能把形式和内容的联系理解为、‘创造为’具体的联系,而且不仅仅是纯形式估计的基础,这就陷入了自由与必然、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不可克服的两难困境之中。”(32)[美]亚伦·贾菲:《论卢卡奇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困境》,凌菲霞译,《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4期。
因此,卢卡奇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政党不是《共产党宣言》中明白条件、必然性与结果,从而根据历史条件采取适当的政治行动的政党,而只是在伦理与道德上“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工人政党更高类型的组织,这表现在它对它所有成员的更高的要求上”,这就难以避免深陷伦理和政治浪漫主义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与其说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3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1页。卢卡奇为了彰显立场和原则的坚定,对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斗争改善自身的处境和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性矛盾与危机的做法是持批评态度的,对具有文明性的资产阶级也是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因此,我们发现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的是基于道德义愤和浪漫情怀,量与质的骤变并没有在他那里进一步深化为通过积极的国家治理对现代社会贫困问题、两极分化、失业和生产过剩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他也始终无法回答革命之后“怎么办”的民族-国家治理逻辑的问题。因此,卢卡奇自视为列宁主义著作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被列宁批评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水平。列宁对卢卡奇1920年在《共产主义》上发表“论议会制问题”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批判了这种在“‘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的做法“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并直接点名批评卢卡奇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34)《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127页。
卢卡奇曾斥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及其后继者们堕入“深渊大酒店”(Grand Hotel Abgrund),但何谓资本主义的深渊是需要进一步商榷的,如果未能深入到无产阶级现实生活领域,不明白在生存、自由和伦理中,生存和物质财富的丰富性是无产阶级的首要需求,而商品形式和资本的雇佣劳动这些条件和情况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卢卡奇自己就永远无法摆脱“认识论的贵族主义”的指责。不过,卢卡奇的可敬之处在于,他坦率承认“他无法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水准进行一种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下分析,同时寄希望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完成这一使命”。(35)刘健:《卢卡奇思想遗产的批判性回顾与研究展望——访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吕迪格·丹内曼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4期。
三、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卢卡奇回到马克思
对比卢卡奇,我们发现马克思对现代资本文明的批判并没有完全绕开文化、意义和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但与卢卡奇不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人类学本体论的意义上强调:“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0页。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把物质欲望视为洪水猛兽,反而将之视为人类学的本体论证明。不过与直观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认为这一本体论的现实性依赖它的对象——被改造和加工后的自然界来加以确保,指出“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既在其总体上、又在其人性中存在”。(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被卢卡奇作为物化所批判的工业和私有财产,被马克思视为人的本质力量打开了的书本。与卢卡奇的乌托邦主义革命理想不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批判被黑格尔视为普遍性中介的货币,而是指出,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客观的力量,其已然成为人的欲望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且是唯一并且具有权力属性的社会关系。虽然在现代社会,人的欲望的实现并不是直接和完全自由的,以交换价值和价值增殖为生产目的的社会关系从一开始已包含着对个人的规定,甚至是完全的否定,但如果在条件不成熟时贸然废除以货币为载体的商品交换形式,就只会回到人对人的直接支配的时代。
此外,马克思比卢卡奇更深刻地分析了现代资本文明形式平等原则下的支配与从属关系,而这才是马克思着力批判和试图矫正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欲望分配逻辑的平等、自由和相关的治理原则都不过是以货币为载体的社会关系的理想化表达,“发展着统治和从属的经济关系”是纯粹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深层逻辑之一,其“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9、290页。在这里,与卢卡奇量质骤变的理论一样,马克思认为要建构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共同体,就需要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进行斗争。但马克思并没有想要连同商品和货币形式这一使得全人类相互联系起来的中介一并摧毁掉,而是主张用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治理的方式,来完成黑格尔所不能解决的贫困与贱民问题。
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第二个层面是作为人的积极存在的自由,这方面倒是和卢卡奇有相通之处,马克思在历史性和对象化活动的语境下,将超越需要和欲望支配逻辑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视为人的真正本体论存在的证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但和卢卡奇不同,对马克思来说,即使是超越需要和欲望逻辑的本体论自由仍然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首要的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自由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和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作为主体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如果人们整日在生存线的边缘挣扎,生存和活着是头等任务,作为“人的积极存在”的自由时间这一本体论的自由就毫无可能,因此工作日的缩短是实现人的积极存在的必要条件。卢卡奇曾经在《技术与社会》中探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但不管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还是《技术与社会》中,卢卡奇都把生产力的发展当作是资本文明唯一的结果,他不知道如果不进行积极的治理,资本逻辑就会成为生产力的桎梏。
因此,充分发挥资本文明的积极性,缩短劳动时间,使得纯粹的劳动时间量不再阻止人类的发展,就需要辩证地增加自由时间,以便全力发展艺术和科学成为现实的可能,“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1页。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循环过程,完全离开商品和资本文明,就会增加这一过程的长度。就中国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4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0页。其中,最重要的路径就是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说,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和共同富裕是并行不悖的。
卢卡奇主张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机构决裂,与资产阶级进行决战。但和卢卡奇一劳永逸的革命观不同,马克思将和资本作斗争理解为长期和过程性的。这是卢卡奇未能处理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向度,即对资本主义量质骤变的斗争,是满足人们基本和丰富的物质需要,并增加从事科学、审美和艺术生产的时间,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辩证运动。不管是卢卡奇还是后来的哈贝马斯等人,都容易从审美的视角评价作为人的积极存在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给予劳动的是一种生产美学的解释,并把劳动看作是外化、对象化和占有本质力量的循环过程。”(42)[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85页。但对马克思来说,人的积极存在同时或者说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也是反过来促使资本的健康发展和避免利润率下降的根本途径。包括卢卡奇在内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未能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等对非物质的认知劳动的深入研究,才建立了劳动时间与人的积极存在的关联(43)参见鲁绍臣:《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转向:根源与出路》,《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5期。。而资本主义长期无限延长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做法,毫无疑问阻碍了这一进程的早日到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极治理,甚至是完全站在资本一边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治理逻辑,使得现代资本变得极其野蛮,并导致两极分化和民族国家间的仇视与斗争。然而,全球的相互联系与分工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重要前提,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逻辑势在必行。
“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44)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唯有不断“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为旨趣的“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完成“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自由的辩证统一,才能科学地避免这一祸根。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45)[德]黑格尔:《黑格尔历史哲学》,潘高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58页。到底是始终停留于以人的欲望为根本的逻辑目的的阶段,还是以物化为前提,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旨趣,就成了两者的根本差异。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来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关于文化与意义共同体的思考很值得借鉴,其与中国古代强调“君子贵乎天道”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民族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虽然马克思也设想了完全合理、完全无剥削和完全自由研究和发展的社会,但那是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当下之中国则应是努力保持物质财富的增长逻辑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逻辑的平衡与辩证统一,其背后的根据是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也就是欲望驱动的生产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驱动的生产力发展的平衡统一。资本现代化是“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终结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历史生成,而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展开伦理、道德与文化建设是促进这一资本现代化的逻辑向“自由个性”的转型,最终实现物质全面丰富、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友善相统一的治理目标:“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最终的理想和目标就是每个国家和民族,每个个体都能够做自己的主人。
对马克思来说,价值与道德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批判是以对历史事实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例如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就是在对商品价值的历史起源作了严格科学的分析之后才作出的。而在卢卡奇那里,价值问题却成了核心问题、要害问题”。(48)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页。而俞吾金先生认为这是谁更优先问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政治实践的关系高度概括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艰辛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果断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都是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49)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1页。可以说,今天中国走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路,同样是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得出的结论。
在此,我们能感受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生命的原始丰富和现代社会关系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留恋原始丰富性和传统生命共同体或完全停留在资本主义物质与商品世界之中,都是荒谬与可笑的重大判断。积极的国家治理总是能根据历史的发展适时调整重点,让他们以合适的方式与比例存在。卢卡奇在晚年通过用辩证法去指导民族-国家的治理工作时指出,其最高的目标就是“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他们对类的命令的自愿完成高度和谐一致”。(50)《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6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8页。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崩溃》一书中指出,卢卡奇始终认为无产阶级不会“接受世界本来的样子”。问题是,离开民族-国家的实体性运行,这不过是一种空想或愿望罢了。作为研究者,一百年后的今天再评价《历史与阶级意识》及卢卡奇的其他作品,我们应该回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本来的样子:其毫无疑问并非“博物馆中的工艺品”。由其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也并非完全终结,但毫无疑问不能将其视为顶礼膜拜的《圣经》。回到当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现实生活,我们将能给予其一个适度的评价:他揭示现代社会众多危机的一种,而由这种危机所带来的不满还在持续增长,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还将持续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回望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