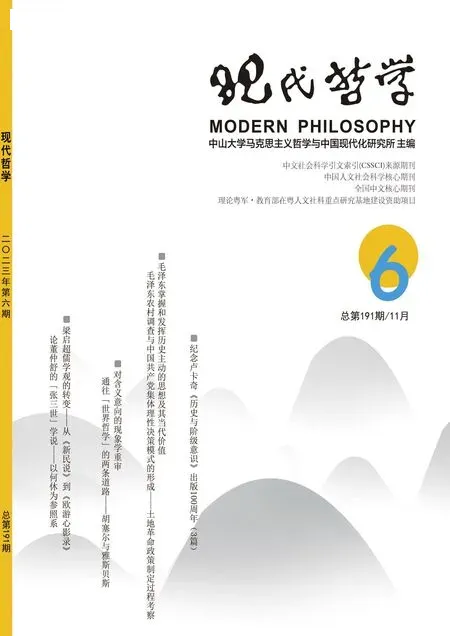通往“世界哲学”的两条道路
——胡塞尔与雅斯贝斯
王嘉新
胡塞尔与雅斯贝斯的思想交往不多。在1913年的第一次愉快交往过后,他们似乎遗忘了对方。(1)See Paola Ricci Sindoni,“Teleology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iography:Husserl and Jaspers”, The Teleologies in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Analecta Husserliana,Vol. 10,ed. by A. T. Tymieniecka,Dordrecht:Springer,1979,pp. 281-282.雅斯贝斯把胡塞尔安置在传统意识主题研究的框架内,走向对人类此在的“生存”分析。在这一表面印象的背后,他们之间有许多的对话空间。胡塞尔没有像雅斯贝斯一样,对二战后各民族之间的哲学与文化交往有那么多的切身体知,因此也没有像雅斯贝斯一样直接提出“世界哲学”的概念。尽管如此,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自身蕴含着包括跨文化哲学在内的一种世界哲学的基本框架。在胡塞尔那里,“世界哲学”关乎“绝对的伦理”“普遍世界知识”;而在雅斯贝斯那里,“世界哲学”意指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哲学形态,一种经过了充分的跨文化交流而达到的普遍可理解的哲学形态。本文试图把二者作为“世界哲学”的理论内容剥离出来,并加以比较研究。
很难说,胡塞尔和雅斯贝斯在世界哲学这一主题上是两个直接竞争的理论模型。毋宁说,它们各自描绘了世界哲学的某些方面;同时,两者都给世界哲学盖上了“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印章。雅斯贝斯拒绝把世界哲学理解为作为普遍科学的哲学的拓展,胡塞尔也反衬出雅斯贝斯进入世界哲学史时的含混与游移不定。本文将在当下的解释学处境中,整理和系统化胡塞尔和雅斯贝斯所提供的世界哲学之框架,最后在与这一框架的比照中,展示张祥龙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方法论探索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
一、胡塞尔如何设想“世界哲学”
很容易想象,在一些理论家的眼中,胡塞尔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哲学中的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us),而且是没有撇清欧洲中心主义的坏的基础主义。(2)游淙祺从瓦登菲尔斯(Bernhard Waldenfels)的立场出发,认为胡塞尔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影响。胡塞尔坚持一种奠基的理念(Grundlegungsidee),并且认为“理性”所发现的“同一个世界”这一事实为一个普遍秩序提供了基础,超越任何文化和历史,因此是非常典型的“欧洲”的哲学普遍主义的观点。(See Chung-Chi Yu, Life-world and Cultural Difference:Husserl,Schutz,and Waldenfels,Würzburg:Königshausen &Neumann,2019,S. 162.)无疑,胡塞尔是基础主义者,更准确地说,胡塞尔是哲学的基础主义者。不过,区别于一般的文化基础主义者,胡塞尔虽然承认哲学根植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城邦,被这种特别的前哲学的生活世界所触发,但他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文化产物,而是一种态度的转换。(3)See Klaus Held,“Husserl und Griechen”,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 22,Freiburg:Alber Verlag,1989,S. 142-146.正如胡塞尔一贯的立场,哲学是一次在希腊发生的“突破”。(4)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Husserliana VI,Dordrecht:Springer,1993,S. 321.下文涉及《胡塞尔全集》之处均依惯例简略为Hua,并以卷数加页码的方式夹注于文中。根据《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与哲学相关的毋宁是超越论现象学的本质、一种本质的自觉、目的论的自觉,这一点优先于历史的、具体的、偶然的经验发生,因此优先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换言之,希腊只是哲学在经验上偶然的“诞生地”(Hua 6,321),并不是希腊使得哲学发生。正如,几何学扎根于希腊世界,但并不是希腊文化创生的,它还依赖几何学家的“第一次的创造活动”(schöpferische Aktivität;Hua 6,367),一种特别的精神成就。因此,胡塞尔的哲学基础主义意味着哲学与文化是异质性的,各有其本质。用米蒂纳(Timo Miettinen)的话说:“理论的理念性的出现,不仅带来一类新的文化对象,而且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创造的视域。”(5)Timo Miettinen,“Husserl and Europe”,Routledge Handbook of Philosophy and Europe,ed. by Darian Meacham &Nicolas de Warren,London:Routledge,2021,p. 78.在胡塞尔看来,作为理论态度的哲学超越了具体文化,无法因果地产生于或者被消解在具体文化的意义关联之中。甚至在贝奈特(Rudolf Bernet)看来,哲学就像宇航员一样,可以降落在任何合适的土壤上将自己再领地化。(6)Rudolf Bernet,“Was ist deutsche Philosophie”,Husserl und deutscher Idealismus,ed. by F. Fabianelli &S. Luft,Dordrecht:Springer,2014. pp. 26-27.从这一视角出发,超越论现象学本身天然地蕴涵着朝向超文化的“世界哲学”的可能。
在对生活世界的结构分析中,胡塞尔特别指出这样一种主体生活的先天结构:在我的世界视域中我具有世界,那么我并不只是具有事实的、有限的与视域相关的世界,而是也具有无限地可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作为在无限可能性的有限空间中的可能经验——无限中的未知。(Hua 39,56-57)胡塞尔强调,这样的世界结构本身说明了,任何在交往的可能性中发生的变化都作为可能性存在于这一个结构之中,在交往中的主体所具有的不同的世界,都能在主体的相互关系中实现一种“同一性的综合”,即关于“同一个世界的各种显现”的综合。(Hua 39,56-57)
这一综合的结构本身就是我的世界结构,胡塞尔强调:“我所说的真的东西,我能追求的这种真的东西,都预设了我的世界视域,我的世界统觉(Weltapperzeption),世界统觉意味着其他人的世界统觉与我的世界统觉是同一个统一体。”(Hua 39,160)我的世界统觉也提供给我一个由可信且熟悉的东西构成的宇宙,因此我的世界是无限的,包含全部我可经验的东西。这些都是以类型化的熟识与否,即在预先的统觉意义中进入到我的经验中的。那么,与我的类型统觉不符的东西就被经验为陌生的。我的周遭世界(Umwelt)也总是包含着陌生性,亲熟与陌生的差异并不是偶然的区分,而是“每个世界的稳固结构”。(Hua 15,431)
胡塞尔特别强调,同一个世界的统觉及其本质的亲熟与陌生之别就是世界的本体论。它提供了全部经验的基底,即主体任何可能的经验都是关于这一世界的。这一世界“对在交往中的人和各种人性而言是作为同一个被构成的,并且就算经验可以在单个主体和主体相互间出现各种接错或者补充性的扩展”,这一世界也是颠扑不破的同一个。它具有“无条件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对任何“不连贯的、可能的现实性”也是有效的。(Hua 39,56-57)在交互主体性理论中揭示的这种“同一世界”理论,为中国人的世界、印度人的世界、德国人的世界等不同的文化概念提供了普遍基础。我的世界总是这样那样的民族-历史-文化之世界中的一种。
主体的周遭世界不只是感知中呈现的时空世界,还是一种民族的周遭世界(völkische Umwelt)。胡塞尔指出:“人之为人总是一种‘人性’中的成员,即一个特定意义上的民族的成员。”(Hua 39,344)这样的民族世界中包含了各种实体(Realitäten)。在人们的共同生活和相互影响中、在代际的传承中,这些实体获得其存在意义(Seinsinn)。胡塞尔举例,如果他在中国看到一个建筑,他无从判断建筑是庙宇还是国家机构。这是他缺失对这一民族世界中实体之存在意义的理解所导致的。胡塞尔认为,这样的实体与时空中的物一样,构成每个主体的周遭世界。更重要的是,这种实体具体且直接地对民族中的每个个体都是有效的。(Hua 39,345)胡塞尔的“周遭世界”理论本身就是跨文化的,跨文化性与包含陌生与亲熟的周遭世界中的开放的类型性统觉本质地关联在一起。胡塞尔讲:“在人之生活过程中,也在人的生活的必然的共同体化(Vergemeinschaftung)过程中,世界从常新的统觉出发创生出不断被信赖的意义,不断更新着自身规定的意义。”(Hua 39,163)共同体化是在同一个世界基础上的无限构成,它在陌生和亲熟的交融中不断提升。
提升至何种限度?按照贝奈特对胡塞尔的解读,人类的共同体化将共同的生活世界提升到“地球”(Erde)的层次,这意味着对周遭世界的所属文化领地进行去领地化。那时,哲学不是随着文化领地消失而不在了,而是从“太空”来对地球进行观察。(7)Rudolf Bernet,“Was ist deutsche Philosophie”,pp. 26-27.换言之,胡塞尔认为“人的生活的必然的共同体化”会真正促使一种有内容的“世界哲学”的意义构成,各种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的结果将为“世界哲学”的生成提供可能;“世界哲学”意味着对具体的周遭世界及其文化类型的普遍化努力,一种哲学的“理论化”。在必然的共同体化之下,超出跨文化理解层面的统觉-理解活动,进入到一种关于整个人类之人性的一般哲学化,这是一种依赖于理论态度达成的“普遍的世界知识”(universale Weltkenntnis)。
在胡塞尔那里,共同体化的过程不是没有目标,它依赖于“神的唯一性”这一理念。在胡塞尔看来,“神”是与人之一般的相关项(Korrelat),是每个真实的乃至想象的人的相关项,也是唯一的同一个世界的相关项。“唯一的神”在胡塞尔那里被等同于人性、等同于人的世界性(Hua 39,164-166),因此胡塞尔也把“唯一的神”称作是“绝对的普遍的人的伦理”。胡塞尔强调:“普遍的伦理与宗教明显只是纯粹的形式,抽象地在它们的普遍一般性中,并且在人与之周遭世界的具体化中,通常是保持着一种未被规定的开放。”(Hua 39,166)而这一未被规定性就成了留给哲学家的任务,即我们这里认为的世界哲学的任务。在胡塞尔看来,通往这样的世界-神的道路可以分为两条,一条当然是在历史中的“启示”(Offenbarung)——通过历史中的人物(Stifter)对这一普遍人性的创造——这一点直接指向雅斯贝斯指出的轴心时代,另外一条道路则是哲学。在胡塞尔看来,哲学这种普遍世界知识是非历史的,它是突入到历史中的(Einbrechendes)。因为它作为普遍知识指向唯一的神和唯一的人性,它就其自身而言是神学的(eo ipso theologisch),但是哲学这条道路并不了解启示,也不以启示为前提条件,因此哲学又是无神论的(atheistisch)。胡塞尔说:“因此,如果这样的一种科学确乎引向了神,那么它的神之路似乎就是无神论的神之道路了,正如无神论通往真正的无条件的普遍人性一样,这种人性被理解为那种超民族的,超历史的规范化的基底,所规范的是真正人性造就的超时间的超经验的东西。”(Hua 39,167)
在胡塞尔看来,通过哲学的“科学性”理论地来实现对同一个世界的普遍知识,即关于人性的普遍规定,既是哲学的原初意涵,也是哲学共同体当下的任务。“哲学共同体是这种普遍兴趣的承载者,并且每个哲学家都在他的部分来实现这种兴趣,通过他的特定任务,他服务于这种普遍的认识,合理地给自己提出这种任务。”(Hua 39,165)在胡塞尔看来,哲学意味着“一种自主的知识的突破,一种通过这种知识激发的新型的普遍的对实践的规范化(Normierung)的突破”(Hua 39,167),这一点当然不受限于哲学家本身所属的文化世界。从胡塞尔的思路来看,如果哲学在希腊城邦取得如欧洲哲学这样的一种有连续性的文化形式,那么在未来“世界哲学”就将是哲学家的内在要求,必然要随着人类的共同体化加深,获得更加普遍的文化形式。世界哲学必定走向对普遍人性的新的科学规定,走向人类根据普遍伦理自觉加之于自身的实践新规范。
二、雅斯贝斯-世界哲学的逻辑结构
雅斯贝斯在其晚年明确提出了“世界哲学”概念。自1937年开始,雅斯贝斯读了大量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材料,这些新材料给其带来很大冲击(8)See Ram Adhar Mall,“Interkulturelle Philosophie und deren Ansätze bei Jaspers”,Karl Jaspers-Philosophie und Politik,hrsg. von Reiner Wiehl &Dominic Kaegi,Heidelberg:Winter Verlag,1999,S. 160;张汝伦:《走向世界哲学——从雅斯贝斯的观点看》,《文史哲》2008年第3期。。雅斯贝斯希望把中国、印度等哲学思想容纳到一个统一的哲学视域之中。从1941年开始,雅斯贝斯甚至把世界哲学史的写作当作是自己毕生工作的总结。(9)Karl Jaspers,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fie,München:Piper Verlag,1984,S. 122.他晚年所有哲学史方面的著作都归属于世界哲学史这一庞大的规划,可见哲学史对雅斯贝斯的特别意义。对世界哲学史而言,一种来临中的“世界哲学”是无法回避的理念,(10)See 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Einleitung,München:Piper Verlag,1982,S. 76.它表达的是一种在个体身上发生的不同思想传统的理性交往所呈现的统一性。
这一统一性何以可能呢?在胡塞尔那里,“同一个世界”是世界哲学之普遍性视角的根本保证。而雅斯贝斯将统一性的哲学根据交给他的大全论(Periechontologie)体系。在雅斯贝斯的晚期思想中有两条平行轨道,一条是哲学逻辑,另一条就是世界哲学史。正如利诺弗纳(Andreas Rinofner)指出的:“雅斯贝斯从一开始就认为,要在哲学逻辑之侧面并且与哲学逻辑一道,推动哲学的世界史计划,这是必须的。”(11)Andreas Rinofner,“Periechontologie und 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Karl Jaspers Philosophie auf dem Weg zur “Weltphilosophie”,ed. by Leonard H. Ehrlich and Richard Wisser,Würzburg:Königshausen &Neumann,1998,S. 55.《哲学逻辑》是关于大全论的系统研究,它保证了这样一种空间,在其中,真理和存在对人来说都成为当下的,这一空间给可以设想的、最广泛意义上的交流提供了场域。(12)See Richard Wisser,“Projekt und Vision einer ‘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Weltphilosophie’ als Folgen der ‘Grundverfassung’ von Karl Jaspers”,Karl Jaspers Philosophie auf dem Weg zur“Weltphilosophie”,S. 66.而哲学史——在雅斯贝斯眼中哲学史一定是世界史——则是“对历史上出现的哲学内容的表达”,实际上是哲学思考本身的各种进路,这些哲学内容之间的关系绝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前后有序(Nacheinander),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交融(Ineinander)(13)See 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Zweites Buch:Geschichte der Gehalte:Einleitung”,Karl Jaspers Philosophie auf dem Weg zur“Weltphilosophie”,S. 12.,这种交融性就发生在大全论提供的空间之中。
根据利诺弗纳的重构,雅斯贝斯把大全论理解为“开放的”(offenhaltend)系统,这一系统的特点是保持着普遍的“立足点之灵活性”(Standpunktsbeweglichkeit)。(14)Andreas Rinofner,“Periechontologie und 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S. 57.不难理解,立足点的灵活性表明,就哲学史进行的哲学活动不受到哲学家所在传统的具体限制。由此,大全论可以给哲学的历史反思提供自由空间,所有的样态、内容和方法论构想都居于其中,并能够以它们本己的方式得到思考。大全论就意味着这样一种统域(das Umgreifende):在其中,“原则上任意一种哲学立场都能就其自身的前提和要求,实际地得到恰当对待”(15)Ibid.,S. 53.。因此,大全论是普遍的哲学史自身的可能性条件。正如萨尼尔(Hans Saner)在《世界哲学史:导论》的编者前言中指出的,雅斯贝斯尝试进行一种“多面的历史写作”(poly-aspekt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16)Hans Saner,“Vorwort des Herausgeb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Einleitung,München:Piper Verlag,1982,S. 6.。多面意味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哲学对话的活动,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哲学活动之间是毫无关系的游离与碰撞,因为在不同的哲学之间存在着“共同关联点”(gemeinsamer Bezugpunkt),它们处在一个统域之中。(17)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Zweites Buch:Geschichte der Gehalte:Einleitung”,S. 7.
大全只是纯粹的理论设定吗?它为什么能够提供支持比较哲学研究的最大空间呢?在萨尼尔整理的“世界哲学史第二卷:历史的内容;导论”这一部分手稿中,雅斯贝斯给出了答案。首先,哲学本身不是固定的知识,而是“内在行动,在这一内在的行动中人才生存地来到了自身”(18)Ibid.,S. 10.。换言之,雅斯贝斯认为,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行动中、交往中的自身意识的生成。思想本身离不开对象化,即主体与客体的分裂(Spaltung),分裂表明两个起初在一起的东西被撕裂开。(19)对分裂与关系差别的辨析,参见[德]汉斯·萨尼尔:《雅斯贝尔斯传》,张继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93页。没有二元的分裂,思想就是不可能的,哲学当然不例外。但是,哲学不同于科学,它并不沉陷在对象性之中,哲学不只在思考主体与客体,而且在这种思考中反思到更深远的统域。雅斯贝斯说:“哲学的事情是那统域,它尽管只是在对象那里才变得澄明(hellwerdend),但是它本身并不是对象。哲学是通过对对象的思考而在这统域的根基中实现无限地自身深化。”(20)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Zweites Buch:Geschichte der Gehalte:Einleitung”,S. 10.在他看来,“在哲学思想中,必然持续发生的是从对所思对象的沉沦中的返回”(21)Ibid.,S. 10.。统域自身是对象性发生的条件,任何对象性的东西都有它在统域中的“真实的符号存在”。哲学的目标在对象性思考的同时返归统域,哲学反抗的是把对象当成是自在的纯粹对象,无视它在统域中的真实缘起。不难看到,“统域”与胡塞尔作为全部意义起源之视域的“生活世界”及其对客观主义的批判何其相似。正如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自然地进入到超越论现象学的目的论历史一样,雅斯贝斯将各种历史的哲学要素都通归指向那无可对象化的“统域整体”(das umgreifende Ganze)。不同的是,雅斯贝斯认为,全部哲学家都不应该按照编年史、更不应该按照目的论的方式被编排,他们每个人都首先作为个体,作为“存在之全体的反映”被理解,他们也作为对话者出现在开放的空间之中。(22)See Karl Jaspers,Die groβen Philosophen,München:Piper Verlag,2012,S. 29.在他看来,这就是世界哲学的一般前提。
雅斯贝斯的“世界哲学”更多的是一种先行的信念,这体现在他对欧洲哲学的批判态度之中。正如他的著名论断所指出的:“我们正走在这样一条从欧洲哲学的日落到世界哲学的黎明的道路上。”(23)Karl Jaspers, Rechenschaft und Ausblick. Reden und Aufsätze,München:R. Piper &Co. Verlag,1951,S. 391.尽管“世界哲学”是来临中的,但它提供了更高的视角让我们审视欧洲哲学。雅斯贝斯有意识地反转了过往的欧洲哲学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惯性。用欧洲的问题意识、思维和概念进入其它思想传统,不仅无法真正公平地对待其它的哲学传统,也无法让欧洲传统本身得到反省。在雅斯贝斯看来,“世界哲学”这一概念的效力就体现在,破除以往被无条件接受的欧洲哲学史叙事。例如,文德尔班的哲学史默许了从黑格尔到当下一直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仿佛希腊、基督教、中世纪以及现代是一个个人所共知的整体”,似乎可以从原则上将它们区分开,并且加以对立。(24)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Zweites Buch:Geschichte der Gehalte:Einleitung”,S. 8.与之不同,雅斯贝斯试图从基本现象的角度提出基本问题(Grundfragen),尝试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将基本问题作为整体,而不是以某个传统为基础的问题作为基本问题。
那么,基本问题何以可能呢?难道问题本身不是在和具体的思想历史的关系中?这些问题的所问一旦被关联到普遍性,难道不会消融不见?雅斯贝斯承认,任何对基本现象的刻画和提问,都意味着提问者具有某种“精神性的诸整体理解”(25)笔者认为,这一含混的提法可以被认为是胡塞尔的文化方面的“周遭世界”概念。。问题是,这样的“某种”理解似乎不足以支持向其它别的样式的理解发问的合法根据,那么世界哲学史的观察者又如何能够提出一个有意义的基本问题呢?雅斯贝斯给出的答案是:观察者起码能够“通过对人的存在根基上的一些规定(Verfassung)”来提出基本问题,“从这一规定出发,我们所有人在各种不同的显现中看到并且经验到那同一个东西”(26)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Zweites Buch:Geschichte der Gehalte:Einleitung”,S. 9.。可以说,雅斯贝斯的哲学史观察,某种意义上践行了胡塞尔所讲的那种专属于哲学家的普遍兴趣,这些关乎人之存在的根本规定,当然是普遍人性的等价词。
尽管雅斯贝斯强调个体的哲学家在大全支撑的理性空间中对各种思想进行主题式的对比研究,但他不试图否认自己的思想在欧洲的传统之中,其《世界哲学史》也特别强调“哲学思考在事实上只能在它的历史关联中发生”(27)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Einleitung,S. 42.。雅斯贝斯认为,如笛卡尔一样的大哲学家,他最激烈地反对旧哲学,但后来者并不认为他脱离了哲学的轨道(28)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Einleitung,S.42.;因此,雅斯贝斯的态度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传统对我们的束缚远远超出了想象。对欧洲哲学中包含的惯性和偏见的克服,需要一种激烈的“世界哲学”的理念作为反剂。
根据利诺弗纳看法,以大全论为视野,雅斯贝斯的主张不能被理解为一种任意理解(verstehen)与接受(akzeptieren)的“解释学系统”,因为“大全论本身是普遍理解的空间,同时也是普遍批判的空间”(29)Andreas Rinofner,“Periechontologie und 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S. 54.。作为一种理论实践的哲学史写作,是饱含真理要求的。只不过雅斯贝斯强调,这一真理要求必须不归属于某个特定的哲学传统。就世界哲学史的写作而言,雅斯贝斯也承认他不得不对哲学的内容首先做出划分(Einteilung);这种划分是来自传统的(30)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Zweites Buch:Geschichte der Gehalte:Einleitung”,S. 15.,包括但不限于印度的、中国的、希腊的哲学,宇宙论、神学、存在论,全部(世界、神)、人等。这样的区分(Trennung)已经造就了“前见”(Vorgriff)。这种划分只是对表面的前景(Vordergrund)的划分,也可能是不恰当的撕裂。雅斯贝斯乐观地认为,不恰当的分裂会在哲学史的写作活动中被克服,即在哲学这种内在行动中发现这些区块之间更深层的关联。因此,“世界哲学”对雅斯贝斯来说同样是一种引导性的理念,它尚未占有具体的结论,世界哲学史“期待着世界哲学的到来,也迎接着世界哲学的到来”(31)See Karl Jaspers,“Nekrolog”,Karl Jaspers Philosophie auf dem Weg zur “Weltphilosophie”,S. 4.。
三、对 照
非常醒目的是,雅斯贝斯的“世界哲学”构想比胡塞尔的更加主动和具有活力。雅斯贝斯不仅肯定了哲学间的交流是理解,更加强调“交流中的理解同时是斗争,而且是一种特别类型的斗争,它不是为了权利,不是某一方的胜利,而是为了双方都能获知的真理”(32)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Einleitung,S. 74-75.。“斗争”这一说法建立在哲学交流之上,在相异者之间的交流的形式就是“斗争”,包括发问、反驳、驳斥,也包括质疑、倾听和坚持己见。因此,雅斯贝斯认为哲学意义上的交流是一种友爱的斗争(liebender Kampf)。通过斗争才能从各自的基本发问扩展到普遍的世界哲学。因此,其它的哲学不只是陌生者,而是被当作必要的对话者,并且是积极的对话者。在这种哲学史写作的背后,是受到永恒哲学召唤的、带有自我意识的寻找,这其中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论基础,另一方面是雅斯贝斯对“理性”概念的改造。从世界哲学的意义看,雅斯贝斯将一般化的理性、交往意愿和交往行动提升到人类共同体层面。
对胡塞尔而言,文化相对性根植于不同的文化世界,即不同的周遭世界的历史性发生以及它们的代际延续。他特别强调:“自然生活都是出自本己-家乡的-传统的生活”,“自然生活的经验与实践也是从传统中得到其规矩的。”(Hua 39,342)这样的传统有它自身的“领地”。(Hua 39,342)对我而言的陌生文化的实体,必然是另一个主体的亲熟文化的实体。没有什么文化的概念、内容、传统中的习俗等是无原初本己世界的。因此,不同领地中的原初产生的“思想”——雅斯贝斯意义上的自身作为“在世界中的人”的生存意识——一定依赖于它的本己世界才能得到理解,任何主体都是通过自身的本己世界来对陌生世界中的这些思想进行统觉式的后理解(nachverstehen)——与雅斯贝斯的生存式的本己化(Aneignung)也是类似的——并且想要彻底地理解一种陌己的文化,就必须走进这一世界的代际传承的历史性之中。然而,在胡塞尔的视角下,这种扎根于文化的思想不同于哲学,因为哲学是在历史中发生的非历史的科学态度。对这些有领地的文化进行哲学研究是可能的,但是反过来,通过具体文化的周遭世界来理解哲学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哲学高于具体世界的周遭文化,只是意味着哲学具有无可替代的特别性。雅斯贝斯认为哲学与科学已经成为“张力至深的极点”(33)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Zweites Buch:Geschichte der Gehalte:Einleitung”,S. 12.,而胡塞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别的严格科学,这一点几乎是两者在奠基一种“世界哲学”概念时显现出的最根本差异。
对胡塞尔来说,“世界哲学”的概念是“哲学”的分析命题,哲学总是作为“世界哲学”对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提供一种理念的规范性要求。对胡塞尔来说,跨文化理解是必然尊重历史性规定的领域,而世界哲学是必然要理论地理解(反思地超越)这种历史规定的领域。显然,可以想象的“世界哲学”的形成离不开一种“经验基础”(Erfahrungsboden;Hua 6,104),即各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共同体化”的过程,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到共历史的进程之中,但是哲学作为一条科学-神(绝对人性-伦理)的道路,已经先于任何共同体化而被哲学揭示,它的具体化应该体现在对人类层面的实践的规范性作用之中。作为理念的世界哲学应当自上而下地对历史发生-实践的跨文化交往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规范。
雅斯贝斯认为,实际上有某种属于“人之存在的真理”(34)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Einleitung,S. 143.,作为对这一真理的多面显示的世界哲学,是一种“整体图景”,这一图景“是作为一种昏暗的背景起作用的,它是一种促动的力量,但自身并不是清晰的”(35)Ibid.,S. 140.。雅斯贝斯甚至着力避免对这一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规定,唯恐落入到某一种传统和哲学的限制之中,因此世界哲学史本身是“在各种图景和脉络的交织中展现的对整体的非直接的观看”(36)Ibid.,S. 141.。在雅斯贝斯看来,“通过这样的哲学思考,我们越过了许多观点和可能性,进入到一个自由的空间,一种漂浮(Schwebe),其中充实不可忽视地增长”(37)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Zweites Buch:Geschichte der Gehalte:Einleitung”,S. 14.。在这种状况中的哲学史追问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历史上存在着若干真正生成的统域吗?存在着哲学信念的多样的、相互排斥的不同起源吗?或者说它们全部围绕着一个原则呢?”(38)Ibid.,S.14.雅斯贝斯干脆就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展开哲学史研究,尽管他设定了大全论的基础。雅斯贝斯把哲学定义为:“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及其自身意识的生成的方式,以及人从这种意识出发生活在整体中的方式。”(39)Karl Jaspers,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Einleitung,S. 20.在这方面,雅斯贝斯的世界哲学理念更多地是理论家个体的内在实践,而胡塞尔则认为世界哲学必定意味着在共同体生活的交融中的社会乃至政治实践。
胡塞尔和雅斯贝斯对于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在必然的共同化进程中的状况有不同的感知。在胡塞尔那里,周遭世界中的“陌生的”东西对我来说并未直接被感知为有“威胁的”,“陌生性”导致“冲突”这一惯常的心理联结并未被真正触及。而在现实的跨文化交往中,与陌生文化的遭遇并不经常被经验为一种有益丰富,而是首先被经验为威胁。更令人沮丧的是,恰好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文化空间中,宗教与规范的基础主义反倒在增加。这说明由科学、技术、消费和媒介带来的全球化过程并没有把人带向一体化,反而带向分化。从这一基本的事实出发,雅斯贝斯对交往意愿的强调就凸显了他本身促成世界哲学的实践意愿,而胡塞尔的世界哲学依赖的经验的共同体化恐怕不容易达成。
四、反 思
雅斯贝斯经历了二战和与战后德国政治的决裂。在移居瑞士之后,他的哲学史计划承载了明确的政治实践意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胡塞尔和雅斯贝斯对“祖国”概念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胡塞尔对“祖国”(Vaterland)表现出相当的热忱,在对“亲熟世界”的刻画中,他反复确认了“祖国”的历史传统形成的领地的同一性。(Hua 39,252,270,421)相比之下,雅斯贝斯则经历了这一概念的丧失。在写给自己的悼词中,雅斯贝斯说:“政治祖国的丧失让他陷入到无根状态。在这种失落中,人之存在的本原,还有与在德国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友人间的友谊,以及对世界公民的梦想支持了他们夫妇。”(40)Karl Jaspers,“Nekrolog”,S. 3-4.对他来说,欧洲的传统这个时候剥去了不可拒绝的一面,成为他获得的“馈赠”的一部分(41)Karl Jaspers,“Nekrolog”,S. 4.。胡塞尔是哲学意义上的普世主义者,他同时紧密地与“德国”这样的周遭世界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胡塞尔比较客观且自然地保留了传统的基本权力,雅斯贝斯则由于与传统的断裂而有意识地进入去传统的、去中心化的对世界哲学的构想。
胡塞尔和雅斯贝斯实际上都已经面对着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一场通往“世界哲学”的运动中——如果这种运动是可能的且真实的——,那么“我们的”“传统的”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这一点该持何种态度?在这一点,他们都不同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欧洲的哲学”这种说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同语反复,因为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希腊的。(42)Martin Heidegger,Was ist Das -die Philosophie,Pfullingen:Neske,1956,S. 6f.哲学与西方-欧洲是锁闭在一起的。胡塞尔认为,哲学扎根于希腊,它曾经塑造了欧洲,未来它可能与其它的地域和文化相结合,成为世界哲学。雅斯贝斯的立场更加激进,他认为哲学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现在到了欧洲摆脱独占哲学的幻觉,进入普遍人性反思的时刻。
瓦登菲尔斯批评胡塞尔,认为胡塞尔天然地具有关乎人性的普遍性设想,而且这种设想“从自我出发,经过他人,最后终于总体性”(43)Chung-Chi Yu, Life-world and Cultural Difference:Husserl,Schutz,and Waldenfels,S. 175.,已经是一种不自觉地从欧洲中心出发的看法。无独有偶,塞萨纳(Andreas Cesana)批评雅斯贝斯,认为他的世界哲学过于受到传统的“永恒哲学”的影响,因而接受了一个过分西方的思想模式(44)Andreas Cesana,“Karl Jaspers und die Herausforderung der interkulturellen Philosophie”,Jahrbuch der Österreichischen Karl-Jaspers-Gesellschaft,Bd. 13,2000,S. 69-88,hier S. 85-86.。个体的哲学家从自己的生存理解出发,与“大哲学家”交流,最终归于真理的“永恒的一”。(45)See Paola Ricci Sindoni,“Teleology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iography:Husserl and Jaspers”,pp. 289-290.因此,无论胡塞尔还是雅斯贝斯,都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具体文化的普遍的视角,这一视角都指向唯一的真理、神。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二者对“世界哲学”的构想实质上是以这一绝对的维度为前提的。
在东方,张祥龙很早就意识到胡塞尔乃至雅斯贝斯思想中的这种西方定式(46)See Xianglong Zhang,“Life-World and Higher Human Nature”,Phenomenology of Interculturality and Life-World,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Sonderband,Freiburg:Alber,1998,S.42-53.,并且就比较哲学尝试了新的方法。在《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中,张祥龙与雅斯贝斯一样,反对哲学思考陷入到主客分离的层次,主张更深层次的构成性贡献——雅斯贝斯认为是“统域”。但是,张祥龙指出,对(比较的)哲学史文本解释敞开的是更加原初的视域,它“既不是纯客观的,也不是纯主观的,而是能引发出那不可事先测度而又合乎某种更本源的尺度的领会势态”,强调“得机得势地理解中西思想关系的本源视野”。(47)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4页。这一本源视野既不把作为绝对理念的世界哲学预设为目的地,也不接受雅斯贝斯设想的人之存在的生存性真理,它甚至只是许诺了差异性和相似性,有意避免同一性与总体性。东西方思想毋宁像“两张有所叠加的航片”,哲学思考只是试图“引发”(ereignen)东西方各自的原初发生。张祥龙认为,在这种引发中,东西方思想将会发生一种原初共鸣,在终极视域的开启和交融中,主体、存在、整体性等“范畴束缚”被有意卸下,而传统的哲学划分如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等——雅斯贝斯觉得这种划分是困扰,但是将其作为解释学前件接受下来了——也被“消解”了。(48)同上,第3页。对于张祥龙来说,从各自的传统中回到各自的原初发生,再让这种原初发生带动与其它传统的原初发生的共鸣,才是一条既通往历史又通往未来的世界哲学之路。这条道路是一条受到海德格尔思想启发的道路,但是扬弃了海德格尔对本源之封闭性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