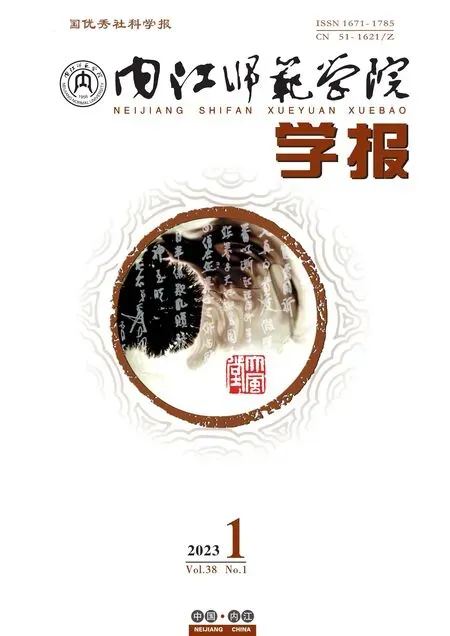对名词形容词化的重新审视
——汉语副名结构内部的异质性
吴 宇 仑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现代汉语中的“副名结构”,顾名思义,就是指副词和名词组合在一起。由于副词一般不能修饰名词性成分,因此副词和名词组合的现象成为一个特殊的“结构”。在白话文早期的发展中便可见副名结构的例子,例如曹禺《日出》中的“顶悲剧”。20世纪6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界围绕“很绅士”“很淑女”等副名结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最早的争议在于有些学者质疑副名结构的存在[1]518-519]、[2-3],认为其要么是特定句式中的偶然现象,要么是动词省略的结果,这些观点在之后的研究中已经被内省和实证的方法逐一反驳[4-6]。在承认副名结构存在的基础上,学界通过不同的视角对其性质进行了讨论,例如文化语言学的视角[7]、构式语法的视角[8]、句法语义接口[9]、语义限制[10]、语用学的视角[11]等等,在此难以一一罗列。不同的学者对副名结构的观点有所不同,尤其在分析副名结构中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功能和地位时,不同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理论,做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分析:一种是认为名词性成分保留了其语法功能,直接以名词性成分的身份与副词组合形成副名结构,可以称为“词性保留说”;另一种认为名词性成分转化为了形容词性的,完成了语法功能的变化后再与副词结合,可以称为“词性转化说”。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争鸣,但是目前没有专门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力图厘清这两种观点的差异性,并探究副名结构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分析方法。具体而言,既然副名结构是一个AdjP是没有争议的,那么其中的名词是否具有其他AdjP中形容词的性质,是考察的重点。
一、“转化说”与“保留说”的得失
(一)“转化说”的得失
“转化说”将副名结构处理为副词和形容词化了的名词的结合,其最初观点的来源可以追溯到Chao[1]。他在论及名词的词类特征时指出名词不能受副词修饰,但他指出有一种似乎是例外的情况①,如下例:
(1)太鼓了
(2)真土
(3)很光
他指出,上边的这些“副词修饰名词”的例子,本质上都是兼类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鼓”“土”“光”都是名词和形容词的兼类,它们是以形容词的身份接受副词的修饰的。这一思想在后来得到了继承并被发展成为了“转化说”,即认为副名结构里所有的名词性成分都是通过功能语类的转化,变成了名词和形容词的兼类,进而获得了受副词修饰的能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例如张谊生[12]、谭景春[5]和杨永林[9]等。
“转化说”的可取之处在于将副名结构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词汇学问题,不在句法层面上对其进行解释,这就避免了对句法层面的一系列句法规则的扰乱。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采用形式句法甚至是生成语法作为理论基础,在形式句法框架下解释副名结构需要面对许多复杂的问题,这里仅仅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根据原则与参数理论时期短语结构规则的X杠范式,所有的短语结构都必须是向心结构[13]。然而,副名结构的句法分布已经证明它是一个形容词性的短语结构,也就是AdjP[2]。问题在于,一个副词性成分Adv和一个名词性成分N(或者NP),如何能生成一个AdjP呢?按照X杠范式,AdjP的中心语必须是一个Adj才对,这就产生了矛盾。
第二,生成语法追求原则(principle)的普遍性,而在世界语言的语类结构规则中,几乎没有N和Adv结合的语类规则,为何在汉语中就出现了这种语类规则呢?难道因为是汉语就要添加一个“副名组合”的参数(parameter)吗?
以上两个例子反映出如果要用句法规则来解释副名结构的生成,是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②[14],因此形式句法的学者大多采用Chomsky提出的“词汇主义方法(lexicalist approach)”的立场,将这些句法中的疑难杂症丢到词法中去。在他们看来,研究副名结构的语义特征,本质上不是研究具有何种语义特征的名词能受副词修饰,而是研究具有何种语义特征的名词容易形容词化变成名形兼类。
除了在理论上简化了句法部分的操作之外,就汉语语言学的实际来说,“转化说”解决了另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关注的汉语的词类划分问题。汉语的词类划分问题走过了漫长的历程,最后得出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且容易操作的结论是:根据不能受“不”修饰这一特征,先划分出名词,再由名词划分其他的词类[15]。在副名结构兴起以前,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大多数名词确实不能被“不”否定,如“*不桌子”“*不苹果”等等。但随着副名结构的能产性不断提高,这一方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典型的例子就是“不绅士”“不淑女”。按照上述的检验方法,“绅士”“淑女”都不是名词,可是它们又可以受数量结构修饰,由此就产生了矛盾。现在,“转化说”为这个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可以受“不”否定,但是又能受数量结构修饰的词,是名词和形容词的兼类。“转化法”的处理方法解决了“不”字鉴定法在面临副名结构时的危机,因此在实践中也被广泛应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每个词条标注词性后,很多经常出现在副名结构里的名词都被标注了“名”和“形”两个词类,例如“绅士”。
但“转化说”并不是无懈可击,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是,名形兼类词的数量问题。随着副名结构能产性的增加,能受副词修饰的名词是越来越多的,例如“很绅士”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有争议,20世纪90年代争议已经很少,而到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争议了。如果随着时间的推进副名结构中名词越来越多,“转化法”又将这些名词全部处理为名形兼类,那么名形兼类词可能就过多了。兼类词多在语言分析中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事实上,语言分析中应该尽量控制它的数量。正如朱德熙[16]所说,如果A类和B类词的兼类过于多,要么说明划分的标准有问题,要么说明A和B本身就不是独立的两类。
(二)“保留说”的得失
与“转化说”类似,“保留说”也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尤其是起源于结构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词类转化”观点的反动。汉语中动词经常可以做主语和宾语,比如“游泳已经学会了”和“喜欢吃饭”,有些早期的语法著作认为这是动词通过词类转变或者“零形式派生”变成了名词,这就如同英语中的“study”就经历了从动词“(to) study”向名词“(the) study”的转化或者零形式派生。20世纪后半叶,随着结构主义对汉语研究的深入,学界对这种观点一般持否定态度[17],例如朱德熙[18]就指出,这种词类转化的说法是“拿印欧语的眼光来看待汉语”,实际的情况是汉语中动词本来就能做主宾语,不需要任何的转化或者派生过程。这种分析方法对后来的汉语学界造成的一个影响是大家对待汉语的词类转化往往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保留说”认为副名结构是真实存在的结构,副名结构就是副词和名词的直接组合,不涉及任何的形容词化过程。
如同“转化说”的支持者大都出身形式句法,相应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留说”的支持者大都出身于认知和功能语言学,尤其以出身于构式语法居多,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们的论文题目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例如“构式”[19]和“非范畴化”[11]等等。在构式语法的框架下,可以在句法层面为副名结构安排一个合理的位置。
“保留说”的一个显著的优点是其认为副名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能为副名结构可以表达很多特殊的文化、语用意义[7][20]提供解释。按照“转化说”的观点,副名结构应该与普通的“程度副词+形容词”的组合没有本质差别,那么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副名结构能表达与普通“程度副词+形容词”不同的文化、语用意义,如果硬要说,只能说这些意义是在词类转化过程中产生的。比起在句法特殊组合中产生了特殊语用意义,在词类转化过程中产生了语用意义这一观点似乎站不住脚。
除了构式语法视野下的研究之外,其他近来提出的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观点似乎也能为副名组合提供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些解释也同样站在“保留说”的立场上。例如,有观点认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必须凸出语言功能这一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考虑在语法、语义之外的“表达”这一层面[21]。对于汉语而言,具体的语法也就是词的组合规则是受到表达的“控制”的。一般位置上的名词本身只具备“指称”这一表达功能,但是有时候发话人想要用名词表达“陈述”这一表达功能,此时名词就会占据一般情况下谓词占据的位置,比如这里的受副词修饰。在这种情况下,名词并不是在语法层面完成了词类的转化,而是在表达层面完成了表达功能的转化,它在语法层面仍然是名词。可见,基于功能的观点对于副名结构是持有“保留说”态度的。
(三)“转化说”和“保留说”的理论问题与经验问题
“转化说”和“保留说”起源于结构主义时期两种不同的分析思路,后来分别被生成语法和构式语法所继承,究其原因,是因为构式语法和生成语法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构式语法采取的是经验论的归纳法手段,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结构过程,它客观地描写语言中的例子,将所有不能从字面直接推导出意义的组合全部称为“构式”,而语言中究竟有多少个构式呢?理论上来说可以是无穷的。因此,可以直接将副名结构看作一个“构式”,这一构式的形式就是“副词+名词”。与之相反,生成语法采用的是唯理论的演绎法手段[13],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构过程,它预设了最简的短语结构方式,句法生成机制直接将不符合短语结构规则的组合排除出去。因此,其句法部分无法容忍“副词+名词”,这样的“例外”必须将其分派到词库部分去解释。不难发现,目前研究中“转化说”与“保留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理论范式的不同引起的,归根结底是一个理论问题。本文无意也无力为生成和功能语言学的争议做出任何贡献,但本文认为,应当暂时搁置理论上的分歧,转而仔细地考察副名结构作为一类结构,其中不同个体的共性与个性。如果副名结构的大多数成员具有相似性,那么一种分析方法可能就足以解决问题,相反,如果大多数成员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那么可能只用一种分析方法无法详尽地做出充分的描写。
二、副名结构的异质性
(一)语法合法性的异质性
以往关于副名结构的研究指出,副名结构随着其中名词性成分语义类的不同,合法性和可接受度也会发生变化。即所谓的副名结构内的名词不同子类存在“层级性”,最典型的层级性是褚泽祥和刘街生提出的“抽象名词>具体名词>专有名词”[10],也就是说,“副词+抽象名词”更易于被接受。其他的研究也观察到了许多影响副名结构可接受度的语义因素,如名词是否具备[+human]特征[12]、名词是否有隐喻义[22]、名词是否有描述性语义特征[6]等等。这些研究都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假设,那就是副名结构内部存在语法合法性的异质性,也就是有些副名结构的例子比起其他的例子更易于接受。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抽象名词>具体名词>专有名词”的层级性已经被经验证据证明存在[23],但是这种层级性只是一个趋势,并不能对语法合法性做出精准的预测。也就是说,随便拿出一个“副词+抽象名词”的例子,未必比一个“副词+专有名词”的例子的语法合法性高。这一点在Wu[22]最近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例如,在他进行的语法合法性判断任务中(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6分),“很+专有名词”的例子“很广州”的平均语法得分为4.65分,“很+抽象名词”的例子“很褒义”的平均语法得分仅为4.16分——单从个别例子来看,“副词+专有名词”的语法合法性很难说一定小于“副词+抽象名词”。这说明了副名结构内部的异质性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并不是仅仅由名词性成分的语义属性这一个特征决定的。
(二)句法表现的异质性
首先,汉语中形容词受单音节副词“很”修饰的时候,一般都可以将“很”从状语位置移动到补语位置,加上表示程度的词缀“得”,从“很X”转变为“X得很”。此时,整个结构从中心语居后变成了中心语居前,用传统语法的话来说就是把整个结构从偏正式变成了补充式。这个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相当能产,无论形容词的音节数目,例如:
(4)很红→红得很
(5)很漂亮→漂亮得很
变换前后的语义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可能有语体色彩上的差异。现在看看副名结构能不能进行同样的变换:
(6)很绅士→绅士得很
(7)很少年→?少年得很
(8)很中国→*中国得很
例(6)到例(8)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例(6)中的“绅士得很”是非常自然的表达,例(7)中“少年得很”合法性就差一些,例(8)中“中国得很”则是完全不合法的。需要注意的是例(8)的不合法不是因为抽离了语境,即使在具体的语境中,“很中国”也不能变换为“中国得很”,例如:
(9)你这件旗袍很中国。
(10)*你这件旗袍中国得很。
由此可见,不是语境的因素,而是副名结构内部的异质性导致了有些用例不能应用于这一种变换中。
形容词的另一个句法特点是不仅可以出现在谓语位置,还可以出现在定语位置修饰名词性成分。然而,副名结构似乎更多地出现在谓语位置。实际上,Chao[1]早就认为所有的副名组合都不能离开谓语位置,他的这一点论断在当代汉语中是否成立呢?不妨来看语言事实:
(11)…很书生气的一个问题,大家没有接下去。(BCC语料库:多领域)
(12)一米八多,双眼皮,很阳光的一个男孩…(BCC语料库:多领域)
(13)有人问了盖茨几个很细节的技术问题,这位世界首富不厌其烦地亲自一一讲解。(BCC语料库:多领域)
以上是从BCC语料库中信手拈来的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说明,至少对于某些用例来说,副名结构是可以出现在名词修饰语中,也就是传统语法中所谓的“做定语”。现在再来看看,是不是所有副名结构都能够自由地出现在定语位置上:
(14)这个说法很概要→很概要的一个说法
(15)这个词很褒义→?很褒义的一个词
(16)这道菜很北京→??很北京的一道菜
上边的例子说明,在能否做定语这种句法环境下,不同的副名结构用例同样表示出了异质性。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例(14)到例(16)关注的并不是副名结构本身的语法合法性,而是语法合法性在位置变化过程中(即箭头所示的过程)中产生的损耗。例如,“很概要”的语法合法性可能本身比“很北京”就要高,但是这不是我们比较的重点,重点在于,“很概要”在变换到定语位置时,其语法合法性较之在谓语位置并未有太大差异。相比之下,“很北京”出现在谓语位置时候和出现在定语位置时候的语法合法性有着比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很北京”做谓语和做定语的能力不相等。
从类型学角度上来说,典型的形容词可以自由地出现在比较结构中,在有些语言里还用形态来标记所谓的“比较格”和“比较级”,汉语中也是一样[24]。这一特点是由形容词的语义特点决定的,大多数的形容词天生用来表示连续的概念,因此具有可分级性,也就可以进入对比,与之相对应的,名词一般是离散的概念,因此不能用来直接比较,这就好比是统计学概念中的名义变量(非数值)和等距变量(数值)一样。副名结构的一个特征就是可以出现在特定语境下的比较,例如:
(17)你比秦始皇还秦始皇
(18)??你比小张更/还秦始皇
这是传统副名结构研究中非常著名的两个句子。然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例(17)中名词“秦始皇”可以被副词“还”修饰,而没有关注副名结构“还秦始皇”出现的特定语境——那就是,只有在前边有“比”字短语,且“比”的宾语和副名结构中的名词同形的时候,例(17)这样的例子才能成立,相反地,没有特定语境的用法诸如例(18)是非常可疑的。因此,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在名词与表示比较基准的“比”字介词短语的宾语不同形的时候,能否形成表示比较的“更+名词”的副名结构。同样,不同的用例在这一个句法操作上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例如:
(19)张三提的问题比李四的更哲学。
(20)韩梅梅比王晓红更淑女。
(21)?张三比李四更大叔。
(22)??张三比李四更法西斯。
(23)*这条街的建筑比那条街更上海。
上面这些例子的语法合法度从例(19)到例(23)依次递减。例(19)和例(20)是非常平常的句子,例(21)相对例(20)有些可疑,例(22)和例(23)则非常可疑甚至完全不合法。这说明,在“在非特定语境下用于比较结构”这一句法能力上,副名结构内部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另一个形容词一般具有的句法能力是可以受多重副词的否定,即使是一个已经包含了副词的AdjP,也可以受其他副词的修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程度副词+形容词”的结构可以受副词“不”的再次修饰达到否定的效果[24],比如以下的例子:
(24)[不[太[漂亮]]]
现在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鉴定一下副名结构,具体而言就是看看副名结构前面能不能受副词“不”的否定:
(25)不太人道主义的做法
(26)不太智能的汽车
(27)?不太学术的遣词造句
(28)??不太良心的商家
(29)??不太波折的爱情
(30)*不太广州的早茶
(31)*不太琼瑶的故事
不同的副名结构的用例同样构成了语法合法度的连续统。例(25)和例(26)这类例子几乎是常见的;例(27)需要具体的语境,例如教师和学生在讨论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例(28)和例(29)中的“太良心”“太波折”虽然在BCC口语语料库中都能找到用例,但加上否定副词“不”之后合法性变得很可疑;例(30)和例(31)则是几乎不合法的组合。基于此,可以说在能否受否定副词“不”否定这一句法能力上,副名结构内部表现出了一定的异质性。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放到并列结构上。并列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尽管其中的成分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名词甚至是介词短语,但是同一个并列结构中的并列成分的语法属性必须一致,动词性成分只能和动词性成分并列,名词性成分只能和名词性成分并列,否则就会违反合法性,例如:
(32)[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歌
(33)*[街上NP、在桥下PP、在田野中PP]唱歌
(34)我喜欢[吃饭和打游戏]
(35)*我喜欢[吃饭V和游戏N]
方括号表示的是并列结构的部分。例(32)和例(34)中的并列结构因为内部成分的语法属性相同而成立,例(33)和例(35)则因为违反了这一原则而被排除。现在回到副名结构,已知副名结构的句法功能大概相当于一个AdjP,那么按照并列结构的规则,其内部的中心语(即名词性成分)应该可以和其他形容词并列③。应用这一检验会发现,与之前相同,不同的副名结构用例对并列这一操作的可接受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试看以下的例子:
(36)约翰[非常[慷慨、绅士]]
(37)那个结论[很[严谨、科学]]
(38)?这件衣服[非常[简朴、书生气]]
(39)*这部小说[很[动人、中国]]
外层方括号表示的是副词加中心语的结构,内层方括号表示副名结构的中心语与其他形容词性的中心语并列形成的并列结构。如以上的例子所示,对于部分副名结构,中心语是可以与形容词性的中心语进行并列的,例如例(36)中副名结构“非常绅士”中的中心语与形容词“慷慨”并列;例(37)中副名结构“很科学”的中心语与形容词“严谨”并列。然而,对于其他的副名结构用例来说,同样的句法操作并不是无伤语法合法性的,例如例(38)中“非常书生气”的中心语与形容词“简朴”并列之后,整个结构的合法性有所损耗,短语变得可疑了;例(39)更加严重,副名结构“很中国”在其中心语和形容词“动人”并列之后,变成了完全不合法的用例。这说明,在中心语是否能与形容词并列这一句法能力上,副名结构内部表现出了一定的异质性。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副名结构的不同用例在是否能进行一系列的句法操作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些句法操作分别是:(1)由“很X”变换为“X得很”;(2)修饰名词作定语;(3)在非特定语境下表示比较含义;(4)受否定副词“不”否定;(5)中心语与其他形容词并列。由此,我们不妨认为副名结构内部在能否承担不同的句法操作上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三)两种异质性的区别与联系
前文分析了以往文献里多次提到的语法合法性的异质性,在承担句法操作上的异质性,似乎很容易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两种异质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具体来说,可能是相关的关系:语法合法性高的副名结构用例可以承担更多的句法操作而不会造成合法性的损耗。遗憾的是,这一结论目前还不能得到语言事实的证明。从经验事实上来说,我们并没有对大量的副名结构进行穷尽式的调查。实际上,因为涉及到语法合法性的主观判断,想要用经验手段比如语法合法性判断任务对所有副名结构进行穷尽式的“普筛”可能费时费力甚至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从本文观察到的小部分的内省语料来看,并不是说语法合法性高的用例就能承担所有的句法操作。以句子(36)和(38)为例,按照之前给出的层级性,“很书生气”(抽象名词)应该比“很绅士”(具体名词)的语法合法度高,可是在中心语和形容词并列之后,例(36)却比例(38)更合法,这说明两种异质性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复杂。
三、副名结构的现状与应该采用的分析方法
(一)现状:共时作为历时的一个剖面
由前文分析可知,在“副名结构”这个范畴内的成员的语法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副名结构”并不像“名词”或者“动词”这样是一个内部成员大多数都具有相同的典型特征的范畴。如何来解释这一特殊性呢?本文认为原因在于共时语言和历时语言的互动。众所周知,语法的演变是一个渐变式的过程,而不是基因变化一样的突变过程,历时语言学研究已经说明,如中动句、存现句、“是”字句等句式的产生,量词、结构助词、介词的产生,乃至具体的词汇的形成,都在历史上有一个渐变的时间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在历时演变中任意一个时期的共时研究,都好比是一个剖面,对于正在变化中的结构,用共时的分析手段或许无法将其归入典型的某一类中去。具体就副名结构而言,我们认为副名结构体现的是一部分名词向名词形容词兼类转化的过程,支持这一方向性的证据有两个:首先,副名结构中的名词首先是典型意义上的名词,也就是说变化的起点是名词;其次,在副名结构中活跃了一段时间之后的用例逐渐获得了名形兼类的用法,例如,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很绅士”中的“绅士”,现在已经获得了形容词的用法,比如可以和形容词并列,试看:
(40)大方、英俊又绅士的男人
这说明变化的结果是名形兼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名词都能进入这一结构,即并非所有名词都在向名形兼类转变,这是合情合理的,假设所有名词都转向名形兼类,那才是荒诞的。什么样的名词能进行“形容词化”,这是一个语义上的问题,比如“桌子”“书包”“手表”这样的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就很难形容词化。相反,“贬义”“政治”“社会”这样的本身抽象的名词可能更容易形容词化一些。
(二)二分法:副形结构与狭义的副名结构
针对副名结构的现状,本文认为,正确的分析方式应该是承认历时意义上的“形容词化”,拒绝共时意义上的“形容词化”,在共时层面采取二分法进行分析。为什么在共时层面不能承认“形容词化”的存在呢?因为这会为句法词法的分析造成非常大的负担,如果认为“很绅士”中的“绅士”在词库中是名词,在结构里转化为了形容词,那么就要有一条特定的规则来描写,增加了理论的复杂性。我们认为,有些副名结构语法合法度高;可以承担各种典型AdjP可以承担的句法操作,对于这样的副名结构,不妨认为它在词库里已经是名形兼类,直接以形容词的身份被副词修饰。典型的例子就是“很绅士”“很淑女”,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已经不是副名结构,而是副形结构。相反,有些副名结构语法合法度低;不能承担各种典型AdjP可以承担的句法操作,这样的副名结构是真正意义上的“副词+名词”的组合,它们是正在演变过程中但还没有完成演变的语言用例。
这种二分法的分析在理论上有优越性。首先,从语言事实上来说,已经完成演变的副形结构往往没有副名结构的语用意义,只有狭义的副名结构才有这种意义。“他很绅士”这句话并没有“他很北京”这句话里的评价意义[20],这是因为副形结构已经是正常的语言表达了,而不是特例。如果用构式语法的话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构式”了,自然也没有构式意义。其次,站在汉语语法独特性以及认知-功能语言学的立场上,汉语“表达层面控制语法层面”、重视话语功能、“属于语义型语言”等特点已经能够为副名结构提供合理的解释,没必要再从语法层面上特别列出一条名词形容词化规则,这并不符合语言描写的经济性。最后,对于生成语法等要求统一的语法体系的理论来说,这种二分法其实也可以避免违反“向心结构”。因为“很绅士”等已经完成转化的副形结构本质上没有违反“向心结构”范式,而“很中国”这样的副名结构,由于其具有特殊的语用意义,完全可以认为它们属于语言运用(performance)而非语言能力(competence),或者属于Chomsky所说的外在语言(E-language)而非内在语言(I-language)。生成语法排斥语用因素,因此对于这种基于语用因素的用法可以直接排除在其理论所规定的“语法”的范围之外。
四、结语
“保留说”和“转化说”是两种对副名结构不同的分析态度,本质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超越了理论的争议后,不难发现,副名结构本身具有异质性,可以二分为副形结构和狭义的副名结构。前者的句法功能近似一个典型的AdjP,后者则与典型AdjP格格不入。这种异质性说明了副名结构是名词向名形兼类转变过程中的体现。从共时分析的角度,二分之后的副形结构适用“转化说”,即其中的中心语在词库内就完成了名形转化,狭义的副名结构则适用于“保留说”,直接以名词身份与副词结合,继而获得了构式意义。
注释:
① 他实际上举了两种所谓的例外情况,这里只阐述了与名词形容词化相关的一种。另一种的本质思想是一些副名结构是特定句式中的产物,不是独立存在的结构。
② 也有一些学者尝试从句法角度解释副名组合,如邓思颖应用VP壳(VP-shell)理论,假设汉语中轻动词v可以直接和NP结合生成vP;还可以认为副词和名词之间存在一个空形容词ADJ充当了整个短语的中心语。这些方法相比将副名结构解释为词类转化,不但在理论上不够精简且存在一定的可疑性,在实际上也缺乏相应的形式证据。
③ 这里我们采用的分析方式不认为有一个空形容词作为中心语,或者轻动词v作为中心语。本文从理论最简的原则出发,认为副名结构的中心语就是其中的名词性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