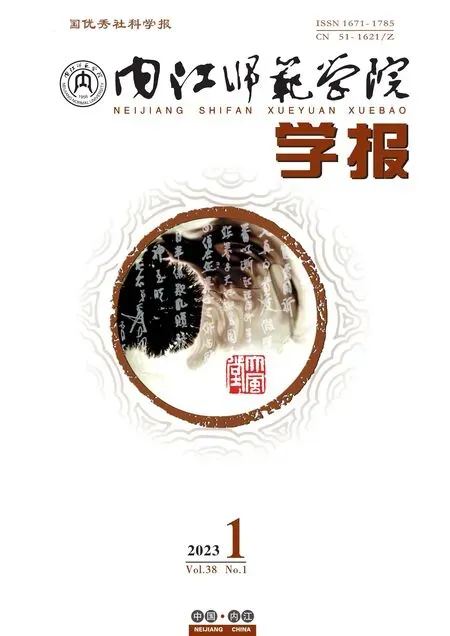王庭筠文学交游研究
李紫岫, 周哲达
(渤海大学 文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00)
王庭筠作为金代极具代表性的文人,其真实的民族属性并非女真族或汉族,而是在数百年前被契丹灭国的渤海国遗裔。渤海遗裔颇受金代统治者重用,他们为金代的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渤海遗裔在辽阳等地迅速壮大了家族势力。王庭筠所在的盖州熊岳王氏家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王氏家族以文学立世,积极与其他渤海遗裔家族互相通聘,维持来之不易的政治地位。金毓黼先生《渤海国志长编》中提到高宪“字仲常,外家王氏,黄华山人王庭筠其舅也。”“(王遵古)娶张浩女,生四子,庭玉、庭坚、庭筠、庭掞。”[1]可见各家族之间互相通婚来强化血缘关系。但文献中很少记载家族之间的内部交往活动。薛瑞兆在《新编全金诗》前言中总结了金诗发展的文化意义,指出这些北方民族诗人中不乏能与历代大家并肩争雄者,王庭筠便是这样一位民族文人代表。王庭筠在渤海遗裔中的文学成就最高,文学作品传世最多。其文学交游的概况亦有迹可循。本论文欲借助王庭筠的交游考辨与其作品分析,总结王庭筠的文学交游情况,并借此窥略金中期渤海遗裔文学交游的概况。
一、游览胜景
游览胜景自古就是文人交游的重要形式。即便在文学地位不太突出的金代,通过游览胜景创作出的优秀诗篇也不在少数。金代文人以中期为最多,文学类型和风格也较初期更为多样化。王庭筠作为中期渤海遗裔文人的代表,在游览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时所创作的诗歌,展现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诉求。
王庭筠的交游活动在文献中少有正面记载。现存文献仅有耶律楚材的和诗《和黄华老人题献陵吴氏成趣园诗》提到王庭筠。王庭筠曾受邀前往献陵成趣园,并题诗一首。成趣园之名取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园日涉以成趣”一句,意在表明想要追求陶渊明那般隐居的悠闲生活。牛贵琥在《金代文学编年史》中提到的成趣园为献州梁子直所建,路铎、党怀英等当时名士都曾到此游历作诗。而从耶律楚材的和诗可知,当时王庭筠游览的成趣园为吴氏所建,并非梁氏。这一说法也仅在此和诗中提及。可见成趣园在当时并不仅是特指某一名园,大概献州成趣园被文士所推崇后,亦有其他富商借此名气修建。正如牛贵琥所言,献州成趣园不过是“和平时期有钱有地位的人为追求享乐、附庸风雅而建造的,和陶渊明一点也不搭界”[2]302。大概吴氏所建的成趣园也是如此。王庭筠受吴氏邀请为其园作诗,而且两个园林同建于献州,不过是以此博出名罢了。可见,无论是以党怀英为首的成趣园,还是王庭筠笔下的成趣园,他们的交游目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好友相聚,而是在交往中掺杂了政治的对立和人情的往来。这种现状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当外部环境安稳时,政权内部自身便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王庭筠无意或是被迫参与党派纷争后,其文学作品的表达也就很难抒发内心纯粹的情感。再者,随着金中期交游影响范围的扩大,社会文化的高度发展,文人们交游的目的不再单一。王庭筠作为中期文学大家,与之相交的文人不乏邀名之嫌。这样的情况在金初期文人交游中是少有的。金初期的海岳楼和中期的成趣园交游目的对照就是最好的证明。王庭筠之父王遵古作为早期文人群体交游的组织者,聚集在此的文人政治地位差距较小。他们不期求以交游邀名,所以他们的交游较为随性单纯。据刘国宾在《渤海诗文辑校》一书记载,皇统九年进士王珦与王遵古诸人游历海岳楼,并共作诗歌《王元仲海岳楼同诸公赋》,全诗为:
十二珠栏倚半空,元龙高卧定谁雄。檐楹翠湿蓬山雨,枕簟凉生弱水风。
物色横陈诗卷里,云涛飞动酒杯中。谪仙会有骑鲸便,八极神游路可通。[3]325
据悉,海岳楼是由王遵古出资修建,主要用以家族藏书和教授本族子侄学习,后来逐渐成为交友会客的胜地。王寂在《鸭江行部志》记载了该诗的创作背景。书中提到在海岳楼宴饮题诗者应有二十五人,其中还包括另一位渤海遗裔张汝霖——也是王遵古的姻兄。其晚年与王庭筠交往颇深。王珦所作诗歌整篇以描写海岳楼壮丽的景色为主,从高悬半空的珠栏到浸湿雨水的檐楹,无一不在透露着海岳楼恢宏的气势。再以“物色横陈诗卷里,云涛飞动酒杯中”一语描绘海岳楼及周遭环境。之后,又在诗中穿插典故,以陈元龙高卧、李白骑鲸等豪放洒脱行为为例来夸赞当时同聚海岳楼的文士都为旷达之辈。尾句中“八极神游路可通”是作者期望未来有更多文士共聚此地。按照王寂的记载及该诗诗题,当时作诗唱和者不在少数,更有赋篇留世。由于年代久远,又饱经战乱纷扰,诗文几乎没有流传。从文献记载来看,蔡珪、赵可、王遵古等人都在海陵王时期及第,郑子聃、张汝霖同年及第。可见当时与王遵古在海岳楼宴饮赋诗之人,大多是当下刚及第不久的青年才俊。而且这些文人多有在辽阳及其周围地区任职的经历,如李晏“稍迁辽阳幕官,与兴陵有藩袛之旧”[4]489。蔡珪曾担任澄州军事判官。而张汝霖又是辽阳人,郑子聃与张汝霖为同期进士,后与王遵古等人交好。可以说,这次海岳楼相聚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是一场以辽阳及附近等地的地方官员组织起来的交游活动。他们以相似的仕宦经历在海岳楼中诗酒唱和,延续了唐宋文人交游雅集的传统。
总的来说,文人雅集作为以王庭筠为首的渤海遗裔与其他文人交游的一个重要纽带,不仅是友人之间的交往媒介,更成为王庭筠家族的文学标识。《新编全金诗》中记载了王寂在明昌二年前往熊岳海岳楼拜见王遵古之诗。其中“先生勇退冀北空,坐笑百雌无一雄。咄咄诸郎有高著,纷纷余子甘下风”[5]589二句不仅夸赞了王庭筠兄弟的文学成就,甚至其祖父王政的英勇退敌的事迹也成为其家族的一个标记。自王寂之后,海岳楼逐渐成为后世文人夸耀渤海王氏的一个标识。李纯甫在其诗《子端山水同裕之赋》中有诗句“只留海岳楼中景,长在经营惨淡中”[6]984。诗题中的子端便是王庭筠,裕之是元好问。这首诗作于王庭筠过世之后。从诗题来看,是二人借王庭筠山水画进行的唱和之作。诗中所提到的海岳楼便是指当时盛极一时的海岳楼。“经营惨淡”借用唐代杜甫的诗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一句,其中“惨淡经营”是指在画作上有独特的构思。由此来看李纯甫在诗歌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与杜诗相同。其人虽已没,但画作中精彩的构思长存,引得后世者为之赞叹。赵秉文亦有此类似的作品,赵秉文作为王庭筠仕宦时期的同僚,两人时有交往,泰和三年其以使者身份前往东北等地,并留有诗歌作品。从《连云岛望海》中“烟中熊岳随潮没”一句,可知作者确曾到过王庭筠故乡熊岳县。《海月》一诗中“为君挂席拾溟海,海岳楼头斫冰雪”[6]1119所提到的便是海岳楼。元好问在其诗《王学士熊岳图二首》中也有“长松手种欲摩天,海岳楼空落照边”[7]之句,这是在王庭筠庭筠所作《熊岳图》上的题画诗。其中“海岳楼空落照边”一句非常委婉地表述自王遵古、王庭筠过世之后,海岳楼文人云集的盛况不再,王氏家族步入衰落局面。
除去人文景观下的交游唱和,自然景观也成为王庭筠交游的雅集胜地。在人文景观交游下王庭筠可能存在邀名心态,但在自然景观中,王庭筠不仅不邀名,甚至在刻意回避这种名声,更多是以一种隐逸的心态与友人同游。这些作品大多是作于隐居期间,所以多真情闲适之作。元好问在《王黄华墓碑》中记载了王庭筠的仕宦经历。尤其是在两次隐居期间,王庭筠借此机会留下了非常多的诗文作品。首先是作者早期隐居黄华山时,文献记载与王庭筠交游者有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渡等,仅有韩玉和李澥在书中有记载。其中李澥在《中州集》记载:“澥字公渡,相人。少从王内翰子端学诗,能行书,工画山水。”[4]1907“相人”指彰德府人。“相”是北宋时期州郡名,金代改称彰德府,也就是王庭筠隐居的地方。由此可推,李澥在大定年间与隐居在黄华山的王庭筠颇有交集。不仅与之学诗,还有书法、绘画大多都师从王庭筠。《归潜志》中亦有记载:“为诗及字画,皆得法于黄华。”[8]28《金史》中评价李澥“诗不如字,字不如画”之语与时人评价王庭筠颇为相似。《中州集》为韩玉作小传。根据记载来看,韩玉祖籍也是彰德府人。书中记载:“温甫,明昌五年经义、辞赋两科进士,入翰林为应奉。”[4]2181明昌五年,王庭筠迁翰林修撰,而韩温甫也在这一年入职翰林,所以二人的相识应该是在明昌五年左右。此外还有《五松亭记》与《李辅之得邺南城雨注瓦以之支琴》。一文一诗都是作者在隐居黄华之时与当时彰德府官员李辅之弼相交游留下的作品。《五松亭记》记载“李辅之丞此邑也,初入寺,爱之不能归”[9]1821之语应是在入山之前李辅之便与王庭筠相识,与王交好之后便请求其为五松亭作记一篇。可见当时王庭筠虽然隐居在黄华山,但依旧与当时名士保持着交游关系。之后在《李辅之得邺南城雨注瓦以之支琴》一诗中再次提到李辅之,可见李弼在王庭筠隐居黄华期间是其一直交往的好友。“可怜此君落君手,爱之不博连城璧”一语中作者以诙谐的口吻轻嘲李弼用价值连城的雨瓦作为琴支,亦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张晋芳在《论金代诗学的北地特质》中提出金代北地文学家因受地域、自身民族特质种种影响,在诗文创作中形成以“真性情”为准则的创作内核。王庭筠在这两首诗中便展现了其作为北地文人“不拘小节、质朴适意的交往习惯”[10]。王庭筠在河南林虑隐居期间,一直希冀能够效仿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因此,在其现存诗文中更多的是对平淡闲适生活的描写。如诗人在《野堂》中提到的“门前剥啄定佳客,檐外孱颜皆好山”亦是作者以一种悠闲的姿态与一二好友隐居黄华山的真实写照。此外,薛瑞兆在《新编全金诗》中新收录了王庭筠的《寄任君谟》。任君谟是金代大书画家任询。《保定府志》记载王庭筠曾随任询学画,对任询书画作品十分推崇。由于任询诗文大部分都已散佚,现仅有此诗作为二人交往的见证。诗中“人物眇然今已矣,先生持此欲安之。狼山深绝无人处,归和渊明五字诗”[5]643二句透露了任询晚年无奈隐居。但王庭筠在诗中以“欲安之”宽慰任询,希望他能如自己一般在山水间寻找真正的安稳。
与王庭筠同为渤海遗裔的高德裔也有交游文学存世。高德裔少年及第,曾在明昌元年与路元、韩琪等人同游王官谷,现存散文《游王官谷记》一则。文中提到“首谒表圣祠下,寻三休之故基,揖天柱之危峰”[2]300。其中“圣祠”就是指祭拜孔子的庙祠,“三休”是指晚唐诗人司空图在山西永济修建的休休亭。高德裔与当地名士交游,模仿魏晋文人在山林间流觞曲水,包括寻找休休亭,大约是众人想要效仿司空图隐逸于此的行为,遂有高韬隐逸的寻亭之举。高德裔在行文中提到自己曾不止一次想要游览王官谷。这次能因职务之便与好友登览此处,畅游在幽山闭谷之中,暂时远离朝堂纷争,倒不失一件畅快之事。
王庭筠此类作品能够被后世文人认可和流传,既体现了自然美景对其个人心态和文学作品的积极影响,也证实了王庭筠能在自然与名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两者的有效办法。既不会使自己被朝堂政务束缚,也能在山水美景间寻找现实的静谧。诗人徜徉在自然山水间,内心淤积的情愫全然倾洒。在这里,王庭筠可以随意潇洒地生活。这样的环境和心态之下所创作出的作品,自然更能体现作者的真实情感。
二、扈从游猎
金代皇帝为了确保其女真本民族勇猛习俗的传承,即便在迁都之后,也一直保持着围猎的习惯。这种行为尤其表现在金世宗、金章宗两朝。金中期两朝皇帝在位期间多次举行围猎活动。其中金世宗多次前往金莲川。金章宗在位二十年,十七年都有秋山围猎的记录。围猎地点在文献记载中并未言明,多以“秋山”代之。金代皇帝会携带部分官员、文士一同前往狩猎场所。围猎之余也会举办诗酒唱和之宴会,并命文人之间同题唱和竞作,以此留下一众应制之作。《大金国志校证》中谈到:“金国酷喜田猎……世宗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谏:曰作乐,曰饭僧,曰围场。其重田猎如此。”[11]春水秋山便是金代特有的一种围猎活动场地。从字面意义来看,“春水”就是指在春天时期进行的围猎活动,“秋山”是主要是指秋猎。赵秉文在其诗《扈从行》提到“春水围鹅秋射鹿”一句可知春秋季围猎的不同。《金史》中记载:“泰和元年,复为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三十余首。上甚嘉之。”[12]泰和元年九月,金章宗再次前往秋山围猎,其同行人员有王庭筠、翰林修撰杨云翼等。杨云翼在扈从期间有诗《谩兴》一首:
乍寒帘幔一灯青,从吏羁情尔许清。叶拥西风秋有思,天垂北斗夜无声。
吟蛩绕梦家千里,过雁连愁月四更。寄语黄华耐岑寂,好看霜蕊到归程。[6]1062
从题目来看,应是作者到了秋山猎场后闲暇之时赠与王庭筠的随意之作。史料记载杨云翼在明昌五年进士第一,迁应奉翰林文字,而此时王庭筠刚从翰林文字迁为翰林修撰。由此可见,二人大约在此时便已相识。之后王庭筠明昌六年罢职,直到泰和元年才恢复翰林修撰。而杨云翼外调多年,也是在泰和元年回到朝廷再次与王庭筠共事。这次二人同赴秋山,虽从诗题看是作者的随心之作,但从诗中内容来看,作者将自己的悲观情绪熔铸于诗中,又以“叶拥西风”“过雁连愁”等典故暗示二人对故乡的思念。在诗中尾联作者直接指出希望王庭筠能够按捺住寂寞,待到霜蕊花开便是二人的归程。这首诗歌若是抛开创作背景,是一首很明显的思乡之作。如果结合当时境况分析,二人跟随皇帝秋山围猎,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理应是一种极大的荣光。但从杨云翼的诗中来看,并没有对能够参与围猎表现出兴奋之感,反而更添一丝迫不得已的意味。杨云翼以此诗赠予王庭筠,也表明受赠之人对皇权富贵所表现出的淡泊心态。纵观杨云翼在扈从秋山之前的仕宦生涯一帆风顺,而在此诗中陡然作思归之语,猜测这应是杨云翼写给王庭筠的安抚之诗。站在王庭筠的立场,劝慰他既来之则安之。而王庭筠此时已是宦海浮沉多年,心态和年龄早已不似往常,即使面对金章宗有意提拔,也无心于此,毕竟多年归隐的生活早已将其塑造成了一个不恋俗世的“陶隐客”。再结合同一时期王庭筠所写的诗歌《超化寺》也可以证实这一猜想。从诗歌中后两联“吾道萧条三已仕,此行衰病独登临。简书催得匆匆去,暗记风烟拟梦寻”[5]634可知,王庭筠再度出仕时已是疾病缠身,且皇帝匆忙召唤。如今这般闲适的生活只能在梦中寻觅了。
史书记载王庭筠在此次秋山围猎中共作应制诗有三十余首。从杨云翼当时所作诗歌不难看出王庭筠应制诗的创作心境。现存文献中仅有宋濂的《题王庭筠秋山应制诗稿》对王庭筠的秋山应制诗有所研究,文中提到:“武元文烈诸孙,虽欲求一乳兔而射之,尚何可得耶。观庭筠之诗而感慨系之矣。自当时言之,孰不效上林羽猎以侈大荣观,而庭筠乃能以秋山不合围为风,则庭筠者,亦良士也哉。”[13]宋濂以古往今来盛衰荣辱对照为例,将金晚期皇室仓促南逃的场景与秋山应制诗下所描写的昌盛繁荣的局面相对照,不由得为之感慨。文中提到作者是阅读了王庭筠的诗歌才感慨颇多。由此可知,当时王庭筠的应制诗多为描写围猎宏大壮观的场景,以及夸赞金章宗执政时期政治清明、天下承平的诗句。宋濂对大肆铺排围猎的行为颇为不满,但读到王庭筠应制诗后,也就是现在仅存的一句残诗“秋山不合围”之后,更多的是对王庭筠的钦佩和夸赞。该句引用《礼记·王制》中“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14]一句,是指天子在狩猎的时候只将猎场的三面围住,留出一面缺口给牲畜逃跑以活路,这样既保证当地物种和谐发展,还能借此在百姓之中展示出帝王的仁爱之心。王庭筠以此为诗,虽是应制之作,但将劝诫之语融入其中,可见王庭筠在当时确实是一位贤臣良士。此外,宋濂在诗稿中透露出直至明朝王庭筠应制之作仅存不足半数。宋濂当时能看到的作品还有《牡丹》《酴醿》《松影》。这些诗虽没有注明时间,但从诗题来看多为奉旨之作。这些诗中也仅有王庭筠的应制诗“秋山不合围”一句别出心裁。也正是这一句的留存,让人们意识到王庭筠虽渴望归隐,但在仕宦期间,也不忘自己作为谏臣的职责。当其他文人还在以繁华胜景的应制之作来为自己博出名时,王庭筠却能将自身利益置之度外来规劝君王,而这样的诗句正揭示了王庭筠对过度专制君权的不认同以及其高尚人格的体现。
扈从游猎之下多出应制之作。王庭筠虽有友人在秋山围猎的交游赠寄之作,从中暗含对归隐生活的思念,但在其扈从期间最具有价值的“秋山不合围”诗句中,不仅提升了当下应制诗的质量,更直接展现了王庭筠高尚的人格品质:虽有归隐之心,但依旧能够恪尽职守。即便是上呈帝王的应制之作,亦能在诗中极具劝谏之语。这样的作品在众多应制之作中是难能可贵的。
三、书画会友
金朝渤海遗裔在文学上时有翘楚,但能够在字画、文学兼有所长者不多,王庭筠便是其中一位。冯璧在诗中评价王庭筠字画:“诗名摩诘画绝世,人品右军书入神。”[3]382是指其诗、画成就堪比唐朝王维,书法堪比东晋王羲之。于东新在《金中期诗话的三种理论》一文认为:“冯璧以王摩诘比拟王庭筠,显然是看到二人诗艺的‘闲逸’之妙。”[15]而王庭筠在其字画创作中也确实秉持着这一观点。无论其境遇如何,王庭筠在书画作品中都尽力营造出一种闲逸的心态。赵秉文早期赠诗评价王庭筠书画为“李白一杯人影月,郑虔三绝画诗书”[6]1249。诗中提到的郑虔三绝是指唐代文士郑虔在诗、书、画兼有造诣。赵秉文如此作比,更是表明了对王庭筠文学艺术造诣的肯定。元好问在《王黄华墓碑》中称赞“世之书法,皆师二王……而公则得于气韵之间”[16]。王庭筠书法能在米芾和黄庭坚之间达到平衡气韵之美,可见其功力之深,因此能在明昌元年被招入书画局当差。王庭筠一生创作诗文字画众多,从当时文人对其诗画的评价来看,书画成就略高于诗文作品。
王庭筠生前颇为爱惜自己的作品,其山水、墨竹之类画品甚高却很少轻易赠送他人。所以在同时代文人文学作品中几乎很少发现相关的交游记载,至于书画类交游更是不见记录。仅有赵秉文《跋黄华墨竹》组诗似作于王庭筠隐居黄华山之时,与另一首赠予王庭筠《寄王学士》大约作于同时期,猜测王庭筠可能赠赵秉文墨竹画。刘祁在《归潜志》中亦记录了这首诗。文中提到的“赵闲闲少尝寄黄华诗,黄华称之‘姓王氏非作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诗至今为人传诵,且赵以此诗初得名”[8]86也可证明是赵秉文早期与王庭筠交游作品。王庭筠多年隐居黄华山,当地的风景名物影响了他在书法、绘画上的创作。归隐后他有更多闲暇时间去感受自然,打磨书画技艺。赵秉文对其所作墨竹画大力称赞,将王庭筠比作北宋著名画家文与可、苏轼。可见当时王庭筠画竹技艺之高。王庭筠在书画地位文献中少有记载,但后人对其书画艺术作品的评价却甚高,尤其是元代文学大家王恽,在其著作《秋涧文集》中有多篇关于王庭筠字画的跋文。
王庭筠现存与友人的交游之作有《风雪松杉图跋》。《风雪松杉图》作者是李山。王庭筠之子王万庆在所作《李山风雪松杉图跋》中提到李山曾入职秘书监,而王庭筠正是在泰和元年为此图作诗跋,可知二人在任职期间交情匪浅。现仅留有一幅画和一首诗跋作为二人之间交往的见证。这幅画现在珍藏于美国,其诗跋全文如下:
“绕院千千万万峰,满天风雪打杉松。地炉火暖黄昏睡,更有何人似我慵。”此参寥诗,非本色住山人不能作也。黄华真逸书,书后,客至曰:“此贾岛诗也。”未知孰是。[9]1822
根据这一段诗跋,前四句是王庭筠在画卷中誊抄前人的诗句,所以其后才会有对作者是谁的争论。王庭筠认为是参寥之诗。参寥,宋代名僧,曾与苏轼同游,也是一名隐士。王庭筠指出只有像参寥这样真正远离尘世之人才能作出此等佳作。后有客人到访认为该诗作者是贾岛,争论许久也未得出准确结论。其实这首诗出自宋代诗人潘阆之手,全名为《宿灵隐寺》。从整幅图画来看,此画中风物与诗歌内容高度重合,不难发现这是一幅诗画图。总而言之,按照王庭筠的观点,他将此诗题于画中是因为“非本色住山人不能作也”。毕竟此时王庭筠已是三度入仕,身心俱疲,内心更多的是对归隐自然的渴望。而作此画的李山也早已到了乞骸骨的年岁。二人归隐心意一拍即合,遂留下这幅千古名画和题跋。
总体来看,在书画交游方面,文献中所透露出的交际范围是相比于其他两种交游形式较小,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前文所提到的作者个人爱惜名声,不愿轻易将自己的书画作品赠予他人。二是王庭筠大部分字画作品作于隐居黄华山之时,本是隐居客,自然与世俗之人相隔,双方之间的交往自然要淡薄得多,抑或是王庭筠有意远离朝堂,仅有类如赵秉文这等主动赠诗交往之人,才能有获得其墨宝的机会。三是时代久远以及金后期战火纷扰,书画难以保存,或许王庭筠曾有参加类似东晋文人兰亭集会的活动也未可知。也就是说,即便王庭筠是以书画会友的方式交游,无论是其早期作品还是晚年间与友人的题画之作,都暗含了作者的隐逸情怀,既有隐逸情怀在内,其交游影响较小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结语
文士之间的交游,促使个人地位得到了凸显,由早期单纯的交友心态逐渐过渡为注重个人文名声名的提高,王庭筠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首先表现在黄华山隐居时期的交游,他第一次及第赴任时声名并不煊赫,反而在隐居黄华山之后,与之相游者如李澥、韩玉等或为当世文坛上客,或是科举新贵,与之交游者无一不彰显着王庭筠的文学地位。再有赵秉文寄诗黄华老人而一举成名天下知。赵秉文借助王庭筠文名的这股东风,为其日后执掌文坛开辟了道路。可见当时王庭筠即便隐居黄华多年其文学才能依旧被世人认可,而世人亦能以与其同游为荣。
王庭筠作为金代渤海遗裔最出色的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隐逸情怀不仅来源于他个人对生活的认知,亦有其遗裔文化的影响。早期诸如王政、王遵古、张汝霖等人,他们都曾仕宦于金朝。其中王遵古曾担任章宗的侍讲老师,张汝霖更是成为世宗培养的顾命大臣。即便是这样高的社会地位,这些遗裔也没有醉心其中,反而在其诗文中多抒发自己对故乡或是对山水美景的眷恋。显而易见,金代渤海遗裔文人虽多出仕,但其骨子里的随性洒脱、渴望自由早已成为后世遗裔仕宦文人奉行的标杆。王庭筠正是受这种心态、文化的影响,在与友人交往或是仕宦期间,隐逸的心境、归隐的情怀往往隐现于诗文之中。除此之外,从整个金中期大环境来看,世宗、章宗两朝不断地收缩皇权,对作为既是外戚又是开国功臣的渤海遗裔有所忌惮,这也是渤海遗裔高层官员数量减少的原因。因此,渤海遗裔仕宦文人在整个中期普遍处于一种高压状态,他们或许已经预料到这一身份限制了他们在官场上的发展,所以索性便沉醉于自然山水之间,寻找一份内心的静谧。
王庭筠现存诗文中虽少有与渤海遗裔这一群体间的交游唱和或是家宴记载,但他积极向外界拓展,不仅与当下名士交谈唱和,而且引得后世文豪如元好问、耶律楚材等人的夸赞,他以宗唐学宋的文学底蕴和深厚的家学修养在金朝文坛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样的文学创作和影响力,已经足以证明王庭筠在当时的文学地位。而王庭筠虽为渤海遗裔,但渤海国文化本就被汉学浸淫,历经百年的渤海遗裔在辽金两朝也一直致力于涵咏文学,无论是辽代的大瑟瑟,还是金代的王庭筠,这类少数民族作家以汉文化的底蕴使本民族的文学闻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