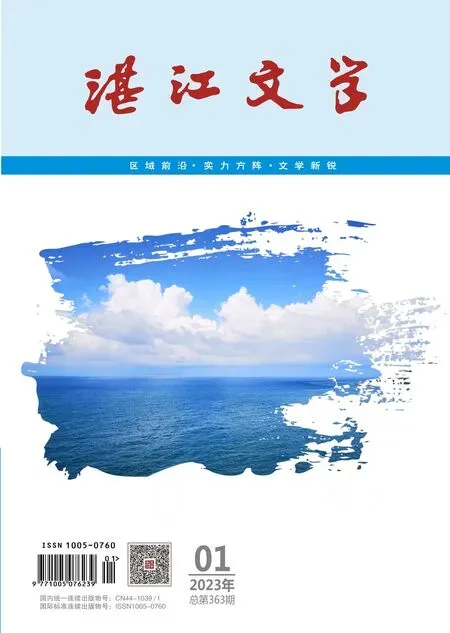茶村天笑
◎ 林 宕
一
还没有走近发亮家的场角,亚军就闻到了一股茶水味道。发亮和他弟弟分家了,许多人去他家吃“分家茶”了。
亚军想转身,脚却不听他,继续往前走。越走近发亮家的场角,钻进他的鼻腔里的茶水味越浓,茶水味中还掺着熏青豆、酱瓜、咸菜等小吃的味道。他的听觉也灵敏起来,他听到了声音,听到了声音中有关他家的事。他们说的是娟娟。
娟娟是亚军刚讨进家门的娘子。几天前,没有跟家里人打招呼,娟娟就一夜不回,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她大概不知道亚军爸当天夜里去过她娘家了,所以,她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事回娘家了,晏了,就在那里过夜了。亚军张开嘴,想说什么,又终于没有说什么,心想,随便它了,反正已经回家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却让村里人嚼起了舌头。
一歇后,亚军站起来,终于往回走了。可他的耳边还在不断传来吃茶现场的声音,这些声音还在说娟娟,很快,也说到了他,甚至说到了他爷娘。他甩甩头,想甩掉这些声音,可是,这是繁难的。他就奔起来,仿佛那些声音是追逐他的几条狗,他越奔越快,最后,奔进了一片杂木林里。
声音的狗似乎没有跟进来。亚军喘着粗气站定。地上的枯叶,在向他散发着一股温热的湿气。他侧转脸来,想倾听吃茶现场上传来的声音,可听到的是头顶上传出了一片鸟鸣声。此时的他,觉得这鸟鸣声从来没有过的好听。可好景不长,树枝里的鸟像是发现了他,不叫了。他又侧转脸来,屏息片刻,什么都听不到了。本来,他认为鸟鸣声没有后,另一种声音会重新传来,可是没有了。比起刚才的鸟鸣声,他觉得突然降临的静更加动听。他高兴地在软软的树叶上往上跳了一下。
可是,好像就是因为这一跳,把那些声音重新跳了出来,那些声音又钻进了他的耳朵里。与此同时,他的眼前还出现了一个吃茶的画面,村里的茶客们被热气缭绕着,他们的嘴巴在频繁落开的过程中,露出沾满了茶垢和烟斑的牙齿。发亮妈拎着一把茶壶,来回走在几张桌子间,给茶客们倒茶。她对茶客们嘴巴里发出的任何话语,都以微笑面对,却不开口,她给茶客们面前的茶杯里倒水,好像就是为了让他们说得更起劲、更畅快。于是,他们真的说得更起劲、更畅快了。是的,村里尽管经常发生这样、那样的大小事情,可像亚军家这样的事,可能要好久才能发生一次,他们怎么能放过它呢?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从自己嘴巴里轻易溜走呢?何况,村里还有“请吃茶”这样的场所,这样的场所把闲人们都集中起来了,闲人就要讲“闲话”,“闲话”最热衷的就是那些村里好久才能发生一回的事。
亚军又看到一张嘴巴落开了,从蜡黄的牙齿缝里蹦出了一句更加难听的话语。
他“嗷”地叫了一声。那只声音的“狗”也窜进了林子里,还咬了他一口。他疼了,龇牙咧嘴了,然后跌坐到了落叶上。声音的“狗”继续咬他,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拧住自己的大腿,忍住,不再龇牙咧嘴。声音的“狗”咬得越厉害,他右手的两指在自己大腿上拧得更厉害。慢慢地,他感觉不到疼痛了。再后来,他的拇指和食指上竟然有了一股快意,这股快意往上传递,到达了他的心里。
亚军居然盼望着茶场上的人继续讲他家的事,讲得更着力,也让声音的“狗”咬他咬得更加着力。
与此同时,小时候的一个情景出现在了他的脑幕上。
二
小时候,亚军与白相淘伴常常互出“雅号”来作践对方。像打乒乓一样,两个人让“赣卵”等一类糟蹋性字眼在两人之间快速往返。慢慢地,跟打架一样,力大气粗的一方还在把“乒乓球”“拍”向对方,力小气短的一方则不再招架,不吭声了,眼睛里也在渗出眼泪。这个眼睛里在渗出眼泪的小孩就是曾经的亚军。
屈辱,让亚军眼睛里的泪水不断掉落,而对方的嘴里仍旧在喷出各种“雅号”。这些“雅号”可以是有形的东西,如天地间各种丑陋的动植物,也可以是一些无形的东西,如“臭屁”等。所以,力大气粗的人只要愿意,他嘴巴里可以源源不断地吐出各种“雅号”,即使新的“雅号”一时想不出,他也可以把先头说过的“雅号”再从头来上一遍。
就在那个力大气粗者的嘴里还在不断喷出“雅号”时,亚军不再落泪,他的嘴巴也动了,只是说出的内容与之前有了差别,之前每当他面前的那人动一次嘴,他动嘴还上的是一句“你是xxx”,这一次,他动嘴还上的是“我是xxx”。力大气粗者先是呆了一下,然后饶有兴致地继续说下去,可很快,他的嘴巴不动了,似乎失去了再说下去的兴趣。同时,轮到年少的亚军“力大气粗”了,他都不等对方“回敬”,嘴巴一开一合地连续动着,不断喷出“我是百脚虫”等一类自我贬损的话,一股快意居然也在他的心底涌动。当他看到对方终于“吃瘪”,不再出声,心里的快意就涌动得更着力了,这快意还升腾起来,升腾到了他的喉咙口,又从他的喉咙口窜出来,变成了嘴角边的一抹笑容。对方脸上则露出了气恼的神色,一挥手,说声操那,然后转身离开。亚军立刻晓得,自己赢了。
可这是怎样的一种赢啊,这是一种帮助对方一道攻击自己后才取得的赢啊,这种赢算赢吗?亚军终于认识到这种赢不算赢,所以,当他后来独自躲到一个林子里时,心底里的那股快意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屈辱感。他又哭了。面对着那棵长满瘤子的大树,他仿佛面对着刚才不断给他出“雅号”的那个人,而那人仍在不断地口吐“雅号”,因而他心底的那股屈辱感越加浓烈了,于是,他又开始自己给自己出“雅号”了,他的嘴巴不断地说、狠狠地说——不知不觉中,他心底的那股屈辱感变成了一股恨意,他在恨自己。他几乎是在咬牙切齿地说自己,他说,我是“赤练蛇”,我是……慢慢地,他心底的那股恨意化解开来,又一次化解成了丝丝快意,这快意迅速浓烈起来,还像先前那次一样,升腾起来,窜出他的喉咙口,再次变成了他嘴角上的一抹笑容。可他没有停止,继续作践自己,那抹笑容就牢牢地停驻在了他的嘴角上,还慢慢扩大。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亚军发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很多时候,自己作践自己,会让他心里获得快感。面对这一发现,他说不清自己该不该高兴。说高兴,不到万不得已,亚军绝不自己作践自己;说不高兴,每次作践自己,那股快感还是会真切地从他心底涌上来。
当小时候作践自己的情景再一次映现在亚军大脑中时,他在布满枯叶的地上站了起来,走出杂木林。
三
亚军朝发亮家的场地上走,这一次,他不再犹豫,走得很快,没费多长时间,就走到了发亮家的屋场前。
不过,还没走近吃茶人群,他的头皮就麻了一下,他以为场上的人都在看他了。他镇静下来,往前走几步,在一个空位上坐下。他认为别人都在等着他说话,就开口说,应该是你们说的,你们为啥要等我说?你们说吧,说说我家里的事……
亚军转一下头颈,瞪着身旁的子云,说:
“你说呀!”
子云说:“说啥?”
“说我家的事啊,说我女人的事。”
“你的脑子坏了。”
子云想伸手摸亚军的头,可亚军别转头,让开了他的手,反而伸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胸口,说:
“子云,你说啊,说说我家的人!我要听,你怎么不说了?”
子云站起来,说:
“你脑子坏了。我不想跟你打架。”
子云挣脱亚军的手,跳到一边,他像是刚刚跳离一个险境,人虽离开,眼睛却仍旧警觉地看着这个“险境”。
可亚军没有追上来,他转了转头颈,说:
“你们不说,我来说。”
没人应他。他又说,我讨了不该讨的女人,这个女人以前跟祥生轧过朋友。现在,她还在想头祥生,那天,她就是跟着祥生走的,一夜不回……
屋场上出人意料地静,大家都在听。亚军就又把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重复了一遍后,他提高嗓音,继续说,我是猪头三,别人想偷我自家女人,不敢出声;自家女人在外头瞎七搭八,也不敢出声……
场上的人都屏息聆听着,好几人脸上露出了笑,可没有一个人出声,似乎亚军的出声已经让他们不会出声了。
亚军的嘴角上泛出白沫,那里也挂上了一丝笑容——在他出声时,面对着他的人都不出声了,这说明他的出声很有效。亚军想,最好在他不在场、不出声时,那些吃茶的人也不会出声,不会讲他和他的家人了,那么,他就彻底赢了——这个念头,是他在获得一份作践自己的快感时生出的,是念头,也可以说是目标。他已经隐约觉得自己离这个目标不远了,只要自己继续努力。
接下来,哪里有请吃茶的地方,他就想去那里,而且还要发声。他要让他们都像那个曾给他出“雅号”的人一样,觉得继续说他家的事很无趣。亚军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的“出声”问题——想到这个目标,亚军觉得身上滋长出了一股力道,也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名武者,即将赶赴不远处的一个擂台。那个擂台要是突然消失了,他感到对他来说倒不是一桩好事,会让他浑身上下刚刚鼓起来的力道没有出处。而且,他也有点担忧别人不再讲他家的事了。
所以,现在的亚军,已变了。
很奇怪,这变了的亚军似乎也改变了娟娟。娟娟对亚军客气起来。要知道,尽管娟娟嫁过来只有两个月,可娟娟已经习惯了对亚军吆五喝六,要不,就是不理不睬。现在,娟娟对亚军和颜悦色了。
她趁周围没有人时,轻声细语地对亚军说:
“我不好。”
亚军不吭声。
娟娟又说:“我不是好人。”
亚军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娟娟,觉得她怎么也跟自己一样了?也开始贬低自己了?
四
在亚军面前说过自己不是好人后,娟娟就打算离开亚军家了。上次,她尽管不辞而别了一整夜,可第二天早上还是回来了。这一次,她真正想离开亚军家了。打点好衣物后,她来到亚军父母前,跪下,说:
“今生欠下的,只能来世还了,来世如果投生一条狗,就来给你们看门;来世如果投生一头牛,就来给你们耕地;来世如果还是投生成一名女的,做女儿还是儿媳妇由你们定……”
看着涕泪交流的娟娟,亚军爸妈一声不吭。待他们想说什么时,娟娟已经不在眼前。
亚军妈摇晃着身子走到亚军跟前,狠狠地抽了他两个耳光,说,你丢尽了我们家的脸。说罢,她似是沉思了一下,举手也抽了自己两个耳光,说,谁都不能怪,让她走吧。
亚军妈愿意让娟娟走,可亚军的亲亲眷眷不情愿。有人还摩拳擦掌了,亚军爸妈制止,亲眷们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可仍有两人不能平复内心的情绪,是亚军的堂叔和表哥。第二天早上,两人向娟娟家走去,他们要去“请”娟娟了。
尽管堂叔和表哥肚皮里还有气,可他们还是按照“请”的规矩,用一根扁担挑起了大竹篮和篾箩,竹篮里放着香糯糕、赤豆粽、莲藕,篮的边缘插着几朵并蒂莲花;篾箩里放着本地产的青角薄稻米,上面插着几朵百合花——堂叔和表哥把娟娟的离去权且当作了一次夫妻正常吵架后的赌气。这在横泾是常有的事,夫妻之间为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后,男方的家人或亲眷就会去女方娘家“请”。而此时,女方的家人一般也在等候着男方的人来“请”,男方的人来“请”了,就说明男方在吵架后认错了,放下了身段。如果男方去“请”得晚了,让女方等待的时候过长,女方的家人会光火,这样,男方就要增加去“请”的次数,第一次是“请”不回的。一般情况下,只要女方因赌气一回到娘家,男方就会立刻去“请”,而且,每增加一次“请”,男方就要多“破财”一回。这笔账,横泾人都会算。
可这一次,娟娟的回娘家并不是吵架这么简单。亚军的堂叔和表哥肚皮里清楚,娟娟的这次回娘家其实不能这样来“请”的。堂叔和表哥挑着担子来“请”娟娟,是权且把娟娟的回娘家当作夫妻间一次正常吵架的结果了。
最初,娟娟爸妈也把娟娟的回家当成了夫妻间正常吵架后的赌气。所以,当亚军的堂叔和表哥到来后,她爸妈客气地让座、递烟泡茶,还催着娟娟尽快收拾东西,跟堂叔和表哥回去。可娟娟不听她爸妈,反而一溜烟地走出家门,直到夜幕降临,她还没有回家。
娟娟爸妈就去外面拷了大曲、买了下酒菜,尽心招待堂叔、表哥吃夜饭。可是,直到半夜,娟娟也没有回来。她爸妈急了,堂叔和表哥倒显得不忧不急,一副要在这里继续等下去的样子。后来,娟娟爸妈在客堂间里给两人打了地铺,让他们睡下。然后,娟娟爸妈走到门外,走到了月光如水的村道上,双双长叹:摊到麻烦事了!
他们明白,娟娟的回家,不是缘于一般的夫妻吵架。他们走到娟娟出嫁前的一名小姐妹家门口,敲门。他们耳热面赤,既希望门被立刻打开,又希望门不要立刻打开。他们觉得自己已没有脸面面对门里走出的人了,不论走出来的是女儿娟娟还是门的主人。
第二天一早,在健康奶牛场的一间铅皮顶小屋里,娟娟爸妈寻到了娟娟。那小屋是挤奶工阿秀的住处,因为要半夜挤奶,阿秀就常年住在这间小屋里。见到她爸妈,娟娟呆了呆,又别过脸去,好像只要别过脸,她爸妈就不会发现她了。她的手臂上套着袖套,一只手上还戴着一只乳胶手套。看来,她在帮阿秀挤奶了。娟娟妈说,回去。娟娟把脸转向了她妈,她的眼睛惺忪、红肿。她妈又说,好了,你已经帮了阿秀大半夜的忙,该回去了!娟娟说,我要夜夜帮阿秀挤奶,我要吃住在这里!娟娟爸妈抖动着嘴唇,说不出话来了。这时候,阿秀提着一双湿手走过来,她对娟娟爸妈说,娟娟也想在这里做,她不是帮我,老牛(奶牛场负责人龚德生被人称为老牛)都答应了给她工钱。显然,阿秀刚才已听见了娟娟妈与娟娟的对话。
娟娟爸妈的嘴唇抖得更厉害了,可还是说不出话来。
娟娟妈的双腿突然一弯,在娟娟面前跪了下来。娟娟的脸快速转开去。阿秀冲上前,要拉娟娟妈,娟娟妈的双臂一挥,居然把阿秀也带到了地上。阿秀迅速立起来,然后伸出手想去为娟娟挡住啥,可已来不及,娟娟爸的巴掌已落在了娟娟的脸上。
娟娟爸对捂着脸的娟娟说:
“我年轻时想跟着你妈分开,你妈都没有跪下来!你这个没良心的,生你出来难道就是要让你妈在你面前跪下来?”
娟娟身子一扭,突然往东面奔去,那里有一排茂盛的荆树,好像这些荆树能够保护她似的。她跑到荆树边后,蹲下身子。她身体两旁的荆树枝条果然开始“保护”她,竟然俯下来,合拢来,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包围圈。娟娟就蹲在这个小小的包围圈里,可这个包围圈并不严实,一阵风吹来,它就散了。这时,娟娟爸奔到了荆树边时,他把不再受包围圈“保护”的娟娟从地上拉了起来,然后几乎是拖着她往前走。娟娟满脸是泪,犟着身子,可脚步倒是在移动,当她走过她妈身边时,她妈终于立起来,跟着娟娟和她爸朝前走,朝前走的还有阿秀。
十多分钟后,娟娟在自家客堂里见到了亚军堂叔和表哥,他们坐在地铺上打牌。他们身边出现了一个敞着口子的包裹,娟娟爸妈看到了里面褪色了的汗衫背心,立刻明白面前的这两个人是准备在这里打“持久战”了。娟娟也明白了这一点,她张张嘴,似乎想说啥,最后只是无望地长吁一口气,然后,像是被猛地抽去筋骨,依着墙角瘫软下去——娟娟明白,她如果坚持下去,只能增添男女双方的麻烦和痛苦,或许给她以及她爸妈带来的麻烦和痛苦更多。她终于从墙角落里站起来,对横泾来的那两个男人说:
“好吧,我跟你们回转。”
五
按照横泾村的风俗,新娘子嫁过来后的第一个立春日过后,男方要在家里拉台子请吃“春茶”。而巧得很,回了娘家后的娟娟也在立春日前的前一天,被亚军堂叔和表哥请回来了。
那天一大早,亚军妈就打开双扇门,把一张“福缘善庆”图贴在了左门扇上。在这张图上,一位老人手拄系着香橼的木杖,背着一个拿磬的小囡,还有一个小囡则立在他一旁击磬。她在右门扇上又贴上一张“魁星点斗”图,魁星正在点“斗”,他的一只脚站立在鳌头上,另一只脚向后踢斗,手里的“神笔”点向被他踢起的“斗”。
在门上贴好图画,亚军妈就把熏青豆、酱瓜片、腌渍菜等小吃放进一只只小碗里,把小碗一一摆上桌面,然后静等村上有空的人来喝茶。
半空中,有一些柳絮在飘动。空气中弥漫着植物芽孢的清新气息,而春阳则散发出着一股温热。
亚军妈不时走到场角上去眺望。先是零星地来了几位老人,接近中午时分,村里的正劳力们吃茶来了,亚军家的客堂里立刻变得热气腾腾,热闹的话语声又与热气交融在一起,客堂里变热了。很快,有人脱得身上只剩背心了。后来,大部分的人坐到了屋外。
在屋外,有人指着右门扇上那张“魁星点斗”图,说亚军的儿子还在娘肚子里呢,怎么开始巴望他考试得头名了?——像这样拿请吃茶的东家说事,甚至开些不重不轻的玩笑,都是正常的。大家甚至可以开新娘子的粗俗玩笑,不要说开一些不咸不淡、无伤大雅的玩笑了。可大家都已经晓得,亚军是那样的一个人:即便你想把玩笑开大也没有用,你想开他的玩笑,他自己先开自己的玩笑了,而且比你开得还大,这玩笑就没法往下开了。
不过亚军今天在哪里?刚才说话的那个人转脸四顾,想寻找亚军的踪影,似乎想让亚军接他的话头,让亚军自己把这个话头说大。可直到现在,无论是在场地上,还是在客堂里,他都没有见到亚军,他只见到了亚军爸妈和他的过门两个多月的新娘子娟娟。
有人问正在走上前来的亚军妈:“亚军呢?”
亚军妈说:“他大嬷嬷生病,他爸让他探望去了。”
那人说:“是他爸把他支开的吧?”
那人真是说对了,亚军嬷嬷的毛病是老毛病呢,最近也没听说发作,他爸却让他去探视。他爸把装着鸡蛋的篮头递给他时说,去,到嬷嬷家,好久没去,她的老腰病又要犯了吧?去嬷嬷家所在的村庄,亚军要走十多里路,一个来回,起码要小半天。亚军爸在他家请吃茶的这天支走他的意图很明显。既然为了支走他,都以亚军的嬷嬷为借口了,亚军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何况,亚军晓得茶客们在嚼舌头时,对吃茶的东家一般不会嚼重话,甚至在嚼舌头时会避开请吃茶的东家。谁会吃了东家的茶,又把开东家的玩笑开大了的?大家在开东家玩笑时都有个度,超过这个度,你是真正在给主人家捣蛋了,在散他们家喜气、触他们家霉头了。所以,在拿东家说事、开东家玩笑时,一方面东家会保持适当的大度和宽容,这叫“聚喜”;另一方面,开东家玩笑的人也会掌握一个度,这叫“不破喜”。总之,拿东家说事、开东家玩笑,是为了热闹,为了让聚集在主人家的喜气更旺、更足。
于是,在亚军家的屋场上,又有人拿那张图开玩笑了,说亚军妈太心急,孙子还没有从娘肚皮里钻出来,就巴望着他独占鳌头。其实这话与先头那人说的话是同一层意思。可尽管是同一层意思,在不同时间段说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今天,这两人的话就是这样,第一个人的话引起了一片开心、喜气的笑声;第二个人的话在还没有引出笑声前,第三个人就轻声接嘴,快生了,你们看。
这时,娟娟正巧走上来了。她端着一只篾箩,篾箩里放着瓜子、冬枣、柿饼等小吃。她这次不该来,一来,就让人看到她变粗变大了的腰身。本来,这腰身也不一定能引起别人的多想,别人会以为她的腰身本来就是那样的。关键是刚才第三个说话的人常去娟娟娘家走亲眷。他在娟娟添罢小吃离开桌边后,鬼头鬼脑地一笑,又小声嘀咕,上次,我见她的腰身还细得像杨柳,好日后的这两个月来,难道她吃了发糕粉?听了他的话后,大家一阵沉默。有人低头喝茶,碗沿边发出了夸张的“哧溜”声,这响声打破了沉默,有人低声附和,是吃了发糕粉。随即,又有人提高了一点声音说,是吃了发糕粉。这个人仰脸看着右门扇上的那张图画,突然叹口气,立了起来,说差不多要上工了,走吧。随即,大家都跟着立起来。
这样看来,茶客们确实遵循了横泾村的一个风俗,尽量不给东家“破喜”,眼见着要给东家“破喜”了,他们选择了离开。
六
亚军从他嬷嬷家回来了。这时候,时间差不多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亚军的脚步却没有往他家的客堂里迈,他走到了他家正屋和猪圈之间的一条小道上,接着,他在六七步远的地方看到了娟娟。
娟娟在小屋的东墙边跳。起初的一刹那,亚军以为娟娟是想去够小屋顶上的啥东西。可娟娟的手不去够,不去碰小屋的屋檐,就举着,跳一次,她的手就举一下;再跳一次,再举一下。亚军在离她六七远的地方立停了。娟娟也看见了他,停止了跳动,也立停不动了。亚军想走上前去,可觉得脚头很重,他转过身来,重新来到了他家的屋场上。
正想走进客堂时,亚军感到眼门前一亮。他抬头,看到铅色的天空中闪起一道细长的亮光。他一惊。横泾人把晴天里发生的闪电称为“天笑”。都说“天笑”是不好的兆头。他还听说,即使在同一片天上发出“天笑”,有人会看到,有人不会看到。看到的人要当心可能会来到眼门前的灾祸,看不到的人眼门前不会有灾祸。亚军的心抽紧了,他又想到了娟娟,连忙返身,走回到了正屋和猪圈之间的那条小道上,重新往北走了几步,走到了娟娟身边。
娟娟又在跳了,举着手臂往上跳,像要去够小屋顶上的啥东西。她也看到了亚军。这次,她没有停下来,继续往上跳,一下,又一下。
亚军似乎已经看到降临到自己眼门前的灾祸了,他要把灾祸的根源扼杀掉——一旦明白自己能做啥了,他就又快速上前一步,他的身体几乎要贴上娟娟的身体了。
娟娟还在跳。亚军一下子拉住了她举着的臂膀。待她站稳,他的手扬起,然后落下。
一声脆响在娟娟的面孔上响起。娟娟脸色惨白,她发出粗重的喘气,高突的胸脯一起一伏。她还要跳,亚军再次拉住她的臂膀,低吼一声:
“再跳,敲断你的腿!”
然后,他喃喃耳语,是我的。
此刻,在嬷嬷家和表哥喝的那半汤盏大曲好像在他身上显效了,他喷出一口酒气,醉了一般继续喃喃而语,是我的,是我与你在厢房里的黄道砖上……
他想起来了自己与同村的阿静的一次经历,那是他成家前的仅有一次经历,那次,他去了阿静家的厢房里。
娟娟也像听到酒话一样,面孔上露出茫然神色。不过,有一点她是明白了,那就是亚军不让她跳了。其实她已经跳了好多次,就差要拿什么东西往自己肚皮上撞了,只是还下不了手。或许,就在她想用啥东西撞自己肚皮时,亚军阻止了她的企图。后来,当她的孩子长大到五六岁时,娟娟有一次摸着她的头顶心,说你这杀胚,命大呢,我跳那么多次,你都没落下。在我要发狠、想用啥东西撞自己肚皮前,你爸阻止了我,所以你命大呢,所以你爸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七
发亮家的“分家茶”刚请好,他又要请吃“监生茶”了,他的老婆生了——在横泾,生孩子的人家请的茶叫“监生茶”。
亚军向发亮家的屋场走去,和上次一样,远远的,他就闻到了一股茶水的味道。这味道中仍掺着熏青豆、酱瓜、咸菜等小吃的味道。他的听觉还是那么灵敏,还没有走近发亮家的屋场,他就听到了茶客们的声音,听到了声音中有关他家的事。
一个声音说,她不想要她肚子里的孩子。
另一个声音说,那说明她不想离开这里了。
亚军也开口了,说,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既然你们那么喜欢讲,那我就告诉你们一些你们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们,即使她不要肚子里的孩子了,我也已经有一个儿子了,现在正由隔壁村的阿静带着……
亚军边说边朝前走。他不再和上次一样,走得很犹豫。他怎么会犹豫呢?他都参与发亮家茶场上的聊天了,尽管他还没有走到那里。
他走到发亮家场角上的一刹那,看到了一个让他惊讶的场景:茶客们纷纷从凳上站起来,还抬头望天。
亚军也抬头望天,他看到太阳已经钻进了一朵铅灰色的云里,天空显得灰蒙蒙的。除了一片灰色,亚军在天空中没有看到什么。可茶客们像是在一片灰色里看到了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脸上露出了异样的神色,他们开始走动,还都把目光集中到了亚军的身上。
他们把天上看到的东西跟亚军联系了起来。当他们纷纷走过亚军身边时,一个人嘀咕了一声,亚军就知道他们在天上看到什么了。而今天,亚军自己却没有在天空中看到什么。亚军的心跳快了,他突然意识到,关于他家的事情,以后的茶场上可能不再有人提及了,他也用不着像小时候那样,跑到茶场上去“作践”自己了。
亚军又抬头。太阳突然从云朵中钻了出来,一束灿烂的阳光投射到了亚军的身上,也给让他身上产生了一股暖意。他低头,想跟以前一样,轻轻松松地加入到茶客的队伍里,可发亮家的屋场上却已空空如也,没有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