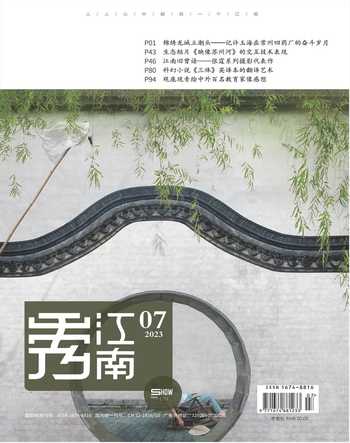《促织》《变形记》:矛盾与错位的交织
王星星



中国文坛自古以来就有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写法,以微小的事物含蓄而内敛地或讽谏社会,或寄寓理想。清代蒲松龄将这种写法运用到小说中,以神仙鬼怪的写法反映黑暗的社会现实、冷漠的人际关系。在十九世纪的西方,一位著名作家—卡夫卡将荒诞离奇的想象与故事情节融入创作中。本是毫不相关的两人却因其创作风格的一丝相似而被联系在了一起。教育部编版高中语文将《促织》《变形记》放在了同一个课题之下,于差异之中又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在写作手法上,英国德语作家、评论家埃利亚斯·卡奈蒂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最令人吃惊的是卡夫卡如此驾轻就熟地掌握的另一种手法:变化成小动物。这种手法通常只有中国人堪与媲美。”又例如在行文逻辑方面,两部小说在荒诞的背后都充满了许多的矛盾与错位。
矛盾视域下的“人虫错位”
《促织》
《促织》写的是在外力的压迫下一家人沦为悲剧角色的故事,《促织》结局看似皆大欢喜,但在一片欢乐中悲剧意蕴却显得更加浓郁,这也是本文处处充满了矛盾的缘故。
《促织》一开始便介绍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尚促织之戏,于是便“歲征民间”,终致庶民倾家荡产。随着背景的介绍,矛盾也由此浮现,为何“此物故非西产”,为何“责常供”?促织并非陕西本地所产,数量极其有限,而宫廷官员们却责其常供,此为一矛盾。宫廷出于对促织的喜爱,“责常供”,地方官员欣然接受,但为何游侠儿“居为奇货”?一头小小的促织,何以“倾数家之产”?此皆为矛盾。驼背巫既然能神机妙算,指出促织的所在地,那为何不提前警示成名的促织将会遭遇何种灾难呢?此又为一矛盾。成名自小读书,未能因读书而飞黄腾达,反而因为一头促织险些丧命,却又因促织而享受莫大的荣华富贵。寒窗苦读几十年未能做到的事,却因一头小小促织在须臾之间便改换了门楣,此又为一矛盾……细读《促织》,不难发现其中处处有矛盾,究其因果,是蒲松龄欲在《促织》的文言内外表达自己的心之所想。
《变形记》
《变形记》写的是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在早晨一觉醒来突然变成了甲虫,面对此种荒诞的场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想尽办法让自己早点去工作赚钱。身体的异化和格里高尔思维的“人化”形成了一种错位,从外形来看,他已经不是人了,但人生的苦恼还紧紧地禁锢住他的思维。同样值得深究的是《变形记》一文中也处处充满了矛盾……
“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虫。”面对这一情景,格里高尔只是稍稍抬头,并没有惊讶于自己的变化,而是想着自己要是能多睡一会儿就好了,身体上的“变异”似乎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面对格里高尔的淡定,其他人的表现如何呢?协理被吓得落荒而逃,而母亲则“突然跳了起来”“魂不守舍地一屁股坐了下去”“父亲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似的发出啾啾声,毫不留情地逼着格里高尔回房间去”。别人的恐慌害怕与格里高尔的淡定或者说麻木形成了矛盾。格里高尔变成虫时,一开始家人是难以置信的,认为他是因为生病才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家人都有了独立赚钱的能力,不再关心格里高尔是否“病好”,反而将他视为累赘,家人前后的态度变化为一矛盾,而文章最为矛盾的地方莫过于变成了虫子的格里高尔一方面有着虫的习性,喜欢爬墙、喜欢吃腐烂的食物,另一方面有着人的思维,希望去上班,虽然自己非常讨厌那份工作,但为了早日还清父亲欠下的债款、为了能够送妹妹去音乐学院上学、为了家人早日过上轻松的生活……他依然选择早上四点起床赶火车去做那令人讨厌的工作,即使在他变成虫之后也是如此想的。虫的习性与人的思想相悖,此为一矛盾。
“人虫错位”的原因探析
《促织》一文与吕毖《明朝小史》卷六“宣德纪”中的一段记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亦自经焉。”一头小小的促织竟“价贵至数十金”,导致两条人命死亡,这与《促织》中成名之子的死亡极其相似。这说明,一切罪恶的源头直指社会,从《促织》细节描写中便可看出。
首先,社会风气是“错位”的。宣德年间,从宫中到民间自上而下掀起了一股娱乐之风—斗促织,可谓祸起宫廷。于是,像成名一样的读书人、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被迫踏上了捕虫之路。皇帝本是造福百姓的最高统治者,却因“娱乐”促织成了间接压迫人民的享乐者;华阴令、里胥、抚军本是造福百姓的官吏,却因为想要上位成了压迫百姓的压迫者、媚上者;成名作为从小读书的知识分子,却因为上级的压迫被迫成为捕虫者、“可怜虫”,整个社会中,人们在其位却不谋其职,流露着一股玩物丧志、“错位”的社会风气。其次,社会制度是“错位”的。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只因皇帝一时的享乐,官员就媚上欺下,向民间征收促织,把难题丢给百姓,从而使百姓苦不堪言,可谓一人喜悦,祸及天下。
卡夫卡生活于物质主义盛行、人情关系淡薄的时代。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们不仅不能享受幸福生活,反而连独立的自我都被社会的荒诞、人际关系的冷漠慢慢侵蚀。为了家人,格里高尔拼命地工作,他身上的个体性被不断地压抑、侵蚀,直至被社会同化变形。“格里高尔变形甲虫”悲剧的恐怖性在于:格里高尔并不是突然骤变为甲虫,而是他在内在生命意志层面上一直都是甲虫,但他自己浑然不觉。“格里高尔试图设想,类似他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否有一天也会发生在这位协理身上。说实在话,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一旦失去了谋生的能力、谋生的手段、谋生的资本,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他的处境就是格里高尔的结局。类似格里高尔的人并不止他一个,或许人们早已异化为“虫”却不自知,而格里高尔的遭遇,不过是在那个物质极其丰裕、人情却淡薄如纱的时代里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扭曲”的人际关系
《促织》和《变形记》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形。《促织》一文中,一国之君未能勤政爱民,反而一心在享乐上,使百姓惨遭苦难;当地县令未能服务于民,反而想着谄媚上官,这是造成百姓民不聊生的直接因素;“市中游侠儿”不理解百姓的难处,却反将促织价格抬高,这是人性的冷漠;成名妻子看到儿子将蟋蟀弄死以后,在儿子被吓得面色灰白的情况下,依旧没有给予安慰,反而指责儿子。成名归来听闻后“如被冰雪”“怒索儿”,看到儿子投井后方“化怒为悲”……在促织的衬托下、在荒诞的社会背景下,一切人际关系都失去了正确的指引,变得单薄如冰。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于老板而言,他是赚钱的工具;于家人而言,他是还债的工具,每个人都从他身上榨取价值,唯独他自己的价值却迟迟未能实现。当他变成虫不能去上班时,协理只因一个小小员工的迟到就上门问罪,在家人的解释下,反而觉得生病哪有工作重要,否定了格里高尔之前的一切努力。格里高尔变成虫以后,尽管母亲会因为他的遭遇而痛哭流涕,但在看到他的面貌时依旧被吓得晕过去;父亲则从未给予他好脸色,驱赶他,甚至用苹果砸他;妹妹刚开始表现出来的同情最后慢慢消失殆尽,变成了憎恶。慢慢地,他从一家人的生活支柱变成了全家的累赘,当家人决定抛弃他时,他也彻底沦为了物质时代的产物,他自我放弃了生命,而全家人却如释重负……
卡夫卡曾说:“人们互相间都有绳索连接着,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低一段,那就够糟;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全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必须和其他人捆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靠经济来联系,人一旦失去了获得金钱的能力,不被家人与单位、社会认可,那么人就无异于虫,而这种虫的雏形早已存在于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
意象“虫”的选择
《促织》中意象“虫”的选择
蒲松龄在《促织》中之所以选促织反映社会现实,一是蒲松龄受到前人写书的影响。分别为吕毖的《明朝小史》记载以及冯梦龙《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中济公火化促织的故事,经过艺术加工铸就《促织》。
二是早在以前人们就有以斗促织为乐的先例。唐朝,人们开始以“斗促织”取乐,京都长安的达官显贵、富豪巨贾,不惜重金求上品促织,养在象牙玛瑙盒中,饲以黄粟泥,一场赌注中,竟达白银万两,如此奢靡之风,令人瞠目结舌。到南宋,宰相贾似道斗促织成癖,在敌人大军入侵时,依旧沉迷于斗促织取乐,忽视朝中事,不久,宋室沦亡。明代,斗促织的娱乐风气达到了高峰,明宣宗酷爱此道,于是促织成为皇宫贡品,并派有官员专门饲养促织。官吏的升降,也以所进促织的优劣为准绳,庸官当道,民怨沸腾。
三是蒲松龄借促织反映社会的不公。一方面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著名学者胡渐逵指出:《促织》深藏的寓意即辛辣地讽刺科举取士,“操童子业,久不售”的成名,却因贡一奇异促织“俾入邑庠”而一举成名,这对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它通过成名贡一促织而入邑庠的故事表明:科举取士中,有的士子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猎取功名的。另一方面是对社会风气的讽刺。虫本来是人的玩物,却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这是统治者的失职,亦是社会风气的荒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俊提到,《聊斋志异》中很有思想价值的部分是暴露社會黑暗现实的作品,当时社会政治腐败、官贪吏虐、豪强横行、生灵涂炭,都在《聊斋志异》中有所反映,如《促织》通过成名一家为捉一头蟋蟀“以塞官责”而经历的种种离合悲欢,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昏庸。
《变形记》中意象“虫”的选择
首先是家庭因素的影响。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一直极为紧张,他曾在长信《致父亲》中提到他的父亲对他的朋友并不友好,甚至于“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我已忘了是何种方式)把他同虫相比”。当父亲把朋友比作虫时,是对朋友的一种侮辱,也是对他心灵的冲击,如同把他也当作了虫一般看待,这为他选择意象“甲虫”埋下铺垫。父亲对于他的逼迫,使卡夫卡对这样的父子关系是这样评价的:“联想起一条虫,尾部被—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他也曾将与父亲之间的斗争比作甲虫的斗争,这些与虫相关的体验一直积压在卡夫卡心中,或许连他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如同虫一般。
其次是自我的写实。甲虫在德文中被译为害虫、臭虫、蟑螂、肮脏的动物,如果不是变成一种令人无法直视之物,就不会吓到协理与房客,其家人的异化也不足以暴露出来。已有3.5亿多年的甲虫是生物进化链上一种古老的物种,它数量众多、个体伤害力小,在人类眼中,甲虫是无足轻重、可任意欺凌剿杀的低等动物。这不正是格里高尔的真实写照吗?身为小职员的他地位低下,在公司受尽了压榨与欺辱,当他不再具备赚钱能力时,家人也彻底否认了他的存在价值,他就如同这甲虫一样被人厌恶、抛弃,而工作与家人的压力就像甲虫巨大而厚重的壳一样,紧紧地压着他。卡夫卡设置了一个极端化的情境,以极度夸张的手法表现精神困境和人的异化,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场现代人的噩梦。
结语
人变成虫是荒诞的,但这荒诞并不是胡编乱造的,细读《促织》《变形记》我们不难发现一切的荒诞在社会与人际关系中都是有据可循的,而这种荒诞不过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正常”的现象。两篇小说都不约而同地以一种离奇、荒诞的手法表现了小人物在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