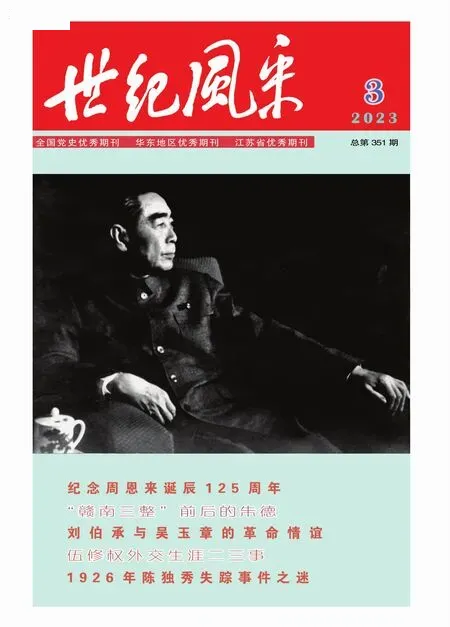张太雷首登共产国际舞台所涉几则史实考辨
黄爱军
张太雷是第一位登上共产国际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人,此前张太雷研究中涉及他首登共产国际舞台若干重要问题,笔者认为与史实有一定出入,在此对所涉若干史实进行考辨。
一、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的翻译是杨明斋,不是张太雷
学术界较流行的说法,张太雷是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大钊等会面时的英文翻译,但此说法与史实有较大出入。其一,此说可能最初出自1949 年李达所写《自传》。但李达的回忆属于孤证,可信度不高。其二,《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就本部组织与活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指出,1920 年4 月维经斯基一行来华,开启了俄共(布)在远东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既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对来华后可能遇到的问题或困难,应有较缜密的安排,包括配置专职翻译杨明斋。再说维经斯基曾在美国生活过,英语说得很好,即使俄语是其母语,专门的英文翻译似没有必要。即便维经斯基的确有找临时英文翻译的需要,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中,难道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英文翻译?如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成员刘仁静,早年在武昌博文教会学校学习的时候,就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基础。他1918 年考入北京大学,初入物理系,后改入哲学系,再后转入英语系,可以熟练阅读英文版马克思著作。让当时还是学生的张太雷专门从天津赶往北京担任英文翻译,岂不是舍近求远?其三,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张太雷按照北洋大学返校的限令,1920 年4 月8 日前已返回北洋大学,并参加了随后至6 月初的毕业考试,且取得良好成绩(大部分成绩都是甲等)。在这期间,张太雷不太可能有时间赴北京担任维经斯基的英文翻译。
二、推荐张太雷赴俄的不太可能是李大钊,应是鲍立威

张太雷(1898-1927)
学术界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张太雷1921 年初赴俄,是受李大钊派遣或推荐。此说法不仅缺少直接史料作支撑,且经不起仔细推敲。其一,当时不少进步青年向往苏俄,希望赴俄留学或考察。如毛泽东在1920 年初,就已有了组织进步青年赴俄留学的打算,并就此事与李大钊等进行商量,稍后即发起组织留俄勤工俭学活动。但并未听闻李大钊在介绍湖南进步青年赴俄留学方面有过具体的安排,而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湖南进步青年,主要是通过毛泽东等创办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先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而后实现赴俄留学的。这说明,李大钊虽然与苏俄有关人士接触较多,但并不具有这方面的独特优势或渠道。其二,李大钊派遣或推荐张太雷赴俄,应属组织行为,不太可能不与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特别是上海发起组进行情况通报。当时中共虽处于草创阶段,但就重要事项进行协商与通报,应是当时的制度或规章。如陈独秀1920 年底南下广州前,就征求了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意见。但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包括北京早期组织重要成员张国焘,均未听闻过张太雷赴远东书记处任职之事,他们是从出席中共一大的尼克尔斯基处听说了成立远东书记处的消息,之前他们“不知道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存在”。其三,持此论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李大钊与哈尔滨东华学校创办人邓洁民是同乡好友,李大钊介绍邓洁民帮助张太雷解决过境诸多问题。这条理由基本不能成立,因为当年东华学校具体负责经办出国护照的张照德,是张太雷的好朋友,这在张太雷家书中有明确记载。
1921 年初维经斯基回国、张太雷赴俄,均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立及其人事安排有关。远东书记处成立于1921 年2 月底3 月初,恰在此时,维经斯基和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并先后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秘书和中国支部书记。显然,维经斯基是奉调回国,并负有物色中国支部中方书记合适人选的任务。维经斯基由广州经北京回国,在北京作停留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物色中国支部中方书记合适人选。维经斯基到北京后,首选的与之协商、推荐中国支部中方书记人选的人,应该是鲍立威,而不是李大钊。
鲍立威是俄共(布)党员,是维经斯基来华后开展建党工作最信任、最倚重的人物之一,是京津地区开展建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这突出体现在:首先,维经斯基来华后,正是经由鲍立威的介绍,才实现了与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会面与座谈。其次,维经斯基来华开展建党工作所依靠对象,首先是俄共(布)在华党员,而不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7 月5 日到7 日在北京举行的俄共(布)在华党员第一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就“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问题交换了看法。涉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样重要事项,不是先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交换看法,由此可见一斑。再次,维经斯基来华开展建党工作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两地的革命委员会,维经斯基负责上海革命委员会,而鲍立威和斯托杨诺维奇则是北京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维经斯基来华后,除了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联系外,还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者进行了联系。1920年6 月9 日维经斯基在一封信中说:“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同中国革命运动所有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为协调和集中工作,正开始筹备一次华北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会议。”除了区声白、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外,张东荪、江亢虎、姚作宾、黄介民等,均是维经斯基联系对象。维经斯基的联系对象,还包括孙中山、戴季陶、陈炯明、吴佩孚等人。也就是说,在维经斯基心目中,李大钊远不是今天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分量。
维经斯基在北京停留期间,找鲍立威协商、推荐中国支部中方书记人选,鲍立威推荐张太雷当在情理之中。其一,早在1918年下半年,鲍立威就从《华北明星报》找到张太雷任其英文翻译。以张太雷良好的英语及语言表达沟通能力,想必很快就与鲍立威建立起了较密切的关系。其二,鲍立威组织成立北京革命委员会时,张太雷是其最重要的联系对象。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张太雷是鲍立威领导的北京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其三,1920 年6 月张太雷北洋大学毕业后,即走上了职业革命家道路,实际是投身到鲍立威在京津开展的革命活动中。张太雷毕业的时间是1920 年6 月,北京党团组织成立的时间是1920 年10 月和11 月,从这个时间节点来分析,如果张太雷不曾南下参加上海的建党、建团活动,其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就与建党建团无关,只能与鲍立威在京津开展的革命活动组织发生联系。
另外,鲍立威具有推荐革命青年赴俄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有些优势和条件甚至具有唯一性,如对入俄人员“给以绸制长方小块的秘密入境证件”。张太雷赴俄前,鲍立威就曾推荐或介绍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凌钺等多人入俄。张太雷赴俄期间,鲍立威“也在帮助脱离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赴俄”。
更为重要的是,原觉悟社成员谌小岑的有关回忆提供了鲍立威推荐或介绍张太雷赴俄方面的线索,也是唯一一条与张太雷赴俄有关的线索。谌小岑回忆说:“在《来报》被查封后的不多几天,张太雷来找我,他要出国到苏联去……过了两天,我去看了一次鲍立威,他告诉我说张太雷已经动身走了。”
三、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是2 人,不是3 人
有些文章认为,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3 人,这与史实不符。其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统计表》记载,中国代表共2 人,其中共产党、青年团代表各1 人。其二,1921 年6 月《俞秀松、张太雷给季诺维也夫的信》,署名“中国代表团代表秀松、张太雷”。其三,1921 年7 月20 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明斋举行的联席会议,主要是听取舒米亚茨基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代表团工作情况的通报。舒米亚茨基之所以向杨明斋作工作情况的通报,因为杨明斋是中共早期组织选派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正式代表,这本身亦说明杨明斋未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张太雷(站者左五)、瞿秋白(站者左四)、俞秀松(坐者右四)、陈为人(坐者左四)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会议期间,与各国部分代表合影
关于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人数是2 人,学术界对此无异议。但对2 人分别是谁则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是张太雷和杨明斋,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张太雷和俞秀松。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俞秀松2 人。
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3 人中,杨明斋是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正式代表,但因错过了开会时间未能参会;俞秀松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但他是上海党组织或团组织推荐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俞秀松的委任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也就是说,俞秀松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而非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张太雷是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的共产国际三大,但他并非是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代表,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委任状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签发的。
不少学者认为,张太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资格,得到了中共早期组织的批准和委任,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代表。此说的依据,就是在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明斋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杨明斋说:“收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来的电报,并得知派遣代表团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和批准张同志的委任状后,他们非常高兴。尽管张同志在他们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状。”而笔者认为,杨明斋所说的“批准了他的委任状”,不太可能是批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委任状,而应是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的委任状。理由是:第一,远东书记处给张太雷中国支部书记的任命书中有“暂任”二字,即具有临时性。张太雷任中国支部书记一职,需要得到中国国内组织的认定。第二,如果远东书记处所发电报中有批准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方面的内容,这与报告建议中共早期组织派遣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方面的内容相矛盾。按照后来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团由张太雷、俞秀松2 人组成的情况来推断,中国代表团的限定人数当为2 人。如果张太雷已占用了1 代表名额,就应建议中共早期组织再派代表1 人与张太雷组成代表团。而实际情况是,中共早期组织收到电报后“决定派遣两同志前去代表大会”,这“两同志”显然不包括张太雷。第三,如果远东书记处所发电报中有批准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方面的内容,即意味着远东书记处给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委任状在前,给中共早期组织发出电报在其后,这显然有悖正常的办事程序或规则。正常的办事程序或规则,应是给中共早期组织发出电报在前,在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代表迟迟未到的情况下,远东书记处相机行事,任命张太雷为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后。第四,如果张太雷的委任状在前,随后又要求中共早期组织批准对张太雷的委任状,这不仅存在越俎代庖的问题,更意味着远东书记处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中共早期组织,这种凌驾于中共早期组织之上的做法,不太可能被具有强烈独立自主意识的中共创建者们所接受。更何况当时中共早期组织尚未确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谈不上与远东书记处存在隶属关系,远东书记处没有相机处理中共早期组织有关问题的权力。
四、同伪“共产党”代表资格之争,舒米亚茨基的作用有待重新认识
有些文章认为,在中国代表团与姚作宾、江亢虎等所代表的伪“共产党”之间发生的“正统”之争,即争取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唯一承认的中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关键时刻,共产国际派驻远东书记处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给了中国共产党最大支持。考之史实,如果舒米亚茨基真心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支持,此种“正统”之争则完全可以避免发生。首先,综观舒米亚茨基向杨明斋通报有关情况的内容,主旨意在说明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舒米亚茨基这里除了具有邀功的因素外,其中仍掺杂有贬低中共早期组织方面的内容,如称“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这显然不符合中共早期组织的实际情形。如果中共早期组织不是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现在已有六个小组,计五十三名成员”从何而来?说自己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不等于实际真的大力支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其次,舒米亚茨基作为远东书记处全权代表,实际亦是指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全权代表,在对待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这件事上,应具有较大的话语权。舒米亚茨基如果要阻止江亢虎、姚作宾等伪“共产党”代表团参会,大会秘书处就不太可能给他们核发代表证。显然,舒米亚茨基并没有这样做。再次,当张太雷得知江亢虎已经抵莫斯科后,即向舒米亚茨基提出不要发给他代表资格证书。舒米亚茨基表示同意。但在大会开幕时,江亢虎却取得代表证并与会。作为远东书记处负责人的舒米亚茨基,恰恰又是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
张太雷研究,是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相比较其他内容而言,张太雷研究的资料更加缺乏,几乎没有一手资料可言。过去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张太雷研究取得的成果,大多建立在并不可靠的回忆材料基础上,有的甚至不加甄别直接拿来当一手资料加以引用。如李达关于张太雷担任维经斯基英文翻译回忆,就曾被学术界经常不断地直接加以引用,使之在学术界广为流传。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与发掘,一手资料缺乏的问题有了很大的改观,运用新史料取得的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运用新史料重新审视过去曾广为流传的某些观点,是深化中共创建史、张太雷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