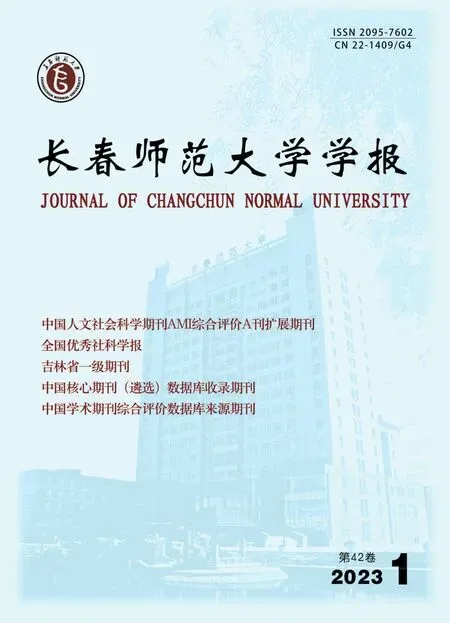末世公子非纨绔,礼教大家真贵族
——论贾琏的贵族修养与人生悲剧
霍彦珊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贾琏是《红楼梦》中毋庸置疑的第二惹人瞩目的贵族公子。相比于宝玉整日混迹胭脂姊妹丛无心科举仕途,贾琏更加实际,也更加真实。在荣国府两位当家人——贾政“不擅俗物”、贾赦“整日只知道和小老婆鬼混”的情况下,面对一个大家族运转必不可少的关系维系,青年时代的贾琏承担了更多责任。这些责任让他更早地见识了权力世界的恶与俗,所以自己不免也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气,但他终究还是良善谦和的,没有如凤姐、贾雨村一类彻底被权力侵蚀而恶魔化。贾琏身上体现的大家公子气度与贵族学识修养隐喻他在那个注定要没落的世家望族找不到保持自己本心的一席之地。如果说贾宝玉是贾氏家族与封建时代的叛逆者,贾琏则是一个顺从者。他染上那个时代贵族男人都可能存在的弊病,如好色、懦弱,却也动真情、有原则。他情多而不滥,懂权术却不害人命,从始至终不曾脱离自己的家族身份,不曾背弃做一个孝子贤孙的使命。他为族人奔波,将自己的才华隐没于时代的染缸。小说结局处,宝玉出走可能找到了自己身份的归宿与解脱,贾琏则是《红楼梦》中彻头彻尾的陪葬者。他的陪葬不同于贾政“卫道士”与“遗老”身份的陪葬,而是一番挣扎后无法脱离身份的葬送。少年时代,他是一个有见识、有才学、有性情的年轻人。他曾清醒地预见家族的走向,感知到一种无可挽回的颓势,却仍一步步被世俗剥蚀而至陨落。这决定了贾琏身上还有一种悲剧的精神与气质,这种气质与他举止言谈间的贵族气息融合,使得他自身成为没落贵族的一曲悲凉挽歌。
一、清润谦和孝子孙,亦狂亦侠亦温文——贾琏的贵族修养
(一)彬彬公子世无双,翩翩如玉行有方——贾琏的贵族品性
贾琏好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食色性也,他“好色不淫”,“淫而不乱”,对性的追求也间接地体现着他贵族的身份、品味与教养。因为贾母一句“腥的臭的,都拉到你屋里去”[1]353,加之贾琏沾染的女人多出身下层,他便被冠以“恶俗”之名,但他的“贵”也恰体现于此处。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一回,凤姐以贾琏名义修书一封,就可让一方守备节度使俯首听命,举手之间害死一对男女。可见贾琏若有欺男霸女之想,绝非没有善后的能力。但对于女子,贾琏从未有强迫之举。贾瑞敢觊觎凤姐,贾珍与儿媳天香楼艳事,显示出两府的男女之事并非森严清明。纵然贾琏与多名女子有过床笫之欢,但与他有染的女子莫不本就风流。林如海病重,贾母在众多子侄辈中唯独挑选贾琏护送黛玉回扬州,书中并没有提过贾琏有失兄长身份的举止。贾琏在见到香菱后可怜她做了薛蟠的房里人,与二姐定下终身之后便为三姐的名声、未来做打算。可见,贾琏虽然好色,却有一定的底线,即不抢占、不淫乱。
在《红楼梦》语境下,好色不能算是男人极大的缺点。贾政尚有赵姨娘、周姨娘,贾宝玉也与袭人多试云雨,更不消说贾赦房中丫头无数。贾琏在凤姐的严管之下,连平儿也不得沾身。这种“出轨”更多是一种生理本能的释放,还未上升到淫秽恶俗的层次。《红楼梦》很容易给读者一个错觉,即贾琏偷娶尤二姐是对凤姐莫大的背叛。然而贾琏贵为荣国府长房长孙,凤姐又无子嗣,贾琏想要纳一房妾并非不合情理。所以我们不能据此苛责贾琏在爱情方面用心不专。
贾琏“风流而不下流”。作为书中的另一个淫俗公子,薛蟠是真正的混世魔王。贾琏之欲与薛蟠之淫不同:薛蟠为抢占香菱而不惜惹出人命官司,事后受到夏金桂几句挑唆就拿起门闩要将其打死;贾琏为二姐请医问药,二姐死后痛不欲生,赊买上等棺木,破门送葬。薛蟠之淫为得女子容貌,是为无情;贾琏之欲为求心灵慰藉,是为有情。无情谓之肉欲,有情则为风流。
贾琏对与自己有过云雨之事的女人,虽不能回馈以名分,却也尽己所能表达一定的心意。与多姑娘情断,他私藏一缕头发;鲍二家的吊死,他拿二百两银子去安抚;尤二姐去世,他搂尸大哭不止。这种心意无法改变这几段感情的灰色色彩,但客观来讲,这些女子的悲剧更多是被时代左右的。贾琏处于视人命官司如微末的贾府,作为皇亲国戚的国舅老爷,却并没有轻贱这些出身低下的女子,已经是一种莫大的难得。这种感情虽然不值得标榜,却与宝玉祭奠晴雯有所相通。贾琏在看待女子的时候虽怀着一定的肉欲淫念,但也不乏悲悯和欣赏。前种情绪让他走入淫俗的圈子,后者却维持着他的贵族修养与体面,让他在床笫之外仍然不失为一个体面的兄长和君子。
(二)勤勉躬亲侍父兄,浊世难改君子行——贾琏的操守与原则
在国公府诗书礼乐的门风熏陶下,贾琏养成了谦谦公子的品格。而在贾府这个世袭大族延续下来的礼教法度浸染之中,贾琏的君子操守与原则进一步得到强化。对父亲,贾琏孝而不迂。书中第一百零六回,贾赦、贾珍等获罪收押在狱,贾政无意打点。贾琏便将田地典当,给父兄做监中使费。大厦倾颓,更易显露人心冷漠。贾赦不算爱子,可是贾琏依旧惦念父亲,为其奔走以尽孝道。
贾琏虽然在男女关系上常为人诟病,可是在涉及钱财、人命的考验时能坚守自己的原则。贾赦因听说石呆子有几把古扇,便命贾琏去“弄”。贾琏作为一个结交六部的贵族公子,绝非没有为父亲“弄”来几把扇子的能力。不过在贾琏的心目中,“弄”就是买,而买不同于强买。面对石呆子“饿死冻死也不卖,要扇子先要我的命”[2]390的态度,贾琏没有仗势欺人,只好作罢。贾雨村设毒计为贾赦夺来扇子,贾琏甚为不齿,扬言:“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家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1]390。可见贾琏不仅自己能够坚守底线,对别人做这种事还是极为蔑视和愤恨的。
贾琏在凤姐强势的对比下往往有懦弱之名,而此时的贾雨村正如日中天,深受贾赦喜爱。从贾琏平日对父亲、兄长恭敬谨慎的态度来看,他并非容易顶撞长辈的人。能够让贾琏担着被打得几日下不了床的后果直陈心中所想,可见懦弱之名有失公允。与其说贾琏懦弱,不如说是在不涉及原则时的一种退让。贾琏在扬言杀凤姐时尚且补上一句“我偿了命,大家干净”[2]359,可见法度与礼教在他心目中的重量。
贾蔷去姑苏采办东西,要“孝敬”贾琏,贾琏劈头教训:“你别兴头,才学着办事,倒先学会了这把戏。”[1]118得知旺儿儿子“原只会吃酒不成人”却要强娶彩霞时,他大怒道:“竟不知这事,且给他一顿棍,锁起来”[1]613。贵族教养与利弊权衡不允许他与妻子决裂,可他也尽己所能去改变一些不正之风。贾琏不是市井无赖,他是万不能大吵大闹的。当王熙凤沾染了市井泼妇“泼皮破落户”的习气,贾琏便更多地选择回避。这种沉默是以牺牲爱情和骄傲为代价换来的短暂宁静,也是贾琏在贵族没落史中没有丢掉的涵养与风度。
贾府另一个以“有原则”著称的人当属贾政。可他不擅家事,不理俗物,不知人情淡薄,始终没有了解过家族与官场的恶俗。贾政不曾看见外界尔虞我诈,自觉夫子清高;贾琏则权衡于浑浊世间,尽力不浸染太深。
在显赫国公府的众多不公之中,在官官相护、豪强联姻时代的不合理背后,贾琏不为难女人、不刁难下人、上敬父兄,下恤奴仆。面对诸多的不公、不平,他身不由己;面对必然承担的后果,他大多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是大家礼教在他身上的遗留,也是贵族修养的重要体现,更是贾琏不同于寻常贵族士绅的难得之处。
(三)十年寒窗奔波忙,一角冰山敛锋藏——贾琏的才华与见识
《红楼梦》作为一部描写贵族生活的古典文学名著,在琴棋书画代表的贵族情趣之外,也有大量笔墨是对生活琐事的描写。红楼女儿们不甚触及的这些,多出自琏凤夫妇的操持、打理。
“谁信世间有此境”,终是“仙境别红尘”[2]148-149。占地十九万亩的大观园不到一年时间建成,这样一个浩大而又琐碎的工程若没有一个能杀伐决断的领导人是很难完成的。书中第十六回交代:“贾政不惯于俗物,只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等几人安插摆布。”[1]118“贾赦只在家高卧,或有话说,便传呼贾琏”[2]131。至于贾珍,在秦可卿出殡时,自己家中事务尚且要请王熙凤料理,其才能可见一斑。赖大等是贾府的奴才,遇事必然不能裁度。所以,除却“不惯俗物”的贾政、“在家高卧”的贾赦、“不是他手尾”的贾珍,贾琏是贾府省亲别墅这一浩大工程的实际领导人。
大观园建成后,贾政带人验收,有事问及贾珍。贾珍不知,所以急急地唤来贾琏。“贾琏忙向靴桶取掖内装的一个纸折略节来”[1]123,一一回答,其严谨周到与恪守职责绝非膏粱子弟的作态可与并论。大观园作为贾府显赫至极的标志及贾府姐妹起居生活的主要场所,其华美与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曹公在文中将其设计到贾琏手中,何尝不是对其执行力与鉴赏力的肯定!
书中借兴儿之口交代,贾琏也曾寒窗苦读数载。贾政送贾母棺椁南下,贾兰、贾环的读书之事也“都交付给贾琏”。对于深受政、赦两位老爷喜欢,日后却对贾府落井下石的贾雨村,贾琏曾有言:“只怕未必不牵连咱们”[2]563。从交际到理家,从读书到为官,贾琏的才华在《红楼梦》中展露的不过是冰山一角。他曾在一定程度上为盛极的贾府锦上添花,于衰败后为其延续零星寿命。
综上,贾琏地位虽高,却凡事亲力亲为;虽生养于锦缎丛中,然不作骄矜之态;虽结交势力广泛,但行事多从法度。于国、于亲,贾琏不曾有大奸、大恶、大逆之举。他为家族奔波,难免于世俗中陷落。贾琏纵然有许多缺陷,却比较客观地反映出曹雪芹时代贵族的修养、礼教。曹公是见证家族鼎盛的贵族男儿,他笔下的贾琏是一位真正的贵族公子。在注定没落的历史必然中,那种留存于钟鸣鼎食之家的诗礼簪缨之气却不该就此消弭。历经几朝几世沉浮,有关家族气脉里的诗书盛世、钟鼓余韵的传承,是贾琏这一人物形象体现出的现实意义。
二、嫡子风光长子责,此身几舍几蹉跎——贾琏的人生悲剧
(一)少小生养锦缎丛,英年便知人情冷——几番离析的爱情
《红楼梦》是一部人生悲剧、家族悲剧与社会悲剧,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大都呈现出悲剧性走向。贾琏的人生悲剧主要反映在爱情婚姻、嫡子责任与家族败落三方面。而凤姐、尤二姐这两个在他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人,既是他悲剧婚姻的组成部分,也是家族和社会环境带给他的无法回避之痛。所以贾琏婚姻与情爱的不幸收场就具有了多重悲剧含义。
1.与凤姐的婚姻悲剧
贾琏的婚姻悲剧与贾府的悲剧同始同终。“言谈爽利”的凤姐与“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的贾琏,本应是一对惺惺相惜的事业型夫妻。从贾珍口中“从小大妹妹玩笑着就杀伐决断”与幼年湘云常到贾府与宝玉玩闹来看,年龄相仿的熙凤与贾琏也应当一同长大,很可能是一对青梅竹马。
刘心武在《贾琏王熙凤的夫妻生活》中评价道,《红楼梦》中“贾琏戏熙凤”写得含蓄传神:“贾琏与王熙凤不是那种因为父母包办,毫无感情,只能在昏夜里让本能催动着发生关系的懵懂夫妻,而是能在亮光下互相欣赏,循序渐进地享受性生活之乐的一对伉俪。”[3]第六十八回《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蒙评曰:“吾谓闹宁国府情有可原,闹宁国府声声是泪。”[2]535想来少年夫妻恩爱,谋事荣辱与共,数年携手默契,人人皆道阿凤好演技,可这一哭一闹也必然掺杂着数不清的真情流露。所以贾琏与熙凤应该有过一段琴瑟和谐的恩爱生活。可是当这对在锦缎丛中长大的夫妻,一在内一在外,接触到贾府辉煌背后积弊已久的事实时,也难以逃脱“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宿命。王熙凤在婚后暴露的刁蛮、高傲,让贾琏不再感受到妻子的温暖。面对家族衰落产生的心理落差与深重的无力感,加之男人的苦闷无处排解,使他开始需要一朵解语花、一个温柔乡。这时出现了千娇百媚、温柔良善胜凤姐百倍的尤二姐。
2.与尤二姐的爱情悲剧
学者大多将尤二姐的死归咎于贾琏,认为是他的不闻不问让凤姐有了可乘之机。然而私以为贾琏在其中充当的最多只是一个后知后觉的形象,贾琏对尤二姐的态度绝非玩弄敷衍。《红楼梦》第六十五回,作者在书中评价尤二姐:“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凭他有什么好处也不算了”[2]512,贾琏的态度是“谁人无过,知错必改就好,故不提以往之淫,只取今日之善”[2]512。他甚至将所有积蓄都交给二姐,与她拜天地、焚纸马,许她一场夫妻之礼,于细节中流露出真心实意。
王熙凤骗尤二姐入府,演技之高足以让贾母、探春等相信,贾琏被蒙蔽也情有可原。尤二姐生病,贾琏为她“请医治药,打鸡骂狗”,事后“搂尸大哭不止”,特意“现开了一个大门”给她出殡,又将一条素习穿的裙子留下作“念心儿”,亲自骑马去选棺木,“好的又贵,中的又不要”,只好五百两银子赊着。[2]541-543如此行为举动,绝非薄情人能有之态。贾琏是贵族公子,不精通女子手段。贾母尚言:“凤丫头倒好意待她,他到这样争风吃醋”[2]539,我们对贾琏的后知后觉也应该宽容。
于妻、于妾,贾琏情多不滥。他畏凤姐、怜二姐、敬平儿,这三个女人在贾琏的情感世界中占有很大比重。对熙凤,他有过懵懂而深重的夫妻之情、多年携手的共事之谊,但凤姐的泼辣、野蛮也让贾琏这个世家公子的自尊心深受伤害。凤姐在这段感情中的迷失,促使她做成杀人害命之举,终成夫妻感情破裂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尤氏,贾琏生过一生一世的念想,当作自己情感的寄托,却被凤姐的善妒和礼教的冷漠扼杀。贾琏对女子的追求,是在奔波劳碌之后对一方温柔天地的渴求,所以他的内心世界同样孤独。这几段夭折的感情除却对女子的伤害外,也给这个温柔良善的男子带来了巨大打击,于他而言也是一种不幸。
(二)冷静敏锐察世情,劳心奔走附耳听——嫡子责任的担当
从《家》中的高觉新到《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再到《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封建大家族的长子对一个家族内部的运转与外部维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尽数献给家族,又不得不面对家族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走向衰亡的必然。他们被责任束缚而困守于一个后世子孙的悲剧结局,在贾琏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王希廉在《红楼梦总评》中说:“贾敬、贾赦,无德无才,贾政有德无才,贾琏小有才而无德,贾珍无德亦无才。”[4]贾琏究竟是否无德另当别论,但在贾府几代人中,他能够得到“有才”二字评价,不失为一种肯定。
周汝昌在《红楼小讲》第三十一讲说道:“贾琏这个当家人被家庭财政给难住了,一时又无计摆布,想出一个奇招儿,求鸳鸯偷运了老太太的体己东西,暂渡难关。”[5]“当家人”一语,将贾琏放在比“管家人”凤姐更高的位置,“家庭财政”中“家庭”二字指明贾琏此举非谋一己私利。贾琏身为荣国府长子嫡孙,为了贾府上下的运作而求丫鬟、求凤姐,甚至求平儿,足见其中辛酸。
书中第一百零二回,贾政恐被贬官,贾琏“即刻出去,不消半日回来”,证实了消息。面对王夫人的担忧,贾琏劝解道,愿意老爷做个京官,“保得住一辈子名声”,“老太太也放心”。从贾琏宽慰王夫人的话语逻辑来看,他不在意钱财权势,甚至不将身家性命放在考虑前列,却独独顾虑到父辈名声。在“因嫌乌纱小,致使枷锁扛”的因果轮回中,贾雨村、贾赦等人一一应验。贾琏不作困兽之争的清醒之举,远非常人可比。薛姨妈处因夏金桂中毒闹得混乱,亏得贾琏带人去震慑,托官员交涉。贾府被抄,政、赦两人被吓得涕泪涟涟、面如土色,一向厉害的王熙凤也“昏死过去”。贾琏向女眷等传达消息时还能顾虑到“怕把老太太吓坏了”,“恐邢夫人又要唬死”,暂且“不敢明说”,沉稳对他而言已是一种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修养和习惯。
贾琏在两府打理家事,过早地了解到人情世故与事态炎凉。书中贾政送贾母棺椁南下,要贾琏去借几千两银子作使费。此时贾府用百两银子都要捉襟见肘,贾琏只好答道:如今人情淡薄,不如抵押田产,或叫贾府曾经的仆人赖尚荣帮忙。贾政则是一副不屑之态,然盘费不够时,还是让人休书一封去赖尚荣任上借贷。由此看,贾政面对人情世故实在单纯;而贾琏在青年时代就领略到人情之冷,且在这样的环境中依旧能做到不愤世、不漠然。贾政是不曾看破,贾雨村是看破便做了,而贾琏是看破不为其所迫,这正是他真正孤独与悲凉的地方。
(三)众人皆醉我独醒,蚍蜉无力厦将倾——家族没落的悲凉
书中第七十二回,贾琏提到宫中周太监向他“借”一千两银子,感叹道:“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元春若在宫中盛宠优渥,绝不会接二连三有太监前来勒索。此时的贾府已显示出越来越不济的景象,贾琏此语正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家族在朝廷中愈加摇坠的地位。
书中第一百零一回,王熙凤的兄长被御史参奏,托贾琏去说打点。贾琏怕王夫人担心,挂念凤姐身体不好,所以压住风声,不叫内院知道。他五更便去求人,回来后见丫头婆子竟都还在睡觉,向凤姐感叹道:“老一辈岂有这个规矩?”朝堂的失宠、亲戚的不争气、下人的怠慢,在一点点磨蚀这个男人的棱角。
贾府衰颓是大势,绝非琏凤二人理家不善,可怜邢、王两位夫人不知,赦、政二位老爷不问。贾府被抄后,从来不问家事的贾政不知府中经济如此拮据,贾琏面对诘问只好“一心委屈,含着眼泪答应了出去”[2]780。贾琏也曾想裁减奴仆,却因为“恐老爷伤心”,被王夫人按下;曾不愿与贾雨村相交,“宁可远着他些好,横竖不和他谋事”,却因为“东府大爷和他更好,老爷也喜欢他”[2]563,不得不与之作态。他是见到家族积弊最深的人,所谓积弊,非一时而就,掣肘的东西太多,即便看出弊病也无能为力。与贾宝玉灵性的爱相比,贾琏的确俗。可是宝玉为数不多的几次被贾政唤来见客,就让他大发牢骚。贾琏却要日夜连年地应承这些,实在不能苛求他保持同宝玉一样的“初心”。
贾琏曾尽一己之力,企图掩盖一种态势,让贾赦、贾政、贾珍、贾宝玉有一方与清客游山玩水、吟诗作对的天地。这既是封建时代和家族带给他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是他自身才华在打磨下绽放的光亮之处。家族带给他荣耀,也带给他责任和无法逃避的结局,这些构成了贾琏自身复杂且矛盾的人格与性格特点,也成为他精神中最悲哀可悯、让人无奈唏嘘的部分。
三、结语
贾琏是生长于末世的贵族公子,为家族奔波劳碌,游走公侯王府,结交朝廷六部。在那个年代或多或少的不合理之中,贾琏不失为一个合格的丈夫与情人,一位勤勉良善的朋友与当家人,一个封建大家族的优秀子孙。他权有限而秉公持正,不受父辈青眼却不谄媚,结交京城权贵而不屑玩权谀上;大到省亲别墅修建亲力亲为,小到为黛玉请太医看病;他也曾苦读数载,也为马上英雄。历史纵然给他许多局限,可他仍在环境的苛求中展现出贵族公子落落大方、彬彬有礼、温润如玉的行事作风。
纵观全书,贾琏为夫,宠妾爱妻,斡旋裙钗丛中,情长也;为子,不忍横夺人命,甘受家法捶楚,良善也;为兄,送颦儿千里别父,独他奔走于扬州,贾母慧眼识之也;为臣,天恩殊落,家族颠覆,冷静带枷留徙,经世之气也。在内协理两府,在外通于朝廷,作为贾府的末世公子,他温润良善,言谈皆是大家风范;教下有方,行事皆为长子气派。贾琏作为曹雪芹笔下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的贾氏子孙,纵然有一定的缺点,也是时代局限下的必然。在贾府的悲剧当中,他演绎了一个生于末世长于末世的贵族公子的悲剧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