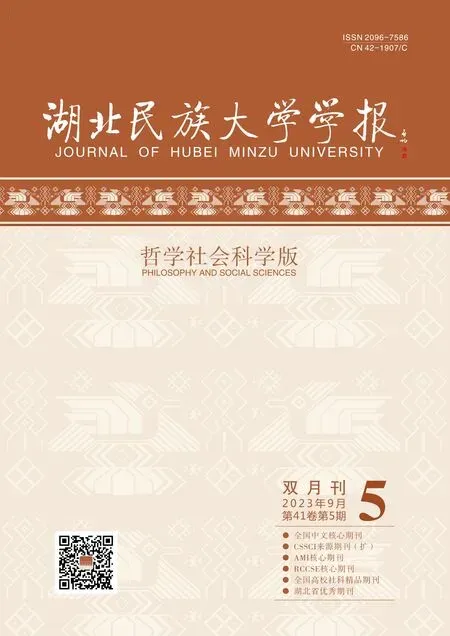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再生产的三重属性
覃锐钧 韦玉妍
文化遗产的权属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议性话题。“谁的文化遗产(价值)?”(1)Taylor, K. New Lives, “New Landscapes. Landscape, Heritage and Rural Revitalisation: Whose Cultural Values?” Built Heritage,vol. 3, 2019, pp.50-63;刘朝晖:《谁的遗产?商业化、生活态与非遗保护的专属权困境》,《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第9-16页。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及其可持续保护与利用的“主体性”等问题。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单一的文化遗产归属权和处置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和可持续保护与利用问题。(2)屈册、张朝枝:《谁的遗产?——元阳梯田旅游经营者遗产认同比较》,《热带地理》2016年第4期,第524-531页。文化遗产的景观再生产不仅被视为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的一项策略,也是使无形文化遗产有形化的过程,成为塑造和传播遗产价值的重要途径,并被应用于多领域多行业的转型或可持续发展实践之中。因此,探讨文化遗产景观再生产的本质属性似乎可以成为超越文化遗产权属之争的研究方向。
文化遗产景观再生产本质上也是一种空间的再生产。列斐伏尔将空间与社会生产进行系统整合,开创了空间生产的社会文化研究新范式。其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3)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1-52页。,来自对马克思社会实践的“矛盾空间”、黑格尔普遍性抽象多样性的“抽象空间”和尼采创意诗性活动的“差异空间”的综摄,并运用三者的“回溯式进步”来强调社会—历史—空间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4)张子凯:《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述评》,《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0-14页。此三者同时存在、地位平等,并且持续不断地叠加互动。(5)Schmid, C., “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owards a Three-dimensional Dialectic,” in K. Goonewardena, S. Kipfer, R. Milgrom and C. Schmid eds.,Space, Difference, 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bv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43; 刘怀玉:《现代性的抽象空间、矛盾空间和差异空间的生产——以黑格尔、马克思、尼采为研究视角》,《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1期,第58-68页。马克思也把空间视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其空间生产思想与其全面生产理论相统一。(6)妥建清、高居家:《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探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第185-192页。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生产”不仅作为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核心概念,关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贯通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精神生产整个过程的一般性概念,已经发展成分析社会实践的“全面生产理论”(7)俞吾金:《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16-22页。。因此,空间生产理论的三元辩证法和全面生产理论的视角为我们研究文化遗产景观再生产的本质属性提供一个研究框架:一是景观再生产的实践维度,表现为各种相关生产活动或者互动关系的集合,同时是可以感知的景观物质性要素;二是围绕景观再生产形成的空间表象,主要包括“被语言描述”和“图像表达”的景观标的物或空间表象;三是通过景观再生产的实践与据此形成的空间表象而生成的表征性空间。它们可以成为表达某种象征意义的符号,也可以成为提供文化遗产再利用的场域,体现某种特定的指向性。
基于以上的理论认知,本文以象州县纳禄村为个案,通过持续六年的田野调查,分析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再造实践,特别关注国家层面在授予纳禄村“中国传统村落”名号之后如何引发地方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以及地方力量又是如何围绕村落文化遗产开展景观再生产,营造出开放性的社会空间。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归纳文化遗产景观再生产的本质属性,提出文化遗产景观化的共富价值与空间生产的另一种正义性,进而为依托文化遗产开展乡村振兴的实践提供多方协同推进的新路径。
一、村落文化遗产的“生成”与景观再生产的个案
村落文化遗产主要指散布在乡村的具有遗产价值的各类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载体。自2012年国务院发起的传统村落调查以来,中国分六期共有5188个村庄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江苏、福建、陕西、四川、安徽、广西等省(市、自治区)同时开展本级传统村落认定。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成为保护和关注的对象。人们普遍认为,“传统村落”(也被称为“老村”“古村落”“特色村”等)保留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是“承载和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8)参见《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2012年4月24日,http://www.gov.cn/zwgk/2012-04/24/content_2121340.htm,2023年7月25日。和“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9)周宏伟:《从文化遗产角度看传统村落》,《中华民居》2022年第3期,第17-18页。。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可视为重新审视和挖掘村落文化遗产的一个典型代表。此外,村落文化遗产也因为扎根于乡土,成为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当前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自然离不开国家话语和地方性知识的双重构建,并上升为一项超然和长期的国家使命,体现了国家对中华民族根性文化进行保护的偏好与努力。(10)王思雅、孙九霞:《乡村振兴视域下传统村落保护的国家话语与地方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第5期,第124-131页。村落文化遗产已经大规模地进入国家治理范围并日益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
纳禄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罗秀镇委的一个自然村。全村共有228户,常住人口881人,耕地面积1968亩,林地2116亩。该村的生计方式经历了以种植水稻、甘蔗、种桑养蚕为主到以种植砂糖橘为主的转变。村所在地被罗秀河的主流和一条支流环绕,村后有一座如枕头型的古鹿山。纳禄村因为山水形胜、生态环境优美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另据当地村民介绍,纳禄村的朱氏先民是明朝靖江王的后裔。明朝末年,清军入关并最终推翻明朝统治,桂林的靖江王朱氏一族为了躲避清军追杀,几经辗转,最终定居此地。清朝年间,传承良好家风的朱氏后人在纳禄村勤于耕读,培育子弟,最终人才辈出,财富日增,修建了留存至今的建筑群。象州古鹿山下的朱府也因此开始声名远播。(11)大明靖江王象州朱氏族委员会:《象州朱氏宗族谱》,内部资料,2015年,第70页。这些被当地人称为“老房子”的传统建筑目前保留有24座共69间。这些建筑结构整齐、规制考究,是当地保存较为完好的传统建筑,也是纳禄村成功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核心资源。
自2012年成功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以来,纳禄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地政府委托专业建筑设计公司和文物保护机构对纳禄村的保护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规划设计。施工单位据此重建和修复了古建筑,并装修和布置了其内部空间。经过持续多年的修复,古建筑重现当年青砖黛瓦、朱门小院的样貌。老房子间的巷道得以重新铺装,损毁和倒塌的墙体和屋顶也得到还原性修复。(12)罗彩娟:《空间、地景与传统村落的开发与保护——以广西象州县纳禄村为例》,《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65-75页。此外,得益于不断注入的项目资金,纳禄村的村容村貌也得到极大地改观。当地政府正在致力于把纳禄村打造成一个乡村旅游景点。在多方持续参与下,纳禄村营造了大量体现国家使命、家园文化和迎合公众的新样态景观。
尽管文化遗产景观再生产的三个空间维度总是同时存在并相对混融的,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当前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再生产实践窥探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当我们将文化遗产景观化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进程和现实场景中加以审视时,其国家性、家园性和开放性则成为当前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化研究无法绕开的三大特征。
二、国家性:文化遗产景观中的国家符号化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通常以多元的想象、叙述和实践,弥补在复杂社会中所遗失的国家“同一性”,从而将宏大的民族国家形象和零碎而杂散的社会日常建立起联结。(13)陈薇:《被“标识”的国家:撤侨话语中的国家认同与家国想象》,《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期,第136-153页。国家的观念因此不断得到凸显和强化,类似特征同样明显地体现在纳禄村的景观再造实践中。
(一)国家认同与景观再生产
就空间实践维度而言,纳禄村诸多再生产景观体现了鲜明的国家认同。一是以朱氏族规表达国家认同。在修复后的老房子主厅中,除了大量运用相关的文字和图片把纳禄村的朱氏家族与明朝时期驻地桂林的靖江王建立直接的关联之外,设计者还在明显的位置展示了最新版本的朱氏族规。族规的第一条写道:“热爱祖国,忠于民族。凡朱氏族人都应胸怀天下,谨重名节,替国分忧,为民谋利;不得因私废公,舍义取利,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在朱氏族规中已经得到认同和宣扬。当地政府与专业设计人员借助朱氏族规塑造了一道新景观,共同表达了国家认同的蕴意。
二是以景观广场表达国家认同。除了运用家法族规的景观设计来表达国家认同,用历史记忆来表达国家认同也是一种普遍的策略。纳禄村的朱氏后人虽然不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但他们认为自己与朱元璋仍然存在血缘上的关联。为此,当地政府结合这样的“地方记忆”和“历史人物”,以及当前国家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把朱元璋反腐败的相关典故引入景观再造项目中。特别突出的例子是当地政府在纳禄村打造了一个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和一个文化景观广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有两块标志性景观石:一块刻着“纳禄村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另外一块是四方体石块,其中一面镌刻着不同字体的“廉”字,另一面则是中文计数用的大写数字和单位。(14)明朝初期朱元璋为了防止官员通过篡改账本数字以侵吞钱粮而设计的技术规范,即把汉字中的数字改为难以涂改的大写字。这一技术规范一直沿用至今。周围的三尊石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朱元璋反腐败的三则典故。此处的一道景观墙中塑有“耕读”“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等大字。文化景观广场是游客参观古建筑的必经之地。广场的东面竖立着朱元璋和他的两位辅政大臣的雕像。雕像的后面是一道背景墙,同样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镌刻着五则朱元璋的反腐败故事。景观广场的《前言》明确写道:“今天我们在这里列出朱元璋的廉政典故,学习它的精华,弃其糟粕,这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是以村名景观墙表达国家认同。入选“中国传统村落”之后,当地政府在纳禄村的村口广场建起一道村名景观墙。竖写的黑色方正大字“中国传统村落”和红底白色楷体字“纳禄村”,彰显其“国”字号身份。可以说,通过“命名”或“封授”是国家政策施行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地方通过“申请(报)”或“接受”名号也表达了国家认同。近年来,纳禄村获得了一系列荣誉称号,比如国家AAA级景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村屯、三星级休闲农业核心示范区、乡村旅游区、生态特色文化旅游示范村等。此外,当地政府还在村口景观池塘边立起一根旗杆并悬挂国旗。他们认为,这是纳禄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称号的象征,也是政府宣示打造乡村综合发展示范点的决心。
(二)国家认同的地方行动
以传统村落为主题的景观再造行动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经由地方政府传达到基层乡村,并影响地方民众对国家的感知和认同。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绝大多数纳禄村民以“服从”和“支持”的态度和行动参与传统村落的景观再造行动中。村干部PWG说:“我们知道打造传统村落对我们肯定是有很多好处的,所以,大多数家庭都愿意把老房子租给政府,由政府来统一维修和管理。”独居在老房子的新乡贤PJX说:“老房子前面有一块地,原来是我的宅基地。我儿子原本打算在这里建一栋楼房,但是政府说要在这里铺石板,方便游客参观。我和儿子最后也同意了。”村民ZMF也说,他家的屋后原来还有一座房子,因年久失修,最后也交给政府改造成小花园。此外,在建设景观广场、道路、景观池塘、游客接待中心、公共厕所、篮球场等项目过程中,需要占用不少家庭的自留地甚至宅基地。但绝大多数的村民都能以超越个人和家庭的立场来权衡利弊,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渡,以此表达对村落未来发展的期待。
(三)景观再生产中的国家表征性
国家通过甄选“名录”的形式启动一个大规模的项目来保护和利用村落文化遗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借用地方资源表征国家意志的惯例。正如山西大寨村的景观化实践同时成为典型村国家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15)郭永平:《文化景观、历史遗产与乡村重塑——以山西省大寨村为考察对象》,《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79-86页。,这样的形式同时成为地方社会经济持续性发展的新杠杆(16)Qin R.J.,Leung H.H.,“Becoming a Traditional Village: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of a Chinese Village,” Sustainability,vol. 13, no. 4, 2021, pp.1-28.。近年来,纳禄村的发展日新月异,这一趋势引发周边的村民“羡慕”或“复杂”的心理,他们认为纳禄村是得到了国家的“偏爱”。地方政府则宣称这是以纳禄村为试点带动周边村落共同发展的规划。可以说,村落文化遗产的景观化实践生成一种新的乡村振兴机制,这一机制为当地人表达发展诉求、国家认同和文化解释提供新的协商空间和“话语的机会”(17)Murti D.C.W.,“Locating Nation in a Village: Fusion of Local and Nation Voices in Penglipuran Bali,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Anthropology, vol. 7, no. 2, 2019, pp.157-177.。地方政府和当地村民正是沿着国家的意志和保护传承民族根性文化的潮流,开辟了乡村振兴的新空间。
同时,景观再生产也把地方的历史叙述整合成多种形式的国家表征。在获得“中国传统村落”名号之后,纳禄村的朱氏后裔甚至是与朱家人通婚的外姓人,开始自称或被称为“皇族后裔”。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学者、记者、游客等群体有意或无意地在各类媒体平台宣传纳禄村的“老房子”和“皇族后裔”的历史故事,并以此作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名片”。村干部LXL还注册了一个名为“纳禄皇室”的土特产商标,用于包装和销售当地的土特产品。“皇族”或“皇室”名称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理解“历史国家”与“现代国家”的一种媒介,也是地方叙述尝试“统合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国族话语’体系”(18)燕海鸣、解立:《标准化的多样性:云南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世界遗产话语和“去地方化”进程》,《东南文化》2020年第2期,第6-12页。的努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村落的名号以及围绕这一名号生成的具象空间和想象空间已经成为国家认同的一种表征。
三、家园性:“家”与社区的景观再生产
作为纳禄村的核心文化遗产,老房子自然成为体现传统家文化的空间。在最大限度地恢复老房子的传统风貌之后,如何利用古建筑的内部空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地政府以“皇族后裔”的名号,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挖掘了朱氏家族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景观化再生产表征“传统的”“家的”“社区的”新空间。
(一)从“家”到“家园”的景观空间再生产
村落中的“家”文化空间景观再造通常以“本地”和“传统”元素为起点。村落中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家”,包括了建筑空间、起居空间、仪式空间,以及空间的使用原则,也被景观设计者通过“修旧如旧”的行业策略进行修复性和创造性地塑造。在此过程中,当地人通过参与协商,传递“正宗地方”的概念。(19)Zhu Y., “Cultural Effects of Authenticity: Contested Heritage Practic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 21, no. 6, 2015, pp.594-608.纳禄村古建筑群的每一座房子大致以相同的布局体现了传统的家庭观念与家族文化。其功能布局一般包括厅堂、起居室、厨房、天井、巷道等。厅堂通常是家庭(族)的重要生活空间,也是重要的仪式性空间。在恢复性装饰中,当地政府参考朱氏后裔的记忆,在厅堂摆放了若干张太师椅和茶几。在主厅的正中间,一个神龛悬置于墙上,下边摆放一张高脚桌。神龛上方是一副对联:“五鹿谈经宗沛国,千秋遗爱祀桐乡”,堂号为“沛国堂”。当地村民说,这是朱家专属的神龛,也是朱家人铭记家族渊源和敬拜先祖的传统做法。装饰后的房间放置了古式木床、橱柜、桌椅等家具。这些老旧的家具和日用品,再加上翻新的青砖青瓦、朱红的木制门窗和石灰黏土硬化的地面,令人仿佛置身明清时期的士大夫家中。
老房子的主厅还成为展示朱氏家风教化和日常生活的空间。当地村民与政府工作人员在深入梳理朱氏与桂林靖江王的关系后,还在老房子里的主宅中展陈了朱家的“祖训族规”、相关的历史图片和世系表。“祖训族规”成为老房子中一个突出的“传统的家”的表象。除了上文提到的最新版朱氏族规之外,在展厅中摆放的《朱氏宗族谱》还记录了最早的两个版本的家(族)规。最早的版本从孝悌、礼让、读书、务农、工艺、经商、亲疏、贫富等八个方面对家族内成员提出训导;第二版本则从品行、祠墓、宗族、名分、职业、蒙养、亲孝、婚邻、邪巫、节俭等十个方面提出族员共同遵守的准则。(20)限于篇幅不在此赘述,相关的完整版本可向作者索取。当地人认为,这是朱氏家族从明朝没落的遭遇中重振家声并再度成为当地名门望族的精神密码。清朝时期,朱氏家族至少培养和输送了六位文官和两位武官,以至于在当地盛传“象县二武六文,皆称纳禄朱府”的美誉。正是因为有不少官员效力于朝廷,成为“吃皇粮”“纳俸禄”的官员,该村的村名因此由“拿鹿村”改名“纳禄村”并沿用至今。
纳禄村文化遗产景观再生产同时扩大为整个村落的基础建设。得益于不断注入的项目和资金支持,纳禄村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村的排污沟完成了全面升级改造,主干道路和环村路也得到拓宽和硬化,实现“户户通车,家家通路”。此外,集景观性和功能性于一体的清心亭(亦称洗衣亭)、景观鱼塘、休闲凉亭、宣传牌坊、户外棋牌桌和健身器材等项目也相继建成。纳禄村俨然已经成为当地一个融合地方传统和现代特色的新型乡村社区。
(二)家园空间的表象叙述
随着村落功能性景观的持续升级,以及不断提升的外界期待,当地村民的自我认同感和自豪感正在不断被激发。村干部在访谈中多次提到,在那场水灾(21)2005年6月21日,纳禄村遭遇了一场特别严重的水灾,村中的泥瓦房被冲毁殆尽。灾情发生后,在当地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纳禄村迅速开展重建家园和恢复生产。后的重建行动中,因为纳禄村的群众团结一心,响应积极,很快被当地政府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原村主任ZFP说,纳禄村的人总是保留相互扶助的优良传统,因此,村民对于很多建设项目都能够很快形成统一意见。WHL女士说,村里的老房子得到国家的重视,又可以发挥新作用,大家都觉得很欣慰。朱氏后裔ZMD自承担老房子日常管理与解说任务以来,他不断搜集和学习关于纳禄村的宣传素材,特别是老房子的空间布局、传说故事、历史文化和朱家的家风家规,以及那些设计独特和构造精妙的技艺。每一次到访我们总能够听到他自豪地讲解关于老房子的新信息。
日益美丽的乡村已经成为村民无法割舍的生活社区和精神家园。有学者认为,不断升级的村落社区营造总是可以重建和促进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地方感。(22)Oakes T., “Heritage as Improvement: Cultural Display and Conteste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9, no. 4, 2013, pp.380-40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纳禄村民开始寻思回村建新房。除了作为颐养天年的精神依托和家园依恋,村民普遍认为,现在的纳禄村发展得越来越好,回村养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年近七旬的贾女士认为,这里水好空气好,生活也很方便,很多亲戚朋友也在这里生活。虽然自己在城市工作了大半辈子,也在那里买了房子,但是她最后还是选择回到纳禄村安度晚年。我们在访谈中还了解到,已经有至少14位年长的村民结束了在外打拼的生涯,重新回到纳禄村生活。
(三)“过去的家”与“现在的家园”的表征性空间
村落文化遗产景观的家园性扎根于中国乡土的文化多样性。乡村居民通过重新整理和“反刍”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不断在行动中审视和调整自我的文化认知和价值定位,积极参与新时代的国家想象和家园变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村落文化遗产的价值被重新发掘和阐释,传承千百年的家文化被赋予新的内涵,并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中扩大了边界。村落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传统元素通过功能化景观再造不断升级,社区功能也因此得到强化。
营造田园诗般的乡村旅游风貌把“过去的家”与“现代的家园”联系起来。作为“一种文化建构”(23)Taylor, Ken, “Landscape, Culture and Heritage: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an Asian Context,” Deakin University Library, Australia,2017,p.23.,景观再生产的过程体现了形成地方认同的过程(24)Mitchell, W. J. T., Landscape and Power (2nd 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1.。通过对老房子进行保护与利用,挖掘和包装其中的历史记忆,重新找回濒临失传的手工艺等传统文化,成为纳禄村一个全新的发展起点。部分嗅觉灵敏的村干部和村民开始试水“在家门口做生意”或者在村中“吃旅游饭”。目前,村中开设了近10家民宿,有5家民宿已经开始对外营业。常年有数十名村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或各种工程项目的建设。“过去的家”正在成为文化遗产并通过景观再造生成乡村旅游资源。“现在的家园”成为可以接续亲情、安享晚年或生计转型的新空间。家园性的概念正在以一个整体性的视角来反思曾经被污名化或误读的乡村,并消解都市社会无法承载或解释的社会群体的境遇。(25)李晓非、朱晓阳:《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概念的“家园”》,《兰州学刊》2015年第1期,第121-130页。可以这样说,当前的乡村家园被赋予更多新的表征意义并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更多更大的想象空间。
四、开放性:面向公众的文化遗产景观化空间
无论是营造一种传统的空间,还是现代的公共性场景,对于纳禄村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地政府、设计者、村民正在以“专业的”理念和多元的视角,共同营造出迎合参访者期待的公共空间,凸显了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化中新的公共属性。
(一)文化遗产景观再生产的公共空间实践
除了通过恢复或修复传统元素之外,相关的社会公共元素也被引入纳禄村的景观再生产中。古建筑中的“农家文化展览馆”(也被称为“村史馆”)体现了这一公共元素的进场。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干部认为,纳禄村将来要走一条乡村旅游的发展之路,所接待的游客大多数来自城镇。为此,他们收集了大量存留在当地的旧农具和手工艺品,如犁、耙、锄、镰刀、筐、簸箕等,以及盛产于当地的富硒红米、手工米饼、红糖、腐竹等土特产品,集中展示在展览馆中,使之成为游客了解当地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和当地特色产品的载体,塑造了“以‘三农’为本质属性”(26)陈兴贵、王美:《反思与展望: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研究30年》,《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14-125页。的传统村落形象。此外,为了增加景观的吸引力和游客的体验感,作为20世纪80年代纳禄村村民一项主要生计的手工炮仗也在展馆里作了场景性展示。此外,当地政府还在修缮后的老房子里展示了纳禄村的发展规划。从规划介绍中可以看出,当地政府正在有计划地把纳禄村纳入当地“全域旅游”网络中加以打造。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一直在引导该村发展桑蚕、优质水稻、甘蔗等传统产业,重点培育优质水果产业,开发采摘园、休闲养生、垂钓、生态农业等体验式的农家风情项目,以吸引周边地市的游客。总之,营造更多开放性景观空间已成为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共同目标。
(二)成为“开放”与“对话”的表象空间
文化遗产的景观再造也为社会资本的进场创造了机会。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化放大或再现了传统的文化元素,迎合了国家对保护传统村落的价值定位,生产了吸引游客以发展乡村旅游的景观资源。虽然有学者反对传统村落的旅游化发展,但是,不可否认,文化遗产已成为中国许多乡村地区在发展主义和资本主义驱动下的发展资源。(27)Chen, Z., Ren, X., &Zhang, Z., “Cultural Heritage as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tik Production amongst China’s Miao Popul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81, no. 1, 2021, pp.182-193.以“遗产”作为资源发展经济也成为许多遗产地首要的追求目标。(28)Taylor K., “New Lives, New Landscapes, Landscape, Heritage and Rural Revitalisation: Whose Cultural Values?” Built Heritage, vol. 3, no. 2, 2019, pp.50-63.2020年,一家来自广东的旅游投资集团在象州县成立旅游发展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开发纳禄村的合同。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的目标是以传统建筑为核心,以当地山水为依托,打造一个集休闲娱乐、生态康养、教育拓展、科普研学、商贸购物等为一体的多元化乡村特色景区。
景观化之后的老房子成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空间”。除了游客的到访与“阅读”之外,纳禄村的传统民居日益成为媒体和文化机构的关注点。近10年来,仅在互联网上可查到的地市级以上的媒体直接采访或报道纳禄村的次数已经超过20次。每年参访纳禄村的单位、机构和组织也是络绎不绝。2020年5月,一场别开生面的“开笔礼”在纳禄村举行,村主任WBS亲自为一家书法培训机构组织的数十名中小学生教授毛笔书法课。2020年11月举办的“穿越明朝·夜游纳禄大型光影艺术节”把纳禄村的知名度推到新的高度。2022年冬季,广西卫视和广西艺术学院在纳禄村举办一场名为“共礼”的公共艺术特展。主办方在深入了解纳禄村前世今生的基础上,创作了11幅与当地景观空间形成或共鸣共生,或对照鲜明,或意味悠长的艺术作品。
(三)伴生共享自由的“第三空间”
乡村文化遗产景观的再造热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乡村价值的回归或开放乡土空间的期盼。在国家力量和当地村民的共同推动下,对村落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利用在有意无意地打开迎接社会公众进入的“第三空间”。索亚认为这一空间是彻底开放且充满象征和想象的,是未完待续的旅程。(29)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导论”,第1、12页。相对于可感知的具象的“第一空间”和可构想的抽象的“第二空间”,传统村落的遗产景观再生产实际上再现了具有他者性的“第三空间”。当前出入纳禄村仍然是免费的,相当多的空间也是开放的。因此,不少游客自驾到此地,开展摄影、垂钓、骑行、露营、烧烤等休闲活动,也有一些团体到此开展素质拓展活动。跟踪调查显示,纳禄村的自由访客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这一趋势也应合了联合国人居署《新城市议程》所倡导“城乡互动和连通”“包括城市与周边地区、近郊和农村之间的连通”的理念,体现了在文化遗产旅游实践中构建合作、共享的社会关系(30)吴兴帜:《文化遗产旅游消费的逻辑与转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8期,第27-32页。的开放性理念。可以说,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再造实际上也伴生了面向社会公众的自由、随性、多元的延展性空间。
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化迎合了社会大众对乡村田园诗般空间的期待。乡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封闭的、落后的、没有文化的,甚至是没有历史的地方。相反,经过再生产之乡村文化遗产景观所形成的空间正在成为城市居民的新宠。它甚至成为寄托乡愁、传承传统文化、释放精神压力、寻找自我的新去处。传统村落中的“家”文化景观、村落新景观和现代的国家性景观已经成为他者“凝视”的文化载体。游客也在对旅游符号的“阅读”中生成旅游、生活和生命的意义。(31)杜彬:《文旅融合背景下文化遗产资源推动旅游空间建设的思考》,《文化遗产》2021年第2期,第32-41页。诚然,这些意义是多元而变动的。随机访谈显示了这种“阅读”的个性化和开放性。游客韦先生说,这座古村落周围河流形成的水景,还有这里成排的老房子和狭长的小巷,以及明朝皇室后裔的历史传说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另一位潘女士说,这里的房子非常简朴,充满了时代感和文化感,具有很强的历史韵味,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总之,纳禄村的遗产景观体现了“第三空间”特有的容许多元主体在其中自由地支配空间、表达自我和建构话语的特征。
五、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迈向民族复兴的文化需要为国家力量深入乡村社会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作为一种“文化的线索”(32)Lewis, Peirce, “Axioms for Reading the Landscape: Some Guides to the American Scene,” In Donald W. Meinig, e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11-32.,村落文化遗产提供了大量建构、解读和体验“国家”“家园”“空间”的地方性文本。村落文化遗产的景观再生产业已成为关联村治导向的国家性、乡村振兴的家园性和公众参与的开放性的实践集合。
村落文化遗产的景观再生产所体现的三重属性绝非偶然。首先,它来自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所强调的多维度生产与再生产。当前的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再生产由国家主导、当地人协同和社会参与,共同作用于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的生产与再生产。其次,它来自国家对于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赓续创新的允诺。最后,它是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促成的新空间的自然体现。
从理论意义上看,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再生产的三重属性超越了对文化遗产景观二元对立归属权的争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充满权力施治、经济博弈和社会互动的复杂过程。文化遗产的价值共享与传递也需要处理诸多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又是某个单一主体无法全面把控的。如果非要强调是“谁的文化遗产”(价值),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化的经验首先强调了其中的“国家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更大的乡村景观的“家园性”,还在于它带来文化遗产景观的“开放性”。乡村文化遗产新景观的再生产,扩大了外界参与、阅读和消费的趋势,形成一个更大范围遗产价值的传递链和循环圈。与此同时,纳禄村成为“中国传统村落”的过程催生了“家”(村落)—“国”(共同体)同构的景观新样态,符合文化遗产景观走向共享的价值取向,也应合了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如果“建筑意识形态依靠城市的构成性中心,将群体、阶级、个人从城市中排出,从文明、社会中排出,这是一种无声的暴力”(33)刘怀玉:《〈空间的生产〉若干问题研究》,《哲学动态》2014年第11期,第18-28页。,那么,当前村落文化遗产的景观再生产却是在打破曾经“封闭的”乡村空间,营造新的开放性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乡村空间生产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友好性,以及实践“文化共富”的空间正义性。
从实践意义上看,遗产景观再生产的三重属性为破解地方文化景观发展困境提供一种可持续的整体发展的洞见。因为它倡导关注文化遗产中不易被发觉的社会经济体系(34)西村幸夫、杜之岩:《历史、文化遗产及背后的系统——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为中心》,《东南文化》2018年第2期,第119-123页。和随着时代变化而调整的社会生产关系。它体现了将地方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生态中作整体分析和审视的价值追求。通过挖掘和塑造文化遗产景观的国家性和家园性来生成地方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以及通过营造地方的家园性和激发公众参与来表达国家认同的路径不失为地方经济社会实现新发展的一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