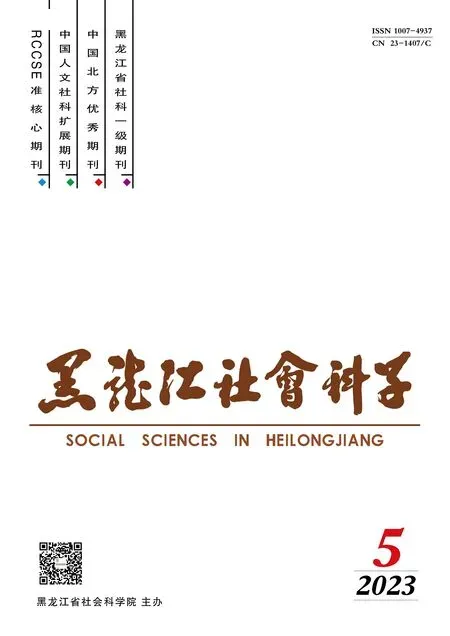黄榦对《大学》的疏解
邓庆平,刘晓伟
(1.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 330022;2.南昌大学 江右哲学研究中心,南昌 330031)
朱熹一生在《大学》上用力最多,直到去世前三天还在修订《大学》“诚意”章注解。他曾自述:“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读书。”[1]258《大学》被朱熹列为“四书”之首,具有奠定为学规模的意义,在朱子学经典体系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点也为朱子最重要的门人黄榦(1152—1221)所重视。黄榦作有《大学经一章解》[2]1-2和《大学章句疏义》[2]2-4,他不仅在新淦的县学讲解《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一章,还就明德等问题与同门展开多次讨论。黄榦对《大学》经一章有完整疏解,对朱子《大学章句》有所发挥与补充,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大学》经一章的结构、明明德、工夫论以及道统论等方面的发挥上。
一、《大学》经一章的结构
朱子在解释《大学》的首句“大学之道”(1)对于《大学》经文中的“大学”二字,有的学者认为当指《大学》一书,故加上书名号,而朱子注解中的“大学”二字则未加书名号,如中华书局版的《四书章句集注》。这里便造成一个矛盾,那就是朱子用“大人之学”来界定的“大学”并非经文首句“大学之道”的《大学》,因此,首句“大学之道”中的“大学”不是指《大学》一书。时指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3]3《大学》即大人之学。在解释《论语》“君子有三畏章”中的“畏大人”一句时,朱子说,“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齿、有德者,皆谓之‘大人’”[1]1173。“朱子承认大人的年龄义与权位义,但最终侧重的是道德义。”[4]黄榦在《大学章句疏义》中则明确“大人之学者兼齿德而言也”[2]3,此处,大人既指年龄较大的成年人,亦指道德高尚的君子。
关注文本结构是黄榦诠释经典的重要特点。在吸收朱熹《大学章句》做法的基础上,他在《大学经一章解》中将《大学》经一章分为五个部分,并认为每个部分主旨不同。
一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言《大学》之纲领,其本末当如此也。”[2]1二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言《大学》工夫,其始终当如此也。”[2]1三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承上文两节明大学之道,以起下文两节之意。”[2]2四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至国治而天下平。“此推言上文三节之意,言明德新民之目,知止能得之序,本末始终之有先后也。”[2]2五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至未之有也。“上文所言大学之道尽矣,此复申言修身齐家乃大学之要,无贵无贱,皆当自勉,其示人之意至矣。”[2]2在《大学章句疏义》中,黄榦将第四部分划分为两个部分,因此,《大学章句疏义》分为六个部分。
在黄榦看来,《大学》经一章的五个部分当中,第一、二部分是重点,第三部分的作用是承上启下,第四部分是在前三个部分基础上的推论,可以看作是明德新民的具体展开。第五部分强调修身齐家为大学之道具体展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因此,黄榦对《大学》的注解以及对朱熹《大学章句》的疏解的重心在第一、二部分。
二、“明明德”章释义
朱子说道:“学者须是为己。圣人教人,只在大学第一句‘明明德’上。”[1]261“明明德指称主体道德生命本性的自我觉醒与显明”[4],为大学三纲领之根本,也是大学之学的根本。在黄榦的注疏当中,“明明德”章也是首要的重点。他曾与同门多次反复讨论《大学》这一章。如开禧二年(1206)在写给李燔的书信中,黄榦提出:
承见教明德章,更平心将诸处说明德参考,如克明峻德,以至于光被四表、懋昭大德、自昭明德、辉光日新其德、予怀明德之类,看两个明字作如何说,与今《大学》是同是别。又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用功处,如何能明其明德。《或问》所谓明之端、明之实,是如何[2]565?
李燔为朱熹的重要门人,曾代朱熹讲学,李燔的朱子学造诣较深,黄榦与其有多次书信往来[5]。这里黄榦一并提出了众多问题,可见其讨论的深入程度。“克明峻德”“光被四表”出自《尚书·尧典》,“懋昭大德”出自《尚书·仲虺之诰》,“自昭明德”出自《周易·晋·象》,“辉光日新其德”出自《周易·大畜·彖》,“予怀明德”出自《诗经》,均与明德有关。首先,黄榦归纳了《大学》之“明明德”与其他经典中的明德说,比较其异同,提出如何理解“明明德”中两个“明”字,以及两个“明”字是否有内在关联。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注“明明德”时讲:“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3]3第一个“明”是动词,是指使之明,第二个“明”与“德”构成一个专有名词即明德,明德是人所具有的某种虚灵不昧的东西。而两个“明”字之间的关系是朱子所未深入辨析的,对于此明德到底是性还是心,朱子与弟子有过很多讨论,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其次,黄榦提出八目何以明其明德,这是涉及明明德的实现问题;最后,黄榦指出了如何理解《或问》中所言明之端、明之实,这是对朱子理解的追问。《大学或问》中,朱子指出:“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后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因其所发,以启明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生之目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体之全哉!”[6]格物致知是在小学工夫基础上的明明德的开端,而诚意、正心与修身则是以此开端来反之于身,以求明德在意、心和身上充分彰显和实现。
黄榦专门作了一篇疏解朱熹《大学章句》的文章即《大学章句疏义》,就朱熹解《大学》时所使用到的许多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与阐发。其中关于“明明德”,他说:
明明德者,明其在己所禀至明之德也。明谓虚灵知觉,纯莹昭著者也。德谓所具之理也。新犹明也,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亦使之去其蒙蔽污浊而复其本然之明也。止谓必至于是而不迁之谓也。至善者,德之当明、民之当新,皆当止于至善,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是明明德新民之至善而学者之所当止也。注云大人之学者兼齿德而言也,又云虚灵不昧者,虚谓知觉,不昧谓纯莹昭著者也。知觉者,物格知至也,纯莹昭著者,意诚心正而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注云具众理应万事者,德即理也,而曰具众理又兼夫应万事而言,此乃直指人心,合全体大用而为言也。具众理者,德之全体,应万事者,德之大用也。云“新者,革其旧之谓”。又云“其旧染之污”者,旧谓蒙蔽污浊,新则去其蒙蔽污浊,故新亦明也。云“至善谓事理当然之极”者,言凡事理皆有当然之对当然之则,乃所谓善也,其极则至善也,不至于当然,不以为善,不至于当然之极不足以为至善。盖言明而新之者,必“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2]3。
这段文字围绕“明明德”与“新民”“止于至善”展开,至少有三层意思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就“明德”而言,朱子《大学章句》将明德视为虚灵不昧的一个整体,而黄榦在此基础上疏解:“明谓虚灵知觉,纯莹昭著者也,德谓所具之理也。”将明德分为明与德两部分,明即虚灵知觉、纯莹昭著之意,此为本然之明,而德从本质上来说是所具之理。朱子认为“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3]94。所谓得其道,也即得其理。黄榦以所具之理来讲德,应该说也是可以成立的。对于朱子原注中的“虚灵不昧”一词,黄榦逐一解释“虚谓知觉,不昧谓纯莹昭著者也”[2]3,且结合八目来进一步理解,他说“知觉者,物格知至也,纯莹昭著者,意诚心正而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也”[2]3。虚灵知觉是对物格知致的要求,而纯莹昭著则是对意诚心正乃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对于朱熹原注“明德”一词中“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黄榦认为“具众理应万事者,德即理也,而曰具众理又兼夫应万事而言,此乃直指人心,合全体大用而为言也。具众理者,德之全体,应万事者,德之大用也”[2]3。德即理,那么明德自然而然地就具备了众理,此乃德之全体,而应万事者则是德之对外的功能作用。
在后来与同门李燔的讨论中,黄榦进一步阐发“明德”之明应该具有内外两层内涵:
《大学》首章旧说以德之发于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为明德,今解以德之存于中者,昭彻而无所蔽为言,故鄙意欲合内外而言之,亦似有理[2]565。
此信作于1207年。黄榦指出,明德既指德发于外之昭著不可掩,也指德之存于中而昭彻无所蔽,也就是说,明德之明应该包括在外的昭著不可掩和在内的昭彻无所蔽。这里的内外与前文从“合全体大用”的角度将明德分解为具众理与应万事是相对应的,具众理即内在的昭彻无所蔽,应万事为明德发于外者而昭著不可掩。
大约在同时,黄榦在写给胡伯量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大学》首章无他疑。但向者以为明德之发于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于中者,洞彻而无所蔽也。故鄙意以为莫若合内外而言之。虚灵指存于中者而言,昭著指发于外者而言。如辉光之类,皆指外者而言之[2]596。
虚灵是对内在洞彻无所蔽的描述,是德之存于中者,而昭著则是德之外在发显的状态,明德应该合内外而言。
第二,在《大学章句疏义》中,黄榦针对朱熹在“既自明其德又当推以及人”[3]3的意义上由明明德引出新民之说,他这里直接点出“新犹明也”,并针对朱熹的“新者,革其旧之谓也”[3]3,“旧染之污者”[3]3,进一步指出新与旧的实质所指。他说:“旧谓蒙蔽污浊,新则去其蒙蔽污浊,故新亦明也。”在黄榦看来,“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为动词,和“新民”之“新”字义相同,都是“其蒙蔽污浊而复其本然之明也”,即恢复本然之明。这点一方面回答了上文所提及的黄榦与李燔书信中讨论两个“明”字义的问题,“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和第二个“明”字含义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将“明明德”与“新民”贯通起来。
第三,对于“止于至善”,黄榦的疏解特色在于区分善与至善,“言凡事理皆有当然之对、当然之则,乃所谓善也,其极则至善也,不至于当然,不以为善,不至于当然之极不足以为至善”[2]3。 至善是由“明明德”至“新民”的当止之处。
至此,黄榦对朱熹《大学章句》进行了逐渐深入的两层疏解,其中不仅有对经典原文的理解,而且还包含他对这些理解的再行疏解,在疏解“明明德”的基础上将“新民”“止于至善”的思想内涵也一并融通起来。这种疏解是以对概念的更细致界定来展开的。
“明德究竟是指心还是性,指心之本体还是性之本体,在《大学章句》及其《或问》中尚难得出答案。”[7]因此,以致造成后来学者对此产生分歧,如牟宗三主张朱子之明德“是就性理说明德之本身”[8]。对此,黄榦明确指出:
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杨德渊惠书亦录示所答之语,此但当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则直截简径。使之自此思索,却见得分晓。今观所答,是未免以心性为两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则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则仁又便是心。《大学》所解明德,则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误以心性为两物,而又欲安排并合,故其说颇觉费力。心之能为性情主宰者,以其虚灵知觉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虚灵知觉也。自当随其所指,各自体认,其浅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则如谢氏常惺惺之谓。此只是能持敬,则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学》所谓明德,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须安排并合也[2]648。
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此心并非一般意义上夹杂善恶的人心,而是纯善的具有虚灵知觉的能为性情主宰者的本心,是物格知致之后的心,此时之心不仅有虚灵知觉的功能,还因致知等为学工夫而内具众理,故黄榦又说对于明德来说“心便是性,性便是心”,心性并非两物。故此关于明德是心还是性的问题便消解了。这一认识与现代学者对朱子“明德”说的最新理解较为接近,如王凯立指出,“朱子对‘明德’的阐述乃兼心性言之,这意味着,‘明德’是心性合一的”[9]。
三、《大学》之工夫
朱子讲“‘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至致知在格物。’‘欲’与‘先’字,谓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节次”[1]310。《大学》八条目是讲工夫次序的。当朱熹弟子问“知止至能得,其间有工夫否”时,朱子说:“有次序,无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见。只知止处,便是工夫。”[1]280从“知止”到“能得”有次序,但此次序并非工夫次序,工夫全在“知止”上,只要知止,后面的定、静、安、虑、得的效验也就自然出现。在黄榦的划分中,“知止至能得”是《大学》经一章的第二部分。与朱子不同的是,黄榦明确将此部分视为《大学》工夫之始终次序。
在黄榦这里,工夫问题与知行观密切相关。知与行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程颐明确提出“须是知了方行得”[10]187,“故人力行,先须要知”[10]187,区分知与行,并主张知先行后,同时他也指出“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10]187,将诚意与力行联系起来。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148,既区分了知与行,还从先后轻重来论知行。这里的行是道德实践,是指从洒扫应对进退到齐家治国平下的客观行为,而致知则被认为是对事物之理的认知。这种知行观过于强调知行在时间意义上的先后之别,容易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知而不行的知行不一问题。这一问题也是现实道德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理学家极力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对此,朱熹提出真知的概念,认为“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11]。这一回答看似解决了知行不一的问题,但是何谓真知、真知何以必能行等问题在朱熹那里并没有得到详细讨论。
朱子重要门人陈淳则公开否定知行先后说,提出知行无先后、知行交进而互相发的观点,认为“二者当齐头著力并做,不是截然为二事,先致知然后力行,只是一套底事。真能知则真能行”(《北溪大全集》四门卷十四)。也就是说,知行是一个整体,陈淳的观点蕴含了知行合一思想,这对朱熹知行二分的观点来看是一大进步,接近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但是陈淳并未进一步说明为何致知与力行是一事,知行何以齐头并做。相比之下,黄榦在新淦县学讲学时指出:“盖始之以致知,则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无所蔽;终之以力行,则天下之理浑然于吾身而所亏。知之不至,则如擿埴索涂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则如弊车羸马而有中道而废之患。”[2]780知行的目的是身心活动全然合乎天下之理,与理合一。其中知是理存于心,而行是理合于身。
在嘉定十二年(1219)所作的《知果州李兵部墓志铭》中,黄榦提出:“大学之道曰知与行,博文约礼,玉振金声,知而不至如眇斯视,行而不力如跛斯履。”[2]148大学之道曰知与行,而且强调知须至、行须力。
黄榦在解读《大学》时明确表达了一个颇有新意的知行观:
盖尝求其所以为学之纲领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学》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诚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 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者,知之事也;笃行者,行之事也。《书》之所谓“惟精惟一”,《易》之所谓“知崇礼卑”,《论语》之所谓“知及仁守”,《孟子》之所谓“始终条理”,无非始之以致知,终之以力行。盖始之以致知则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无所蔽,终之以力行则天下之理浑然于吾身而所亏。知之不至则如擿埴索涂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则如弊车羸马而有中道而废之患。然则有志于圣贤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无他道也。秦汉以来,一世之士不骛于词章则溺于训诂,不陷于功利则惑于异端,是固不足以语圣贤之学矣[2]780-781。
这是黄榦在新淦县学的讲学,当时共四讲,这是其中之一,也是从知与行的角度理解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一章。这里黄榦明确界定了知与行,并从知行观的角度贯通诸部经典和道统。他指出知行问题是为学纲领,物格知至是知之事,而意诚心正则是行之事。《中庸》中的学问思辨都是知之事,而笃行是行之事。知是意识当中的认知,行则包括诚意、正心等意志与情感活动,也包括日用之间的身体活动,也就是既包括内在的除了认知之外的主观心理活动,也包括外在的客观活动。而且,黄榦还指出格物致知为始之事,诚意正心修身等力行为终之事。这里的知为始、行为终看上去与朱子提倡的知先行后是一致的,但其实质还是不同。要讲清楚这点,需要了解黄榦如何理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点可以参考《大学经一章解》:
明明德于天下者,治国齐家,新民之事也。不曰新而曰明,新即明也,曰治曰齐,皆所以新之也。修身正心诚意,明明德之事也,曰修曰正曰诚,皆所以明之也。致知者,明德新民皆欲止于至善,然非知所止则无以得所止焉,故新民必本于明德,而明德又本于致知也,格物者,亦知不可以徒致,必事事物物皆有以穷极其理也,物格而后知至,物者,理之寓也,物之理无不穷则吾之知无不致矣。知无不至则是非昭晰而意无不诚矣,意者,心之发,意诚则心无不正矣。心者,身之主,心正则身无不修矣,身者,家之仪,身修则家无不齐矣。自家以及天下,则推此以及彼尔,曰齐曰治曰平,远近亲疏之势也。
此推言上文三节之意,言明德新民之目,知止能得之序,本末始终之有先后也[2]2。
所谓格物致知,应就事事物物皆能穷尽其理,只有穷尽所有事物之理,才可谓知致。但必须注意,这里穷尽的物之理并非今天科学所追求的客观知识,而是人们处事接物之理,是人们应对外在事事物物的道德原理与规范,即道德知识。因此,格物致知便是要求人们掌握为人处世的所有道德原理与规范,并推之极致,即至善。修身正心诚意是明明德之事,新民须以明德为本,而明德则又以致知为本,即格物致知为诚意、正心、修身之本。值得注意的是,黄榦这里对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修身关系的描述使用的是“本于”,而没有使用始与终的讲法。《大学》经文中明确讲“事有终始”,而此“事”是指《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如果注意到黄榦对知止的诠释,我们会发现,上文中“始之以致知”并非工夫实践的开端之意:
承上文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而欲得其所止则当先知其所止。谓一事一物必先研究其至善之所在,使此心晓然所谓知止也。事物所当止之地,既知之矣,则此心之中皆有一定不可易之理,所谓有定也。理既有定,事物未接则无所疑惑,湛然而静矣,所谓能静也。心既能静,则事物之来莫能动摇泰然而安矣,所谓能安也。能静能安,则酬酢万变思虑精审,所谓能虑也。能虑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理,所谓能得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于至善,至善之理又在于必至而不迁,故此一节但以止为言。曰知曰得,止之两端。定者,知所止之验,虑者,得所止之始。曰静曰安,则原于知而终于得,有必至不迁之意矣。注云志有定向则必至之意也。注云心不妄动,所处而安则不迁之意也[2]3-4。
这里,黄榦通过对朱熹《大学章句》的进一步疏通阐发了大学工夫实践的始终次序。知止即心中清楚一事一物的至善之理,也就是知道应对一事一物的最佳道德原理和规范。定乃是心中对理的确定;静乃未曾接物时的宁静状态;安则是指外来事物不能动摇我们的安定心境;虑即在任何情境下都能思虑精审,进而使得各种举止、容仪、行为都合乎天理,是为能得。由知止而进于意志之定向、情感之宁静、心境之安定、思虑之精审和举止、仪容、交际等外在客观行为之中理,从知止到能得是一个由知止而引发的一系列内在心理变化最后导致外在客观行为改变的过程,是一有始有终之事。“知止为始,能得为终。物既有本末,事既有终始,则学者行事处物必当知所先后,则交用其力而进为有序,则去道不远矣。”[2]2这一过程在黄榦看来,便是《大学》所言的工夫全过程,这里的始终是针对工夫的实际发生过程而言的,从知止开始,一直经历定、静、安、虑,最后到能得。
从知止到能得的次序和《大学》八目之始终次序当是不同。如上文所讲,以格物致知为始之事,诚意正心修身等力行为终之事。可以说,《大学》八目的始与终并非工夫实践的实际开始与结束,更多的应该是逻辑意义上的基础与完成。
当然,这种逻辑意义上的始终对于工夫展开的实际过程来说,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黄榦强调“盖始之以致知则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无所蔽,终之以力行则天下之理浑然于吾身而所亏。知之不至则如擿埴索涂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则如弊车羸马而有中道而废之患”[2]780-781。知与行并非相隔绝的两个不同阶段,而是有着内在关联,这种关联在于它们都统一于由知止开端的工夫实践当中。所谓知之始便是知止这一工夫开端。知止而后有定,“定者,知所止之验”,也就是说,知止包含了格物致知之意,但并非只是单纯的认知,其还内在地包含了必至的力行意志,是知与行的统一。由于缺乏对诚意正心这些情感意志活动的重视,故而常常发生知而不行的现象。这是后世对朱子以格物致知为工夫起始说的最大批评。黄榦虽然也持知行相分的观点,但这种相分更多的是理论逻辑上而非工夫实践。他以知止作为工夫实践的开端,从根本上避免了朱子思想中以格物致知为大学工夫开端可能导致知行分离不一的倾向,表达了知行合一的观点。
《大学》明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朱子讲“致知,知之始;诚意,行之始”[1]305,而且“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1]264。从行上讲诚意、正心、修身,诚意为行之始。黄榦也明确指出“意诚心正者,行之事也”[2]780,他对诚意的这种理解在王阳明那里得到了强化。王阳明为避免知行二分所带来的知而不行等问题,主张知行合一。王阳明说道:“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12]180他对行的界定和朱熹等人不同,“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13],于是好好色、恶恶臭等一类的意识活动也叫作行,“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见那恶臭时便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12]19。对好色的喜好、对恶臭的厌恶,既是一种情感,同时也是一种意志活动,是见闻时自然而然同时发动相应的好恶情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从整体上来看,这种发动是知行合一的。在这个意义上,知行不一的问题也便被消解。
四、《大学》的道统地位
朱子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1]249《大学》作为四书之一,在道统传承中意义重大。
黄榦认为,孔子在道统谱系的地位与创作《大学》密切相关:
至于夫子,既无位以行其道,于是博采古先帝王教人之法而著为《大学》之书,其言大学之道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而继之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亦不过于知与行而已[2]794。
孔子之前的传道人物都是圣王合一的,有学也有位,而自孔子开始,则圣王分离,他虽无王者之权位,但博采古先帝王教人之法而作《大学》,其言在知行关系,即知为始,行为终。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黄榦进一步指出:
至于夫子则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复礼。”其著《大学》则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无非数圣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统于周公者也。颜子得于博文约礼、克己复礼之言,曾子得之《大学》之义,故其亲受道统之传者如此……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2]10。
该篇文献通常被视为黄榦道统思想的集中表达,我们考证其创作时间大概是嘉定五年(1212)到嘉定七年(1214)十月之间,其中对孔子传道内容的阐发更为详细。《大学》是孔子吸收先圣教人之法而作,传之曾子。其思想主旨是孔子所得于周公之道,是颜曾乃至后来朱熹所得道统的重要内涵。朱熹之所以在道统谱系中影响巨大,原因之一是他精心为《大学》作注解,并被弟子传承。因此,《大学》在儒家道统中地位非常重要。
在《复李公晦书》中,黄榦还反复论证《大学》为四书之首,对“先《近思》而后四子”的观点予以辩驳。黄榦明确说道:“‘先《近思》而后四子’,却不见朱先生有此语,陈安卿所谓‘《近思》,四子之阶梯’,亦不知何所据而云。而且朱先生以《大学》为先者,特以为学之法,其条目纲领莫如此书耳,若《近思》则无所不载,不应在《大学》之先。至于首卷,则尝见先生说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后来觉得无头,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远思’也。”[2]602朱熹在关于读书次第的问题上,并没有对《近思录》有直接的安排,但由于陈淳记录的“《近思录》,四子之阶梯”[1]2629这条语录,《近思录》被视为学习朱子学的首要文本。然而,黄榦对此语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坚持朱子以《大学》为首要读物的立场,并且指出《近思录》本身存在不适合初学者的问题。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近思录》以及《近思录》与四书的关系问题成为朱子学发展早期的一个重要争议[14]。
黄榦还在《书晦庵先生正本大学》中对朱子修订《大学章句》及其最初出版情况有所介绍:
先生《大学》修改无虚日,诸生传录几数十本,诚意一章犹未终前三日所更定,既以语门人曰:“《大学》一书至是,始无憾矣。”今惟建阳后山蔡氏所刊为定本,潮倅廖君德明得之以授潮阳尉赵君师恕,赵君锓板县庠,且虑传本之多,无以取信后来,因属榦记之[2]736-737。
此文作于朱熹去世后一年,即嘉泰元年(1201)十一月,其明确了朱熹《大学章句》的最后定本以及早期的刻印传播状况。这也是朱子及其门人高度重视《大学》的一个直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