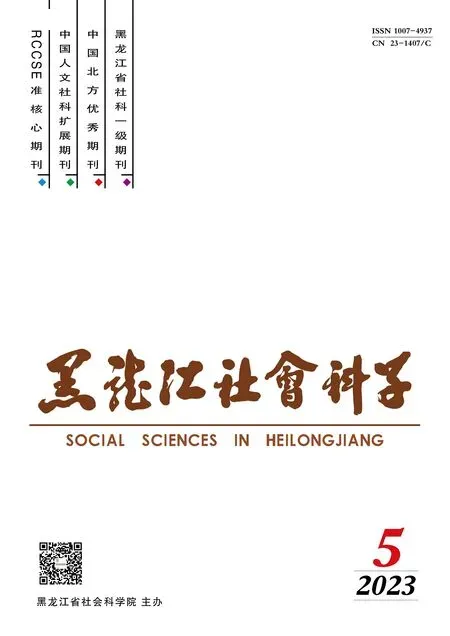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发微
张 国 庆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沈阳 110136)
辽天祚帝乾统元年(1101)《梁援墓志》及乾统七年《梁援妻张氏墓志》,1979年同时出土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大榆树堡乡四道叉子村一座辽墓中。《梁援墓志》志盖中间篆刻“大辽国故中书相梁公墓志铭”12字,《梁援妻张氏墓志》志盖中间篆刻“大辽故安定梁中令赵国夫人墓志铭序”16字。志文显示,梁援病逝于乾统元年八月初五,享年68岁。古人年龄以虚岁计,依此前推,梁援当生于辽兴宗重熙三年(1034)。梁援妻张氏则病逝于乾统七年三月初二,享年67岁。梁援夫妇主要生活在辽中后期的兴宗和道宗朝。
梁氏祖籍定州,梁援四世祖梁文规,五代时官至吏部尚书,后寓居燕台(又名黄金台,今河北易县易水南)。辽天显年间,太宗耶律德光兴兵助石敬瑭为后晋皇帝,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与辽,梁氏遂归于契丹,后北上定居于辽西医巫闾山脚下。
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梁援荣登进士甲科,步入仕途,先后在地方和朝中任职,最终结衔为“大辽故经邦忠亮同德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上柱国、赵国公,食邑一万户、食实封一千户,赠侍中,谥号忠懿”,是为道宗朝重臣之一。“母以子贵,妻以夫荣。”梁援妻张氏,藉夫荫终封赵国夫人。
梁援《辽史》无传,然其死后孟初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内容丰富翔实、情节细腻生动,可补《辽史》之缺漏。譬如梁援曾祖梁廷嗣奏请、景宗皇帝诏赐医巫闾山脚下周峪为梁氏家族新茔所;梁援青幼之年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后伴读昭怀太子,与权臣耶律乙辛斗争,在中京城及兴中府主持与崇佛活动相关联的地方行政事务;等等。梁援妻张氏墓志铭的作者为杨丘文,志文除记其生平及夫、子相关事迹外,还重点讲述了张氏曾多次被皇帝“诰封”的过程,对了解辽朝“外命妇”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此前,已有学者就梁援墓志所记辽朝史事做过考释[1],但仍有可以讨论之处。故笔者不揣浅陋,拟结合相关石刻资料、传世文献及考古实物,对梁、张二志中所涉辽朝之史事前人讨论未尽之处,溯源求真、发微考实,或许对充分利用出土石刻文字拓展辽朝历史研究之范畴有所裨益。
一、宫籍诏除,本贯改隶:降(归)辽汉人身份转化的终极标志
《梁援墓志》载:
国家属在俊孝,同镇百僚。暨(寿昌)七年正月,孝文皇帝(辽道宗)登遐,遂充玄宫都部署,及撰上谥册文哀敬之,诚可谓极矣!山陵毕,诏免本属之宫籍,移隶于中都大定县,敕格余人不以为例,示特宠也[2]522。
上已述及,梁氏家族祖籍定州,后寓居燕台。梁援高祖梁文规于太宗朝归辽北上,梁援曾祖梁廷嗣于景宗朝定居于医巫闾山脚下。但归辽的梁氏族人,何者何时以何身份被没入“宫籍”,志文并没有交代。
所谓“宫籍”,应即“斡鲁朵”宫户之籍。《辽史》卷31《营卫志上》云:“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3]361-362这里的“籍户口”,应该是指将隶属于斡鲁朵(宫卫)的人户登记入册。据文献记载,辽朝隶“宫籍”之宫户,来源大致有四:一是契丹皇帝、大臣外出征伐俘获的中原汉民,以及灭渤海国后的渤海遗民等;二是籍没的本国罪犯家属;三是随契丹后妃陪嫁到皇家的媵臣;四是主动附籍的少数游牧部族。由此可见,隶“宫籍”者,大多身份卑微、地位低下,属于从事劳动生产的奴隶性质。但梁氏家族似乎例外。据《梁援墓志》记载,自梁援高祖梁文规、曾祖梁廷嗣、祖父梁延敬、父亲梁仲方,直至梁援及其子孙,梁氏家族几代人均在辽国朝廷或地方为官[梁文规官至“防御使”,梁廷嗣官至“宁远军节度使”,梁延敬为“内供奉班祗候”,梁仲方官至“宥州刺史”(应为遥授),梁援官至“知枢密院事”,梁援长子梁庆先“权应奉阁下文字”,梁援次子梁庆元为“閤门通事舍人”][2]520、522,属于典型的官宦世家,既不身份卑微,也不地位低下。也就是说,梁氏族人入辽定居,隶属“宫籍”后,似乎并没有对他们入仕为官及社会地位的提升等造成多大影响。
笔者分析,隶“宫籍”的梁氏家族,应属于斡鲁朵中比较特殊的“著帐户”。辽朝皇帝四时捺钵,帝后的行居车帐被称为“宫帐”,身边的服侍人员,如仆役、侍从、警卫等人户即为著帐户。组成著帐户的人员,大多亦为被籍没的犯罪官员贵族家属。《辽史》卷31《营卫志上》云:“著帐户:本诸斡鲁朵(户)析出,及诸罪没入者。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亲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3]371但著帐户中还有另外一类人,即契丹后妃入宫时的陪嫁者——媵臣。虽然媵臣中的多数仍属帝后身边从事劳作的家奴,身份与一般宫户无异,但李锡厚先生认为,媵臣著帐户中有一部分人,因与契丹皇帝及后妃们的关系特殊,“多夤缘获得权势、地位”,“成为宫卫中的权贵”[4](笔者赞同李先生的观点。但李先生举兴宗和道宗朝权臣耶律乙辛为例,言其“陪从入宫”,因得帝后亲幸,累获升迁,似不妥。耶律乙辛为契丹“五院部人”,其身份并非有“宫籍”的宫户或著帐户)。笔者以为,梁氏家族即属此类。据《梁援墓志》记载分析,穆宗朝时青幼之年的梁廷嗣可能已入东宫,成为皇储耶律璟的伴读或伴射。后来耶律璟即位,是为辽景宗。因此前二人之特殊关系,景宗皇帝不仅提拔梁廷嗣为节度使,还赐其伴侣、宅地、茔园。《梁援墓志》载:“(梁文规)有二子,次曰廷嗣,宰范阳县。景宗登极,有龙潜之旧,诏养母夫人孟氏为之妻,并以大水泺之侧地四十里,契丹人凡七户皆赐之。特授贵德州节度副使。尝以天授穆宗所赐衣带宝玉器币以进,价直巨万。及奏对称旨,拜宁远军节度使,恩赉甚厚。奏乞医巫闾山之近地永为别业,上嘉其内徙,命即赐之。诏奉先军节度使崔匡道为营寿藏,以监周峪为茔所,仍用居民三十户租赋赡给之。且以高阳旧茔时有水害,远奉輤车来葬于新地,其诸近属仍隶故乡。”[2]520
但隶“宫籍”者,毕竟在世俗观念及户籍法规等方面被视为或划入低贱之列,故而即便身居高职、富贵无比,仍内心时时感到矮人三分。因而,才有一朝重臣梁援在极力操办已故道宗皇帝丧礼之后,被新即位的天祚皇帝“诏免本属之宫籍,移隶于中都大定县,敕格余人不以为例,示特宠也”之结果。
辽朝各族生民均有固定之户籍,除隶“宫籍”外,还有或隶某州县,或隶某部族者,等等。梁援家族被免除“宫籍”之后,“移隶于中都大定县”。大定县为辽中京大定府的附郭县。从此,梁援家族便隶籍“中都大定县”。检索《辽史》,类似梁援出“宫籍”后隶属州县者还有汉官姚景行。《辽史》卷96《姚景行传》云:“姚景行,始名景禧。祖汉英,本周将,应历初来聘,用敌国礼,帝怒,留之,隶汉人宫分。及景行既贵,始出籍,贯兴中县。”[3]1402-1403兴中县,为兴中府之附郭县。
中原汉人被俘降辽或其他原因归辽而隶“宫籍”,数代之后,族中有人官高爵显、军功政绩特别突出,亦会如梁援家族那样得到当朝皇帝恩赐,被免除“宫籍”,籍属改隶,从而身份、地位彻底改变。其中,太祖至圣宗朝的韩知古—韩德让一系之韩氏家族,便属显例。
韩知古—韩德让一系韩氏家族原籍蓟州玉田,即今河北玉田。韩知古年仅6岁便被南下攻掠中原的契丹铁骑俘掠至塞外契丹腹地,成为契丹贵族的家奴(《辽史》卷74《韩知古传》云:“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3]1233。不久,淳钦皇后述律平与太祖耶律阿保机成婚,韩知古作为述律平的陪嫁媵臣,一同来到了阿保机家(《辽史》卷74《韩知古传》:“后来嫔,知古从焉”)[3]1233。韩知古的媵臣身份,在其后世子孙的墓志中也得到了印证。如兴宗重熙六年《韩橁墓志》即云:“我圣元皇帝凤翔松漠,虎视蓟丘。获桑野之媵臣,建柳城之冢社。威宣十乘,化被一隅。”[2]203“圣元皇帝”,即辽太祖;“桑野媵臣”,指的就是韩知古。韩知古有个精通医学的儿子韩匡嗣,在韩匡嗣的引荐之下,阿保机专门召见了韩知古,通过交谈,终于识得有用人才。于是韩知古逐渐被委以重任,才能得以发挥,为阿保机“变家为国”,建立并巩固辽朝这一新生政权,起到了重大作用(《辽史》卷74《韩知古传》:“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因间言。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顷之,拜左仆射,与康墨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3]1233。
大概在韩知古来到阿保机身边的某一时期,韩知古便以媵臣的身份,始隶于阿保机“算斡鲁朵”(弘义宫)之“宫籍”。与梁援梁氏家族情况类似,韩知古—韩德让一系韩氏家族虽然也隶属“宫籍”,法律上属于低贱的家奴身份,但实际上却没有影响其族人为官及迁升的进程。从太祖朝到圣宗朝,韩知古—韩匡嗣—韩德让祖孙三代,官职爵位一路迁升:韩知古从彰武军节度使,经左仆射,至中书令;韩匡嗣从太祖庙详稳(二仪殿将军),经始平军节度使、上京留守(临潢尹)、南(燕)京留守、卢龙军节度使、晋昌军节度使等,至西南路招讨使,还先后被赐封燕王、秦王,拜匡运协赞功臣;韩德让从东头承(供)奉官、枢密院通事、上京皇城使、彰德军节度使,经辽兴军节度使、南院枢密使、政事令等,至北府宰相、枢密使、监修国史、大丞相,还先后被赐封楚王、齐王,拜保节功臣、守正功臣[《辽史》卷74《韩知古传》《韩匡嗣传》、卷82《耶律隆运传》[3];圣宗统和三年(985)《韩匡嗣墓志》、统和二十九年《韩德让墓志》]。
而韩德让所取得的非凡军功政绩,则是圣宗皇帝和承天太后诏除韩氏家族“宫籍”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韩德让的主要军功政绩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与几位契丹大臣一起,协助承天太后辅佐年幼的圣宗皇帝承继大统,确保辽朝皇权顺利交接,防止了皇室内乱的发生;其二,统帅辽军,攻伐北宋,立有战功;其三,促成辽宋停战结盟,努力维护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其四,推进吏治改革;其五,发展社会经济。
鉴于大丞相韩德让卓越的军功政绩,统和二十三年,圣宗皇帝颁诏,赐韩德让一支韩氏族人免除“宫籍”。至此,韩氏族人实现了身份由贱到贵的彻底转变。《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载:“(韩德让)徙王晋,赐姓,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乃改赐今名,位亲王上,赐田宅及陪葬地”[3]1290;《韩德让墓志》亦云:“运洽太平,功高难赏。将何殊礼,用表徽章。诏于昌黎之世家,除其本贯;赐以耶律之国姓,冠于宗盟。”[5]
所谓“横帐”,是指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一系子孙为核心的契丹皇族之帐。《辽史》卷116《国语解》云:“德祖(阿保机之父)族属号三父房,称横帐,宗室之尤贵者。”[3]1538(关于横帐的具体含义,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可参看陈晓伟的最新研究[6])韩德让出“宫籍”后,户贯没有如梁援、姚景行那样改隶州县,而是隶属横帐,足证圣宗皇帝和承天太后对其极为看重与极度倚重。诚如《契丹国志》卷18《耶律隆运传》所云:“隆运(韩德让)孜孜奉国,知无不为,忠孝至诚,出于天性。帝以隆运辅翼功前后少比,乃赐铁券誓文,躬自亲书,斋戒焚香,于北斗星下读之,宣示番汉诸臣。又以隆运一族附籍横帐,列于景宗庙位。”[7]
韩德让出“宫籍”、隶横帐,身份彻底改变,社会地位也升达巅峰。圣宗太平七年(1027)《耶律遂正墓志》载:“隆运,官至大丞相,以位极人臣,上赐国姓,兼连御署,故与天子同姓耶律”[8]68;《韩德让墓志》云:“预公朝而免常朝,邻御座而设独座。不名不拜,绝席绝班。虽宠遇优隆,曾无比拟;而名称赫焕,别有褒崇。改封晋国王,加食邑二千户,食实封壹千户,仍别赐经天纬地匡时致主霸国功臣。……今皇上念虽天子必有长也,言有兄也,益重元昆,永为冢宰,乃连御讳,赐名隆运。”[5]
韩德让身份、地位彻底改变,还表现在仿契丹帝后斡鲁朵的“文中王府”的组建。据《韩德让墓志》记载,“文忠王”是韩德让死后所得之谥号,所以文忠王府应为韩德让死后所建。《辽史》卷31《营卫志上》载:“大丞相晋国王耶律隆运,本韩氏,名德让。以功赐国姓,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赠尚书令,谥文忠。无子,以皇族魏王贴不子耶鲁为嗣,早卒;天祚皇帝又以皇子敖鲁斡继之。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3]370有辽一代,辽朝皇帝、个别皇太后及个别皇太弟共建有12个斡鲁朵,算上韩德让的文忠王府,共计13个宫卫。
韩德让去世后,韩氏子孙大多仍在朝廷或地方为官。圣宗开泰六年(1017)《韩相墓志》说,韩氏族人“代生贤相,世出名王,建带河砺岳之功,居列鼎累茵之贵”[2]151;兴宗重熙六年《韩橁墓志》亦载,韩氏家族“谱系于国姓,其余戚属族人,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2]204。
二、母以子贵,妻以夫荣:官宦之家女性诰封命妇的基本条件
《梁援墓志》载:
夫人清河张氏,职方郎中靖之女,纯淑有礼法,累封赵国夫人。先是皇太后赐之冠帔,(张氏)以齐国夫人(梁援母亲)未有是命,固以为让。皇太后并赐之[2]522。
《梁援妻张氏墓志》载:
国夫人(张氏)初进封清河县君,次封郡君。时蒙星使至宅,特赐冠帔。(张氏)备礼而告曰:尊婆荥阳太夫人,未经恩赐,让而不纳。使回具此敷奏,寻赐二道,益旌其孝义。后加清河郡夫人,续授申国夫人,次封韩国夫人,迁至赵国夫人。皆以属先臣之入相,承大国以疏封。不逾二年,三更国号[2]567。
由梁援暨妻张氏墓志可知,辽朝官员之妻的封号,一般是随着丈夫封号的变化而得以累进。道宗寿昌六年(1100)夏,梁援赐封韩国公,同年冬十一月,又进封赵国公;梁援妻张氏累封的外命妇名号依次即为:清河县君—清河郡君—清河郡夫人—申国夫人—韩国夫人—赵国夫人。
中国古代皇室女性成员及朝野品官之家女子有封号者,被称为“命妇”。有学者考察,命妇起源于春秋时期,至唐代始形成制度[9]。而命妇又有“内命妇”和“外命妇”之分。唐人杜佑《通典·职官典》注云:“皇帝妃嫔及太子良娣以下为内命妇;公主及王妃以下为外命妇。”唐统天先生认为,辽朝内命妇始于太祖朝,嫔妃有贵妃、惠妃、德妃等封号,女官有尚寝、尚服、尚功等职位;外命妇始于太宗朝,有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及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等系列封号[10]。此外,辽代石刻文字显示,某些被封王爵的官员之妻诰封为“某国王妃”,亦应属于外命妇之列。
检索辽代石刻文字,尤其是女性墓志,笔者发现,辽朝官宦之家女子受封为外命妇,具备“女贞”“妇德”“母仪”[道宗大安七年(1091)《萧乌卢本娘子墓志》][8]205-206是基本前提。而三者之中,妇德又被格外看重。如兴宗朝枢密都丞旨王泽的妻子、陇西郡夫人(应是死后追赠)李氏。兴宗重熙十四年《王泽妻李氏墓志》云:“(李氏)厚夫妇之和,无返掌跬步之闲,赞有□颜;奉舅姑之孝,虽烦暑凛寒之极,略无怠色。洎予登贡版,彩仕缨,生贵人,茂华族,盖夫人内助之所致也。属重熙五祀,翠华临幸于雄燕。今主上授予带□车之资,掌都宣之职,特封陇西郡君,从夫荫也。赐以冠帔,旌妇礼也。”[2]240又如圣宗朝太保耶律污斡里的第二任妻子、萧氏夫人。圣宗统和二十七年《萧氏夫人墓志》载:“夫人之德兼令淑,志在肃雍。孟母许其贤明,卫诗高其圣善。才期有幸,契鱼水以长欢;如何不臧,悲梧桐之半谢。良人既殒,何痛如之,久处孀居,但遵昼哭。昭圣皇帝以闺仪备著,女德迥全,不将同穴之心,别易从人之志,可宜封册,式同岁寒,乃封箫(萧)氏夫人。不恃贵以骄人,不以富而傲物;身久宁而心愈谨,名渐高而貌益恭。”[8]47
辽朝官员之妻、母能诰封为外命妇,除了自身必备的妇德之外,还必须藉夫、子之贵,承荫才能得以“疏封”,即所谓“母以子贵,妻以夫荣”。唐宋时期,官员之妻、母诰封为不同等第和不同名号的外命妇,所依据的条件就是她们的丈夫或儿子的品级职爵。尽管传世文献及石刻文字均不载辽朝官员之品级,但石刻文字显示,辽朝官员之妻、母的外命妇名号常常随着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官爵职衔的迁升而迁升。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辽朝官员抑或有品级,概为文献及石刻所漏载。
第一,妻子诰封外命妇,均是藉夫之贵。如圣宗朝永兴宫汉儿渤海都部署耿延毅之妻、漆水郡君耶律氏。圣宗统和三十年《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载:“妇道既彰,皇恩乃降。于统和二十五年,内授漆水郡君。丝纶遽捧,弥崇命妇之荣;爵号惟新,大显从夫之贵。”[2]143又如圣宗朝中书令萧谐领之妻、秦国太妃耶律氏。兴宗重熙十四年《秦国太妃墓志》云:“妃(耶律氏)始封吴越国太夫人,从王(萧谐领)爵也。俄属鼎驾登遐,传归众嫡,璇宫正位,协侑基图。载惟凤极之怀,爰锡迨先之命。重熙癸酉岁,王追册为魏王,妃册命为魏国太妃。密印泥书,贲于幽隧,褕衣绘羽,章厥王门。乙亥岁,上两殿之徽名,覃九瀛之庆泽。王再追册为晋国王,妃进册为齐国太妃。仁孝皇帝、崇圣皇后外孙、孙也。仁慈继体,孝敬因心。尊亲则尚邦媛之贤,燕齿则从家人之礼。聿遵加慧,益用慰心。壬午岁,进册为秦国太妃。”[8]90-91可见,耶律氏前几个封号均属藉夫之贵,只是最后一个应为帝后之恩赐。
第二,母及祖母诰封外命妇,必为承子孙之荫。如道宗朝大理正孟有孚的母亲、清河县太君张氏。道宗寿昌二年《孟有孚墓志》载:“母张氏,性淑善,有礼法。从长子荫,封清河县太君。”[2]470又如兴宗朝侍御史李位的母亲、扶风县太君马氏。兴宗重熙十三年《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载:“(李继成)夫人即宣政殿学士、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马得臣之长女。早承姆训,□丝克擅于女工;自适吾门,蘋藻颇勤于妇道。一自良匹,早亡诸孤。并恒深鞠勉,□遣进修。趋庭虽失于严君,择邻幸凭于慈母。学惟时习,道乃日彰,果致荣名,得谐禄养。重熙十一祀,仲子秩峻亚列,政布外台,授将作少监、知北安州军州事。次岁,以国家加上徽称,普均鸿渥,爰降丝纶之命,特疏汤沐之封。于春正月,母因子贵,夫人特封扶风县太君。”[8]88
辽朝官员的妻、母,藉夫、子之贵,承荫而疏封为外命妇,大多是她们在世之时。但也有部分女性在她们去世之后,因子孙为官显贵,被追赠为外命妇。如张俭是圣宗、兴宗两朝重臣,他已故的祖母李氏,便被追“赠赵国太夫人”;已故的母亲刘氏,“累赠至燕国太夫人”(兴宗重熙二十二年《张俭墓志》)[2]266。又如天祚帝朝的西头供奉官姚璹母亲曹氏,死后承长子姚球之荫而被“追封谯国县太君”。天祚帝天庆七年(1117)《姚璹墓志》载:“公有昆弟二人,兄长讳球,起复西上閤门使、陇州团练使,今充南宋正旦国信副使,皇朝谓之重委”;“母曹氏,追封谯国县太君,从兄(姚璹兄姚球)荫也。”[2]665
石刻文字显示,在辽朝官员之妻、母诰封为外命妇的诸多名号中,有一种比较特殊,即契丹语汉译之名号。如“迤逦免”,圣宗太平七年《耿知新墓志》载:“大横帐、燕京留守、燕王、移镇南王、累赠陈国王,乃外祖父也。封陈国迤逦免夫人,乃外祖母也。”[2]185又“乙失娩”,圣宗统和二十六年《耶律元宁墓志》云:“夫人先公三年而亡,即西南路招讨都监、太尉之长女,封乙失娩,从夫贵也。始女于室,以孝敬奉父母;暨妇于家,以柔顺事舅姑。”[8]44又“乙林免”,兴宗重熙十年《北大王墓志》载:“(北大王)又娶得索胡驸马、袅胡公主孙,奚王、西南面都招讨大王、何你乙林免之小女中哥。贞顺成风,言容作范。六年内加北大王,(中哥)封为乙林免。”[2]223此外,道宗咸雍五年(1069)《萧闛妻耶律骨欲迷已墓志》中见“乙里娩”[8]126。刘凤翥先生依据《辽史》卷116《国语解》中有“阿点夷离的:阿点,贵称;夷离的,大臣夫人之称”[3]1535之语,认为辽代石刻文字中出现的“迤逦免”“乙林免”等,应为契丹语“夫人”之汉译[11]。可见,“迤逦免”“乙失娩”“乙林免”“乙里娩”及“夷离的”等,为音同(近)字不同的契丹语外命妇夫人之封号。
三、既恋红尘,又慕净土:信佛居士丧葬活动中的佛、俗双重仪轨
《梁援墓志》载:
方将从容庙朝,图经国之效,命数弗移,奄遘薨殁,时享年六十有八矣!当病亟之夕,仆隶间如闻有清乐声,岂神灵所适者获乐地耶?遂以其年十月日葬于先茔之次[2]522。
《梁援妻张氏墓志》载:
因寝疾,至乾统七年三月二日如眠薨于白霫私第。左右善邻皆聆空中仙乐之音,次宵一尼支观想中,于西方相遇,其亲识数人梦寐颇同。以当年四月十七日癸酉,祔葬于闾岳景宗所赐坟地,从中书令之故茔也[2]566。
以上志文显示,梁援和他的妻子张氏去世前后,均有与佛教相关的“灵异现象”出现。而从志文记载亦可知,梁援及其家人均笃信佛教。《梁援墓志》载梁援出生前夕,其母曾“梦异僧乘白云自空而下,化为彩凤入于怀”;道宗大安“十年(应为四年),(梁援)起复兴中尹。百里内野蚕成茧,驰驿以进,诏充御服绵续及贯念珠以赐诸沙门”;梁援在任兴中尹及上京留守期间,“境内迭降甘露,驿进行在,召建道场十昼夜于京师”[2]520-521;等等。《梁援妻张氏墓志》亦载,梁援和张氏有一孙女名曰“引璋,自小不留髻发,行解双美,性相兼修,年十五赐紫,加慈惠大德”[2]567。因梁援夫妇及其子孙大都信佛、崇佛,因而志文中才有梁援夫妇去世后,在佛教“清乐”“仙乐”的引导之下,“往生竺域”[2]568之说。
梁援夫妇应属于信佛居士。既留恋今世红尘,亦向往来生净土,应是有辽一代所有信佛居士们的心理诉求及行为轨迹所在。体现在他们去世后的丧葬活动方面,便是采用看似矛盾的佛、俗并举的双轨仪制。
第一,信佛居士去世后,在家人为其举办的丧事活动中有不少与佛教相关的内容,以此昭显逝者家属希望已故亲人能早日往生佛教净土。
譬如采用火葬。在佛教里,火葬被称为“荼毗”,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寂灭后,所取葬式即为荼毗。道宗大安五年《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云:“古之葬者弗封树,虑其伤心,若掩骼埋胔之类,欲人之弗得见也。而后世朴散,转加乎文,遂有贵贱丘圹高厚之制。及佛教来,又变其饬终归全之道,皆从火化,使中国送往,一类烧羌。至收余烬为浮图,令人瞻仰,不复顾归土及泉之义。”[2]413辽朝信佛居士逝后火葬,石刻文字多有记载。如道宗大康四年(1078)《秦德昌墓志》载:“咸雍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秦德昌)端坐屈指念佛,捐馆于榆州公署,享寿七十八。垂终之日,于黑雾中有霹雳声西北而去,兜率之兆也。焚殓时,殊无秽气,舌牙与颌,确然不灰,盖平生持《莲经》不谈他短之致也。”[8]167“兜率”,指佛教弥勒净土。又如天祚帝天庆六年《张世卿墓志》载:“(张世卿)天庆六年丙申岁闰正月四日遘疾而终,享年七十有四。遵命依西天荼毗,礼毕,得头骨与舌,宛然不灰,盖一生积善之感也。”[2]656
又如延请寺院僧人诵经念佛,超度死者亡灵。比较典型者,当属道宗朝亡故的率府副率萧闛及妻耶律骨欲迷已的丧事活动。耶律骨欲迷已病逝于道宗咸雍五年(1069)二月二十五日,年仅24岁。咸雍五年《萧闛妻耶律骨欲迷已墓志》载:耶律骨欲迷已去世后,“遂归全于白霫之壤,至蒙谷山于罔极寺前,具阴仪而权厝之。以当年冬十月二十八日,袝祖姑秦晋国大长公主寝园之午位,圹其吉地,襚而藏焉,礼也。自口玉之后,凡丧轊所抵之处,至寿堂横钥已来,而父氏母氏,暨于同气齐体,诸姑二妹,例以发箱金,奉椟币,日饭苾蒭不减数十人;净设道场,精诵神咒,分阅贝典,仅逾半稔,登登不绝,引卷还帙,难可胜计,成就种种之功德,率为资荐。仍于窀穸之前,匠梵幢一所,庶期沾一尘,覆一影,或往生于慈氏天宫,或托质于弥陀佛国,愿满果圆,准如影响”[8]126-127。妻子逝后第二年,年仅28岁的萧闛也因病故去。咸雍七年《萧闛墓志》云:“无何!咸雍六年孟夏之月二十八日,寝疾,殁于徽郡甲第之园囿,春秋二十有八。想其谓尘世之厌居,望天宫之遽返,以次岁夏四月十五日癸时,归葬于白霫香台山罔极寺之离位,故燕王、秦晋国大长公主先茔,合袝先娘子耶律氏之故穴。”[8]136在萧闛的丧事活动中,弟弟萧阐及儿子萧勃特钵里亦延请附近寺院的僧人诵经念佛。咸雍七年《办佛事碑》虽已残破,但仍能从中大致看出此次佛教道场的宏大与隆重:“将军(萧闛)倾逝,自来资荐去灵功德,具下项开(下残)生天道场一个月,斋僧四百人。开梵(下残)日,持《陀罗尼经》并诸真言二万一千(下残)佛名七万□。已上功德,男勃特钵里(下残)僧五百五十人,看读经、律、论一千四百六十部(下残)百六十五帙。次道场三昼夜,斋僧四十人(下残)三卷计七遍,持陀罗尼诸真言一百八十六(下残)次陀罗尼诸真言并佛菩萨名号计一百七十(下残)一千八百四十遍。已以功德,弟阐疏。道场七昼夜,斋僧九十八人,持诵诸经四帙计六十遍,持《大悲心》四十九遍,诸佛名号三万□。已上功德,大王、乙里娩疏。咸雍七年岁次庚亥四月丙辰朔十五日癸时记。”[8]134
再如随葬与佛教相关的各种物品等,以昭示逝者生前笃信佛教,并冀望其早日往生净土。如在墓中随葬或于坟旁树立密宗陀罗尼经幢。圣宗和兴宗朝重臣张俭之子张嗣甫于太平九年夭折,年仅14岁,其坟旁即立有经幢。兴宗重熙五年《张嗣甫墓志》载:“爰从龟卜,用叶牛眠。乃闭玄堂,乃建灵塔。影覆尘沾,愿往生于净土;天长地久,永安厝于佳城。以重熙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葬于燕京幽都县礼贤乡胡村里。”[2]202这里的“灵塔”即为密宗之“坟幢”。又如在葬具上书写密宗陀罗尼真言。有辽一代,一些信佛居士病逝后,家人常在其木棺顶部、棺盖四刹等处墨书密宗陀罗尼经咒,希冀逝者早日逃离地狱之苦,最终往生佛国净土。位于今河北张家口宣化下八里村的辽末崇佛世家张氏家族墓如张匡正墓、张文藻墓、张世本墓、张世卿墓、张世古墓中,均发现了于棺盖及棺壁四周墨书汉、梵两种文字的密宗陀罗尼经咒及其记言[12]24、83、132、199、246。又如在墓室中随葬各种佛教物件。“迦陵频伽”为佛教传说中象征吉祥的妙音鸟,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南郊辽人赵德均墓中即发现了一件铜制迦陵频伽,呈人首鸟身飞翔之状[13]。
考古资料显示,辽朝信佛居士墓的墓道、墓室等处壁画亦蕴含有佛教文化之内容。如对墓主生前备经、备茶及诵经、念佛活动场景的描绘,河北宣化辽末张世卿墓的后室东壁绘有一幅《备经、备茶图》,反映的是两个侍吏为墓主人诵经准备经书和茶饮的场面[12]207-208。又如对供养佛教“三宝”(佛、法、僧)场景的描绘,河北宣化辽末韩师训墓室壁画《备经图》中,置于小几上的四卷佛经,反映的就是典型的“法供养”场景[14]。
第二,丧事活动中还有与佛教仪轨并行、看似相互矛盾的各类俗事行为。辽朝信佛居士的崇佛、信佛活动,一般均在自家或府衙进行,大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尘世生活。特别是一些男性官员,他们的一生,除了信佛、崇佛之外,还要求取功名,入仕为官;正常婚配,娶妻生子;获得财富,饮酒食肉(部分居士于斋戒日吃素,又长斋者除外);等等。生前红尘俗世的千般美好,让他们在临终前有着无限的留恋与不舍。古人奉死若生,《荀子·礼论》云:“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齐东方先生亦言:“古人往往把死者看成是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在丧葬活动中试图通过想象重建死者生前的生活,或企盼死者享受不曾拥有的奢侈,这给墓葬带来一些期望和神秘。”[15]有辽一代,为使逝者能在地下继续“享受生活”,他们的家人遂想方设法在墓室内外为其营造“生活场景”。
笔者仍以辽代后期崇佛、信佛的西京归化州张氏和韩氏家族丧事活动为例。为使逝者有一个良好的地下“生活环境”,家人在为其营造墓地时,首先要考虑阴宅的“风水”,即选择所谓的“牛眠之地”。欧阳询《艺文类聚》卷40所引张衡《冢赋》,曾描绘时人想象中逝者理想的地下生活环境为:“载舆载步,地势是观。隆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乃心斯安。尔乃堕巍山,平险陆,刊菆林,凿磐石,起峻垄,构大椁,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坛,罗竹籓其域。系以修隧,洽以沟渎。曲折相连,迤靡相属。乃树灵木,灵木戎戎。繁霜峨峨,匪雕匪琢。周旋顾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绳,正之以日。有觉其材,以构玄室。奕奕将将,崇栋广宇。在冬不凉,在夏不暑。祭祀以居,神明是处。修隧之际,亦有掖门。掖门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车之道,交通旧馆。寒渊虑弘,存不忘亡。”而位于今河北宣化下八里村东北的辽末张氏家族墓地,附近地势略高,北面是山,山峦连绵,岗阜错落,犹如两翼,合环回抱;其中有两座前后错列的山峰,据出土的张世卿等人墓志记载,此二峰在辽时被称为“兴福山”和“七宝山”;山前为一黄土坡,北高南低,缓缓下落:“墓群即坐落在缓坡的斜面上,背靠兴福、七宝二山,南望洋河,符合古人选择墓地的条件。”[12]3-4
辽朝信佛居士逝后入葬,除了随葬与佛教相关的物品外,还有大量生前日常生活所用的物品,以便他们在“地下生活”中继续使用。譬如各种陶器和瓷器。河北宣化张匡正墓中即出土有随葬的各类陶器,既有冥器,也有实用器,如陶执壶、陶盆、陶碗等;随葬的瓷器则有三彩器、黄绿釉器和白瓷器,如瓷壶、瓷碗、瓷碟等[12]42-46。其他则如:随葬的铁器,既有生产工具,如铁锄、铁锹等,也有生活用具,如铁剪、铁炉等[12]115;随葬的木器,主要有木桌、木椅、木衣架等生活用具[12]59-61;随葬的骨器,常见的有骨梳、骨簪等,如张匡正墓出土有骨梳,韩师训墓出土有骨簪[12]62-63、157、304;随葬的铜器,以铜镜为多,如张匡正墓即出土有铜镜,而张文藻墓出土有铜耳坠,张世卿墓出土有铜钵[12]48、221-222。此外,为使已故亲人仍有各种美味“享用”,墓中还随葬了大量食物,如张文藻墓中即出土了多种植物类食材及食物:保存在陶仓中的粟、盛于黄釉碗中的板栗,以及肉豆蔻、秋子梨、葡萄、枣等[12]122-123。
通过以上对辽朝信佛居士丧事活动中佛、俗双轨仪制的阐述,可见信佛居士既眷恋今生的俗世生活,又想往来世的佛教净土。这种现象看似存在矛盾,其实并不相悖。十年前,笔者曾关注到某些辽朝官员集佛教、儒学思想于一身之现象,撰文探讨了辽朝佛教、儒学的关系。笔者认为,“儒学主张为人要做到入世进取,仁义忠孝;佛教则要求信众出世解脱,行善乐施。在辽朝儒学与佛教相融互补的关系层面,这两种人生追求既有相似与重合、又有较大差异的要素,时常出现在同一人身上,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有人既崇儒——受儒家学说熏陶而入仕,修身齐家、理政治国均严守儒学之准则,在职期间,努力做到清廉忠正,勤政爱民;与此同时,该人又崇佛——于公事之暇诵经念佛,慈悲利他,在其多元的人生中,寻觅另一种净逸与恬淡”[16]。此论或可作为所有既恋红尘、又慕净土的辽朝信佛居士们心理及行为的合理诠释。
余 论
仔细钩沉和认真爬梳出土石刻文字资料,可以发现一些传世历史文献鲜见或漏载的辽朝史事细微之处,用为研究对象,或可拓展辽朝历史问题研究之范畴。譬如本文所论之辽朝官员脱“宫籍”后对其身份地位彻底转变的影响、辽朝官员母妻诰封为命妇的基本条件、“红尘”与“净土”视域下辽朝佛教居士丧葬活动中的双重仪轨,以及此前笔者撰写的《辽〈秦德昌墓志〉“记事”发覆》(待刊)、《辽〈韩橁墓志〉“记事”发微》二文所涉墓志铭由谁撰写更真实可信、外事交涉中“非礼”与“遵规”的辩证施用、皇帝“遥授”官员节镇使职虚衔的真实目的、地理评价对志主军功政绩的影响等等。
但“问题”的发现并不等于“文章题目”的定型,因为史学研究一般要遵循“孤证不立”的原则。因而,发现“问题”后,还要到其他石刻资料及传世文献中搜寻相类之史例,以期佐证发现的“问题”的真实性。譬如,笔者阅读《秦德昌墓志》后发现,关于撰写墓志铭,秦德昌的家人认为,由熟悉志主的外人撰写墓志铭,或可因作者“情无妄交,言不妄发”[8]166而避免所撰志文的虚夸与不实。检索其他辽人墓志铭,相类的认知在《邓中举墓志》《宁鉴墓志铭》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辽人墓志铭中也表达有与之不一致的观点。反对者认为,由丧家“请托”的外人中,有些人并不熟知志主的全部人生轨迹,加之受学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请托”的外人撰写的墓志铭,难免出现详略不当、挂一漏万等现象。再者,“请托”的外人撰写墓志铭,往往在丧家的要求或暗示之下,对志主家世郡望、事功德行等方面或假托溢美或隐讳虚饰。因而反对者呼吁,由熟悉逝者的家人或戚属撰写墓志铭,或许是减少逝者事迹缺漏和讹误的一种选择。此类观点在《王泽墓志》《马直温妻张馆墓志》《丁求谨墓志》中都有所体现。笔者以为,这种无解之纠结,不仅仅出现在辽朝,受文体及其特殊用途的影响,应该自墓志铭产生的那天就开始了。
传世文献对石刻资料中所见“问题”的佐证也很重要。笔者在《辽〈秦德昌墓志〉“记事”发覆》一文中,曾以《秦德昌墓志》所记秦德昌出使西夏,“非礼”夏王李元昊为例,论述辽朝外事交涉中“非礼”与“遵规”的辩证施用问题。为佐证这一观点,笔者钩沉《辽史·列传》,发现在《牛温舒传》《耶律合里只传》中,确有相类之记载。由此便可证明:在辽国的外事交涉中,如果是对方有错在先,辽国又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其差遣之使臣对待出使国人员往往就会取“不可以柔而致”的姿态,表现出某些“非礼”举动;而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岁月,使臣的言行举止,则符合外交礼节,并体现出对出使国的尊重和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