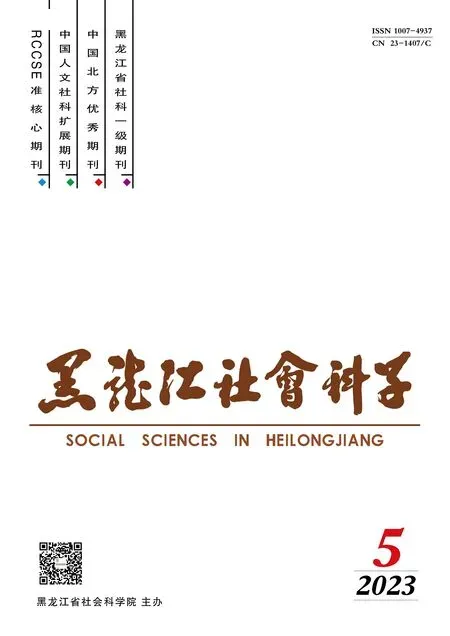以文制武:明代九边武官所处的权力与舆论世界
程 彩 萍
(廊坊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有明一代,沿边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因此边防事务备受重视。北边卫所设置较早,朱元璋时期利用卫所守土实边、管理军民事务,形成了初步的军事防区:“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后,以西北边境与胡虏密迩、虑为边患,故于甘州设立陕西行都司,宁夏设立五卫所,大同设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设立万全都司,古营州设立大宁都司,于辽东古襄平设立辽东都司:各统属卫,如臂指之相使,气脉之相属,以捍御夷虏。”(马文升:《为经略近京边备以豫防虏患事疏》)[1]卷64,545永乐以后,中央逐渐派遣勋臣或都督充当总兵镇守北边,卫所军职受总兵节制、听从调度,九边防御体系也由此逐渐完善:“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明史》卷91《兵志三》)[2]2235可见,九边武官处于卫所、军镇多层管理体制之下,而且随着以文统武格局的形成,除了要遵守军纪、军法外,九边武官又受到文臣节制、内官监督、言官弹劾等多重约束,增加了九边军事司法运行的复杂性。目前学界对明代九边的整体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3],本文拟对明代九边武官在日常军政及作战过程中受到的行政监督、军法威慑、舆论压力进行探讨,以期深化对九边事权分配与制衡所带来影响的分析。
一、日常军政中九边武官所受监督与约束
明代军政事务涉及较广,卫指挥使司“凡管理卫事,惟属掌印、佥书……分理屯田、验军、营操、巡捕、漕运、备御、出哨、入卫、戍守、军器诸杂务”(《明史》卷76《职官志五》)[2]1873。九边武官须遵守相应规定、履行职责,这些内容明确记载于接受朝廷任命的敕书中。如宣德元年(1426)八月,朝廷命指挥芮勋守居庸关,其敕曰:“今命尔守关,军士必勤训练,关隘屯堡必严守备,讥察奸伪不可懈怠,或有警急即遣人驰奏,一切边务必与附近总兵官协谋审处,毋慢毋忽。”(《明宣宗实录》卷20,宣德元年八月丁卯)[4]528
边镇武官是否认真履行了以上职责,一方面会通过军政考选进行考核,另一方面则通过中央巡视制度进行监督。巡视边镇或边关制度始于明初,明成祖给成山侯王通的敕书中强调了巡视军政的重要性:“修边,国之重务,其军政不可不肃。昔太祖高皇帝,数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当时军政修举,今西北边备尤为急务,而各卫所比年军政弛慢,官多具员,卒多缺伍,缓急何以制之?今命尔往陕西及潼关等处阅视军实,务俾队伍整齐,甲兵坚利,备御严固,庶几国家足兵之美,尔其勉尽厥心,用副委任。”(《明太宗实录》卷200,永乐十六年五月丙辰)[4]2083
随着九边防御体系的建设以及以文驭武格局的发展,九边职官体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了使用武官镇守边关、经营军镇外,明廷开始陆续派遣文臣与内官前往九边,对武官进行监督和考察,加强对武官的行政约束。朝廷曾“每季遣官巡视居庸、山海等处关隘,有设置未备、器械未精、军士未足、守卒年久未更者,逐一理之”,后来停罢,宣德十年经兵部尚书王骥奏请,再次命监察御史、给事中巡视边关(《明英宗实录》卷2,宣德十年二月乙巳)[4]40。
明代中央巡视或阅视制度至弘治时期被确定为三年举行一次。弘治三年(1490)兵部奏请敕各边守臣及时修理墩墙,并每三年仍特遣大臣阅视以行劝愆,孝宗批准曰:“边备事重,正宜以时修葺,其如所奏,令各边守臣整理,仍三年一遣大臣阅视,不得虚应故事。”(《明孝宗实录》卷42,弘治三年九月乙卯)[4]867巡视期间,会考察军马、器械、城堡等军政是否修举,并对不称职的武臣进行弹劾。嘉隆时期又进一步细化了巡视的内容以及对边臣是否称职进行衡量的标准。隆庆五年(1571),高拱奏准赐敕一道戒谕边臣,责其成效。又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风力科道官二三员分投阅视:“要见钱粮比上年积下若干,险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马比上年添补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俱比上年拓广若干,眀白开报。若果著有成绩,当与擒斩同功;若果仍袭故常,当与失机同罪,而必不可赦。”[5]从高拱所述内容看,涉及军饷供应类的包括钱粮、屯田、盐法,防御工事类的则如关隘、城堡等,以及军队人数和装备等,皆为日常军政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为了提高武臣修举军政的积极性,高拱建议将其提高到与指挥作战同一层次,对懒于修举军政者,与失误军机同等处罚。张居正亦指出,阅视时以“八事”为最紧要者,即使遇到三年一次的贡市亦不能撤销,可同时进行:“然阅视以八事为殿最,贡市以款虏为勤劳;阅视优于要职,贡市逮于卑官,固自并行而不悖。”[6]
明代派遣中央大臣巡视九边的制度亦时有变化和调整,主要是围绕时间和人员安排,比如选择三年一次派遣大臣阅视还是令巡按御史每年一次阅视。杨嗣昌认为令巡按御史阅视边关与其本身职责并行不悖,可谓一举两得,而针对有些人对巡阅频繁产生的顾虑,他则指出年年阅视的必要性:“兵马钱粮,年年有销耗,季季有开除。战守机宜,时时有变更,事事有因革。将领贤否,应处罚者,尚不待于时刻,岂可淹于三年,人情积玩,边事积坏。巡边御史果能务行实事,不徒虚文,则一年一阅,其关于整饬,鼓励不小。”[7]崇祯十年(1637)九月十九日,皇帝批准了其建议。
除了巡视与监督制度之外,明代建立的巡抚、总督制度对九边武官形成了更为全面和固定的行政约束。《明史》卷73《职官志二》载:“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遣尚书赛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初名巡抚,或名镇守。”[2]1767此时巡抚的派遣并未固定,其职责亦未明确规定,对武官节制与否尚难确定。至明英宗时期,巡抚制度逐渐成熟和固定,从巡抚苏松江浙一带扩展到北边。正统八年(1443)九月,命监察御史李纯巡抚辽东,令其专门整理屯田之事。辽东位于边远地带,地域广阔、军马众多,粮草则俱凭屯种供给。而彼时都司卫所官往往占种膏腴,私役军士,虚报子粒,导致军士饥寒,因而逃避军役,故特遣巡抚予以革除弊病。敕书中写道:“今特命尔代浚总督屯粮,比较子粒,提调仓场,收支粮草,务在区画得宜,尤在敷宣德意,扶植良善。遇有官吏酷害,私役占种等事,除军职具奏,其余就行拿问。”(《明英宗实录》卷108,正统八年九月戊寅)[4]2195
随着巡抚职权的不断扩大,逐渐具备“从宜处置”“便宜处置”的权力,遂也兼及提督军务、节制兵马等事项。天顺二年(1458),升陕西布政司左布政使芮钊、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陈翌、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王宇俱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分别巡抚甘肃、宁夏、宣府。赐之敕曰:“今特命尔等巡抚各边地方,训练军马,整饬边务,抚恤士卒,防御贼寇,务令衣甲齐备,器械锋利,城堡、墩台修治坚完,屯田、粮草督理充足。禁约管军头目,不许贪图财物、科克下人及役军余、私营家产,违者轻则量情发落,重则奏闻区处。凡一应边务事情、军马词讼及利有当兴、弊有当革者,悉听从宜处置。”(《明英宗实录》卷291,天顺二年五月壬寅)[4]6219巡抚芮钊等人须禁约管军头目科敛、私役军人,轻罪可以直接发落,遇紧要之事,仍然要与镇守、总兵等官会同处理。成化九年(1473)颁给巡抚辽东、大同等处都御史彭谊、郑宁的敕书中,对其管辖权限有明确交代:“中间若役占军士、委用非人,以致军旅不精、守御无备者,指实具奏。管军头目自都指挥而下有贪懦无为者,从公罢黜,别选材武智能者代之。应逮问者,就尔逮问区处,以示警戒。”(《明宪宗实录》卷120,成化九年九月壬子)[4]2321
纵观嘉靖至万历时期颁给巡抚的敕书,与上述成化年间的敕书内容基本一致。嘉靖十五年(1536),御史张景总结颁给各边巡抚敕书中涉及的职权说:“敕内有防御虏寇、修理城池、整饬军马、区画粮饷、谨关隘、明赏罚诸事。”(《明世宗实录》卷184,嘉靖十五年二月乙巳)[4]3907隆庆五年,在给辽东巡抚张学颜的敕书中写道:“有警则公同镇守、总兵等官,调度官军,相机杀贼。禁约管军头目,不许科扰、克害及隐占、私役,有误战守。违者,轻则量情惩治,重则毋畏势豪,径自参奏拿问。”(《敕巡抚辽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学颜》)[8]286安抚军民、监督武臣是巡抚的重要职权,辽东“守边官员行事乖方,以致地方不靖”,故有必要派巡抚前往处理。万历时期,颁给巡抚保定兼提督紫荆等关孙丕扬的敕书中亦提到:“所属官员廉能干济者量加旌奖,贪酷不才者从公黜罚。军民人等词讼即与受理,军职及文职五品以上有犯,奏闻区处,其余就便拿问,或发巡按御史究治。”(《敕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孙丕扬》)[8]278可见,巡抚掌握着赏罚大权,虽不能直接按律处置武臣,但具有监督、约束、举劾武臣的权力。事实上,在任的巡抚确实弹劾了很多不称职的武官。如辽东巡抚胡本惠弹劾铁岭等处守备都指挥佥事皇甫英不严设备,“以致虏寇入境杀掠人畜”,并将其发遣到巡按御史朱暟处审理。皇甫英论罪当斩,最终给予降三级、于当地立功的处分(《明英宗实录》卷354,天顺七年秋七月丙申)[4]7079。
成化年间,由于西北战事紧张,为了更有效地调度军马,朝廷开始派遣专门统辖军务的总督。成化十年正月,首加王越以总制之名,统驭各处总兵、巡抚。此为临时性质,战事稍息,即将总制召回。总制兼有文臣提督军务、武臣节制军马的双重权力,其设置成为文臣总督军务的一个重要尝试。而陕西三边总制的出现,也遵循了明代先由武臣统军、后添设文臣参赞军务,文武制衡,最终实现以文驭武的发展趋势。据《明会典》记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弘治十年议遣重臣,总制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十五年以后,或设或革。至嘉靖四年始定设。四镇兵马钱粮一应军务从宜处置。镇巡以下悉听节制,军前不用命者,都指挥以下听以军法从事。”嘉靖十五年,宣大延宁皆有虏警,复设宣大总制官,并更名为总督,陕西三边总制亦更名为总督(《明世宗实录》卷193,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甲寅)[4]4069。自后,一直沿用总督之称。
总督较巡抚而言,具备直接节制总兵官等武臣的权力。弘治十四年,命秦纮总制陕西固原等处军务,其敕曰:“命尔总制,凡军马钱粮等项,宜逐一从新整理,俱许便宜处置。遇有虏寇侵犯,即便随宜调遣各路军马相机剿杀,各该镇巡等官悉听节制。”(《明孝宗实录》卷179,弘治十四年九月甲辰)[4]3311隆庆二年,谭纶以兵部左侍郎出任蓟辽总督,其敕曰:“其蓟、辽、保定镇巡并各镇参游所属地方,各道兵备添设修筑墩堡等项官员,俱听尔节制。各领兵等官敢有临阵不用命者,自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其余军卫、有司官员有犯,轻则径自提问,重则参奏究治,庸懦不职者一体纠劾。凡军中一应事宜,并敕内该载未尽者,悉听尔便宜区处。”(《敕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谭纶》)[8]245均可见一斑。
万历二年(1574),升杨兆为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蓟辽,其对武官的节制具体到“蓟辽、昌平、保定镇巡、协守、分守、副、参、兵备及统领、入卫领班等项官员”,“许以军法从事”的范围扩大到参将以下:“各领兵将官有临阵退缩、承遣逗遛、抗违军令,及沿习旧套割取死首冒功脱罪者,参将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以上先取死罪招由,奏闻处治。”(《敕总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兆》)[8]247显然,总督被授予辖区内最大军权,不仅督察日常军政,而且有权节制武臣、调度军队。
晚明时期总督制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比总督辖区更广的经略。万历十八年,朝廷命兵部尚书郑雒经略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宣府、大同、山西七镇军务,兼理总督。经略郑雒因管辖范围太广,欲辞去其任:“臣欲往甘肃,则洮河难顾,欲驱流寇,则套虏难防。恐四夷闻之,谓臣一人之身,忽然而经略,又忽然而总督,边事日去,国体益轻。”然神宗不允所辞(《明神宗实录》卷230,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己巳朔)[4]4259。兵科给事中薛三才亦力荐郑雒兼管总督事务:“论事权,经略之权重于总督,论责任,总督之责专于经略,一人操其重权,又一人分其专责,事体未便。乞敕该部酌议,仍敕郑雒兼理总督,庶事权不分,而雒亦得以安心,殚力于西陲矣。”(《明神宗实录》卷230,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己巳朔)[4]4259可见经略之事权更大,明末辽东战事频仍,熊廷弼、王在晋皆曾担任过辽东经略。
明廷除了派文官赴边地整理边务、节制官军外,还派遣镇守内官与总兵协同镇守。如派御马监太监王清前往宁夏镇守,其敕曰:“今特命尔与总兵官都督同知张泰镇守宁夏地方,修理边墙、城池,操练军马。遇有贼寇,相机战守。凡事须与总兵、巡抚等官公同计议停当而行,不许偏私执拗己见,有误事机。尔为朝廷内臣,受兹委托,尤宜奉公守法、表率将士。”[9]藩镇,32从敕书规定的镇守内官的职权来看,其可参与边镇军政、管理军务,但并无节制总兵的权力;内官作为皇帝的心腹更多的是起到监督边将的作用[10]。这样就将边镇武官置于文官节制、内官防备的制度约束之中:“自设立武卫之后,次第添置,抚之以台臣,驭之以将领,佐之以裨监,赞之以督理。尤虑安攘之术未尽,首命中臣寅同镇守,盖欲参知戎务、心腹朝廷、防闲内外之深意也。”[9]公署,40
二、战时九边武官所受“军法从事”之权的威慑
战时面对紧急形势,有些总督、经略被授予尚方宝剑,对于临阵退缩的武臣可以先斩后奏。万历二十年,宁夏哱拜发动叛乱,明廷命三边总督魏学曾统率大军镇压,然因赏格未明、军威不振,致延宕数月尚未平息。神宗下旨切责“威令不肃,诸将生玩其间,复有希功忌能、观望之念”,并“赐学曾剑一口,将帅不用命者,军前斩首以殉”(《明神宗实录》卷249,万历二十年六月己丑朔)[4]4630。然总督魏学曾仍然师久无功,遂“以(叶)梦熊代,赐剑专征,用蜡书约城中内应,遂擒哱拜、哱承恩以献”(《明神宗实录》卷323,万历二十六年六月庚午)[4]6006。万历四十六年,女真南侵,攻打清河,而总兵杜松等尚未出关,而其他各镇除了宣大、山西总兵官率兵起程外,大多按兵不动。兵部奏称形势紧急,一旦清河失守则危及全辽、延及畿辅,因此必须严督各总兵前往增援:“我皇上起用经略,虽责以征剿之重任,而未尝畀以生杀之大权,是以臣前具末议,首请赐上方剑正为阃外之制。权不重则令不遵,非是无以震慑人心,而使之争先效命耳……伏乞皇上查照往例赐剑尚方,凡将帅有不用命者,自总兵以下,经略俱得以军法从事。”[11]神宗予以批准:“尔部便遵屡旨,并各镇兵马都催他星驰出关,以听调度。着赐剑一口,将帅以下有不用命者,先斩后奏,务期剿灭狂虏,以奠危疆。”(《明神宗实录》卷573,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庚申)[4]10821熊廷弼经略辽东时亦曾赐尚方剑:“将士不用命者,副总兵而下先斩后奏,兵饷额解外特发帑金以佐军需。”(《明熹宗实录》卷12,天启元年七月甲辰)[4]588此类奉命专征,皇帝旨在通过赐尚方剑以重事权兼隆礼数。
上述总督、经略被授予“军法从事”与“便宜处置”乃至“先斩后奏”的权力,也即无须经过奏闻、审理等司法程序,依照军法律令便可施以相应的惩罚措施。正统九年,命左副都御史王翱提督辽东军务,其敕曰:“尔等整搠见操官军,务要人马精健……遇贼近边即相机剿杀,飞报附近边军互相策应,敢有怠慢误事者,悉以军法从事。朝廷以尔廉公有为,谙练兵务,特简拔委任,一应军务,悉听尔便宜处置。”(《明英宗实录》卷118,正统九年秋七月丁卯)[4]2386弘治十四年,西北有警,孝宗命提督军务都御史史琳、总兵官朱晖等率京军前往,继而朱晖奏乞假以便宜之权,授其敕书遂曰:“参将而下及所在各该镇巡等官悉听节制,官军头目人等敢有违犯号令者,重以军法处治。其有临阵退缩、不用命者,指挥以下就便斩首示众,然后奏闻。其斩获首级,俱送纪功官处审验明白,从实开报,以凭升赏,不许冒滥。”(《明孝宗实录》卷173,弘治十四年四月戊子)[4]3154
所谓“军法从事”,即以军令、律法为依据,此外还有专门的号令,往往比较严厉。如永乐十二年(1414)所颁“军中赏罚号令”有很多详细规定,包括是否尽力杀敌、队伍是否整齐、军器物资是否爱惜、有无掳掠无辜以及是否泄露军机等多个方面,奖惩力度较大。其中规定:“临阵交锋,务要一时向前杀败虏贼,如不尽力杀败虏贼者,全伍皆斩。”(《明太宗实录》卷150,永乐十二年四月己酉)[4]1747又规定:“有将军器故意抛落遗失及盗卖者,治以重罪。”(《明太宗实录》卷150,永乐十二年四月己酉)[4]1748《大明律》则载:“凡将帅关拨一应军器,征守事讫,停留不回纳还官者,十日杖六十,每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辄弃毁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二十件以上斩。遗失及误毁者,各减三等,军人各又减一等,并验数追陪。”[12]
阵前军法的实施,自明太祖时就受到重视。当时浙江左丞胡德济在大将军徐达军中,因临事畏缩被械送至京。明太祖念其旧劳特命宥之,同时遣使敕谕徐达以后要在军中严格执行军法:“迩者浙江左丞胡德济临事畏缩,将军不以军法从事,乃械送京师,必欲朝廷治之。将军欲效卫青不斩苏建,独不见穰苴之待庄贾乎?且慢军功者,悉归之朝廷,则将军之威玩而号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当就军中戮之,足以警众,所谓阃外之事,将军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议其功过,又非阃外之比矣。彼尝有救信州之功,守诸暨之劳,故不忍加诛。惧将军缘此缓其军法,是用遣使即军中谕意,自今务威克厥爱,毋事姑息。”(《明太祖实录》卷51,洪武三年夏四月乙酉)[4]1008
军法能否得以实施关系到全军纪律是否严明,因此除了总督等拥有“军法从事”之权外,朱鉴还主张给予总兵一定的生杀大权:“况总兵既无擅杀之权,军壮又无畏法之心,以致调往避难者相继而逃,临阵畏死者成队而退,习为常事,全无纪律。再不假以威权、申以军令,诚恐因循月久,姑息日深,草场不敢放收,粮道不得速通,马必瘦死,人不聊生,必堕贼计,致误事机。”(朱鉴:《陈言边务疏略》)[1]卷35,269夏良胜亦提出:“军威以杀为主,故曰军旅之后,必有凶年,全胜之功,古今几见……我屡败而未戮一将与卒,故进则死,而退则可生,胜败之异,职此之由。伏望陛下申令主帅,使副属而下,俱得按法行诛。”(夏良胜:《论用兵十二便宜状》)[1]卷154,1542成化元年九月,陕西巡抚项忠也上疏请求授予总兵“军法从事”之权:“今陕西三边挂印总兵,遇敌逗遛,无一人肯当前者,虽云智勇未能如古名将,盖亦委任有未专焉。况锋镝交于原野,机会变于斯须,呼吸之间有生有死,若不委以军法从事之柄,孰肯轻生以御敌哉!今军士但闻敌之可畏,而不畏总兵之号令,以总兵之权轻也……宜敕各边总兵官,今后闻有大敌在前,军中有违主将号令者,悉以军法从事,庶几成功。”(《明宪宗实录》卷21,成化元年九月壬戌)[4]417
辽东巡抚毕自肃曾因辽事不靖长达十年,导致中央与地方苦于筹备军饷,将士苦于艰险,士卒苦于锋镝,就如何解决战事提出若干建议,其中一条为“严赏罚之令”,建议兵部刊行专门的军法,以备赏罚:“闻之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圣王无以治天下,况兵凶战危……今当敕兵部考定军法,刊之为令,何者宜赏,何者宜罚,使彼众自晓然无疑,一遇赏罚求之于令足矣。而又矢公虚断以信,必贿赂、情面举无所施,然后人知法在必行。”[13]军法的严格实施显然有利于防御力量的加强,如贾俊巡抚宁夏,“持宪度、严军法,数年虏不敢犯”[14]。
然而,因“军法从事”之权关系到官军生死,故皇帝对此极为谨慎,并不轻易授予,且授予时一方面会在敕书内写明,另一方面还要强调所谓军法并不专杀,也要依据律法,按照轻重论处。如弘治十年九月,孝宗召见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讨论大同总兵官吴江奏请“临阵以军法从事”之事。孝宗认为如准其所奏,“恐边将轻易启妄杀之渐”。刘健对曰:“临阵用军法,自古如此。两军相持,退者不斩,则人不效死,何以取胜?”孝宗曰:“虽然,亦不可径许。若命大将出师,敕书内方有军法从事之语。各边总兵官亲御大敌,官军有临阵退缩者,止许以军法严令从重处治,如此方可。”而李东阳坚持认为:“今既奏请,若明言不许,却恐号令从此不行。”孝宗最终采纳了谢迁的提议:“今遵圣谕批答,仍用一‘是’字为宜,且军法亦不专为杀,轻重各有法,决打亦军法也。”[15]
可见,战时厉行“军法从事”虽然可以严明军纪,促使官军勇无直前、进而取得胜利,然而实际上留给总督、巡抚、将帅等发挥的空间是有限的。对总督、巡抚而言,通常情况下武官有罪仍要奏请处置,自行斩杀则犯了擅杀之罪。弘治时期宣府巡抚雍泰即因责罚参将而被罢官。时参将李稽不法,部下上告其恶,雍泰“具草将闻于上”,结果“稽跪堂下,乞受责,图自新。太(泰)曰‘此亦军法也’,缚下杖之”。由于雍泰当庭杖打参将,“言官遂劾太(泰)以擅辱命官罢”[16]。李稽则奏雍泰“凌虐将官,贻患边徼”。通过稽查,法司议奏:“雍泰凌虐李稽,虽云过当,而稽实以罪系狱,其致死人命虽不以私,而用刑非制。”随后雍泰被勒令致仕,最终被革职为民。其自陈“公罪律应免问,乞垂矜宥”,不允(《明孝宗实录》卷177,弘治十四年闰七月辛卯)[4]3253。
综上,不论日常军政中对九边武官的监督与约束,还是战时对其的军令制约,皆体现了明代以文驭武的发展趋势。“军法从事”的实施对象不仅包含军士,亦包含武臣,甚至总兵以下皆受制约,从理论上突破了军职有犯须奏请处置的司法程序。然而获得“军法从事”之权并不等同于完全掌握了生杀大权,总督、巡抚不经皇帝批准、未经法司勘问,直接按军法处置武官,稍有差池就会引来非议,甚至被处罚。可见授予总督、巡抚等“军法从事”之权,主要意在产生威慑力量,有利于立军威、行军纪,宣示将兵之权。
三、朝野舆论对边将所受司法约束的影响
边将犯公罪尤其犯“失误军机”罪的司法审判,往往涉及功过的评定,其关系到军中赏罚是否严明,因而备受关注,其处理甚至超出了司法领域的范畴,受到朝廷政治的影响。而朝廷的言官则会对涉事官员进行劾奏,以阻止其逃脱罪责,言官群体对九边武官的牵制与影响即由此显现出来。
隆庆初年大同失事一案的审判便体现了群臣的政治舆论作用。事情起因为蒙古入犯大同,持续七日方撤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总督陈其学、巡抚李秋却虚报军情:“本镇探得虏情,预为之备,以故虏无所利,总兵赵苛等先有邀击,皆有俘斩功,宜加赏录。”而巡按御史燕儒宦所言则与其相反:“虏自入境来,我兵无敢发一矢与之敌者,攻陷堡塞,杀掳人畜甚多,宜正诸臣玩愒之罪。”这件事迅速引起朝廷文官的注意,都给事中张卤等率先劾奏:“边臣欺罔,请严究如法。”由于双方各执一词,于是兵部奏请下御史勘实以闻。而穆宗却令总兵官赵苛等戴罪防秋,参将袁世械等交由御史提问。言官如给事中查铎、御史王圻等则再次提议将其治罪。随之巡按御史燕儒宦更详述事发经过:“(赵)苛遂提兵远屯,参将方琦等皆不设备,游击施汝清等又畏缩不前,遂令怀、应、山阴之间任其蹂躏,陷堡塞大者二所,小者九十一所,杀掠男女及创残者数千人,掠马畜粮刍以万计。我军虽尝出边,稍有擒斩,然竟未接一战。”(《明穆宗实录》卷38,隆庆三年十月甲辰)[4]955
针对此事,穆宗令内阁发表看法,大学士赵贞吉主张顺应群臣公论,依照律法严惩失机将官:“边事为平章第一要务,于今反漫然视之。国家之事最重者边防,欲整理边防,在正朝廷纪纲耳。赏罚乃纪纲之大者,若大同一镇功罪不明,赏罚不当,则诸边视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复整理矣。此乃社稷之计也,我辈则社稷之隶,又安可不勉乎?今正大同之罪,只以‘祖法’、‘国是’、‘公论’、‘清议’八个字断之足矣。八字理明词严,‘主将不固守’,祖法也;隆庆元年皇上处治蓟州、山西失事之律,国是也;大同巡按所奏,科道所劾,公论也;当事之臣,请赂不行,持法不废,清议也。守祖法、定国是、张公论、畏清议,非我辈其谁哉!”面对“今兵部题覆,仍循回护之方;阁臣拟票,尚存姑息之意”的情形,赵贞吉以打算隐退表明自己的立场,据理力争(赵贞吉:《议边事疏》)[1]卷255,2691。最终得旨:“赵苛避事殃民,本有常刑,姑降实级三级,陈其学降俸二级,李秋夺俸半年,胡镇、文良臣各降一级。麻贵赏银二十两,麻锦、葛柰各十两,方琦等六人皆谪戍,施汝清等九人下御史问,又以镇巡官或不宜于本镇,命兵部同吏部议更置之。”(《明穆宗实录》卷38,隆庆三年十月甲辰)[4]
隆庆三年大同失事一案的处置引起较大反响,除兵部与司法机关外,言官、阁僚也纷纷发表意见,最终皇帝面对舆论压力,选择给予失机边将一定的惩罚。由此可见,对于九边武官犯罪的审判不仅属于法律体系,还牵扯监察、舆论等多重体系。明朝的各种权力因素纷繁复杂,交织在一起,或促进或阻碍,从不同方面影响着军事司法实践的运行。
因军事形势所迫,文臣要员纷纷就防御战略各抒己见、为皇帝献计献策,明初以来便不鲜见,至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谈兵”之风:“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对兵学的热情甚至超越了对诗文的热情,其中还夹带有彰显风雅的色彩。”[17]文臣对九边的关注,不仅包括时政军情、用兵部署,还涉及九边用人、武将优劣等各个方面。除了在某一案件中对九边武官施加舆论压力外,文臣对功过评定的标准亦产生一定影响,并形成了不同看法。
一种看法为“使功不如使过”。如分守辽阳副总兵都指挥使孙文毅坐守备不设当死罪,巡抚都御史张鼐则引用宗泽成就岳飞之事,认为孙文毅雄健骁勇、武艺精绝,为一时将才,当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宋岳飞犯法将刑,宗泽奇之,使立功赎罪。今辽阳贼巢遍野,声息不绝,杀此壮士,诚为可惜,且使功不如使过,文毅系于囹圄已三年,若获再用,必有后效。乞不为常例释送总兵处听调领军,如遇贼能斩获首级五颗者,宥其死,或立奇功破贼全胜,则仍复其原袭祖职。”由于张鼐的保荐,孙文毅被免于发遣,以平虏卫军身份存留本处听用,候有功如例升赏(《明孝宗实录》卷200,弘治十六年六月辛亥)[4]3716。刘健上疏陈奏安边之策,其中亦提到:“各处守边官员,有因误事降级带俸差操,及为事罢黜者,中间多系曾经战阵,谙练边事之人。合无令兵部通查,送赴军前立功,其有才堪领军者,就领军杀贼。”(刘健:《御虏安边事宜疏》)[1]卷52,40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功不掩过,须按律处置。如胡世宁引用《大明律》中“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见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除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依地理远近,发各卫充军”的记载,提出不应以朝廷爵禄,赏有罪之人。又如针对法司所奏征讨官当论功定议的处理办法,胡世宁表示反对,其引用明太宗的敕谕提出赏罚分明的重要性:“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胡世宁又认为:“今论官私罪,徒流以下径拟还职,虽杂犯斩绞,亦止发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无功亦得还职,全非太祖定律之意。”(胡世宁:《备边千策疏》)[1]卷136,1354
守边、征战的武官是否可以按照军功论赏罚,而忽略其他罪行,明代文臣士大夫并未达成一致。有些守边武官在文官的帮助下获得了重新立功升迁的机会,但亦有武官在文官的非议中被罢官。如陕西庄浪卫土官指挥鲁氏家族,据徐阶所述,可知其由盛转衰即与文官诽谤有关:“臣闻鲁姓系陕西庄浪卫指挥,其家旧有名于西边,号曰鲁家人马,后因人疑之谤之,不敢收养家丁,渐亦衰弱。近年有鲁聪者,任古北口参将,颇骁勇,被劾革任。凡武官之善战者,多粗率,而抚按、兵备等专要责其奉承,一不如意,便寻事论劾,轻者罢官,重者问军问死。”(徐阶:《答重城谕二》)[1]卷244,2548明代中期以后武官地位逐渐下降,在朝堂之上渐失影响力,在边境亦处处受到制约,处境可谓艰难。
余 论
古语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体现了将官的军权之大,君主亦因此对将官有所忌惮。明朝边将无调兵之权,在中央要听从兵部部署,在地方则要服从总督、巡抚调配,事权被一再分割。从九边官员的陆续增设可以看出边将逐渐受制于各类文官的情况:“凡天下要害去处,专设官统兵戍守,俱于公、侯、伯、都指挥等官内推举充任,是镇守事权专在总兵官矣。以后因各边设置未备,器械未精,军伍不足,乃兵部三年一次具题,差文武大臣一员阅实,又差御史二员分行巡视,是都御史添设之由也。当其时,阅实而已,此后未知何因起巡抚地方之文,又不知何因起赞理军务之文,于是巡抚得以制总兵,而事权在巡抚矣。又因巡抚事权轻,而各镇军马难于调遣,又设总督都御史,如蓟辽总督,则嘉靖二十九年添设也。此皆一时权宜之计,因事而起,然自是总督得以制巡抚,而事权在总督矣。至于失事之后,查勘功罪,必行巡按,乃巡按不行自勘,必委兵备道,该道委府县官……至于总兵,则上自总督,下至通判知县,无不制之。”(吴时来:《目击时艰乞破常格责实效以安边御虏保大业疏》)[1]卷384,4165
黄宗羲总结明代文臣将兵制度曰:“有明虽失其制,总兵皆用武人,然必听节制于督抚或经略。则是督抚、经略,将也,总兵,偏裨也。”[18]明代在九边施行以文驭武的统治策略,欲使各方协同防御,然而现实中却往往互相掣肘,妨碍边务。冯琦在给吕坤的书信中即言:“且如陕西一省两司之上,有巡抚,有总督,又有经略大臣……昔之总督,即今之经略。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衔以为重,久之亦为地方官矣,则又出中朝之尊贵者以临之。礼节滋烦,文移滋费,而彼此牵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则众任之,事败而罪亦不独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视荫玩日,其原皆出于此。”(冯琦:《答吕新吾方伯》)[1]卷440,4827兵部尚书毛伯温亦评论曰:“属者陛下轸疆圉之急,总督大臣并置,文武谋勇相资,事宜允济矣。然臣犹有过虑者四。自古阃外之臣彼此调和,则士豫附,但事权相埒,则嫌隙易生,可虑者一。自古命将出师,最忌中制,若往复奏请,必致坐失机宜,可虑者二。近年边务废弛已极,非旦夕可以责成,恐言者随议其后,可虑者三。总督大臣得专生杀,诸将往往不遵约束,遂求故引去,即加以罪,亦所甘心,可虑者四。”有鉴于此,毛伯温奏称“臣请特诏文武二臣同心决策,共济时难,军中一切机宜,不从中覆,虽有小失,朝议宜谅其心”(《明世宗实录》卷273,嘉靖二十二年四月丁酉)[4]5366,世宗嘉纳之。
针对武官与文官之间的矛盾,除了劝诫九边文武大臣和谐相处外,明人还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想方设法,试图解决因官员掣肘出现的弊端。一种办法为支持文臣将兵,加重总督之权,进一步完善总督巡抚制度,使事权归一。如赵伸提议:“今之总督出将入相,文事武备,非其人与,是故任之专也,各镇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镇不得而并也。且用兵之道,妙于变化,主于奇正,彼己相取,远近相生。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选将练兵、出奇制变,听自一人而已。”(赵伸:《筹边疏》)[1]卷234,2459
另一种办法为使责有所归,施行分责制度。如汪道昆对九边主要官员的职责进行了详细划分:“臣惟分布调度,理饷程功,总督事也;缮边防、固城守,实行伍、辑士民,巡抚事也;明间谍、谨烽堠、精教练、严约束、勒部曲、审机宜,料敌制胜,总兵事也;慎出纳,给饷以时,户部分司事也;足食利兵,巡工训士,慎听闾伍之讼,毋失其和,兵备事也;治一旅之师,当一面之守,守必固,战必胜,诸将事也。凡此则皆功能相济,体统相维……故臣请自督抚而下,各分责成:调度失宜,功罪失实,罪在总督;完缮不豫,罪在巡抚;虏形不察,军政无纪,战阵无勇,罪在总兵;刍饷不给,致失机事,罪在户部分司;信地不严,专责不举,罪在监司部将。”(汪道昆:《蓟镇善后事宜疏》)[1]卷337,3609
上述两种方案从不同角度,针对九边军权运行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然而事实上,文臣统兵的趋势越演越烈,分权制衡的态势达到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守边将官不仅受到兵备道、巡按御史、都察院、兵部等机构与官员的监督与考核,还要受到来自朝野包括言官、其他文人士大夫的舆论压力。边将事权虽被削弱,责任却未减轻,一旦失事,或所辖军官出现失误,则要承担失误军机之责,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弹劾。左都御史吴时来认为,边方失事只怪罪于将官显然不妥:“总兵官兵力既薄,事权又轻,又有中制之患。至于失事,罪独归之将官,所由解体也。夫督抚职掌,不过调度,原无提兵杀贼之文也。巡按职掌,不过监军纪功,原无调遣之文也。兵部调遣,虚文也,缓不及事也,兵机倏忽,一刻万变,乃欲以遥度之智,中制之权,纷乱听闻,使将官口实于此,诚非事体。”(吴时来:《目击时艰乞破常格责实效以安边御虏保大业疏》)[1]卷384,4165
在以文驭武的政治环境下,“武职多要仰仗文臣的垂青与庇佑方能在军中立足”[17],总督、巡抚、镇守内官具有保奏之权,可使犯过武官减轻甚至避免处罚。如西安左卫指挥使杨宏最初“以失机问拟充军”,总制秦纮为之论辩,后又荐其知兵练事、才任统驭,故特宥之,降二级为指挥佥事(《明武宗实录》卷4,弘治十八年八月壬申)[4]139。可见,对于九边武官的司法约束与实践,因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较多的不确定性;边将功过的评定以及是否能够以功抵过,一定程度上掌握在皇帝与朝臣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