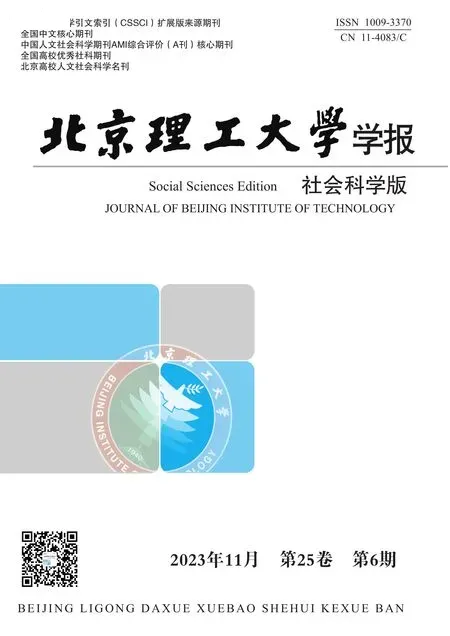家事诉讼多元化证明标准反思与层次性构建
李亚楠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证明标准是法官对待证事实形成内心确信的衡量尺度。当待证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明活动达到特定证明标准时,法官就认定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当待证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明程度无法达到证明标准时,待证事实就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只能以证明责任的承担拟制法律事实。中国刑事诉讼中主要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民事诉讼中则主要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家事案件属于民事案件,一般来说应当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但在纷繁复杂的家事案件中,既有高职权主义的公益案件、非讼案件,又有职权主义稍弱的身份诉讼案件和准辩论主义的财产诉讼案件。家事诉讼中是否需要根据不同案件类型设置有别于高度盖然性的特殊证明标准是家事审判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民事诉讼现有规定存在几种特殊证明标准: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9 条和《民事证据规定》第86 条的规定,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口头遗嘱或赠与采取较高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采取较低的或然性平衡标准。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写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40 条第2 款规定,家庭暴力行为的事实认定适用或然性平衡标准。近年来,随着家事审判朝专业化和独立化方向发展,陆续有学者提出家事诉讼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应当根据家事案件的不同类型,扩大现有特殊证明标准的适用范围,在家事诉讼中建立以高度盖然性为基准、以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为辅助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1]2-11[2]42-63[3]320。这种提议是否恰当,值得详细探讨。需要明确的是,对于程序事项的证明,各国普遍采取相对较低的证明标准。这无可厚非,因而不纳入本文探讨范围。本文所探讨的仅限于实体事项的证明标准。
一、家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域外考察
家事诉讼属于民事诉讼,原则上适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英美法系采或然性平衡标准,大陆法系采高度盖然性标准。家事诉讼中一些特殊事项是否适用特殊证明标准曾在域外引发过很长时间的争论。
(一)英美法系对家事诉讼特殊证明标准的争论
在英美法系国家,没有辩论主义和法院依职权调查的理论存在,认为所有的家事案件都是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诉讼案件,但通常对儿童保护案件(Child Protection)特殊照顾,在审理过程中赋予较多的职权主义色彩。换言之,英美法系国家通常将家事案件分为家事私益案件和涉及儿童保护的公益案件。是否增设特殊证明标准的争论集中在儿童保护案件中犯罪事实的证明和家事私益案件中准犯罪事实的证明上。
首先,儿童保护案件虽属于家事案件,但经常涉及对监护人恶性行为的指控,如强奸、猥亵、故意伤害等。这些事实的证明适用何种证明标准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英国曾出现过三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采取介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间的标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根据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但这些指控在家事诉讼中仍可能根据或然性平衡标准被认定为真实,此时被告所受到的污名和耻辱并不比他被定罪少。因此,尽管家事诉讼中这些事实的证明无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但所需的证明标准应当与被指控恶行的严重性质相称,即应以超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来认定这些指控,但无须达到与刑事诉讼同样的严苛标准①Re W (Minors) (Sexual Abuse: Standard of Proof) 〔1994〕 1 FLR 419, at 430。。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采取动态的证明标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指控的罪名越重,所需的证据就应当越有说服力,证明标准应当更高,以此达成平衡。因为指控越严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例如父亲强奸女儿的可能性比殴打女儿的可能性要小,而殴打女儿的可能性比发脾气打她耳光的可能性要小。在权衡各种可能性并认定争议事实是否发生时,事件内在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就越是要有证据证明它确实发生过,才能在概率的权衡下确定它的发生②Re Dellow's Will Trusts 〔1964〕 1 WLR 451, at 455; Re G. (A Minor) (Child Abuse: Standard of Proof) 〔1987〕 1 WLR 1 461, at 1 466; Re W(Minors) (Sexual Abuse: Standard of Proof)〔1994〕 1 FLR 419, at 429。。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采取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在某些民事案件中脱离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以第三个标准取代,则需要确定该标准是什么,以及何时适用,这是一个困难所在。改变证明标准的唯一结果是使证明标准与指控事实的严重性相称,但这实际上并不会对家事纠纷的解决有多大的帮助,反而可能造成混乱和不明朗的情况,因此最好沿用传统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且,尽管家事诉讼有其特殊性,但它仍然是民事诉讼的一种,没有理由认为家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或应当是个例外③Re H. and Others (Minors) (Sexual Abuse: Standard of Proof) 〔1996〕 AC 563。。
第一种观点虽然认为应当采取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第三种证明标准,却没有指出具体应当适用何种证明标准。第二种观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动态证明标准看起来很美,却意味着每个案件的证明标准都不相同,缺乏清晰和明确的可操作性,无端增加法官事实认定及说理的难度。并且,这种动态证明标准实际上并不会对处理案件本身造成多大的改变,反而会削弱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因为越是严重的指控,要求达到的证明程度越高,证明的难度就越大,事实就越不容易被认定,未成年人就越处于不利地位。这是极不合理甚至荒谬的。再者,一件事情内在的发生概率与该事实是否的确发生并不存在关联,小概率事件(如父亲强奸女儿)并非不会发生,大概率事件(如父亲掌掴女儿)也并非一定发生,不管是小概率事件还是大概率事件都应当根据具体的证据及证明标准去判断其是否确实发生了④BR (Proof of Facts), Re〔2015〕 EWFC 41。。可见,第二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采取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来认定家事诉讼中涉及的争议事实才是更妥当合理的做法。因此,第三种观点逐渐占据上风,成为英国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通说和定论。在其他英美法系国家,也普遍认为家事诉讼中涉及的刑事犯罪事实证明应当采取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其次,家事诉讼中还会涉及一些准犯罪⑤准犯罪(quasi-criminal)是指法院有权对作为或不作为进行惩罚,就好像它们是罪犯一样。准犯罪将民事案件中的行为当作刑事诉讼中发生的行为来处理,是一种可能导致类似于刑事处罚的民事诉讼。常见的准犯罪行为有藐视法庭、通奸、欺诈等。https://dictionary.law.com/;https://www.law.cornell.edu/wex/quasi-criminal_(proceeding)。行为的指控,如通奸、欺诈等。这些个别事项在英美法系国家曾采用过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但目前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取消了这种做法而采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加拿大,普通法的权威曾认为离婚诉讼中的通奸或者民事诉讼中犯罪类型行为如欺诈,采用更高的证据标准。但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后来的判例中明确,正确的证明标准应当是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如果有严重的指控需要认定,事实裁决者可以考虑证据的力度,有权更加谨慎地审查证据。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由满足的程度来定义的,这并不意味着在民事诉讼中存在不同的证明标准。”[4]210-211在澳大利亚,婚姻诉讼中的证据标准也曾有过很大争议,但后来澳大利亚高级法院对此问题进行了明确回应,认为婚姻诉讼中通奸的证明标准是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只是法庭在认定诸如通奸这样的严重指控前应非常小心和谨慎地行事。澳大利亚家事法院将高级法院的意见视为法律遵行[5]398。在英国苏格兰地区,通奸或否定婚生亲子关系的证明曾采取过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但现在非婚生子女的概念已被废除,并且在废除之前,非婚生子女和通奸的证明就已经改采民事诉讼证明标准[6]547-548。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家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曾被认为是不确定的,因为通奸、虐待和遗弃等婚姻过错行为的认定附带着污名。尽管离婚案件在本质上属于民事案件,但由于婚姻过错的证明在《1969 年离婚改革法》(Divorce Reform Act 1969)生效之前是获得离婚判决的必要证据,这些过错行为被认为具有准刑事性质,因此导致一些人赞成在这些案件中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后来,随着离婚判决条件的放宽,婚姻过错行为的准犯罪行为性质受到削弱,有相当多的人认为采取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更合适。发展到现在,家事诉讼应当统一适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已在英国十分明确[7]138。
(二)大陆法系对家事诉讼特殊证明标准的争论
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将家事案件分为家事诉讼案件和家事非讼案件,其中诉讼案件又可细分为家事财产诉讼和家事身份诉讼。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为身份关系的认定较为特殊,对家事诉讼特殊证明标准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家事身份诉讼即人事诉讼中,尤其集中在亲子关系的认定上。此外,还有少量针对家庭暴力事实认定的讨论。
在法国,无论是确认亲子关系还是否认亲子关系之诉,法院均可以命令当事人为血液鉴定或DNA 鉴定,以全部证据方法确定真实确切的亲子关系。在否认婚生子女之诉中,虽然需要证明不能为父之事实,但判例承认所有的证据方法,特别是承认血液鉴定。可见,法国倾向于生物学上的真实主义。但是,1949 年《生命伦理法》规定应尊重人体完整性、不可分性原则,关于血液采集及DNA 鉴定,未得受检者同意不得实行。因此,在受检者不同意受检的情况下,法院只能从受检者的不当拒绝去推定亲子关系的存在与否,此时仍适用普通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8]452-455。
在德国,人事诉讼是否应设定比较高的证明标准存在争议。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 600 条之4 规定:“确认父子关系之诉讼中,推定与生母于受胎期间有同居事实之人为子女之父。该推定有明显事实怀疑其不为父者,不适用之。”[9]1185有学者认为该规定使用了“明显”之语,因而认为是提高了否认婚生子女诉讼上推翻妻从夫受胎的证明标准。但通说和判例均认为,婚生推定之反对事实应当由夫负举证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达到民事诉讼通常证明标准便足以证成[8]457。而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典型判例安娜斯塔西娅一案中,原告要求以较低证明标准确认其身份以继承财产,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表明法院应当背离法律的规定,为其降低身份关系的证明标准[10]91-101。理论界的通说也认为,只有不能达到高度肯定性的典型困难情形才可以考虑简化证明[10]107-108。
在日本,有学者认为,人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比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因为从尊重符合血缘关系的社会秩序来看,应强烈要求探知客观的真实并基于此为正确的裁判。并且,判决的效力及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为重视身份关系的安定性,法官应当就要件事实形成符合真实的确实性心证。但是,证明标准只能在无损于自由心证的范围内予以提高,否则会演变成限制证据。因为若设定比通常情形显著更高的证明标准,会妨碍科学证据以外证据方法的使用,结果无异于只承认某种法定证据,反而违背了自由心证的理念。在当事人拒绝鉴定的情形下,若人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设定得比民事诉讼高,法院基于全辩论意旨推定父子关系几乎不可能,要求法官在不使用科学鉴定的情况下进行事实认定未免过于严苛。因此,日本学者认为应强烈促使当事人协助鉴定,若当事人仍不履行协助义务,应根据违反证明妨碍或事案解明义务转换举证责任即可,即在现行法的范围内解决身份关系的认定问题,而不是去变动证明标准[8]459-461。
在中国台湾,有学者认为,为追求实体真实的发现,人事诉讼的证明应与刑事诉讼具有同样高程度真实性的证明。然而,尽管证明标准设置越高,基于此认定事实所作的判决被推翻的可能性越少,但这也使得举证越难成功,正当权利人的权益就越不容易得到保护。人事诉讼中本应依职权探知,尽量搜集所有证据方法来判断要件事实是否存在,却因为提高了证明标准造成事实认定依然困难,实非所宜。许士宦认为,从权利性质和两造当事人之间的公平来看,高度盖然性标准已经足以调和裁判真实性和当事人之间公平这两项要求,不应适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就此认为人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同。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社会性及人伦秩序要求,有关身份关系的要件事实虽不要求与刑事案件排除合理怀疑相同程度的证明标准,但应比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对于否定婚生亲子关系的反对事实,即“妻非自夫受胎”的证明标准,出于在诉讼法利益上的衡量,应当要求适用更高程度的证明标准,以确保发现真实和确保判决的安定性[8]468-476。
除亲子关系的认定标准外,中国台湾实务界还有见解认为,对于家庭暴力事实的认定,有超过50%的可能性时即可肯定事实之存在,法院应为有利于声请人之认定。但中国台湾并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姜世明认为该见解可能是受美国宾州家庭暴力防治法规定的影响,这种实务观点是否是有意识地认为家庭暴力的认定应低于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仍值得怀疑[11]147。
(三)评析
从两大法系国家对家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争论点来看,两大法系的关注点存在较大区别。英美法系的论争集中在家事诉讼中犯罪事实和准犯罪事实这两类特殊性质的事实方面,而大陆法系的争论集中在身份关系事实尤其是亲子关系的认定上。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别是因为,亲子关系的认定问题通常包括在准犯罪事实通奸的认定中,英美法系国家并不专门探讨亲子关系认定问题。而在大陆法系,由于追求判决结果的一致性,并不像英美法系那样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视为平行的关系,如果家事诉讼中涉及犯罪事实的认定,就会中止审理,等待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不会另行根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认定。因此大陆法系国家没有关于家事诉讼中犯罪事实认定应采取何种证明标准的讨论。
从两大法系国家对家事诉讼证明标准争论的结果来看,英美法系国家曾在家事诉讼中采取过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但随着实体法的修改和观念转变,英美法系国家逐渐达成共识,认为家事诉讼应当统一适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法国、日本的通说及判例均认为家事诉讼应当适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要肆意变动;中国台湾部分学者主张人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比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稍高,但这种较高的证明标准不得超过必要限度,即明显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见,尽管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个国家对家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态度有所不同,但他们均反对在家事诉讼中适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主张建立以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为辅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
从各国争论的焦点来看,可以得出两点共识:第一,家事诉讼中特殊事实的证明标准不应该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因为过高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案件事实难以证明,不利于权利人的保护以及维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第二,家事诉讼中一些特殊事实的证明可能需要高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但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殊标准。但要明确一个能够恰如其分地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标准是困难的。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学者明确指出了这样的适宜标准。为此,一些国家的司法机关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不要肆意变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但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仍可灵活权衡证明一项指控所需证据的强度或质量。
二、中国家事诉讼多元化证明标准的反思
家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域外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理论争鸣,却未形成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虽采用过多元化证明标准却最终尘埃落定,回归于统一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中国,一些学者提出要根据家事案件的不同类型建立以高度盖然性为基准、以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为辅助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但其提议并不是根据家事案件的不同类型或性质分别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而是从全部家事案件中零星地挑选出一些特定案件或特定事项,认为这些案件或事项应纳入现有特殊证明标准的扩展适用范围。目前相关的立法规定和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几类特殊事项上。
(一)欺诈、胁迫和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
2015 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9 条对欺诈、胁迫和恶意串通提高了证明标准的设置,即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撰写的权威著作,该条款的设置是借鉴了域外国家证明标准的层次化理论,目的是根据“实体法的立法意图”[12]361-362、为了“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保障交易安全的民商事立法目的”[13]231。这些理由遭到了中国许多学者的强烈质疑和一一驳斥。反对该规定的学者认为,域外国家并未提供提高证明标准的比较法论据;中国相关实体法也没有提高证明标准的规定和表述;提高证明标准不仅不能起到维护法律秩序稳定性、保障交易案件的民商事立法目的,反而会有碍于该目的的实现[14]258-279。将这些事实的证明标准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会不恰当地增加受害人或权利人的证明难度,产生负面导向功能[15]89-100;法官恣意裁判风险增大、证伪功能受限[16]140-152;并可能冲击到高度盖然性的一般标准,模糊民事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界线,是对证明标准功能不切实际的期待[14]278。令人费解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阐述该规定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时提醒大家注意:“对于本条规定的提高证明标准的情形,需要严格把握其文义” “审判实践中对这些事实也应适用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17]。似乎在说明本条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仍然是“高度盖然性”标准,只是高于一般“高度盖然性”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而非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尽管存在诸多质疑,2019 年《民事证据规定》第86 条对《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9 条进行了重申,却未对学界的上述质疑作出回应[18]。该规定被学者解读为以确立比高度盖然性更高标准的方式防范高度盖然性标准在实践中被“折扣执行”,不允许高度盖然性标准滑向优势证据标准[14]27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显著低于刑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其准确内涵更接近于“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19]。
刑事诉讼中之所以要适用最高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为了保障人权,避免无辜的人遭受莫须有的罪名。但家事诉讼并不涉及人权的保障,而应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因此,针对欺诈、胁迫和恶意串通设置刑事诉讼中的最高证明标准是不妥当的,反而阻碍权利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尤其是欺诈、胁迫和恶意串通在家事案件中主要涉及财产争议,职权探知主义的适用是克制的,仅凭当事人举证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未免强人所难。并且,家事诉讼中的欺诈、胁迫和恶意串通行为并不涉及经济交易的安全稳定,而是涉及家庭伦理道德的维护,此处若将证明标准提高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不利于对欺诈、胁迫和恶意串通等不道德行为的打击和遏制。因此,在家事诉讼中,对于欺诈、胁迫和恶意串通的事实证明应适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宜,不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从立法原意和实践适用来看,中国民事诉讼中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也应当理解为稍高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但显著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二)口头遗嘱或赠与的证明标准
由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都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9 条和《民事证据规定》第86 条规定中,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的证明标准一同受到了学者的质疑。
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证明标准的提高,立法者的用意十分明显,一是因为口头遗嘱是危急情况下作出的,没有事后可感知的载体以供确认,更容易受到质疑;二是因为口头赠与的事实容易捏造,不可轻易认定,即便未能被认定,被赠与人损失的也仅仅是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13]231-232。可见,立法者之所以提高证明标准,是因为其更倾向于保护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保护赠予人不遭受财产损失,实质上是对不劳而轻易获取额外财产的打压和遏制,似乎是对中国继承、婚约财产、赠与“第三者”财产等案件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抵制,具有较明显的中国式特色。口头遗嘱和赠与涉及中国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将这些事实的证明标准提高“可能更多地出于通过法律的指引作用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16]143。
口头承诺的事项没有实物载体,其在证据形式上本就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即便存在一定的证据材料,法官仍很难形成内心确信。实行高度盖然性标准已经是很高的要求,实在不应“雪上加霜”地将其标准提高至只有在刑事诉讼中才适用的最高证明标准[15]98。因此,将口头遗嘱或赠与的证明标准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一并解释为稍高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但显著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才是合理的。
(三)家庭暴力的证明标准
家庭暴力行为本质上属于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中国法院曾以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要求来认定家事案件中的家庭暴力事实,导致原告不仅需要证明伤害后果还要证明此系被告所为,且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尽管一些受害人提交了报警证明、医院诊断书、鉴定书、证人证言等证据,但只要加害人矢口否认,家庭暴力的事实仍很难得到认定[20]76-79。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对家暴行为的举证责任倒置,并采取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非刑事诉讼证明标准[20]76-79[21]103-111[22]6-22[23]86-93。当前,实务界已经改变了原有不当做法,采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来判定家庭暴力事实是否存在①〔2021〕甘05 民终79 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表示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是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尽管如此,家庭暴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困难重重。出于对前人研究的承继,张海燕等将这种困难依旧归罪于现有证明标准过高,建议采取更低的“或然性平衡”标准[1]2-11[2]60[3]320。殊不知中国家事审判实践中有关家庭暴力的认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的证明困难恐怕已不再是此前证明标准过高的问题,而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综合结果②这些因素包括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偏差、法官人身安全保障问题、安全高效化解纠纷的终极目标、法官调查取证的工作量等。[21]103-111[22]6-22。
由于2002 年原《民事证据规定》第73 条将证明标准表述为“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在该规定实施期间,雷明光提出家庭暴力的证明标准应采“盖然性优势”标准,是建立在对2002 年原《民事证据规定》第73 规定作“盖然性优势”标准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即认为家庭暴力的证明应采民事诉讼证明标准[23]86-93。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 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40 条第2 款规定的“优势证据标准”也是旨在强调家庭暴力的证明应采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非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不是强调家庭暴力的证明应低于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然而,随着2015 年中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8 条对证明标准的表述发生改变,替代了2002 年原《民事证据规定》第73 条规定,中国当前学者普遍认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而将此前规定或学者所称的“盖然性优势”或“优势证据标准”理解为低于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这种理解实际上是脱离了叙述背景下的误读。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主要采取表见证明、举证责任倒置、加大法院职权调查力度的方式来解决家庭暴力的认定难题,未曾通过降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方式,唯一能找到降低认定标准的例证是作为人身保护令申请基础的“家庭暴力”。在美国,仅有少数州在立法上坚持了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多数州采取了较低的 “充足(sufficient)” “合理(reasonable)” 或 “正当原因(good cause)” 标准,其中半数以上州立法规定,人身保护令是否颁发交由法院在较低证明标准的基础上自由裁量[24]。但这种证明标准的降低并非因为涉及家庭暴力,而是属于禁令制度的内容,是因为禁令申请不会完全遵循对席审理和辩论原则,采用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才适用了更低的证明标准[25]。
家事审判中的家庭暴力事实认定(人身保护令申请除外)不存在降低证明标准的理论依据。中国在举证责任倒置和加大法院职权调查力度方面已经降低了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明难度,平衡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地位,不宜再降低证明标准打破现有平衡。
(四)亲子关系的证明标准
中国现有规定中没有关于亲子关系证明标准的特殊规定,因此与其他案件事实一样适用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但是,由于确认或否认亲子关系涉及对原有身份关系的推翻,影响到整个家庭甚至两个家庭之间的身份关系、社会人伦、未成年人及其父母一方或双方的名誉问题,应当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在证明标准上对法官自由心证有更高程度的要求便不足为奇了[26]98-99[27]191。但中国也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亲子关系认定案件因涉及对妇女、未成年子女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应当降低证明标准[1]10。
随着DNA 鉴定技术的提高,直接证明亲子关系是否存在几乎可达到100%的确信度。但是,若不能获得这样的直接证据,实践中法院还需要考虑出生证明、血型、户籍、证人证言、共同生活和抚养事实等多项间接证据综合认定亲子关系或否定亲子关系,并要求达到所需的证明标准。司法实践中对亲子关系的间接证明本就十分困难,若单纯为了慎重起见设定更高的证明标准只会进一步加大当事人行使权利的难度。但若为了保护妇女及其未成年子女利益而降低证明标准也缺乏理论依据。因为利益保护必须建立在具备合法利益的前提之上,尚未判定其是否具备合法利益,何谈保护?肆意降低证明标准只会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退一步说,即便这一逻辑成立,难道合法婚姻关系下的妇女和婚生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就不保护吗?允许“小三”及非婚生子女适用较低证明标准,使其从原本属于“原配”及婚生子女的财产利益中更容易获得抚养费或遗产继承利益,这对“原配”及婚生子女公平吗?虽然非婚生子女具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合法权利,但适用一般证明标准便可,特意为其降低证明标准真的合适吗?符合公序良俗和婚姻家庭伦理观吗?既然是出于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子女利益,为何不为了保护“原配”及婚生子女的利益而提高亲子关系认定的证明标准?最起码他们的合法权益是确定的。显然,为保护妇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降低证明标准的逻辑无法成立。既然提高或降低证明标准都不具有正当合理性,亲子关系的事实证明应保持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为宜。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婚姻效力、婚姻关系的确认和解除、法定继承的分配原则等案件”“因其证明对象涉及社会公益、安定秩序、伦理道德以及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等因素”应提高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1]10;夫妻共同财产认定应降低至或然性平衡标准,但未提供任何论证理由[3]320。这些提议过于轻率,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家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绝大多数都涉及社会公益、安定秩序、伦理道德和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难道都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吗?抑或是,只要是家事诉讼中遇到证明较为困难的事项,都降低至或然性平衡标准?家事诉讼虽具有特殊性,但本质上仍属于民事诉讼,改变传统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规则必须有足够充分、不得不改变的理由,且新设立的证明标准必须能够切实地对双方当事人都更加公平公正,才有予以改变的必要。如此轻率地变更一般证明标准,恐怕容易造成司法适用上的混乱和不公。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法律规定中的一些特殊事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口头遗嘱或遗赠)适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即便从立法原意上看也应理解为稍高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远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家庭暴力适用更低的证明标准同样缺乏理论依据。现有特殊证明标准的规定尚且遭受广泛质疑,其他事项在缺乏足够论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轻易纳入特殊证明标准的扩展适用范围。中国某些学者提议的家事诉讼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理由不够充分。
三、家事诉讼层次性证明标准的理论构建
既然不宜在家事诉讼中构建以高度盖然性为基准、以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为辅助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到底如何设置证明标准才是恰当适宜的呢?不管是中国还是域外理论和实务的探讨,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对于家事诉讼中一些较为特殊的事项,若适用高于民事诉讼而低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到底何种标准才恰如其分呢?抑或是保持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变,但如何实现在具体的案件中灵活权衡证据的强度或质量呢?为解决这一难题,从多元化证明标准的理论来源——层次性理论出发探寻答案。
(一)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理论
层次性是证明标准的基本特征,多元化证明标准来源于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理论。有学者认为,根据证明标准本身的抽象和具体程度,证明标准可分为 3 个层次:第 1 层次是最为抽象的证明标准,即理论界探讨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第 2 层次是法律规定中的各种证明标准,如 “证据确实充分” “排除合理怀疑” “高度盖然性” “或然性平衡” 等标准;第 3 层次是具体、明确、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如各种实物证据的具体采信标准、科学证据的采信标准、电子证据的采信标准等[28]102-105。
第 1 层次抽象的证明标准并不复杂,“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认同。人们通常所说的证明标准是第 2 层次意义上的证明标准,这一层次的证明标准又可细分为多个层次[29]50。美国学者曾将之划分为 9 个层次,由高到低分别是:“绝对确定”,这是任何法律都不要求的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刑事案件中的定罪标准;“明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适用于死刑案件中保释请求的驳回以及部分民事案件;“优势证明”, 适用于大多数民事案件以及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肯定性抗辩;“合理根据”, 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及扣留、控诉书和起诉状的发布、撤销缓刑及假释,以及执行逮捕;“合理相信”, 适用于拦截和搜身;“有合理怀疑”, 适用于宣告无罪;“怀疑”,适用于开展侦查;“无信息”, 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30-31]。德国学者曾以刻度盘为工具将证明程度划分为100 份,从0%~100%分为不同级别:0%为绝对不可能;1%~24%为非常不可能;26%~49%为不太可能;51%~74%为大致可能;75%~99%为非常可能,即高度盖然性;100%为绝对可能。日本学者也曾把法官的心证按强度分为 4 级:第 1 级为微弱的心证;第 2 级为大致的心证;第 3 级为盖然的确信心证;第 4 级为必然的心证[32]65。在司法实践中,待证事实的证明需要达到何种程度的证明标准应当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决定了审判是否公平、公正。若证明标准设置得过高,举证责任就会过重,对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不公平,并影响到审判的效率;若证明标准设置得过低,争议事实的认定便变得草率,对不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也不够公平。因此,各国根据待证事实的性质和类别分别设置适宜、合理的证明标准,由此便产生了多元化证明标准。
一般而言,不同程序适用不同程度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较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稍高,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最高[27]110-112。而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于一些具有特殊性质的事实证明,也可以设置特殊标准。以英国为例:在刑事诉讼中,为避免无辜的人被定罪,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法律规定中的最高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但被告人承担积极抗辩事由的证明标准却仅需达到“或然性平衡”;民事诉讼中一般采取“或然性平衡”标准,但藐视法庭、律师的职业不当行为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申请文件更正需达到“强有力的、无可辩驳”标准,户籍变更应达到“明确无误”标准[33]。可见,证明标准本身是多元的、富有层次性的,各个国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不同性质的事实认定规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事实认定及判决结果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的。
由于第 2 层次的证明标准仍较为抽象,张卫平认为证明标准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一种为我们所掌握、适用的,同时又是外在的、客观统一的、具体的证明尺度”是不存在的[32]68。王敏远也认为,在神明裁判与法定证据消失之后,法律就不再可能对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作出规定[34]。但何家弘认为,在人们常说的第 2 层次证明标准之外还存在第 3 层次的具体证明标准,这种具体标准也是“标准”,因此可具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当然是存在的。尽管再具体的证明标准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法官的自由心证,但越是在法官队伍道德修养和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就越需要法制化、规范化的具体证明标准规范司法证明活动。他认为,第 3 层次的证明标准包括两层内容,一是单种证据的采信标准,二是全案证据的采信标准。在具体的案件中,不管是单种证据还是全案证据都要从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和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考察,虽然不能就所有证据的采信问题都制定具体的明确标准,但可以部分构建第 3 层次证明标准。事实上,这样的标准在实践中已经存在,如《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电子证据的采信标准等[28]104-105。
笔者赞同何家弘的观点。第 3 层次的证明标准是对第 2 层次证明标准的细化和延伸,司法实践中为了便利当事人举证和法官裁判,针对部分特殊类型的案件或事项制定较为具体的采信标准是完全可行的。中国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推出的家事诉讼示范证据清单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在家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代理率不高,法律意识和举证能力普遍不足以克服举证困难,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制定具体有可操作性的第 3 层次证明标准不仅能够起到指引当事人举证的作用,也有助于规范法官审理案件。对于家事诉讼中一些较为特殊的事项,设置恰如其分的证明标准抑或是灵活权衡具体案件中证据的强度或质量可能恰恰需要通过这种第 3 层次的证明标准来实现。
(二)家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构建
家事案件类型纷繁复杂,出于对真实利益的追求、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道德的指引,对家事诉讼中的一些特殊事实有增加证明强度或降低证明强度的特殊要求无可厚非,但若将证明标准提高至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显然是不恰当的。从各国实务见解和学术观点来看,家事诉讼中是否可以根据特殊事实证明及案件情况适当降低或提高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仍值得商榷。若企图依靠第 2 层次抽象证明标准的改变来实现家事司法公正只会南辕北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维持高度盖然性统一证明标准的基础上部分构建第 3 层次具体证明标准方可解决这一难题。
首先,在第 2 层次抽象证明标准上增加额外的特殊证明标准容易造成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混乱。从证明标准本身的特质来说,法律规定的确可以在 0%~100% 的区间任意设置多个证明标准,但理论和实务中长久形成和适用的证明标准寥寥,无非是或然性平衡、高度盖然性和排除合理怀疑这几个为数不多的证明标准,按百分比可大致表示为51%、75%和95%。在这 3 个常用证明标准之间拉开适当梯度,尤其是将它们通常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程序或者适用于不同性质的证明事项,易于为法律实务工作者区分和把握。
若在这 3 个证明标准之间插入60%、80%的证明标准,则容易造成混乱。尤其是当新增的60%、80%的证明标准与原有的75%一同用于家事诉讼程序且具有相同性质的证明事项时,混乱几乎不可避免。因为审判实践中的各种事实证明是无法具体量化的,法官虽然容易辨别出某个事实的证明度达到了51%而未达到75%,或达到了75%但未达到95%,却很难断定虽达到了51%但是否达到了60%,或者虽达到了75%但是否达到了80%。换言之,由于证明标准之间的梯度区分并不明显,只会增加法官肆意裁判的风险,增设证明标准的预期目的难以实现。
其次,既然不宜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相同性质的证明事项适用不同证明标准,可否对家事诉讼中涉及的犯罪事实、准犯罪事实或身份关系事实这些具有特殊性质的证明事项按照类型划分,提高证明标准至80%或降低证明标准至60%呢?或者直接将证明标准的降低或提高设置为现成已有的51%和95%证明标准也可以避免适用混乱的问题。但这种做法同样不可,因为提高或降低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缺乏理论依据。
具体来说,家事诉讼中涉及的特殊性事实包括监护侵害案件中的性侵、虐待、遗弃、暴力伤害,撤销婚姻或婚姻无效案件中的欺诈、胁迫,继承案件中的恶意串通,确认或否认亲子关系案件中的通奸,离婚案件中的赌博、吸毒、家庭暴力、重婚等。如果主张对这些事实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无非是因为这些事实比较重要,不可轻易认定,但这些事实本身就不好证明,再提高证明标准只会增加权利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难度,有失公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学者一直在倡导降低家庭暴力证明标准的原因。但若出于保护受害者而降低特殊事实的证明标准同样缺乏充分理由,因为这样做将导致事实认定过于轻率。为了保护受害的弱势一方,完全可以通过引入事案解明义务、部分举证责任倒置、法官合理判定举证责任转移、加强职权调查等方法予以调整,不一定非得降低证明标准。况且降低证明标准并不能起到多么实际的效果,反而在各方面制度努力改进的情况下超出实质公正的修正程度,造成新的不公。事实上,法律很难在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之外找到一个更中立、更公正的立场,例如,监护侵害案件到底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而降低证明标准还是为了确保监护人不被无辜冤枉而提高证明标准?亲子关系认定到底是为了保护已婚女性及婚生子女的利益提高证明标准还是为了保护未婚女性及非婚生子女的利益而降低证明标准?在尚未找到一个更加合适方案的情况下,保持传统的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不变才是最妥当的选择。
再次,围绕高度盖然性构建第 3 层次具体证明标准才具有可操作性。第 2 层次的抽象证明标准事实上将 0%~100% 的证明度大致划分为几个小区间,与其说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是精准的75%和95%证明度,不如说它们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或区间。域外各国和中国学者所寻求的“稍高于高度盖然性而低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动态证明标准”或“清晰且有说服力的标准”从本质上来说仍是高度盖然性标准。要想对证明度设置得更精准一些,不能寄希望于这些虚幻的抽象标准,而应当依靠第 3 层次的具体证明标准。因为只有具体证明标准才能精准地实现诸如70%或80%的证明度。这就好比要在“合格”“良好”和“优秀” 3 个梯度的学生中找出介于“良好”和“优秀”之间的学生一样,依赖更具体的标准如各科平均分操作才更加实际,也避免了人为的主观臆断风险,评判起来更具操作性和客观公正性。
总之,家事诉讼中一些特殊事项的证明如果有必要对证明强度有所调整以适应不同情形下的需要,这种对证明强度的浮动性要求恰好可以通过第 3 层次具体证明标准予以实现。寄希望于第 2 层级的证明标准来实现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即便以“高度盖然性”为基准在家事诉讼程序中设置了较低的“或然性平衡”标准和较高的“清晰且有说服力”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仍容易发生模糊和混乱,法官无所适从,只能恣意裁判,影响到法律的安定性,有架空实体法规范之嫌[11]145。与其在抽象的第 2 层次证明标准上做文章,不如直接在家事诉讼中确立统一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以保持法律的统一性和安定性,并在必要时辅之以具体的第 3 层次证明标准,进一步对特殊事实的证明力度和强度提出适宜要求。例如,2013 年《广东法院家事审判工作规程(试行)》第14 条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的伤情照片、医院病历、接警或者出警记录、带有威胁内容的录音和手机短信,加害人出具的悔过书、保证书,受害人报警时的电话记录等,均可以作为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存在的直接证据”便可以作为第 3 层次具体证明标准,只要当事人提供了其中的一种或多种证据,满足相应要求就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存在。这种具体的证明标准比将证明标准降低至“或然性平衡”有效得多。当然,这只是对第 3 层次证明标准进行尝试的一种设想,具体如何制定第 3 层次证明标准仍有赖于经验丰富的审判实务工作者的集体智慧。
四、结语
在家事诉讼中,不管是高职权主义的公益案件、非讼案件,还是职权主义稍弱的身份诉讼案件,抑或是适用准辩论主义的财产诉讼案件,都是家事案件,理应适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提高或降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会为家事审判实践带来多大改善,反而模糊了判案标准,让法官无所适从。中国家事诉讼中实体事项的证明应回归“高度盖然性”的统一证明标准,并进一步探索完善某些特殊事项证明所需的第3 层次具体证明标准。“实践证明,精细化的规则指引远比抽象的证明标准分层更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规范法官自由心证、实在化事实认定活动,从而也是对证明标准主观性和自由心证局限的有效克服。”[14]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