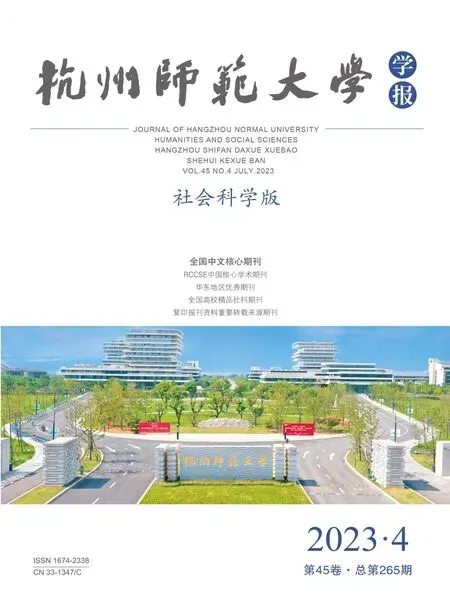近代宣教读物的特殊编译模式
——以《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编印为例
李思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新教来华早期,传教士们编印了诸多报刊和书籍,以《英华字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国丛报》以及中译《圣经》等最为著名。《英华字典》是最早的中英字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分别创办于马六甲和广州,被视为现代中文报刊的源头;《中国丛报》是传教士在中国较早创办的英文杂志;《圣经》中译本的翻译出版就更是新教来华初期的一大成就。除此之外,传教士们也撰写、出版了一些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宗旨的中文读物,这些布道读物是针对中国读者撰写或翻译的,如梁发的《劝世良言》、马礼逊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等较具代表性。《劝世良言》《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由中国人或外国人自撰,是新教出版史上较早问世的中文布道书;《张远两友相论》的意义则在于它的对话体、文学性以及可观的出版量。本文将要讨论的《圣书日课初学便用》一书,其刻印亦由梁发主持,译、编则经由众手。这本宗教读物的编译、印刷、传播及后来的遭禁,使它在近代印刷出版史上颇具典型性。《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编译出版,因为有新教来华人员的参与,而在编译模式、文本属性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因素,是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一次译印活动。
一、关于《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记载
麦沾恩《梁发传》的英文版曾经提到《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圣书日课》这本书是英国出版的学校用书,系由《圣经》文本萃选而成,无注解,无评论。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也是从《圣经》中译本里节取相同段落而成。中文译本是在广州印的,监印人为梁发。居住广州的外侨捐助了初版费用,英美两国的圣书公会则资助了第二版。这书三卷为一套,不仅向(参加府试的)生员(students)分发,还由梁发携带到广州周边的村镇,连同马礼逊编印的小杂志一道分发。”[1](PP.69-70)
不知何故,胡簪云的中译本《梁发传》在正文中删除了这段文字,但又在书后的“附录一”(即梁发著述简表)中提到了这本书:“一八三一年,在广州著《圣书日课初学便用》。此书系英国及外地学校协会所出的《圣经》课本的翻译。初版由广州地方的英美人和商行捐资镌版及印行。一八三二年再版则由英国及外地学校协会出资印刷。”[2](P.143)这是沿袭了伟烈亚力的记载。[3](P.150)
《马礼逊回忆录》多次提到这本书。马礼逊说:“邓拿单先生,公谊会信徒,长期在华行商,给了联合会二百银元以印刷中文的《圣书日课初学便用》。裨治文先生正为此挑选材料。小儿也在霍克博士的《祷告辅导》中选出经节。我希望一旦有钱,就用来出中文版。”[4](PP. 440-441)这里的“祷告辅导”,指霍克博士(Dr. Hawker)所写的“HelptoPrayer”一书。霍克博士(Dr. Hawker)即Robert Hawker,书的全称为TheChristian'spocketcompanion;oranhelptoprayer,gatheredwhollyfromtheScriptures。[5] 马礼逊后来又提到,英国海外学校协会的《圣书日课》在中国出版[4](P. 473),时为1831年。
由以上的记载可知:(一)《圣书日课初学便用》所据英文底本是英国海外学校协会出版的“ScriptureLessonsforSchools”一书,前者虽是后者的中译本,但并不是新译,而是从马礼逊、米怜合译的中文《圣经》里节取相应段落“组装”而成。严格来说,这本书的译者是马礼逊、米怜,但这本书的编纂过程颇耗人力。(二)裨治文参与了《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编纂工作,马儒翰也曾从霍克博士的《祷告辅导》中选出一些经节供编纂使用。(三)居住广州的外侨捐助了初版费用,英美两国的圣书公会则资助了第二版。(四)这本书的印刷工作由梁发主持完成。(五)梁发曾在中国人中间大量分发此书。他不仅向(参加府试的)生员分发,还分发到广州周边的村镇。以上的记载也留下了一些疑点及相互矛盾之处。
马礼逊多次提到这部作品,但并没有说清楚这本书究竟是谁的。1831年7月13日,时在澳门的马礼逊写信给雅裨理牧师,“梁发正忙于他的《圣经日课》,希望两三个月就可以完成。但我终日为他的安全提心吊胆,因为他要把这些印刷品带到广州城去[4](P.449)。这段话中提到“他的《圣经日课》”,“他的”是译者邓肇明在翻译时加的,指梁发正在做的印刷工作。英文原文是“Leang-Afa is busy on theScriptureLessons”,马礼逊没有说梁发是此书的作者或译者。
在另外一些场合,马礼逊又说过:“我的《古圣奉神天示道家训》及《圣经日课初学使用》系一式印刷,为我们的信仰提供历史、教义和实践上的注脚。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把这两本书当作小册,拨专款大量印行。版面已经刻好了,一俟有更多的钱便可刷印。我希望寄一本《圣经日课》给你们。”[6](P.518)这是马礼逊1832年在澳门写给圣教书会(The Tract Society)的信。《古圣奉神天示道家训》即DomesticInstructor一书,此处《圣经日课初学使用》系笔误,当是《圣经日课初学便用》,即ScriptureLessonsforSchools一书。这一次,马礼逊的话又有歧义,因为他说“我的《古圣奉神天示道家训》及《圣经日课初学便用》系一式印刷”,前者是“我的”没有问题,《圣经日课初学便用》也是“我的”吗?
伟烈亚力则将《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归到了梁发的名下,列为梁发已出版的个人成果(“his published works”)。这一做法若非出于误记,则可表明伟烈亚力认为梁发对此书出版的贡献最大。
二、梁发与《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编译出版
马礼逊的含糊表述隐藏了梁发参与此书编纂的相关信息。因此,如今要解决的问题是梁发除承担此书的雕刻及印刷工作,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此书的编纂工作?而编纂工作又包括中文《圣经》译文的节选、文字的润色修订、书稿的誊抄与整理等,梁发所承担的是哪些方面工作?贡献如何?马礼逊曾坦承,“碰到难题,若没有饱学的本土人从旁指点,自己就无法解决”[5](P.513),梁发算是“饱学的本土人”当中的一位吗?从常情推断,梁发当是参与了此书的编纂的,但是要为此推断提供证明并非易事。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于嘉庆乙亥(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梁发参与撰稿。麦沾恩云,“梁发在马六甲时,曾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那个月刊上发表许多论文”[2](P.144)。伟烈亚力也指出,米怜、马礼逊、梁发、麦都思等四人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主要供稿人。[7](P.19)
至于梁发个人著述的单行本,则以1819年出版的《救世录撮要略解》为最早。该书共37页,除正文外,另附《圣经》节选、祷文数篇、圣诗三首和《十诫》。关于此书,值得注意者有如下四点。一是这本书的意义。麦沾恩认为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写成的改正教布道书籍”[2](P.25)。二是写作地点与动因。写作地点是广州和高明,动因是梁发要在家乡高明传道。梁发离开马六甲重返广州,是在米怜夫人病逝(1819年3月20日)一个月后。稍后他又回到故乡高明,“梁发一心要拯救他的本乡人,因此就做了一本布道小书,里面讲到偶像之无用与改信基督之必要”[2](PP.24-25)。三是写作及出版过程。梁发将原稿拿给马礼逊看,获得马礼逊认可并由马礼逊安排付印,印量200本。四是这本书的遭遇。此事遭人告发,官府得报派人前来搜捕,梁发被捕入狱,被打了三十大板,书版也被没收。梁发交了罚金,始获释放。[2](PP.25-27)这次著书所遭遇的坎坷,对梁发刺激和影响极大。他愈挫愈勇,信心更加坚定,并且由印书而著书,在信仰与才干两方面均赢得马礼逊、米怜的赞赏,益受重视和信任。
马礼逊于1820年11月(或12月)给英国圣书公会的信中写道:“一位本土的印刷工人,自米怜给他施洗后已经有些日子。他根据新约的一些经节,写了一本小册子并予以印行。他认为读这本书要比我们所出版的其他书籍更能启发他的心灵(more edifying to his mind)。自此以后,他要为义(righteousness)受逼迫了。在这里我盼望上帝之道既已启迪了他,定会继续保守他的心怀意念。我相信他真正感受到上帝真理的大能力;由此可见《圣经》在这个拜偶像国家中的功效。”[4](P.38)这里说的本土印刷工人便是梁发。米怜也对重返马六甲的梁发更加器重,“接待之如兄弟,赞成他专心研究《圣经》”[2](PP.29-30)。自此之后,伦敦会传教士对梁发有了更高期许,他不再只是一个印工,而是一心研读《圣经》、志在撰述的布道人了。他与马礼逊也有了更高层面上的探讨,例如中文《圣经》的翻译问题。马礼逊说,“梁阿发惋惜圣经某些难明的章节,譬如先知书,因为他缺少释经的书籍”[6](P.395)。
1820年10月20日,米怜在马六甲写信给马礼逊,随信寄上了《张远两友相论》(Treatise on the Soul)的草稿,希望马礼逊代为修改。约在同时,梁发也写成了《救世录撮要略解》。其他传教士的部分著述也得到过梁发的帮助。帝礼士名下的两篇作品《鸦片速改文》《新嘉坡栽种会告诉中国做产之人》便是梁发协助撰写或翻译的。[7](PP.79-80)
1820年,《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英文原书ScriptureLessonsforSchools在伦敦出版。[8]马礼逊大约是在返回英国期间得到了这本书。1826年9月19日,马礼逊从英国回到澳门,这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马礼逊首次提到这本书:“儒翰每天早上学几段《圣书日课初学便用》。之后,我们一同看这几段的原文,又在中文圣经中重读一遍。”[6](P.469)
梁发接触这本书,应在此时,因为梁发曾在一封写于1827年9月的信中说,“愚今在老先生马礼逊门下,习读真道,一载有余”[2](P.40)。从1826年9月到1827年9月,正是“一载”。马儒翰所读的《圣书日课初学便用》英文原书,梁发必曾寓目。马礼逊在其寓所主持此书的中英文对读,梁发亦应参与。1827年夏季,梁发随马礼逊同住澳门,日夕过从。马礼逊说:“梁发已与我同住了一个夏季,他曾读过《圣经》的大部分,且每日前来求我为之解释其不能了解之点,退而将所得以笔记之。” [2](P.38)
梁发在这期间又有译著。其中,最得马礼逊称赏的,是他对保罗《致罗马人书》的意译。马礼逊说:“梁发曾取保罗《致罗马人书》而意译之,此书对于我辈外国传教士甚为有用,因此书提示我侪以适用之字句,且使我侪可自评其观念之错误而改正之。” [2](P.38)
《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对梁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一个最直观的证据是:《劝世良言》在节录《约翰福音》时的章节选择与《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完全相同。《约翰福音》第3章共36节,《圣书日课初学便用》节选的是第1至21节,梁发在《劝世良言》中所选摘的也正是第1至21节。
除了章节征引可以证实《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对梁发有影响,从梁发在《劝世良言》一书中的具体论述也能看出《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对他的影响。在《劝世良言》卷二“崇真辟邪论”这一题目下,梁发共撰有四篇“论”,前三论分别为“论救世主耶稣降世之意”“论富人难得天堂之永福”“论问鬼之邪妄”,第四论题为“圣经若翰福音篇第三章论复生之义”。这第四论,是对《约翰福音》第3章第1至21节的重述(译)。这部分内容,见于《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卷2第9章,该章题为“被圣风造化新作之心为最紧的”[9](PP.17-19)。与英文原著相对应的内容,是在ScriptureLessonsforSchools一书的Part Ⅲ,题为“The Necessity of Regeneration”。[8](PP.104-105)《劝世良言》该篇以“论复生之义”为题,即与《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原书所用标题“The Necessity of Regeneration”意义接近。
从上述马礼逊、伟烈亚力的相关记载,以及《劝世良言》所受影响的痕迹可以断定,梁发确实深度参与了《圣书日课初学便用》一书的编译出版。
三、《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等书之传播与遭禁
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为分发派送这些书籍,非常用心。卫三畏曾说:“为了制作这些书我们雇佣了当地人,梁阿发就是在看他刻的印版的过程中成为第一个皈依者的。他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印书,而且已经散发了好几千本。不久前在广州举行乡试,来了两万五千多人。梁阿发让一些苦力将他的箱子带到了大厅,在那里他迅速地将《圣经》分发给那些聪明的年轻人,他一干就是三天。”[10](P.24)这些都表明,梁发不只参与了这些布道书籍的编、译与刻版,还将书籍四处分发派送。
梁发与屈亚昂一年内就在广东省内分发布道书籍4万册(份)。其中包括100部《新约》(全5册)、5000部《圣书日课初学便用》(5册)、5000张单页;另有100部《圣书日课初学便用》送往广西,400部送往沿海地区,400部送往南洋。[11](PP.27-29)可见《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分发量是一度超过《新约》的。
马礼逊在致伦敦会的信函中,曾提到他们到处分发《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情形。他们不仅在中国本土分发,还带到了高丽、日本和琉球。马礼逊说:“我请郭士立带备中文圣经、祷告书和小册,并一百份《圣经日课》,在高丽、日本及琉球群岛分发;如蒙上天照顾,他就要出发了。”[6](P.521)
基督教书籍的印刷与散布在清朝是违禁行为,1819年梁发在家乡高明刊刻《救世录撮要略解》一书就因被乡人告发,遭官府逮捕罚款。但“民不告,官不究”,大多时候这仍处于未加控制的放任状态。伟烈亚力在谈到梁发、屈亚昂到广州分发宣道读物时说,“他们自由接触(应试的)生员,向他们分发的小册有7000多册”[7](P.12)。梁发在1819年的被捕,可以理解为一次地方性事件。到了1835年,基督教书籍在中国本土的派发行为引起更高层级的警觉,“北京政府特派钦差一人到广州去查究及逮捕一切为外人做书和为外人印刷华文书籍的中国人”[2](P.95)。
这次查办,发生在1835至1836年。遭到逮捕审讯的是屈亚昂之子屈亚熙,另外马礼逊之子马儒翰(官方称“咉吗”)和部分在华洋商也接受了审问。梁发闻风潜逃,避往马六甲、新加坡。不过这次官方查禁事件,受影响的只是英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等美国传教士仍能继续在广州、澳门等地从事印刷出版和布道工作。据麦沾恩记述,马礼逊去世后的五年中,“广州地方不见一个英国传教士,幸而美国传教士能在不安定的局面之下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可是这时的工作真是十分的困难而且成效极少”[2](P.98)。梁发再回广州,已是1839年的年底了,适值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梁发之子梁进德亦受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之聘担任英文翻译。梁发兼得天时、地利、人和,“处境稍为安全”,遂能放心大胆地“在广州和附近省城各地进行工作”。[2](P.100)这段时间,传道形势极为有利。马礼逊的女婿合信、米怜的儿子美魏茶也受伦敦会之派来到广州,这对梁发是极大的鼓舞。1840年3至4月间,梁发为4个中国人施洗,广州共有教友12人。[2](PP.102-103)
清廷对《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等书的这次查禁事件,从当时官方立场来看,只是诸多“社会案件”中的普通一件。在浩如烟海的清代官方文献史料中,幸而留下了这次查禁事件的有关档案(下称“禀文”)。学界已有专文对这件档案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12]以下不拟重复叙述事件本末,而是着重分析在官方询问时屈亚熙、洋商、马儒翰等所讲述的刻书情由,以及官方为事件定性时所引的“成例”。
关于这次查禁的书籍,禀文记载,经“前署广州府知府潘尚楫暨委员周寿龄督同南海、番禺、香山等县”地方官员查访,在澳门洋人住处“查起夷书八种”,分别是《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正道之论》《赎罪之道传》《诚崇拜类函》《赌博明论略讲》《救世主坐山教训》《圣书日课》《圣书袖珍》。有关最后三种,禀文载:“均无撰人名氏。其标写刊刻年分,不出壬辰、癸巳、甲午三年。”[12](P.94)壬辰、癸巳、甲午分别为道光十二、十三、十四年,即1832、1833、1834年。
关于这些书籍的刊印经过,禀文分别介绍了屈亚熙和马儒翰的供述。禀文介绍屈亚熙供述道:“据供,伊随父屈亚昂学习刻字,不通文义,现蒙查获各书,系道光十二、三、四等年咭唎国住澳夷人吗,雇倩伊父同伙梁亚发到澳刊刻,伊亦随父帮刻两次。其底本不知来历,刻成后即交吗收去,不知如何分散。伊并无勾串夷人刊刻传教之事。吗于十四年六月病故,伊仍在澳觅工,致被访获。伊父及梁亚发闻拿避匿,不知逃往何处。吗有子咉吗,可以提质等语。”[12](P.94)同时,官方也请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询问洋商伍绍荣等,打听在广州经商的外国人的来历及相关书籍的刊刻情形。禀文载:“据该洋商转据夷商喇吐等信复,此项夷书由来已久,因天竺、咭唎、咪唎等国有人通晓汉文,能刊汉字,但不工致,故携书至澳,交吗刊版刷印,带回本国,在澳夷商亦多喜买看,并非内地编造等语。”[12](P.94)
屈亚熙既然将马儒翰供出,官方遂讯问马儒翰。禀文载:“讯据供系咭唎国夷人,先与其父吗至澳门居住,夷书由来已久,不知起自何年,亦不知何人编造。因系崇信天主劝人为善之书,各本国之人要看者甚多,从前仅有钞本,后虽刊刻,不能工致,是以伊父于道光十二、三、四等年在省托相识之刻工梁亚发,雇倩屈亚昂与其子屈亚熙前往澳门夷楼刊书几次。每次约有数月,不能确记日期。每月每人工银四元。共刻过《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及《诚崇拜类函》等书八种。刻毕屈亚昂等即行辞出。伊父亦于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省病故,地保、洋商都可查问。伊在省在澳止管买卖,并未经手夷书。” [12](P.95)
关于官方对这次事件的定性。先看书籍定性。禀文载:“其大旨类皆劝人崇信耶稣。”官方认定这些书籍大旨皆“劝人崇信耶稣”,这个定性是准确的。但是官方对这些书籍的写作水平很不以为然。禀文载:“详核各书,或割裂经传,文义不通;或近似鼓词,语言鄙陋。”[12](P.94)对参与人员的定性,由上引禀文中屈亚熙、喇吐、马儒翰的供述或答词可知,相关参与人员重点强调了如下四点:(一)这些书籍“由来已久,不知起自何年,亦不知何人编造”;(二)这些书籍于风化有益,“系崇信天主劝人为善之书”;(三)读这些书籍的人主要是外国人,“各本国之人要看者甚多”;(四)参与刊刻者只管受雇刻书,并无更多了解和参与,即禀文所述“反复研讯,诘无内地勾通编造传习情事”。
这些避重就轻的供述,为案件最终从轻发落提供了可能。官方为事件定性,除参考以上有关人员的供述,还援引乾隆四十九年、嘉庆二十年查办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相关案件的处置成例。最终,屈亚熙“照违制律仗一百、加枷号两个月”;两位在逃人员(梁发、屈亚昂)“等到案审明”再做发落,“所得工资,不能记忆确数,免其追缴”——这一条最能见出官方确属“从轻发落”;马礼逊父子“刊书寄回及散给夷人”,“应予免议”,“饬将其父刊存违禁书本、板片尽行呈缴销毁”。[12](P.96)
四、小结
从《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编译出版及分发、遭禁的整个过程,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初步的判断:(一)清政府包括地方大员对新教传教士所刻布道读物的判断和定性并不明确,更多是从政教秩序(“正风俗而绝异端”)及地方治安角度看待的。(二)道光年间的教禁依然严厉,但执行略有松动。对马礼逊父子、屈亚昂父子及梁发等人的处置固然严厉,但将中国人受雇参与刻书跟信教、传教区分开来,也颇为人性化。官方态度之友善,当事人是有感受的。据伟烈亚力说,屈亚熙被羁押了较长时间,但“所受的待遇不错”[7](P.12)。事实上,参与刻书便是开始了教义的研习,如前引卫三畏说到梁发时曾提及:“梁阿发就是在看他刻的印版的过程中成为第一个皈依者的。”(三)从不同宗教文化之间交流碰撞的层面看,清朝官方及主流知识界尚不清楚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两个教派的背景和差异,对新教传教士所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缺乏了解,因此未能引起足够的警惕。(四)从本国文化政策的水平与效果看,当新兴资本主义扩张力量迫近国门并已开始在中国本土扎根时,官方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除视为违禁个案加以查办和严惩外,并无追踪了解外来宗教文化和书籍报刊的兴趣。
具体到《圣书日课初学便用》一书本身。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散发数量一度超过《新约》,也在于其编译出版方式的特殊性。它是由马礼逊、裨治文、马儒翰、梁发、屈亚昂等多国人员参与完成的;虽是中译,却非新译,而是自马礼逊、米怜《圣经》中译本中择取相应段落组装而来。另外,其编译时间几乎与梁发《劝世良言》一书的撰写同步,《劝世良言》不仅在节录《圣经》文字时参考过《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在具体论述方面也受到《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影响。至于该书出版后广为散发,一度引起清朝官方的注意,成为1835年被清廷查禁的八种书籍之一,就更是出版史上的重要事件。总之,在新教早期来华出版史上,《圣书日课初学便用》的编译出版,是非常特殊也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次编译出版活动。(1)学界对《圣书日课初学便用》仍很陌生,对它的关注仍然有限。戈公振《英京读书记》曾提到梁发写有“《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劝世良言》小书”。近年不少出版社在重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时,将《英京读书记》中的两种书名,或误标点为“《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劝世良言小书》”,如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岳麓书社2011年版、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或误标点为“《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劝世良言小书》”,如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