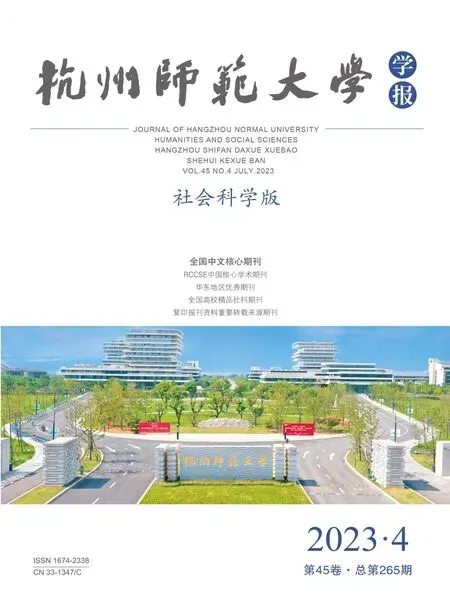牟宗三与唐君毅气论之比较
蔡家和
(台湾东海大学 哲学系,台湾 台中 40704)
一、前言
唐君毅与牟宗三先生同为“当代新儒家”之代表人物,面对当代中西学术之会通与诠释,在诸如气、物质、形质、材料、形下或自然等词汇之理解上,则是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进路。本文则专就“气”这一概念,来探讨并比较两位先生之研究方法与结果。
唐先生之言“气”,常就中国哲学固有之意义来发挥,其视“氣”为“气”,乃是一种云气上升与下降的过程,具备了自动义、历程义、流行义,甚至包含了精神价值义。至于牟先生所言“气”,其中一部分撷取于程朱学的形下之气,另有一部分则撷取于西学的物质义,于是站在气必须为理所御之观点。否则,只言气,则此“气”将归于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若以气化、物化之自然主义为主,则人也将下堕而同化于物,造成理想性之灭杀,而天理灭矣!此即是牟先生所担忧者。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可以先试问:“气”者,是何意涵?这里先依中国哲学之发展来略做介绍。先秦诸子百家之中,尤以阴阳家最重气。此外,如老子所言“冲气以为和”,庄子言气化之生成观,孟子亦有养浩然之气与夜气等说。到了汉代,儒家与阴阳家的结合,则形成一个气化宇宙观,其中以元气来形容太极。魏晋时代,世人特重人之情才与个性。宋明学则有所谓的理气论,同时也有气论的主张。明末清初,刘蕺山与黄宗羲师徒可谓重气思想之代表,视四气之周流,即若元亨利贞、诚通诚复。到了王夫之,他继承张载学说而反对心学,并且修正程朱,可谓转入气论一家之言。至清代乾嘉时期,戴震继承汉学,再次提出气化宇宙观,视一阴一阳之“道”同于五“行”;阴阳五行都是气——此乃尚未成形之气,至于天下万物、品类,则为已成形之气,也就是一切皆是气!而所谓的形上与形下,只是气之成形前与成形后的不同而已,前者为未定形之气,后者为已定形之气。以上大致为中国哲学气论之时代发展。
而在西学主流中,诸如形下、气、情感、物质等这些近似“气”的语词与概念,则常未被以第一义看待,甚至是一种贬义(如柏氏之“贱肉体”)。这种看法与中国的程朱理学相近。他们视感性犹如脱缰野马,若不加以理性控制,则将“盲爽发狂”而导致灾难。也就是说,西方广义之理性主义与宋明的程朱理学,都有重理贬气的倾向。(1)《船山全书》载:“苟其识夫在人之气,唯阴阳为仁义,而无同异无攻取,则以配义与道而塞乎两间(因气为理)。故心、气交养,斯孟子以体天地之诚而存太极之实。若贵性贱气,以归不善于气,则亦乐用其虚而弃其实,其弊亦将与告子等。夫告子之不知性也,则亦不知气而已矣。”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054—1055页。这里故将等同告子,提到《易传》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若立天地阴阳以比配仁义,则气不应该被贬低。又提到“贵性贱气”,此乃暗批程朱,因此引文出自《读四书大全说》,系针对程朱一系《四书大全》而起,船山视程朱之学容易尊性而贬情。朱子批告子为气论,而船山也是气论,所以船山反对朱子的解法。
二、牟先生之气论
(一)孟子的“同嗜”无必然性
牟先生的学问大体系建立于儒家与康德之对校。他有时以儒家来提升康德,有时则以西方的民主科学与康德之重思辨知识来补充中哲之不足。在这些过程中,牟先生或有意或无意地将西学之格义,渗入于中哲之诠释。有趣的是,西学主流之重理性传统(2)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皆可谓西方哲学之主流。柏拉图的“哲人王”,要由理性之最高者来担当。亚里士多德视人为理性动物,重视逻辑与理性推理。康德则提出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建立了重视理性之传统。,恰好与程朱理学(3)唐君毅亦曾把东西方之朱子与康德做比配,其曰:“至于朱子之承程门之言心性,以融合于周濂溪、张横渠之太极阴阳之天道论;则正大类于康德之本大陆理性主义之传,又受经验主义者如休谟等之影响,而主张知识不能及于可能经验以外。康德除依纯粹理性,以言成就科学知识之可能条件外,尤重道德理性。以为唯由道德理性,可建立形上学之信仰。此则西方思想之发展之转近乎东方中国者。”见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唐君毅全集》第10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438页。之主张有着相似性,而这也让牟先生找到了可发挥的空间。例如,当诠释《孟子·告子上》之第四章“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1](P.327)时,牟先生言道:
这是以同嗜之不能定嗜炙由外表示亦不能以同长定义外。孟子此例亦只是依一般常情而论。其实嗜炙既是口味问题,亦不必有同嗜,此同嗜之同并无必然性。(4)此翻孟子案。又这只是随同长举同嗜为例方便表明同长不必能表示敬长之义是外,实则告子亦不是单以同长来表示义外,其要点只在义随客观事实而定,故谓之外。客观是什么,我就应当说它是什么。这种应当之义是由客观事实而定,亦可以说由认知之知识而定,亦可以说是“义者宜也”之义,例如冬天宜于裘,夏天宜于葛,凡此皆无道德的意义。[2](P.14)
牟先生认定“嗜炙者,无道德意义”,即把道德之性与食色之性两者断开二分,而认为孟子借此比喻“义之为内”,并不恰当;因为“嗜炙”只有一般性,而没有必然性(5)牟先生与康德一样,视道德理性才有必然性,而感性、食色等,则只有一般性。故牟先生在《孟子·告子上》第五章,批评公都子以“冬日饮汤,夏日饮水”的回答乃是不伦不类,因为饮食并不能证明仁义之内在。此可参见牟宗三《圆善论》,《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8页。同书第4页中,牟先生又说:“下文告子则就原则以明性为材料之中性义。此原则即是‘生之谓性’。”这是贬低告子的“生之谓性”,视之只有材质义。,则所谓“同嗜”“义内”等论证,也就显得莫名其妙。
然而,孟子明讲“口之于味,有同耆焉”,此处之“同”,并没有“一般性或必然性”的区分。“一般性或必然性”的区分,是从康德那里挟带进来的概念。于是牟先生此章的诠释反倒像是在批评孟子,而不只是批评告子。牟先生这样的做法,也有几分近似朱子之视告子“认性为气”。如朱子注“生之谓性”:
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 [1](P.326)
朱子以为,性是理,而不可为气或形下,因此食色等气性也就不可能是真性。
然这是程朱的性理论,却未必是先秦的性情论。如孟子言:“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1](P.330)这里指出,口味之同嗜,未必就不是性,又哪里有牟先生所谓“一般性或必然性”的区分呢?
“一般性或必然性”的区别,乃是康德所强调的。其范畴表中的四项十二类,其中的“程态”项下,三分为“可能、现实、必然”三种。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将一般人所认为的“道德为相对,幸福为绝对”,转反而为“道德为绝对,幸福为相对”。于是,幸福如口味者,便只是相对、一般的,而不是绝对与必然。如康德言:“他意欲财富吗?则将有多少忧心、忌妒与轻蔑,他可不因此财富而引到他身上来!……他愿有长寿吗?有谁能保证他那不是长期的受苦?”[3](P.54)这意思是,在甲为幸福者,在乙可能是灾难。所以,幸福只有一般性,而没有必然性。
再看康德与牟先生如何看待形下的快乐,其言:
一个人他若知道如何以快乐(享受之快乐,通过一切官觉而成者)款待其客人以至于使人皆大欢喜,我们便说此人有审美力。(案:在中国大体说这人趣味不俗,或是漂亮人物。)但是这普遍性在这里却只依比较相对的意义而被了解;而所应用的规律像一切经验的规律一样,皆只是一般性的规律,而不是普遍性的规律。[4](P.158)
在康德而言,感官刺激者都只到“妩媚”,还进不到普遍性之美;前者只有一般性,而不具备普遍性。牟先生亦取康德之说,视这感官之适意只是相对、一般性的一种趣味而已(6)“一切能与颜色与音调相结合者,乃只是它们两者底组合之‘适意性’,而并不是它们两者底组合之‘美’。但是另一方面,第一,让我们考虑音乐中的那些振动间的比例之数学性格,以及我们之关于此比例之判断之数学性格。”见牟宗三译《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6册,第339页。这意思是,只是感觉适意,尚不能为美,须要是数学形式之比例,才得为美。康德重视形式,而不是感觉、质料等内容。;它能透过感官刺激以取悦大众,使大众感觉快乐、愉悦,造就形下幸福的成分,却终归不是道德或美感的真善美的必然成分。
以上可以看出,牟先生在此一套孟子诠释中,相继采用了康德“一般性或必然性”的区分而贬低感性,以及朱子的贱情诠释等观点,以至于所做出的孟子诠释,与各家不大相同。
(二)调整孟子的“道德情感”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反对休谟及胡企孙的道德情感。其曰:
我把道德情感一原则,划归于幸福原则之下,是因为每一经验的兴趣(利益)皆凭借一事物所供给的舒适而承允效贡献于我们的福利,不管这舒适是直接地被供给而未顾及[未来的]利益,抑或是因顾及[未来的]利益而被供给。同样,我们必须也如胡企孙(Francis Hutcheson)一样,把“同情别人的幸福”一原则划归于他所假定的“道德感”(moral sense)之下。[3](P.95)
康德把道德情感比配至幸福原则——此属形下,而非道德原则。又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提到:倘有一丁点的道德,便能胜过所有幸福之加总。(7)“此时只剩下了一个善的意志,纵然如此,它也好似珠宝一样,必仍以其自己之光而照耀,好似一在其自身即有全部价值者。其有用或无成果,既不能对这价值增加什么事,亦不能从这价值中减损什么事。”见牟宗三译《康德的道德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5册,第17页。像是胡企孙与休谟那般地以道德情感为宣说者,此乃康德所反对,而这也影响了牟先生。牟先生偏好宋明理学之中的心学,视之真能重新上接孟子心学;这是一种“心即理”之说,此中的“心”即是形上的,而非形下、一般的道德感。牟先生译注曰:
康德此处把“道德情感”说成“设想的特别感觉”,与“道德感”合在一起说。康德反对假定“道德感觉”以为说明道德之基础,而对于道德情感则另有解说,似又不必视为“特别感觉”。又“道德情感”与其所反对的“道德感觉”不可视为与孟子四端之心为同类。此须彻底了解孟学之发展,到最后可与康德学相比观。(8)见牟宗三译《康德的道德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5册,第95页。以此而言,康德批休谟的道德感可为形下之情;而孟子的恻隐之情,乃即“情即理”,为形上之情。
康德因贬低感性,连带也低视道德情感。然孟子学与心学亦有道德情感,如恻隐、羞恶之情等。故牟先生认为,康德所贬抑的情感,不同于孟子的四端之心;以孟子的四端之心,或如“理义之悦我心”云云,都是一种“心即理”——心与理都是形上的,而不是康德所说的特殊情感。
牟先生以为,孟子的四端之情是超越的觉情,虽然这也是一种情感,但具备着特殊之因果性——其因在自由意志,其果落于形下现象界,倘若没有理性之全神是气的下贯,则仍是低落的情感。因此,重点在于理之下贯与否?如若有理之下贯,则为四端,反之,则为七情。此甚近程朱学之“以理驭气”“人之骑马”。然而,若在孟子,则是其气可动志,其志亦可动气,不是只有单方面的影响。牟先生的说法并非全同于孟子。
此外,牟先生强调,康德所批评的道德情感无关于孟子学,因孟子的“心即理”,此中的心或理皆属形上,而非形下。牟先生言:
依孟子学,道德的必然性是性分之不容已,此不容已不是强制,是从“本心即性”之本身说,不是关联着我们的习心说,“由仁义行”之义务亦是如此。自愿、悦,是这本心之悦,不是感性的喜爱或性好之倾向。心悦理义,心即理义,此心与理义(道德法则)为必然地一致。[3](P.284)
在康德而言,人心无法悦于理义。因为理义是一种责成、义务与承担,自然也是辛苦的,何来心之愉悦?然孟子的“心悦理义”却是一种高尚的乐趣,如同孟子所称的“君子三乐”(9)《孟子·尽心》:“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然牟先生把三乐视为幸福,因为在“所欲”“所乐”处,还未到道德的“所性”。,是君子圆成人格、死而后已的向往与归趋。
而到了牟先生这里,则将“心即理”作为一种“判准”——心与理都是形上,并且包括孟子、陆九渊、王阳明等皆属之,这自然也就不会有康德所谓“感性之悦乐理义”情况的出现。也因此,牟先生视康德学的层次与成就,大致介于阳明与朱子之间——阳明学为自律,朱子学为他律(10)康德之自由意志不能呈现,而阳明则可;至于康德为自律,而朱子为他律(牟先生之判),故康德在阳明与朱子之间。唐君毅先生曾以一字形容西方哲学,为“对”,而东方哲学为“通”。以“对”者,则对越上帝法则,彼大我小,人只能尊敬法则;以“通”者,则人之心可即于理,人可成圣。;而置于中间的康德学,则视道德实践为畏途,“后段班”的朱子亦视之沉重与艰苦,若是阳明则容易许多。
(三)以康德解说二种情感
那么,阳明的“心即理”本义为何?阳明提出“致良知”说,此良知乃是即理而即气者,亦是说阳明用良知来把朱子的理与气合而为一。阳明曰: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形象方所求哉。真阴之精,即真阳之气之母,真阳之气,即真阴之精之父,阴根阳,阳根阴,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说明,则凡若此类,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则如来书所云,三关、七返、九还之属,尚有无穷可疑者也。[5](P.216)
阳明在此书信中回答元神、元气、元精等说,最后则以良知而一以贯之。所谓良知者,可有神、气、精等三个面向,此如阴阳之相伴,阴阳非二,理气亦非二,故阳明亦不贬低气。
但牟先生所谓阳明的良知或“心即理”,其中的心与理都是形上,而不能杂有形下的真阴真阳、元神元气等。如其对于阳明“四句教”的诠释:
至善是心之本体,犹言是心之自体实相,简言之,就是心之当体自己也。此心须当下即认为是超越之本心,不是中性的气之灵之心也。心之自体是如此,然其发动不能不受私欲气质之阻隔或影响因而被歪曲,因此“有善有恶意之动”。其发动即得名曰“意”。故“意”可以说是经验层上的。[6](P.195)
此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区别开来,即阳明的“心即理”,乃属道德形上之先验层次;至于恶的加入,则为经验层次意念之扰动所致。亦是说,阳明之心体、本心属于形上,而不同于朱子形下的气之灵之心。
不过,如此诠释似已加入康德“先验性与经验性”的区分,而与上文所引阳明将良知通贯于真阳、真阴或元神、元气等说法,有所不同。依笔者拙见,阳明所提出的良知,乃是即体即用者,他有意结合朱子所二分的理与气,透过良知而一以贯之。可是,到了牟先生这里,则将他所喜好的阳明心学,包括心与理都推至形上层次,而与形下层次对立、区别开来,此则合于康德。
康德贬低情感,认为道德乃义务之事,人不可能悦乐于道德。而这与孟子、阳明等并不同,如阳明言“乐是心之本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而牟先生推尊心学家,盛赞孟子与阳明,但他所理解的孟子、阳明心学,对于情感或气的态度,则如同康德或朱子一般地贬低(11)在牟先生而言,孟子的超越觉情,源于仁义之理的下贯而成,重点在理之下贯与否。至于阳明的“心即理”,自是指本然超越之心体,不具备一丝一毫的形下之情。,然后再反过来解释孟子所说的“悦理义”,并非属于感性层次,而是形上、理性之层次。如此,牟先生似将儒家的悦乐,分为形上与形下、尊与卑两层。(12)这让人联想到,当牟先生诠释张载时,亦将张载的“神”与“清”皆各分为两层。李明辉教授亦有相同之看法:“对于朱子而言,喜怒哀乐只是七情之概称,故属于气,为形而下者。但刘蕺山却别出心裁,将喜怒哀乐与七情分开,特称之为四气,并且将四气提升到超越层面。”参见李明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这也分形上与形下之情。
其实,孟子、阳明等所言悦乐,如孟子的“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君子有三乐”,自不异于孔子的“不亦悦乎”“不亦乐乎”“乐以忘忧”等。这固然不离于情感,却也透着《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展现的即性即情之意义,而为一种“性情论”。四端之乐可同于七情之乐,只重在中节与否。
三、唐先生之气论
唐先生之治学,习惯将中哲整体之发展摊开来看,不偏取某种主义或学说,而给予每种思想一个地位;他虽也研究西学,却谨慎地处理中西学之间根本的不同与分际。(13)唐先生的作品,常以中国的大中至正之整全圆满性,用来摄受西方之偏至之说。如西方主流哲学常是知而不行,此则理智过用,而意志薄弱;反之,其宗教革命家则大多行而不知。至于中国则能强调知行合一。又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发展,亚里士多德视人为理性动物;柏拉图推崇哲人王,以其理性最多,并在《斐多篇》中认为人死而离开肉体,即是一种灵魂之解脱,此显示重精神而贬肉体、感性,近于毕达哥拉斯。他的宋明学诠释不同于牟先生,牟先生的“宋明三系”里没有气论的地位(14)牟先生的“三系说”,包括了陆王心学、五峰蕺山主客兼备的“心即理”,以及伊川朱子“存有而不活动”之理。,而唐先生的分系则包括了理学、心学与气学;而如张载、蕺山、船山等人,唐先生便视之为气学人物。(15)唐先生曰:“宋明理学中,我们通常分为程朱、陆王二派,而实则张横渠乃自成一派。程朱一派之中心概念是理。陆王一派之中心概念是心。张横渠之中心概念是气。”见唐君毅《哲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第211页。以下介绍唐先生的气学研究。
(一)中、西论气之根本不同
当唐先生研究宋明学时,发现到张载便是以“气”作为其思想之第一义,甚至此是就整个中哲史关于气论之发展所沉淀后的总结:中国人的宇宙充塞着道德价值。而这与西方主流之气论有很大的不同。唐先生言:
张横渠之此种宇宙观,与西方唯物论或一般自然主义之思想有一更大之不同。因在后者常以为宇宙乃无价值或为罗素所谓守伦理的中立的。中国传统之思想,则自《易传》(16)“至《易传》之成书其时代应亦在晚周。”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二》,《唐君毅全集》第20卷,第112页。之系统下来,直到汉儒与宋明儒,皆以宇宙为充满元亨利贞或仁义礼智之价值的。此亦颇同于怀特海所谓宇宙之一切存在之历程,皆为一价值实现之历程之说。[7](P.224)
西学之中与“气”相近的语词,诸如物质、质料,或是自然主义、唯物论等,这里面大致没有中哲“气”的概念。其较相近而可比拟者,则如怀特海的历程哲学——宇宙之一切历程具备着价值之实现义。
然怀氏之历程气论,较难成为西学主流。而若以其他西方的气论、宇宙论来诠释中国气论则不恰当,如罗素之心、物区分下的物,乃是价值中立,不具备精神之价值义,这与中国所言“气”之充满仁义礼智不同。西方主流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便偏重形式,而不重质料,质料只是存有层里的最低阶,是待动的、充满惯性与惰性的,须待不动之动者上帝的推动方能有所作为,而反观中哲之“气”,本身即是自动者。
因此,与牟先生常取西学之近者来会通或讨论不同,唐先生的气论研究,大致不取西学做比配,而是由中国历来之气论着手,逐一地理解与探讨,尽量贴近气论之发展来勾勒出“气”之义理。
(二)先秦至汉代:顺天应时之道
先秦时代,除了老子的“冲气以为和”、庄子的气化宇宙观,或是孟子的“养气”“夜气”等说,战国阴阳家如邹衍等便已盛言气,而影响后代深远,可谓自此即奠定了中国传统之中重视阴阳、顺天应时的观念。此如唐先生言:“此阴阳家所开启之顺天应时之道,其影响于中国后世之文化风俗及民间生活者,为中国人之重节气如清明、端阳、七巧、中秋、重九、冬至、过年之类。但在汉世,尚不必已全有此诸节气。”[8](P.159)汉代思想家收摄了先秦的九流十家,形成思想上的一大综合。如司马谈的《论六家旨要》便论及阴阳,董仲舒亦十分重视阴阳与气学等。又如《易经》中原本二进制的四象八卦,汉代阴阳家还将之与重气的纬书结合,于是此时出现了天干、地支、五行等学说。可见汉代相当强调天人合一,并且重视气化。
(三)魏晋:精神情感的自然表现
唐先生在《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形容魏晋精神为“重情感的自然表现”,诸如嵇康之“越名教而任自然”,又有王弼的“圣人有情”。唐先生言:
汉代以后的魏晋清谈所开启的思想,通常称为玄学思想。这种思想,大体上是轻名教而贵自然。故亦被视为自然主义。但这种自然主义,并非如近代西方根据自然科学来建立之自然主义。此所谓自然(17)西方的“自然”,可译为nature,其中亦包含“性、本性”,近似“生之谓性”。这与东方所说的“自然”有很大区别。,初只为指人所自然表现的情感之哀乐等。贵自然,初只是说作人要率真。[9](P.14)
魏晋时代的“贵自然”,与西方基于科学主义所建立的自然主义,可谓天差地别。此时代的“自然”,有以下几个特色:
其一,“自己而然”,而非一般说的“大自然”(nature)。西学乃是以“自然”与“超自然”相对,前者通常指物质世界,或科学可掌握者;后者如自由意志、神的存在等。魏晋的“自己而然”重视“自尔独化”,比较类似西学的“存在主义”,乃是一种回光返照后怡然自得的情怀、重个体的自由与存在感受。
其二,透过情感,将“自然空灵化”。魏晋文人重情、重自然,更把自然空灵化,形成一种凌虚观照,从而造就道家之艺术精神层次,此乃西方所无。(18)康德的“美学”虽也讲“情”(“知情意”的情),然而仍被要求须与“知性”协合一致,由此展现出“无目的之目的性”,始为“美”。若只是感官的刺激,则与“美”的普遍性不协合。牟宗三先生称道家为无相判断。
其三,讲究率真,去除人伪。魏晋“自然”的对立面是“不自然”,也就是“人伪”而有所造作,凡此都将影响自然情感的活动,以及灵性的提升;若不能率真而行,则将困顿、残缺,而推展不开。
王弼便曾与何晏辩论“圣人有情”,王弼主有情,而何晏主无情。且看王弼如何主张: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10](PP.765-769)
“圣人有情”之说出于庄子。庄子所谓的“无情”不是冷酷、毫无情感,而是不以其情而内伤其身。(19)如《庄子·德充符》中所言:“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乃王弼所言“圣人有情”的基础,亦是魏晋重情的表现。而王弼之重情,还特别强调相感、相应,亦即情感上的感通、默契感应或感动等。对此,唐先生言:
按王弼言《易》重感应,而《易》卦之咸卦即言感。物必相感,而后成其变易。相感则有物之来应或往应。故感应不可分。王弼之注《易》,重得其应;亦即重得其应,以成其相感,而成变易。故咸卦虽为三十四卦之一,而在王弼之易学中,则有一特殊地位,而为可通一切变易之事之全者。王弼注咸卦“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曰:“二气相与,乃化生也。”[8](P.295)
情感的发生,要先有感应、交感。咸者,感也,感应之中,必有情感作用的发生,王弼形容此如“二气相与”,譬如阴与阳、男与女情感的相与。此乃魏晋之重情与艺术精神的开展,与西方的自然主义始终不同。而在唐先生的中国思想建构中亦有感通学的一席之地。(20)唐先生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中,言孔子之仁,就是一种感通,所谓对己对人对天地鬼神之感通。虽《论语》未有感通之文字概念,但《论语》有达字,此达为通达,又《论语》有一以贯之,乃通而为一的意思。
(四)宋明之终:回到先秦的性情论
唐先生亦有宋明三系说,分别是心学、理学与气学,此分系较牟先生更重气论。(21)牟先生并未给予气论一个地位,恐其偏向唯物论。他诠释张载与蕺山都是理气论,视蕺山为“体用显微紧吸于一起而呈现”,然这还是理气为二的讲法。他也曾评船山为好的历史哲学家,却不是好的哲学家,大概也是因船山的气论使然。唐先生言:“吾人亦可沿汉儒重气之思想,而谓此气为天地万物之本,此气为形而上,无形而至虚,乃以太极即气之太极,如张横渠王船山之说。” [11](P.432)此指张子与船山的“气”,都是形上之气(22)“感即合也,咸也。以万物本一,故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则无合。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见张载《正蒙·乾称》,《张载集》,台北,世界书局,1970年,第63页。这里强调阴阳之相感。,或高看的气,且能上接汉儒的重气思想。船山曾批判心学,而继承张子之气论。因此,二人的“气”乃是一种流行的存在,具备历程义与自动义。
唐先生高看蕺山的“气”,认为蕺山思想也是一种气论、性情论,有别于程朱的性理论,而回归于先秦,因先秦亦是性情论(23)孔子关于“情”的内容涵义与理论建构,虽尚未完善,但见于“兴观群怨”说,或《论语》“三月不知肉味”、学习之乐等各种表现,皆可谓寓“情”于礼乐教化之中。。如孟子的即心言性、即心言情;荀子亦经常性情连用,而不是性理相连;《论语》亦无“理”字。此可参见清儒颜元之说:
发者情也,能发而见于事者才也;则非情、才无以见性,非气质无所为情、才,即无所为性。是情非他,即性之见也;才非他,即性之能也;气质非他,即性、情、才之气质也。一理而异其名也。[12](P.27)
颜元之论性,重视其中的气质、情、才……,若舍情与才,则无以见性。如孟子曰“不能尽其才”,又曰“非才之罪”“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即是就情、才而言性,其中的情,虽指实情,亦可关联至情感,如孟子以情言心,而为“恻隐之心”。此可同于唐先生之旨趣。
(五)清代:以共感共情诠释孟子
宋明程朱学倾向低看情欲,而高举天理,然清学之兴发,则对此反动而来,例如戴震便曾批评理学乃是“以理杀人”。对此,唐先生评曰:
清代人在学术思想方面,则大均反对宋明儒之忽略人之自然情欲之地位,重静而轻动,重先天之心性之会悟,而忽略后天之习惯之养成,又忽略民生日用及现实社会中之种种问题。如颜李戴焦之思想,皆由此等处反对宋明儒。……文物文字,是感觉可直接把握的,情欲、行动、习惯及民生日用之问题,亦是一般的感觉经验世界的问题。[9](P.19)
这里显示,清儒较宋明重视情欲、习惯、文物文字等经验世界,其中戴震更提出“达情遂欲”,即在情之感通处而以情絜情,将此情欲推扩而充达,而以共感共情来诠释孟子。譬如孟子曾提醒齐宣王最好也能推扩其好色、好货之心,来使百姓安居乐业、愉悦幸福,如此也就提升了同情共感的高度。
(六)厘清中哲“气”的原意
由上可知唐先生对气的看法,首先不采西方诸如物质、材料、有惰性之自然等定义,而是老实地追溯中哲史上气论之发展来谈。他有以下结论:
“中涵浮沉、升降、动静之性。……散殊而可象为气”等,亦似当初是说自然之物质宇宙之事,故人遂恒唯物论或唯气论解之。此则自明末清初之耶稣会士如利玛窦、孙璋等,已谓横渠之天道论同西方之唯物论之说,与中国古儒真教之以天为一神明者不类。[13](P.73)
张载的天是气化的天,而古儒之天则有一上帝居于其间,如《诗经·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两者彼此不同,也与西方唯物论相去甚远,此乃利玛窦对张载之理解有误。
近代学者如冯友兰先生,即常取西方格义而反过来检视中国哲学,美其名曰“接着讲”,实乃接西方新实在论而讲。但唐先生反对这方法,其解释如下:
(张子)恒被人视为西方唯物论一类的说法。其以虚与气化二名,合以说明宇宙之太和及人之性,尤有“虚与气不相资”,而二元之嫌。然实则张横渠所谓虚气不二之太和,自其实在性方面言之,实只是一气。……如冯友兰等又以气为相当于西方哲学中如亚里士多德所谓材料,实则皆不是。中国先哲用气字,可以指精神之气,如志气;可指生命之气,如生气;亦可指物质之气,如地气。此三种气,在中国思想家又常是贯通之为一以说。于是以气指物质之气时,亦常同时指生命之气、精神之气。[7](P.217)
唐先生在此做一统整,归纳出中哲之“气”字,可有三义:一是“志气”,谓精神之气,可至大而至刚;二是“生气”,生命之气、有机之气,而非死气、无机物;三是“地气”,诸如人间烟火气、柴米油盐酱醋茶等,近于物质之气,可资以长养生命万物。最重要的是,中国思想家又常将此三者贯通为一,因此,即使在一般物质、山河大地之中,亦可承载着生命、价值等意义。
而冯先生取亚氏之材料而用以比配中国之“气”,并不适当。亚氏的材料因,乃是待动的,属于中立而为惰性、惯性之物质,须待“不动之动者”上帝来推动始可。反观中国的“气”,本身是自动义的,且有流行之历程,更有着精神价值于其中。此二者如何比配?因此冯先生的“接着讲”,并不能如实地照着张载而讲。此外,牟先生取康德与程朱之重理性思想,而贬低情欲、气论,如此做法,亦未必能合于历来中国思想中“气”的涵义。
四、结语与反思
(一)“气”者,即形下而即形上
唐、牟两位大哲对于气论的判断有很大不同。唐先生领略出自中国哲学《易传》以来元亨利贞之“气”,其中具备着仁、义、礼、智等价值义。而牟先生则以程朱,甚至西哲作为引介,而低看质料义(24)“惟尽才者,必赖生命之充沛足以尽之。尽情尽气者亦然。生命之发皇,乃为强度者。可一而不可再。生命枯,则露才者必物化于才而为不才,过情者必物化于情而为不情,使气者必物化于气而为无气。是故尽才、尽情、尽气,皆有限度。”见牟宗三《历史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册,第91页。若理不生气,任凭气,则是有限者。;透过自然主义、中性与料、物质等概念,回过头来格义、比配于“气”,而后做出贬抑。(25)牟先生虽顺着《易传》而言寂感之真几,然此寂感之真几,指的是“心即理”,都是指形上之感通,而不及于气与情。
但如前文所述,将中哲气论比配于西学唯物论并不妥当。中哲传统下的“气”自始即具备精神义、自动义,而唯物论则是西方断开于精神、仅以物质为本的中性义,此物质是待动、惯性的,不具备任何价值义。此二说之间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曾对程朱学提出反省,而有以下关于气论之描述,似可作为对于牟先生说法的响应:
先生之辨,虽为明晰,然详以理驭气,仍为二之。气必待驭于理,则气为死物,抑知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14](PP.355-356)
此乃黄宗羲对程朱学者,包括朱子、曹端等人的反省。其视气为自动浮沉、升降,不消待理之驾驭方能升降,亦是张载、唐先生等所谓的气之自动流行与存在。若言“以理驭气”,则是二分理、气,而“气”竟成死物。真正的气论乃是一种真实与具体的存在(26)“仁、义、礼、智、乐,俱是虚名。人生堕地,只有父母兄弟,此一段不可解之情,与生俱来,此之谓实,于是而始有仁义之名。”黄宗羲《孟子师说》卷4,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此指理是虚的,气与情才是真实存在。,其中也有理也有气,但是理是抽象的;理、气之间只是一物而两名,并非两物而一体。比如,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经常将理、气合言而曰“理气”,说的其实只是“气”,此乃有理之气、气自有理,而以气为尊。
(二)罪恶从何来?
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确常将气与理二者相对来看。若在程朱理气论,则是性与情对;若在西方,则是理性与感性(情感)相对。它们都强调,感官刺激、感性,诸如名利食色等,需受到理性之控制,方不致“盲爽发狂”;小体若不受控于大体,则蔽于物,造成爱之欲生而恶之欲死等偏激情况,这些虽都不是直接的恶,但容易流于恶。且小体之蔽,亦是大体之自由意志所许,故不该只是小体为恶。
反之,如果“气”具备自动义与精神义,如元亨利贞,或是春夏秋冬之递嬗不息,从而比配于仁义礼智,此中不待理之驾驭,“气”本身即是活物、有机物,系即形下而即形上者。理与气不需二分,唯有一“气”而其中自有理——抽象的理,理不需要高看。而这也是唐先生对于“气”的看法。
牟先生采取了程朱学中气质可能障碍理性的观点,视官能感性容易造成流弊,因而亟欲防堵。然如船山之言:“乃耳目之小,亦其定分,而谁令小人从之?故曰小不害大,罪在从之者也。”[15](P.1089)罪恶之生发,当须怪谁?孟子曰“非才之罪”。而船山以为,却也不是情之罪咎,而是在情与才二者之交流与盲从下,罪在小体之“蔽”于物、“从”于物,而不从大体,非小体之罪,乃错在“从之者不当”,方才致罪。错在后天之“习”,而不是先天之情;错在“自导”,而不是罪情。
不过程朱似有“气禀有罪”之说,程颢言:“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16](P.10)这里见到,气禀为性而有可能为恶,故程朱归恶于气,气若有恶,则人天生为恶,而不用负责。而这说法,与前述船山不同。又程朱近于牟,船山近于唐。
(三)唐主张感通形上学,牟重理性而轻感性
唐先生颇重先秦思想中的“性情论”,例如儒家的悦乐思想、孔颜之乐、乐以忘忧,或是孟子的“君子三乐”等,此中的乐,即是情感。当此之时,不必区分形上、形下,不须贬低情感,而能即气即理;也不需添加康德所谓的特殊因果性,回到中哲的性理(形上)与情感(形下)之间可以上下通贯,可以以志帅气,亦可以以气帅志,则如“君子三乐”,也就不是低等的幸福或快乐,此即不同于西学主流之观点。
唐先生自己对于“情”“感通”等,似有一定的偏好,或说特别的哲学感受,甚至可以称他的学问为“感通形上学”。所谓感通,也就不能离开气与情,就像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意向传达,而能起到抚慰人心的作用。(27)“当一作品真成为一桥梁时,此作品遂即真实存在于心与心之相互感应之间。”见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唐君毅全集》第13卷,第73页。此言文学之感通感应,指文学如《诗经》之能兴观群怨,亦是重要。唐先生认为佛经始于赞叹,《孟子》终于崇敬孔子,这些都是情感。此中,气与情都是具体的存在,理才是抽象玄远的存在,透过如此的肯认,能令人回到真实具体之存在,同时与他者交感互通,这便是唐先生所追寻的。唐先生反对的是唯物论而不是气论,气论是有精神价值的。
而牟先生择取西学主流之重理主义以诠释儒学,在中国或许只有程朱学较能接近,然程朱本质上亦不如西学之极端二元性。(28)“中国儒者之以性理言心,与西哲之以理性言心之不同,在性理之必表现于情,而自始为实践的。西哲所尚之理性,其初乃纯知的,因而亦不必为实践的。纯知的理性之运用,最后恒不免于产生矛盾辩证之历程。”见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唐君毅全集》第9卷,第104—105页。这意思是,程朱理学虽以理性言心,然留有情之余地,如四端、七情之不同,而不似西方二元割裂之甚。但牟先生仍认同尊理而贬情的路数,因为他担忧若过于靠向气论,则人也将变成物,从而落入西学定义下阴阳不定、形下之情与乐,于是造成罪恶。唐、牟二先生所言的气,其实不是同一概念,在唐先生而言,气是有精神价值性的;在牟先生而言,其气近如康德的自然,而排除了自由,故与唐先生之气不同,唐先生的气非为唯物之说,因为中国只有成物之道而无唯物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