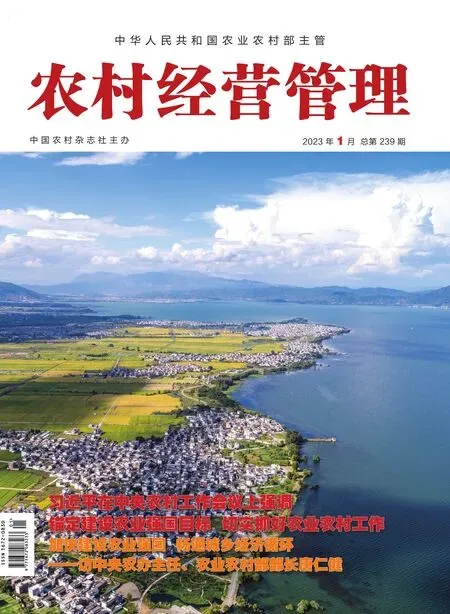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亟待完善
郭君平 曲 颂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城乡共同富裕以及经济健康发展。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这一重要论述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的具体部署和深入阐释。目前,受农业生产成本的“地板”和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双重挤压,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增长空间有限;同时,受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外出务工潮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支撑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动能不断减弱。在此形势背景下,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来挖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潜力,将成为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举措。
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如何科学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为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机制,早在2015 年我国就在33 个县(市、区)开展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并在盘活土地资源、增加农民收益、积累改革经验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2016 年,财政部和原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指出试点地区应征收一定比例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用以协调国家、村集体和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2019 年,财政部又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取消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制度,采取土地增值税的形式对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转移查征课税,不过并未明晰首次入市成本扣除项目类型与标准(为后续立法预留了空间)。2020 年施行的《土地管理法》明确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标志着相关法律障碍得以破除。2021 年实施的《民法典》继承了《土地管理法》的做法,未详细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办法,以致各地试点方案差别较大,至今未形成全国统一方案。
除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加快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改革步伐外,学术界也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与现实矛盾冲突的倒逼下,对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激烈辨析,目前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涨价归公论”,认为农地转非的巨额增值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规划管制带来的结果,主张按农地价格对农民予以补偿,其余增值部分由政府享有并用于宏观调控,如保障失地进城农民安居权利、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等。“涨价归公论”虽秉承了增值源于社会经济进步的理念,实行规划始于公、增值收益归于公,但这种置失地农民合法权益于不顾的做法有失公允。二是“涨价归农论”,主张“农地转非”后的自然增值部分全部归农民所有,其理论依据是“土地非农开发权补偿论”和“农地资源价值补偿论”,前者认为农民应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具体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以及“非农开发权”等权利;后者认为农民应获得可反映土地直接使用价值(如种植作物、修路建房等)和选择价值(即未来使用价值)的地价。“涨价归农论”虽意在维护失地农民利益,但过于强调支配和占有下的绝对控制,易因形成食利阶层、加剧社会贫富分化而被否决。三是“兼顾公农论”,认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应体现社会公平,要兼顾农民利益和全体公民利益(使两者冲突最小化)。“兼顾公农论”以通观全局的视野,从平衡各方利益出发,引入始于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令》的“土地发展权”,可纠正“涨价归公论”与“涨价归农论”之弊。毋庸置疑,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理论上对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归属主体的认知逐步达成共识,倾向于按照“公私共享”的原则兼顾效率与公平。

“地者,政之本也”。土地增值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市民、村集体以及农民等多方利益主体,其博弈力量的强弱关系决定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失衡性。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实践的核心逐渐从归属主体转向分配格局与形式,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于“初次分配—代内分配—代际分配”的改革框架,在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基础上,加快构建全民共享型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第一,建立基于交易双方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包含政府、集体、农民等多类主体的良性协商谈判机制,由此形成兼顾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土地增值收益初次分配格局。第二,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前者重点统筹完善区域间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后者侧重推动城乡、近远郊等之间的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由此形成可调控区域与城乡收益的代内公平分配格局。第三,设立代际补偿基金和土地发展基金,将土地增值收益向后代人转移,避免政府对土地增值收益“寅吃卯粮”,由此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平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