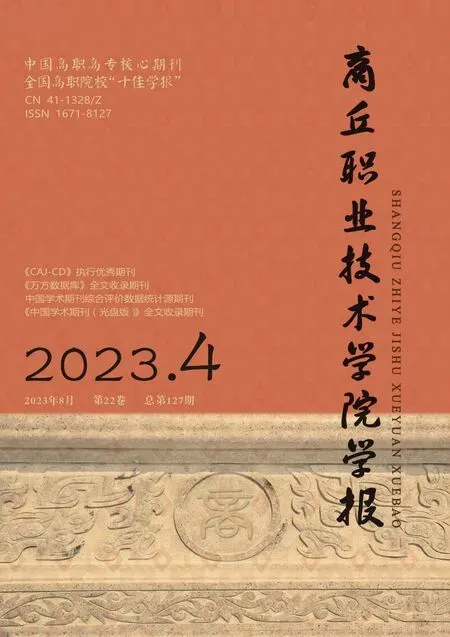戏仿:《女勇士》的自我重建之路
王 倩,慈龙保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育学院, 安徽 合肥 238000)
纵观英美文学史,几乎所有的少数族裔作家在写作中都会将其自身的文化传统融于自己的作品当中。例如: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中充斥着对黑人受难者的同情和对白人压迫者的痛斥;美国华裔文学作家赵健秀小说中充满了对美国华裔,尤其是美国华裔男性的重写。在众多凭借本民族文化发出各种异质且响亮声音的少数族裔作家当中,汤亭亭可以说是最具世界影响力但也是受争议最大的美国华裔作家之一。一方面,汤亭亭因其熟练的写作技巧和深远的思想内容而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誉;另一方面,又因其对传统文化的“扭曲”与“篡改”而招致各方批判。《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简·克莱默这样评论道:“《女勇士》是一本出色的回忆录……是一次灵魂的探索。”[1]12尽管对汤亭亭高超的写作技巧及其在中美文化交锋中所做出的努力,吴青云表示了欣赏,但“我仍然认为她对(传统)文化的改写有失其本真性”[2]3。举世闻名的“赵汤之战”的导火索也是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的。对于以赵健秀为首的美国华裔作家而言,汤亭亭是一位为了寻求美国读者和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甚至不惜违背良心对传统文化进行“歪曲”和“篡改” 的作家。面对诸多诘难,汤亭亭在1992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应道:“关于此件事,我认为有必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解释:一、种族文化的归属问题。在这一点上赵健秀认为其属于像他一样的真正的中国人。二、文化传播问题。我认为神话不是由文本而是由口头传送,我们每次说出的和每次听到的故事都会有所不同。文化传播的版本并不局限于一种权威模式而是多种多样。”[1]7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汤亭亭引用、移植、改写传统文化的目的,并不在于扭曲传统文化,而是为了在空间上对民族文化进行更好的补充和丰富,在时间上对民族文化进行延续和传承。通过对传统神话故事进行戏仿,汤亭亭和其他陷于东西方两种文化困境的美国华裔才有了自我重塑的机会。
一、中美两种文化间的徘徊
作为美国历史上一支独特的队伍,华裔为了快速融入美国文化,反而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却被美国主流文化拒之门外。此时的他们已经成为后殖民批评家口中的“离散者”(Diaporans)。处在拒绝与被拒绝的困境当中,美国华裔急需找寻出路,以突破重围。作为第二代美国华裔,汤亭亭也同样受此困扰。《女勇士》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该小说描述了一个接受美国教育、但又被以母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熏陶的美国华裔女孩的成长历程。处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之间,一开始“我”竭尽所能逃离那个神秘遥远的国度,转而投向美国社会。中国,在“我”看来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养女儿就等于是养鸟……无利可图……养了也等于是帮别人养”[3]76。无名姑姑的死,更是加重了“我”对东方的误解。在中国古代,妇女要严格遵守所谓的“三从”(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随子)和“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此时,妇女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为了逃离这个“怪异的”社会,“我”转身奋力投向美国的怀抱,但是和其他人的境遇一样,“我”被美国社会无情地拒之门外。拒绝接受本土文化,又同时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拒绝,“我”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此时的汤亭亭已别无选择,只能利用其特殊的边缘身份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创建出一个模糊的文本世界,即所谓的“第三空间”。根据霍米·巴巴所言:“在这个‘第三空间’内所有文化意义都可以被建构,没有固定的含义,这里允许有不同文化的存在。”[4]142正是为了创建这一“第三空间”,汤亭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改编和重写。通过改编中国神话,汤亭亭向我们揭示了西方社会的本质和美国华裔的生存状况。通过戏仿,汤亭亭旨在呼吁读者对美国华裔的现状进行反思,进而客观公正地看待美国华裔文化的归属和身份归属问题。戏仿,一方面消解了以“宏大叙事”为主的美国主流文化,解构和颠覆了美国神话;另一方面也帮助汤亭亭自己,以及像她一样的美国华裔进行了身份重构。
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被殖民者的自我身份的分裂问题。他们被灌输的理念是要努力获得永远也无法获得的白皮肤,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戴上白人为他们准备的“白面具”。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指出:“这种‘黑皮肤,白面具’的精神分裂现象导致被殖民者在使用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时与本土文化的疏离,也导致被殖民者在使用殖民者的语言表述,再现自己时‘将自己弱智化、原始化、使其丧失文明,并将其本质化’。”[5]4尽管法农在这里面并非特指东方人,但其深刻地揭示了身份分裂问题。
作为后殖民理论研究领域的后起之星,霍米· 巴巴在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核心理论——“模糊性,戏仿,混杂”为殖民话语、反殖民抵抗等奠定了基础。以混杂理论为基础的“戏仿”理论更是为以汤亭亭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在解构和颠覆西方霸权、重构自我身份方面起到了推动性作用。霍米·巴巴认为,“戏仿”是殖民者展现出的权利欲望,它颠覆“他者”,但与此同时对殖民统治本身也产生了一种破坏性力量,“它实际上犹如一种战略性伪装”[4]129-131。自20世纪以来,自我身份,尤其是族裔身份寻求问题已经成为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重要主题之一。没有确切固定的身份,美国华裔在这个多元文化环境下既失去了传统文化的庇护又不能与美国主流文化融合,其民族性已丧失了原先的确定性。
巴巴在《民族与民族性》中指出:“民族目前处于边缘地位,处于混杂与模糊的境地。”[4]138这也就是说,民族本身是非确定的。因此,民族文化也非固定不变。徘徊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美国华裔作家只有借助于“戏仿”这一策略进行创作才能突破自我。“戏仿”既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原封不动地照搬,也不是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趋炎附势,而是一种拥有无限力量的异质声音。巴巴认为:“‘戏仿’把殖民霸权看成是一种片面的、不完整的权利,从而动摇了霸权本身,并影响了这种霸权所赖以生存的差异性。”[4]138正是这种对本土文化的戏仿,才使得汤亭亭能够在巴巴的“第三空间”中寻得自己的根。
二、花木兰:战场上的女勇士
对于美国华裔作家是否必须照搬中国神话进行创作,汤亭亭认为:“我们应该比记录神话做得更多,因为那只是一种对先人的崇拜。我所做的是以一种新方式来传承中华文化。”[1]73也就是说,通过戏仿,美国华裔作家才能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一个隐形的边缘世界(建筑在父母因对故土的思念和在美国社会中感到的疏离感而对保留本土文化的最后一丝希望之上)当中”[2]9,汤亭亭不得不解构母亲的神秘莫测的故事,以求在两个世界当中寻得一个和谐共处的“第三空间”。通过借鉴中国传统故事,进而对美国华裔身份进行解构并加以重构。“戏仿”策略在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创造了一个“第三空间”。
花木兰是中国古代的巾帼英雄,因其替父从军抵抗外敌而流传千古。然而,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既不是那个替父从军的孝顺闺女,也不是那个击败入侵者的女将,而是一位拥有强烈种族与性别意识的独立女性。经过戏仿的花木兰此时已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战场”上一位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新型女性。
从小被大鸟引入山中,并在山上学武15载后,为保卫村庄,花木兰下山返乡。自此,花木兰组建军队,女扮男装打败暴君,并将其杀死。此时的花木兰已不是那位抵御敌寇的女英雄,而是怀揣为乡亲报仇,并高度宣扬自我成就和个性的反抗者。此外,这位花木兰拜师学艺的初衷除了“打败蛮夷和强盗之外”,还有自己的私心,那就是不必像其他山下姑娘一样“挖山芋”[4]22。她甚至希望“因其的责任感而被铭记”[4]23。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在战场上与原版一样英勇无比,“我仅一次没上战场,那就是我生孩子的那天”[4]40。戏仿后的花木兰并不是孤身一人,而是与丈夫并肩作战。在美国人眼中,传统的中国女性没有自主选择配偶的权利,他们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背景中结婚生子。通过戏仿,汤亭亭成功解构和颠覆美国主流文化中华裔女性的软弱“他者”形象。这位戏仿的女复仇者,实际上帮助被压迫的美国华裔尤其是华裔女性发泄了愤怒,“花木兰使我也想成为一个女勇士”[4]20。“从神话故事当中,我认识到谁才是我真正的敌人”[4]48,进而进行了逐渐激烈的反抗。当文具店老板叫我“黄鬼”的时候,我此时已经具备了反抗意识,但只能够以“不流利的英语小声进行没多大用处的反抗”,然因饭店老板又一次对华裔的嘲笑,“我”展现出了更强烈的反抗意识——“拒绝打印请帖”[4]48-49。尽管身材矮小,社会地位低下,“我”仍旧大胆地对身材高大的美国老板进行反抗,正如神话中的花木兰首次面对巨人时一样。作为汤亭亭的化身,女勇士给予美国主流文化的霸权和歧视思想一次强烈的冲击。
此外,除了对花木兰的戏仿,汤亭亭还对中国民间传说“岳母刺字”进行了戏仿。为了使岳飞牢记使命,岳母在其背上刻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汤亭亭利用汉字的单音节特点或是误解或是故意地将“报”理解为报仇(revenge)。“我们会在你背上刻上报仇字样,这样无论你到哪,发生了什么,人民都会记得你所做出的牺牲,并将你永远铭记于心”[4]34。爸爸在字上涂上墨水,妈妈将血迹擦净,然后我背上出现了“一排士兵,我的士兵”[4]34-35的字样。
这一戏仿惹恼了很多中国读者和华裔作家。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戏仿,汤亭亭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写作目的——促使其他华裔意识到不能再做弱势群体,而要像文中的女勇士一样能够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求自我身份。霍米·巴巴认为:“民族就如同叙述一样,在神话时代往往失去自己的源头。”[6]“戏仿”成为“少数族裔在夹缝中寻求文化生存、文化归属并最终达到自我赋权的一种话语策略”[7]。
三、东西方和谐之歌
正如康诺利所说:“身份就是区分多种事物的依据,同时,它也为生活所需。我们的任务就是辨认出社会中的不协调部分,从而使自身结构理想化,进而提出反对策略,并通过这样来反映出制度理想化本身与其所容或所克之间矛盾的多个方面。”[8]对自我身份的寻求,尤其是由母女冲突而引发的寻求,长久以来就已经成为华裔作家笔下的主题之一。代表传统文化的母亲和代表新生文化的女儿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本土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著名的美国华裔评论家林英敏曾经说道:“少数民族的疏离感不仅是由主流文化的排斥造成的,而且也是由父母的严厉批评所带来的。”[5]123
母亲通常借助讲故事或者送孩子去汉语学校的方式,让孩子铭记本土文化,传承文化遗产。但有时候,这些做法因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作为第二代美国华裔,他们所奋力追求的是独立的个人权利。中国古代女性的境遇,知之甚少的中国传统以及美国学校里的缄默中国学生,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采取行动。为了反抗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我’拒绝做饭。当我洗盘子时,我就会故意摔碎一两个……听到有人骂我坏女孩,我就会号啕大哭”。 因为我认为“坏女孩就是男孩的代名词”[9]。为了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便把让学校里一个沉默女生开口说话作为己任,“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没看出来我是在帮你吗?你难道想一辈子都像哑巴一样吗”[3]180。令她失望的是,她所做的不但没有使女孩开口,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母女俩最终认识到暴力冲突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她们才有可能在这个冲突纷呈的异国文化中寻求到一个“第三空间”。
在《女勇士》的最后一部分,汤亭亭借蔡琰之手为美国华裔以及本土美国人奏出一首荡气回肠的《胡笳十八拍》。蔡琰,蔡勇之女,又名蔡文姬,东汉著名诗人。蔡琰在董卓叛变中被掳,继而成为匈奴首领的妻子,后在曹操掌权后,重新被赎回。
原本沉浸在背井离乡之痛的蔡琰变成了汤亭亭笔下的勇士。“在偏远战场上奋力拼搏,在临近战役中奋勇杀敌”,像蛮夷女人一样“在沙场上分娩”[3]208。与历史上在月光下独奏哀曲、伤心绝望的蔡琰不同,汤亭亭所展示的却是一个勇敢乐观、敢与胡人羌笛合奏的乐者。被捕之后的蔡琰,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竭尽所能与这个民族相融合。这音乐“像沙漠里的风一样颤抖着冉冉升起”,起初像尖锐冰冷的噪音一样“打扰了蔡琰,令她痛苦,使她不能集中精力思考”[3]208。不知多少个不眠夜后,蔡琰渐渐意识到了音乐背后的种种渴望。然后在她的帐篷外,“胡人听到了一个女人如此高昂清亮的歌声,像是对婴儿歌唱,正好和他们的羌笛声合拍”,“歌词像是中文,但胡人从中体会到了凄凉与悲愤”,从歌声中“他们甚至捕捉了和他们一样的永久漂离之感”[3]209。
正是借助于戏仿,汤亭亭笔下的蔡琰才从“流浪人变为幸存者,从奴隶变为勇士,从失语者变为歌者。流放的生活成为艺术之灵感,情感创伤成为精神之食粮,凄凉孤独成为相互理解”[2]47。戏仿的蔡琰故事不仅仅反映了母女之间的关系由剑拔弩张到相互妥协,一直到最终的相互谅解,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中美文化之间从对话、协商、妥协到最终融合的发展进程。如同蔡琰的儿子一样,“我”拒绝接受甚至怨恨母亲所讲的故事,“我”拒绝说话企图逃离传统文化的束缚。然时光飞逝,随着双方交流的加强, “(这次)她的孩子没有笑,而是和她一起坐在篝火旁在胡人的伴奏中合唱”[3]209。“我可以让妈妈知道我的计划,这样她和我的世界就会更加融合,我就不再孤单了”[3]198,接着“我跟她说了我的故事,开头是她的,结尾是我的”[3]206。
但是“我”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有所区别。借助丰富的想象力,“我”对母亲的故事进行了戏仿,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版本。“我”所发出的既是不同于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声音,也是有别于美国社会背景下的声音。这个声音是通过相互同情、相互理解而产生的一个混合体。蔡琰与胡人及儿子之间的鸿沟,以及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隔阂,实际上映射出中美文化之间的障碍。一方面,“她的创作成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交融界面,为中国故事创设了表达的新场域”;另一方面,“它们再次激活了中国故事,使其产生了新的活力”[10]。汤亭亭正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戏仿,演绎了一段东西方文化从隔阂到融合的故事。汤亭亭曾不止一次地重申“我是一个美国女性。我也是一个美国华裔女性”[2]5。
四、结语
从侠女花木兰到诗人蔡琰,汤亭亭再造了不同特色的女勇士。对传统故事的戏仿再加上母女之间的真诚交流,不仅仅逐渐治愈了“我”的心理创伤,澄清了误解,重塑了母女关系,更是缓和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紧张气氛。她所写的一切都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戏仿加以改编。通过戏仿,汤亭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性别战场上奋勇抗争的侠女形象,并以此来重构美国主流文化。通过对蔡琰诗歌的改写,汤亭亭找到了发声途径,并借此搭建了两种文化相互交流沟通之桥。
正是通过戏仿,才使得美国华裔在中美两种文化困境中重新构建了自我。因此,我们应该正视汤亭亭的特殊身份,公允看待汤亭亭“扭曲歪解”中国神话一说。只有将自己与母亲所分别代表的世界相分离,“我”才有可能将中国的过去、美国的现在加以重塑。正是通过戏仿,“我”才有能力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混合体,使华裔美国人的尴尬身份得以解构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