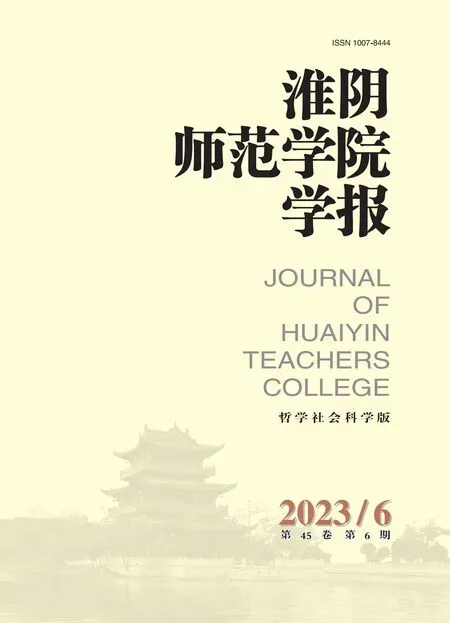董恂《江北运程》的成书经过与纂辑特点
李 强
(淮阴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 江苏 淮安 223001)
董恂(1807—1892),字忱甫,号酝卿,江苏扬州甘泉县(今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人。他在道光二十年(1840)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先后担任过顺天府尹、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等职。董恂深知遭运事务对清政府至关重要,故他在顺天府尹任上着手纂辑了历代有关运河的资料汇编,这就是《江北运程》。《江北运程》是董恂经世致用精神的心血结晶,是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我们今天考察和研究大运河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一、成书经过及版本
《江北运程》一书记述了自长江北岸瓜洲镇至北京的各段运河的运程:“书所纪者,江北运程也,即所纪以为之名。”[1]311该书是一部150多万字(1)关于《江北运程》的规模,蒋超认为“近百万字”,王云、李泉认为“一百多万字”,这两种说法都与实际出入太大。据笔者点校该书时统计,该书有150多万字。的有关京杭运河江北段运程的大型资料纂辑。大运河是董恂生命里的重要的一部分,董恂出生于坐落在运河边的邵伯镇旧宅,成长于邵伯镇,运河的繁忙运输、运河的水患、运河的治理,都是他曾耳濡目染的。走上仕途以后,从京城出发去赴任、返京述职、回乡等,运河也是他首选的交通方式。漕粮是皇族、中央官僚、拱卫京师部队、在京旗人等的粮食供应来源,漕运之重要可以想见。董恂在论及漕运的重要性时说:“京师控天下上游,朝祭之需,官之禄,主之廪,兵之饷,咸于漕乎取给,而饷为最。综材官、技击、厮养、羡卒,名载饷册者,十七万人。家以八口计,则食饷者百有三十有六万;即家五口,食饷者亦宜八十有五万。此断非籴数十百乡镇,乡镇籴数千百斛,所克济。……微漕东南粟,蔑由职是故也。”[1]310-311而这个深刻认识,与董恂出仕以后的读书、任职、治河、接收漕粮、实地考察运河等有关。道光二十二年(1842),董恂签分户部,公事之余,他读了前代《漕运全书》,并以朱、紫、蓝、墨四色笔作了标记;随后,他又读了治河名家张鹏翮、杨锡绂等人的治河著作。道光二十四年(1844),董恂被任命为漕运全书馆总纂,他“挥汗如雨,连宵达旦,以速补迟”[2]216-217,这部官修大书终于得以迅速完成。该书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肯定,很快得以发刊。咸丰二年(1852),董恂曾验收海运南粮,目睹了漕运的种种弊端。验收事毕,董恂又被任命为湖南粮储道,此次赴任,他“拟由水路查看运道”[2]233,并将“沿途目击”写成《转漕衡湘笔记》。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考察。董恂后来在自编年谱中说:“后来纂辑《江北运程》一书及《楚漕江程》一书,皆本此笔记。”[2]234
《江北运程》是董恂在顺天府尹官署空青水碧斋完成的,该书成书实属不易。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战祸之危,顺天府首当其冲,战火所到之处,处处人心惶惶,形势异常艰难。但董恂和赵小山在混乱的局势面前,临危不乱,正常处理公务;公务之余,坚持纂辑、校对《江北运程》不辍。董恂在年谱中说:“是夜(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圆明园火。……是年,幕宾赵小山通家(熙和)以校对《江北运程》书,守不去,豫以遗言作札寄其家。次年,事大定,乃吿归。”[2]263-265赵小山说:“其时幕僚星散,师昕夕筹军国,神色自若。每从巡防处归,苟片刻暇,即手操不律,纂辑如故。和无事,亦相从参校如故。”[3]805该书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咸丰十年岁次庚申辑于京兆尹署空青水碧斋”[1]310。赵小山说:“于斯时(咸丰十年)也,校稿本讫,校初缮、清本亦先后讫。”[3]805但董恂非常审慎,并未就此定稿。据年谱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月杪补纂《江北运程》初稿成”[2]266。同治二年(1863),“九月杪,《江北运程》稿第二次录竣”[2]288。同治四年(1865),董恂在请赵小山作跋的信中说:“前书(《江北运程》)再缮清本,同门铁岭耀朗川、续炽庵(陈善昌)两孝廉昆仲分校一过。……今三缮清本成矣。始终其事,繄惟足下是赖,足下其许我乎?”[3]805-806但是赵小山的《跋》并未立即完成。同治五年(1866),公子剑秋(疑为董恂子董莲)“南来,复将师意”[3]806。同年,赵小山和董莲一同返京,董恂在年谱中写道:“八月十九日子莲归自邵,女兰同来宁,赵小山亦偕来,有《喜晤小山西席入都诗》。”[2]304至此,赵小山才又“出前后稿本、清本,字梳句比。……凡十阅月,综校毕”[3]806。这是赵小山最后一次校对《江北运程》。10个月后,校对完成,《江北运程》终于定稿,而赵小山的跋也在《江北运程》校对“蒇事”的同治六年(1867)六月完成。
目前,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等图书馆所藏的线装古籍《江北运程》都没有标明刻印的具体时间,只在卷四十“江北运程卷四十终”栏下双列标有“京都琉璃厂龙文斋陈恭超刊”[3]804字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刊刻该书的书坊是北京琉璃厂龙文斋,刊刻人是陈恭超(陈恭超资料不详),但具体刊刻时间现在还无法确定。虽然现在有“于咸丰十年刻印成书”“流传下来的只有咸丰十年刻本”,[4]“清咸丰刻本”[1]309,有“清咸丰十年刻本”和“清同治六年刻本”[5],“流传下来的版本有咸丰十年(1860)刻本”[6]等说法,但是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不正确。
董恂曾将此书作为礼物送给丁韪良,“董恂著作等身,他的主要作品都曾赠送给我,其中一本是关于大运河的地形史”[7]。
二、编撰体例与特点
该书正文四十卷,卷首一卷,共四十一卷。卷首前有董恂用他最擅长的隶书作的序。序后有“江北运程并有漕诸省图”一幅,“江北运程河湖闸坝全图”一幅。卷首由“总略”和“纲汇”两部分组成。“总略”用极凝练的文字分卷介绍了每一卷所记述的运河起讫地点及这一区间河道的长度。全书所记运河历经顺天、直隶、山东、江苏等地的四十五个州县,河道全长“共二千九百二十七里四分”[1]319。“纲汇”的内容是“总略”的子目,分卷简要介绍了各河段的行政机构设置、运河两岸的城市村镇、仓储数目、每年入仓漕粮数额、闸坝名、桥梁名称,河流湖泊的交汇情形等。
《江北运程》正文以运河为经,详细记述了自北京开始南至长江北岸瓜洲镇各段运河的里程;以运河流经区域为纬,分别记述左右两岸的城镇、村庄、沿线闸坝、减河、运河沿线贮存漕粮的仓库数目及各仓的容量、从古至今有关的水利工程、历代河道治理与变迁等,还介绍了汇入运河的自然河流的源头、流经区域、汇入运河的情况,湖泊的形成与变迁。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董恂在书中阐明了自己的治河思想。董恂的治河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河要看大局和通达,要追求长远利益。董恂在书中一再告诫治河人员,治河不能满足于一时、一隅的平安与稳妥。治河不能“泥于名称,拘于今古”,“或暂免一方之害,或微规目前之利,而不知统计全局之利害,其贻患不仅在一时也,故谨著之”[1]548。二是不懂治河,不可妄言治河。治理运河是一项耗费巨大且难度大的工程,贸然治理,或者说方法不当,不但白白耗费了国家财力和民力,而且水患问题依然肆虐,危害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国家的稳定。三是评价古人治河的优劣得失。比如,董恂这样评价朱衡和盛应期:“衡庐河傍昼夜调度,与应期日夜止宿水次同一劳勚。乃一则求缓一月毕功而不能,一则朝议方讙而已报蒇事,遂使成败殊途,黜陟异报,益以知应期急欲成功以杜众口之良非得已也。然而衡则又有幸功欲速之劾,部议所谓非常之功,怨谤易起,不其然耶!”[3]142又比如,“窃惟张(张伯行)作筹因时补救之方,叶(叶方恒)作叙历代经营之迹,均留心运道者,所宜详绎也,爰并识之。”[1]554四是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治河官员鸣不平;也以此委婉地向统治者进言,应当给予治河官员更多的信任,不该轻信言官。为了避黄利运,朱衡主持开挖了新河,可谓功劳巨大。在治理和疏浚新河方面,盛应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疏治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应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数万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谓糜财用劳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夺应期官归田里,而新渠之议寝焉。”董恂评论道:“应期果毅任事,日夜止宿水次,求缓期一月毕功不许,呜呼!劳人力而役诸河,言者坐而论诸国,千古同慨矣!”[3]138
第二,董恂是本着经世致用的精神纂辑《江北运程》的。首先,董恂深刻认识到漕运畅通对京师的重要性。正如赵小山在《跋》中所说:“师念京储未裕,而运道弗讲,以江之南之不靖,田畴之不易,固无粟可漕也。即有粟,而江以北无程以运,奈何?师于是乎搜讨旧闻、表章、成宪,备采疏、牍、笺、启,旁及诗、古文、词,又成是书。”[3]805正因为董恂看到了运河畅通的重要性,所以他希望运河不畅的现状得到改善,他在交代纂辑《江北运程》的缘起也说:“臣恂受命入尹京兆之三载,距道光之季粤西隍池弄兵之始,一星终矣。荆、扬、徐、豫、青、兖之漕之不达于冀者,若七八稔,若五六稔,若四三稔。运道久荒,弗之治。”[1]311其次,董恂有验收漕粮和治理运河的经历,深知运河与漕运的弊端。因此,他在书中不但考证了列朝列代对运河的利用、治理以及运河的变迁,还以加按语的形式深刻总结了列朝列代利用和治理运河的得失。再次,他所援引的文献也体现了这一特点。魏源和包世臣等改革派曾改革漕运弊政,且成效显著。魏源还编有《皇朝经世文编》一书,该书所选文章但求“致用”,故有清一代的作者不论“硕公庞儒,俊士畸民”,尽皆囊括;文章按重要性排序,而非作者的官衔和社会地位。该书的卷四十六至卷四十八讲漕运,卷九十六至卷一百二十讲河防、运河、水利。因此,可以说魏源是一位在漕运、运河治理等方面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这一点也为董恂所看重,《江北运程》中的很多资料就直接引自《皇朝经世文编》,甚至连魏源的评语也一并引用。
第三,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长江以北的运河有两个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二是清口水利枢纽,一是南旺水利枢纽。这两个水利枢纽是明清两代运河治理的重要工程,也是大难题。《江北运程》以这两个水利枢纽工程为中心谋篇布局,相对于其他河段而言,董恂对这两个水利枢纽工程文献的罗列尤为翔实。以清口水利枢纽为例,该水利枢纽工程坐落在淮安府。徐仰庭《河口灌塘渡运说》:“清河县河口,为漕运咽喉。”[3]538“国朝踵明制,定鼎燕京,漕挽东南数百万粟,势不得不资黄济运,则黄不可使之北;不得不用淮刷黄,则淮又不可使之东。故治淮所以治黄,治黄、淮即所以治运。而淮郡实为其扼束,故治河之法,较之他处,其难百倍云。”[3]438董恂仅叙述淮安府境内的运河就用了十卷的篇幅,可见董恂对该段运河的重视程度。
第四,董恂视野开阔,实事求是,所引用的文献广博,详略得当,对文献作了精心的考辨。该书大量引用了正史、文集、方志、档案文书、奏稿,以及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堪称运河百科全书。董恂深受扬州学派的影响,“尤讲求考据之学”[2]469,故《江北运程》“或所引两书同载一事,而字句不同,有可折衷者,折衷之;不,则各存其旧,以附疑事毋质之义”[3]806。他在书中的具体做法是,在考证文献之舛讹、错误之后,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已经湮灭无闻或者不可能查考到的地名,他干脆书以“其地无考”;对于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则以“并录备考”的方式标出,留待将来解决或把问题留给后人。例如,在卷十二中说:“此录戴氏震校本(指水经注)。戴氏以原本经注互淆,重加厘定,注有误为经者仍降为注,经有误为注者仍升为经。”[1]654
第五,为我们留下了他直观考察到的运河沿岸的情形。董恂在该书中引用了自己关于运河的笔记,一是《转漕衡湘笔记》,一是《魏阙重瞻笔记》,可谓是神来之笔。两笔记以白描的笔法记述了董恂在考察运河时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犹如影像、照片一般,极具画面感,读时令人对当时的历史社会场景和画面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董恂还引用了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中有关河防、水利的内容。麟庆也是一位治水名臣,他在《鸿雪因缘图记》中以图文相辅相成的形式,如实记录了他为官以后所至所闻的各地山川、古迹、风土、民俗、河防、水利、盐务等,保存和反映了道光年间广阔的社会风貌。该书中保留的河防、水利资料,是今人研究运河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与董恂的笔记可以互相参证,可谓是相得益彰。
结语
《江北运程》是董恂本着恢复运河漕运宏愿并多次实地考察运河之后的心血结晶,他博采诸书,旁征博引,精心纂辑,保留和使用了大量史料,应该说是一座宝库。赵小山说:“是书为经世远猷。”[3]806徐珂说,董恂“自幼至老,手不释卷,汗牛充栋,著述等身,舆地一科,尤为精阐。所著有《江北运程记》《楚漕江程记》为生平心力所注,尤稗国计”[8]。《清史稿·艺文志》将之归入“政书类邦计之属”[9]4310。京杭大运河是清王朝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生命线[10],它深刻的影响了清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江北运程》则是我们今天整理运河与漕运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利用运河与漕运文化遗产的宝贵资料。
此外,董恂曾任湖南粮储道,他还据其亲历行程,纂辑了另一部关于运河的著作《楚漕江程》。该书主要讲述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以南各省漕运水道、里程及有关工程等,其体例结构、纂辑方式等都与《江北运程》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