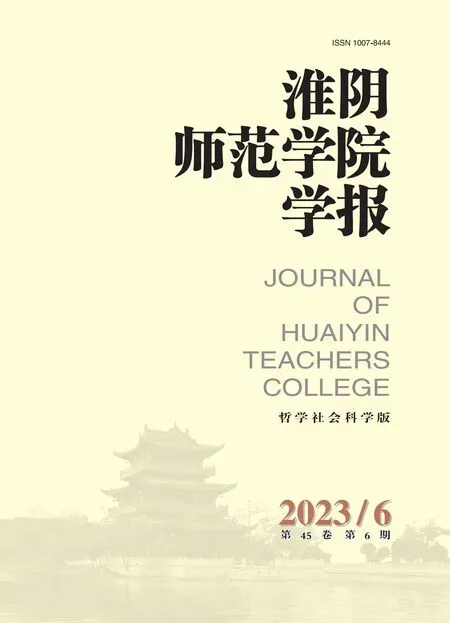抗战时期天津玉澜词社考论
杜运威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全面抗战初期,天津文坛受战争影响,相当一段时间持续处于沉寂、萧条的状态。至1940年后,随着各类报刊的再次兴盛才有所改变。但兴盛的内容与抗战之前已经完全不同。战前主要是新文学占据主流,抗战过程中则是旧文学比较活跃。彼时各报刊发起了关于“文坛在哪里”的讨论。奇岚《关于文坛》有云:“天津的诗人组织了城南诗社,天津词人组织了玉澜词社,都是耆英隽秀,文艺名流,好像天津的文坛,便在‘这里’了。有人喊着天津文坛在哪里,那真使人糊涂。这也许是新文艺家对于旧文艺不明白的原因。”[1]其实除了城南和玉澜,彼时天津还有冷枫诗社、俦社、水西诗社、不易诗社、河东诗社、丽则诗社等各类大小社团。他们频繁集会,盛极一时。玉澜词社是当时天津唯一专事词业的团体,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目前学界对玉澜词社已有所关注,如潘静如《清遗民诗词结社考》、杨传庆《民国天津文人结社考论》、曹新华《民国词史考论》等,以上虽是简介性概述,但披沙拣金之功不可抹杀。成就最突出者当数余意《民国玉澜词社发覆》,作者以不少新材料为支撑,纠正了词社成员及社集方面的部分讹误。然而当下人们对玉澜词社的基本认识与实际情形还有较大差距。首先,对词社存在时间的判断出现错误。其次,词社成员至今尚无完整统计。第三,社集次数及具体活动情形只有余意先生提及的5次[2],而实际上至少有19次之多。第四,词社成员之创作理念尚不明确。第五,因没有社集刊刻,且参与者别集较少,导致人们误以为只有社集而不大作词,限制了对该词社成就的宏观判断。笔者详细检阅了抗战时期天津一带的报刊,如《新天津》《东亚晨报》《新天津画报》《立言画刊》等,发现不少关于玉澜词社的信息,可对以上问题有所补正。
一、词社成立及主要成员
如众所知,玉澜词社之命名取自“京韵大鼓演员林红玉、张翠兰之‘玉兰’二字”,后改为“玉澜”[3]。词社发起于1940年端午节(6月10日),最早发起人是冷枫诗社成员王寰如、王禹人和赵琴轩。[4]本次主要是筹划成立事宜,并未布置社课题目,不能算是“第一次雅集”。经发起人多次引荐,词社规模才有所扩大。如《玉澜词社将放异彩》云:“该社拟再敦约王孝廉莘农督促指导,闻该社关系人前往接洽,想王君为倡导词坛及提携后进计,当不致推却也。并闻津市文艺作家姚君素君(即姚灵犀)……名重一时,对于填词一项,饶有心得,现已加入该社。此君更有意约上谷名士王君伯龙参加,王君为诗词名宿,姚君日内向其说项,倘能参加,则玉澜济济一堂,当另有一番盛况也。”[5]姚灵犀正是后来《新天津画报》的主编,人脉遍及天津整个文坛。王伯龙也是地方名人,有“诗书画三绝之号,早年办报沪上,来津曾办《维纳丝》杂志,近与《立言》《银线》等报办专页,……交游遍天下,名流皆友好。”[6]姚、王两人又介绍向迪琮、周公阜等人入社,玉澜词社队伍由此逐渐扩大。据《文艺消息》载:“本市玉澜词社,自成立以来,经社长胡峻门指导,王吟笙两孝廉倡导,加入新社友甚多,如上谷名士王伯龙等,皆一时词坛名宿,最近姚灵犀君又介绍词学大家向仲坚先生及政府周公阜秘书,张异荪先生介绍吾津大音乐家杨芝华先生,姚品侯先生介绍城南诗社社友张吉贞、金致淇两先生同时加入……”[7]至此,经过近三个月的筹建,词社成员已经达到了十余人。
1940年9月7日,词社成员在致美斋饭店举办筹建后的第一次雅集活动,并确立每月一集、每集必交社课的基本规范,标志着玉澜词社正式成立并进入常规化发展阶段。报刊讯息载,本次活动参加者有向仲坚、童曼秋、姚灵犀、王伯龙、冯孝绰、胡峻门、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当场由向仲老讲述词之发源,溯其源流,阐发精详……本期课题即由仲老拟定,(一)吊费宫人故里(望海潮),(二)中秋(好事近)……”[8]摄影照片最后刊登于《新天津画报》1940年9月26日第1版。本次活动有“周公阜、金致淇、张吉贞、杨芝华、杨轶伦、张国威、高鸿志或赴北京,或因事未到”[9]。
此后,词社大部分是每月一集。当然也存在因社员不齐或其他变故而推迟雅集的情形。据目前所存史料看,活动时间持续两年多。天津各报刊有关词社的最后一条材料是1943年2月28日的《玉澜词社在玉波楼举行春宴创议为赵幼梅立碑》:“玉澜词社,于二十四夕,假玉波楼举行春宴,导师向仲坚先生,方自海上归来,颇感劳顿,故未参加。李择庐先生及姚灵犀、杨绍颜、金致淇、王寰如、杜彣庵、王禹人、赵琴轩、张聊公诸君均到。王伯龙亦因感冒未莅,特遣使来书道歉,书中并言及李海寰送来朱燮老所撰故藏斋老人赵幼梅先生碑文一篇,拟在红十字会院中立石,……饭罢由择老命课题。‘癸未春宴’,调寄《临江仙》,至九时许始散。”[10]自此之后,未见关于玉澜词社的相关活动讯息。同是本年,寇泰逢等倡导组建癸未文社、甲申文社,正是梦碧词社之前身。据杨轶伦《梦碧沿革小记》载:“梦碧吟社者,吾友寇泰逢社长之所创立也,实为现在沽上唯一研究词学之组织。初成立于民国三十二年,名癸未文社……俟后冷枫、玉澜诸友好,亦多闻风加入,社友已至三十余人。”[11]简而言之,1943年是天津词坛由玉澜词社时期向梦碧词社时期的过渡转折阶段。
所以,玉澜词社发起于1940年端午节,同年9月正式集会,至1943年2月后才逐渐消解,前后持续两年半时间。基于以上出现的各类材料,梳理出词社的成员有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高守吾、胡峻门、王吟笙、王莘农、姚灵犀、王伯龙、张异荪、姚品侯、向迪琮、周公阜、杨芝华、张吉贞、金致淇、童曼秋、杨轶伦、张国威、高鸿志、李择庐、杨绍颜、杜彣庵、张聊公等24人,以及后来在历次雅集中不断加入的杨寿枬、马醉大、冯孝绰、张靖远、韩世琦、石松亭、杨轶伦、章一山、王益友、王仰伯、张筱江、高润田、项更生等。这一群体规模几乎占据了天津文坛的半壁江山。
二、词社雅集活动考
人们对玉澜词社认知不足的原因之一是所见资料有限,认为社集活动较少,影响不大。然据笔者爬梳考索,玉澜词社至少组织了19次雅集活动,在天津文坛是有独特地位的。现据相关文献整理如下:
第一集:1940年9月7日,于法租界致美斋,到者10人(见上文)。社课是《望海潮·吊费宫人故里》《好事近·中秋》。
第二集:1940年10月8日,仍于致美斋,到者有向迪琮、王伯龙、童曼秋、周公阜、姚灵犀、石松亭、韩世琦、冯孝绰、张国威、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王仰伯、金致淇,张吉贞、孙正荪等人。社课是《苏幕遮》或《八声甘州》,命题为“庚辰重九”。[12]
第三集:1940年11月2日,仍于致美斋,到者有向迪琮、姚灵犀、胡峻门、王伯龙、张吉贞、冯孝绰、张国威、童曼秋、韩世琦、张异荪、金致湛、王仰伯、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新加入杨寿枬、马醉天(别署西泠词客)。社课《踏莎行》《台城路》。席间张吉贞、金致淇抚奏“平沙落雁”一阕,遂命题为“听张、金二君弹琴”。[13]又杨味枬和向迪琮谈论词学渊源,博奥详尽。
第四集:1940年11月30日,仍于致美斋。到者向迪琮、杨寿枬、胡峻门、杨芝华、张吉贞、冯孝绰、张靖远、姚灵犀、张异荪、韩世琦、王禹人、赵琴轩、王寰如等13人。社课为《洞仙歌》(限东坡作三十八字体)和《鹧鸪天》。[14]
第五集:1941年1月11日,仍于致美斋。到者有向迪琮、童曼秋、胡峻门、周公阜、杨芝华、姚灵犀、石松亭、韩世琦、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社课为《水龙吟》《阮郎归》,不限体韵。席间,补祝姚灵犀寿辰(农历十一月十九生辰)。又童曼秋、杨芝华、韩世琦三先生畅谈现在昆曲没落之感想,拟组织一曲社。[15]
第六集:1941年2月3日,仍于致美斋。到者有杨味芸、王伯龙、周公阜、姚灵犀、杨芝华、张吉贞、石松亭、张国威、杨少严、王禹人、王寰如、张异荪、赵琴轩等。杨味芸拟社课为《玉楼春》(首句平起)、《蓦山溪》。本月底,周公阜寿辰,社友预为庆祝。[16]按:余意先生将本次社集确立为第五次雅集,实际上是第六次。
第七集:1941年3月3日[17],仍于致美斋。到者有向迪琮、童曼秋、周公阜、杨芝华、张靖远、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社课《满江红》《西江月》。评定上集作品,以姚灵犀、周公阜为最优。[18]
第八集:1941年4月4日,仍于致美斋。到者向迪琮、杨寿枬、胡峻门、姚灵犀、韩世琦、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冯孝绰,及新入社者杨轶伦。向迪琮拟社课《倦寻芳》《雨中花》。[19]
第九集:1941年5月26日之前某日,仍于致美斋。到者有向迪琮、胡峻门、童曼秋、姚灵犀、周公阜、石松亭、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社课《行香子》(仿东坡体)、《更漏子》《望江南》(以“烟深好”为起句咏天津风物)。向迪琮携来《同声月刊》数册。[20]
第十集:1941年6月28日之前某日,仍于致美斋。到者有向迪琮、周公阜、姚灵犀、张靖远、张吉贞、张异荪、石松亭、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新加入者张聊公。社课为《长亭怨慢》《小重山》。[21]
第十一集:1941年8月7日前某日,仍在致美斋。到者有胡峻门、周公阜、张聊公、姚灵犀、杨少严、杨轶伦、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10人。周公阜拟社课《绮罗香》《南乡子·消夏》。[22]
第十二集:1941年9月5日,仍在致美斋。到者有章一山、金息侯、李择庐、杨寿枬、胡峻门、向迪琮、王伯龙、姚灵犀、周公阜、张吉贞、金致淇、王益友、冯孝绰、杨芝华、张筱江、高润田、项更生、石松亭、齐文清、张异荪、牟莲塘、韩世琦、王仰伯、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26人。社课为《金人捧露盘引·七夕感赋》《鹊桥仙·前题》。[23]
第十三集:1941年9月30日[24],向迪琮大公子向伯文在惠中饭店举办婚礼,玉澜词社成员藉此雅集。到者有杨寿枬、王伯龙、姚灵犀、周公阜、胡简白、童曼秋、钱仲英、金致淇、张吉贞、石松亭、杨芝华、张靖远、韩世琦、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本期社课为《百字令·中秋和东坡》《人月圆》。[25]
第十四集:1941年10月28日,仍在致美斋。到者有向迪琮、姚灵犀、杨绍颜、项更生、杜彣庵、刘仲华、赵子久、曹烜五、石松亭、杨轶伦、王仰伯、胡峻门、韩世琦、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17人。社课为《霜天晓角·辛巳重九》《惜秋华》。[26]
第十五集:1941年12月4日,仍在致美斋。到者有向迪琮、周公阜、姚灵犀、张异荪、曾公赞、张国威、张聊公、杜彣庵、赵子久、刘仲华、王仰伯、韩世琦、王寰如、赵琴轩、王禹人等15人。社课为《霜天晓角》《诉衷情》。[27]
第十六集:1942年4月17日,仍在致美斋,此日正值上巳节,到者有向迪琮、胡峻门、王伯龙、姚君素、周公阜、石松亭、杜彣庵、韩世琦、杨轶伦、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13人。社课为《菩萨蛮》《谒金门》。[28]
第十七集:1942年6月25日,仍在致美斋。到者有向迪琮、张聊公、石松亭、刘仲华、赵子久、杨绍颜、杜彣庵、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等。社课为《青玉案》(用贺方回韵)、《减字木兰花》。[29]从本次社集开始,改为每年雅集四次,按春夏秋冬季举行。[30]前上巳节一次算本年度春季雅集,本次即夏季社集。
第十八集:1942年9月2日,在鸿运食堂举办秋季雅集。到者有向迪琮、王伯龙、王寰如、石松亭、童曼秋、张聊公、姚灵犀、冯孝绰、王禹人、韩世琦、赵琴轩、王仰伯、杜彣庵等。社课为《抛绣球》(仿阳春体)、《如梦令》。席间,补祝向迪琮、王伯龙、石松亭、王寰如四位寿辰。石松亭答谢同人为其太夫人作寿诗。[31]
第十九集:词社原拟重阳节雅集,唯因多数同人系城南社友,遂改于国历新年举行[32]。然国历新年前后未见相关报道。目前,仅见1943年2月24日社集。活动地点改在玉波楼。到者有李择庐、姚灵犀、杨绍颜、金致淇、王寰如、杜彣庵、王禹人、赵琴轩、张聊公等。社课为《临江仙》,题咏“癸未春宴”。[10]
以上即是笔者所知关于玉澜词社的雅集情况。不难看出,第十六集是词社前后两个阶段的分水岭。此后雅集频率由原来一月一集改为每季一集。社集频率的下降严重影响了社团的生存活力,最终难以为继。
上文词社讯息作者较多,如“梦”“梦龙”“非词人”等,其到底何人,至今未解。核查报刊中同类署名者,发现《征求诗钟揭晓》署名为“梦龙值课”,文章最后又附录“王寰如谢教”[33],可推测“梦龙”即王寰如也。又有《梦龙鼓话》一文署名亦为“王寰如”[34],可资佐证。又恬静《王寰如》云:“近来与赵琴轩、王禹人、姚君素……诸先生所组织之玉澜词社,在各报披露社集纪事,均系寰如先生所撰。”[35]此又一证据。关于“非词人”,轶伦《再谈笔名》载:“老友王寰如,笔名‘非词人’,君每作关于玉澜词社之消息稿件时,必用此署名焉,亦可以想见其·谦之意矣。”[36]据以上史料,知“梦”是“梦龙”简称,而“梦龙”和“非词人”皆是王寰如笔名。
三、师法北宋的审美取向
从以上社集中我们看到导师向迪琮在该社团中的重要位置。也意味着,向迪琮的词学审美取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玉澜词社的群体走向。向迪琮(1889—1969),字仲坚,别号柳溪,四川双流(今成都双流区)人,先后任北京内务部水利科科长、行政院参议、天津海河工程局局长等职,后执教四川大学,著《柳溪长短句》《柳溪词话》。他多次向玉澜社员阐述词学渊源以及创作词体所应秉持的基本法则。如“学填词,固须多所试作,而尤要在多阅读前人之作,以资揣摩,又谓诗词之作法,与诗不同,要在悉心体会,明其变异,潜心追求,自有进步”[27]。又“席间向老畅谈词律,及与当代词家况夔笙、邵次公两先生之唱和”[14]。又评王寰如词曰:“词须注重句法及格律,古微翁言词为人籁,非经千锤百炼未易观成。”[37]从所见资料看,向迪琮似乎特别强调词律之重要性。导师杨寿枬也多次“畅述填词取法,须力求格律,可由浅入深,如熟练时较诗尤有兴趣,同人拜服”[16]。又如第十九集时,“席上李择老与灵犀诸君纵谈白石、屯田词律之严”[10]。对待格律之严谨还显示在社课命题上,如第四集社课《洞仙歌》(限东坡作三十八字体);第六集《玉楼春》(首句平起),又《蓦山溪》(后三字句均叶韵从黄山谷体);第九集《行香子》(仿东坡体)。限体意味着学员填词时在关键位置的平仄,乃至四声都必须与模仿对象一致。这些迹象表明,向迪琮及玉澜词社是十分强调格律的。王履康《柳溪长短句序》云:向氏“丙丁而还,邃于科律,是则傍柳系马,非四仄所能晐;废寝忘餐,缘一字而未惬”[38]。向迪琮《柳溪词话》也提出:“元明以后,倚声家仅循平仄,而于四声之说,皆淡漠置之。万氏《词律》,仅守上去二音,而于四声亦多疏漏。……今世不守律者,往往自托豪放不羁,不知东坡赋《戚氏》,其四声与乐章多合。稼轩之赋《兰陵王》,与美成音节亦无大谬。今虽音律失传,而词格具在,自未可畏难苟安,自放律外。蹈伯时所谓不协,则成长短诗之讥。”[39]基于以上梳理,我们很容易将玉澜词社纳入彼时“四声之争”十分激烈的格律派阵营中。[40]
与沤社、如社、午社等词学社团所不同的是,玉澜词社对格律的强调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社员是非专业词人,他们对词之文体属性的认知还不够深入。向迪琮和杨寿枬试图用词社这一平台向众人灌输遵守词体规范的意识,而并不是强调格律与抒情之间审美偏向的问题。
撇开以上容易误解的问题,单就审美取向来说,向迪琮在词体“格律”与“抒情”抉择之间,更倾向于后者。从其反对师法南宋,而主张学习北宋的填词门径即可得到佐证,曰:“窃以为小令始于五代,迄于汴京已集大成。古今选本颇多,无须赘辑。惟慢词始于柳公,至美成而益光大。厥后词格渐靡,境界尤低。而有清一代流传选本,大多偏重南宋,北声寝微,良用惋惜。”[41]又《清声阁诗余序》云:“昔半塘翁论词三要,曰:重、拙、大。大不是豪,重不是滞,拙不是涩。此惟汴京诸老能之,临安以后不克逮也。”[42]晚清民国以来,词坛一度被主张南宋的梦窗风笼罩,以致所作之词貌似高雅醇厚,实则晦涩难解。吴眉孙《覆夏瞿禅书》说得很清楚: “顾今之以梦窗自矜许者,愚以为率堆砌填凑,语多费解,乃复以四声之说,吆喝向人,殊不知四声便算一字不误,其词未必便工也。”[43]玉澜词社社员王禹人对此有相同观点:“词在宋代是可歌唱的,不过后来被少数人们关在象牙塔内,把本质改变了,只用在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上加功夫,不如是不配给士大夫读阅,同时一般文人往此路追求,造成葬送词归墓中悲剧……”[44]基于此现状,向迪琮倡导师范北宋的理念得到了词社同人的一致肯定,如《玉澜词社雅集志略》载:“向先生初述词学源流……盛称蒋鹿潭词,皆为诸家所喜。从之入手,后始取法北宋,各专一家,小令以二晏最工,初学者所应揣摹……”[9]又词社参与者云:“在一个秋爽的晚上,曾举行一次谒师宴会,仲老(向迪琮)当筵发表词学心得,介绍读晏小山、周邦彦二氏作品。正合我们同人的意思,从此入门,定能达到我们理想的志愿。我们的志愿是人人能作,人人能懂,恢复词的本色。”[44]向迪琮倡导北宋的思路既满足了玉澜词社大部分非专业词人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为了实现“恢复词之本色”的终极目标。
需要提醒的另一方面是,词社成员中不少人是当时报刊的主笔,他们毕生的主要创作是小说、随笔、漫谈、掌故、花边新闻之类,以报刊发销量为目的,所作多迎合大众口味。而强调词之抒情性乃至娱乐性的审美诉求,与他们平民化的文学主张是契合的。如姚灵犀(1899—1963),本名姚君素,字衮雪,号灵犀,江苏丹徒人。1940年,主编《新天津画报》,一时间声名鹊起。而玉澜词社社友王伯龙、赵琴轩、张聊公、杨轶伦等都是画报主笔,他们的文学品位有相似之处。以词社发起人赵琴轩为例,他著有《春在人间》《虹桥蝶梦》,擅长长篇小说。“他的风格以一种轻松的幽默为特色,他由各种的环境和动情的眼睛吸收了热力、想象、创造,他的作品是浪漫的,但是骨子里却含着严肃的意义。”[45]由此很容易看清赵琴轩强调文学之抒情性、娱乐性的根本特质。检索《新天津》《东亚晨报》等同时期的天津报刊,发现王寰如、王禹人、张异荪、高守吾、金致淇、马醉天、石松亭等社员,也经常发表各类短文随笔。《新天津》报主编杨春霖明确指出:“本报标榜平民化,不党不偏,为民众之喉舌,为贪污之仇敌,此早为各界读者之定评。”[46]所以,玉澜词社倡导北宋、偏重抒情的创作理念既是对晚清以来推崇梦窗、严守四声的反驳,也是大部分社员平民化文学思想的折射。
四、“学舞刑天”的反抗精神
很多学者指出,玉澜词社“虽有课题,但作者不多,只在饭店集会联欢,未几停办”[3],最后也无词作结集。该认知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王寰如的历次社集讯息中明确介绍了社员积极创作的具体情况,如第二集时强调“首集尚有未克交卷者,已限期补作,不许曳白”[12]。第四集时,又交代向迪琮“将前两期所交课卷批改传观,并每篇详述应改正之处,力求改善”[14]。又第五集云:“向仲老发表上次课卷,均加以批改,及评语,对社友殊多奖掖,甚为欣悦。”[15]又第七集强调:“每月雅集一次,课作多佳什妙句,传诵一时,诚为文坛佳话,……席间觥筹交错,畅谈甚欢,并发表上期课卷,批评删改,以姚灵犀、周公阜两社友之作为最优,颇加赞许。”[18]所以,玉澜词社的实际创作量是十分可观的,但所交社卷后来有没有汇总,目前没有文献记载,也无流传。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是小部分优秀作品被推荐到《新天津画报》《新天津》《东亚晨报》等报刊发表。笔者从中爬梳出55首社课词作,另有此阶段社员其他作品15首,以此管窥玉澜词社之整体创作成就。
1948年,王禹人邀请寇泰逢给“玉澜词社题名录”题词,寇氏词云:“闲鸥劫外,词海玉澜分一派。学舞刑天,半壁斜阳费管弦。春星暂聚,杯底光阴弹指去。粉蠹笺零,旧约题襟墨尚馨。”[47]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寇泰逢自然看到了玉澜词社“学舞刑天”的反抗精神,但到底是如何反抗的?寇氏并未直说,我们只能立足社课作品进一步分解。
从词社第一集第一次社课之“吊费宫人故里”即可窥其端倪。费宫人,后人又名费贞娥,是明皇宫一侍女。甲申之变后,决心效法豫让、要离(古时刺客),刺杀李自成,为国复仇,然未遂。后杀其弟李固,并自刎。1937年6月4日,程砚秋所扮《费宫人》新剧在上海正式演出,因“描写亡国惨状,激发爱国热忱”而广受欢迎。[48]而费宫人故里就位于天津“东门内,今名‘大费家胡同’”[49]。1940年,京津一带已经沦陷,且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隶属汪伪政府。在此背景下,以“吊费宫人故里”为社课题目本身就有特殊旨向,如王伯龙《望海潮》:
明珰翠羽,神鸦社鼓,露筋犹有荒祠。僻巷黄昏,疏林斜照,行人难觅遗碑。往事最堪悲。剩千家野哭,劫火横飞。孽子孤臣,凭谁只手拯倾危。 金台风雪凄迷。但惊沙铁骑,折戟残旂。大将殉忠,权阉误国,刹那血溅宫闱。肝胆□蛾眉。叹渠魁未剪,侠骨先灰。小部梨园,至今能貌古威仪。
貌似凭吊古迹,实则分明借此大抒“权阉误国”的愤慨,讴歌贞娥之反抗精神,呼唤“拯倾危”之英雄再现。向迪琮给予该词高度评价,曰:“悲壮沉雄,似东坡大江东去格调。”因为沦陷区言说语境比较复杂,报刊媒体上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刊载抗日类文字,很多文人只能利用这种方式间接表达。“费宫人故里”恰是天津词人最好的宣泄窗口。明于此,自能看清玉澜词社“学舞刑天”之精神所在。再看王寰如、石松亭二词:
神京板荡,故宫禾黍,难寻遗烈芳踪。血渍丹墀,愁连青琐,谁能如此从容。禁苑月朦胧。铜壶滴清泪,寒析匆匆。白刃飞霜,红妆替艳恨无穷。 昨宵偶步楼东。任肩担冷月,袖绾寒风。 回忆前尘,缅怀故里,令人徒吊孤忠。今也又何从。一醉千愁解,往事空空。万古坚贞,时绕魂梦中。(王寰如《望海潮》)
蓬莱宫阙,渔阳鼙鼓,长安覆局谁论。东海水枯,西山石竭,贞娥故里犹存。波浪撼津门。尚歌吹夜沸,商女如云。景物全非,永留坊巷属宫人。 流传曲谱翻新,道当能护主,刺虎奸身。篝火夜鸣,妖星昼见,凭谁盥靖烟尘。斜月照遗村。倘回軿一看,一倍酸辛。休与明妃一例,环珮望归魂。(石松亭《望海潮》)
向迪琮评王寰如词云“须注重句法及格律”,主要因为最后一句“万古坚贞,时绕魂梦中”有出律嫌疑。在守律层面,不少玉澜社友做得确实还不够,但并不影响词作之情感烈度。王、石两词都以费宫人为牵引,将目光转移到了当下。王寰如聚焦自身“今也又何从”的迷茫,石松亭则嘲讽今日天津仍“歌吹夜沸,商女如云”的病态。二人共同吟咏出抗日战争背景下沦陷区文人的真实心声,即迷茫、忧虑与批判、渴望并存的复杂生态。前者相关作品还有如高守吾《满江红》:“ 枝上鸟,声泣泣。幕上燕,闲闲立。正夕阳斜照,断垣残迹。镇朔楼头惊鬼哭,爱春园侧行人织。莽尘寰谁与话兴衰,伤今昔。”又王伯龙《八声甘州·重阳》:“一晌瞢腾未解,蓦伤离感逝,吊梦哀吟,更黄华霜老,篱畔独徘徊。且商略几番风雨,叹兀龙豪气已全摧。危栏外,莽烟波处,断雁南飞。”后者类似作品有向迪琮《满江红》云:“乱后亲知谁与问,望中蕨薇谁堪活。整欹冠,扶病强登临,飘零客。”石松亭《金缕曲》云:“挟霸气剑锋犀利,岳岳高楼吞湖海,溯英风为问何人比,龙川外恐无俪。”张聊公《秋夜闻蟋蟀于庭阶,适读宋史,叙贾似道事,怃然有感》一诗歌说得更加直接:“赵氏江山为汝亡,当时艳说半间堂。从来玩物皆丧志,玉垒金盆梦一场。”[50]所以,玉澜词社的雅集唱和绝不限于嘘寒问暖、觥筹交错,它搭建起天津文化人相互沟通、勉励、督促、告诫的社交平台,又借助《新天津画报》《新天津》等报刊打通了与社会对话的渠道,藉此婉转表达了内心的政治诉求与期望。
当然也不可回避,因为雅集的应酬形式和娱乐属性,部分社课内容限制在祝寿、咏物、节庆等范围内,难以激发词人更深邃的思考。又因为天津未直接经历战火淬炼,作家对抗日战争的正面书写还比较狭窄。加之部分社员是初学者,词体规范掌握得还不够熟练,导致玉澜词社的整体创作成就不够突出。
如果我们站到整个天津文学的生态维度俯视,则更能看清玉澜词社局限性的根本因素。1941年春,《新天津》报发起关于“天津文坛在哪厢?”的讨论[51],折射出部分文人对当时文学现状的不满和反思。杨莲笙《天津文坛》和二元《漫谈文坛》两篇文章揭露了该问题的关键。杨氏看到了媒体介质的局限性:“如今,我们(天津)的文坛确是病了,营养不足,而不是消化不良。……所谓文坛荒寞,也就是底盘太可怜,不用往大处说,写上一万字的短篇创作,在天津能够发表吗?写上五六百字的杂文小品,就很够可以啦,二三千字的论文就有点行不得也之势。”[52]二元则看到了作家和读者的局限性:“最近在某报看到一位某君谈起文坛来,说他最近未有写作,有人向他索稿,他不肯应酬,也便不写,因为应酬作品是不会好的。此公所谈,实获我心,我与此公相反者是专门写应酬稿子,文章内容如何,向不注意,其原因有二:(一)不是应酬的文字,未必有人肯看;(二)应酬的文字可以卖钱。我所注意的一点却是后者。卖文换钱,是为了生计。”[53]传媒介质、作家、读者等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天津文坛的格局。这也是玉澜词社创作内容偏向应酬一类的重要原因。
但正如本文篇首奇岚《关于文坛》所指出的,天津文坛的萧条针对的主要是新文艺,而当时旧文艺是比较活跃的。究其本质原因还是新文艺的内在问题,即表达策略的捉襟见肘。处于沦陷区的京津文坛,本身就因为舆论环境的特殊而难以做到慷慨直言,尤其是1941年,日军对沦陷区发起“自强化治安运动”后,素来“不党不偏,为民众之喉舌”的几家报纸都被迫压缩版面,用于转载报道政务信息,这本身就是妥协的无奈表现。此期文学社会功能之脆弱更是可想而知。面对“和平文学”“东亚共荣”的政治压迫,新文学家要么转入地下创作,继而面临着影响缩小的现状;要么只能创作应酬一类文字,继而连作家自己都难以持续。与新文艺不同,旧文学本身就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内在渊源十分深厚,有丰富的典故系统、历史素材及表达策略,既能满足人们意内言外的情感寄托,也能适应舆论严峻形势下的批判讽刺,上文“吊费宫人故里”就是典型案例之一。
结语
综上所述,玉澜词社是抗战时期活跃于天津一带的词学社团。1940年6月10日,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三人发起筹建,后得到姚灵犀、王伯龙、向迪琮等人响应,经过近三个月的准备,于9月7日在法租界致美斋饭庄正式成立。会上确立了每月一集、集必有课的基本规则。1942年4月第十六次社集时,修改为一季一集,但只维持了一年时间,就在1943年2月第十九次社集后逐渐消散。玉澜词社的灵魂人物是向迪琮,他特别强调词体抒发情感的重要性,提出师法北宋的新主张,该理念与许多社员的平民化文学思想有契合之处,遂得到了词社同人的一致肯定,也激发了大家的创作热情。由于词社没有结集刊刻,具体创作情况已经难以厘清,但部分优秀作品被推荐到《新天津画报》《新天津》《东亚晨报》等报刊发表,给窥探词社创作成就提供了参考。基于所搜集的70首词作,发现玉澜词社同人多借助别有深意的历史素材和写作策略,来间接表达出积极反抗的心声。当然,面对抗日战争局势的不明朗,作家难免流露出迷茫、忧虑等复杂情绪。玉澜词社的雅集活动为他们搭建起相互沟通、勉励、督促、告诫的社交平台。社员又借助各类报刊,实现了表达政治理想的诉求。看到以上成就的同时,也要承认部分成员对词体属性的认知还不够深入,社课内容存在应酬肤浅的缺陷。然而,与同时期的天津新文学比较而言,还是有可取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