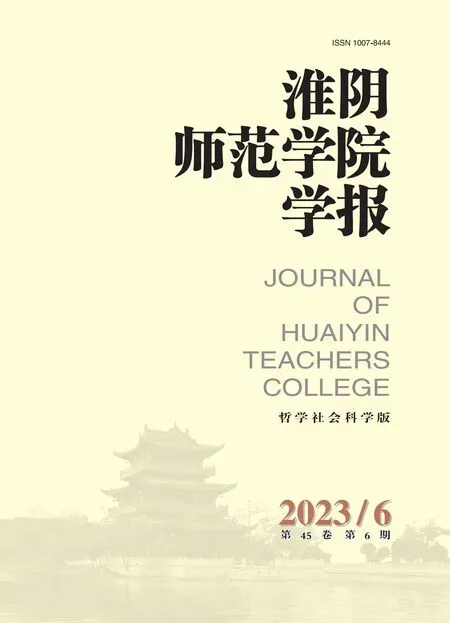走近真实的章学诚
——陈其泰先生《文史通义选读》书后
屈 宁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来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文史通义选读》,是陈其泰师晚年研治《文史通义》的又一重要著作,也是其长期潜心研究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总结性成果。该书以导读、注解、旁批和点评相结合,对章氏其人、其书、其学、其时代作了精审而细致的解读,是一部文本注释与思想阐释相结合、兼具学术创新性和工具书意义的匠心之作。今不揣浅陋,略表书后语,以就正于方家。
一、突破传统“大梁本”注本的局限
目前学界关于《文史通义》的注解,影响较著者主要有叶(长青)注本、叶(瑛)注本、仓(修良)注本和罗(炳良)注本。除仓注本外,诸本概以“大梁本”为底本。“大梁本”所收皆章学诚生平学术专论,故流传较广,但章氏所作序跋书说皆不载。仓注本融通“大梁本”与“章氏遗书本”,内容最详,惜重在编而疏于注,学术导向性稍弱。陈其泰先生新撰的选读本,正可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不足。该书一方面立足于“章氏遗书本”,补注多篇章氏论学札记和书信,有助于进一步解决“知其所以为言”的问题;另一方面尤重点评,力求揭示各篇主旨,且名为选读,实则所论远超篇目所及,体现出对章氏学术体系的贯通性思考。
全书所增篇目主要包括《〈唐书纠谬〉书后》《〈郑学斋记〉书后》两篇学术札记及与邵晋涵论学的书信和家书。两封“书后”乃是彰显章氏与当世学风互动的重要史料。其中,《〈唐书纠谬〉书后》主要着眼于学术批评问题。吴缜治史长于考证,章氏虽与之史学风格不符,却能给出客观公正之论,直言校雠攻辨之书“有功古人而光于后学”。然而吴氏所做这样一项重要工作,却因“指摘”他人而遭受非议,“实学术之大不公,亦人心之大缺陷!”[1]451陈先生此处批语,可谓一语道出章氏心声。《唐书纠谬》一书命运多舛,章氏《文史通义》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在致友人信中写道:“议仆书者多矣,少见多怪,本不足奇,然必待有所见,而后怪之可也。仆属草未成书,未外见一字,而如沸之口已哗议其书之不合,此种悠悠,尚足与之辨乎?”[2]他表彰吴缜的学术,既是出于学术公论,同时亦暗含着对当时极端学风的批评,以及对自身著述为考据学风所淹没的强烈不满。
《〈郑学斋记〉书后》则是以评述郑玄经学成就为例,阐述治学的精神和方法。章氏在肯定戴震“学于郑而不尽由于郑”的严谨学风的同时,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当时学界三种不良学风倾向,即“墨守而愚”“墨守而黠”和“愚心自是”。对此,书中分别作了十分透彻的解读,指出:第一种人“只会拘守前人成说,永远停留于资料的整理纂辑层面,不会作联系分析,不会贯通上下,发现实质性问题,缺乏创造精神”;第二种人只知道背诵前人成果,“作为炫耀自己的资本,装腔作势,藉以吓人,这种人最为可恶,只会败坏学术风气,断送学术进境”;第三种人“习惯于从定义出发,杂取前人的若干言论,不深入钻研,不作逻辑严密思考,就轻率发言,学无根柢,似是而非”[1]470。此三者,实则分别暗指当时烦琐的考据之学、狭隘的章句之学和空洞的义理之学,是乾嘉学风流弊的缩影。章氏撰写《文史通义》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补偏救弊,从理论上阐述古代完整的学术体系。
至于致友人信和家书,亦是了解章氏学术性格、学术志向和学术逻辑不可或缺的一手材料。以《家书二》为例,该篇主要表曝自身的学术取向和学术坚守,其中关于当时汉学风尚问题,所论至为关键:
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1]
从中可见章氏于考据学之真实态度,他从未否认过考据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也从未轻视过当时考据学大家的成就,他反对的只是误以考据为学问之全部的偏颇做法,他本人反其道而为之,也绝非宣告与主流学界决裂,只是发挥义理所长罢了。对此,陈先生在旁批中写道:“对当世考证大家有充分的肯定,对考证学风的泛滥有清醒的分析和抉择,对本人的治学宗旨有充分的自信。”[1]503用排比句的方式,层层递进地道出了章氏对于考据学的辩证认识和自身学术取向的生成问题。
章学诚治学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强调“知人论世”,谓之“文德”,此亦乾嘉学人之共识。今人研读其著述,理应自觉贯彻这一原则。“章氏遗书本”外篇内容,虽非学术专论,但实可与内篇所论相发明,亦是解读章氏思想的重要背景材料,从中可窥见其家学、生平、交游和志向。唯有借助这些材料,才能真正读懂章学诚。这也正是《文史通义选读》以“章氏遗书本”为底本的一个重要考量。
此外,以“章氏遗书本”为底本还有一重要深意,即章氏次子章华绂在编次“大梁本”时,出于审慎的考虑,在篇目顺序上多有改动。如将《浙东学术》这一章氏晚年定论,从《博约》三篇之后移至《书坊刻诗话后》《妇学》等篇之前,从内篇二降至内篇五;又将原本与《浙东学术》并排的《朱陆》篇,从内篇二降至内篇三,置于《习固》《文德》篇之间很不显眼的位置;《说林》篇更是比“章氏遗书本”少了整整七则。不唯如此,而且对于一些重要篇章中的关键语句也多有删改。如《原道》诸篇,两相比较,“章氏遗书本有利于更准确地反映出章学诚的学术见解”[1]102。
至于其余诸篇,虽篇目一同于“大梁本”,但作者在解读时,往往兼及其他相关篇章,集中阐述诸篇在主旨和结构上之关联,故名为选读,实有统摄全书之效。如《博约》上篇,指出可与《答沈枫墀论学》《又答沈枫墀》两封书简结合来读。书简中所倡“学欲其博,守欲其约”的治学要领,以及对学术研究必经的“博览”“习试”“旁通”“专精”诸阶段的梳理,在观点上“足与《博约》篇互相发明”。[1]137-138又如《说林》篇,“与《文史通义》各篇互相阐发之处甚多”,开篇提出的“道学公私”的命题,即与《原道》《原学》诸篇主旨相呼应;第三十四则中对“学古”与“古学”的区分,第四十八则中“所以持世者,存乎识”的观点,则是对《博约》中篇有关“学问”与“功力”关系认识的“有力回应和补充”;第二十七则中“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的看法,则与《书教》下篇中“神奇”与“臭腐”辩证关系之论,以及“师《尚书》之意,……救纪传之极弊”的主张“前后呼应”。[1]292-293《答客问》三篇,则上承《申郑》篇,“是对《申郑》篇论点的进一步阐发”。[1]363《〈郑学斋记〉书后》中对戴震“学于郑而不尽由于郑”的学术态度的肯定,则与《书〈朱陆〉篇后》中对戴震《原善》诸篇的推崇,“所言完全一致”。[1]471凡此,都体现出作者对《文史通义》全书著述体系的宏观性把握和贯通性思考,有助于读者在体察章氏撰述思路的同时,对全书作有针对性的专题式研读。
二、以清学史和史学史的双重视角揭示章氏思想的特点和生成
章学诚治学长于言理,此亦《文史通义》最显著之特点,所以注解该书,不能局限于文意的疏通,思想的解读更为关键,这就需要有清学史和史学史的双重学术背景,而此二者恰为陈先生极擅长之领域,故在解析章氏思想方面,往往游刃有余。
如《家书五》,主要阐发关于宋明理学的态度问题,乃是了解章学诚学术旨趣十分重要的材料。文章开篇写道:
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然风气之盛,则村荒学究皆可抵掌而升讲席;风气之衰,虽朱、程大贤犹见议于末学矣。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1]
此论旨在通过分析理学的盛衰流变,提醒时人应理性看待不同的学风和流派。乾嘉时期,理学虽整体衰颓,但在思维方法和立身处世方面仍有借鉴意义,而这正是当时学界所亟缺者。对此,不唯章氏大声疾呼,汉学家中的有识之士亦有觉醒,段玉裁晚年的学术反思即与章氏所论颇相契合:“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3]段氏所描绘的这一情景,正是章学诚撰写此封家书的主要学术背景。对此,陈先生格外点出“宋学太不讲”一句,认为乃全文精华之所在,尽显“章氏见识之不凡,目光之深远”[1]520。可谓一语切中章氏立论的核心旨趣。
关于章氏的理学观,书中亦作了精当概括:一是“肯定理学是儒学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二是“虽然理学在今日已经颓波不可复返,甚至被通儒公开耻笑,但有识之士不能为这种风气所左右,而应该对其价值有清醒的估计。……理学家讲理在事外当然错误,但研究任何事物,都不能不重视‘理’”。三是“承认理学的价值,不能是不加分析地‘维持宋学’,而是应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忌凿空立说”。四是后学者应善于从理学家之言论中摘其精华,不惟有益身心,亦可为行文之助。[1]524此四条阐释,集中体现出作者深厚的清学史尤其是理学史素养,不唯有助于理解章氏学术思维特点的生成问题,且能够进一步启发读者对乾嘉时期理学发展状况和汉、宋学术关系问题的思考。章氏在学术上的成功,根本上源于他对宋明理学思维的批判性继承。反观同时代的许多汉学家,虽大多主张兼习宋学,但他们对宋学的理解和接受仅限于制行之学,对其方法论上的那套思辨哲学则尽加排斥,说到底是一种“假宋学”,至少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宋学,这与章氏所理解的“维持宋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又如《书教》下篇,章氏集中论及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对此,陈先生在旁批中指出:“至明清时期,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上多被采用。实践向前发展了,理论工作却滞后。章氏对纪事本末体优点的概括,正为时代所迫切需要。”[1]49此论同样言简意赅,暗含深意,如果不是对明清史学的演进有着深刻的洞察,很难得出如此具有理论高度的认识。
作为一种晚出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在南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用于对旧史的改编,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发展,直至明清之际始在编纂模式上逐渐实现从“钞史”到“著史”的转变,不仅广泛用于当代史的撰述和对旧史的改造,而且在体例上亦有新的变化。如《明季南北略》记述人物、事件、时文、奏议等,皆独立成篇,这与章学诚“因事命篇”,以各种类型的“传”囊括历史全部内容的设想,颇有相通之处,近于一种近代意义上的“专史”写法。或许计六奇本人并未在编纂体例上苦心经营,他采取这种比较灵活的历史专篇的写法可能主要受限于史料本身,但却折射出纪事本末体普遍为史家所重这一客观事实,以至于梁启超也对其书大加赞赏,认为“用纪事本末体组织颇善”[4]。以上所论,即是旁批中所言明清时期纪事本末体在编纂学上多被采用的情况。
历史编纂学实践既源于史家思想认识上的突破,也会推动历史编纂学理论的发展。明清学者对纪事本末体的重视在编纂思想层面亦有体现。如谷应泰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概括为“首尾毕具,分部就班”,较之编年体“包举而该浃”,较之纪传体“简练而隐括”[5]谷应泰序。此论堪称章学诚“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之说的思想前驱。傅以渐亦指出,由于编年、纪传二体在纪事方面都存在天然缺陷,“一事而散漫百年之中,一事而纵横数人之手”,要改变这一困境,“断非纪事不为功”[5]傅以渐序,揭示出传统历史编纂学格局从“二体争先”到“史体三分”的历史必然性。这些认识不可不谓重要,甚至可视作章学诚史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思想来源,但由于多散见于史书序跋中,并非史学专论,更难称理论自觉,故而影响终究有限。此即旁批中所言历史编纂理论远远滞后于实践的问题。这句话虽点到为止,但暗含着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纪事本末体发展源流和明清历史编纂学演进历程的深刻认识,也唯有基于这样一种贯通的学术视角,才能真正揭示出章学诚思想的独特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这类言简意赅的旁批,对于解读章氏思想甚为关键,因其往往在篇章关键处立论,高度概括,直击要害。周作人在谈及郝懿行的《宋琐语》一书时,即对书中简短之评注赞不绝口,直言“舌短之注,看似寻常,却于此中可以见到多少常识与机智,正是大不易及”[6]。今读陈先生之旁批,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研究尤其是史学史研究最强调“通”,研究时段越往后,往往“通”的难度越大。章氏思想不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且是对两千年古代史学乃至古代学术传统的总结,阐发难度极大。陈先生的解读在这方面颇具启发意义,为我们历史地、长时段地审视章氏的学说体系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和方法。
三、从方法论的高度总结章氏治学经验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除了文本和思想价值,还在于具有方法论层面的范式意义。唯有对古人治学的经验予以总结和发扬,才能不断创造出新的经典,这也是弘扬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任务。我们今天审视章学诚的学问,不能局限于《文史通义》中的具体观点和主张,还应从中总结其一生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体察其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此亦新注本的又一显著特色,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丛书编纂的宗旨之一。
其一,敢于立言的学术勇气和责任担当。强调学贵独创,既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一项优良传统,也是清代浙东学派的显著特点。然而,有没有见识是一回事,敢不敢于表曝见识又是一回事,而章氏在这方面堪为表率。对此,书中作了许多细致入微的解读。
如《原道》上篇,针对章氏提出的“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的观点,在旁批中写道:“石破天惊之伟论!破除千百年来视六经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圣人神秘莫测一类根深蒂固的迂见。”[1]78篇末评语进一步阐述道:“当时主流学术界几乎无人理解其价值,邵晋涵与章氏交往多年,他坦言连章学诚的朋友中的人士都对《原道》篇的内容不满,认为‘陈腐取憎’,题目太熟,没有新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至有移书相规诫者’。大家都跟着风气跑,章氏却具有自觉的意识,敢于顶着压力,进行真理性的探索。”并举出章氏次子章华绂刊刻“大梁本”时,出于忌讳删改《原道》篇关键语句的例子,“由此更可明白章学诚著书时具有何等的理论勇气”![1]88-89
又如《原道》中篇,章氏有如下论述:
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1]
陈先生指出,此处“非如”一词乃“不像”之意,前后对比的色彩极其鲜明,尤能彰显章氏立论的勇气,集中体现出对后世将“道”神秘化、凝固化做法的不解和不满。然而“大梁本顾忌这种观点会遭到世俗人士的非难,因此将‘非如’径改为‘不如’,意为‘比不上’。如此一改,便与章氏原意相反了。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1]102。这一解读,尤为精审,不唯破除了读者的阅读障碍,而且一语道出“非如”一词所用之妙处,尽显章氏“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本色。
其二,强烈的现实关怀。注重理论建构是章氏学术的最大特点,他继承并发展了程朱理学读书穷理的宗旨和思辨逻辑,同时又以义理的玄虚化为戒,大力倡言“借事言理”的学术逻辑。可以说,在理学思维与史学思想的结合上,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他是古代学者中做得最好的。对此,陈先生总结道:“理论应当有的放矢,理论应当体现对现实的关怀,而不能只评论往事,发思古之幽情,章学诚正是这样做,最后归结到对当代不良学术风尚的针砭。”[1]365
如《答客问》上篇末再次论及道器关系、经史关系等诸多宏观理论问题: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1]
此处全是理学家的行文风格,无论是“即器明道”,还是“六经皆史”,都是看似深奥艰涩的义理性论述,实则暗含着对当时学风流弊的深刻反思。章氏围绕“器”“文”“道”三者关系,对当时学界的三种偏颇学风分别作了有力针砭,强调如果一味泥于文辞雕饰和训诂考据,其弊不减于理学空谈,意在暗讽当时学风已然走向了与宋明理学时代完全相反的又一极端。对此,陈先生指出:章氏此论,乃是针对烦琐考证、夸耀文辞和性理空谈三种不良学风倾向而发,目的是“要为学术研究开出一条新路”,这在当时是很迫切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出于谨慎,他并未具体展开来谈,只是从古代学术体系和学术逻辑上立论,但却“很具批判锋芒,而又表达巧妙”。[1]365
又如《文德》篇,主要论述历史主义的认识论问题,虽通篇无一字言及乾嘉学术,但所论无不与乾嘉学术有关,尤其是结尾处“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正是暗讽当时无识文人,批评他们只会苛求古人,不解古人立言的背景和处境,就妄下结论,实则远不及古人矣。对此,陈先生评论曰:“他著述的态度极其认真,凡撰文必有的放矢,……他大力阐发‘临文必敬’‘论古必恕’这两大原则,也是为了矫正时弊而大力倡言之。”[1]199可谓一语道出章氏理论探索的现实用意。
其三,突出的辩证思维。章学诚作为理论家还有一显著特点,即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古今学术的流变,逻辑缜密,析理透彻,绝不拘于门户之见,更杜绝一切意气之论。对此,陈先生总结道:“章氏在辩证思维方面有极高的智慧,他从总结学术史演变和本人治学的体会,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社会风尚、学术流别、治学得失,都运用了辩证观点进行评析,这是其学术思想能自立为一家、《文史通义》能够成为文化经典的深刻内涵和保证。”[1]295通观全书,小至旁批,大到导读和评语,都蕴含着对章氏这一重要学术思维的精当分析。
如《朱陆》篇,乃章氏理学观的缩影,他在肯定朱熹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数传弟子皆能秉承其治学方法,做到“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至于后世“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乃是对朱学精神的背离,须严格予以区分。这实际上是从学术史演变的视角,以辩证的眼光廓清了南宋以来理学发展的阶段性和流派问题。对于章氏的这一辩证认识,书中总结道:“其时理学之颓势早成定局,甚至在社会上受到公开的嘲笑,章学诚却能中肯地总结出朱子学派具有‘求一贯于多学而识’、治学缜密等优胜之处,确实显示出其总结学术史所具有的特识。再联系到章氏自视为清代浙东学派的继承者,这一学派的源头王阳明、刘宗周属于陆王学派,以此可证明章氏确能摆脱门户之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学者的得失。”[1]188-189也就是说,章氏此论不唯跳出了汉学思维的局限,也超越了自身学术渊源与流派的限制,在当时绝大多数学者仅将理学视作修身之学,将理学家仅仅视作“师”而非“儒”的情况下,章氏却敢公开承认其方法论上的合理性,尽显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理性辩证的学术思维。
章学诚不仅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宋明理学,对于当世风靡的汉学亦能理性看待。如《答客问》中篇,章氏旗帜鲜明地提出“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交相为用的重要命题,陈先生认为“讲得实在精彩,……这一至理名言,实是章学诚总结学术史的经验而得,也是对当时自立门户的不良倾向提出切中要害的忠告”。对于章氏有关“比次之书”价值的辩证认识,书中亦作了精当评述。章氏一方面强调这是学问研究的必经阶段,同时又告诫学者不可满足于此。陈先生强调指出,章学诚所说的“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只是为了说明学问研究的不同阶段,绝无高下之分,所谓“愚”的本意是“需要老实巴交下苦功夫,把原始资料实实在在整理好”,但不能将其视作学问的终点或全部,否则不仅不能达到“登诸著作之堂”的目的,“而且恰恰会失去为后人提供原始资料的价值”。[1]378-380
总之,章氏长于辩证分析,与其本人注重学术史考察的治学风格有关,同时也与乾嘉时代“实事求是”的整体学风相契合。虽然章氏学术取向不为考据学家所认可,但在“唯求其是”的问题上,他们并无本质不同,只不过,后者主要着眼于事实和文本之真,章氏则旨在探索思想认识之真。
结语
以上所论三项,主要基于全书在研究思路、视角和方法上的考量,不唯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章学诚的思想大有裨益,对于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其他重要思想家也同样适用。唯稍有遗憾者,限于篇幅和精力,选读篇目有限,将来如能进一步通释全书,那既是学界之幸,亦是实斋之幸。
另,思想史的研究向来难度极大,尤其是对于实斋这样极具思辨性和哲理性的天才史学家而言。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在完成《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一书后不无感慨地说:“他既是独立性的旗帜,也是正统性的旗帜,他仍然难以捉摸。”[7]这是实斋的学术魅力,也是思想史的独特魅力。窃以为,关于《文史通义》的研究,至少还可以再尝试作如下探索。
一是章学诚的学术影响和《文史通义》的传播问题。现代学界普遍认为章氏跻身一流学者行列乃是民国初年以后事,但这并不意味着章氏学术在整个清代中后期都处于寂寂无闻的状态,相反,在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如焦循、阮元、段玉裁、邵晋涵、钱泳、朱锡庚等,都与章氏有着密切的学术交集,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和传抄着他的作品,甚至有将其视作当世马、班者。只不过,碍于当时的学术环境,他们评述章氏学术的方式较隐讳,接受程度有限罢了。或许是受章氏书中各种愤世嫉俗、怀才不遇之论的影响,抑或是受传统的“汉宋之争”的学术思维的干扰,加之受乾嘉时期《文史通义》阅读史方面的材料的限制,导致我们今天的许多认识,无形中放大了乾嘉学人尤其是考据学家与章学诚之间的学术距离。从这一意义上讲,从阅读史、接受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实斋的思想流布和乾嘉学术的真实生态,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是《文史通义》的性质和篇目问题。由于此书在章氏生前并未全部刊印,章氏本人也未审定全书目录,以至于目前关于该书的真实篇目问题,仍悬而未决。从目前新发现的一些史料来看,乾嘉时期即存在将章氏所作本朝人物传记视作《文史通义》内容的情况,由于章氏生前作品散出较多,可能存在时人疏于区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这类最能体现章氏修史理念的史传作品,原本即在章氏构撰《文史通义》的框架之中,他对该书的定义,很可能近于一种类似先秦诸子之学的自成体系的一家之学。这样来看,无论是“大梁本”,还是“章氏遗书本”,只收录其各类文章,可能已经违背或是割裂了章氏的学术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