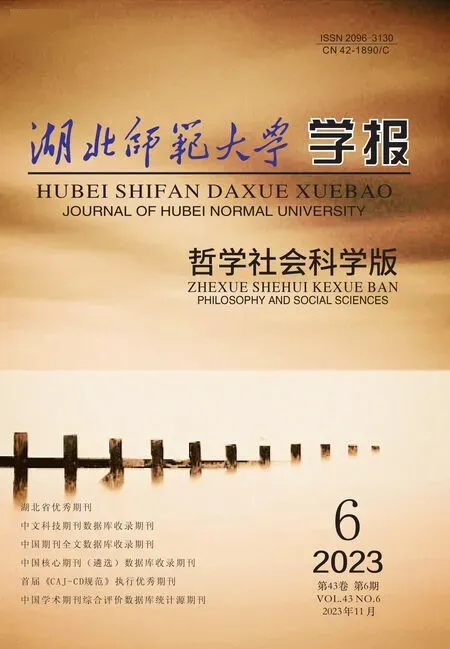文章翻译学的若干问题及其语言学理据
丰国欣
(湖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兴起了一些由中国学者提出的翻译理论,它们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解释翻译的本质,指导翻译实践,并基本摆脱了翻译理论研究跟着西方译论转的局面,丰富了中国译论研究的内容,渐渐形成了中国译论研究框架和体系。本文推崇著名语言学家、资深翻译家潘文国教授创立的文章翻译学[1]~[12],梳理该理论体系的若干问题,论述其语言学理据,揭示其中国特色。
鉴于很多自创的翻译理论声称具有中国特色,所以本文的梳理和论述过程也是对这种认识的冷静思考。我们认为,具有创立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意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种翻译理论是否具有中国特色、是否更适合指导中国的翻译实践,则需要认真思考、讨论、选择:其标准和依据是什么?
二、文章翻译学及其中国特色
(一)关于文章学
文章翻译学,顾名思义,是文章学和翻译学的结合,所以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文章学。中国传统文章学在国家治理、百姓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曹丕在《典论》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3]曹丕把文章的撰写抬高到了极致,提醒人们写文章要用心,因为文章是治理国家的重大事业,是流传万代的不朽之事。
中国传统文章学有着独特的内涵,与西方的篇章学、写作学、语法学、修辞学、风格学、文体学、文艺学等等都有相似之处,但又不等于其中任何一种,它融通文字学、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修辞学、语体学、文体学、风格学、信息学、美学、符号学等众多学科的机理,有一种全息观、全局观,体现了汉语的整体思维特点。它发轫于先秦,成型于两汉的训诂章句之学和六朝的辞章声律之学,充实于隋唐的注疏之学和宋元的圈点之学,完成于明清的评注之学,这就构成了“以文治文”的传统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章学的内容包含六部分:第一、句读之学:根据意思来断句,在不同处点断的学问;第二、章句之学:这是分章析段的研究,可包括章句之学、科判之学和义疏之学;第三、语助之学:指汉语虚词研究,应该属于篇章学而不是句法学;第四、文体之学:传统的“文体”有两个意思,一个相当于现代所说的“体裁”,另一个相当于现代所说的“风格”;第五、文式之学:“文式”指文章法式,或者特定体裁文章(语篇)在形式上的具体要求;第六、文法之学:它不同于西方的Grammar,讲的是作文之法,是古人篇章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丰富程度远远超过西方的语篇分析,可细分成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等等。
中国传统文章学与翻译学的关系十分紧密,人们常常在其照应下做翻译,做翻译就是做文章。
(二)关于文章翻译学
文章翻译学是“文章学翻译学”的简称,英语里没有对应的或者十分贴切的表示方法,只好将就地翻译成“compositional translatology”,其目的是为中国典籍翻译量身打造,主张做翻译就是做文章,例如,林语堂就有这样的翻译主张和理念,这才有他的“创译一体”[15]的翻译方法。
自潘文国创立文章翻译学以来,该理论发展了近20年,体系不断完善,内涵不断丰富,其主要观点[11],[16]~[18]可以梳理、概括如下:
1.“道”“器”结合
我们先考察文章翻译学的“道”。
文章翻译学把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19]作为自己所主张的“道”,这既是构建译论的需要,也是澄清长期误解严复“信、达、雅”的举措。
在较长的时间里,人们对严复“信、达、雅”的理解存在各种误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第一、误认为“信、达、雅”源于Tytler的翻译三原则①[20],认为Tytler是原文中心论,而严复是译文中心论,其实这是某些人的想象;第二、误认为“信、达、雅”是译文的标准或要求;第三、误认为“雅”和“信”相冲突,太“雅”就失“信”;第四、批评严复本人也做不到“信、达、雅”,因为严复的翻译过于“雅”,这就没有“信”了;第五、很多翻译研究者修改“信、达、雅”,把它换成不同措辞,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很多教材都在曲解“信、达、雅”。
其实要弄清楚严复“信、达、雅”的含义很简单,把他的原文找来分析便是。在《天演论译例言》[19]里,严复引用了三条古人语录来证明他的主张:“《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所以“信、达、雅”真正的含义是sincerity、 communicability和norm[19],本是文章学的主张,也可以当作翻译的楷模。
从《易· 乾》里那句话可以看出,“信”其实指的是对读者的诚信,而不是对原文作者的忠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严复首先想到的是译者的道德责任,对原作者的忠实顶多是附带的意思,是“副产品”。“达”首先涉及的是意义,而不是语言,理由有二:一是在严复引用孔子的那句话中,“达”也是指意义的传达,二是严复把自己的翻译方法称作“达旨”,也是这个意思;“达”指语言的通达也是副产品。所以用communicability表示“达”最接近严复的意思,其他的表达法,如intelligibility、 readability、 clarity和comprehensibility等都不贴切。严复主张的“雅”,实际上是采用一种通用的、正式的、标准的、成熟的语言来从事翻译,只有用这样的语言才便于“达”。这个理解从严复的原文中可以看出:“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可见,“雅”是“尔雅”的缩略。“尔雅”在现代汉语里不大使用,在古汉语里,“尔”义为“近”,“雅”义为“正”,而不是“文雅”(和“高雅”“典雅”等词中的“雅”不同),“尔雅”即“近于正”,就是“接近正规、标准、规范等”的意义。这个意义的“雅”与“言”组成“雅言”,孔子在《论语》里用过,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标准语”“通语”“普通话”的意思。因此,严复主张的“雅”其实就是采用一种通用的、正式的、标准的、成熟的语言来从事翻译,因为只有这样的语言才便于“达”[19]。
可见,“信、达、雅”并不是指原文、译文和语言风格,而是指道德标准(信)、内容标准(达)和语言标准(雅)。严复进一步阐述了“信、达、雅”之间的关系,关于“信”和“达”,严复说,“顾信矣不大,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关于“达”与“雅”的关系,他说:“……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把严复这些论述联系起来,就可以看清“信、达、雅”是翻译连贯又分层级的标准体系:“信”是基本标准,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信”只有通过(正确)“传达意义”才能表现出来,这是进一步的标准;为了传达意义,最简便的办法就是采用“雅言”或标准语,这是最高的标准。这样分析,“雅”在严复理论中占据中心地位,只有“雅”才是到达“达”的最好途径;而“达”是达到“信”的唯一方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信、达、雅”中,“雅”是核心,否定“雅”实际就否定了严复的全部体系[19]。
总之,以严复为代表的传统中国译学与以“忠实”为核心的西方译学走的是两条路:西方译论建立在西方语言学基础上,要求译文“忠实、通顺”,走的是一条技术主义的路线;而中国译论建立在传统文章学的基础上,强调为人先于为文,走的是一条人文主义的道路;“信、达、雅”其实就是“德、学、才”[19]。
我们再考察文章翻译学的“器”。
与“译事三难信达雅”相对应,潘文国提出“译文三合义体气”[8][9],作为文章翻译学的“器”,“义、体、气”是“信、达、雅”的操作层面,是翻译过程中可操作的手法。这里的“合”是“相合、对应、匹配”的意思,即译文和原文要在三个方面做到相合:“义合、体合、气合。”从译者角度看,“三合”是操作手法,是“译而使之合”,也可称作“三传”:“传义、传体、传气。”从读者角度看,“三合”是批评标准,是“验其是否合”,也可称“三品”:“品义、品体、品气。”“三合”有高低之分,“义合”是最低要求,“体合”其次,“气合”则是高要求,也是努力目标[8][9]。
“义合”要求译文和原文在字、辞、句、篇各方面的意义必须结合。这里说的是“义”而不是“意”,强调客观意义,而不是主观意义;“义”包含辞义、组织义、系统义;“合”并不是指逐字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而是“对应(correspondence)、匹配(match)”。“体合”好像量体裁衣,要合身。如果说“义合”是内容,则“体合”就是形式,从中文的传统看,即便是非文学的文章也要讲形式,也要讲艺术;中国古代文章分类虽然繁复,但从语言要素来看,主要有四大要素:韵、对、言、声,掌握这些要素,表现这些要素,就可以做到了“体合”。“气合”中的“气”就是生理之气,体现在中国文章学中就是音节的调配和句子长短的安排,并不是西方人想象的那么神秘不测;三者关系:过分强调“义合”可能造成“死”的结果,死扣字眼,过于强调“体合”可能造成“板”的结果,不知变通,为了避免“死”“板”,就需要“气合”来穿插,以追求灵动的翻译效果[8][9]。
2.人品与文品,为人先于为学
中国文章学自始至终将文品和人品联系在一起,为人先于为学;所谓“道德文章”,是先有道德,而后才有文章;严复的“信”出自《易经》的“修辞立其诚”,“诚”指的就是人品;因此文章翻译学就要找回“为人先于为学”的优秀传统,做到“为人先于为译”,才谈得上做好具体的翻译工作[11]。
3.不区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
传统的“文章”包罗万象,从经书到诗词韵文再到各种实际应用文字,因此传统译论讨论的对象并不限于文学翻译,甚至主要不是文学翻译。由于对“信、达、雅”的误解,以为“雅”只有文学翻译才要[11]。
4.重文采
文章翻译学不区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但又同时适应文学和非文学翻译,秘密何在?就在于从文章学的角度看,一切文章都要讲文采。《文心雕龙·情采》[21]所谓“圣贤辞书,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就是说文采是所有文章的自然要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那么“言而有文”就成了文章学的追求,“信、达、雅”的“雅”是针对所有文章而言的,不管是作的,还是译的[11]。
5.重“气”
曹丕在《典论·论文》[13]说“文以气为主”,后来成为历代文章家追求的目标。“气”并不复杂,与韩语[22]所说的“言之长短”“声之高下”有关,清代刘大櫆[23]说得更加清楚,“气”就是音节字句,“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
本节梳理并阐述了文章翻译学的若干问题,这个过程揭示了其用途,即为典籍外译量身打造;由于典籍都是美文,所以也适用于美文中译;同时还适用于一般翻译。梳理和阐述本身也是展示文章翻译学的中国特色的过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章翻译学源于中国历史文化,指向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汉语言和中国文化特色,因此是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下节我们讨论文章翻译学的语言学理据,这既是从语言学角度论述文章翻译学的合理性,又是从语言学角度进一步揭示文章翻译学的中国特色。
三、文章翻译学的语言学理据
所谓“文章翻译学的语言学理据”,就是考察文章翻译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上文系统梳理了文章翻译学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阐述理据的过程,包括阐述了其语言学理据。上述内容说明,文章翻译学产生于中国语言文化,以中国语言文化为学术资源,解决中国翻译问题,特别是典籍翻译问题。如上文所言,这不仅可以从语言学角度说明文章翻译学的合理性,而且还可以揭示文章翻译学的中国特色。不管是哪一种翻译理论,归根到底都是要实现语码转换的,所以有必要把语言理据单独提出来分析一下。
谈到理据,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纯理论问题,但实际上,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一个操作问题。中国的文章翻译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这个译论和汉语之间存在一致性。这是我们分析、评判文章翻译学合理性的标准,是一种内部评判方式。
我们曾论述过汉语“字”和英语“语素”之间的关系[24],认为两者性质不同,各自构成自己的“词”。推理下来,构成成分不同,势必导致汉语“词”和英语(印欧语)“词”的性质也不同。既然如此,这两种“词”有什么区别?“字”究竟构成的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文心雕龙·章句》中的一段话:“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21]
诚然,这里说的是文章学的道理:从形式上体现出汉语顶真修辞之妙,但也明显揭示了语言结构:字—句—章—篇、篇—章—句—字,反映了汉语结构的层级和互动原理,以及“字”的作用机制。只要是文章,无论是原文,还是译文,都遵守这个规律:文章的展开是建立在语言结构之上。
西方系统语法认为,语言是由“语素——词——短语——小句——句子”组成。因此,语素构成的是词。不过,词确实是印欧语之中的语言实体,而语素则是语言学家为了分析词这个实体而切分出来的,并不是天然的,所以用语素分析印欧语的内部结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困难。例如,“数”范畴在词的内部结构中常常用一个语素表示,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像books就是两个语素组成,其中“-s”是表示“数”范畴的语素;可是men、feet就没办法分析了,它们明显也包含了“数”范畴,但没办法通过一个语素体现出来,有人认为这是古英语里留下的中缀痕迹,但即便是这样,也无法把men和feet分析成两个语素,所以语素分析解释不了这类现象。再如“-ceive”,由于意义不清晰,既非前缀,又非后缀,一般词汇学教材上都称之为“粘着词干”,这是让人捉摸不透的术语,与词干的定义不一致。尽管如此,人们基本没有对“语素构词”这个认识进行质疑。
印欧语这个观念影响着汉语研究,引导人们分析汉语词的语素。曾经在较长的时间里,对汉语结构的层级分析偏离了汉语传统,套用“语素——词——短语——小句——句子”模式,结果问题重重。以字本位理论[25]~[31]流派为主体的学者极力主张回归文章学传统,以字为基础单位,探索汉语的各种问题。我们已经就汉语里的“字”和印欧语里的“语素”的异质性有了统一的认识,既然两者性质不同,那么两者构成的语言实体也不同。如此说来,“字”既然不是语素,它构成的语言实体也就不是“词”了。
那么,汉语里“字”究竟构成的是什么?
徐通锵[26]把语言单位分为“字、辞、块、读、句”五级,汪平[27]把语言单位分为“字、辞、读、句子”四级,程雨民[28]认为“字”是语素,不承认汉语有“词”这一级,把语言单位分为“字(语素)、字组、短语、句子”四级。而潘文国[29]则把语言单位分为“字、辞、读、句、篇”五级,并以此构建了汉语章句学,并形成章句学的精髓。
与其他几位学者不同的是,潘文国设置了“辞”这一级,其含义是:“介乎音节词(即字)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29]
这种设置和《文心雕龙》的精神是一致的,更贴近文章学的含义,和汉语的语义性质是一致的。这种“由字构辞”[30]为基础的层级设置,我们更愿意接受,理由分述如下:
第一,这种层级模式中设置了“篇”这一级,这是与其他学者最大不同的地方,正是这一点:“我们完全突破了20世纪以来认为‘语法’即‘句法’的框框,而把它扩大到语篇的范围。”[31]
在西方语法传统之中,句子是最大的单位,之所以“篇”不在其中,是因为“篇”是语义性质的,而语素、词、短语、小句和句子是结构单位,是语言形式,“篇”和它们之间是“体现”关系,只要能够体现一个语义整体就是一个“篇”。但汉语就不同了,同印欧语相比,字本位认为汉语是语义型的语言,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形态,无法形成形式语法,它的语法是语义性质的,因此在语法层级设置中可以加进“篇”这一级,“篇”和其他四级“字、辞、读、句”是相同性质的。很多语言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如屈承熹指出:“句法和篇章有许多交叉之点;如果只关注一方面,而不适当考虑另一方面,则问题至多只能解决一部分。我们不敢说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却觉得已经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向。”[32]
在屈先生看来,必须在“篇”之中,汉语语法才可以构建。其实,对语义型语言来说,句法和篇章不仅仅是“交叉”的问题,而是同质的,即“篇”在汉语中与“字、辞、读、句”都是语义性质的,但是在印欧语里“篇”与“语素、词、短语、小句、句子”性质不同,前者是语义单位,后者是结构单位。这样构建汉语的“层级”,让汉语摆脱了印欧语观念,回归到了自己的传统,正视了汉语的基本事实,具体体现了“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21]的原理。
第二,其实,汉语不仅“因字而生句”,而且“因字而生辞”。“字、辞、读、句、篇”五级设置,既揭示了汉语语义本质,又为研究“字”所构成的语言实体的性质明确了方向,形成“由字构辞”[30]论。这就从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文章学和文章翻译学的合理性。
第三,这种设置,为翻译英汉复杂句时必须改变源语言句子结构找到了理论依据。英译汉时,要把英语的树式结构翻译成汉语的竹式结构;汉译英时,要注意凝练汉语复杂句中各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逻辑关系,翻译成英语的树式结构。
汉语和印欧语性质不同,“词”“辞”当然是不同的,但两者之间是可以产生联系的:“辞”包含着印欧语里的“词”和“短语”。设置汉语的“辞”这一级语言单位,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了“词”和“短语(词组)”划界的难题。这个问题或许在印欧语里依然存在,但在汉语里设置“辞”这个单位就使得这个难题不存在了,因为“词”和“短语(词组)”不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了,而是被“辞”所包含,两者都是“辞”。潘文国先生说得更加具体:“把‘词’扩大到‘辞’,这是为了给困扰现代汉语多年的词和短语难以划界问题找一条出路:既然词与短语在理论上如此难以划清,而按现代语法学家的研究,汉语中词与短语在结构上又无很大不同,那为什么不能换一个思路呢?这就是根本不去追求勉强将它们划清,在一般情况下将它们统称为‘辞’,不区分是词还是短语,只有在特殊需要的时候才给不同的称呼。”[31]
第四,由字构辞,相对印欧语的“语素构词”来说,绝对不是仅仅换一个名称,而是形成了汉语自身的分析系统,这是因为最基本的单位往往驾驭整个语言系统。正如徐通锵指出的:“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系统,而语言基本单位则是这种复杂系统的核心,处于枢纽地位上。要认识语言的结构脉络,就必须紧紧抓住它的基本单位。……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基本单位有两个,即词和句子,而汉语只有一个,这就是字。”[33]潘文国先生几乎同时指出:“‘字’是汉语各个平面研究的交汇点……在语法上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是‘字法’与‘句法’的交接点……。”[29]
两位语言学家道出了同一个道理:“由字构辞”的原理是汉语整个系统运作的机制,进而向上位语言单位扩展,形成语义运作的逻辑线路。这也是表达机制,翻译就是表达的一种方式。
“由字构辞”对文章翻译学及其研究的启示。
第一,“由字构辞”,奠定了“字、辞、读、句、篇”五级汉语单位的基础,成为汉语各个层面得以实现的深层机制,确定了汉语语言统一性。这是翻译学构建的基础,假如翻译学的构建不考虑具体语言规则,那么所形成的所谓体系就不具备学理性,也就没有合理性了。文章翻译学恰好就是以这个语言学原理为基础的。
第二,“由字构辞”原理更能说明汉语“词”“短语(词组)”和“句子”同形同质的原由,如“地震”“天亮”在现代汉语里既可以理解为“词”,又可以理解为“短语(词组)”,还可以理解为“句子”,这是因为它们都是通过“由字构辞”原理组成的“辞”。这一原理在翻译实践中可以成为具体的操作方法。
第三,“由字构辞”不仅是汉语的构辞原理,而且是汉语的编码基础,是文章学和文章翻译学存在的基石。在语言学基础理论中树立“由字构辞”的观念,不仅澄清了汉语里“字”和“语素”的纠缠,而且也揭示了“语素”在印欧语里的不足之处。“字”在汉语里是现成的、天然的,而“语素”在印欧语里是人为的,是语言学家为了分析词的内部结构而设立的。所以在汉语里用“字”分析“辞”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可是在印欧语里用“语素”分析“词”却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在汉语里张冠李戴地把“语素”用来分析汉语的“词”和“辞”了。文章学和文章翻译学的构建如果不关注语言自身的这些规律,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述文章翻译学的理据,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可以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本文仅从“由字构辞”原理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其他角度将另外行文进行论述。
四、结论
我们论述了“由字构辞”的合理性和理论意义,探索汉语“由字构辞”的规律,揭示了汉语研究中从“词”到“辞”的本质。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来看,用“辞”指代音节词和句子之间的那级语言实体,更加符合汉语自身的规律。“由字构辞”作为汉语的构辞原理,不仅是汉语构辞研究的成果,而且具体解释了传统文章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一个规律:文章学、汉语语言学、文章翻译学在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它们源于同一个理念,指向同一个目标。这就是文章翻译学的语言学理据。
鉴别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不能以提出者是中国人在中国提出为标准和依据,而应该甄别一种翻译理论的“基因”是否是中国的,即更看重在中国文化、历史中渐渐形成的、并以中国文化、历史为学术资源的、旨在解决中国的翻译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化外译的翻译问题。当然中国特色翻译形成后,不排斥其具有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愿推崇文章翻译学,进一步探究其合理性。当然,这绝非有否定其他理论合理性的意思。
注释:
①18世纪末叶,爱丁堡大学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三原则:1)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翻译应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2)That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翻译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3)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译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自然)。
——针对对外汉语语素教学构想